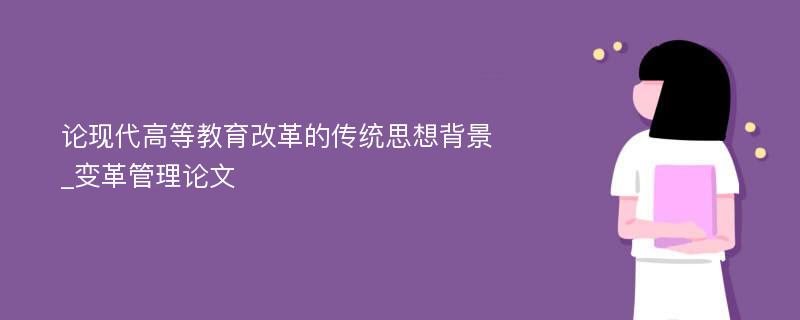
论近代高等教育变革的传统思想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近代论文,背景论文,传统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03)03-0052-04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基于什么样的思想背景?艾尔曼认为,“在19世纪中期西方的影响还未全面到来之前,中国知识阶层对作为思想与学术正统的传统儒学经典的批判,已经在18世纪达到高潮。他们通过语言、数学、天文、地理、金石实证性研究,重新审视儒学遗产诸多理论的合理性,并经由史学化,使其变成了寻常的史学研究对象和材料。”[1]不少学者也试图证实,在近代之前,在传统社会内部已经孕育了可以接纳一个全新的社会谱系的内在理路,如明末开始在江南地带出现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西方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在明清之际的传播,清代朴学中业已孕育了近代科学赖以发展的实证精神等因素,中国因此具备了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可能,只是西方的入侵打断了这一自然进程,导致了鸦片战争后在与西方的激烈冲突中的被迫变革。这都促使我们去郑重地思考,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是以什么样的思想背景实现变革的。
一、儒学地域化与晚清社会变革
在梁启超及其追随者和目前多数奉信进步主义的研究者看来,自1840年至1949年的近代中国,是沿着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这样的核心事件,由器物向制度再向思想逐步过渡的整体性回应路径展开的。这很容易让人获得这样的认识,即近代中国历史存在一个非此即彼式的线性变迁结构,而且后继的运动总是以否定前一运动的话语预设为前提的。历史的真相是否真是如此?在杨念群看来,近代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从整体上对西方做出回应的机制,作为对中国社会发展提出构想并付诸实践的主体力量,近代知识精英面对西方入侵而做出的变革回应,是分别来自传统内部的三种地域化儒学话语——湖湘学派、岭南学派和江浙学派——相继占据主导位置,并以传统的而不是西方的思想理路来设计变革方式的过程。虽然确实存在着一个对西学有所选择的回应频率和节奏,但其发生的真实序列并非如梁启超所描述的那样是纯粹时间性的,而是不平衡的空间交错的态势,也不应是否定论式的联系,每一次运动的话语阐释实际也应该包涵着前一层面的合理因素。而之所以出现三种不同的知识群体逐次占据时代的主导话语并引致变革,就在于宋以后儒学民间化带来的儒学地域化,打破了官方化儒学形态的单一控制网络,并在不同地区构建了多元化的知识资源与思维方式,从而深刻地影响着相应地域的近代知识分子。[2]当西方凭藉其科技优势闯入中国时,带给中国思想界的变化,首先是以对儒学经典知识解释路径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依据其思想与知识分野,分别对中国社会内部变革提出了迥然不同的应对策略。葛兆光也指出,由于中国的学术自产生之日起就是面向世俗生活的,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须臾不曾离开过,这种特质使儒学体系本身是开放的,随着世俗社会的发展,就会不断有新的知识元素突破传统的边界。[3]即作为经典思想的儒学本身是不断发展的,而且是一种可重塑的知识资源,其原初状态的多元性已经孕育了多元后续思想的可能。显然,当传统思想在面对西方的入侵进行内部变革的设计与实践时,西方的思想资源也就会以适当的方式被吸纳进中国近代思想的体系之中。
如果按照历史的进程逐一分析的话,发近代变革思想先声虽是龚自珍,但真正付诸实践的却是湖湘知识分子。湖湘学的传统是(1)由人道而及天道,注重在日用伦常中获得本体性超越的途径,(2)注重把义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4]杨念群认为,正是湖湘学人在秉承程灏、张栻学脉并兼朱熹学影响而有所开发,采用修德与治术相结合的方法来消弥道统与政统日渐分离的界限,由平定太平天国和西人入侵所致的机遇,使湘人得以施展抱负,才得以以经世致用和“帝王之学”话语为深层作用背景酝酿并实践了洋务浪潮。[5]由于此后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梁启超对维新时期其思想地位的放大,就使湖湘学派的洋务运动似乎自此便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实际的情况是,康梁推动下极力变法图强的光绪皇帝对维新的理解和慈禧实施的新政,都未能脱开湖湘人开启的洋务运动的路径。作为湖湘一脉思想的接续者,湖湘践履洋务的追随者与参与者,张之洞以系统论述中体西用思想而在清末乃至其后思想界成为最受推重、受到批判也最为激烈的人物。张之洞在以器卫道的思想路径上部分地修正了曾国藩等人只寻求外势治术而不及王道的缺陷。其对体用二元分法的引申——由传统的道器分法而至中体西用——无疑打破了中国传统思想界的坚冰:以理学为正朔的道德哲学的一元论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也就孕育了其后数十年间中国思想界的变化走向,如五四时期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直到物质与精神的二元统一论的引介。比之岭南学派的乌托邦思想的滥觞,张之洞的思想可能因其务实而颇符合当时中西融合的实际状况,1901年后被慈禧钦定为新政的路子也说明了其价值所在。
一旦当甲午战争后湖湘人相继退出清王朝的权力核心地带,随后占据思想界主导的儒学话语则是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主张维新的岭南学派。在康有为庞杂而宏大的维新思想体系中,核心仍在于通过对公羊三世说的阐扬,效仿汉初董仲舒重构“政治神话”。与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学诠释汉代秦的合法性不同的是,康有为试图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政教合一的立宪君主制:给予孔子以宗教性的“素王”身份,以作为独立于政治系统之外的精神监护人,从而形成如西方基督教新教改革时期的巨大精神背景,并依靠重塑君主的道德化身来达致外王的目的,最终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甲午战败无疑为康有为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良机。通过康及其弟子梁启超的宣传与鼓动,其变法主张很快得到传播并逐渐为光绪皇帝所接受,试图通过变法而在权力的争斗中占据主动的光绪旋即决定将之付诸实施。而一旦当被康寄予厚望的光绪皇帝,从思想上和实际的变法实践上,都无法达致康所希望的结果时,维新变法自然走向失败。究其主要原因,则在于其使孔子宗教化的非理性变革路径与儒学世俗化、人文化的发展路径有着根本性的差距,对以礼制维系的王权权威带来了其所不能接受的挑战。与康有为有所不同,岭南知识分子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梁启超,由于早期多受阳明学浙宗的影响,尽管服膺其师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并在五四前是康最得力的追随者,梁却始终把人性中“善”之本性的复萌作为实现大同世界的终极目的。即梁启超将岭南学派内在的道德至上的心理原则从光绪一人泛化放大到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置于对人类本性的道德启蒙上,而不是对改制变迁的持久关注上。[6]这可以看作是后来梁与康分离并极倡新民的根源所在。
二、江浙学派与高等教育变革的思想背景
地域化儒学的分野,也决定了不同地域知识群体在什么范围和多大程度上,能够容纳和接受西学中的异质文化成分。本文所关注的近代高等教育的变革,恰是具有实证科学因素的地域化儒学——江浙学派,在书院教育中实行具有专门化特征的分斋教学与西学相融会后间接所致的结果。杨念群认为,较之湖湘学派和岭南学派,江浙学人的学术传统更容易吸收西学中的科学内容。杨向奎和余英时也指出,清代朴学并非如多数人认为的那样沉湎于汉学考据、训诂而失于对义理的探寻,只不过从学术的路径上说,认同的是道学问而后才能致尊德行的路径。受晚明开始的西学东渐的影响,江浙知识群体的朴学传统出现了两大思想特征:用数之有形阐述“理”之无形,用技艺实学拓展格致的传统界限。在江浙学人看来,儒之“道”寓于“艺”,而“道”之发显为形,就必须通过对“艺”之具体形象的衡量为其限定,衡量的工具即为“数”。这使江浙文人常常把数学作为某种能够被用来推测抽象之“理”的工具,使之变为某种易于把握的东西,至少不再使“理”如宋明新儒家认为的那样,仅凭自我体悟就可获得。这种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去推测“理”之存在的方式,与江浙一大批学者认定宋明儒学的“理”无法被抽象阐释的观念是十分一致的。另一个思想特征则体现于江浙文人总是首先把理论的探讨落实于器技工艺或经典训诂的“实学”层面上。科学践履型人才的大量集中与考据大师的层出叠现所显示出的江浙学人行为模式的独特性,就是江浙学人承袭上述两个思想传统的结果。一些学者因此将江浙学人这种思想特征称为“技术传统”或者“知识主义”。艾尔曼认为,正是17、18世纪儒学话语出现的向知识主义的转向,为中国学术摆脱儒家道德理论与信条的束缚准备了条件。[7]余英时也认为,虽然清代的儒学并不必然导致现代科学的兴起,但其发展至少已显示了这种基本改变的可能性;而儒学的现代课题主要是如何建立一种客观认知的精神,清代儒学通过整理经典文献以恢复原始儒家的真面貌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严肃的客观认知的路径,恰好为儒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提供了一个始点”。[8]也就是说,近代江浙学人显然不完全是基于西学冲击的刺激,而仅仅是在学术专门化过程中从传统儒学的分类方法中谋求使研究对象趋于专精的合理依据,其意图也仅在于抗衡宋明“性理之学”的笼统与时文的空疏,而这恰恰不自觉地与近代科学发展的分类原则有一致的地方。
当然,教育要吸取的部分西学内容必须能从儒学传统中引伸推导出来,以便符合“古已有之”的西学中源原则。[9]自清乾嘉始,源自宋代胡瑷的分斋教学,逐渐成为在以江浙学派主持的书院教育形成的一个重要传统,因与现代高等教育分科教学颇为接近,随后成为实现教育体制变革的媒介。这一个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由阮元建于1801年的诂经精舍。谢国桢就指出,“自阮文达倡立诂经、学海,乃专示士子以考证训诂之学,兼习天算推步之术,士子各以性之所迁,志其所学,学有专门,已含有分科之意。”[10]这就点明了诂经精舍模式泛化于各地域的实质意义,即以学有专门的近代分科手段,淡化性理之学传承已久的道德伦理内涵。除诂经精舍外,江浙区域以分斋之法课土的书院尚有龙门书院、上海求志书院,分置经学、史学、掌故、算学、舆地、词章六斋,江阴南菁书院则分四斋并各设一长。而一些考据学人在书院的讲学,如俞樾除任教于诂经精舍外至少主讲过5所书院,卢文主讲过龙城、钟山、暨阳、娄东等数所书院,钱大昕主讲过钟山、紫阳、娄东等书院,冯桂芬则掌教过正谊、敬业、紫阳、惜阴4所书院,就使学术专门化路径的渗透到江浙乃至各地的书院教育中。
在1904年后书院变革为学堂的过程中,这批受过经古考据之学训练的专门化学人更是借助于分斋课士等学术传授方式,顺利地使书院中固有的儒学传统因素熔铸于中西契合的制度框架之中。究其原因,其一,分斋课程以经学为中心的发散式结构,虽然源自于儒学传统,却并不排斥西学的融入,而且很有可能使西学的部分观念作为经古之学的自然延伸而渗透其中。因为在许多江浙学者看来,西学的内蕴自明代以来早已包涵在经学研习视野之内。其二,从1896年《礼部议复整顿各省书院折》对整顿各省书院的意见,即“宜仿其意分类为六:曰经学,经说、讲义,训诂附焉;曰史学,时务附焉;曰掌故之学,洋务、条约、税则附焉;曰舆地之学,测量、图绘附焉;曰算学,格致、制造附焉;曰译学,各国语言文学附焉。士之肄业者,或专攻一艺,或兼习数艺,各从其便”[11]中不难发现,书院整顿的主导意见,恰是试图使西学与中学在儒学传统的知识分类空间中达到某种平衡和妥协。清末教育改革也正是以此为突破口,即作为整体的近代江浙书院在体系、制度、课程等方面与近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的接洽,包括上述的分斋课士及算学与天文、地舆等科学课程的设置所体现出的专门化倾向和书院管理上的教管分离,才使江浙学人在教育变革上的理论构想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化程序予以实施。[12]同时,如果要使“艺学”成为知识阶层正统意义上的修养内容,就必须使之在科举正途中取得一席之地,而且必须逐步扩大其在科举网络中的比重。1874年李鸿章倡设算学科其意图即在此,其后奏请设经济特科也一样。1904年新学制颁布和1905年科举废除后,清廷仍旧对学堂出身的毕业生给予一定的功名更是对这种做法的一种延续。对擅长器技之道之人,给予与精于帖括词章之学的儒生以同样的功名待遇,正是明末清初江浙士人群体学术“专门化”思想传统在近代的一种折射。
东西方传统在近代中国教育变革中的契合也说明,一种文化如果要向渗入到另一种异质的文化结构中并立足其中,就必须寻求异质文化中与之相类似的因子,只有寻求到这种因子并使二者结合,才能最终完成文化的变革与过渡。[13]当然,江浙朴学书院分斋教学的传统的传播还有赖于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群体间的互动。由平定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湖湘人士在朝野上下可谓呼风唤雨,但是格致、算学、制器之术却并非其长项,恰是江浙士子以入幕形式解决了这一难题。由于江浙知识群体数量相当庞大,自清以来就出现的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江浙学人游幕的现象,至清末就更为普遍。特别是以算学、制器之术见长的一些知识分子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皆因曾国藩、李鸿章等开办洋务企业、译书局等而入幕就事,才有近代科学的广泛推介、洋务学堂的举办,从而开近代新式教育的先声。至于在洋务运动中引进西方科学课程的新式书院的开设与旧式书院增设西学课程,都或多或少受到江浙学人或承袭朴学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至于维新时期,由革新潮流而带来的书院改革与学制改革也就正当其时。
当然,当我们将视野放宽至整个近代思想界,就会发现近代知识分子固然未能脱开对经学传统的秉承,佛学、子学在近代的复兴,都可以看作是从传统思想与学术库中寻求解决近代问题的表现。而每一种变革的思潮都或多或少可以看到不同学术与思想背景相互融混的情景,以致于很难绝对地讲,某一种思潮是完全承袭自某一特定的、来自前近代的传统,只能说其内在的思想理路具有某种延续性。因此,上述儒学地域化所致近代思想界的变化,尤其是近代教育体制的变革,也只是就可延展的线路所做的试图使其符合历史发展轨迹的诠释,并不是一种全局性的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