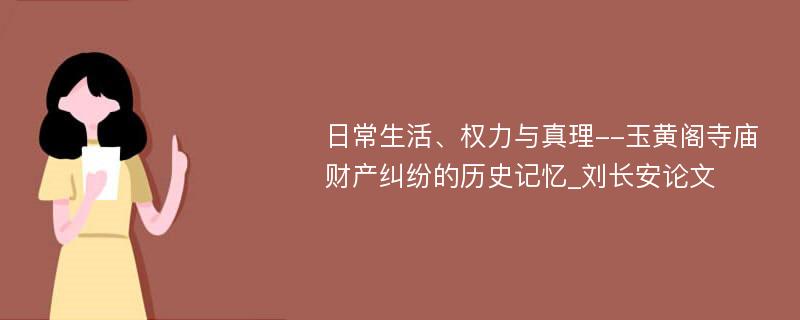
日常生活、权力与真相——玉皇阁庙产之争的历史记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常生活论文,之争论文,真相论文,权力论文,记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言
在历史学家们所讲述的义和团运动——这一宏大的历史事件的下面,埋藏着大量参差错落的记忆碎片。梨园屯的玉皇阁庙产之争就是一个这种意义上的一小簇碎片。它之所以“小”,是因为它在一系列事件中位居尾末,历史学家也许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事件等级,帮助我们记忆了这簇碎片。他们告诉我们这是个小事件,因为它分有了义和团运动——这一宏大事件的些许历史意义,才值得记忆。(注:在这种叙事模式中,小事件的重要性是借由大事件的意义而得以确定的。其中“义和拳”名号的出现和其“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倍受关注。梨园屯讼争的小事件借此而嵌入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这一更大的宏观历史叙事中去。这种叙事发挥效力的基础在于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简要的总结”所建立的一套事件的等级制和相应的单一线性时间系列(李猛,1996,第3页)。)
但是,当我们翻阅档案,查考口述记录之时,却不无惊讶地发现:在大事件的意义之光照射不到的角落,有那么多的记忆碎片被遗忘。在历史的暗夜里,它们闪烁着点点微光,或喃喃低语,或高声呼号,但我们却听不出它们的意义。也许意义不仅需要听,还需要看。因为缺少光,我们看不清,我们只是听见,只是隐隐感到它们的能量和我们自己的不安。我们不禁要问:历史的记忆究竟是谁的记忆?它在讲述谁?
也许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光源,让它通过历史距离的透镜重新审视这些碎片,体会它们的意义。有一个光源看来可能存在于村落的内部,或许它就是村落的日常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说,梨园屯庙产之争作为一个事件,是村落的日常生活与外部世界的一场遭遇。也许这个事件对于义和团运动这个宏大的事件来讲,是微不足道的,但从村落内部的生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来说,它却意义重大。因为,村落平静的生活开始被拖入历史,在与权力的碰撞中,许多人的平凡而安静的生活遭到毁灭,因之他们被铭刻进记忆——他们变得声名显赫或恶誉昭彰。无论如何,今天我们看到他们有幸或不幸留下的片纸只言,对他们来说也许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许,正是因为生命与权力相撞产生的巨大回响还萦绕在空旷的历史之夜里,我们这些习惯遗忘的人才会感到不安。于是,我们就想重新编织一张记忆之网,把这些碎片打捞上来,用重新点燃的火炙烤它们,企图透过那龟裂的纹理窥见村落的命运和历史的力量。
几种话语中的梨园屯讼争(注:人们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可以用种种不同的方式建立联系。问题是“历史与记忆的纠结”不能以流行版的“罗生门”式的怀疑论对待,不是什么人或人性还值不值得相信,还值不值得抱有希望的问题;而是我们对“过去”的种种解释,必须在“罗生门舞台”并置,必须作为一部小说的“复调”一起出场,我们才能对这些解释进行再解释,才能对“真正的”人性、“真实的”过去得以构造的基础进行再认识。“事件、经验和神话”的区分不能用历史学家、过去经历者和神话编织者的主体立场来解释,而必须用这些“主体”位置的生成条件来理解(柯文,1997)。)
故事发生地梨园屯身处一块特殊的“飞地”——山东冠县十八村(实际上是二十四村)中。冠县十八村虽然行政上归山东省东昌府冠县辖制,但它既不与冠县相连,也不在山东省境内,而是孤悬于直隶境中,距冠县县城140多里。冠县县志记载十八村:“地势远隔,风俗攸殊。盗匪充斥,民教杂处。孤悬境外,隐然独立一小邑,控制既鞭长草及,治理亦梗塞而不通。”(《冠县县志》,卷一,1934年铅印本)
(一)“既已明立分单于先,何得追悔混控于后”
梨园屯的民教诉讼起因于一块玉皇庙地基。康熙年间,本村的廪贡生李成龙捐土地和房宅一所,此后,本村他姓富户也捐了一些土地,共同支撑一所护济义学。村民们在这块公地上又修了一座玉皇阁,作为在本村举办迎神赛会的场所(路遥,1990)。
可能是在1860年代的战火中,义学和玉皇阁都遭到了破坏,此后风吹雨淋,村里又无力修复,到我们的故事发生的年代,这些屋舍都只剩下断壁残垣。(《教务教案档》,第5辑,459页)
1869年(同治八年),本村的天主教民提出要议分义学田地,梨园屯全村三街会首和地保一同商议同意分给。
传教士斯格瑞格勒事后追述说,“1869年新皈依的基督徒声称:他们过去曾捐过钱,他们请求斯格瑞格勒为他们获得一部分庙产,当这位传教士在应邀参加的‘正式宴会’上提出此事时,村里的头面人物们——‘惊讶的异教徒们答以遁词。’经与当地的布道员(教民)们进一步讨论后,头面人物们同意分庙产。皈依者得到了坍塌的庙,非基督徒们仍拥有土地。村里的头面人物们和地保于1869年3月1日草拟了一份分配契据并签了字,接着得到了冠县知县的批准。”(狄德满,1992)
1869年分单档案有存:“立清分单冠县邑北境梨园屯圣教会、汉教。公因村中旧有义学房宅一所、护济义学田地三十八亩。今同三街会首地保公同商议,情愿按四股清分。汉教三股,应分田地三十八亩。圣教会应分房宅一处,上带破厅房三间,破西屋三间,大门一座,计宅地三亩零九厘一毫,以备建造天主堂应用。邀同各街会首地保觌面较明,并无争论,同心情愿,各无忌言,亦无反复。恐后无凭,立清分单存证。同治八年新正月十九日。”接下来有村中头面人物共十二个人的签名:左令臣、姜锡广、高清林、阎凤池、阎培元、王太兴、李福恒、刘长安、阎德华、姜锡武、阎立业、王俊成(《教务教案档》第5辑,458页)。12人含盖了当地的六大姓:左、姜、高、阎、王、李。头面人物中除阎姓没从富户中产生外,皆首推富户。刘姓虽人不多,但刘长安是监生,所以列为会首。王俊成虽只有10亩土地,但他善口才而有威望,也列为会首(路遥,1990)。
此后四年,平静无事。
可四年之后,即从1873年到1892年这二十多年间,民教争讼几经反复。官司从冠县打到东昌府,又从东昌府打到济东道,再从济东道打到山东巡抚衙门,而法国公使和清朝总理衙门又斡旋于其间。一部村落日常生活的戏剧越演越大,角色越来越繁复,情节越来越曲折,直到发展成一出政治剧。
1873年(同治12年)民教双方第一次互控到县。村民一方出头的是当年在分单上列名的会首之一——阎立业,教民一方的代表人物是教会长王桂龄。当时的冠县县令是韩光鼎。阎立业控告教民毁义学庙宇,立天主堂,王桂龄告村民一方索地建阁,有违前约。此间圣公会山东教区主教顾立爵(汉名)向县令移交当年的分单和几年来教会为这块地所纳钱粮的凭证——串票八张。县令“提集两造,讯取确切供词,核与分单相符。”认为“此案既已明立分单于先,何得追悔混控于后。殊属不合。”遂将阎立业等人分别“责压示罚”,并准许河北文生朱升堂等将他们保释完案。(《教务教案档》,第4辑,271页)。
关于这次争讼,梨园屯老人们多回忆说是因为教民私卖了庙地:“奉教的分到庙后,他们就对神父说:‘村里的人要卖这座庙,咱要了它盖堂吧!’神父看中这个地方后,同意买庙盖堂了。神父花钱买了庙,钱没有给梨园屯的人们,都叫奉教的偷着分了。”(1966,梨园屯高警世口述)
而传教士们是另一种叙述,他们说教民们分得庙基后因无力修盖,转而把地基献到了传教士梁多明(意籍)名下修盖教堂。(《教务教案档》,第5辑,458页)
路遥先生认为村民回忆卖庙地时的梁司铎是继梁多明死后的另一分管梨园屯教区的意籍人——梁明德。村民回忆说拿出三块银元宝(每块50两)交给教民买庙地的就是他。1873年(同治12年)他命令教民迅速盖起天主堂才引起了村民的公愤。(路遥,1990)
最有意思的是顾立爵的说法,“1873年,三个富裕的非基督教徒获得了‘生员’身份,为了演示与他们的新地位相当的威势,他们控告基督徒,‘指控他们强行拆庙,强占土地。,”(狄德满,1992)
1873年的判决做出后并没有什么资料记载双方的动静。但到了1881年,村里举行玉皇神会,冲突开始了。
关于1881年的冲突,教会方面有所记叙:“1881年2月8日那一天,人们穿过条条街道,扛来一座神像,抵在教堂门上。一大群手持矛和剑的人,聚集在教堂院里。虽然一位进行抗议的天主教妇女受了重伤,但其余的教徒仍镇定自若,‘避免了对村里基督徒的一场彻底大屠杀’。”“2月12日,梨园屯的左宝员召集了2000名群众,手持矛、剑和棍棒,捣毁了教堂门,把玉皇像安置在教堂里。”(狄德满,1992)
中国官方调查叙述:1869(同治8年)间教民把地基转送教士建立天主教堂。此后,玉皇像就在教堂左近处设堂供奉。1881年(光绪12年)正月初九,该村举办玉皇神会。乡民们雇人表演彩船小戏,经过天主堂门外时,游人聚集观看,十分拥挤,把教堂大门挤开。堂中的教民出来理论,当时人多口杂,有人说天主堂本来就是借用的玉皇阁地基,等将来重塑玉皇像,还要送进去供奉。(《教务教案档》,第4辑,277~278页)
法国公使宝海在给总理衙门的照会中讲,梨园屯地方有匪徒把教堂门打坏,率领众人闯进教堂,并在堂院中作戏耍玩。一些教民不力拦阻,便上前理论,被殴有重伤,并威胁说要派天津领事狄隆往山东调查教案(《教务教案档》,第4辑,261页)。县令韩光鼎是从山东教区主教顾立爵那里得知此事的。韩令调查后认为,1881年的冲突,“亦不过空言争论。并未砸毁大门。亦无强逼教民住宅作戏子寓处。以及将土神送入天主堂情事。”他认为“左宝元虽未率众滋扰。究系好事。阎东付亦属恃教逞刁。”所以对他们“分别薄责示罚”。至于该教堂的地基“断令民教仍归和好暂行借用,俟该教民等另买地基设立教堂,再议归还”。取结完案。(《教务教案档》,第4辑,277~278页)
很奇怪,教民一方对这一变化巨大的断判是何看法,并无记载,1881年到1887年,双方也无继续争讼。
(二)“法既不能遍加,理亦难以周谕”
但事实上教民们并不愿意去另觅地建堂。1887年,方济各会教士费若瑟带来砖瓦,要在地基上盖起一座西式正规教堂,以取代旧建筑。教堂房屋已动工数日,刘长安和左建勋以及阎立业等人率领数百人持械将建堂木料砖瓦等物抢走,费若瑟和教民们吓得躲了起来。村民们拆了建设中的教堂,在原地盖起了一座新庙。法国公使李梅转引山东主教马天恩的说法:“光绪13年(1887年)间,……费教士在该庄置买砖瓦木料,欲重建被坏教堂房屋,业已动工数日,突有该庄恶棍左建勋、刘长安等纠集众数百余人,各持器械,胆将木料银钱等物抢掠一空。”(《教务教案档》,第5辑,458页)当时梨园屯的教士卫宝禄(法籍)移文韩令的继任何世箴称,村民们一面由刘长安等人去县里具禀,一面就着手建庙。何世箴认定刘长安等“理曲肇衅。本应究惩。”但“姑念衅非一日,议出多人。从宽详革监生。”并断令于1888年2月前限期拆还教堂。(《教务教案档》,第5辑,464~465页)
但村民一方并未屈服。一方面武装护庙,一方面继续上控。据村里老人回忆,十八魁的说法第一次出现。六大冤的诉讼阵容也第一次聚齐。
“第一次拆堂盖庙时,(村里)打了十八把双手带(刀),派了十八个人护庙,这就是老十八魁。”(1988,梨园屯阎万瀛口述)“十八魁没阎家人,是赵老汉一伙,后来老十八魁闹不住,阎书勤看不惯才加进去的。”(1988,梨园屯阎万才口述)
“高老街(东山),阎得行(德盛),王老括(文昌),左老村(建勋)在外头打官司,剩下三个在家中布置,敛钱打官司。打了五六年,官司没赢,才叫‘六大冤’”。(1988,梨园屯阎万瀛,阎尊巧口述)
这里的六位绅士包括被革去监生学衔的刘长安,捐班监生左建勋,文生王世昌,捐班生员姜汝能,捐班生员高东山,武生员阎得盛。(1988,梨园屯王伯林、左棕周口述;路遥,1990)
教民一方对判决和事态更不满意,由王谦(伯三,三歪)带领,先行上控。
村民一方则由三位绅士出面,随后上控。
双方先告到了东昌府,随后又告到了济东道,最后告到了山东巡抚衙门。省和府把该案批给县里重审。此时,何世箴“奉文卸事”,新任县令魏起鹏“传讯两造。供词各执”。何世箴随后又复任,与魏起鹏共同审理此案。但,“正在提讯间,即据王三歪等与刘长安等各联名呈称,案经绅耄潘光美等开解调处,伊等均各悔悟,不愿终讼。伊王三歪等情愿将教堂所占庙基归与该村为庙,伊刘长安等与庄众亦情愿另购地基,为王三歪等新建教堂。”
何世箴和魏起鹏断判此案的逻辑是“此等案件,人众心齐。法既不能遍加,理亦难以周谕。”“刘长安等肇衅理曲,本应仍照前断勒令拆还教堂,惟念该民教等居同里皋,若令嫌隙滋深,难保不别酿祸患。即经绅耄调停,两造悔悟请和,莫如就此完结,以期民教得以互释前嫌,永保相安。”于是,“随各捐银一百两为之津贴,督饬克日兴工照旧教堂格局修造完竣。所赔衣物并饬如数缴案,分别验明,谕令教民当堂具领,取结完案。”(《教务教案档》,第5辑,465页)
如此在绅耄和官方的调解之下,教民和村民之间达成了妥协。
此后两年,民教相安无事。其间,1889年和1890年两次,法国公使依据马天恩的要求,坚持依据同治八年所立分单,在原地基上建堂,“本大臣查前经接到山东马主教函称:卷查同治十三年三月初七日,有前任韩令移文内称,此案既已明立分单于前,何得追悔混控于后,殊属不合。并将分单串票移交敝管业,未言暂行借用之说。况前任何令禀内,亦有断令刘长安等至来年二月间即行迁移神像。亦无暂行借用之说。”
值得注意的是,法使从这两次判审中得出的推论:“可见此事教堂并未霸占庙宇地基,原由地方官屡以此地为教堂教产业。”而且称教民接受调解具结之事,教堂执业不知,要求地方官和马天恩当面商量还堂事宜。(《教务教案档》,第5辑,469页)
而山东巡抚张曜给总理衙门的回文转引了地方官的说法,认为教民具结是与当时的李姓传教士“商酌妥协”之后达成的,而且查知该诉讼起时,传教士是卫姓,到息讼的时候已换为李姓,到现在已结案一年多了,听说教士又换了好几个。所以才说:“实无别项轇轕未清之件”。总之,这两年间法使虽有抗议,但地方官以此案已结,避而不见马天恩主教。(《教务教案档》,第5辑,466页)
(三)“非好民之好,恶民之恶,岂能为民父母?”
1891年,情势逆转,长江流域哥老会反教的氛围之下,山东反教情绪高涨:“三月河南哥匪为乱,焚毁教堂案件,层见迭失。山东至七月间正逢乡试,士子云集,奸徒乘间混迹,妄相鼓簧,散布匿名揭贴,一时讹言四起,情形岌可危。”朝廷谕旨命令地方官切实保护教士教民,否则,“即著据实严参”,“其从前各省未结各案并着该将军督抚从速办结,不得任听属员畏难延宕以清积牍。”(教务纪略,卷首)在此情势下,总理衙门咨文山东巡抚福润,要求梨园屯一案地方官与山东主教迅速当面商谈办结。(《教务教案档》,第5辑,525页)
福润令东昌知府李清和越过县官直接“提集讯明”,断令将庙宇让与教民,改建教堂。并恐民心不服,由该县何令捐银二百两,京钱一千串,“听民另购地基,建盖新庙,移置神像,取结完案。”
但教民复扬言“必将控争之人按名拿究,方肯甘休”,以至“众情不服”。村长左建勋将办团枪械移入庙内,意图守卫,并请临清人魏合意道士来庙里住持。教民们都吓得逃走或躲避起来。巡抚福润饬令济东道张上达“亲往相机妥办”。张上达督同东昌府李清和,临清州牧陶锡祺和冠县县令何世箴传集附近绅耄“晓以利害,剀切开导,将滋事愚民全行解散。”(《教务教案档》,第5辑,528~529页)
在官绅的斡旋下,“六大冤”只好答应不再起诉。路遥先生依调查考证,此次邀集的绅耄不是十八村的士绅,而是临近曲周、威县的士绅,有曲周井湖寨武举张伦远,威县文生郑一魁,文生庞清音等(路遥,1990)。张道亲自监督拆庙并由教民一方将地基查收。“同时,张还为非教徒在另一个地方盖了座庙。‘他也企图引诱天主教一方把他们的教堂迁到另一个位置,但他们拒绝了。’”(狄德满,1992)
村民回忆说:“后来何世箴给讲和花钱买盖堂地九亩;也买了盖庙地,也不知多少亩,比盖堂地少,并出钱把庙、堂都给盖起来了(瓦房),将原来的庙址和庙地归为官地。但是奉教的不去,硬要去原来庙的地方盖庙不可。这样,村(人)民祭新庙唱戏开光时,又闹起来了,这回奉教的都吓得跑到外村去了。”(1966,梨园屯高警世口述)
“当时唱戏,十八魁保庙是功臣,但把他们晒大个儿了。他们不服。阎德盛第二天放火烧了礼台。第三天,阎书勤大骂了起来,拿大刀把供桌给砍了,七县官都跑了。府官跑到了老官寨,神父也跑了,奉教的也跑了。”(1988,梨园屯阎万瀛口述)
六位绅士虽然在1892年5月那次官绅调处中表示不再上诉,但此后他们明显是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又上控到东昌府。据说王世昌在公堂上质问知府:“非好民之好,恶民之恶,岂能为民父母?”知府判王世昌、左建勋、阎德盛各两年监禁。“出来之后六位绅士无脸面向村里要钱,自掏腰包充作诉讼之费,不再打官司了。”(1960,河北镇魏村韩灯宵口述;1960,干集张兰亭、牛老池口述)
陆衍科回忆说,有八位村民(一般穷人)后来还想出面交涉。“他们先问了六绅士,想联合他们同往。这时,六位绅士气馁说:‘我们不去了,这次有洋人撑腰,要去你们去吧。’八人见他们这些有身份的人都不敢去,他们也只好作罢。这八个人被后人称为‘八大讼’。”“这时村民因官府不为民做主,便决心与教民拼命,共举阎书勤、高小麻为首领,号称“十八魁”。阎书勤等人打的是红拳,事起后他又联合了梅花拳首领赵三多,拜他为师。赵三多又联合了大王曲的梅拳首领陈老明。赵三多、阎书勤等人在梨园屯闹事时改称‘义和拳’。‘义和’即大家联合起来的意思。六绅士见事情闹大,都离开了梨园屯。”(1982,干集陆衍科口述)
话语、权力、历史记忆
也许有的人会说,小事件的重新深描与大事件的叙述相比也不过是一次不同的切割和编织。成为事件,这本身已经远离日常生活了,因为,日常生活之境是“无事件”的。但是,难道我们真的能够触及历史上“无事件”的日常生活吗?没有话语,没有那与权力合谋或与权力对抗留下的片纸只言,剩下的沉默难道不只能是虚无?的确,小事件的深描也不过是一次重新切割和编织。但是,这绝不是第一次。从这些村庄生活被写入公文或私人日记,从他们进入村民们的传奇叙事时起,不知经历了多少次折叠——切割——展开——再折叠。也许我们不能触及村落日常生活本身,但我们能不能努力去揭示——在权力与话语的往来之间,村落的日常生活和常人的卑微生命是如何第一次被编织进了事件?
(一)日常生活、常人、历史
要解答这个问题,梨园屯的王姓教民之死值得补叙一下。因为这个小人物的死亡事件使我们关心的东西从历史中凸现了出来。
“当时教民以王伯三为首。王伯三就是王老宅的父亲。上头来传教时,要在梨园屯买地盖堂。买堂的钱都被王伯三贪污了,大教一分也没得。当时他的权力很大,上头依仗他。
王伯三(代表教民)王世昌(代表村民)、一起上邱县打官司。王世昌在县官面前跪下,王伯三不跪,还用经本打县官。这位县官是何二糊涂的儿子,何二糊涂曾任冠县县官。县官大怒,把王伯三治死了。……”(1988,梨园屯耿双印口述)
“王三死在冠县。先是何官,后是他儿子做县官。王三是天主教的头儿。王三对何官说:‘我是天主教的状元。’何县官说:‘我就打你这个状元。’他死后七天没出殡。那时在教的见官大三级……”(1988,梨园屯于成田口述)
“……生官司时,偷卖庙基的王某某公然说:‘我是个状元,是神父付给我的状元。’被邱县县长打得皮绽裂开,用小车推回家来,在路上死了。”(1960,蒋庄蒋金聚口述)
据官方档案记载,这个冠县教民的真名实姓是王桂龄。光绪七年(1881年)法使宝海向总理衙门施加压力,要求将山东省教案尽早办理完结。宝海的函中援引山东主教顾立爵的说法,称“教民与讼之案总不得平安,皆因不奉教者于讼后反视教民为可欺。”(《教务教案档》,第4辑,261页)梨园屯教民王桂龄是1873年玉皇庙讼争中的教民一方代表,顾立爵认为1873年案已结,但非教民一方的左保元见王桂龄已死,屡向教堂滋扰,属故意寻衅。原来1881年玉皇神会冲突是发生在王桂龄死之后的。王是梨园屯教民的第二代教会长。王桂龄一案官方调查说:“冠县教民王桂龄等被差送县责押一案,缘邱县民程光合因拖欠漕钱,经县传案押追。程光合之子程二羊素习天主教。贿串同教之冠县人王桂龄又邀同教之刘洛六即刘西长,雇坐郝双魁轿车,行抵邱县,乘醉直闯县署喧嚷。该县出见,王桂龄等不服咆哮,该县将王桂龄等酌量责罚,同郝双魁一并递籍,王桂龄递至冠县,在保病故。经冠县验讯详报,并将刘洛六等取保释放完案。”(《教务教案档》,第4辑,277页)
有关王姓教民的记载和回忆是如此的含混矛盾,在教会方面,他一定算不上以身殉教的“圣徒”,而且他恐怕因个人品行连“义人”也称不上。但是,在不奉教的村民的回忆里,他却足足够得上一个形象逼真的异类“精英”。
他丑恶卑鄙,令人嫉恨,因为传教士依仗他,他是教会长,势力很大,他利用自己位置的便利,上下其手,偷偷把玉皇庙基卖给了神父。
他胆大狂妄,令人震惊:他模拟官仪,雇轿闯入县衙,而县官咆哮,竟然用经本打官长。
他滑稽可笑,令人怪悯:向县官自称是状元,但可惜状元学衔是神父给的,他是天主教的状元,天主教的状元自然不是状元,冲撞官长自然要受责打,可怜一芥草民,禁不住官长的“酌量责罚”。
也许这个小人物本该沉寂在无声的日常生活里,就象那村庄里许许多多的常人一样。但他却有幸与某种权力并肩或不幸与某种权力相对抗,他留下名字的方式,正是他被毁灭的方式。
他那被记忆的形象之所以含糊混乱,是因为他与各种权力的关系本来就纠缠不清。他被文字提交给了权力,他被权力以文字勾画了身份,他被权力记忆,也被权力遗忘。也许各种权力本来希望他能活着,或者作为教会的活的共谋,或者作为官长权威的活的教具,或者作为村落重新凝聚的活着的儆戒。但可惜,一个平常小村民的脆弱肉身不堪这许多重负。
而我们,这些重新审视这些记忆残片的我们,也许会说,难道不正是日常生活以命运的形式出现,难道不正是生命以毁灭的形式向我们展现自己才使今天留下的短促叙述浸透着可怕的力量吗?难道不是与权力共谋,难道不是被文字提交给权力,难道不是被权力和文字镇压,才留下了这片纸只言吗?如果没有历史的力量介入村庄的日常生活,如果权力不在身体上留下烙印,我们又怎么能知道村庄的生活曾经是自足的,常人的生命曾经是自得的,“无名”也许是幸运的呢?
如果日常生活不走出沉默,如果它不往来于权力和话语之间,我们怎么能听到它的声音,怎么能窥见它的“本来状态”呢?
(二)地方惯行、西方势力、清朝国家
档案中的分单蕴涵了太多的历史记忆,它是话语和权力相互纠缠的产物,它是村庄内外力量交战的一个舞台。
我们似乎可以假设,在民教矛盾仍限于村落内部时,国家的控制意志和梨园屯地方权力网络之间的关系只是遥遥相望。那么,是1873年(同治12年)的互控第一次把国家的力量引入梨园屯村落里来吗?当有的历史学家把1869年的分单看作是常规的村落自治“惯行”的一个结果和表现时,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这种仓促的肯定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这份分单虽欲明确的是圣教会与汉教的“分家”,但契约末尾除了汉教一方的12个精英人物和4个地保的具名外,教会的一方则阙如。这和华北农村一般明署立约双方姓名的分单形式大不相合。把这份分单看作是梨园屯独立的村社自治惯习的产品这一假设,遮蔽了后面沉默的国家的力量。而这种国家意志向村落内部的悄悄延伸正是中国与西方世界冲突的产物。
柏尔德密协定是理解国家控制意志延伸的关键。
1860年的《中法北京续约》中文本第六款的末尾有“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文句。这一条是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私自添加上的。这自然是欺骗行为。(《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147页;史式微,1983)
但1865年初,法使柏尔德密与总理衙门达成一项协议,规定中国政府承认法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租买房地产的权利。不过契据内须写明“立文契人某某(此系卖产人姓名)卖与本处天主教堂公产”字样,不必专列传教士及奉教人之名。(《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221页)这就是所谓柏尔德密协定。这一协议实际上是对1860年《续约》中私添内容的确认。
不过,总理衙门认为,根据《柏尔德密协议》,卖给教堂的产业,不列传教士及奉教人之名,“产权不致落入外人之手,于中国仍属无伤。”而且,总署把这个章程通知各省时,附有密令,暗示各省“必须调查地方民众对这买卖是赞成或是反对”,而卖业主人“亦须于卖前报明地方官。应否准其卖出,由官方酌定”。(史式微,1983;路遥,1990)
1871年总理衙门向各国使臣提出的条款中进一步规定:“所有教中买地建堂或租赁公所当与公正原业主在该管地方官呈报,查明于风水有无妨碍。即是地方官核准尤必本地民人众口同声,无怨无恶,始可照同治四年定章注明:上系中国教民公共之产,不可伪托他人卖产成交,更不得听任奸民蒙蔽私自买卖成交。”这可以说是对所谓密令的基本意旨的公开表达。(教务纪略,卷三,章程)
如此看来,1869年分单的特异形式就不能被单纯的梨园屯地方的惯行所解释了。把3亩宅地分给圣教会以备建造天主堂应用当然算不上是外国传教士在内地买租地产,但教民分得宅地后即献与教士求助修盖教堂,分单上不列传教士和奉教人之名恐怕也将这一节预先考虑在内了。教会方面的回忆是有帮助的:教民分庙产的要求最初是通过外国传教士与村中会首们提出的;分单做出后还得到了县官的批准。
所以,如果说普通村民与教民凭依当时当地村落的“惯行”分割的只是村里的公产的使用权,那么,至少这个村落惯行的产物在诞生之时起就已经和国家的控制意志达成沟通了。那么,后来围绕分单展开的争讼就不能只理解成梨园屯地方村社持有的公产所有权不可分割的共有意识与传教士持有的绝对的、排他的近代产权观念的对立。因为这里除了村民和传教士的理解之外还有第三种理解——国家的意志。(注:佐藤先生的重要思想本人是在张彦丽女士的帮助下得以了解的。佐藤先生强调分析庙争诉讼的关键不是庙基的献与卖,而是对分单的的不同理解(佐藤公彦,1993)。这一点对我很有启发。但与佐藤先生不同的是,我不是从梨园屯的地方惯行与西方的近代产权观的对立来分析争讼的发展。因为在我们看来,没有纯粹的知识,没有纯粹的理解,知识与权力,理解和支配,是密不可分的。)
(三)权力、策略、真相
1869年的一纸分单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权力的配置和策略的展布。一方面,外国传教士的影响和村内教民力量的发展相结合。获得建堂的地基将使传教士拥有一个过往的居所和扩大影响的根据地;而如建起教堂,不仅一些贫穷的教民可搬入居住,本村教民的日常宗教活动也不必再到外村教堂去进行——教民在村内将获得一个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国家的控制意志和乡绅主导的传统村落秩序也悄悄合作。官方希望借助与绅士支配的村落的默契回应外来的冲突与渗透,绅士希图借助国家的力量控制村落内部教民的发展,维持住自己对村落的支配。
1881年和1869年韩令的两次断讼最值得重温。
1881年韩令的第二次判决与他的第一判的区别可以说是依据不同的“事实”,做出了不同的断判。
首先,历次判决都没有提到教民献地或卖地于传教士是否合法的问题。原因在于国家对此问题的控制意志早已在分单中体现了。分单上并未列传教士及奉教人之名,依官方的逻辑,产权最终也“不至落入外人之手”。所以1873年韩令的判断并非以庙基为教会持有绝对所有权的地产,交纳钱粮是使用土地、享有收益而应履行的理所当然的义务。
排除这一层问题,韩的“此案既已明立分单于先,何得追悔混控于后。殊属不合”,且将阎立业等人“责压示罚”的断处,可以说是依据一种纯粹的司法理性进行的。韩的断案逻辑是两造明立的分单应当遵守。既然分单内写明圣教会分得的宅地是准备建天主堂用的,那么教民方面当然有对这块地基拆庙建堂的使用权。也因此,阎立业等索地建阁为“追悔混控”,依法当罚。
但1881年韩的第二次判决“断令民教仍归和好暂行借用,俟该教民等另买地基设立教堂,再议归还”则依据的是另一种的理性。现在的新“事实”是民教双方的“趋向殊途,不免龃龉”。1881年,梨园屯已经从战后的疲敝衰颓中苏醒过来——凝聚村落共同体的重要仪式活动玉皇神会恢复举行。迎神赛会中,冲扰教堂的人们宣称教堂不过暂行借用,俟来日重塑玉皇像还要放回原庙处供奉——这表明了村民一方共同体意识的高涨。而教会一方毫不示弱,顾立爵在直接致函韩令,要求查办的同时,通过法使直接向总理衙门提及此事。对韩令来说,与地方秩序安定这一“大体”紧密相关的民教纷争的“事实”,要比依据分单,只要梨园屯教民群体存在,圣教会就对庙基有建堂的使用权这一孤立的法律“事实”更重要。
所以,教堂地基“暂行借用”的断判是附属于民教和好的断令的。对左保元和阎东付的“分别薄责示罚”是为了让村民一方“不可好事”,让教民一方“不可恃教”。但这里,治理的理性隐藏在司法理性的背后,也促生了新的“法律事实”。与其说村民一方索地建阁的要求是基于当时当地对分单的“活契”或“典”的“地方性知识”,不如说这种“地方性知识”是在冲突的背景下被官方代表的公共权力及其治理理性所“发现”的。
结语
在研究档案和口述记录时,我们原本希望借助日常生活之光进入历史当事人的本来世界,去倾听他们的第一次诉说。
但我们最终发现,日常生活本身并不是光源,真正的光生自日常生活与历史的遭遇,生自生命与权力之间的碰撞。这遭遇和碰撞之中产生的记忆残片不是别的,它们不是权力所说的,就是权力促使人们说的。除了这些话语的可理解部分和不可理解部分之外,我们听不到任何其他东西。事实已经是话语的事实,话语已经是权力的话语。我们唯一能做的也许只是去捕捉那些“事件”。而事件的“真相”不是别的,它是生活穿越不同的空间时留下的权力烙印。
但问题是,事件系列所展现的真相并非“大事件因果”逻辑可穷尽的,那些日常生活的空间和常人的时间以命运的形式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些东西。这些微小的东西无疑是义和团运动这一大历史的边陲,但庙堂纪念的旷野也许更能让我们见到新的记忆之光——我们至少知道,村庄在诉说什么样的历史,是谁在使它说话。
标签:刘长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