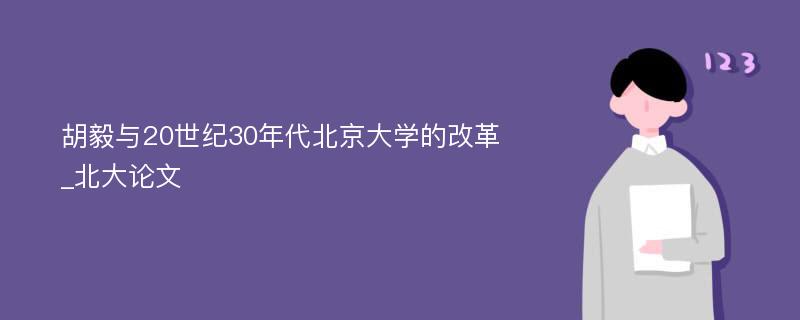
胡適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北大的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论文,三十年论文,北大论文,胡適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圖分類號]G64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14)04-0138-12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北京大學一躍而成為中國新思想的先鋒大本營,引發了南北不同大學的學人關於歷史、文化與現代民族國家關係的討論,開啟了中國現代史上學術地緣與派分的先河。在後五四時代,因北伐、遷都等一系列軍事、政治變革,北京大學先後被改組合併成京師大學校、中華大學和北平大學①,學校的獨立性求之不得,遑論發展。與北京大學地位下降形成吊詭的是,北伐後“北大派”勢力大盛,輿論稱“迨至國民革命成功,國府奠都金陵,曩時北大師生因緣時會,學優則仕。上自首都教育行政機關,下至大學專門校務,並及各種國立學會圖書館等事業,靡不兼容並包,極一時之盛。”②雖然1929年夏北京大學復校運動成功,校名得以恢復,而其“最高學府”的地位早因首都南遷,被中央大學取而代之,北大地位的下降已成為不爭的事實。本文即在這一背景之下,來探討胡適三十年代初重返北大,主持北大改革的背景、舉措及觀念,並進而探討這場改革對三十年代中國學術地緣與派分的影響。③ 一、北大紀念刊蔡元培序言解析 1929年12月17日是北大成立三十一周年校慶紀念日,本來“三十一”年並沒有任何特別的“紀念日”意義,但對北大人而言卻非同一般,因為是北大復校後第一個校慶日,尤顯得特殊,因此大張旗鼓地舉行隆重的校慶紀念活動,並出版紀念專刊,請老校長蔡元培作序。蔡先生對遷都後北大面臨的境況有一清醒的認識,他所寫就的短序,不同其他序言類文章的客套與委婉,語言異常冷峻地告誡北大同人:“若要維持不易動搖的狀態,至少應注意兩點”: 1.“要去盡虛榮心而發起自信心。”針對北大同人中有一部分人,好引北大過去歷史的光榮,尤以五四一役為口頭禪,蔡元培特別指出:“不知北大過去中差強人意之舉,半由於人才之集中,半亦由於地位之特別。”蔡解釋說,蓋當時首都僅有此惟一之國立大學,所以於不知不覺的艱難之中,“而隱隱然取得領袖之資格,而所謂貪於功以為己力之嫌疑,亦即由此而起。”換言之,北大取得“最高學府”地位多由於因緣際會,與首都地位息息相關,所以他特別警告:“今則首都既已南遷。一市之中,大學林立,一國之中,大學更林立,北大不過許多大學中的一校,決不宜狃於已往的光榮,妄自尊大。”話中對北大的“全國最高學府”地位幾乎全盤否定。 2.“要以學術為惟一目的,而不要想包辦一切。”活動紀念中,學生們重點回顧與展望北大的歷史與使命,所希望者多從政治與學術並兼立論,對於北大人在社會上包辦一切相當自得。但蔡元培卻當頭棒喝,提出警告“要以學術為惟一之目的,而不要想包辦一切”。對於北大同人以前從事政治活動的歷史,蔡元培解釋為特殊情勢下不得已而為之的暫時行為,且犧牲太多,“從前在腐敗政府之下,服務社會者又不可多得,自命為知識階級的大學,不得不事事引為己任。若就求學目的說起來,犧牲未免太多,然在責無旁貸的時期,即亦無可如何。”現在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今則政府均屬同志,勉為其難;宣傳黨義運動民眾等事,又已有黨部負了專責。”故此,他提出北大人不能包辦一切,應專心治學,“我們正好乘黨政重任未尚加肩的時候,多做點預備的功夫,就是多做點學術上的預備。若此刻早已分心他事,荒棄學業,他日重任加身,始發不學無術的悔恨,就無及了。所以應守分工的例,不想包辦一切而專治學術。”④這實際上是委婉告誡北大人勿再斤斤於政治。 蔡元培先生之所以在北大三十一周年校慶之際,講了如此不太合時宜的話,實則對於北大此時的境況有一清醒的認識。事實上,至三十年代初,北大是一個各方面均亟待振興的大學。不僅由於首都遷移,北大作為“全國最高學府”的傳統地位受到來自中央大學的直接挑戰,且其他各國立大學快速發展,北大本身的辦學物質條件與人才資源相形見絀。 就經費而論,北方的清華大學以庚款為基金,校務發展迅速,建築設備均遠勝於北大,南方的中央、中山、武大在國民政府的扶持下,校園建設、經費撥付均優於北大。北大獨立後的經費還是自1919年以來的常數,即每月7.5萬元,每年經費為85萬元,到蔣夢麟接手時,“至今未改,故異常困難”⑤。而同期1931、1932年中央大學的經費預算達192萬元⑥,北大的經費尚不及中央大學的一半。北大獨立之初,其基礎設施已遠速落後於其他國立大學,僅就1931年當時國立大學的設備價值來看,國立武漢大學為910,070元,國立清華大學為511,096元,國立中央大學為436,342元,國立中山大學為186,084危,國立北平大學為105,350元,而國立北京大學僅有30,917元。⑦這表明北京大學的設備總值與其他國立大學相較差距甚遠。 就人才而論,當時南方受革命影響,風氣為之一振,北大的老教授受時局困擾,多南下或他就,北大名教授減少甚多。雖然陳大齊任上多次公開籲請北大老教授重回北大,無奈受制於經濟等因素,效果並不理想。就當時大學教員的工資水平而言,南方的待遇較北方優越。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在1927年6月公佈大學教員薪俸數目:教授月俸400元至600元,副教授260元至400元,講師160元至260元,助教100元至160元。而在北方,據國立京師大學校職員薪俸規程,教授月俸160元至300元,北方無副教授名目,僅有預科教授,倘其地位與副教授相同,其最高薪俸不過260元,等於南方副教授之最低薪,最低不過120元,助教月俸為20至30元。⑧這一情形在三十年代初蔣氏接手後並沒有多大變化,“那時候,北京改成了北平,已不是向來人才集中的文化中心了,各方面的學人都紛紛南去了。一個大學教授的最高俸給還是每月三百元,遠比不上政府各部的一個科長。”⑨這顯然對北大招引人才不利。 二、胡適的“妙計”:北大與中基會的合作計劃 1930年12月23日,在北大學生歡迎新校長蔣夢麟的大會上,蔣作了專門的演講,特別提到:“現北大最感困難者為聘教授,經費問題次之。”他作了這樣的解釋:“以前全國人才集中北大,大學不多,且未整頓,故北大易聘優秀教授。今各大學中多半為北大同人,黨政各界,均有北大同人插足。此種困難之點,諸君想可諒解。”⑩在動亂的年代裡振興北大,面臨外部的政治社會環境和內部經費人才的雙重壓力。就外部而言,蔣夢麟亦十分清楚大學與政治的關係:“政治腐敗,我們那裡能不談政治;既談政治,教育界那裡能不遭到政客的摧殘,仇視,利用。即退一步,我們可以不談政治,然而那裡不能主持公道?主持公道,即不公道的一班人,就與我們搗亂。”就內部而言,辦理大學多年的他十分清楚,要提高學術,“第一要工具,第二要人才”,“沒有經費怎麼辦得動”(11)。蔣夢麟上任後,首先面臨教授薪俸太低、學校經費不足且不穩、圖書設備無力擴充等困難。經費困難(政府的支持有限),人才難求,學風不振,蔣氏面臨如此困難,他力圖重振北大,所依靠也主要是五四新文化時期的老北大人了,特別是胡適、傅斯年等一批學界有影響力的自由教育者,蔣夢麟後來回憶說:“九一八事變後,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參謀’就是適之與孟真二位。事無大小,都就商於二位。他們兩位代北大請到了好多位國內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後之復興,他們兩位的功勞,實在是太大了。”(12)其實,在“九一八”之前,蔣夢麟著手對北大進行改革之初,就已經商量於胡適,在這一過程中,胡適所起的作用最大。 胡適三十年代初重回北大,個中原因頗為複雜,既有政治環境因素,亦有學術上的考量。就政治而言,二十年代後期,胡適放言政治,得罪國民黨要人,故而在上海期間,他受國民黨各派政治勢力包圍,甚至對其有圍剿之勢。(13)在此情形之下,離開上海這個國民黨統治的核心區域,尋求新的安身立命之所,亦屬常情。就學術而論,胡適在學術界的迅猛成長,與北大這一大平臺關係甚深。胡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暴得大名”緣自北大的舞臺,他並由此而成為北大新文化派的領袖。李璜回憶說,“適之自五四前後新文化運動以來,其在北大的影響力,七八年間還在繼續增高。並且他既任中美庚款分配於文化教育(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的董事,而在十五年又兼任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的委員,好象他比別人大有辦法,可以呼朋引伴,不免遭受嫉視。……並且適之提出一個‘北大人’的口號,以標榜北大為全國學術的中心,頗見其團結同事的技巧。”(14)正如研究者指出,自1920年代後半期開始,胡適的系列開風氣之先的著作遭到各派學人或隱或顯的批評指責,其學術領袖地位受到嚴重的挑戰。(15)此時考慮回到北大,恐怕或多或少欲借北大之力,重新領導學術思想潮流。1930年5月,胡適因在《新月》上借人權問題對國民黨當局進行批評,遭到官方組織的“圍剿”,被迫辭去中國公學校長一職。6月胡適因事北上,受到北大代理校長陳大齊及教授周作人等的歡迎,陳、周極力拉攏胡適返回北大。最終經不起蔡元培、蔣夢麟一班師友的勸說,胡適於11月28日攜眷離開上海,回到北大,並替蔣夢麟校長設計了一條北大復興的“妙計”。 正如傅斯年抗戰勝利後對胡適所言:“先生當年曾有一妙計,以中基會助北大,今日更須有妙計。惜中基會已不成也。”(16)傅所言的“妙計”即為中基會與北大合作的計劃,即中基會與北大每年各提出二十萬元,以五年為期,雙方共提出二百萬元,作為合作特別款項,專作設立研究講座、獎學金、專任教授以及購置圖書儀器和設備之用。 胡適提出北大與中基會合作的“妙計”,綠於他與中基會的淵源。中基會全稱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是1924年9月成立的專門負責接收、保管及支配美國第二次“退還”的庚子賠款餘額的專門機構。胡適早在1927年6月以來,就長期被選為中基會的董事。國民革命成功,國民政府對中基會的改組進行直接干預,胡適等自由派學者進行了抵制,但在國民黨的壓力之下,那些所謂反國民黨者和“與軍閥勾結者”包括顧維鈞、顏惠慶、張伯苓、郭秉文、周詒春等均被迫“辭職”,而與北大有淵源的胡適、蔡元培、蔣夢麟、李石曾等在中基會的聲勢更大,這也是後來中基會三十年代與北大合作的人事基礎。1929年6月29日,在天津舉行中基會董事會年會上,胡適被舉為董事,並任書記,(17)此後日漸成為其中的要角。 在1931年中基會開會之前,胡適為首的北大人就已積極活動,從胡適留下的日記中可以看出其活動之頻繁與用心之良苦。他基本上分三步實現中基會與北大的合作:第一步,爭取中基會董事對北大表示“同情”。1931年1月7日,胡適運動任鴻雋與中基會美國董事顧臨談及北大補助案一事,“叔永已與Greene[顧臨]談過北大補助案事,他也很同情。”(18)8日,“九點半去看Mr.Greene[顧臨先生];在旅館見著金陵女大校長吳貽芳女士,又見著Dr.Stuart[斯圖亞特博士],Stuart贊成北大補助案。”在胡適與美國董事顧臨協商後,得到顧的支持,可以說中基會決定補助北大一事在會前已經決定好了。第二步,使其計劃成為中基會與北大“合作”而非資助,以免去其他機構的藉口。胡適“妙計”關鍵的一步,就是力勸校長蔣夢麟從北大校方經費中拿出相當款項共同合作,而蔣夢麟當初對於北大每年劃出二十萬元還心存疑慮,8日胡適早起與蔣夢麟談,“大家勸他主張北大也拿出二十萬元來,使以後別的機關不容易藉口”,在胡適等人的勸說下,最初猶豫的蔣夢麟終於答應。(19)第三步,是在中基會年會上由與北大關係並不密切的美國董事顧臨提出此案,而不由其他與北大有密切關係者提出,而且作為董事的北大校長蔣夢麟為避嫌則回避,以對外界有一交待。胡適的考慮十分周全,他在日記中詳細記載了他這一“妙計”實施的過程,事情的發展也一步一步照其計劃順利進行,難怪傅斯年等人十餘年後重提出這一計劃時,稱為之“妙計”,十分自得。 1月9日中基會在上海開第五次常會,顧臨出面提議中基會與北大的合作計劃,由於事前進行了廣泛的溝通,會上順利通過,決定中基會每年捐助北京大學二十萬元,北大以同樣的經費一起合作,為期五年,專作延聘研究講座專任教授之用。10日晚,胡適草擬北大補助案對外談話稿,寫成已近深夜兩點,足見其重視與苦心。(20)11日,作為中基會名譽秘書的胡適對外發表談話,特別說明“此次常會中,美國董事顧臨君提議,自民國二十年度起,由基金會每年提出國幣二十萬元,贈與國立北京大學,以五年為期,專作設立研究講座及專任教授之用。”其條件主要有三項:(一)基金會與北京大學每年各提出二十萬元,共四十萬元,作特別款項,以五年為期。(二)此款之用途有五項:甲、設立研究講座,每座年俸自六千元至九千元;乙、設立專任教授,每座年俸自四千八百元至六千元;丙、每一講座教席各附有相當之書籍設備費。丁、設立助學金額,以援助苦學之高材生;戊、設立獎學金,為獎勵研究有成績之學生在國內或國外作高深研究之用;(三)上項研究講座及專任教授,皆須全力作學術研究及指導學生作學術研究,不得兼任校外有給或無給之教務或事務。” 胡適強調“蔣董因避嫌自請退席”,並申明:“上項合作辦法之用意,在於指定一個有歷史地位之大學,試辦大學教育之根本救濟。”並特別說明設立講座與專任教授的理由主要在於“今日之大學教育有三層最大困難”:一為教授俸給太低。國立大學的教授月俸,尚不如政府各部一科長。北大教授最高月俸只有三百元,故人人皆靠兼差以自給。二為學校經費不固定,貧士不敢依賴一校的俸給以為生活。三為學校經費十之七八用在薪俸,無餘財以購置書籍儀器,故雖有專門學者,亦不能專力作高深之學術研究。“上項辦法,意在提高教授俸給,擔保經費之固定,並充分擴充書籍儀器之設備,一舉而三層困難皆可解決。”胡適估計此案成立之後,可設立:九個平均年俸七千元之講座;十五個平均年俸五千四百元之專任教授;十五個每年二百元之助學金額;十五個每年六百元之獎學金額;兩個每年一萬元之留學研究生額。其餘之二十餘萬元,則作為購置書籍儀器及整頓圖書館試驗室之用。五年之中,合計有二百萬元,專作提高學術研究之用。胡適最後強調:“試辦雖限於北大一校,其影響所及,必將提醒全國各大學急起直追,與北大為學術上之競爭。”(21)揣摩胡適此語,他樂觀估計此計劃實施後,北大又可引導潮流,成為真正的“最高學府”了。 中基會與北大合作特款在1934年稍作調整,時間延長至1937年止(較原議延長了兩年),中基會此後每年改撥10萬元,而北大每年仍撥20萬元。最終因時局影響,合款提前一年結束,1936年的款項亦未撥足,不過至1936年底,合作特款共支用195萬元,與原計劃的總款相差無幾。(22)這一筆鉅款正是北大三十年代“中興”的經濟保障基礎。北大在三十年代能夠集中大批一流人才,中基會的特別補助費是關鍵。應特別指出的是,三十年代北大“中興”的動力不是官方扶持,而是來自民間色彩甚重的經濟法團組織。其成功實得益於北大在而五四後建立起來的強大的人脈關係網絡,這集中反映出在國民黨上臺後教育格局變動下北大人的因應之道。 有了中基會的款項,胡適等人便放手聘請教授來北大了。1931年1月中基會第五次常會後,幹事長任鴻雋及北大校長蔣夢麟共同聘定胡適、翁文灝、傅斯年、陶孟和、孫洪芬為顧問委員,負責議決教授人選以及各項經費的分配,其中胡適起了主導作用。這也是蔣夢麟對胡適、傅斯年所言“聘請新教授‘你們’來做,辭退舊人由‘我’來做。”不過“夢麟此時尚不願與舊人開火,故此時文科事,夢麟主張暫時擱一擱再說。”(23)所以胡適等人最初的工作主要是聘“新人”。 值得注意的是,胡適等人請回的主要是老“北大人”,即主要以北大老教授、尤其是以新派教授為主。胡適可謂馬不停蹄地到處“挖角”。1931年1月8日汪緝齋來與胡適談,他不願在中山大學受氣,胡適勸他回北大,努力造一個好的心理學實驗室。(24)是月11日胡適到中央研究院,“約了西林、仲揆談話,後來周鯁生也來了。他們都願意回北大,但事實上有困難,故這次談話無結果。(我本想勸西林即回北大去辦理科)”(25)此事因為是在挖中央研究院的人,引起了院長蔡元培的不滿,2月20日蔡元培專門致函胡適,稱“北大講座人選由先生各方接洽,必無才難之嘆,乃必欲拉及巽甫仲揆諸君,不免使研究院為難;務請與夢麟兄從長計議,使各方面均過得去為妙。”(26)最終,“中央研究院地質所主任李四光已允來校,蔡先生(元培現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因關心北大教務,允借教授一年。”(27)北大與中央研究院以二人兼職來協調。是月27日胡適親赴青島,“晚上先在金甫家,與實秋、一多、金甫談。金甫肯回北京大學,並約聞梁二君同去。所躊躇者,青島大學不易丟手。我明天到濟南,當與何思源兄一商。”(28)2月7日,“趙太侔來談,他不願楊金甫來北大。”(29)儘管楊振聲願攜聞一多、梁實秋同去北大,但北大方面胡適尚不能完全左右人事,主要是因為蔣夢麟剛接手北大校長,不願樹敵太多,此時也不願拿“舊人開火”,此事暫時作罷。 經過胡適等人半年多的接洽,北大最終確定了研究教授的名單。1931年8月5日北大中基會合作研究特款顧問委員會開第一次正式會,到會者有蔣夢麟、任叔永、翁詠霓、陶孟和、傅斯年、孫洪芬、胡適。推定蔣夢麟為委員長,孫洪芬為秘書。通過聘請下列十五人為研究教授:汪敬熙(心理學)、王守競(物理)、曾昭掄(化學)、劉樹杞(化學)、馮祖荀(數學)、許驤(生物)、丁文江(地質)、李四光(地質)、劉志揚(法學)、趙迺摶(經濟)、周作人(國文)、劉復(國文)、陳受頤(史學)、徐志摩(國文)、湯用彤(哲學)。(30)此後五年中,還陸續添聘了江澤涵、薩本棟、謝家榮、張景鉞、饒毓泰、朱物華、葛利普(A.W.Grabau)、斯柏納(E.Sperner)、奧斯谷(A.W.Osgood)、張頤、葉公超、張忠紱、吳寶良。這份名單中,其中九人於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有研究者認為,這相當於五年之內為北大引進近30位“院士級”學者,北大何愁不中興。(31) 這份名單主要集中反映了蔣夢麟、胡適等人的意見,尤其是胡適“集一時之選”重振北大的雄心,後來胡適對此亦頗為自豪,“蔣氏自擔任恢復北大後,經九個月的籌備,在民二十年九月十七日開學。延聘全國有名學術名宿,故開學後,立刻恢復以前的校譽。”(32) 三、文學院的改革:聘新人與辭舊人 胡適等人在設計北大復興時,專門提到學術提高對於北大的意義。1930年11月3日回北大前夕他在日記中寫道:“其實北大此時已無大希望,只有研究院可以有一線希望。”(33)為此,他專門商請蔡元培擔任北大研究院院長,以此號召老教授重返北大。1931年9月14日北大開學,胡適專門作了演說:“北大此前只有虛名,以後全看我們能否做到一點實際。以前‘大’,只是在矮人國裡出頭,以後須十分努力。”對於學術獨立問題,他專門提到陳垣曾對他所言,“漢學的正統此時在西京呢?還在巴黎?”他們相對嘆氣,盼望十年之後也許可以在北京,“今日必須承認我不‘大’,方可有救。”(34)胡適在北大開學典禮上重提此事,用意在激起北大人在學術上努力提升。 不過在胡適眼中,何謂學術,如何提高,也有側重點,甚至有其個人的私意。錢穆回憶說:“余初到之年,北大歷史系第一次開會,適之為文學院長,曾言辦文學院其實只是辦歷史系。因其時適之已主張哲學關門,則哲學系宜非所重。又文學系仍多治舊文學者掌教,一時未能排除……此見當時學術界凡主張開新風氣者,於文學則偏重元明之下,史學則偏重先秦以上,文史兩途已相懸絕。其在文學上,對於白話文新文學以外,可以掃蕩不理。而對於史學,則先秦以下,不能存而不論,但亦急切難有成就。於是適之對北大歷史系之興趣,亦遂逐漸減輕。”(35)這段觀察大體可以看出胡適辦理北大文學院的主張,透露出幾層重要信息:哲學非胡適所重,文學則以白話新文學為尚,史學則先秦為主,後者與前期整理國故運動有相當的延續性。 1931年胡適擔任北大文學院長時,“主張哲學關門”,這和傅斯年主持中山大學文學院時“廢哲學”的主張有其相似的地方。(36)1929年胡適在日記中道:“哲學的根本取消:問題可解決的,都解決了。一時不能解決的,如將來有解決的可能,還得靠科學實驗的幫助與證實。科學不能解決的,哲學也休想解決;即使提出解決,也不過是一個待證的假設,不足以取信於現代的人。”(37)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畢業的胡適,竟主張關閉哲學系,這的確讓人費解,研究者王汎森認為或許是與傅斯年的共鳴,認為所有哲學皆該消滅,並認為中國沒有哲學是一件值得慶倖的事情。(38)在這一指導思想下,在北大的講座教授聘任中,畢業於英國愛丁堡大學(一說牛津大學,待考)的哲學博士張頤沒有通過,湯用彤還專門為此給胡適去信,為之鳴不平,並敦請胡適設法“轉圜”(39),此事後來未成,張頤沒有成為第一批講座教授。 國文系的人員聘請,胡適認為學術只是求其新,所有北大聘請的人員當以新為主。胡適力薦徐志摩即是明顯一例。1931年初,胡適欲聘請新月詩人徐志摩為北大講座教授,徐志摩本人卻自認不是學者,心存疑慮,頗不自信,“北大我當然願意,但不知要我教什麼課程,也不知是否基金的位置,我有資格承當不,錢有多少,我都得知道。”(40)到了8月,徐志摩收到北大講座教授聘書,仍然不安,“基金講座的消息轉教我發愁。你是知道我的,我不是個學者,教書也只能算是玩票,如今日要我正式上臺我有些慌。且不能說外面的側目,我確是自視闕然,覺得愧不敢當。我想辭,你以為怎樣,老大哥?講座的全部名單報上有發表否,文科另有哪幾位?”(41)徐志摩自認為不是學者,且對於文科另聘何人十分關心,底氣不足可以想見。雖然胡適本人清楚徐志摩的學問功力有限,認為“志摩之選,也頗勉強”,但最終還是力排眾議,堅持聘請徐為講座,除了私交的因素外,更主要的恐怕還是借助新派力量進入國文系,達到逐步改造北大國文系的目的。 1934年4月,胡適打算請梁實秋擔任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專門致信梁:“北大文學院現在又要我回去,我也想費一年工夫來整頓一番,最苦的是一時不容易尋得相當的幫忙的人。我常想到你,但我不願拆山大的台,不願叫太侔為難。現在山大已入安定狀態了,你能不能離開山大,來北大做一個外國文學的研究教授?研究教授月薪五百元,教課六點鐘,待遇方面總算過得去,但我所希望者是你和朱光潛君一班兼通中西文學的人能將北大養成一個健全的文學中心。”(42)看來,胡適對梁期望甚高,欲借梁這樣的“新人”在北大重建“新文學中心”。不過,傅斯年卻不以為然,認為梁不過是“浮華得名之士”,並非“新才”,他專門致信校長蔣夢麟,對胡適舉薦梁實秋提出異議:“梁實秋事,如斯年有贊成之必要,謹當贊成。若詢斯年自己見解,則斯年疑其學比行皆無所底,未能訓練青年。此時辦學校,似應找新才,不應多注意浮華得名之士,未知適之先生以為何如?”(43)不過胡適的意見還是起主要作用,5月此事即已確定下來,胡適致梁實秋信中說:“研究教授事,我已與夢麟商量過,當無問題;現在因‘北大中基會合款顧問委員會’尚未開會,故未正式通過。……我感覺近年全國尚無一個第一流的大學文科,殊難怪文藝思想之幼稚零亂。此時似宜集中人才,匯於一處,造成一個文科的‘P.U.M.C’。四五年至十年之後,應該可以換點新氣象。”(44)顯然有意將北大文科辦得象美國普林斯頓、麻省理工之類的學術中心。 不過此事一波三折,6月胡適致函梁實秋,對其不能來北大頗為失望:“你的信使我們大失望。我已經與蔣校長商量三次,終不能得妥善辦法。因為我們今年急需你來幫忙,所以得你同意後即不曾作任何準備。倘此時你不能來,我們本年非得另尋一個相當的人不可,而此時在國內那兒去尋一個比得上你的人來救我們之急!(這不是灌米湯!!)你能否向山大告假一年,先來北大?如一年之後山大還非你回去不可,你再回去。如一年之後,山大已得人,可以不需你回去,你就可以繼續留下去。如此辦法能得太侔兄允許否?金甫今天也來說此事,我更為難。我曾對他說:‘此時北大困難是這樣的:今年我們需要一個頂好的人;如實秋不來,我們也得尋一個勉強比得上他的人。此人如是好的,一年之後就不便辭他。此人若是不好,我們今年就要有大麻煩。這邊(北大)辭退一個教授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所以我們不願輕易聘教授來代替實秋。’”(45)胡適之所以急迫地想拉梁實秋來北大,其目的如同梁實秋後來回憶所言:“北大除了教授名義之外,還有所謂名譽教授與研究教授的名義,名譽教授是對某些資深教授的禮遇,固無論矣,所謂研究教授則是胡先生的創意,他想借基金會資助吸收一些比較年輕的人到北大,作為生力軍,新血輪,待遇比一般教授高出四分之一,授課時數亦相當減少。……我的用意在說明胡先生主北大文學院的一番抱負。”(46)這個抱負就是要以新文化來重建學術中心。 三十年代蔣、胡、傅等借重中基會和中研院的合作,努力解決經費與人才的問題,謀求北大的“中興”。不過當時聘請新人不易,辭退舊人則更有相當難度。連胡適本人也說“奪人飯碗”是其不願做的事。早在1931年2月蔣夢麟長校後對北大制度進行改革,設立院長制,而北大文學院舊人則借助前代理校長陳大齊擔當院長來排斥胡適,胡適致好友楊振聲的信中說得清楚不過:“夢麟因百年交卸校長後即無位置,故曾約他任文科主任,他未允接受。此次夢麟決計改院長制不能不先請他做文科院長,他仍未允。但一班舊人怕飯碗不牢,故卅一日曾包圍夢麟,反對院長。及見反對不了,便又求請百年任文科院長。但此時百年尚不允,以後尚不可知。……文科院長,我極希望你能來幹。孟真則不願你離開青大,夢麟此時尚不願與舊人開火。故此文科事,夢麟主張暫擱一擱再說。”(47)真正對於北大舊人的改造則在1934年,胡適以辭退舊人來解決北大文學院中“浙人”長期把持而不得進步的局面。 對於自五四運動以來北大為浙人把持的現象,也多為當時其他學者私下痛批,楊樹達在日記中多次對北大文科由浙人把持的局面表示強烈不滿。(48)1929年1月25日楊樹達又提及陳垣的不滿:“談及北平教育界情形,援庵深以浙派盤據把持不重學術為恨。於此知天下自有真是非,宵小之徒不能掩盡於下人耳目也。”(49)整體而言,蔣夢麟出掌北大之前,北大文學院為浙人所控制。1928年至1931年在北大以旁聽生名義進修的吉川幸次郎,對當時的北大文學院教授80%為浙江人以及北大浙人與外部非浙人的矛盾衝突印象深刻。(50)更為嚴重的是,這種現象造成學術上不進步的局面,即真才實學、著述宏富者進不了北大國文系。如1925年6月1日楊樹達就為吳承仕不為北大所接受而鳴不平:“檢齋為章門高第弟子,學問精實。其同門多在北大任職,以檢齋列章門稍後,每非議之;實則檢齋學在己上妒忌之故。一日,余以請吳任教告同事馬幼漁教授。馬云:‘專門在家著述之人,何必請之!’馬君固列章門下,十年不作一文者也。”(51)顯然“十年不作一文”與現代大學格格不入。 1934年胡適等在北大國文系實行課程改革,其中心就是“以研求純文藝為主”,這其中涉及到人事難題,就是通過辭退舊人、引進新人來完成。上文中胡適力爭梁實秋來北大即是引進新人的一例。當時決定辭退的舊人有國文系林損、許之衡,並波及國文系主任馬裕藻。4月,當林損得知下學期沒有聘任他時,反應十分激烈。16日下午林損自己到北大公報欄揭一帖,自言已停職、學生不必上課,並分別致函校長與文學院院長質問。其中致蔣夢麟函稱:“自公來長斯校,為日久矣,學生交相責難,瘖不敢聲。而校政隱加操切,以無恥之心,而行機變之巧,損甚傷之。”(52)致函胡適稱:“損與足下,猶石勒之與李陽也。鐵馬金戈,尊拳毒手,其寓於文字者微矣。傾聞足下又有所媒孽,人生世上,奄盡罹之。教授雞肋,棄之何惜。敬避賢路,以質高明。”(53) 當天胡適回信林損:“今天讀手書,有‘尊拳毒手,其寓於文字者微矣’之論,我不懂先生所指的是那一篇文字。我在這十幾年中,寫了一兩百萬字的雜作,從來沒有一個半個字‘寓’及先生。胡適之向來不會在文字裡寓意罵人。如有罵人的工夫,我自會公開化的罵,決不用‘寓’也。來信又說:‘頃聞足下又有所媒孽’,這話我也不懂。我對人對事,若有所主張,無不可對人說,何必作‘媒孽’工夫?來函又有‘避賢路’之語,敬聞命矣。”(54)胡適之所以辭退林損,依照傅斯年等的解釋,似乎主要還是新舊之爭,其實還有林損自身原因,正如胡適晚年所講:“公鐸的天份很高,整天喝酒、罵人、不用功,怎麼給人家競爭呢?天份高的不用功,也是不行的,章太炎、黃季剛,他們天分高,他們是很用功的啊。”(55)與林公鐸私交不錯的劉半農在日記中亦有公論:“以私交言,公鐸是余來平後最老同事之一,今如此去職,心實不安,然公鐸恃才傲物,十數年來不求長進。專以發瘋罵世為業,上堂教書,直是性(信)口胡說,咎由自取,不能盡責夢麟也。”(56)這種客觀評論則可反映出胡適辭退林損等舊人是符合現代大學學術要求的公允標準。 林損對外稱自己辭職原因,“係與蔣(夢麟)胡(適之)兩先生學說不同”,(57)只言及學術觀念的衝突,甚至還有個人的恩怨在其中。其實,在筆者看來,觀念與個性二者兼而有之,正如時在北大念書的張中行先生所言:“林先生傲慢,上課喜歡東拉西扯,罵人卻是有懈可擊。但他發牢騷,多半是反對白話,反對新式標點,這都是胡博士提倡的。自己有了權整頓,開刀祭旗的人是反對自己最厲害的,這不免使人聯想到公報私仇。”(58)時國文系主任馬裕藻向報界說明,“此次國文系改革問題,一方固屬思想問題,他方面又為主張問題”,他特別指出,“大學則不應思想統一,必須新舊並用,始能獲得研究結果。”(59)言下之意對於胡適以新排舊相當不滿,劉半農4月20日的日記有如下記載:“到馬幼漁處小談,夢麟已決定辭退林公鐸、許守白二人,並以適之代幼漁為中國文學系主任,幼漁甚憤憤也。”(60) 辭退林損之所以引起大的風波,一方面固然反映出北大多年來文科中新舊兩派之間的積怨與衝突,另一方面在於外界輿論的介入。周作人回憶稱“在民國三十年頃北大改組時標榜革新,他(指林損——引者注)和許之衡一起被學校所辭退了。……他大寫抗議文章,在《世界日報》上發表的致胡博士(其時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的信中,有‘遺我一矢’之語,但是胡適之並不回答,所以這件事不久就平息了。”(61)當時《北平晨報》、《申報》都對北大校內這場人事糾紛加以報導,故引起社會上的廣泛關注。 身為北大新文化派主將的傅斯年仍不滿蔣、胡的人事改革不徹底,尤其是不滿馬裕藻尚保留教授一職。他先後致信胡適與蔣夢麟,談及國文系問題如何徹底解決。傅斯年4月28日致胡適函稱:“在上海見北大國文系之記載為之興奮,今日看到林撰小丑之文,為之憤怒,恨不得立刻返北平參加惡戰,可已如此。”傅將此事形容為“惡戰”,可見其心目中北大新舊之間的關係勢同水火,傅斯年認為這是因為校長處置不力,“想孟麟先生不得不快刀斬亂麻矣”,並表示“此等敗類竟容許其在北大,如此小人,亦吾等一切人之恥也。”在傅斯年看來,“此輩之最可惡者,非林而實與彼借新舊不同之論而欺人”,所以他大膽反問“試問林與諸醜於舊有何貢獻?”最終的結論是:“此小戀棧之惡計,下流撒謊之恥態耳。”所以才有“越想越氣,皆希努力到底”。(62) 傅斯年言辭之所以如此激烈,一方面反映出他對於舊派的不容忍,另一方面反映出學術上人事更替與學風的轉移。林損事件並非單純一個教授被辭退之事,而是有更深的內涵:一則事關當時北大改革中大學教師的學術評價標準;二則關係到民初以來北大教授群體中的派系力量在新形勢下的分化組合。自此,五四時代著名的“三沈二馬”,經過這場風波,馬裕藻最後也被胡適擠了下來,由胡自兼中國文學系主任,沈亦不安於位,到輔仁大學去擔任文學院長,在北大改任名譽教授,聊以保持一點關係。(63)胡適對於北大國文系的人事改革大功告成。 三十年代胡適重返北大後,成為校長蔣夢麟最重要的支持者和參謀者。在缺乏政府扶持的前提下,胡適長袖善舞,運用五四後北大派的勢力,充分借助中基會這一平臺,實施了北大與中基會的合作計劃,成功解決了北大改革的經費瓶頸難題。正是在胡適等的運作之下,北大通過聘新人辭舊人的方法,完成了現代學術的轉型,實現了北大三十年代的“中興”,在這一過程中,胡適居功至偉。胡適等在北大改革的成功,歸功於“北大派”的勢力,正如有研究者評論說:“在民國教育史上,隱然存在一個‘北大派’。蔡元培、蔣夢麟、胡適以及傅斯年等人打通北大和中央研究院,掌控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等實力部門,其影響非同尋常。”(64)有研究者稱,在那樣一個時代,成為“學霸”或“學閥”必須有學術以外的網絡、綿密的政府關係,同時與僅有的一些基金會如中基會及中英庚款董事會保持密切的關係。(65)胡適這樣的學術文化精英,正是憑藉這一學術之外的社會網絡,完成了三十年代北大的改革。 對於北大三十年代的改革成效與評價,圈內與圈外頗為不同。當事的要角胡適本人對這場改革頗為自許,1946年10月10日胡適在北大開學典禮上演講,專門講到北大三十年代的“中興”,“現在北大能有這樣的規模,都是那時蔣氏所籌劃的。所以這個時期,可稱為‘中興時期’。蔣氏自擔任恢復北大後,經九個月的籌備,在民二十年九月十七日開學。延聘全國有名學術名宿,故開學後,立刻恢復以前的校譽。可是開學的第二天,東北‘九一八’事變發動,日本揭開了侵略的真面具。從此平津地區師生都預感失掉了安心讀書的機會。所以自蔣氏長校後至‘七七’事變,雖然北大中興時期,亦為最困難時期。不過雖然處在這樣的環境中,北大仍借中華教育基金的一筆鉅款,建築了宿舍、地質館和圖書館等。所以在此時期,困難固然最大,工作也最多。”(66)顯然,胡適對這一時期北大的中興努力與成績十分看重。同樣,蔣夢麟後來亦將胡適與蔡元培相提並論,稱其是“北大的功臣”(67),他在回憶錄中,對這場改革的成效有一總結:“一度曾是革命活動和學生運動漩渦的北大,已經逐漸轉變為學術中心。”(68) 與北大派內部的自我肯定相比,當時社會上對此評價卻不一。1933年魯迅給台靜農的信中,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北大老同事、老朋友的變化,至為不滿,認為這是北大精神的衰落,下語極重:“北大墮落至此,殊可嘆息,若將標語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時代在前面’,則較切矣。”(69)在魯迅看來,蔣、胡對北大的改革,已失卻了北大的精神。就北大精神而論,五四時期代理北大校務的蔣夢麟有一總結,稱“北大之精神”內涵有二:“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70)此時在魯迅看來,蔣、胡對北大的改革,不僅失去了“包容”,也失去了“自由”,所以才會有“五四失精神”、“時代在前面”的尖銳批評。 魯迅冷峻的批評,實則道出了胡適改革北大背後學術派分的深意。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北京大學與東南大學在學術文化上立異,形成了二十年代中國學術文化上的“雙峰對峙、二水分流”的格局。二十年代中期以來,北伐、遷都等系列重大政治格局的變動,因政治中心南移,東南大學的繼續者中央大學一躍而成為首都最高學府,地位日益提升。在這一大背景之下,胡適通過北大改革(尤其是對北大文學院的改革),使北大日益成為新文化派的重要陣地,從北大排擠出來的老派教授如黃侃、朱希祖、林損等紛紛轉移陣地到了南京的中央大學。胡適改革北大的目的顯然是要維繫北大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形成的地位,進而強化了南北新舊二京的中央大學和北京大學之間學術文化多方面的競爭,從而為這場大學改革打上深深的地緣與派分烙印。因此,三十年代胡適在北大的改革,亦成為後人不斷指認民國學分南北的重要表徵了。 ①參見拙作:《北伐前後北京的國立大學合併風潮(1925-1929)》,廣州:《中山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 ②《整頓學風》,天津:《大公報》,1930年12月8日。 ③胡適是近年學術界研究的熱點民國人物之一,有關胡適與北京大學的討論,重要論文有歐陽哲生的《胡適與北京大學》(北京:《北京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探討了五四時期、三十年代及內戰時期胡適與北大的關係,提出北大自由主義的傳統與胡適有重要的關聯的觀點。 ④以上所引均見蔡元培:《國立北京大學卅一周年紀念刊序》,北平:《國立北京大學卅一周年紀念刊》,第7~8頁,1929年12月17日。 ⑤《北京大學大裁員》,北平:《北平晨報》,1932年9月10日。 ⑥詳見羅家倫:《兩年來之中央大學》,收入《南京大學百年實錄》上卷《中央大學史料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316頁。 ⑦《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丙編,上海:開明書店,1934年,第34頁。 ⑧《南北教員薪俸之比較觀》,天津:《益世報》,1927年9月22日。 ⑨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7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93頁。 ⑩《北大學生會昨開迎蔣大會》,北平:《京報》,1930年12月24日。 (11)蔣夢麟:《過渡時代之思想與教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第189頁。 (12)(67)蔣夢麟:《憶孟真》,台北:《中央日報》,1950年12月30日。 (13)詳見羅志田:《再造文明的嘗試——胡適傳(1891-1929)》,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97~301頁。 (14)李璜:《回國任教對當時學術界的觀察》(《學鈍室回憶錄》第七章),台北:《傳記文學》,第21卷第5期,1972年11月。 (15)桑兵:《橫看成嶺側成峰:學術視差與胡適的學術地位》,北京:《歷史研究》,2003年第5期。 (16)(62)歐陽哲生編:《傅斯年全集》,第7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95、129頁。 (17)耿雲志:《胡適年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1頁。 (18)(19)(20)(21)(24)(25)(26)(28)(29)(30)(34)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6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8、12~14、12~14、6、9、69、45、53、141~142、152頁。 (22)楊萃華:《中基會對科學的贊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142~143頁。 (23)(47)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541~542頁。 (27)《北大三院平均發展蔣夢麟昨日之重要談話》,北平:《北平晨報》,1931年4月26日。 (31)章清:《“學術社會”的建構與知識分子的“權勢網絡”——〈獨立評論〉群體及其角色與身份》,北京:《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 (32)(66)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97~498頁。 (33)(37)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5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41、429頁。 (35)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169頁。 (36)胡適對“哲學”一詞的理解有其個性色彩,參見歐陽哲生《中國近代學人對哲學的理解》一文的第二部分,北京:《中國哲學史》,2006年第4期。桑兵教授曾當面提示,傅斯年對於“哲學”的理解與胡適有很大的不同。 (38)(65)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5~306、337頁。 (39)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531頁。 (40)(41)虞坤林編:《志摩的信》,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年,第289、296頁。 (42)(44)(45)(54)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中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615、620、621~622、614頁。 (43)歐陽哲生編:《傅斯年全集》,第4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0頁。 (46)朱文華編:《自由之師——名人筆下的胡適 胡適筆下的名人》,上海:東方出版社中心,1998年,第90頁。 (48)(49)(51)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5、43、45、57、63、70、72頁;第70頁:第26頁。 (50)參見自桑兵:《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北京:《歷史研究》,1999年第3期。 (52)《林公鐸致蔣夢麟書》(原整理者將時間定為“1934年夏”,不很準確,根據《申報》1934年4月19日《北大教授糾紛林損與胡適意見衝突而辭職》一文,其致校長函中有“以無恥之心”等語,當知即此函,故時間當在4月19日前幾日,與致胡適的信應為同期),張憲文整理:《林公鐸藏札二十九通》,北京:《文獻》,1992年第3期。 (53)《林公鐸致胡適書》(原整理者把此函時間定為1934年夏,不甚準確,據胡適的回信,具體時間為4月16日之前幾日),張憲文整理:《林公鐸藏札二十九通》。 (55)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09頁。 (56)(60)劉小蕙:《父親劉半農》附錄《劉半農日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62頁。 (57)《蔣夢麟否認裁併學系》,北平:《北平晨報》,1934年4月18日。 (58)張中行:《負暄瑣話》,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5頁。 (59)《北大主任馬裕藻談國文系糾紛內幕情形 係急進與緩進改革主張不同》,北平:《京報》,1934年4月25日。 (61)周作人:《知堂回想錄》,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51~552頁。 (63)陳平原、夏曉虹編:《北大舊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140頁。 (64)張曉唯:《舊時的大學和學人》“自序”,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6年,第2頁。 (68)蔣夢麟:《西潮·新潮》,長沙:岳麓書社,2000年,第200頁。 (69)參見錢理群:《“北大精神”與北大“失精神”》,《學人》第13輯,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17頁。魯迅類似的批評還有不少,錢理群認為是身居高位的教授與年輕學人之間發生了“新的奴役”,與現代大學在建立新體制中,規範化知識生產所產生的保守性文化品格有關。參見蔣夢麟:《西潮·新潮》,第17~18頁。 (70)蒋夢麟:《北大之精神》,北平:北大總務部日刊課二五紀念冊編輯處:《北京大學二十五周年紀念刊》,1923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