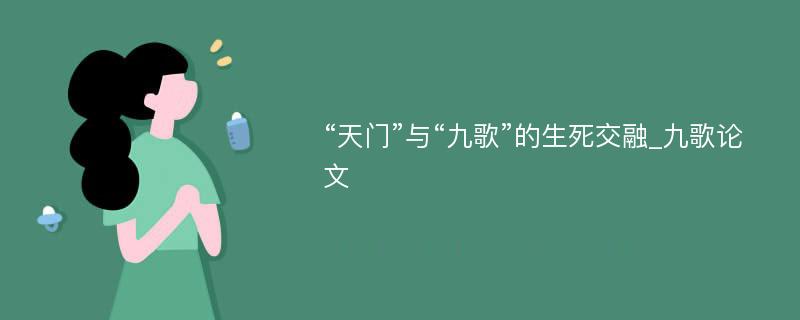
“天门”与《九歌》二司命的生死交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门论文,生死论文,九歌论文,二司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4)06-0108-04 屈原《九歌》组诗中有《大司命》《少司命》二篇,篇中所言或以为是人神关系,如王逸注以为写的是屈原对二司命的请求,《大司命》是屈原“要司命”“配神俱行”“冀得陈己情”,《少司命》是“屈原言己无新相知之乐,而有生别离之忧也”。朱熹注以为写的是巫师娱神,“大司命阳神而尊,故但为主祭者之词”。“少司命亦阳神而少卑者,故为女巫之言以接之”。或以为是写神与神之间的关系,明汪瑗《楚辞集解》以为二司命是相当于父子关系的神灵,“《大司命》《少司命》固可谓一篇,如禹、汤、文、武谓之三王,而文、武固可谓一人也。”“二司盖其职相同,犹文、武之其道相同,大可以兼小,犹文、武父可以兼子,固得谓之一篇也。”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以为《大司命》《少司命》“近似‘国风’中的恋歌”[1](346),姜亮夫认为“《大司命》和《少司命》配成夫妇神”[2](82)。虽然人们对二司命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猜测,但二司命同为天神,大司命主“寿夭”,少司命主“幼艾”,这样的认识是有共识的。本文以为,二司命是生、死观念的神格化,《大司命》《少司命》描写了通过天门所实现的生死交融,揭示了生命活动的道德价值。 一、战国人与汉代人观念中的“天门”不同 《大司命》首句“广开兮天门”,洪兴祖补注引《淮南子·原道训》东汉高诱注云:“天门,上帝所居紫微宫门也。”《淮南子》原文,用“经纪山川,蹈腾昆仑,排阊阖,沦天门”来写“冯夷、大丙之御”技艺高超,其中的“阊阖”是“始升天之门”,位于“昆仑之丘,实惟帝之下都”(《山海经·西次三经》)。而“天门”是“紫微宫门”,处于星空紫微垣内。高诱注与王充《论衡·道虚》“天之门在西北,升天之人,宜从昆仑上”的说法相呼应。但以天门为紫微宫门,这不是战国时代的看法,而是汉武帝开发西域时代形成的新观念。战国至秦,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秦始皇等主要向东方海上求仙。到汉武帝才把求仙领域扩展到内陆的名山大川,祭祀足迹“遍于五岳、四渎”(《史记·封禅书》)。元朔三年,张骞从匈奴逃回汉朝,向汉武帝详细地汇报了西域的情况,其中谈到“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也”(《汉书·西域传》),汉武帝对于西行寻访西王母仙迹产生了极大兴趣。在王煜等学者看来,汉武帝崇祀太一神、伐大宛得天马等活动都与登昆仑成神仙的追求有关[3]。武帝时所作《郊祀歌·天马》云:“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其中确包含有驾天马登昆仑求仙的意图。汉代人认为,天门的形状为双阙状,《神异经·西北荒经》云:“西北荒中有二金阙,高百丈,金阙银盘,圆五十丈。二阙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径三丈,光照千里。中有金阶,西北入两阙中,名曰天门。”出土文物中有天门的画像,作双阙状,与文献记载一致。重庆市巫山县20世纪80年代出土东汉鎏金铜牌14件,其中5件铜牌中央有榜题“天门”二字,两侧为双阙,下方端坐神仙西王母,周围有青龙、朱雀、白虎、三青鸟、九尾狐等神兽,空隙处布满云纹。同类铜牌在甘肃成县博物馆有发现。1988年,四川省简阳县鬼头山出土东汉墓画像石棺,“石棺右侧正中是天国的入口——天门,隶书‘天门’二字,纵写于画面正中上方。天门为双阙左右两阙形制相同,均为单层,阙身上窄下宽,阙顶为四阿房殿式,正脊上各有一凤鸟,长尾上翘,相对伫立栖息,以示祥瑞。两阙楼阁间有长廊相连,形成门状。大门正中,有一人头戴高冠,身着长袍,拱手肃立作迎谒状。阙右侧有‘大可’二字,可能为‘大司’的略写。”[4]这些文献和文物证明,高诱的天门注符合他所处时代的普遍观念,但这样的天门并不是《大司命》中的天门。 战国时代,人们的天门观念与对太阳运行轨迹的观察有密切联系。《淮南子·原道训》中的天门可能指太阳落山的地方,而不是紫微宫门。这一段谈到天门的话是有所本的,从现在掌握的文献看,应该出自于唐勒赋作。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唐勒赋《论义御》写到御者分三类,其中大丈夫御是“夜走夕日而入日蒙汜”,圣贤御是“入日上皇”,他们的任务都与太阳运行有关,“入日”就是将太阳送进天门,蒙汜、上皇是太阳歇息的地方[5](P309-315)。在战国时代的文献中,《山海经》提到了天门。《山海经·大荒西经》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姖天门,日月所入。”这里的天门,与人类出入的家门比类,指的是日月升降的山峰。这种天门是自然世界实有的,不同于“紫微宫门”那样想象性的东西。 日月出入之门分处东山西山,从东山跑到西山,人们就能将日月的运行轨迹在大地上踩踏出来,但山外还有山,即是有善跑的夸父逐日,也难以找到那不可移动的天门。古人的智慧是修建观象台,以观象台为天门。以山为天门,人们能够从东西方向的明暗变化中测定地球自转一周的长度,这就是一天24小时。以观象台为天门,人们能够从南北方向的寒暑变化中测定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长度。据《尚书·尧典》记载,唐尧时代的天文观测已经对二分二至有精密测定:“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2003-2004年在山西襄汾陶寺,考古发现了与尧舜时代相近的距今4050±115年的观象台建筑基址[6],观象台是一座直径约五十米的半圆形平台,台座顶部有一半圆形观测台,以观测台为圆心,由西向东方向,呈扇状辐射着十三个土坑,推测原有十三根夯土柱。古代人应是利用这十三柱之间的十二道观测缝来观测正东方向的塔儿山日出,借此掌握十二月的变化过程。观测缝的形制是两柱夹一缝,日月从缝间升降,这样的观测缝无疑就是人造的天门。 二、昼夜之门也是生死之门 当一天、一年的时间可以通过天门来测定以后,人们就可以据此制定历法,对于每一天、每一年的生活加以安排和控制。但还有更长的时间段落,人的一生从生到死,又该用哪座天门来度量和安排呢?源于楚文化的庄子学派已将日月出入与生死变化联系起来,《庄子·至乐》云“死生为昼夜”,《田子方》云“死生、终始将为昼夜”。《庄子·庚桑楚》第六章重点从生死变化角度定义了天门:“出无本,入无窍;有所出而无窍者有实。有实而无乎处,有长而无乎本剽。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无见其形,是谓天门。天门者,无有也。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圣人藏乎是。”这里的天门泛指一切变化的门户,指的是造化之门、大道之门,开了天眼的圣人能看到这样的天门,它不存在于现实世界,而是藏在人们的心中,圣人在哪里,天门也就在哪里。小到个人的得失、去就、出处、进退、屈伸、生死转化,大到自然世界的昼夜、寒暑、阴阳演化,都是从天门开始,又回到天门结束。万物由天门化生出来,却看不见其来源根底,万物消逝复入天门,却找不到其踪迹藏所。有了天门,空间之边际,时间之始终,似乎都可把握。万物经由天门在时空中出生入死,无中生有,化有为无。人们守住了天门,也就守住了大道。 屈原的作品也喜欢将日月运行与人类命运联系起来,《离骚》描写屈原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登天,第一次登天:“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最后来到天门前,“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因为外在的原因没能成功进入天门。第二次登天:“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最终却因为对故乡的眷恋放弃了进入天门。“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惜诵》也说:“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杭。……欲释阶而登天兮,犹有曩之态也。”屈原登天都是由东而西,与太阳的运行方向一致,登天就是伴随太阳行走,故关注“日忽忽其将暮”,但登天的目的是要改变自身命运,故不同于“朝日”“入日”等观测活动,屈原还要“折若木以拂日”。由此可见,《大司命》中的天门是控制昼夜和死生的法门,大司命“入不言兮出不辞”,“乘清气兮御阴阳”,出入天门,伴随日月行进,同时又掌控生死,“纷总总兮九州,何寿夭兮在予”。 日月运行是连续的,观测却需要切分,天门就是人类建立的切分点。有天门进行空间定位,出入、生死的时间切分就成为可能。但切分可能会破坏事物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会造成认识的偏颇。如何避免这样的失误呢?《庄子》提出来一种“得其环中”的认识方法。对于一件事物,我们要既见其生,又见其死,从整体上来把握事物。“以无有为首,以生为体,以死为尻;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宗者?吾与之为友。”(《庚桑楚》)还要追根溯源,弄清事物的来龙去脉,认清事物的连续性。“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至乐》)对于不同的事物,要看到相互之间的区别,更要注意相互之间的联系。《寓言》云:“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正是由于不同事物之间存在着区别和联系,世界才显得丰富和富有活力,能够不断地传承延续。事物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不同种类之间先后传接,根据环境的不同发生变化,但其生命本质保持稳定,能量传递保持恒定,《至乐》云:“种有几,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蝴蝶。蝴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化而为鸟,其名为干余骨。干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酰。颐辂生乎食酰,黄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笋,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各种事物虽有生死变化,但都是“机”的演变。“机”指超过人的控制水平的机体,它自然存在,自动运行,在万物之中,又超乎万物之上。万物生死变化只是机的显化和运用,这些变化围绕着机构成一个连绵不绝的演化环,机处于环中。环中就是天门,可以在此控制变化,沟通生死。《齐物论》云:“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则阳》指出,冉相氏就是“得其环中”,才能做到随物自成,与物契合,成就圣王之业。 庄子学派通过天门、环中认清了世界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其出机、入机都在强调对于生死变化的超越。屈原《大司命》《少司命》也以天门定位,却格外重视对生死变化的整合,通过整合来把握生命形态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作为神灵,二司命代表着生、死两极,各自向着生、死作极限运动,大司命代表死,他借助玄云、飘风、冻雨等大自然的异常现象来加强死亡的威风,他像人类收获成熟的庄稼一样去收割人的灵魂,要用死亡之威将生命世界寂灭,“何寿夭兮在予”“众莫知兮余所为”,他收取生命果实的方式是独裁的、神秘的,众人没有资格知道。少司命代表生,她借助秋兰、蘼芜来辟邪,借助瑶华、桂枝来增强生命力①,其目的就是要追求永生,她甚至“竦长剑兮拥幼艾”,拿起武器来捍卫生的尊严。 但是现实世界存在的既不是寂灭,也不是永生,而是生死相依、生死循环的具体人生。二司命虽然是祭祀的对象,但作品所表现的只能是屈原对现实人生的看法。在具体人生里,无论是个人身上还是族群之中,不存在单纯的死或单纯的生,生与死两极一体,相互依存,不断地分化组合,循环回归,生长的同时也就在死亡,死亡发生后,马上就会转化成其他的生命形态。生死结合与转化的途径是天门,二司命出入天门,追寻的就是生死相依。二司命这一对生死恋人是一见钟情:“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他们总是前后相随,同时出现:“君回翔兮以下,踰空桑兮从女。”“吾与君兮斋速,导帝之兮九坑。”他们喜欢相聚相守:“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对于别离充满疑虑和担忧:“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老冉冉兮既极,不寝近兮愈疏。”别离之后相互思念:“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但控制天门的是“帝”,天门是造化之门、大道之门,天门所在即道之所在,“帝”代表了道。郑樵《六书略》云:“帝象萼蒂之形,假为蒂。”帝如同花萼,包含着无穷的生机。《老子·道经》第四章以为道体虚无,“象帝之先”,“帝”处于道之后,有之前,是“有”的开端,为万物之始。二司命亲近帝,“夕宿兮帝郊”,就是等待着帝将生死法则灌输到生命体中。每一条生命中都包含了生死法则,生命的展开过程就是生死法则的释放过程,这是自然之道。当然,我们的文化中更强调了生的一面,王弼注《周易·益》以为“帝者,生物之主,兴益之宗”,帝是宇宙万物的生殖之神,对于万物一视同仁,都有“生育之功”,代表着公平、正义、道德等生存法则,生命的展开过程也是生存法则的自悟过程,这是生活之道。在万物之中,惟有人能自悟,每一个自悟生存法则的人都是开了天眼的人,天门就存在于他的心中。二司命“导帝之兮九阬”,那是由于九州都有自悟了生存法则的人出现,天门在他的心中打开,居于天门中的帝自然也就降临他的身体。对于开悟生活之道的人来说,生死离合属于自然法则,人们对此无需忧虑悲伤,“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只要坚守公平、正义、道德等生存法则,人生自然圆满,故生死虽不由己,有道者却“愿若今兮无亏”。 三、出入天门与力量崇拜 《大司命》《少司命》将生死观念神格化,体现出对死亡和生存极限力量的崇拜。神格化与力量崇拜也是《九歌》组诗的整体特点。《九歌》十一篇,五祭天神,四祭地祇,一祭人鬼,最后的《礼魂》为送神曲。组诗源于民间祭祀诗,王逸《楚辞章句》认为,屈原《九歌》是在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祭神曲基础上创作的。“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朱熹《楚辞集注》也说:“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其中有无冤结,有无忠君爱国之意,还可以讨论,把《九歌》的创作放在屈原流放沅湘以后,则多遭否认。郭沫若说:“以《九歌》歌辞的清新,调子的活泼来说,我们可以断定《九歌》是屈原未失意时的作品。”[7]赵逵夫先生也认为《九歌》当作于楚怀王七年前后屈原供职于兰台期间[8](P1069)。从内容看,这组诗与祭祀祈祷的巫歌不同,汤漳平指出,《九歌》歌咏诸神故事,却非祭神祈福之作,无求神报秦之词,与一般祀神曲完全不同[9](P89)在《大司命》《少司命》中,屈原能够借助神灵的立场,理性地看待生死现象,展现出客观认识自然法则和自觉遵循生存法则的意识。这不再是流于集体表象的原始思维,而是一种理性思维能力。从目的看,这组诗是为了力量崇拜,不是为了“神道设教”。“神道设教”一语出自《周易·观·彖》。圣人以神道设教为业,其效果是“天下服”。但圣人本身对神道是不信的,以此设教不过是为教化氓民的需要。《九歌》创造了人格神,却没有神道设教意图。屈原要表达的是对于力量的崇拜,组诗充满对光明、黑暗、死亡、生存、生殖、战斗等力量的崇拜,而天门出入为这些力量提供了修复重生的机会。力量崇拜总是向极致发展,与北方求善的中和思想完全不同。 战国中后期,“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刘向《战国策序》),秦楚争霸的形势已经明朗。此时,生长在“土厚水深”环境中的北方诸子文化的主流已经破除了人格神观念,完成了“人文的转向”[10](P4)。至于“水势浩洋”的南方泽国人民,则“崇尚虚无,活泼进取,有遗世特立之风”[11](P233)。屈原与楚同姓,为宗室之后,其一生志业就是要在楚国实行变法,“坚持法治,反对心治”,“举贤授能”,“力耕强本,富农安民,反对游大人以成名”,“励战图强,统一天下”,“禁止朋党,竭忠诚以事君”,“反壅蔽”,“赏罚当,诛讥罢”[12](P176-191)。屈原推行的这些变法措施是从北方学来的,但屈原并不想让北方文化全面覆盖南楚文化。从《九歌》这组祭神歌可以看出,屈原在变法的同时,仍然想保留人格神的观念。或者说,屈原将楚族巫师创造的神灵世界提升成为超离现实世界之上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充满力量,这种力量能够通过天门得到恢复,具有碾压一切艰难困苦的威力。 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世界各大文明进入轴心突破期,但文明突破的进程是各不相同的。余英时对比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等文明突破进程后指出,其他文明突破属于外向超越,而中华文明的突破属于“内向超越”[13]。就中华文明内部来看,南北文化的差异是很大的,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已指出南北地理环境不同,经济形态不同,造成南北诸子学、经学、理学、考据学、文学都有极大的差异。屈原《九歌》借助形象把握概念的方式,依托神灵超出现实人生之外的观察视角,对于事物性质作极限探索的趋向,都代表着南方文化的特长。鲁迅对于代表南方文化的《楚辞》有很高的评价:“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14]屈原所代表的南楚文明突破道路主要是力的突破,这与北方诸子期待着内在的善的拯救不同。力的突破赋予屈原作品一种朝气,一种浪漫气息,一种不怕牺牲的精神,在汉代以后对于中国文化不断发生影响,与诸子之善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 ①《少司命》“秋兰兮蘼芜,罗生兮堂下。”这些堂前种植的花草具有药用价值,《神农本草经》草部以兰草为上品,以蘼芜为中品。兰草可“杀蛊毒,辟不祥。久服益气、轻身、不老,通神明。”蘼芜“主治欬逆,定惊气,辟邪恶,除蛊毒鬼注,去三虫。久服通神。”《大司命》“折疏麻兮瑶华”,王逸注:“疏麻,神麻也。瑶华,玉华也。”洪兴祖补注引说者曰:“瑶华,麻花也。其色白,故比于瑶。此花香,服食可致长寿,故以为美,将以赠远。”《大司命》“结桂枝兮延伫”,桂枝同瑶华一样,也是不死之药,《说文解字》解释桂是“江南木,百药之长”,《神农本草经》认为牡桂“久服通神、轻身、不老。”菌桂“久服,轻身、不老,面生光华,媚好常如童子。”其所食用的牡桂、菌桂都指肥厚的桂皮。《东皇太一》《东君》提到“桂酒”“桂浆”,这是用桂花酿造的酒。传说古仙人常食桂皮,饮桂酒,《搜神记》卷一记载,殷时有彭祖“号七百岁,常食桂芝。”《神仙传》云:“离娄公服竹汁,饵桂得仙。许由父箕山得丹石桂英,今在中岳。”《拾遗记》云:“闇河之北,有紫桂成林,群仙饵焉。”《列仙传》云:“范蠡好食桂,饮水卖药,人世世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