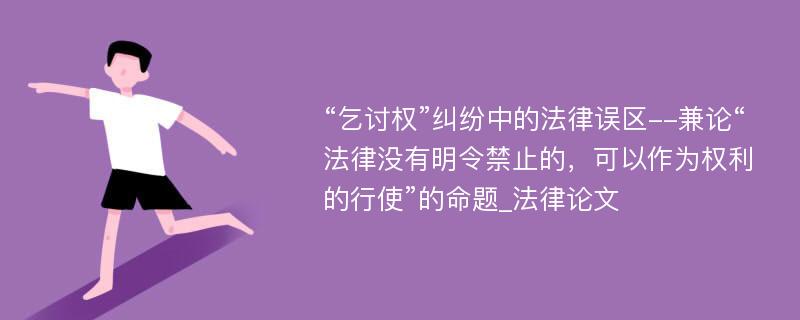
“行乞权”之争的法理误区——兼评“法无明文禁止之处即可作权利的推定”命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处论文,法理论文,明文论文,之争论文,可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乞丐问题不是一个新话题,1999年上半年《中国青年报》就曾展开过为期四个月的讨论。当时讨论的主题是:“爱心会不会献给骗子。”这次讨论的引发在于一部即将出台的法规。2003年底,由北京交通委法制处牵头起草的《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办法》(送审稿)的公布(在首都之窗网站上征求公众意见),推动了人们对乞丐生存状态的进一步关注。耐人寻味的是,该法规所包含的禁止在地铁等轨道交通的车站出入口、车站内或列车内乞讨、卖艺、吸烟的内容,并没有生发出人们对卖艺权(实为表演权)和吸烟权的争辩(注:该法第20条运营安全禁止性规定禁止11种危害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行为,其中包括在车站出入口、车站和列车车职内乞讨、卖艺。),却使人们将视线投向乞丐的权利,引发出有关乞丐的权利,或说“行乞权”的话题。反对者将允许城市行乞与倡导宽容精神和培育“善良之心”相联系,认为该法规的制订实际上是剥夺了乞丐自由乞讨的权利,有的还从该法的执行需要“巨大的行政管理成本”的角度加以评判。总之,称该法为恶法的人数并不在少数。
本文作者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并在《法制日报》上发表了对此问题的基本看法后,受到某些批评。种种批评观点暴露出长期以来在法理学基本观念上的一系列误区,其中积淀最深,从而误导最甚的是“法无明文禁止之处即可作权利的推定”的命题。
一、关于“行乞权”的基本观点[1]
乞丐是指以乞讨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或人群体。乞讨行为是乞丐的日常行为。乞丐有无行乞权,其实说的是公民有没有乞讨的权利。讨论这一话题,必须明确几个相关问题。
首先,严格地说,乞讨行为从来都不是一种被社会道德或国家法律所倡导的行为(注:这场讨论的批评主要因本文作者的这一观点引起。)。
“行乞权”在我国宪法法律中找不到其相应的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第45条),但从此项规定中引伸不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公民的行乞权。且不说这里讲的“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的主体是指“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而不包括年轻力壮、健康或有劳动能力者,仅从后面的限定也可看出,对于这项权利,国家所予以保障和发展的措施和制度中,并不包括国家有为乞讨行为提供合适场所或方便的责任。
也就是说,乞讨的权利并没有成为我国法律制度所保护的一项权利。就人们对它的长期默认态度来看,它在本质上已成为一项习惯权利,或说是一种法外权利。法外权利不是为国家法律所保护的权利,也没有相应的法律义务作它实现的条件或保障。又由于行乞不为社会普遍的道德所赞许,它不是一种道德权利,因此它的存在还缺欠相应的道德义务的支持。当一个乞丐走来向你伸出手时,你没有义务施舍与他,你的这一拒绝行为既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也不会受到道德舆论的谴责。
其次,行乞自由即便成为公民的一项法定权利,它也不是无度的,它的界限是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乞丐是社会(主要是城市)的寄生体。在现代社会中,乞丐群体的存在虽说是现代文明的副产品,却决不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他们给一座城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一目了然的。一个四处可见乞丐的地区或城市,对于游客来讲是没有吸引力的。这除了在于乞丐的衣着让人不快之外,更在于许多行乞者令人厌烦的行为方式(反复纠缠),尤其是那种租用流浪儿童行乞,或衣着褴褛伪装成残疾人在地上哀叫着爬来爬去的乞丐,更是令路人惟恐躲闪不及;至于栖身于建筑物拐角或地铁入口处的乞丐,他们在夜晚的显现不仅成为人们通行中的障碍,还多少威胁着夜行者的安全感。“有碍景观”、“妨碍交通”、“扰乱社会治安”的评价由此而出。所以,现代社会在强调公民有不受他人纠缠和冒犯的人身自由之时,对于这类寄生现象越来越持以一种否定态度。在一些国家(如新加坡)中,法律将乞讨行为明确规定为犯罪行为,或者对乞讨的区域加以明确的规定(如美国哥伦比亚州),便是基于乞丐及其乞讨行为对于当地旅游业所构成的威胁直接损害到国家利益后果的考虑。
《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办法》的出台表明了对于乞讨行为的管制和限制。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第一,该法不是一部禁止乞讨行为的法律文件,而是一部在内容上涉及限制乞讨行为范围的地方性法律文件(注:明确这一点十分重要。在讨论中,批评者完全不顾这一事实,反复使用“清理”、“驱赶”、“禁止”、“剥夺”之类的词。可见在他们看来,所谓的“行乞权”是一种不可加以任何限制的、绝对的自由权,只要一加限制便成“剥夺”或“禁止”。),之所以对地铁等轨道交通的车站内或列车上的乞丐加以限制,在于其环境的特殊性(人员流动性、密集性、风险性程度较高),在这里非常态的行乞行为一旦失控,其后果不堪设想;第二,它的出台并不是对公民基本人权的否定,行乞权不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在我国也不具有法的形式,该法实际上是将一项习惯权利纳入法制的轨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反而表明了在此范围外行乞行为的被允许和合法性。
从本质上说,乞丐群体存在的根源是贫困。消除乞丐及乞讨现象,除了加强对公民“自强自立”的道德教育外,关键在于铲除产生它们的贫困根源。换言之,面对日益增多的城市乞丐,应当引起我们关注的不是“行乞权”的是否存在,而是如何建立一种对处于贫困状态中的人们进行援助的完备的社会救济体系和制度。就这一点来讲,加拿大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加拿大各地都设有免费餐厅,给失业者和流浪的人提供食物。这些食品不算差,也有肉。作者在温哥华市访问期间曾见到一些露宿街头的流浪汉。他们白天蜷缩在街道两旁,拉小提琴或弹奏其他乐器,晚上盖一张报纸席地而睡。对于这些“文明乞丐”,在夏季警察一般不管,到了冬天,警察会用车把他们拉到警察收容所里。加拿大慈善组织十分活跃,募捐活动较多,募捐钱或物品均可。人们把衣物放在大袋子里,并附上写有捐赠对象的条子,每隔一个时期,社区就会有一些慈善机构人员上门来索取它们。在各个大超市门前,也都设有一个捐款捐物的专门橱柜,一些顾客会将他们多买的或特意买的商品放入里面。所有捐赠的这些物品都将被集中起来送到一个专门地方,给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注:所以,人们说,在加拿大是饿不死人的,对于社会的穷人来讲,吃有免费餐厅,穿有捐赠者,住有警察收容所,上街乞讨只是讨平日的零花钱。据作者的一位朋友说,他认识一对波兰裔的夫妇,以乞讨为生,每日可乞得100~200加元(合人民币500~1000元)。)。
加拿大的这些措施自然是与它的高税收和高福利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其中非政府组织(如慈善组织)的积极参与(如募捐活动)给予我们以某种启迪。但是,当网上报道哈尔滨市救助站建立后的一个月中并未如期地受到其援助对象(乞丐们)的欢迎,许多乞丐“宁可街头乞讨,也不愿搬进救助站”的新闻时,人们看到,在行乞演变成一个特定人群体的一种职业行为后,欲图归化这一寄生群体,改变其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种种努力有何等的困难。乞丐的消失绝不是建立几个救助站和施舍几文钱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关于这个问题才是更应引起人们思索的问题。
二、批评者的基本观点及对之反驳
作者以上的观点见报后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批评者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2]。
观点之一:乞讨权利无须法律来证明。
批评者认为,任何有现代法律意识的人都知道,“法无明文禁止之事不为罪过”,由此乞讨权利无须法律来证明,因为人们不仅能做法律明文规定允许做的事,也可以做法律明文禁止之外的事。由于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利相当有限,而人活动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如果人们只能做法律载明可以做的事,那么很可能陷入动辄得咎的境地。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保护公民的财产、言论、集会、结社等项权利的理由在于,这些权利是最基本、最重要,值得作为示例列举出来,但这决不意味着说没有列举的权利就不是合法权利。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是执法人员的责任,而普通公民没有义务证明自己不违法。既然乞讨行为未被宪法法律所禁止,而法不禁止即自由,那么依据权利推定原则,乞讨权就是由生存权这一基本权利而推导出来的次权利或从权利,这一自由权的行使只要未侵害到他人的、集体的、国家的公共利益,它就不得被禁止或剥夺。只要未被明令禁止,就是合法的权利,这种合法的权利不可被侵犯,行政力量的禁止是一种违反法律的行为。
观点之二:“生存权高于一切”,行乞权是生存权。
批评者认为,乞丐的行乞权虽然是一种“行为权”,但不可与一般人的一些行为权同日而语。正因为行乞是他们惟一的谋生手段,因此“行乞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利,它实质上就是生存权。生存权是一切权利的基础,取消了某些人的生存权,由此派生的其他权利的制度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作为最基本的人权,没有人的生存权就没有一切。一切权利皆由生存权派生,本质上生存权优先于其他一切权利。当任何法律规定违反了人的生存权时,它都是无效的,都必须为人的生存权让路。因此,尊重乞丐的“行乞权”(生存权),应该是这个标榜“法治”的“文明社会”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的一个严厉前提,否则即使建立起来,在各种力量的冲击下也有可能陷于崩溃。从人权的角度看,乞讨行为是社会财富资源匮乏的必然产物,国家与政府是人权的义务主体,政府无权动用行政力量清理、驱赶乞丐,禁止他们行乞。
观点之三:行乞权是穷人的道德权利。
批评者认为,乞丐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的人,在面临匮乏、生活无着、政府亦无力进行社会救济的前提下,乞讨成为穷人的惟一可选择的权利,是他们能够得到救助的惟一的社会保障形式。行乞权的本质是乞丐这一穷人群体的生存权,或说天然的不可剥夺的维持生存的基本权利,行乞权就是他们进行自我救助的道德权利。在普遍社会化保障制度付之阙如的前提下,乞讨权就成为那些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贫困者即穷人为谋求生存而享有的道德权利。施舍行为是一种无偿的赠与行为,是一种善行。从权利和义务的角度分析,乞讨者是行乞权这一道德权利的主体,施舍者则为道德义务的主体,人们道德上的同情和怜悯是行乞权实现的主观条件,施舍这一道德善行则是该权利最终实现的客观条件。所以,行乞权在本质上就是生活不幸者的道德权利。人们施舍或不施舍是一个道德权利问题,即使乞丐行乞的权利妨碍到了其他人不受干扰权利,在公共场合对他人造成一定的影响,妨碍到了公共秩序等,从法律层面上讲都必须对此进行容忍,最多只能进行道德谴责,而不能动用行政力量甚至立法剥夺他们行乞的权利。
这些论述在基本概念和逻辑上的混乱一目了然。这里,我们不想过多地责备批评者在一些命题的表述上是如何的不准确,仅就这些观点所借用的论据来看,也是站不住的。
不难看出,由于没有一个批评者能以历史的和现实的一个实例来否定本文作者关于“乞讨行为从来都不是一种被社会道德或国家法律所倡导的行为”的观点,故而其批评的基本思路只有三个:一是从“法无明文禁止之事不为罪过”命题推导出“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作权利的推定”,继而再推出“行乞权无需法律证明”的论断;二是强调“行乞权是一项穷人的道德权利”,并将它发挥为“行乞权是一项道德权利”;三是由强调行乞权是一项生存权,推论出行乞权不可被限制的观点。
这些思路或观点都是有严重缺陷的,至少它们在法理上是经不起推敲的。
首先,从“法无明文禁止之处不为罪”推导不出“法无明文禁止之处即可作权利的推定”的命题。现代法治社会的司法制度有一对重要原则,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公民来讲,“法无明文禁止之处不为罪”(这里的“罪”是指“犯罪”或“有罪”,而不是“罪过”,“罪过”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伦理学概念);二是,对于国家机关及其人员来讲,法无明文规定之处都不可为。前一种表述就是罪刑法定原则,后一种表述便是权力制约原则。然而,无论从这两项原则中的哪一项来看都推导不出可为,也就是说推导不出“法无明文禁止之处即可作权利的推定”的命题。
法定权利是指在法律上明示的权利,在法律上没有明示的权利不是法律权利,倘若要将某一种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行为,或冒犯他人的行为说成是一项合法的权利,那么就需要明示它的出处,至少对于学者(尤其是处于学术讨论中的学者)来讲理应如此。在现代社会中,如果说证明公民行为的违法性是执法者的义务的话,那么在受到疑问时证明自己的行为合法或不违法有时也是公民的义务,如行车人在受到盘问时向交警出示驾驶证,考生在考场上向监考人出示准考证,企事业单位职工入门时向门卫出示出入证或工作证,储户存款时向银行出示自己的身份证,犯罪嫌疑人在审讯中或法庭上出示自己“不在现场”的证据等。所谓只能由某一方(如执法人员)来证明公民行为合法性的说法决不是一种教条,实践中一切行为者(包括国家权力者和普通公民)都有义务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这些义务早已渗透在各种规章制度和法律程序中。
其次,行乞既不是一项法定权利,也不是一项“穷人的道德权利”,更不是一项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权利。批评者所说的“穷人”概念是不清晰的,是仅指乞丐群体(其中并非都是穷人),还是泛指一切穷人?如果是前者,行乞行为倒也合乎乞丐群体(特别是那些已职业化了的乞丐群体)内部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如果是指后者,则问题就出来了——在许多穷人那里,不劳而获、丧失人格尊严的行乞恰恰是为他们所鄙视的行为(注:作者曾在云南傣族哈尼族地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期,在那里,即便是处于最艰难时期或最困苦的生活境况中,行乞也是被热爱劳动的广大傣族哈尼族群众所鄙视的行为。)。
道德权利需要道德义务为其支撑点,那么,应该施舍乞丐的道德义务主体是谁呢?是富人,还是所有的社会成员?如果行乞是一种普遍的道德权利,那么等于说,道德义务的主体应该是所有的社会成员。然而,生活中人们给予乞丐施舍的原因诸多,多数是出于某种恻隐之心(仁慈或善良本性),但是绝不是出自于某种道德义务的要求。如果施舍是一种道德义务的话,那么拒绝乞丐的行为理应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或责难,生活中的事实却是,没有人会认为走过乞丐身边而不予施舍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可见,给予乞丐以施舍并不是人们的一项道德义务,而乞丐的乞讨也不是一项道德权利。
现代社会从不宣传施舍乞丐是公民的一种美德或道德义务。历史上和现实中也没有任何一种社会道德是提倡行乞的。相反,倡导自尊、自强、自立、自爱、爱劳动、不劳动不得食,鄙视好逸恶劳等这些与行乞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则是近代社会以来,特别是现代社会所积极倡导的。行乞行为不符合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正是它所具有的明显的寄生性和反人格尊严的特点,使得它在任何社会和时期都无法成为一个社会所提倡和普遍认可的道德行为和道德权利,从而也不会被提升到法的层面明示为一项法律权利(注:封建时代一些乐善好施的地主或乡绅通过临时性的“施粥”或“施衣”对穷人进行救济,并非出自道德义务的要求,或是对穷人行乞行为的肯定,而是出自其某种利益的需要(如减缓社会矛盾冲突或笼络人心),或某种宗教情感或其做人的准则等。)。
行乞行为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在现代社会中,行乞被视为是不文明的行为。随着社会的进步,终将去除这一寄生现象。在社会文明的发展中,行乞行为越来越妨碍到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其消极意义也越来越大,正是这样,限制乞丐行为被视为是现代社会进步的表现。在西方多数国家,限制乞丐行为已成为一项明确的法律制度,行乞行为受到如下限制:如公共场所不得行乞,不得假装残疾人行乞,不能以令人厌恶或欺诈的方法行乞,不得指使、威逼、唆使未成年人或他人行乞等,违反者将受到刑罚惩处。如《意大利刑法典》和《美国模范刑法典》中都有类似的条款[3]。
再次,行乞权也不是公民的生存权。批评者关于行乞权是天赋权利、生存权和道德权利的表述(将这些含义不同的权利混杂在一起,表明了批评者们在权利概念上的混乱),存在着明显的漏洞:一是,这里“生存权”的主体不明——是特定的个体或群体(即乞丐或乞丐群体),还是全体社会成员?二是“生存权”的含义不明——是仅仅指活着,或不劳而获地寄生着的权利,还是指有尊严、有价值、自主地活着的权利?三是,如果行乞权是公民的生存权,那么与公民的集会、结社等权利相比,它显然应该是更为基本的权利,按照批评者的逻辑,它理应被明示为一种法定权利,然而,历史上及现代社会中任何国家的宪法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点——它们都未将行乞权列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未由生存权中推导出这一所谓的“次权利”或“从权利”,更不用说在行乞权与其他权利发生冲突时予以它优先地位了。乞丐享有与其他公民一样的生存权,但是这一生存权不是行乞权。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所说受社会帮助的主体是指“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而不是乞丐。当宪法将劳动的义务作为公民的基本义务时,它便对以不劳而获的行乞形式生存的方式作了否定。
据媒体报道:收容遣送措施取消后,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工作面临新的情况和问题。去年下半年以来,“一些大中城市繁华路段的流浪乞讨人员数量大增,强讨恶要现象突出,组织、利用未成年人进行乞讨和从事非法活动的情况明显增加,且绝大多数流浪乞讨人员不愿意接受救助”——仅从这一点便可看出,所谓“如果不让乞丐乞讨,他们就会因无生活来源而悲惨地死去”的说法有多么的荒诞——其中有职业乞讨人员,有为发家致富者、好逸恶劳者。“一些流浪乞讨人员结成帮派、团伙,划地为界,争夺地盘,严重危害城市社会治安秩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亟待从政策上、法律上和管理上加以解决。”[4]
可见,对乞丐行为加强法制管理,已是涉及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城市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最后,行乞的本质也不是一种单纯接受馈赠的行为。馈赠是行为主体自觉地、主动地将自己的东西无代价地或不索取回报地给予(否则就是交换)对方的行为,它一般不是索要的结果。以合同法中关于赠与的规定来推导行乞行为的合法性,甚至将乞丐与行人的关系视为合同关系,纯属牵强附会。其一,这一关系也不是依赠与合同而生的关系。在赠与关系中,主动给予行为在前,接受行为在后;赠与合同最重要的特征是赠与一方的自愿性和义务性;而行乞是索要行为,在乞丐与行人的关系中,索要在前,给予在后,行人的施舍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义务性。其二,这一关系不是合同关系。我国《合同法》(1999)对于“合同”有一明确的定义:“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2条)并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第118条)行人与乞丐、行乞与施舍之间不构成如此合同关系,正是这样,当一个施主未将允诺给予某个乞丐的财物给该乞丐时,该乞丐无权要求他交付这些财物。因为这里既不存在着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性质,也不存在着赠与合同或协议。
行乞权之争不仅表明了广大公民对于立法活动的积极参与,而且有助于推动人们对社会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进一步关注,以及对社会制度完善的深层思考。在这场讨论中,话题被人们一再地转换,从而从最初的“北京市出台一部含有限制乞丐行乞范围的法规是否违宪”的话题引发出诸多的话题,如:“限制行乞范围是否是对‘行乞权’的否定?”“‘行乞权’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它是否需要法律上的明示?”“限制行乞行为是否与现代文明相悖?”
问题的一一出现,表明了讨论的步步深入,而当我们将对整个争论的视线转向批评者的主要论据(即“法无明文禁止之处即可作权利的推定”)时,这一古老的命题便清楚地暴露出它的虚假性(注:多年来,作者曾多次指出这一命题存在的问题,但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三、法理误区之析
在“行乞权”之争中,暴露出长期以来法理上,以及近些年来人们在人权概念上的种种误区。
误区之一:“法无明文禁止之处即可作权利的推定。”
这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人们反复使用,从而成了一个习惯性的、似乎不证自明的命题。但是,只要细加分析便不难看出,这是一个虚假的命题。这一命题的虚假性或不真实性在于,它的前提是虚设的——它假设了除法规范之外,没有其他规范的存在。事实上,无论是从逻辑上讲,还是在实践中,从法无明文禁止之处并不能必然地推导出权利。换言之,所谓“未被明令禁止,就是合法的权利”的说法是错误的。这是因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并非只有法,法规范只是诸多社会规范中的一种。国家不可能将所有的群体规范都提升到法律的层面,将所有的行为都纳入法的控制或管辖之内。在法无明文规定之处还有国家政策、道德规范、宗教戒律、市场规则,以及其他群体规范(如党纪、企事业规章制度、乡规民约)等在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如,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公民可以不分场合地随地吐痰、任意吸烟、讲粗话脏话,那么是否可以由此推论公民就有这样的权利呢?不能,因为还有其他社会规范在制约着公民的行为。
这样,权利就不可以作任意的推定。换言之,从法无明文禁止之处我们不可能作权利的推定。事实上我们常常不仅推导不出法定权利,也推导不出法外权利。法定权利是法所明示的权利,即在法律上可以和能够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自由度。明示的权利用不着“从法无明令禁止”之处去推定,而从法无明文规定之处当然推导不出“明示的权利”,如果“只要未被明令禁止,就是合法的权利”的话,那么这种“合法”不知指的是合乎什么法?法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明确性,这里的“合法”指的是合乎明示的法,还是合乎暗示的法?法外权利是在法规范之外的权利,从法无明文禁止之处去推导非法律形式的其他权利的存在,这等于说,不是法律权利就一定是其他权利。这在逻辑上是站不住的。
社会生活中的许多行为不是依据法所规定的样式而存在,而是依据文化传统、习俗、群体规范而存在。如,法律不可能对人们的服饰、发型、衣着做出明确的规定或禁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或可以由此推导出,任意着装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因为这里至少有两个界限:一是公序良俗,也即社会普遍的道德规范和习俗;二是正式群体的规范。因此,在公共场合随地吐痰、任意吸烟、讲粗话脏话、裸走之类的自由,不被视为是公民的应有权利,而在接待外宾的会客室或学术研讨会上衣着泳装或举止野蛮粗俗,更是令人惊愕或使人难以容忍,尽管它们并不被法律所明文禁止。
误区之二:将人权视为一种排除义务的绝对权利。
将人权看作是可以凌驾于一切社会规范之上不加制约的一种特权,或者在各种权利之间进行阶位比较,将某一种权利看作是可以凌驾于其他权利之上的优势权利,如视生存权高于发展权,所谓的“行乞权”高于人身权等。与此相适应,认为弱势群体的权利在价值阶位上高于非弱势群体的权利。种种诸如此类的做法是近些年来在讨论人权问题时较为流行的。
人权是指人按其本性所应当享有的在社会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由度。这次修宪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使得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法律制度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以及国家必须承担其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我国在人权保护方面的重大进步。但是必须明确的是,第一,人权作为人的权利,其自由不是无度的,而是内含着义务的要求,权利内含的义务性界限是国家履行其保护人权的责任的前提或条件——公民权利的享有以同时履行不超越这一权利合理界限的义务为条件,惟此该权利才受到国家权力的支持或保障。这就是说,不含义务界限的人权是不存在的。《世界人权宣言》(1948)明确规定:“人人对于社会负有义务。”(第29条)《联合国人权公约》(1966)的“前文”中也有相似的规定:“明认个人对他人及对其隶属之社会,负有义务,故职责所在,必须力求本盟约所确认各种权利之促进及遵守。”[5]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第5条)这些说的都是人权享有的条件性或人权的界限。那种一遇法律限制就说侵犯人权,视“人权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的做法,是对人权概念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宪法表述的误解。
第二,公民的权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种权利及其主体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都应受到保护而不应受到侵犯。如公民有行走在安全的马路上、有在安全的环境中工作、有免受突然事件的恐吓或他人纠缠等权利,这些人身权与公民的其他权利是同等阶位的,不存在着何者为更高的问题。那种认为个人的需要和利益应该具有道德优先权,比社会的需要和利益更为重要的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公民或个人没有优先于社会的特权,各种权利及其主体在道德价位上是平等的。法律对老人、儿童和残疾人的权利予以特别保护的原因在于,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其权利更易于受到伤害,而不是因为这些权利具有更高的道德价值。实践中政府协调各种权利冲突的依据,常常不是源自对何种权利的道德价值更高的判断,而是出自对利弊的权衡。这些观点早在多年前就已为美国自然法学家德沃金在他的《认真对待权利》一书中所一再强调。
第三,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具有为其他生物所没有的特有的理性和社会性,这种社会性和理性是与人的尊严、价值和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后者是一个人得以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人权就是能使自己成为人、能使一个人成为与他人同样的人的权利。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凡是与人的尊严、价值和地位相关的权利都逐渐地转为人权的重要内容。在社会生活中,法律无法将一个人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一切方面都加以规范,它只能对那些关系到个人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方面做出规定,这些规定就形成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即基本人权。那些未能上升到法的层面上被规范,但被人们所承认的自由就构成了法外权利。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其文明程度的提高,一方面,一些法外权利会被逐渐淘汰、消亡;另一方面,一些法外权利会被提升到法的层面上,或者被纳入到法所管辖的范围内,由法律对它们的自由度或界限做出明确的规定。以法规的形式限制乞丐行乞范围,实际上是为这项法外权利设立法的界限,也即为乞丐的行为自由划定界限。
误区之三:以绝对主义的态度来看待社会宽容。
社会进步首先要摒弃的是那些不符合文明的现象。宽容不等于肯定,也不等于文明。宽容一种丑恶的行为或社会现象(如不劳而获的寄生现象),就个人来讲,并非是一种美德;就社会来讲,在于管理者暂时还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然而,社会宽容是有限度的,它不是包容一切。我们不应以绝对主义的态度来看待社会宽容,更不能从中推导出宽容对象(如行乞行为或现象)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同理,国家颁布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办法,目的是为了改变目前乞丐的生存状况,而不是为了鼓励、纵容或保护他们的行乞行为。
法理上种种误区的存在,表明了辨明相关理念的必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行乞权之争的学术价值之一。
收稿日期:2004-0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