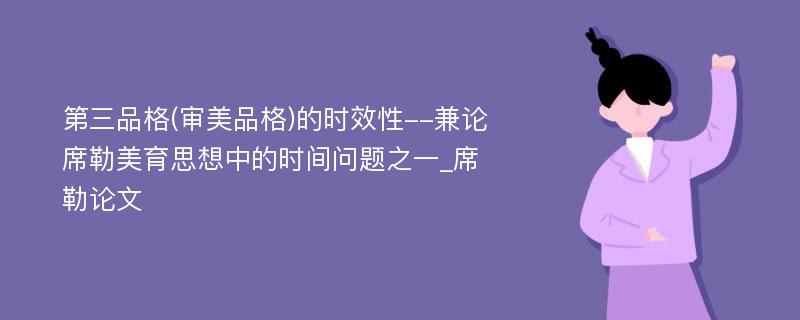
第三种性格(审美性格)之中的时间性——论席勒美育思想中的时间性问题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席勒论文,性格论文,时间性论文,美育论文,第三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G40~0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12(2015)05~0084~06 作为一位美学家,能有如此关注最广大民众日常审美生活现实的炽热情怀,且能如此敏锐地觉察到其中的危机,并提出深谋远虑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审美教育的解决策略,席勒应是西方美学史上极不多见的、灿若晨星般的思想巨子。 一、在席勒美育思想中弥漫性地存在的“时间性”话语 自“时间性”来审视并叙述席勒的美育与美学思想是一个久违且内在的视角,这一视角并不出自于把席勒的美育思想作为一个既有的材料,来进行合乎学理的分析与阐释,而是出自于在席勒《审美教育书简》之中“弥漫性”地存在着的“时间性”话语。在西方美学史上,对席勒的这一时间性美学或美育思想进行关注的莫过于黑格尔。黑格尔在《美学》中曾简洁地总结席勒的美学思想,他说:“有时间性的人有两种方式可以和有理念性的人合而为一,一种方式是由代表道德、法律和理智之类种族共同性的国家把个性否定掉;另一种方式是由个人把自己提升到他的种族,就是由有时间性的人提升到有理念性的人。理性要求统一,要求种族共同性;自然要求杂多,要求个性,人须同时服从这两种法令权威。”[1]但是黑格尔无时间性的理念美学并没有汲取席勒这一思想中的精华。 这一“时间性”话语既关乎个体的审美活动作为一种内时间意识的构成,又关乎这一审美活动作为价值与意义实现的时间性之绽出性或者兴发性的存在。上述两个水乳交融般的时间性话语其实正是审美活动之中时间性维度的两个侧面或者两种基本的可能性,其一是审美活动的价值仅仅体现为一个持续的、流畅的愉悦过程,其二是审美价值或者意义的寻求与实现才是这一时间性过程的根本动力。 自席勒美育思想的整体而言,审美价值作为一种鲜活的动力正是来自于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之间的对立,是这种对立与撕扯彰显了包括审美冲动在内的游戏冲动的价值与意义,而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原本的、自明性的呈现方式正是体现了“时间性”话语的“弥漫性”。自感性冲动而言,在时间性上的体现是迫于眼前与现成的变动不居;自理性冲动而言,在时间性上的体现则是永恒的不变动——即无时间性;只有游戏冲动能够把两者及其时间性特征完善地融合起来,其中尤以审美活动为甚,因而,这正是席勒美学与美育思想之中时间性问题的原本的根源所在,也是席勒美学思想对西方美学史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所在,这一贡献就在于席勒第一次清晰地把审美活动的价值及其呈现状态坦露为时间性视野。这一伟大贡献决定了西方美学史开始由在绝对主观与绝对客观之间来回摇摆向主客不分离的存在论或者人生论美学观的转折。 正是“时间性话语”恰如其分且如其所是的加入,才使得席勒美学虽则不像其他学院派的美学家的著述那样概念清晰、思维系统严密、论辩滴水不漏,却显得可爱、生动、鲜活、亲近,这并不是单纯的文风或者文体因素使然,而是因为席勒的美育与美学思想彻底地贯彻了主客不分离的描述审美活动的基本原则,并因而保持了审美活动构成的完整性,因而也就解决了美学研究对象——审美活动构成的完整性,所以,席勒的美育思想与美学思想在西方美学史之中显得卓尔不群,完全可以说,他开启了一个新的美学时代。 就席勒美学思想整体而言,他一再声称自己的美学思想继承于康德,而且在《审美教育书简》之中的第1封信中就表达对康德思想的忠诚,他说:“诚然,我不愿向您隐瞒,下边的看法大多是以康德的原则为依据,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如果使您联想到任何另外的哲学学派,请您把这归之于我的无能,不要归诸康德的原则。”[2]10不仅如此,从《审美教育书简》一书来看,席勒所讲的审美教育只是以艺术作品为对象的审美教育,这与康德的思想确无二致。但是,席勒美学在康德基础上的创造同样是极为辉煌的,而且我认为从对美学学科贡献角度来看,可以说,席勒远远把康德抛在了身后,尤其是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之中完全突破了以往美学在主客之间来回剧烈摇摆的倾向,他直接把“游戏活动”、“审美活动”视为美学研究与美育理论研究的唯一的、也是最高的出发点,并把这一逻辑始终保持在自己的视域之内。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之中,当他说起“审美超功利”的时候,很显然,这是一个全称判断,而且是一个过于张扬主体性,往往会导致审美活动无法保全的、教条式的判断,或者说,康德美学是一种只适用于艺术作品、只适用于视觉与听觉的美学,当然,仅仅凭这一点,康德美学就已经能够成为现代意义上美学学科的创始与伟大开端。那么,康德美学之所以是过于高扬主体性的美学,就是因为他只是认为美感仅仅与主体有关,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就可以任意处置,而没有意识到在一个已经完成的审美活动之中,审美主体是始终指向审美对象的,美感之所以能够被开启乃至延续,就是因为其奠基于对审美对象的始终指向之上。其中,极为典型的案例就是康德把一个简单到极点的对玫瑰花的审美活动,肢解为只有眼睛看到其形状之美好微妙才是静观的、观照式的、漠然的审美,而如果鼻子同时闻到其沁人肺腑之香则不是审美,事实上,在一个已经完成的对玫瑰花的审美活动之中,视觉与嗅觉是同时“始终—指向”玫瑰花的,如果要保持审美活动的完整性,就必须坦然地、不加任何偏见地描述在这一审美活动整体之中所出现的任何因素。可见,在康德美学中,最为关键的缺失在于没有把审美活动之中的“时间性”作为基本事实加以对待,那就是,既没有在审美价值上保持审美活动的完整性——即没有把审美活动理解为受审美价值与意义推动而开启并持续兴发着的“过程”或者“事件”,而且在这一“过程”之中,审美主体是始终指向审美对象的;也没有把审美活动理解为只有奠基在审美对象之上才会形成的内时间意识。这一切,都是因为康德太抬举审美主体了,太蔑视审美对象了,以至于把主客之间的关系处置成了“主奴”关系。 而席勒恰恰在康德美学最薄弱之处有了堪称伟大的创举,这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西方美学史最为关键的转折之一,其原因正在于——席勒不仅仅把审美活动作为美学研究的唯一对象,而且把审美活动之中存在的“时间性”及其存在的诸维度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在这里,他不仅把时间性理解为审美活动作为一种人类寻求价值与意义活动所绽出的原初视域,而且更是把时间领会为受不同价值与意义驱动而绽出的不同视域,完全把时间与人生意义与价值的领会与实现相对接,由于人生意义与价值是多元的,因而其与人生的关系会有极为丰富的体现,那么,这些不同的价值与意义在时间性上就会有完全不同的体现,有长有短,有丰盈有单一,可以说,这种时间观与20世纪在现象学领域尤其是胡塞尔与海德格尔这两位巨擘所开创的全新的时间观是一致的,而且完全可以称得上海德格尔“此在是对存在的领悟”这种时间观的先声。 在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的27封信之中,从第11封信开始直至最后一封信,他一直都在全神贯注地探讨“时间”问题,其所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人格”与“状态”之中的时间性问题,感性冲动、形式冲动与游戏冲动之中的时间性问题,审美活动作为一种内时间意识在构成上与理性活动的差异,理性在审美活动之中的兴发性存在,等等。 从其内在的联系来看,第11封信里所提出的“人格”与“状态”相矛盾的时间性是全书的机杼所在,也是席勒何以会提出美育思想的动机所在,从此出发,席勒进而演绎出三种时间性状态——即时间性较为迫切而浅近的感性冲动、时间性较为稀薄而永恒的形式冲动、时间性较为流畅且能同时包容以上两种冲动特性的游戏冲动,接下来,席勒又侧重对游戏冲动的最佳形态之一——审美活动作为内时间意识的构成及其特性做出了极为卓著的分析,并且在此基础上为理性在审美活动之中觅得了最为坚实的存在状态——依寓于审美活动之中并在内时间意识的构成中开启出来且持存延续,从而解决了在第11封信之中提出的之所以要倡导美育的问题。这是席勒美学思想之中时间性问题的一个完整而严密的思维链条,也正是席勒美学思想与审美教育思想的完美交织乃至交融。 二、美育活动之时间视域的自然显露 席勒在著作中并不是直接把现实问题一一道出,而是在第3封信之中,先指出“两种性格”——即“自然性格”与“伦理性格”之间的冲突,而后提出“第三种性格”来进行化解。就此著整体而言,这“自然性格”与“伦理性格”之间的冲突及其解决,正是贯穿于全书的核心与根本所在。 席勒审美教育思想的两大贡献就体现于此。其一,审美教育活动的意义在于以“第三种性格”来解决上述两种性格之间的冲突,在此后的行文中,席勒就更为明确地表述为以“游戏冲动”来解决“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之间的冲突。其二,“审美活动”作为最佳的“游戏冲动”与“感性冲动”、“形式冲动”两者之间在存在或构成状态上有着根本的差异,因而才能够肩负审美教育的重任,而且审美教育活动本身的构成状态就是如此。 而以上两大贡献正是在“时间性”的角度或者视野之内展开的,自前者而言,席勒解决的正是美育何以存在,更准确地说是其可能性——即“意义”的问题,这正是时间性之于美学的第一种可能性——审美教育活动(同时就是审美活动本身,只不过是更为理想的审美活动,因为其“意义”比一般的审美活动更为充盈丰富)产生于“意义”,产生于两种性格或者两种冲动之间的永恒冲突必须得以解决的“可能性”,正如海德格尔在西方哲学史上对“时间”或者“时间性”所做的革命性的阐释——“在这里,时间性将被展示出来,作为我们成为此在的这种存在者的存在之意义。……把此在解释为时间性,并不就算为主导问题即一般的存在意义问题提供了答案,但却为赢得这一答案准备好了地基。”[3] 最简捷地说,如果没有存在的意义与可能性——即“冲动”,审美教育活动是难以想象的,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审美教育活动在时间性状态上是难以想象的,先不要说审美教育活动的延续与持存,其能不能产生、开启就存在根本性的问题。就后者而言,席勒解决了时间性之于美学的第二种可能性——即审美教育活动作为理想化的游戏冲动或者审美活动在内时间意识维度上的构成状态问题,并且对审美活动与另外两种冲动在内时间意识的角度同样进行了卓著的对比。而且,以上两个方面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完全可以简捷地表述为——审美教育活动或者理想的审美活动是一种出于对意义的寻求或者冲动而开启并持存着的过程或者内时间意识,而且仅仅如此。 席勒在第3封信开头就为人的价值寻求设定了一个“时间”上的前景,他认为,人理应从纯自然的状态前进到理性的阶段,把物质的必然升华为道德的必然。但是,从时间的先后而言,人从感官的轻睡中苏醒过来,发现自己已在国家之中,在他还未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理性地位之前,强制就按照纯自然法则来安排他,在这个阶段,人只是处在自然的规定之中。而人在成年期,就必须以人为的方式去弥补童年期的不足,以便在观念中形式一个“自然状态”,但是这个状态只能通过人的“理性规定”来假设,即由童年期个人化的快乐原则转向成年期“契约化”的现实原则。而且,席勒认为,从个人到民族都要经历同样的不断提升进程,对于民族而言,就是要从“自然国家”改组成为“伦理国家”。 在两段不多的文字之中,充满了多重范畴的对立,这些对立完全可以用之后的、高度抽象的“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概念加以概括,比如从自然与理性、自然法则与伦理法则、童年与成年、独立地位与契约地位、自然国家与伦理国家、物质的人与伦理的人、现实的与推论的、兽性的与人性的,等等,在这些对立之中最为典型的体现就是在“时间”或者“时间性”上的维度展开的,因而本文所说的时间就绝不是客观时间意义上的时间,而是在人生意义或者价值实现领域之内的主观时间或者现象学意义上的时间,席勒把这种对立归结为:“倘若理性要废弃自然国家——因为要想代之以理性国家,就必须这样做——那么,它就得为了推论的伦理的人而牺牲现实的物质的人,就得为了一个仅仅是可能的(纵使从道德上看必然的)社会的理想而牺牲社会的存在。理性从人身上夺走的是人实际占有的,没有了这些他就一无所有,为了补偿,理性给人指出的是人可能和应该占有的。假使理性对人期望过殷,那么,为了人能有人性(人还缺乏人性,但缺乏人性无伤人的存在),它就甚至会夺走人获得兽性的手段,而兽性又是人性的条件。这样,人还没有来得及用自己意志握紧法则,理性就已经从人的脚下把自然的梯子撤走。”[2]17从中可以看出,“自然性格”与“伦理性格”之间的对立,正在于“时间性”之上的感性欲望所具有的“迫近性”与来自于“推论”或者“可能性”、“应该”的“遥不可及性”之间的对立,而且,席勒提出,如果不能实现两者的融合,那么,人就会处在两种极端的冲动之间来回剧烈摇摆。 可以看出,席勒美学思想不像康德那样是从一个被过度高扬了的主体性出发的,而是从一个不受扭曲的、完整的现实出发,尤其是从“意义”与“价值”寻求所自然而然导致或生发的现实出发的,那么,“自然性格”与“伦理性格”就是由“意义”生发的,这两者皆有其内在的、不可取代的价值。只是席勒是出于把两者相融合的角度,才提出应该发展“第三性格”,很显然,这种想法是对审美教育活动的过誉,虽然审美活动或者审美教育活动的确能够极为理想地把感性与理性相融合。因而,席勒的美育思想带有很强的空想色彩,不过,这种空想却也带有美丽的诗意,尤其是在他那颗诗人的心中以及美妙的语言之中,这种空想显得那么可爱。事实上,在绝对的或者极端的感性与理性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不偏不倚的领域,而且无法使用出自单纯的感性领域或者理性领域之中的概念与术语或者知识体系对其进行描述、阐释,这个领域在席勒看来就是“游戏”。 就席勒所处时代及此前的西方文化与学术来看,一直是在绝对的主观与客观之间来回地剧烈摇摆,而且在这两个方向上都发展出了极为辉煌灿烂的文化,最为典型的理想文化形态就是科学文化与宗教文化,在哲学上也是神学哲学与科学哲学极为发达,但是这种过于偏向绝对主观与绝对客观的哲学以及其滋生的美学知识系统——即神学美学系统与认识论美学系统,无法对处在“主客之间”的审美活动做出适当的描述与分析,也就是说,科学活动与宗教活动本身虽然在其构成上是主客不分的,但是其意义与价值却在于寻求绝对客观的知识与绝对主观的神灵。而审美活动则只能是主客不分的,即只有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对《红楼梦》的阅读之时,那种特定的、独一无二的审美活动才会诞生并持存;当阅读过程结束之后,审美活动也就结束了。西方的文化与学术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同样是一个在两者之间来回剧烈摇摆的情势,要么是单纯地倾向感性,要么是单纯地倾向理性,当然,从主导的方面来看,一般是主张理性活动是对感性活动的提升与压制,对于感性活动以及处在感性活动与理性活动之间的这一活动领域的“意义”缺乏必要的认识,当然,就更谈不上对感性活动以及这一感性与理性不分离的活动领域的构成形态进行具体而深入的分析了,尤其是从“意义”袒露的“时间性”视域。 而席勒正是从“意义”出发来审视人类各种活动的形态及其构成的,如上所述,席勒认为“自然性格”与“伦理性格”都是有意义的人类活动,而且也是必须的,不能互相替代或者僭越,虽然“理性活动”的“意义”往往在约定俗成的维度上远远高于“感性活动”。而且,也正如上述所言,席勒在第3封信之中,就已经提及在“感性活动”与“理性活动”之间的对立包含有时间性因素,在其后,席勒更是在一个比喻当中直接把“时间性”视域凸现出来,他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道德社会在观念中正在形成的时候,决不可让物质社会在时间上有片刻停顿,绝不可为了人的尊严而使人的生存陷入险境。一个能工巧匠修理钟表时总是先让齿轮走完再让钟表停下来,而修理国家这架活的钟表则必须让它走动,这就是说,必须是在钟表转动的情况下来更换转动着的齿轮。”[2]17~18在这段话中,席勒既描述了“自然性格”作为一种感性冲动在时间性上所具有的不可抑止的现在感与迫近感以及与“伦理性格”之间在“时间性”上的对立,又同时提出了塑造“第三种性格”的立足之处正是“意义”的驱使,而且也暗示出这种性格本身也必然是在时间性视域中才能得以现身。 具体而言,在席勒看来,“自然性格”自私而暴虐,其锋芒所向不是维护社会而是破坏社会;而“伦理性格”则是依据假设而定,而且这种性格无法体现为质料感坚实的感性活动,在席勒认为是:“从未显现过,所以立法者就无法支配它,也无法有把握地指望它。”[2]18因而,席勒认为,有必要去弥补两者的缺陷,“重要的是,要从物质性格中区分出任意性,要从道德性格中区分出自由,重要的是,使前者同法则相一致,使后者同印象相联系,重要的是,使前者离物质再远一些,使后者离物质再近一些,从而造出第三种性格。”[2]18这就是“第三种性格”得以产生的“意义”所在,也是其开启乃至持存过程的时间性之源,其根本的特性与构成状态在于:“这种性格和那两种都有连带关系,它开辟了从纯粹是力的支配过渡到法则支配的道路,它不会妨碍道德性格的发展,反倒会为目所不能见的伦理性提供一种感性的保证。”[2]18由于他是始终从生活或者人生“意义”出发来为自己的美学思想奠基的,所以席勒在自己美学思想以及知识系统之中,就必须清晰而完整地保持“意义”的实际状态,而不是只停留在口头上抽象地谈论“意义”。 这个“意义”的实际状态就是主客不能分离地存在,准确地说就是主体“始终—指向”客体的,因而不是绝对的客观,也不是绝对的主观,正是由于人类对不同的“价值”与“意义”的孜孜以求,他们才会“始终—指向”不同的对象,并为对象所奠基,人类的生活才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态,仅就席勒所说的这三种“性格”而言,“性格”绝不是仅仅发生在与对象或者客体无关的纯粹意识、精神或者心灵的层面,而是应该理解为一种生活的行为、事件或者实践,更应该理解为一个为了寻求“意义”与“价值”而持续地存在着、兴发着的行为、实践或者事件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主体是“始终—指向”客体或者对象的,这正是源源始始的时间性视域。 三、“第三种性格”对理性、感性“时间性”冲突的调节 在席勒看来,能够把“自然性格”与“伦理性格”融汇起来的“第三种性格”是一种极为圆满的性格,这对于一个人来说就是能够把眼前与未来完满地结合起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同样如此——即从“自然国家”到“伦理国家”,但是“自然国家”并不消失,而且其间必须经由一个可靠的中间环节。他认为,这是确凿不移的,也就是只有“第三种性格”成为一个民族的主导性格,国家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才不会产生危害,他说:“也只有这样的性格才能保证这一转变的延续。”这同样确定无疑地表明,这三种性格都是一种时间性的行为,而不只是一种孤立的心理现象。因为“道德国家”要建立起来的是系统而庞大的伦理法则,这些伦理法则体系显然是绝对超出个体利益与好恶的,是客观而普遍的立法。如果能够做到好德如好色,那就是最好了,席勒说,如果指望人的伦理行为就像是出自于自然或者本能,那么,这种行为本身就必须是自然的与本能的,也就是说伦理道德行为要出自于本能的冲动。要实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做到:“倘若人要保持这种选择的功能,而且在各种力的因果联系中他仍然是一个可靠的环节,那就只能由此而实现:那两种动机所产生的效果在现象世界中是完全相同的,他所欲求的物质总是同一的,尽管形式极不相同;也就是说,他的冲动与他的理性是完全一致的,因而能做到普遍的立法。”[2]20 如前所述,在西方哲学史上,“感性”是往往受到“理性”压制与否定的,席勒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人作为国家之中的国民,其注定会受到国家的制约、决定或者影响,因而,个人的未来与国家的未来是裹挟在一起的。席勒在第4封信之中提出,“伦理国家”往往会造成个体与国民在感性面貌上的丧失,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个体的“理性”与国家的“理性”是完全一致的,并且会受到国家的强行施行。 在席勒的思想之中,“理性”就是一个在心理学意义上的理想“自我”,也可以说是一个预期的“意义”,他说:“每个个人——可以这样说——按其天赋和规定在自己心中都是一个纯粹的、理想的人,他生活的伟大任务就是在他各种各样的变换之中,同这个理想的人永不改变的一体性保持一致。”[2]20那么,“伦理国家”所寻求的正是这样纯粹的人格,而且国家要做的就是:“竭力以客观的、可以说是标准的形式把各个主体的多样性统一成一体。”[2]21 在第4封信之中,席勒继续对“自然性格”与“伦理性格”所做的对比仍然与时间性密不可分,而且更为具体地说,是与“意义”以及“主客体”之间的构成状态直接相关。席勒对感性与理性之“意义”的看法同样不偏不倚,他说:“在片面的道德评价中,这种区分固然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只要理性的法则无条件地生效,理性就满足了;但在完全的人类学的评价中,这种区分就更得予以考虑,因为在那里内容与形式同样重要,同时活生生的感觉也有一份发言权。”而席勒将其对立简洁地表述为:“理性要求一体性,而自然要求多样性,这两个‘立法机构’人都得应付。”[2]21理性活动与自然活动本身之中的两个基本的相关项是主体与客体,也就是说,在其活动之时,主体是始终指向客体的,但是由于价值与意义寻求的差异,理性活动要经由一个主客不分的时间性过程,最终的目的是要达到客观、抽象或者普遍性的“理性”本身,这一“理性”本身却是与个体的好恶不相干的,在“理性”本身里再也没有个体的因素,也就是说,“理性”彻头彻尾是超越性的。 但是在感性活动之中,由于所“始终—指向”的对象的变化,感觉本身就必然会变化,而“始终”正是其中的时间性因素。鉴于国家之于个人的影响更大,所以席勒提出国家应该在维护理性原则的同时,要爱惜来自于感性的生动与多样性,他说:“人铭记理性的法则是由于有不受诱惑的意识,人铭记自然的法则是由于有不可泯灭的情感。因此,倘若伦理性格只靠牺牲自然性格来保持自己的地位,那就证明还缺乏教化,倘若一部国家宪法只有通过泯灭多样性才能促成一体性,那样的宪法就还是非常不完善的。国家不应只尊重个体中那些客观的和类属的性格,还应尊重他们主观的和特殊的性格;国家在扩大目不能见的伦理王国的同时,不应使现象王国变得荒无人迹。”[2]21因而,席勒所面对的问题一直就是两元对立的冲突,这些冲突的形态虽然多种多样,但是都是围绕着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冲突或者以此作为机杼而呈现出来的。 在席勒看来,“第三种性格”就是教育与教化的目的。如果能够得到理想的教育与教化,那么,一个美好的未来就会在个人与国家之前呈现;也只有在个体或者国民业已形成“第三种性格”的基础之上,一个强制的国家才会演化为自由国家;但正如上述,国家对于个人或者国民而言往往是处于绝对强者与压制者的地位,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就会是在国家尤其是自由国家之中才会形成这样完整性的性格。因而,席勒在此必然把目光投向国家对个人性格的养成——也就是教育以及审美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