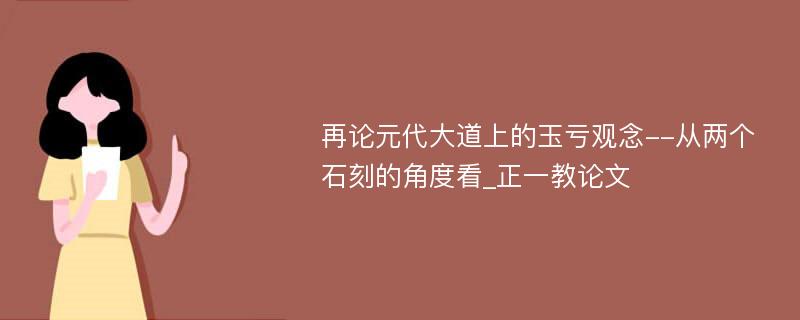
元代大道教玉虚观系的再探讨——从两通石刻拓片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拓片论文,元代论文,石刻论文,玉虚观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道教为金代中叶兴起于河北地区的一支新道教,与全真、太一教在金元两代兴盛一 时。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垣先生即曾在其名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专辟一卷《 大道篇》,对大道教在金元两代的发展情况予以探讨。但苦于当时传世资料太少,留下 许多问题尚待澄清。截至80年代以前,除袁冀(袁国藩)《元代真大道教考》一文对大道 教史有所增补外(注:原载《大陆杂志》43—4,后收入作者《元史研究论集》,台北商 务印书馆1974年版。),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986年,陈智超先生在新 发现材料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指出大道教在蒙元之际曾发生过分裂,出 现了天宝宫与玉虚宫(作者认为原为玉虚观,后升为玉虚宫)两支,并对其历任掌教传授 及教派发展、宫观分布、组织机构等进行了详尽研究,把这方面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 步,大道教的真实面目也因此渐趋明朗。(注:陈智超:《许昌天宝宫访碑记》,《中 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6期;《真大道教新史料——兼评袁国藩<元代真大道教考>》 ,《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4期;《金元真大道教史补》,《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 。陈文有关大道教的研究成果,目前已为国内道教史论著普遍采用。)最近,笔者在研 究过程中,又找到一通与大道教有关的拓片,发现此拓片既为《道家金石略》(陈垣编 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所不载,也向来为道教史研究者所忽 略,而通过此拓片,再与《道家金石略》所收另一通拓片进行对比,应当会对大道教在 元代的发展演变得出一些新的认识。为此,特撰此文,希望能引起有关专家学者的重视 。
一
首先介绍《道家金石略》没有收录的拓片。该拓片现藏国家图书馆,编号为顾1016, 曾收入国家图书馆金石组所编《北京图书馆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64册(中州古籍 出版社1990年版),题为《代祀济渎投龙简记》,《全元文》第2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 01年版)据此过录全文。原拓高73厘米,宽79厘米。以下为拓片原文。
代祀济渎投龙简记 进士史芝书丹
今皇帝意谓纂祚以来,上天垂祐,国泰民安,特遣代礼官中顺大夫、左侍仪、奉御也 先乃,赍御香法信醮用物仪,诣大都玉虚观修建金箓大斋三昼夜。于正月二十八日,集 十方经箓道士一坛,预奏上天,开闻三界。二月一日,奏表发牒,启行法事。至初三日 子刻,设醮三百六十分位,进词拜表,质明事毕。续奉圣旨,复委宣授掌管诸路正一大 道七祖圆明玄悟真人杜福春、奉御黑驴,赍奉金龙玉简纽璧青丝,诣济渎灵泉水府投进 。于三月初三日,率领中顺大夫、怀孟路总管兼诸军奥鲁严忠祐,从仕郎、济源县尹兼 诸军奥鲁赵镇,主簿兼尉郭衡,就济渎渊德殿,修设太上投龙进璧清醮二十四分。仰答 □□灵明,用申诚恳。有兹盛事,当纪其实,因以□□记云。
至元十二祀三月日,怀孟路教授袁志远记。
宣授济庙提点李若存、知庙郭若能立石。
济渎,在今河南省济源县,属岳镇海渎中的四渎之一,为中国历代王朝传统祭祀场所 ,留下了大量相关石刻资料。元朝建立后,从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起开始正式实行岳 镇海渎代祀制度,“其天子亲遣使致祭者三:曰社稷,曰先农,曰宣圣。而岳镇海渎, 使者奉玺书即其处行事,称代祀”(注:《元史》卷七二《祭礼志一》,中华书局点校 本。有关元朝代祀的研究,可参见日本学者森田宪司《元朝における代祀について》, 日本道教学会《东方宗教》第98号(2001年)。)。岳镇海渎的代祀,依地理方位的不同 ,先后有过五道、三道,复为五道的区域划分。“道遣使二人,集贤院奏遣汉宫,翰林 院奏遣蒙古官,出玺书给驿以行。中统初,遣道士,或副以汉官。”(注:《元史》卷 七六《祭礼志五》。)至元十二年,为公元1275年。据拓片所载,当年正月二十八日, 元朝政府曾在大都玉虚观,也就是大道教玉虚观系的总部所在地,召集全国各地道士, 举行了为期三天的金箓大醮。文中划线部分提到的“宣授掌管诸路正一大道七祖圆明玄 悟真人杜福春”,在当年二月,奉命代祀济渎。当时,济渎所在地怀孟路的最高地方行 政长官为严忠祐,他是大蒙古国时期著名汉人世侯严实的幼子,后官温州路总管。(注 :严忠祐资料,可参见萧启庆《元代几个汉军世家的仕宦与婚姻——元代统治菁英研究 之二》所附表三《东平严氏世系》、表十九《东平严氏仕进资料》,《蒙元史新研》, 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288、318页。)杜福春一行抵达当地后, 于三月三日,率领严忠祐及其属下,在济渎渊德殿举行了代祀仪式。此外,还需提到的 是,元朝此次遣使代祀济渎,并不是一次孤立的活动。据《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至元十二年二月庚午,“命怯薛丹察罕不花、侍仪副使关思义、真人李德和,代祀岳、 渎、后土”。李德和为大道教天宝宫系的七祖,奉命代祀的时间,与杜福春差不多,二 人参加的应是不同道分的代祀活动。其中,李德和因参与代祀后土,而元代后土祠正是 在此前不久设于平阳路临汾县(注:《元史》卷八《世祖纪五》至元十二年二月甲辰条 ,另可参见程钜夫《雪楼集》卷一《皇太后遣使祭诸神文一十九首·后土》,陶氏涉园 刻本。),故其活动范围应主要在西面,杜福春则分管南面。
杜福春的名字,以前仅见《至元辩伪录》卷六《焚毁伪道藏经碑》(《佛祖历代通载》 卷二一内容与之相同),因他是与天宝宫系七祖李德和一起参加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 )佛道大辩论的,陈智超先生在《金元真大道教史补》一文中曾推测他有可能就是大道 教玉虚观系六祖崇玄体道普惠真人刘有明的继承者,也就是玉虚观系的七祖。现在,陈 先生这一推测应该说已完全得到证实,而且,杜福春的封号“圆明玄悟真人”,以前不 见于任何记载,亦可补史乘之缺。不过,笔者这里最感兴趣的是,杜福春的头衔中为什 么会出现“正一”二字?即为什么会是“宣授掌管诸路正一大道七祖”,而不是“宣授 掌管诸路大道七祖”?他当时是受命以大道教掌教身份兼管北方的正一符箓道派,还是 所在的玉虚观系教派名称已经由“大道”更名为“正一大道”?
接下来是《道家金石略》收录的一通拓片。此拓片原为缪荃孙氏艺风堂藏品,现藏北 京大学图书馆,后收入《道家金石略》(第863页)。原碑高二尺一寸,广一尺六寸,十 七行,行二十三字。以下为拓片原文:
周天大醮投龙简记
泰定改元甲子之春正月,诏玄教大宗师玄德真人吴全节、太一崇玄体素演道真人嗣教 七祖蔡天祐、五福太一真人吕志彝、正一大道真人刘尚平、玄教嗣师真人夏文泳,率法 师道士几千人,修建金箓周天大醮于大都崇真万寿宫,为位二千四百,昼夜凡七。受厘 之日,天颜甚愉,重封香币,遣太一七祖真人蔡天祐,承德郎、郊祀署令马怀吉,捧刻 玉宝符,玄璧龙纽,驰诣济渎清源投奠。五月初三日至祠下,醮祭如礼,质明沉龙简于 水府,礼成而退。郡守嘉议大夫、怀庆路总管李德贞,奉议大夫、孟州知州刘士冕,怀 庆路知事苏让等咸与焉,谨记。
济源县尉权县事禹邦献。
泰定元年五月 日立。
这通拓片也与代祀济渎有关,标明的年份为泰定元年,也就是公元1324年。当年正月 ,玄教掌教吴全节、太一掌教蔡天祐等道教首领奉命在玄教总部——大都崇真万寿宫为 元朝皇帝举行金箓周天大醮。仪式结束后,太一掌教蔡天祐等奉命南下,于五月三日会 同当地官员代祀济渎。这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文中划线部分的“正一大道真人刘尚平 ”,此人它处不见记载,但他真人头衔前面的“正一大道”四字,肯定不是元朝习惯上 的道教四字真人封号。与之性质类似的还有拓片中提到的“五福太一真人吕志彝”。“ 五福太一”又常作“五福太乙”,为道教传统信仰中统御五方五帝的至上天神——太一 十神之一(注:据沈括《梦溪笔谈》(中华书局点校本)卷三:“十神太一,一曰太一, 次曰五福太一,三曰天一太一,四曰地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基太一,七曰民基 太一,八曰大游太一,九曰九气太一,十曰十神太一。”),曾受到宋朝皇室的大力尊 崇,对宗教信仰采取兼容并蓄政策的元朝也是如此。据《元史》记载,早在成宗大德元 年(公元1297年)正月,元朝即建有“五福太乙神坛”(注:《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 》。)。此后,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二月,“命道士祭五福太一神”(注:《元史》卷 二九《泰定帝纪一》。)。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八月,“以立冬祀五福十神、太一真 君”(注:《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二年(公元1331年)正月,“敕每岁四祭五 福太一星”。二月,“创建五福太一宫于京城乾隅”(注:《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 》。)。苏天爵的文集中,有一篇《五福太乙宫上梁祝文》,即应为其所作(注:《滋溪 文稿》卷二四,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卷七二《祭祀志一》又云:“五福太乙 有坛畤,以道流主之,皆所未详。”由此看来,这个吕志彝,很有可能就是肩负此项皇 家使命的道士。既然吕志彝的真人头衔代表的只是他的职掌范围,我们同样有理由认为 刘尚平的真人头衔也是如此。如果这一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刘尚平的“正一大道真人 ”头衔与杜福春的“宣授掌管诸路正一大道七祖”头衔肯定有着某种密切联系。
二
我们现在再回到前面所提出的问题,既然“正一大道”的称呼在元代前期、中期曾两 度出现,那么它是大道教玉虚观系兼管北方正一符箓道派的结果呢?还是大道教玉虚观 系更改了教派名称了呢?
先看第一种情况。
元代道教的分布格局,在北方主要为全真、太一、大道等道教新派,在南方则主要是 以龙虎山天师教为首的传统符箓道派。不过,这种格局只是大略言之。拿北方来说,全 真教等新道派出现后,虽然有不少旧道派改宗新派,但仍有不少旧道派保留下来,并继 续得到发展。像易州龙兴观,即出自龙虎山三十代天师张继先门下,“祖师韩真人,初 与同志萧、路、杜三真人浮江而南,拜三十代天师,受天心正一法,得法而归北方,学 者遂共立萧、韩、路、杜四真人之教”(注:《易州龙兴观宗支恒产记》,《道家金石 略》,第986页。)。在金、元两代,龙兴观一直是传授正一盟威法箓的道观,而且在当 地还发展了不少支观(注:这方面的材料,《道家金石略》收入很多,除了《易州龙兴 观宗支恒产记》外,还有《易州玉泉观碑铭》(第866—868页)、《易州龙兴观懿旨碑》 (第937页)、《易州龙兴观提点缑公功行记》(第980页)、《易州龙兴观宗支道派》(第9 87—989页)等。)。再如,忽必烈早年颇受宠信的王一清,也是一个正一道士。丙辰年( 公元1256年)忽必烈建开平府时,曾请他作醮五天,并南下代祠济渎。(注:《创建开平 府祭告济渎记》,《道家金石略》,第865页。日本学者樱井智美曾在1998年8月于内蒙 古正蓝旗召开的中国蒙古史学会学术研讨会上提出过与此有关的研究报告,并专门探讨 过王一清其人。)忽必烈率军南下伐宋期间,王一清奉命潜往龙虎山,与三十五代天师 张可大秘密接洽。(注:《元史》卷二○二《释老传》。)不久,又奉命到鄂州前线晓谕 南宋守将,结果被杀。(注: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七《宿州与宋国三省枢 密院书》,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这个活跃一时的王一清,是北方道士,还是 南方道士,我们目前还无法完全确定。(注:《至元辩伪录》卷四在叙述公元1258年第 一次佛道大辨论时,提及道教一方参加的阵容为“道士张真人、蛮子王先生、道录樊志 应、道判魏志阳、讲师周志立等二百余人”,其中的“道士张真人”,当为全真教掌教 张志敬,“蛮子王先生”为何人,无从察考,但从其“蛮子”的称呼来看,像是个南方 人,不知是否即为王一清。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那么,此次佛道大辩论的道教一方 全为全真道士的传统观点就值得商榷了。)但他的法脉,肯定也是在北方传播的,他的 弟子文德圭,后来还受命住持彰德府大上清正一宫,并被元朝封为“纯静抱一辅化真人 ”(注:《大上清正一宫碑》,《道家金石略》,第856页。)。
不过,尽管北方有传授正一盟威法箓的教派踪迹可寻,但元朝对道教各派的行政管理 ,主要采取的是按地域,而不是按教派分而治之的政策,即基本上是由全真教主持北方 道教事务,龙虎宗及其支脉玄教共同主持南方道教事务。当时,全真教这方面的常设管 理机构为“玄门道教所”(注:《纯阳万寿宫札付碑》,《道家金石略》,第791—792 页。),龙虎宗与玄教则分别为“江南诸路道教所”与“江淮荆襄等路道教总摄所”( 注:《承天观公据》、《灵应观甲乙住持札付碑》,《道家金石略》,第875—878、93 8—941页。按,承天观与灵应观,一在太平路,一在杭州路,二者均位于江南地区,但 又都离长江不远,属龙虎宗与玄教双重管辖地带,因而上述两通拓片都有龙虎宗与玄教 共同处理道教事务的记载。)。这种管辖权的分配,使得北方许多传统符箓道派,大都 划归全真教统辖,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前面提到的易州龙兴观。据《易州龙兴观提点缑公 功行记》,龙兴观提点缑德宁,先是“至正六年(公元1346年),受长春宫真人法旨,玄 远安素大师、玄坛提举”,后又于“八年正月,进神仙玄门演道大宗师掌教大真人法旨 ,令充本宗门下提点,仍赐金襕紫服”(注:《道家金石略》,第980页。)。长春宫为 全真教的总部——堂下,“神仙玄门演道大宗师掌教大真人”则指全真教的末代掌教完 颜德明,这表明,易州龙兴观应当是归全真教管辖的。相反,由大道教兼管北方正一教 的事例,我们在现存文献中却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
既然排除了玉虚观系管辖北方正一符箓道派的可能,那么,它改名为“正一大道”的 可能性当然也就大大加强了。由于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玉虚观所立碑文仍题为《玉虚 观大道教祖师传授之碑》(注:《顺天府志》卷八《玉虚观大道教祖师传授之碑》(节文 ),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缪荃孙辑本。),则玉虚观系改名,似不早于该年,本文前面提 到的“正一大道”名称出现于至元十二年,则玉虚观系改名的最迟年份应不晚于是年, 也就是说,玉虚观系更改教派名称的时间应当在至元三年到十二年之间。那么,玉虚观 系为什么要改名为“正一大道”呢?笔者觉得有必要从早期大道教与符箓道派的历史渊 源中寻找线索。
众所周知,大道教自创立时起,就是一个民间伦理色彩较为浓厚的教派。始创人刘德 仁曾立教戒九条:“一曰视物犹己,勿萌戕害凶嗔之心。二曰忠于君,孝于亲,诚于人 ,辞无绮语,口无恶声。三曰除邪淫,守清静。四曰远势利,安贱贫,力耕而食,量入 为用。五曰毋事博奕,毋习盗窃。六曰毋饮酒茹荤,衣食取足,毋为骄盈。七曰虚心而 弱志,和光而同尘。八曰毋恃强梁,谦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注:宋 濂:《宋文宪公集》卷二六《书刘真人事》,《四部备要》本。)这些戒条都是一些洁 身自好的社会伦理规范与处世规则。《元史》卷二○二《释老传》称“其教以苦节危行 为要,而不妄取于人,不苟侈于已”,可谓点出了大道教义的理论精髓。由此可见,大 道教起初的立教宗旨与符箓道派应当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正一”,是符箓道派特有 的名称,指正一盟威秘箓,及行此经典的符箓道派及道众,其中主要指江西龙虎山天师 所传龙虎宗一脉。龙虎宗后来在元代又融合了其他符箓道派,发展成为今天的正一教。 至于北方的传统符箓道派,由于金朝全真、太一、大道等新道派的兴起,发展历史几乎 被完全淹没。目前的道教史研究著作,在叙述金元之际中国北方的道教发展史时,对新 道派不惜倾注大量笔墨,可对旧道派却不著一词,也给人造成一种旧道派在北方几近绝 迹的假象,但前面已经提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北方符箓道派不仅续有传人,而且在 与新道派的接触中互有影响,大道教即为这方面的一个实例。
大道教与正一符箓道派发生关系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大道三祖张信真(公元1164—12 18年)。明嘉靖《青州府志》卷一六《仙释传》(注:天一阁明代方志丛刊本。)与明王 圻《续文献通考》卷二四三《仙释考》(注:现代出版社影印万历刻本。),都曾提到他 先是从二祖陈师正学道,后又于燕京天长观问天师,授正一盟威秘箓。只不过因为天师 是江西龙虎山张天师的专门称谓,天长观不应该有此称号的道士,学者们才普遍对这段 材料持保留态度。燕京天长观,据《顺天府志》卷八引《元一统志》,“在旧城昊天寺 之东会仙坊内”,始建于唐开元年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道教观宇。金朝统治期间,曾 多次征召道教各派名道居此,其中就有大道教的创始人刘德仁。(注:《宋文宪公集》 卷二六《书刘真人事》。)全真教掌教丘处机西行回京后,将其扩建为全真教观宇。虽 然天长观在金代未必有天师其人,但曾由旧道派把持,却是毫无疑问的,其中极有可能 就有传授正一盟威秘箓的道士。如果再结合“正一大道”称呼的两度出现,由此透露出 的大道教与符箓道派所发生的接触,更不应被轻易否定。而且,如果再作大胆假设的话 ,大道教出现的这种向符箓道派靠拢的倾向,因与其立教宗旨相悖,很有可能会在教内 产生意见分歧。大道教最后走向分裂,教内的这种意见分歧或许正是其中一个重要诱因 。
三
大道教的分裂始末,由于缺少文献记载,至今仍是迷雾一团。这里只简单谈一下笔者 的一些看法。笔者认为:虽然从理论上讲,天宝宫系的真大道教更符合原来的大道教义 ,但就掌教的传承系统而言,玉虚观系的正一大道教才算是大道教的嫡脉正传,而且起 初地位也在天宝宫系之上,天宝宫系则是从大道教分裂出来的一个新教派,只是后来居 上,才最终成为“大道正宗”。笔者的这一结论是在对两大教派现有记载反复推敲后得 出的。
首先,天宝宫系在追溯历任掌教传授时,称四祖毛希琮“见姓达聪,罔愆成法,心厌 尘世,不永斯年,掌教五星有奇,得年三十八岁,复以教法逊与五祖太玄真人郦君”; 五祖郦希成“阐教三十六年,享寿七十八岁”;六祖孙德福“敷化一十五年,享寿五十 六岁,于至元癸酉四月念(廿?)二日以微疾而终”(注:《洛京缑山改建先天宫记》,《 道家金石略》,第818页。)。至元癸酉为公元1273年,由此逆推51年,郦希成出任掌教 的时间应该在公元1222年前后。陈垣与陈智超先生均认为,四祖毛希琮在公元1223年去 世,五祖郦希成担任掌教的时间应当在公元1223年到公元1259年。但有的材料显示,毛 希琮在公元1223年后依然健在,因为直到公元1227年全真掌教丘处机于长春宫踞厕而亡 时,毛希琮还曾作诗讥讽:“一把形骸瘦骨头,长春一旦变为秋。和濉带屎亡圊厕,一 道流来两道流。”(注:《至元辩伪录》卷三,大正新修大藏经本。)对此,陈垣先生《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认为“轻薄殊不足信”,陈智超先生《金元真大道教史补》也认 为:“毛希琮比丘处机早卒四年,何能有诋毁丘死之语?”但玉虚观系的记载:“四祖 毛希琮号纯阳子,复得希夷之传。丁亥(公元1227年),葺玉虚观以居之。戊子(公元122 8年),乃立李希安为五祖。”(注:《顺天府志》卷八《玉虚观大道教祖师传授之碑》( 节文)。)无疑表明毛希琮最晚的活动年代应当在公元1228年。这一记载,不仅比天宝宫 系出现得要早,而且由当朝显赫人物出面——参知政事杨果撰文,商挺书写,中书省右 丞相史天泽立石,树碑于玉虚观以晓示众人,真实性不容轻易否定。而且,天宝宫系的 记载称:“四祖师毛君(毛希琮),暑月病剧,速召而来燕。既承其法,拂袖有深山之隐 ,慕道之徒,翕然而从。”(注:《重修隆阳宫碑》,《道家金石略》,第823页。)其 中的“拂袖有深山之隐”之语,无疑表明郦希成在当时是没有接任成掌教职位的,不管 这是出于他的主观意愿,还是出于万般无奈。因此,综合以上记载,我们有理由认为, 大道教实际上是由毛希琮最终传给李希安的,即使天宝宫系的说法属实,也只能说是毛 希琮曾一度有过传位郦希成的念头,此后仍由毛希琮主持大道教,直到公元1228年立李 希安为接班人为止。
其次,四祖毛希琮与两位五祖郦希成、李希安,从他们的名字都有“希”字来看,应 是同辈师兄弟,或许同为三祖张信真的弟子。前面谈到,张信真曾在天长观学习过正一 盟威秘箓,他的这种经历很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弟子,而这种与大道创教宗旨迥然有 别的教法,势必会在弟子中间产生分歧。从天宝宫系称毛希琮“罔愆成法”的评价来看 ,毛希琮在天宝宫系眼中似乎走得还不是太远,但在当时双方实际上已经剑拔弩张了。 郦希成作为教门举正却跑到山东去阐教,不知是否是受教内势力排挤所致,但天宝宫系 把他接任掌教的年代定在毛希琮生前,显然已不承认此后毛希琮掌教的合法性。所谓“ 初,大道郦五祖者,逃难此山(妫川水谷)”,“逆魔乱起,始终十五载,遭逢十七大魔 ,以五祖道德崇高,威灵显赫,魔不胜道,寻乃自平”之类的记载(注:王恽:《秋涧 集》卷五《游妫川水谷太玄道宫》诗注,《四部丛刊》本;《洛京缑山改建先天宫记》 ,《道家金石略》,第818页。),反映出双方的斗争是很激烈的。
其三,元人吴澄在回顾天宝宫系的发展历史时,有过这样一段叙述:“郦始居天宝宫 ,际遇国朝,名吾教曰真大道,自为一枝,不属在前道教所掌。”(注:吴澄《吴文正 公集》卷二六《天宝宫碑》,台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这一事件发生在“宪宗皇帝 即位之四年”(注:《顺天府志》卷七《大元创建天宝宫碑》(节文)。),即公元1254年 。其中,吴澄所说的“在前道教”,显然应指玉虚观系而言。因为在此之前,玉虚观系 五祖李希安已经“岁在辛丑(公元1241年),被征命,辞老不起,宪宗皇帝以法服赐之” (注:《顺天府志》卷八《玉虚观大道教祖师传授之碑》(节文)。),获得蒙古统治者的 青睐。即便天宝宫系自立门户后,它同玉虚观系的地位在起初也不尽平等,这从两大系 统掌教的封号可以体现出来。元代道教封号分帝君、真君、大真人、真人、大师等不同 等级,同一等级以封号字数多者为优(有二、四、六、八字等区别)。元初,帝君、真君 、大真人封号还未出现,道教最高封号者为真人,其中势力最大的全真教掌教封号多为 六字。大道教势力相对较弱,两大掌教传承系统中,天宝宫系五祖郦希成的封号为太玄 真人,玉虚观系五祖李希安的封号为冲和妙应真人(注:李希安的真人封号在《玉虚观 大道教祖师传授之碑》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据《顺天府志》卷八引《元一统志·福元观 》:“至元四年夏,嗣教六祖刘有明立碑颂大道冲和妙应真人道行。”刘有明至元三年 嗣任掌教,其立碑所颂扬者,很有可能就是李希安。),比前者多出二字;天宝宫系六 祖孙德福的封号为通玄真人,玉虚观系六祖刘有明的封号为崇玄体道普惠真人,比前者 多出四字。从中不难看出,二者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还是有高低之分的。
郦希成了争得大道正宗地位,作了很多舆论准备。据《大元创建天宝宫碑》(节文): “无忧(即大道教创始人刘德仁)之厌世也,谓门弟子曰:‘后五十年吾复来此。’及期 而太玄郦君(郦希成)方嗣玄法,识者谓无忧后身也。自是其教日盛,风行四方,学者响 应。”就在毛希琮修葺玉虚观的同一年,郦希成也在燕京创建了天宝宫。“初,太玄之 主法席也,岁在丁亥,冲虚高弟刘希祥(冲虚为三祖张信真,刘希祥属‘希’字辈,当 为郦希成、李希安的师兄弟)等市燕故都开阳里废宅为焚修之所,为殿为门,像设俨然 ,辟道院以栖云众,正函丈以遵(尊?)师席……(至元)十年,敕赐宫额曰‘天宝’。” 为了与玉虚观系争夺正统,郦希成还特地将教派命名为“真大道”,用教内人士的话来 说,就是“教门得真假之分”(注:《洛京缑山改建先天宫记》,《道家金石略》,第8 18页。)。在他们看来,既然天宝宫系所传大道为“真”,那么玉虚观系所传自然就是 “假”的,或者说是“伪”的了。到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在八祖岳德文的请求下, 《制赠大道正宗四世称号碑》正式树立于天宝宫,这表明,在经过多年努力后,真大道 教的正宗地位已完全得到元朝政府的认可。
四
最后简单谈一下正一大道教在元代的发展走向问题。不少道教史论著在谈到大道教分 裂后的历史时,因对玉虚观系七祖杜福春之后的传承不甚明了,多主张玉虚观系此后因 势力微弱,并入了天宝宫系,而合并后的真大道教,最后又融入了全真教。(注:卿希 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页。)现在看来,问题 并没有那么简单。如本文前引第二通碑拓资料所述,至少到泰定元年,依然还有正一大 道(玉虚观系)真人刘尚平的存在,他在教内的身份虽还不能十分确定,但从与他一起参 加周天大醮的道士身份来看,他即使不是正一大道的掌教,也是仅次于掌教级的人物( 当然,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而与刘尚平一起参加周天大醮的道士所属教派,不论 是玄教,还是太一教,都是清一色的符箓道派。这表明,直到元朝中期,正一大道教的 符箓色彩依然较为浓厚,这与当时张清志所主持的真大道教风格完全迥异。从这种意义 上讲,二者合并的可能性应该说是微乎其微。相反,如果说正一大道教与玄教、太一教 一样,最后都融入了正一教,至少在逻辑上倒能说得通。
目前有的道教史论著,讨论元代道教各派的发展史,当出现掌教传承不明、无法考证 的情况时,经常过早地得出该派有可能并入另一派的结论,而从我翻检这方面资料的印 象来看,元代后期道教各派传承的不明,更有可能是因为资料散佚的缘故。像茅山宗, 以前的道教史论著乃至各种辞书,大都认为茅山宗到第四十五代宗师刘大彬即不见传承 ,而我们现在却仍能发现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有关“宣授冲素明道贞一真人、嗣上 清经箓四十六代宗师、主领三茅山道教、住持元符万宁宫事王天符”(注:《三清阁石 星门记》,《句容金石记》卷六,《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 03年版,第811页;《茅山元符万宁宫碑》,《道家金石略》,第989页。这位王天符, 很可能就是王袆《王忠文公集》卷一七《跋五牙元精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提到的“茅山王宗师”。)的记载。大道教应当也是如此,虽然两派掌教的记载,到泰 定年间即已不见史乘,但我们绝不能就此认为它们不久就消亡了。实际上,真大道教直 到元朝末年仍有活动见于记载。(注:《道家金石略》所录真大道教碑拓最晚到元统三 年(公元1335年)(见《辉州颐真宫圣旨碑》,第835页)。陈智超前揭文则提到后至元二 年(公元1336年)与五年(公元1339年)两通新发现的真大道教碑刻。)我想,在元末战乱 发生以前,这些教派更有可能都存在,它们的分化瓦解与重新整合应当是更晚的事情。
附:大道教传承表
(初祖)无忧普济开微洞明真君刘德仁
(二祖)大通演教真人陈师正
(三祖)冲虚静照真人张信真
(四祖)体玄妙行真人毛希琮
天宝宫系(真大道教) 玉虚观系(正一大道教)
(五祖)太玄真人郦希成(五祖)冲和妙应真人李希安
(六祖)通玄真人孙德福(六祖)崇玄体道普惠真人刘有明
(七祖)颐真体道真人李德和(七祖)圆明玄悟真人杜福春
(八祖)崇玄广化真人岳德文(不详)真人刘尚平
(九祖)崇真广道真人赵□□
(十祖)明照湛然普化真人赵德松
(十一祖)明真慧照观复真人郑进元
(十二祖)凝神冲妙玄应真人张清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