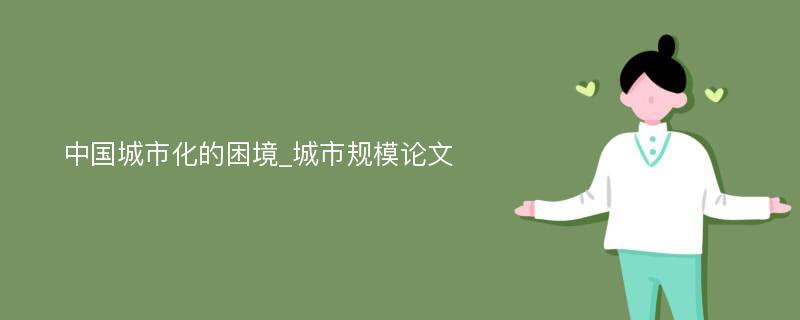
我国城市化的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文献标识码〕 A
一 城市化与工业化孰重
城市化虽然是人们十分熟悉和普遍关注的话题,但理解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却不是这么简单。这里提出“城市化与工业化孰重”的命题,不是字面上城市化与工业化谁更重要的意思,而是如何处理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内在关系。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内在关系机理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城市化必须在工业化达到一定水平后才会产生,或者说,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基础条件。对于我国而言,不仅城市化水平低下,而且工业化水平也并不高。因此,不能在轻视工业化基础条件建设的观念下来盲目推进城市化。另外,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很大的平衡性,这主要是由于工业化水平的地区间巨大的不平衡性所导致的。因此,我国不同地区的城市化需求规模差异必然是很大的。规定我国城市化进程和限定我国城市化模式都是十分有害的。
第二,城市化对工业化的拉动功能是存在的,但不能过度估价城市化对工业化的带动功能。实际上,城市化对工业化带动能力的提升必须至少具有三个前提:一是该地区或该城市具有产业基础或区位条件或人力资本,即具有相对比较优势条件;二是该地区或该城市具有产业集聚能力,特别是新兴产业或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能力(这是城市相别于农村、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优于城市化水平低的地方的重要秉赋);三是该地区或该城市具有政策上的优势。如我国深圳特区通过政策优势来形成生产要素集聚的区域优势,进一步提升了区域工业化水平。这其中尤以第二个条件最为关键。不难发现,要同时达到这三个条件的地区或城市是很少的。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弱化城市化对区域工业化的带动能力,进而反过来对区域城市化产生不利影响。我国不少率先推进城市化的沿海城市,都是期望通过相对发达的城市化水平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进而提升自身利用外资的能力。但由于缺少上述第二个条件的有力支撑,国家对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又基本收回,因此,这些沿海城市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城市化拉动工业化的效果。
第三,提供充裕的就业机会和提高生活环境质量是决定城市化绩效高低的主要因素。就我国目前城市化而言,由于城市化与工业化互动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不少地区的城市化缺少工业化基础,城市化没有能拉动区域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亦导致城市第三产业需求严重不足,发展缓慢。必须强调,我国不少地区城市化指导思想和考核目标只是限于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城市基础设施修建和改造的情况,而这些都只是城市化的外部表征,其不应成为衡量我国城市化的内在指标。
在我国城市化战略目标和战略选择上也要及时创新。两院院士周干峙教授在今年政协会议上提出,要冷静对待城市化,对城市化要科学地引导,城市化并不仅仅是把城市搞大一些,弄漂亮一些,要尽量花小的代价取得长远的效益。他强调,工业经济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健康的城市化发展必须与城市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相对而言,大、中城市比小城市或小城镇在产业集聚,特别是新兴产业或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竞争优势建设方面的优越条件要多得多,因此,要创造条件,放手让大中城市迅速成长起来。20世纪80年代初召开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了我国城市化发展战略,即“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这成为20多年来指导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这20多年中,我国一直奉行控制大城市发展的方针。但客观上,由于我国大城市在各种条件供给方面比小城市要优越得多,我国大城市规模并没有得到控制,大城市个数20年来扩大了一倍。而大城市的产业集聚能力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因此,我国不宜采取单一的控制大城市发展的战略,我国大中城市发展战略必须相应创新。同时,对我国大中城市发展的重点不能仅仅定位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而且要扩展到能形成产业集聚,特别是新兴产业或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竞争优势建设的新型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上来。
二 城市化中的政府独角戏
城市化中的政府独角戏主要是指各级政府承担了城市化发展战略、城市规划、城市基础设施供给、运营、维修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筹集和城市功能定位等多方面的主体工作甚至全部工作。在我国当前的城市化浪潮中,有三个现象特别耐人寻味。一是各级政府对城市化“情有独钟”。在不少地区,由于工业化水平的不配套或者滞后,地方政府的这种城市化偏好往往是“剃头挑子一头热”,这使得这些地方政府对城市化的推进努力得不偿失。二是各级地方政府大多用过多供给城市基础设施来替代城市化,大部分是将城市基础设施供给与城市化划等号。三是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其由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化主角角色向转轨时期城市化独角角色的快速转移。因此,在我国大多数地区城市化浪潮中,特别是一些工业化水平还相对很低的地区,工业化和居民对更高的城市化的需求规模很小,此时地方政府就成了推动这些地区城市化的主要力量或全部力量。
导致我国地方政府实现其由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化主角角色向转轨时期城市化独角角色的转移并承担城市化中的政府独角作用的原因主要如下:第一,由于国有资本在工业化进程中运作效率普遍低下,同时缺少优秀的国有企业家人才和对有能力的国有企业家人才的有效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地方政府在有限的国有资本工业化投资决策中已变得十分“慎重”。二是由于我国目前地方城市化建设市场竞争压力小,各级地方政府来不及科学分析城市基础设施超额供给的潜在风险,对城市基础设施成本收益缺少科学的论证,导致我国绝大多数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成本回收十分困难,有的甚至永远难以收回投资成本。这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在加大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方面的风险将会呈现递增趋势。这也暴露了地方各级政府片面地用加大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来替代城市化是多么的危险。三是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干预经济的观念和欲望历来很强。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各级政府“沉溺于”工业化主角角色而长期不能自拔;改革开放20多年来,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由于非国有经济的迅速成长壮大,国有经济开始从工业化的许多产业层面退出。相对于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地级市以下的地方政府,在垄断产业占有和市场开放等规定方面处于劣势,因此,不得不从传统的工业化中退出。而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只能由城市化浪潮中政府独角角色来替代。这正是我国地方各级政府在城市化浪潮中对“独角”角色“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四是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从目前情况分析,各级地方政府不论在自然垄断性的公共产品供给和非自然性公共产品供给方面都承担着投资主体的地位。这要求对这种单一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主体结构进行优化调整,促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要求提供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体制改革的制度供给。这也是提高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市场化意识、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重要方面。五是与政府政绩目标有关。必须承认,当前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推进城市化,至少具有“一箭双雕”的政绩效应:一是规避了对其工业化组织不力的风险和指责,用城市化替代了工业化;二是能通过种种“形象工程”达到在任政绩的最大化(而不是城市建设收益最大化)。
要改变我国地方各级政府在城市化浪潮中“独角”角色及其风险递增的被动局面,除了进行城市投资体制改革制度创新外,还要有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各级政府要摆脱城市化建设与政绩的一一对应关系,从单方面考虑政绩的误区中走出来。这既有政府考核目标的改变,又要求各级政府要敢于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中退出。二是要有政策连续性,建立政府与企业在城市化建设中共同遵守“游戏规则”的平等环境和机制。这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各级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经营企业的优惠政策条件要具有连续性和权威性,这对激发民间资本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其二,在城市规划和城市功能定位以及城市基础设施投入方向和结构上,也要保证政策连续性,要从制度源头遏制由于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的更替而导致城市规划的“另起炉灶”现象的屡禁不止,从制度上根绝“一个书记一条街,一任县长一座城”的现象。三是在城市规划上要强调长远性和规范性,形成防止地方政府特别是主要领导在任时城市规划一个人说了算、接任者一个人再说了算的无序状况的制度约束,根治我国城市规划中的短期行为。
三 城市化的泡沫
城市化的泡沫虽然没有房地产泡沫那么让人比较直接地观察到,但城市化的泡沫却在我国大多数城市程度不等地存在。
——城市重复改造屡见不鲜。如旧城改造,拆城改造等。这无疑形成了巨大的投资浪费,既加大了城市建设投资规模,更加剧了我国城市化的成本和风险。二次和三次改造的投资和成本往往是先前的数倍。
——城市道路建设和管理建设中改、拆现象也很普遍。这不仅加大了城市化投资成本,而且影响了城市的美学效果,人为造成交通拥挤和交通不便。
——我国近几年房地产投资成倍增长,对改变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一方面,城市房地产供给过热和资金大量涌入城市房地产必然形成经济泡沫。住宅空置率居高不下,并在不断攀升,高档写字楼和高档别墅空置率都很高,房地产商炒作土地比比皆是。不少地方居民住房价格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投资对金融资本的依赖过度,房地产业与金融业关系具有畸型倾向。
——在城市化浪潮中,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不顾实际地提出城市化发展目标,如“三年建座新城市,五年旧城翻两番”,城市化建设中的“浮夸”时有发生。由于政绩目标动力的驱使,以及没有形成对各级政府城市化推动绩效的评价和监督体系,使不少地方政府城市建设目标和城市规划中的“急功近利”倾向严重,使城市化发展决策理性不足。
我国城市化泡沫产生的原因,一是体制上的原因。这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对城市化投资参与过度及政府政绩考核导向所致。二是决策机制上的原因。这突出表现在城市规划上。地方政府官员在城市功能定位、城市基础设施供给和投资机制、城市规划等方面人治现象普遍,决策失误难以从源头上加以控制。三是企业投资盲目以及部分开发商和城市基础设施运营商对政府城市化决策的影响力上升,以及政府官员与城市基础设施企业和开发商之间的“利益联盟机制”所致。
四 城市化的需求空间究竟有多大
需求因素是影响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前文讨论的我国城市化建设中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孰重”、“城市化中政府独角戏现象”和“城市化供给的泡沫”等三个问题,也都涉及到一个基本的判断,即我国城市化需求究竟有多大。当然,静态或孤立地分析我国城市化需求的规模和性质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我国城市化需求既具有潜需求的性质,又具有高速增长的性质。但不可否认,我国城市化需求受到如下实际因素的制约:一是工业化发展水平和工业化景气度。工业化发展水平对现实的我国城市化需求具有直接影响,而工业化景气度对我国未来的城市化需求则产生多重影响;二是居民收入水平和居民预期收入水平。这需要通过提高就业机会、改善就业环境和提高人力资本开发水平来实现;三是城市化供给能力和供给价格。过高的城市化供给价格和过低的城市化供给能力只会压抑我国的城市化需求,并对我国未来城市化能力的提升产生消极影响。四是城市集聚能力的大小。这里的城市集聚能力既包括城市人口集聚能力,又包括产业集聚,特别是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能力。我国目前城市化供给和城市化需求过多偏重于城市人口集聚能力因素,而轻视产业集聚能力所引致的城市化供求规模的变化。因此,从发展趋势分析,我国未来城市化需求和供给必须重点针对产业集群导向。
笔者认为,以下因素影响我国城市化需求规模的持续上升。其一,城市居高不下的房价。其二,城市居民预期收入不高的倾向;其三,企业景气度波动高的因素;其四,我国利用外资拐点的可能出现;其五,城市化需求刺激增长的人口因素不明显。特别是由于近九亿农民仍被排斥在城市化之外,城市对农民进城体制性障碍和政策性障碍还不可能完全清除,城市就业机会和工作收入水平难以成为诱使农民城市化或城镇化的有效动力。另外,对大量渴望城镇化的农民而言,农村小城镇建设的成本和门槛也在明显提高。
五 城市化供给过剩
导致我国城市化供给过剩的主要因素有:一是恶性竞争因素。我国目前城市之间特别是大中城市以及大城市与周边地区中小城市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合作机制不但没有建立,而且形成了恶性竞争的局面。城市化的决策者不仅受政绩的驱使,而且合作战略不到位。二是不少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所谓城市化率,将城市化率与城市人口、城市基础设施供给规模等同起来。因此,用行政手段和区划调整来扩大城市管辖面积,并为城市获得未来土地级差收入提供条件。与城市绿化、城市生态、城市文化和教育设施建设等供给相比,城市道路、桥梁、城市轨道交通设施供给等方面严重过剩。由于缺少城市之间的合作机制、可操作性的城市政府规划权力实施的责任追究机制,导致区域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布局和供给的不合理。在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和供给过程中,城市化发展的理性让位于政府官员的盲目性和自我利益的膨胀性。三是由于城市化发展条件和城市化需求水平具有世界上最大不平衡性导致我国各级地方政府都义无反顾地将其主要精力投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城市化浪潮中来了。正如前面分析的,我国各级政府在城市化建设中的合作和协作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不少地方城市化供给过剩不可避免。世界城市化规律表明,城市化发展速度和绩效与城市规模、城市条件和城市化需求密切相关。实践表明,世界大城市城市化速度远高于小城市,从而得到了更快的发展。
我国大小城市包括众多小城镇一并进行城市化建设,固然对改变我国落后的城市化水平有积极作用,但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在城市化条件、需求规模等方面存在着天壤之别,这种“一哄而上”式的城市化推进机制必然会导致城市化供给过剩。必须强调,虽然选择以小城镇为重点的城市化战略,对改变我国相对低下的城市化水平有一定益处,但由于城市化供给过剩,小城镇建设“空壳”特别是小城镇和小城市产业集聚能力低下等客观原因,我国这种城市化不仅必然带来城市化供给过剩,而且是一条成本最高、居住效益和生态效益皆差的模式。相比于大中城市,农村小城镇建设除了占用土地资源不经济、城市基础设施使用效率低、产业集聚能力小外,还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居住条件、环境和生活方式”。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仍然是小城镇产业集聚能力低下的制约因素。这是导致农村小城镇建设占用土地资源不经济、城市基础设施使用效率低及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居住条件、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主导原因。必须强调,城市化难以用农村小城镇建设来完全替代,正是因为从根本上来讲,农村小城镇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居住条件、环境和生活方式”。因此,即使一大批农村小城镇建立起来了,而且很多周边的农民都进入小城镇“工作”和“生活”,但这显然绝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居民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方式”。这肯定也不是我国推进城市化的根本目标。
〔收稿日期〕 2003-1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