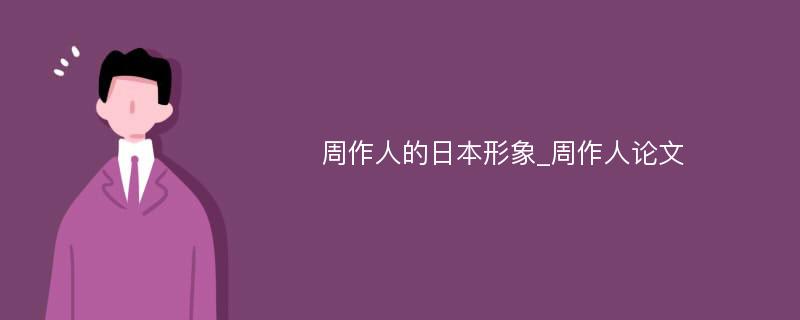
周作人笔下的日本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笔下论文,形象论文,周作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4)-01-0108-11 在写于1945年9月的《过去的工作》中,周作人曾对自己的日本研究作了一个总结:“我谈日本的事情可以说是始于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与胡适之刘半农二君担任小说组,五月间写《日本近三十年间小说之发达》一文,讲演一过,这可以算是起头,以后写了不少文章,一直到民国二十六年六月给《国闻周报》写《日本管窥之四》,这才告一结束,尝戏称日本研究小店的关门卸招牌,这正是实在的事。”[1:82]事实上,周作人对于日本的研究并没有真正结束,直到生命最后的岁月,他仍然“颇关心日本的新兴宗教”,并曾请素未谋面却书信频传的香港友人鲍耀明为之代购“高木宏夫著的《日本の新兴宗教》”[2:346]。 周作人在日本住过6年,据他自己说,其活动范围“只在东京一处”,而且“那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但是他仍然认为:“假如这足以代表全日本,地方与时代都不成问题”,“那么我的所了解即使很浅也总不太错”[3:117]。可见,他对自己的日本研究还是颇具信心的。在中日学界,推重周作人的日本研究向不乏人,胡适在1921年5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像周作人先生那样能赏识日本的真正文化的,可有几人吗?”[4:213]日本学者山田敬三的评价更高,他认为周作人“精通日本文化”,“表现出超出日本人之上的透彻见解”[5];另一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在比照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时,也特别强调了“在中国的文学家之中,还找不到像周作人那样与日本及日本文化关系如此紧密的人”[6]。 面对这样一个终其一生孜孜不倦研究日本、并在中日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我们要从其纷繁复杂的日本描述中勾勒出清晰的日本形象并非易事,但认真爬梳并仔细探究却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一、可亲可敬的日本:简素生活、物哀美学和创造性的模拟 (一)简素生活 晚年的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曾饶有兴味地提及,一般的中国留学生初到日本,吃到清淡、枯槁的日本饭菜,没有油水,一定大惊大恨。在下宿或分租房间的地方,住着矮小、简易的日本屋子,没有床铺,一定失望沮丧。知堂老人的回想在郁达夫和鲁迅那里都可得到印证。郁达夫初到日本时,就曾经觉得日本的一般国民生活,远没有中国那么舒适:“房子是那么的矮小的,睡觉是在铺地的席子上睡的,摆在四脚高盘里的菜蔬,不是一块烧鱼,就是几块同木片似的牛蒡……”[7:156];鲁迅对于日本的生活也不是很喜欢:“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即所谓旅馆,亦殊不宏”,“其风景尚佳,下宿则大劣”[8:321]。但周作人的感觉显然“并不如此”,相反,对于那地方与时代的空气不久便感到“协和”,且颇有留恋之意。从日本归国不久,他就有古诗云:“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3:118]。这种“乐不思蜀”的情怀中很大一部分就源于其对于日本饮食起居的满意。 在周作人的笔下,日本的食物是那样的“清淡质素,他没有富家厨房的多油多团粉。”[9:64]日本的点心虽是豆米的成品,但那“优雅的行色,朴素的味道,很合于茶食的资格,如各色羊羹”,“尤有特殊的风味”。日本人用茶淘饭,名曰“茶渍”,以腌菜及“泽庵”等为佐,很有清淡而甘香的风味[10:20-22]。日本的家庭宴会,虽然“自较丰盛,但其清淡则如故,亦仍以菜蔬鱼介为主,鸡豚在所不废,唯多用其瘦者,故亦不油腻也”[11:218-219]。日本的房屋是那样的“清洁有致”,那样的“质素”:“中国公寓住室总在方丈以上,而板床桌椅之外无他余地,令人感到局促,无安闲之趣。大抵中国的房屋与西洋的相同,都是宜于富丽而不宜于简陋,一间房子造成,还是行百里者半九十,非是有相当器具陈设不能算完成,日本则土木功毕,铺席糊窗,即可居住,别无一点不足,而且还觉得清疏有致。”[9:65]尽管他在后来提到,这样的房屋也有缺点,那就是这种土木建筑“宜夏而不宜冬,其次是容易引火,和易于小偷行窃”。但是,他对于这种房屋的肯定居多,“我喜欢的还是那房子的简素适用,特别便于简易生活”,“从前在日本旅行在吉松高锅等山村住宿,坐在旅馆的朴素一室内凭窗看山,或着浴衣躺在席上,要一壶茶来吃,这比向来住过的好些洋式中国式的旅舍都要觉得舒服,简单而省费。”[11:212-213]和这样清疏有致的房屋风格相一致的,是日本的衣裳:“日本的衣裳之制大抵都根据中国而逐渐有所变革,乃成今状,盖与其房屋起居最适合,若以现今和服住于洋房中,或以华服住日本房,亦不甚相适也。”穿着日本的和服,踩着日本的木屐,无疑使周作人觉得很洒脱:“这个木屐也是我所喜欢着用的……甲戌(1934年)夏间我住东京去,特地到大震灾时没有毁坏的本乡菊坂去寄寓,晚上穿了和服木屐,曳杖往帝大前面一带去散步,看看旧书店和地摊,很是自在,若是穿着洋服就觉得拘束,特别是那么大热天。”[11:215-216] 饮食起居之外,周作人“也很喜欢”日本的生活习惯,因为其“清洁、有理、洒脱”[9:66]。对于极具特色的日本澡堂,他表现出由衷的喜欢。对于部分中国人认为澡堂公浴不卫生,他作了反驳并指出,日本的澡堂很是清洁。他描述澡堂的结构很清楚,应该是做过一番研究的。 日本清淡的食物、素朴的房屋建筑、自在的穿着和好清洁的习惯,不仅给周作人留下异常深刻的印象,而且让他对这个国度产生一种格外亲切的感觉。到其晚年回首往昔时,这些基本印象依然清晰可见:“这印象很是平常,可是也很深,因为我在这以后五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更或是修正。简单一句话,是在它生活上的爱好自然,与崇尚简素。”[11:207] (二)物哀美学 日本民族视悲凉、忧伤为美,这种审美观在江户时代平民气的文学中尤为明显。周作人笔下多次提到江户时代的作家(如写作《江户艺术论》的永井荷风等),他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有着非同一般的喜欢。他用自己同样喜欢的中国明代文学来与之对比,认为中国的明末清初“何尝不是一个新文学时期”,可是读书人“多少有点功名”,当时出过冯梦龙、金圣叹、李笠翁几个人,稍微奇特一点,却已被看作文坛外的流氓,至今还不太为人所看得起。而日本江户时代的文学在历史上可以真正称得上是平民的,诗文小说都有新发展。作者大抵是些平民,“偶然也有小武士小官吏,如横井也有即其一人,但因为没有科举的圈子,跨上长刀是公人,解下刀来就在破席子上坐地,与平民诗人一同做起俳谐歌来,没有乡绅的架子。”[9:68]这种平民气的文学以表现“物哀”为美,用周作人的话来说:“日本的平民艺术仿佛善于用优美的形式包藏着深切的悲哀,这似乎是与中国很不相同的一点。”[11:785]他在《论小诗》中,用一个对比揭示了日本文学所追求的典雅与悲凉、冷寂的“物哀”美学:日本的歌实在可以说是理想的小诗了。在中国新诗上它也略有影响,但是与印度不同,因为其态度是现世的。如泰戈尔在《迷途的鸟》里说:“流水唱道,‘我唱我的歌,那时我得我的自由。’”(王靖君译文)与谢野晶子的短歌之一云:“拿了咒诅的歌稿,按住了黑色的胡蝶。”在这里,大约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同,因此受他们影响的中国小诗当然也可以分为两派了[12:46]。 日本文学中这种“物哀”的美学风格,如果走向反面就往往走入阴暗颓废的一面,鲁迅对日本艺术就有这样一种印象:“浮世绘虽是民间艺术,但所画的多是妓女和戏子,胖胖的身体,斜视的眼睛——Erotic(色情的)眼睛。”[13:293]“篇末有译者附记,以为小说里有一种Kosmopolitish的倾向,同时还有一种厌世的东洋色彩,这是极确凿的。”[14:160]但在周作人笔下,“物哀”美学则极力彰显出日本审美意识中淡雅的一面。他认为日本的国民天生有一种对艺术的感受性,对于天物之美,别能领会,引起优美的感情;如用形色表现,便成种种美术及工业的作品,多极幽雅纤丽;如用言语表现,便成种种诗歌。就在平常家庭装饰,一花一石或食用事物,一名一字,也有一种风趣。而表现在语言上,日本语则“联读起来,很是质朴,却又和谐”[15:109]。 (三)创造性的模拟 除了对日本简素生活的体认和对物哀美学的赞赏,周作人对当时部分国人对于日本文化的不以为然也持不同态度。他认为日本自有其文明:“日本古今的文化诚然是取材于中国与西洋,却经过一番调剂,成为他自己的东西,正如罗马文明之出于希腊而自成一家(或者日本的成功还过于罗马),所以我们尽可以说日本自有他的文明,在艺术与生活方面最为显著,虽然没有什么哲学思想。”[16:315]换言之,日本的文化虽则缺乏原创性,但是“它的模仿,却是创造的意义”[17:92]。 早在1918年讲演《日本近三十年间小说之发达》时,周作人就说“日本新文学便是不求调和,只去模仿的好;又不只是模仿思想形式,却将他的精神,倾注在自己的心里,混合了,随后又倾倒出来,模拟而独创的好。”[18:2]他还由此得出结论:因为日本文学界有诚意去模仿,并倾注在自己心中而又倾倒出来,所以能生出许多独创的著作,造就了日本的20世纪文学。到1931年《艺术与生活》出版时,周作人更将这种“创造性的模拟”推广到日本的文化上,强调“日本的文化是创造性的模拟”[15:134],并进一步认为,要救旧文学的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日本就是个榜样。”[15:148] 日本文化的创造性模拟,使其对于新事物的接受程度相当之快,这在周作人看来,正可与当时中国因循守旧的文化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日本自明治上半文学革命,一时虽有雅俗折衷言文一致种种主张,结果用了语体文,至于今日虽是法西斯蒂高唱入云之际,也并没有人再来提出文言复兴,因为日本就是极右倾的人物也知道这些文字上的玩意竟是很无聊极无用的事,日本维新后,科学的医术从西洋传了进去,玄学的汉法医随即倒地,再也爬不起,中国则不然。”[19:64]日本对西医的接受之快也是周作人所特别称许的:“中国与日本不同,不是由本国医生自发研究,由玄学的旧法转入科学的新法,所以只有前后两期而无东西两派,乃是别由外国医生来宣传讲授,结果于玄学的中医外添了科学的西医,于是两方面对立至今。”[20:93] 一个敞开胸怀、将新事物不求调和地倾倒在自己的心中,一个很快接受新事物、对腐朽旧事物并没有太多留恋的日本形象,在周作人笔下几乎定格。一旦这个形象建立起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下面的话:“医学史上所记便是这些仁人之用心,不过大小稍有不同,我翻阅过二家小史,对于法国巴斯德和日本杉(田玄)白德事迹,常不禁感叹,我想假如人类要找一点足以自夸的文明证据,大约只可求之于这方面罢。”[21:14]也就是说,法国医生也好,日本医生也好,在周作人笔下无疑都代表着一种先进文明的形象。对于日本的明治时代,周作人更是不吝赞美之辞,称其是一个“全面进步”的时代:“文艺复兴应该是整个而不是局部的,照这样看去,日本的明治时代可以够得上这样说……这个看法实在是很对的,因为明治文学的发达并不是单独的一件事,那时候在艺术、文史、理论的与应用的科学以至法政军事各方面,同样有极大的进展,事实与理论正是相合。”[22:20] 参照鲁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情形就有些不同。鲁迅也认为日本文化是一种创造性的模拟,如“他们的遣唐使似乎稍不同,别择得颇有些和我们异趣。所以日本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廷中仍无太监,妇女们也终于不缠足。”[23:20]这颇类似于周作人的口吻,但是鲁迅并没有漠视甚至无视这种文化接受背后的血与泪,他谈到日本在接受基督教的过程中的文化冲突:“日本幕府时代,曾大杀基督教徒,刑罚很凶,但不准发表,世无知者。到近几年,乃出版当时的文献不少。曾见《切利支丹殉教记》,其中记有拷问教徒的情形,或牵到温泉旁边,用热汤浇身;或周围生火,慢慢的烤炙,这本是‘火刑’,但主管者却将火移远,改死刑为虐杀了。”[24:14] 二、可恨却可理解的日本:从侵略野心到宗教情绪 (一)侵略野性 当然,日本在周作人笔下也并非全是可亲可敬的印象,早在1920年代谈及中日两国关系时,他就注意到其侵略野心的存在。只是在那时的周作人看来,这种侵略野心主要表现在那些来到中国的日本浪人与支那通身上。这些日本人“全不了解中国,只皮相地观察一点旧社会的情形,学会吟诗步韵,打躬作揖,叉麻雀打茶围等技艺,便以为完全知道中国了,其实他不过传染了些中国的恶习,凭空添了个坏中国人罢了。别一种人把中国看作日本的领土,是到殖民地来做主人翁,来对土人发挥祖传的武士道的,于是把在本国社会里不能施展的野性尽情发露。在北京的日本商民中尽多这样的乱暴人物,别处可想而知。”[16:318] 那时同样让周作人反感的还有日本在中国内地发行的汉文报纸《顺天时报》,他认定这类报纸是“日本军阀政府之机关,它无一不用了帝国的眼光,故意地教化我们”[16:321]。它的实质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队以新闻或学校为工具,阳托圣道之名,阴行奴化之实”[16:325]。对于这一时期的周作人来说,日本的文化侵略最恶劣的表现是劝中国同胞苟全性命,趁早养成上等奴才、高级顺民,以供驱使。因此,对于《顺天时报》之类的文化侵略机构,周作人是极端厌恶的:“日本汉文报纸是日本侵略扰乱中国之最为恶辣的手段,顺天时报则是此类汉文报中最恶辣的一种”[16:327]。对于日本的文化侵略,尤其是出版方面的举动,鲁迅也很愤慨:“如此善政,行了还不到一年,不料竟出了《新生》的《闲话皇帝》事件。大约是受了日本领事的警告罢,那雷厉风行的办法,比对于‘反动文字’还要严:立刻该报禁售,该社封门,编辑者杜重远已经自认该稿未经审查,判处徒刑,不准上诉的了,却又革掉了七位审查官,一面又往书店里大搜涉及日本的旧书,墙壁上贴满了‘敦睦邦交’的告示。”[25:463]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周作人对日本文化侵略野心的批评中,仍夹杂着他对于日本的一种迷恋情感。几乎在所有对于日本负面形象的描述中,周作人都夹杂了“要正确看待日本”和自己对于日本的维护之情,这种态度和情绪在他的文章里清晰可见。以下这段文字,很能见出周作人对日本极其复杂的一种情绪: 因为这个缘故,无论我怎样爱好日本,我的意见与日本的普通人总有极大的隔阂,而且对于他们的有些言动不能不感到愤恨。愤的是因为它伤了我为中国人的自尊心,恨的是因为它动摇了我对于日本的憧憬。我还未为此而破坏了我的梦,但我不是什么超越的贤人,实在不能无所恨惜。我知道这是没法的,世上没有这样如意的事,只有喜悦而无恨惜;所以我也就不再有什么怨尤,只是这样的做下去:可爱的就爱,可恨的就恨:似乎亲日,似乎排日,都无不可,而且这或者正是唯一可行之道[16:322]。(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周作人回环往复的文体风格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最后那句复杂的话语更像未能得到自己“爱人”青睐的幽怨。事实上,周作人“个人化”的倾向在这段话中表现得很是明显,即他对于日本有着很深的感情。因此,即使在这段“排日”时期,他对于日本的批评文章中仍大量存在“爱”、“喜欢”、“憧憬”、“真正的亲日派”、“梦”等词语,这些词语无疑道出了他对日本极其复杂的纠结心态。 (二)宗教情绪 大约在1930年代后期,其时日本的侵略野心在中国已全面暴露,但在周作人笔下,那个具有侵略野心的日本形象却基本淡出甚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具有“宗教情绪”的日本形象。这是周作人日本形象构建的一次重要变化,他甚至宣称自己以往的研究都是一种错误:“鄙人在卢沟桥事变之前曾声明,自己以前所走的路全是错的,即是从文学艺术方面下手去理解日本国民精神,这事完全是徒劳。只有宗教一路或有希望,因我觉得这里中日两国国民最是不同,我们要能够懂得日本国民的宗教情绪,才可希望了解他的思想与行动。”[22:46] 如果对周作人曲折隐晦的文体风格没有足够充分的了解,我们很难捉摸他的真正意思。事实上,周作人并没有完全放弃继续从文学文化以及一些日常生活角度来看待日本,一直到他写《知堂回想录》的时候,他很多地方仍然坚持着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日本。此时增加一个宗教角度来看待日本,只不过是一种类似于德里达所谓的“延异”①策略。当他用“宗教情绪”来理解日本时,这背后其实隐含了他对于那个可亲可敬的日本的迷恋和对“侵略野心”的回避。 如上所述,对于日本的侵略野心,周作人的看法颇复杂。一方面,他无法否认日本的丑恶一面;另一方面,他的迷恋意识又使他对这种丑恶面的揭示存在拒斥的态度。用“宗教情绪”来揭示1930年代日本的国民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是对不在场的“侵略野心”的一个补充与替代。通过这种“延异”,周作人和日本的“侵略野心”巧妙地拉开了距离,这正反映了其下意识的一种思想状态。关于宗教情绪和日本的国民性之间的关系,周作人的言说完全称得上是不厌其烦: 我想谈日本文化也须得先将宗教懂得个大概,才能来说别的,现在还是谈不到,近来也胡乱的写作,不过那都是关于中国的。自己的事情不能全不知道,说到日本文化,现今暂时不得“远虑”,等到把宗教一关打通了以后[22:47]。 我常觉得中国人民的感情与思想集中于鬼,日本则集中于神,故欲了解中国须得研究礼俗,了解日本须得研究宗教[22:82]。 日本国民富于宗教心,祭祀正是宗教仪式,而中国人是人间主义者,以为神亦是为人生而存在着,此二者之间正有不易渡越的壕堑[26:116]。 日本文化与中国民族不一致是什么呢?我不能知道,所以我不能说,但是我也很考虑,我猜想,这或者是宗教罢[3:124]? 我很抱歉自己所说的话多是否定的,但是我略叙我对于日本的感想,又完全把它否定了,却也只剩下一句肯定的话。即是说了解日本须自宗教入手[3:126-127]。 要了解日本的国民性,他的一切好的和坏行动,不单是限于文学艺术一方面的成就,这需要从宗教下手,从他的与中国人截不相同的宗教感情去加以研究,这事现在无法讨论,所以只好不谈。因为这所谓宗教当然并不是佛教,乃是佛教以前固有的“神道”,这种宗教现在知道与朝鲜满洲的萨满教是一体的,但与南洋的宗教关系现今还没有听说去调查研究,我们外行更不配来插嘴了[11:207]。 一方面反复强调了解日本的国民性需从宗教入手,另一方面又说现在还无法展开充分讨论,个中的难言之隐和纠结缠绕可见一斑。 三、日本形象的背后:迷恋的主体和个人化叙述 像所有形象学意义上的形象一样,周作人的“日本形象”也源于周作人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或潜意识之中。 对周作人来说,建构一个可亲可敬的日本形象可谓得心应手。在日本留学的最初几年,因为兄长鲁迅负责他的生活起居,所以他得以相对悠闲地度过自己的留学时光,而这个保留了诸多故国传统神韵的异乡与他的个性气质及期待的理想生活又是那么“协和”,这就使得他从一开始就对日本抱有一种亲善的态度,甚至不无迷恋。他曾多次提到自己的5个“故乡”,在这几个地方,他将东京排在绍兴之后,北京、杭州、南京之前,甚至在他旅居北京之后,想起日本仍很是怀恋:“想起德川时代江户的二百五十年的繁华,当然有这样一种享乐的流风杂韵留传到今日,虽然比起京都来自然有点不及。北京建都已有五百余年之久,论理于衣食住方面应有多少精微的造就,但实际似乎并不如此,即以茶食而论,就不曾知道什么特殊的有滋味的东西。”[27:51]除了日常生活和个性气质的亲近,周作人也和鲁迅、郁达夫这些留日学生一样,在那个时代风潮中很自然就站在一种民族立场和启蒙立场上来看待日本。因为对于“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异国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以及“日俄战争”的胜利,都使其成为一个心目中的“师者”形象。鲁迅就曾经说:“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会摹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否则,只不过是一个恨恨而死而已。”[28:82]“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29:320-321] 可以想见,一旦中日两国关系处于正常时期,这种民族立场和启蒙立场与周作人的个人立场非常完美地统一在一起,基于此建构起来的可亲可敬的日本形象自然可圈可点。在津津乐道日本的简素生活、物哀美学和创造性的模拟的过程中,周作人获得一种个人和时代相一致的情感抒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一度认为日本是能和中国一起分享实现建立起“地上的天国”的理想战友和师者。在他看来,中国和日本的文化曾经属于同一系统:“儒道释三种思想本是知道的,那么这里没有什么隔阂,了解自然容易得多”[30:179],并且,日本是一个“一半是异域,一半是古昔”[31:159]的国度,让日本替“我们保存好些古代文化,又替我们去试验新兴的文化,都足以资我们的利用”[16:317],这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事。此时的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种种阐述,不仅对当时的中国人是一个很好的接受渠道,即使到今日依然有颇多值得参考的价值和意义。 但是,一旦中日两国的关系处于紧张时期,周作人的个人立场和民族立场产生裂痕就在所难免,形象建构的紧张关系也随之而来。在这一点上,周作人和鲁迅就显出不一致的特质。对于鲁迅来说,他认为日本虽然是一个先进的地方,但并不是什么理想中的乌托邦,因为日本是一个“也有臭虫的”国家:“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有。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日本人笑中国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样的弄文字”[32:345]。由于周作人的成长从某种意义上一直受到兄长鲁迅的“保护”,而且他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思想中更多“个人”和“人类”的价值判断,再加上他对日本“一见如故”的感情倾向,使他最终没有形成鲁迅那样一种从民族角度、启蒙角度看待日本的一贯立场,导致他在建构日本形象时常常处于一种紧张的矛盾张力之中。当民族立场和启蒙立场盖过了个人立场时,周作人笔下的负面日本形象就表现为可恨的具有侵略野心的日本形象,这种负面的日本形象,仅在1920-30年代较集中地呈现。需要指出的是,和鲁迅、郁达夫相比,这种负面的日本形象仍夹杂了太多带有维护意味的主观情感色彩,因为日本于周作人而言,那种“爱”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更是精神层面的,其中隐含了他的诸多“人间理想”,以至于欲“恨”而不能。于是,当个人化的立场——这种个人立场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迷恋——压倒了民族立场和启蒙立场,宗教情绪就成了周作人为负面的日本形象寻求解释的主要策略。大约在1930年代中期左右,周作人从启蒙的位置退了回来,在十字街头的塔上冷眼旁观这个世界,此时民族立场和启蒙立场已经成为过去,个人化叙述开始占据他文本的主导位置,个人化的立场随之成为其文学世界的主要出发点和价值中心。因此,尽量回避从民族立场和启蒙立场来建构日本形象成为他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努力方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宗教日本”的建构过程中,他没有感受到民族、启蒙视角所带来的压力,只不过,他不断地通过各种文本策略,自觉不自觉地调整自己的叙事角度,从而使这种异国形象的建构尽量成为一种个人化的情感抒发。无可否认,这样的形象建构和情感抒发在1930到1940年代的中国是不合时宜的,在当时饱受诟病在所难免。时过境迁,这样一种力求从个人出发来表现自己心目中的异国形象的方式,仍然值得商榷,但作为深入理解日本的一种特定角度,其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注释: ①德里达自创的术语,在解构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所谓“延异”,即延缓的踪迹,它与代表着稳定的语言—思想对应关系的逻格斯中心主义针锋相对,表示最终意义不断被延缓的状态。标签:周作人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日本生活论文; 文化侵略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