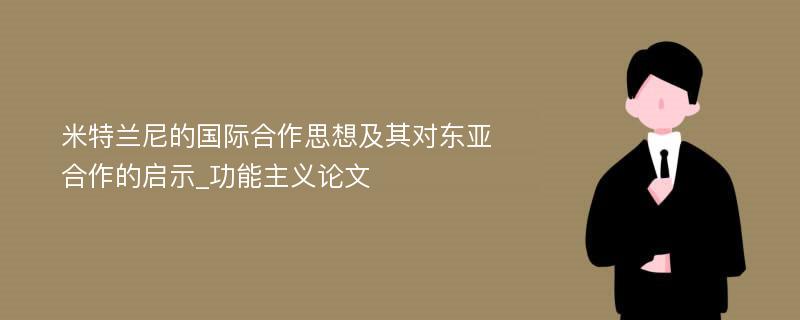
米特兰尼的国际合作思想及其对东亚合作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国际合作论文,其对论文,特兰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的东亚合作是区域主义运动的新实践,被一些学者称为新区域主义的主要代表。①在观察和思考东亚合作的时候,人们自然会想到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体化运动及其理论。肇始于1955年欧洲煤钢联营,西欧一体化运动已经断断续续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尽管不乏问题,但成就有目共睹,成为世界上迄今最为成功的区域合作范例。以其作为研究案例,学术界产生了包括功能主义、联邦主义、新功能主义、沟通理论以及政府间主义等多种流派的一体化理论。正因为这样,不少学者致力于比较东亚合作和欧盟一体化,希望能够从欧洲的经验和理论中,恰当地描述、解释和预测东亚合作。②
然而,由于东亚与西欧存在众多差异,而且两种合作实践所依赖的国际大环境迥然不同,尽管欧洲经验对东亚不乏启迪,但如果过多地套用一体化理论,不但有碍于客观解释与描述东亚合作的实践,甚至会误判东亚合作的未来走向。因为一体化理论毕竟只是“主要由政治科学家们发展出来的用于阐述欧洲一体化进程背后之逻辑与因素的解释”。③鉴于此,思考和构建东亚合作理论,还应有另外两个不能忽视的维度:一是发掘东亚合作的特殊性,以东亚合作的实践为素材建构新的区域主义理论;二是从欧洲一体化运动之前的先贤们对区域合作的原创性思考之中寻找智慧和启迪。
本文属于第二种维度的尝试。戴维·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通常被尊为一体化理论中功能主义学派的首创者,有趣的是,不同于“事后诸葛亮”式的旨在解释和描述西欧一体化实践的各种理论流派,米特兰尼对功能主义国际合作的阐发却远早于西欧的一体化实践。也就是说,米特兰尼的理论并不是基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现的西欧一体化合作实践。但值得注意的是,米氏理论却为西欧的一体化运动提供了卓越的解释与指导。沿此逻辑,笔者认为,我们同样可以从米特兰尼的思想中汲取建构东亚合作的理论营养。此外,尽管被贴上西欧区域一体化理论的标签,但米特兰尼的思想内涵实际上与西欧一体化实践和理论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本人甚至还时时对之加以批判。
本文旨在重新挖掘与了解米特兰尼及其功能主义的主张。文章首先介绍米特兰尼的生平,接着梳理其功能主义思想的来源、背景与主张,分析米特兰尼对欧洲区域合作的态度。针对东亚合作的现状和问题,文章最后集中讨论米特兰尼思想对解决东亚合作问题的启迪与借鉴。
一、米特兰尼其人
米特兰尼1888年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1912年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社会学。在当时社会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米特兰尼希望能够将社会学的知识和理论用于研究东欧的农民问题。但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米特兰尼带来了巨大影响,将他推到了国际关系领域。实际上,这场战争给当时任何醉心于社会改革的人都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正如米特兰尼后来所说:“从那时开始,任何希望社会自由与进步的人都不得不首先从国际和平入手。”④
战争期间,他进入英国外交部的智囊部门,专门就东欧和巴尔干问题提供政策咨询与建议。1916年,他加入国联协会(League of Nations Society),在英国宣传国际组织对维护世界和平的积极作用。1919年,他成为英国工党的国际问题咨询委员会成员,1919-1921年在《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担任记者,专门报道巴黎和会,之后负责该报的外交事务专栏,但最后由于政见不同离开报社进入伦敦经济学院。
1921年初,他结识了当时担任第一次世界大战丛书总编的美国学者肖特维尔(James Shotwell),该丛书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助。受肖特维尔的委托,米特兰尼担任了该丛书欧洲战争卷的编写人,由此开始了与美国学术界的联系。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哈佛大学获得了一个为期两年的教职席位。在此期间,他为学生开设了比较政府的系列讲座,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分析政府和政治进程,他称之为“系统分析”,这为后来卡尔·多伊奇等学者的理论奠定了基础,也成为随后“功能主义”理论的雏形。1933年,他进入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政治经济学院,参与了对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的研究,这一经历促使他进一步澄清了自己对“功能”的理解。
二战爆发后,受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Toynbee)的邀请,他回到英国加入战时隶属于外交部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外国新闻与研究小组,由于在此未受重用,米特兰尼于1942年离开,但在此期间,他却完成了专著《一个能够运转的和平体系:国际组织的功能性发展之我见》(A Working Peace System:An Argument for the 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该书于1943年出版发行,并使他一举成名,从此以后,“功能主义”就成为其思想的主要标签。之后,他出任英国尤尼莱维尔公司的国际顾问直至1975年去世。⑤
二、米特兰尼的国际合作主张
米特兰尼的亲身经历以及自己的犹太人出身,使他对社会改革尤为热衷,而对政府的控制和干预抱有戒心。他是当时英国“多元主义”思想的信奉者,“多元主义”认为,一个社会的最基本构成单位、社会中最富活力的源泉是各种自我管理的组织,这些组织具有“功能性的代表性”,即它们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力量与阶层,所以它们具有合法性并理应受到保护和尊重。显然,这种多元主义思想具有一定的反国家和反政府倾向,把政府看做是社会改革的绊脚石。⑥
米特兰尼的功能主义思想首次出现在1924年。为了落实国际联盟的《日内瓦议定书》(Geneva Protocols)中的制裁条款,也为了协调与反对介入国联事务的国会之间的关系,美国裁军与安全咨询小组负责人委托米特兰尼起草一份备忘录,阐明一个国家特别是美国在承担制裁任务时所面临的困难以及可能变通的方法。在这份备忘录中,米特兰尼提出:一个普遍的、没有具体化的(generalized)制裁任务给每个国家带来的义务和影响大不一样,如果想使制裁有效,那么就应当从“能力”(facultative)上分解制裁责任,只有这样才更有效,并可以鼓励更多的国家参与。⑦此处“按能力划分任务”可谓是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思想的最早版本。数年之后,在一份批评法国提出建立泛欧联盟计划的文章中,米特兰尼再次阐发了他的功能主义:“国家日渐褪去其老式的独裁主义迹象而承担新的‘服务’功能。这种进步在国际领域尤为突出,因为没有一个稳定权威,所以出于普遍需要的功能性合作在这里茁壮成长。实际上,在现代世界中,独立国家间的关系必须从功能上而不是按照边界线进行安排。”⑧米特兰尼赋予“功能”极大的作用与重要性。他说:“我们在此发现了功能的一个重大作用,也可称之为技术性自决(technical self-determination)的作用。正如我们所见,在很大程度上,功能可以自我决定,正如功能决定自己适当的机构。这也可以通过实践显示出来:行动本身的性质决定需要什么样的特定条件以及决定相关权威机构的权力方式。所以可以说,功能决定适合其行为的政治工具,同时规定了每一阶段的革新调整。”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是一个追求国际法制与合作的理想主义时代,但米特兰尼却没有无视国际形势而盲目地热衷于乌托邦式的国际大同,他认为当时的世界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变之中,其中有三个事件意义特别重大:第一,殖民体系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急剧增生;第二,各个国家的政府通过经济规划将社会安全与福利的责任加诸自身;第三,国际社会致力于建立一个适合上述两个现象的有法制和秩序的国际体系。“这就是我们正在面对的世界。”特别突出的是,米特兰尼一直强调“20世纪世界的特征是技术问题日益增加,而这些问题只有通过跨国合作才能解决”。⑩
针对这一问题,当时的学术界出现了两种观点:第一种主张建立世界政府,第二种则主张加强地区合作。不同于上述区别,米特兰尼把“功能主义”运用到了国家间合作。实际上,与米特兰尼亦师亦友的霍布豪斯(L.T.Hobhouse)、同时代的伍尔夫(Leonard Woolf)以及社会学家科尔(G.D.H.Cole)都谈到了国际合作并涉及功能主义,“但米特兰尼所做的是离析这些观念,把它们从社会学的背景中分离出来,给它们定义,赋予它们清晰的制度性与组织性的轮廓,而这些都是早期著作所缺乏的。此外,相比其他的多元主义论者,他还把这些概念变成了他社会思想的核心。”(11)此外,由于他在英国外交部、国联以及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工作过,因而,不同于很多纸上谈兵的书院派学者,这些切身经历使米特兰尼心目中的功能更为具体和形象。很显然,对米特兰尼而言,主权国家及其政府实际上并不愿意主动进行国际合作,就像它们不热衷于国内的社会改革一样。米特兰尼对国家与政府的不信任伴随其一生,1932年在哈佛大学讲课时他就表达了对“全权国家”(Comprehensive State)的担忧,40年后,他依然写道:“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国家,只要政府的权力得到增加,代议性的部门(representative elements)就会衰落。”(12)
可以理解,米特兰尼呼吁加强国际合作,但他心目中的理想世界绝不是一个“单一的世界社会”或“单一的全球共同体”。恰恰相反,那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合作的层次包括个人、地区、跨国以及全球。实际上,他认为这个多元化的世界已经初露端倪,正因为如此,仅靠国家和政府的治理是不够的,所以他主张的多层次的功能性合作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反映了多元化世界的需要。也只有这种多元化、多层次的合作安排,“社会才会朝着更加均衡、健康和减少对抗与敌意的方向发展。”所以,在米特兰尼这里,他没有后来新功能主义者把多个独立的社会变成一个“单一共同体”或一体化目标导向的忧虑。(13)他所展望的前景完全不是一个类似世界性国家的共同体,而是一个“法制”的多彩和多元化的世界,其中的法律秩序“并非无视外交与司法契约,但却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14)
三、米特兰尼与西欧区域合作
1955年成立的欧洲煤钢联营首次实践了类似于米特兰尼强调的多层次的功能性国际合作。米氏对煤钢联营的技术专家型领导方式、行业的代表性、决策时高层必须与生产商和消费者共同协商等机制大加赞赏,认为这种安排“对那些了解自己工作的人和技术专家都有警醒作用”,提供了“超国家自治的自由和更多的合作交流点”。(15)
但是,作为一名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米特兰尼并没有因为符合自己的设计而一味地赞美西欧区域合作。实际上,他关注的并不是什么样的区域,而是以功能为标准的机构性国际合作。随着西欧区域合作的发展,特别是其中的相关机构越来越多、权力越来越大,人们开始谈论区域合作的目标是要走向一体化。与之遥相呼应并互为因果,学术界出现了主张并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联邦主义和新功能主义等理论流派。米特兰尼开始变得谨慎,反思和批评的言论越来越多。在进行区域合作的方式上,米特兰尼反对联邦主义,他认为这种方式的最终结果可能会导致“国家主义”的集权而不是多元化。“不管怎样,现有条件下一个区域的‘一体化’的最终结果一定会重蹈民族国家的习性与方式。”所以,他反对莫内(Jean Monnet)提出的选举欧洲议会的建议,而对欧洲共同市场赞赏有加,认为它应当是欧洲的未来,因为其权力“并没有交给一个联合的行政中心”。(16)
对将自己奉为鼻祖的“新功能主义”,米特兰尼没有公开反对,但他对显著的一体化导向表示不满。他读到一篇出自自称为自己信徒之手的文章,文章中说“从自治和专门的政府开始,[米特兰尼]认为有可能构建一个全面的国家”,米特兰尼在旁边批注:“我可从来没有梦想过这样的东西。”实际上,他反对新功能主义关于区域合作的线性推理,“如果欧洲在决策程序和外交防务方面都想统一起来并使之永久化,……那就意味着一个共同的行政权威,……那是一个共同的政府。……那实际上是政治联盟。”正因为这样,他称新功能主义为“联邦性功能主义”和“半功能主义”,意在反对新功能主义关于转移效忠以组成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的主张。(17)由此,米特兰尼也开始对欧洲经济共同体持反对态度,认为其中很多官员的心态都受到一体化论者的影响,希望把欧洲经济共同体逐步变成一个中央集权单位,他这样评论道:“[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进程有部分新颖之处,但其终极的希望却深深根植于政治组织的主权领土的古老观念。”(18)
在约瑟夫·奈1968年编辑出版的《国际区域主义》论文集中,他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一体化的前景:联邦性还是功能性?》的文章以表达对欧盟进展的担忧,奈这样总结米特兰尼的观点和立场:
由米特兰尼所撰写的第三篇文章对欧洲区域主义为世界秩序带来的有益价值呈现了一种不同的观点。尽管他承认如果只局限于像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煤钢联营这样机构的最适度功能性作用,欧洲的经验或许是有益的,但米特兰尼认为欧洲区域进程中的这些官员们扩张的野心与宽泛的任务使得欧洲没有走向一种超越主权民族国家的新形式,而只是出现一个更大的欧洲主权国家。一个‘联邦制’这样的国家也未能使他满意,因为他认为联邦是一种保守的政治体制,其中尽是复杂的内部斗争与平衡,但对外部世界却较为‘封闭’。所以,他认为欧洲一体化对世界的‘示范效应’或许不是超越主权国家体系的新形式,反而可能纵容类似更大主权体的‘硬化’,而它们之间未必和平。米特兰尼倾向于一种基于功能主义概念的组织原则:不同种类的国际组织满足具体的技术性和功能性需要,它们超越国家边界,产生一个相互依赖的网络,这个网络会逐渐使得国家主权不再相干,或至少减少国家主权间冲突的潜在因子。尽管区域主义并不见得与功能主义相互冲突(实际上,一些人认为功能主义对区域主义提供了最丰富的营养),但米特兰尼还是担心所谓的区域主义会诱使人们超越纯粹的功能主义去追求联邦主义,从而远离与全球的联系与纽带。对米特兰尼而言,欧洲共同市场的官员们把功能主义作为追求一个联邦欧洲的工具,这无疑是19世纪意大利爱国志士马志尼简单想法的回归:他认为建立民族国家就能走向[世界]和平。(19)
因此,相比后来越来越陷入欧洲区域合作细枝末节的新功能主义,以及其他一体化理论流派,米特兰尼的功能主义是“有关合作、协作、分享与和平的”理论。它“着重强调构成这个世界社会基础的各种不同行为体之间要充分建立合法的联系。……它拒绝把国际社会比喻为撞球(billiard ball)游戏;它更加重视相互依赖……范围的扩大;他更喜欢用‘世界政治’或‘世界社会’这种用语,而不喜欢用‘国际政治’;它以间接方式逐步地降低政府的作用,并通过各种各样功能性的、跨国的联系去促进国际合作”。(20)
实际上,正是米特兰尼对国家作用不断增长的担忧,以及他提出以功能主义对其加以遏制的主张,引起了国际关系理论经典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的注意和肯定,为此,摩根索专门为他1966年再版的《一个能够运转的和平体系》写了序言,对米特兰尼的观点赞赏有加。不同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米特兰尼对国际合作与区域合作中的“国家中心”有着独特的警觉,他一直批评欧洲区域合作进程中的国家倾向。“他非常正确地指出很多一体化‘功能主义者’的主要目标是沿着民族国家逻辑的一个欧洲政治共同体。实际上,如果我们反思国际组织的整体弱点,民族国家的影子无处不在:国际组织的所有评价标准(能力、共同意志、权威的单一性)都是主权国家的核心特征。”(21)
米特兰尼对主权国家以及更大范围的主权国家模式的担忧,还反映了另一个问题:主权的敏感性以及主权国家在此过程中可能的对抗。尽管米特兰尼没有指明这种建造新型国家的努力一定会遭遇主权国家的反对,但他对政府不热衷于国内社会改革的指责已经暗含主权国家未必积极进行国际合作,特别是对于任何有碍主权的跨国合作,主权国家即使表面上不会公开反对,但一定会在暗地里作梗。实际上,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很多国家热衷区域合作的真正动机不是赞同一体化,而是旨在加强自己的国内合法性与主权。(22)这实在是对一体化导向的区域合作的莫大讽刺。这大概也正是米特兰尼的批评所影射的一点,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国际形势变化后,欧洲主权国家政府的态度随之变化,使得当时被很多学者视为必然走向一体化的西欧一体化运动陷入低谷、止步不前,甚至发生反一体化的逆向外溢,而围绕上述区域主义实践的一体化理论也宣告破产并被认为“过时”。(23)直至80年代后半期至90年代初在欧洲新一轮的区域主义实践中,诸如“辅助性原则”以及“多层治理”等概念被学者相继提出。这些变化都使人们不由得佩服米特兰尼的先见之明和他的功能主义主张。
米特兰尼去世的1975年正是欧洲区域合作的低潮,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西欧区域合作的新一轮发展。西欧的区域合作发展历经曲折,而且产生了大量的理论思考。(24)但其中比较明晰、却往往遭受外界误解的一点是,目前的欧盟并不是一个类似国家的组织。作为政府间主义理论的倡导者,同时也是欧洲区域合作研究的权威,莫劳夫奇克突出强调了政府在区域合作过程中发挥的主导作用,他指出“欧洲正在力图协调其外交政策,但它在这方面的举动非常像典型的国际组织的行事方式,不像一个独特的‘超国家’机构”。他重申欧盟绝非“一个集中化的、等级制的法律结构,这对国家主权是一种侵犯”。恰恰相反,“欧盟是一个高度分散的国际制度,比通常的看法即认为它是一个正式的法律主权差远了。”其实,仔细考察其秘书处和欧盟等机构,抑或分析《欧洲人权宪章》的规章制度,都可以看出欧盟更像是一个“意愿联盟”。(25)或许正是有了米特兰尼对“全权国家”可能的预防性批评与提醒,才使得欧洲避免了走向“欧洲合众国”的道路。如果米特兰尼健在,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他一定不乏批评,但欧洲区域合作这种“非国家”的走向应当足以令其感到安慰。
此外,与后来主要用于描述、解释以及试图规划欧洲区域合作的众多理论相比,米特兰尼关于功能性国际合作的思想的普适性更强,对包括东亚在内的欧洲外的区域合作的指导意义或许更大。两位长期从事新区域主义研究的学者曾发出感慨:“不乏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区域一体化主要实践个案的欧盟,竟然构成了发展区域一体化比较研究与理论探索的一个主要障碍。”(26)无独有偶,对米特兰尼之后的欧洲一体化理论进行系统检视的莫劳夫奇克深有同感:“所有这些解释都把欧洲共同体看成是世界政治中独一无二的一个特例,并且需要一种独特的理论。这一假定导致过去40多年来,作为一个学科的区域一体化研究从国际合作的整体研究中分裂出来。怪诞的结果是,当今宣称欧共体成员政府的行为属于正常行为倒是最极端的了。”(27)莫劳夫奇克这里所点出的“国际合作的整体研究”,与米特兰尼的功能主义合作有共通之处。就此而言,米特兰尼功能主义国际合作的思想与理论,就像对欧洲区域合作一样,也会对东亚合作有更直接的启迪与警示意义。
四、东亚合作的进展与困境
尽管历史上有过不同的形态,但人们时下所谈论的东亚合作主要是指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其他区域合作运动热潮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东南亚国家以及东北亚国家间的合作态势。(28)它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最早的动议出自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在1990年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EAEG)倡议,但比较显著与系统化的发展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国际上也多称东亚金融危机或东亚危机)之后。(29)在危机爆发当年的1997年底,东盟成员国和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举行了首次领导人会议,以“10+3”为标志的东亚合作应运而生。之后,每年的“10+3”领导人会议都如期举行并不断出台新的举措,特别是在2002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提出在2010年之前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蓝图以来,东亚合作更是获得新的动力,日本与韩国也随之启动了加强与东盟国家进行合作的新机制。(30)
以中国—东盟关系改善为主要推动力的“东亚竞争性区域主义”引起了域外大国的关注与竞争性参与,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成功“嵌入”东亚合作。从2005年开始,这三个国家每年与东亚13国举行“东亚峰会”,“10+6”成为与“10+3”并行的另一个东亚合作机制。此外,美国这两年来也有新的举动,在2006年11月越南召开的第14届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美国总统布什明确提出支持并呼吁成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当时即有美国权威人士指出这是美国政府对东亚合作发起的一次“较为全面的综合回应”。(31)主要由于美国的原因,FTAAP迅速进入APEC工作议程,成为2008年11月秘鲁APEC峰会领导人宣言中关于加强APEC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排行第二的目标。(32)
东亚合作在过去十年的发展有目共睹。东亚国家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对话机制逐步完善,领导人会晤频繁。根据东盟秘书处专门统计的《东盟+3和东盟+1合作框架进展资料统计》,截止到2008年1月11日,仅在“10+3”框架下的合作机制就已经多达41个。(33)更引人注目的是,2008年底,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举行了二战以来的第一次领导人会议,正式确立了三国伙伴关系,共同发表了《中日韩合作行动计划(草案)》,并决定将三国领导人会晤机制化,2009年和2010年将分别在中国和韩国举行第二次和第三次峰会。可以期待,中日韩三国的独立对话,将对东亚合作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34)
东亚合作的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持续关注与争论。一方面,有学者发现东亚合作的独特性及其成功之处,并力图寻找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东亚的现象,称东亚为新区域主义的典型代表,将东亚的区域合作进程分为三个阶段:以内向型、政治经济为主导和追随欧洲模式为特征的“旧区域主义”;以开放、外向型、经济主导、与民族主义和跨国主义相关联为特征的“新区域主义”;以亚洲性和金融整合为特征的“第二轮新区域主义”。(35)还有学者提出诸如“竞争性区域主义”、小国引导型、开放区域主义等概念。(36)卡赞斯坦和大河原更指出,不能用现有理论来解释和预测东亚合作的未来,其根源在于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纠缠于“范式分裂”(“paradigmatic ciashes”),即为了能够拿出一个简明有力、连贯一致和自圆其说的理论,不同学派的学者们总是认定或坚持一种范式而无视并否认其他范式。他们呼吁在研究东亚合作时,必须采纳“分析上的兼收并蓄”(“analytical eclecticism”),认识到“国际关系中重要的实践性谜团最好只能通过对各种力量与因素加以综合进行解释”。(37)
但另一方面,关于东亚合作的另一种声音同样引人深思。如有人认为东亚区域动议的出现与日本所带动的东亚经济区域主义紧密相连,这种合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虽然90年代后开始有了政治和安全内容,但整体而言,冷战后东亚区域主义的出现是中国崛起的一个问题。(38)即便对人们通常认为构成东亚合作根基的经济方面,也有学者提出质疑。经过对东亚贸易、投资、地区机构、金融、领导权的大量对比分析,一位美国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东亚区域内经济往来的扩展是与整个东亚特别是中国对区域外的经济往来密度增加成正比的,也就是说,东亚地区经济相互依存本身并没有明显增加。加之“相对于在经济区域主义方面取得一些成功的其他地区而言,[东亚]地区的差异性或多样性是非常巨大的。……所有这些差异降低了东亚合作的基础。与该地区一些政治领导人的宣称正好相反,根本就没有能够把这些国家拉在一起的‘亚洲方式’,没有本质上不同于西方的共同观念”。这位学者总结道,东亚“走向区域融合的实际行动远比它们的言词要少得多”。(39)
除了学术上的争论,东亚地区的现实发展确实问题多多。尽管合作声势很大,但真正具有成效的合作并不多见。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发展的一种反映。而地区政治与安全形势更令人担忧。“中日对抗而不是和解成为当今中日关系的主旋律”,“东亚国家之间的安全顾虑、主权和领土纠纷决定了它们还不可能放弃把武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真正重要的地区意识和地区认同尚未在东亚形成”,再加之美国对东亚区域动议的猜忌和反对,东亚合作“既没有内在动力,更没有外在条件”。(40)另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最新数据,从1988年到2007年,东亚国家的年度军事开支分别为768亿、802亿、838亿、864亿、917亿、929亿、935亿、951亿、990亿、1000亿、1000亿、1010亿、1040亿、1100亿、1160亿、1220亿、1270亿、1320亿、1400亿和1520亿美元(以2005年物价与汇率为基准),尽管其增长率与绝对值并非最高,但东亚却是世界上20年来军事开支连年持续增长的唯一地区,即便是在东亚金融危机的1997年和1998年,这一数字也没有减少。(41)军事开支是个涉及诸多方面的复杂问题,但至少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亚国家军事备战与对抗的存在。
一方面是领导人会晤频繁,各种会议、声明见诸媒体的欣欣向荣的合作景象,以及被这种表象和欧洲一体化发展激发的社会各界的过高预期;另一方面却是大家日常感受到的本地区的争端、冲突与军备竞赛。那么,造成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东亚合作困境的根源在哪里?这是一个需要仔细研究的复杂问题。在笔者看来,这里的“雷声”来自政府主导的各种合作声势,而雨点则是非政府层面的各种功能性领域的跟进。在现有的41个“10+3”合作机制中,只有经济贸易投资领域中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研究专家组”的参与者是个人研究者(Private Researchers),其余都是由政府各级官员参加的合作机制。(42)就此而言,目前东亚合作“10+3”框架下98%的合作机制都由政府发起。
五、米特兰尼对东亚合作的启示
东亚合作现实发展的困境呼吁新的思维与路径。已经有很多学者提出了应对之策:或主张建立一个多元的“东亚共同体”,中日和解合作,共同领导东亚合作;(43)或建议应当“暂时同步搁置或冻结霸权干涉和大国对抗问题”;(44)或指出美国是东亚特殊的“域外国家”,东亚国家应当有足够的开放心态和胸怀,接纳美国融入或半融入东亚一体化进程,使之成为东亚一体化的成员或半成员,抑或是东亚共同体的“特殊成员”;有人还提出以中国为主导、暂时排除日本的“英国方式”;(45)更有主张继续发挥东盟的核心与桥梁作用,以小带大,最终提升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水平;(46)还有人提出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甚至创立与欧元相一致的“亚元”等等。(47)上述建议皆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却存在一个共同的前提:都需要主权国家政府的牵头与领导。而现实情况是,如果东亚地区的国家能够同心协力,也就不存在上述问题了。目前东亚合作的困境恰恰在于各个主权国家之间还缺乏强化区域合作的互信、诚意与动力。所以,真正的出路在于如何打破和克服这一点。从这一点看来,米特兰尼及其功能主义的主张对提升东亚合作的发展与规划颇有意义。
第一,我们所处的时代,与米特兰尼当时所界定的世界都处在巨变之中,全球化不但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现象,更演变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48)在此进程中,各种非政府和非国家角色大量涌现,成为国际社会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线。托马斯·弗雷德曼甚至提出,当今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已经演变成为主权国家、超级市场和超级个人三者之间的权力博弈。(49)也就是说,米特兰尼所展望的“技术性问题日益增加”已经成为人人可以感触的现实。
第二,由于上述原因,突出和鼓励功能性组织在东亚国家间合作中发挥作用,无疑是个可取同时也是不得不为之的办法。这一点在强势政府的东亚地区尤为重要:一方面,政府的作用虽然强大但亦有限,不可能渗透到合作的各个领域,多层面的国际合作势必需要多层面的功能性组织加以充实与补充;另一方面,这些功能性组织可以相对摆脱敏感的主权与政治问题,更多地从具体的问题与功能出发来决定具体的合作形式。显然,功能性领域的局部成功不但会深化该领域的合作,而且还可能产生一定的“外溢”,带动和鼓励其他相关领域的合作愿望。最终,功能领域合作的发展会促使政府逐渐认识到合作未必一定意味着主权的流失,从而逐步建构政府对跨国合作的新认识,使得东亚合作走出困境,上一个新台阶。
第三,在东亚合作过程中,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米特兰尼一直批评的一体化导向。一体化只可能是区域合作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终极目的,区域合作的真正目的在于整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时至今日,即便是欧盟在涉及一体化的问题上依然困难重重,更何况在成员国差异性和多样性程度巨大的东亚地区,一体化导向不但不现实,而且不可能,更会妨碍而不是促进合作。
第四,根据米特兰尼当初对西欧区域合作的批评,以及西欧一体化实践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陷入困境的经历来看,米特兰尼的功能性国际合作主张的价值和意义更大。这种非政府主导的功能性合作能够夯实区域合作的基础和韧性,特别是在各国政府因突然事件而对合作态度逆转时,这种功能性的合作可以避免遭受政府的直接影响而前功尽弃,为未来的合作保留基础。此外,米特兰尼的主张还是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国际合作与和平方案,不会导致比国家更大的新的政治行为体的出现,这不但符合东亚合作的现实,更可使东亚合作成为东亚国家走向整个国际和全球合作的一环,最终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和平。
米特兰尼的逻辑简单明了:世界的发展变化使得国家间需要合作,国际合作可行且最有效的方式是功能性合作,国际合作的目的是保持世界的多元、和谐与繁荣。在东亚合作中,如果主导合作进程的各国政府能够恪守这一逻辑,避免好高骛远,支持并鼓励各种层面的功能性组织发挥作用,那么东亚合作就能够走出困局,步入健康、持续发展从而最终确保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和谐与繁荣之路。
注释:
①陈峰君、祁建华主编:《新地区主义与东亚合作》,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陈勇:《新区域主义与东亚经济一体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Norman D.Palmer,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Lexington,Mass.:Lexington Books,1991.
②陈晓律:《东亚如何效仿欧盟?》,《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1期;汪丽萍:《东亚区域合作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模式比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魏玲、诺伯特·霍夫曼:《“对欧洲一体化和东亚合作的再思考”会议综述》,《外交评论》,2006年第6期;赵怀普:《欧洲一体化对东亚合作的若干启示》,《外交评论》,2005年第2期;李富有、于静:《欧洲模式借鉴:东亚货币合作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协调》,《当代经济科学》,2004年第2期。
③"Integration Theory",in David Phinnemore and Lee McGowan,eds.,A Dictionary of the European Union,2 nd Edition,Routledge Reference Resources Online,Taylor & Francis Publishing Group,2004.
④David Mitrany,The Functional Theory of Politics,London: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cience,1975,pp.4-5.
⑤有学者对米特兰尼作如下评价:“甚至直到晚年,他也未曾有过多少学术上的追随者,但是后来却有重要的学者颇不知耻地利用他的著作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肯尼思·汤普森:《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耿协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3、234页。Cornelia Navari,"David Mitrany and International Functionalism",in David Long and Peter Wilson,eds.,Thinkers of the Twenty Years' Crisis:Inter-War Idealism Reassessed,Oxford:Clarendon Press,1995,pp.214-217.
⑥Cornelia Navari,"David Mitrany and International Functionalism",pp.218-219.
⑦David Mitrany,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Sanction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5,p.9.转引自 David Long and Peter Wilson,eds.,Thinkers of the Twenty Years' Crisis:Inter-War Idealism Reassessed,p.228。
⑧David Mitrany,"Pan-Europa:A Hope or a Danger?" The Political Quarterly,1/4,1930,pp.457-478.
⑨David Mitrany,The Functional Theory of Politics,p.118.
⑩David Mitrany,"The Prospect of Integration:Federal or Functional?" in Joseph S.Nye Jr.,ed.,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Readings,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8,p.44.注意到这种巨变的还有另一位知名学者波兰尼,见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s,Boston:Bearns Press,1944。中译本见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11)Cornelia Navari,"David Mitrany and International Functionalism",p.227.
(12)David Mitrany,"The Functional Approac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Affairs,Vol.47,No.3,1971,p.536.
(13)Cornelia Navari,"David Mitrany and International Functionalism",p.231.
(14)David Mitrany,"The Prospect of European Integration:Federal or Functional",in A.J.R.Groom and Paul Taylor,eds.,Functionalism:Theory and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1975,p.66.
(15)David Mitrany,"The Prospect of European Integration",pp.69-70.
(16)David Mitrany,"The Prospect of European Integration",pp.55,59.
(17)Cornelia Navari,"David Mitrany and International Functionalism",p.233.
(18)David Mitrany,"The Functional Approac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p.535.
(19)Joseph S.Nye,Jr.,ed.,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Readings,p.viii.
(20)肯尼思·汤普森:《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第245页。
(21)Cornelia Navari,"David Mitrany and International Functionalism",p.237.
(22)Amita Acharya,"Regionalism and Regime Security in the Third World:Comparing the Origins of the ASEAN and the GCC",in Brian L.Job,ed.,The (In)Security Dilemma: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Third World States,Boulder,Colorado:Lynne Rienner,1991,pp.143-164.
(23)Ernst B.Hass,The Obsolescenc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24)关于欧洲一体化理论的发展,参考朱立群:《欧洲一体化理论:研究问题、路径与特点》,《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4期,第1-18页。
(25)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欧洲的选择〉对亚洲地区一体化的启示》,《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2期,第66、67页。
(26)Shaun Breslin and Richard Higgott,"Studying Regions:Learning from the Old,Constructing the New",New Political Economy,Vol.5,No.3,2000,p.343.
(27)Andrew Moravcsik,The Choice for Europe: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pp.4-5.
(28)Richard Stubbs,"ASEAN Plus Three:Emerging East Asian Regionalism",Asian Survey,Vol.42,No.3,May/June 2002,pp.440-455; Mark Beeson,"ASEAN Plus Three and the Rise of Reactionary Regionalism",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Strategic Affairs,Vol.25,Issue 2,August 2003,pp.251-268.
(29)Douglas Webber,"Two Funerals and a Wedding? The Ups and Downs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and Asia-Pacific after the Asian Crisis",Pacific Review,Vol.14,Issue 3,August 2001,pp.339-372.
(30)张振江:《东盟在东亚合作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3期;张振江:《东亚合作的发展与中国的作用》,《亚太经济》,2004年第3期。
(31)C.F.Bergsten,"Toward a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Policy Brief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07-2,Washington: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February 2007,http://www.petersoninstitute.org/publications/pb/pb07-2.pdf.
(32)Sixteenth 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A New Commitment to Asia-Pacific Development",Lima,Peru,22-23 November,2008,http://www.apec.org/etc/medialib/apec_media_library/downloads/news_uploads/2008/aelm/aelm.Par.0002.File.tmp/08_aelm_LeadersStatement.pdf.
(33)Database on the Cooperation Progressing in the ASEAN Plus Three and ASEAN Plus One Cooperation Frameworks,January 11,2008,pp.1-65,http://www.aseansec.org/ASEAN+3Database.pdf.
(34)张振江:《中日韩三国峰会:从敦亲睦邻走向和谐世界》,《羊城晚报》,2008年12月9日,A15。
(35)Liu Fu-Kuo and Philippe Regnier,eds.,Regionalism in East Asia:Paradigm Shifting? London:Routledge Curzon,2003,p.xiv.
(36)Zhang Zhenjiang,"China's Globalization and its Policy",Journal of Ritsumeikan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No.92.
(37)Peter J.Katzenstein and Nobuo Okawara,"Japan,Asian-Pacific Security,and the Case for Analytical Eclecticism",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6,No.3,Winter 2001/02,p.154; Peter J.Katzenstein and Rudra Sil,"Rethinking Asian Security:A Case for Analytical Eclecticism",in J.J.Suh et al.,eds.,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Identity,Power,and Efficiency,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1-33.
(38)Barry Buzan and Ole Waever,Regions and Powers: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44.
(39)Edward J.Lincoln,East Asian Economic Regionalism,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4,pp.250-252,3.
(40)潘忠岐:《霸权干涉、大国对抗与东亚地区安全的建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6期,第38-44页。
(41)SIPRI Yearbook 2008,http://www.sipri.org/contents/milap/milex/mex_wnr_table.html.它们所指的“东亚国家”包括东盟10国、中、日、韩、朝鲜、蒙古和中国台湾地区,特此说明。
(42)Database on the Cooperation Progressing in the ASEAN Plus Three and ASEAN Plus One Cooperation Frameworks,pp.1-65.这41个机制包括:政治安全与政治协调机制5个,经济贸易投资机制6个,宏观经济政策、货币与金融机制5个,农业渔业林业1个,能源机制4个,环境机制2个,旅游1个,跨国犯罪2个,健康1个,劳工1个,文化艺术2个,科学与技术2个,电信2个,信息1个,社会福利1个,青年1个,妇女1个,农村发展与根治贫困1个,自然灾害1个,矿业1个。即便这里表明参加者是“个人研究者”,但根据后来出台报告的作者可以看出,这些研究机构仍然与各自的政府密切相关。http://www.aseansec.org/17880.htm.
(43)曹云华:《论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领导权问题》,《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4期。
(44)潘忠岐:《霸权干涉、大国对抗与东亚地区安全的建构》,第43页。
(45)王毅:《亚洲区域合作与中日关系》,《外交评论》,2005年第2期,第56-60页。
(46)张振江:《东盟在东亚合作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潘忠岐:《霸权干涉、大国对抗与东亚地区安全的建构》,第44页。
(47)这方面的建议很多,主要在经济学界,如袁天昂:《从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看“华元”及“亚元”的推出》,《时代金融》,2006年第6期;张梦:《“亚元”试水从人民币起步?》,《管理与财富》,2006年第6期。
(48)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译序”第1、25页。
(49)Thomas L.Friedman,The Lexus and the Oliver Tree: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New York:Random House Inc,2000,pp.1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