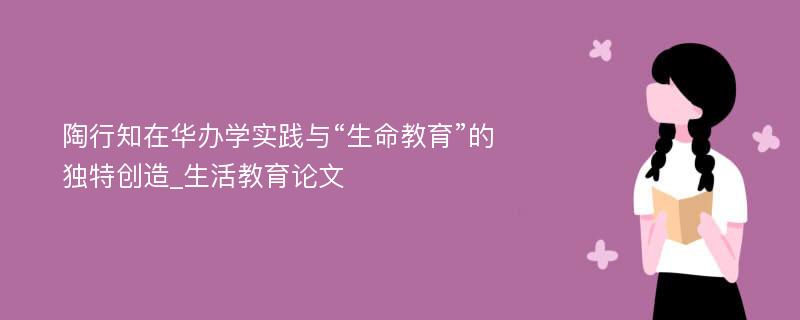
陶行知本土办学实践与“生活教育”的独特创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论文,独特论文,行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陶行知(1891-1946)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之后就始终奋战在中国教育改革的第一线,先是受聘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育学教授,一度热衷于中华教育改进社和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几年下来,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位舒适的大学教授和一般的社会活动家,而是以不挫之志在教育改革前沿开疆辟土,先后创办了别具风貌的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山海工学团以及后来的重庆育才学校。与此同时,他还在本土办学实践中不断验证和修正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提出了独具特色的“生活教育”理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杜威,为民族教育学的本土建构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筚路蓝缕,开创中国乡村师范教育的新大陆——南京晓庄师范学校 1917年9月,留美归来的陶行知即应聘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专任教师兼教务助理,其后不久,先后升任主任教员、代理教务主任、教务主任。他不仅主讲教育学、教育行政学等课程,而且借重杜威实用主义的实验精神,首倡“教学法”取代“教授法”的教学改革,力行“男女同校”与男女平等受教育权。他还热心教育团体工作,以务实、创新精神融入中国新教育洪流,积极投身于影响深远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和平民教育促进会,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教育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进程。 多年教育改革实践与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切体悟,使陶行知逐步认识到“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指出中国教育的出路与生路乃在于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的重建。在他看来,乡村学校直接关系到农民切身的生活质量,“办得好,能叫农民上天堂;办得不好,能叫农民下地狱”。[1]因此,他决定亲自办学,精心设计了其心目中的乡村学校——晓庄实验乡村师范学校,指出这一实验学校的精神“可以拿本校校旗之意义来代表。旗之中心有一个小圆圈,里面有个‘活’字,代表所要培养之生活力。圈外有个等边三角,代表学教做合一。三角上面有一个‘心’放在当中,表示关心甘苦之意。左边有一支笔,右边有一把锄头。三角之外有一大圆圈放射光芒,好比是太阳光。四面有一百个金星布满全旗,代表一百万个学校,改造一万个乡村,使个个乡村都得到光,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光。”[2] 1927年1月10日,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的招生广告正式刊载报端,直言本校的培养目标是:“(一)农夫的身手;(二)科学的头脑;(三)改造社会的精神”;考试科目为“(一)务农或土木工操作一日;(二)智慧测验;(三)常识测验;(四)作文一篇;(五)五分钟演说”。与该培养宗旨相呼应,该广告还特别表示:“本校准备:(一)田园二百亩供学生耕种;(二)荒山十里供学生造林;(三)最少的经费供学生自造茅屋住;(四)中心学校数处供学生实地教学做;(五)指导员数人指导学生教学做。”至于“考试资格”的要求更是别出心裁:“初中、高中、大学末一年半程度学生;有农事和土木工经验;及在职教师有相当程度,并愿意与农民共甘苦、有志增进农民生产力、发展农民自治力者,皆可投考。倘有志兴办乡村小学者,为预备师资见,选择合格学生,保送来校投考,尤所欢迎。”[3]其后,考试如期举行,首次正式录取当为13人,后又从补考中再招3名。 1927年3月15日,南京晓庄师范学校举办开学典礼。除指导员和16名新生外,前来参加开学活动的还有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江问渔、南京市教育局陈鹤琴等,以及附近的许多农民。陶行知在开学典礼上说:“本校特异于平常的学校有两点:一无校舍,二无教员。大凡一个学校创立,总要有房子才能开课。我们在这空旷的山麓行开学礼,实在是罕见。要知道我们的校舍上面盖的是青天,下面踏的是大地,我们的精神一样的要充溢于天地间。所造的草屋,不过是避风躲雨之所。本校只有指导员而无教师。”[4]然而,正是因为没有校舍,只有简易的茅草屋;没有教员,只有独特的指导员,陶行知决心不按常规套路办学,立定从“农村实际生活”出发办农民内心所需要的学校。声称:“本校的办法,是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本校全部生活,是‘教’、‘学’、‘做’。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我们的实际生活,就是我们的全部课程;我们的课程,就是我们的实际生活。我们每天早晨五时有一个十分钟至十五分钟的寅会,筹划每天应进行的工作,是取一日之计在于寅的意义。寅会毕,即武术。本校无体操课,即以武术代。上午大部分时间阅书。所阅之书,一为学校规定者;一为随个人自己性之所好者。下午工作有农事及简单仪器制造、到民间去等。晚上有平民夜校及做笔记、日记等。”[5]在这样的学校里,陶行知要求指导员和学生要整天滚打在一起,“与学生共教、共学、共做、共生活”。[6]指导员和学生在晓庄师范这一大家庭里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意见,其日常的生活作息安排,从起床之后的晨会、早操、清扫,到活动、耕作、自习,井然有序,确实“带有斯巴达式的简洁和明快”。[7] 晓庄师范学校在成立一年多之后,改名为晓庄学校。就组织架构而言,该校设校长1人(陶行知任校长);下设第一院——小学师范学院(赵叔愚任院长),第二院——幼稚师范学院(陈鹤琴任院长);另设中心小学8所、中心幼稚园4所、民众学校3所、中心茶园2所、中心木匠店1所、联合救火会1所、石印工厂1所等。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陶行知所创办的“小学师范学院”与其“中心小学”有着密不可分的重要关系。他说:“中心小学是以乡村实际生活为中心,同时又是试验乡村师范的中心。平常师范学校的小学叫做附属小学,我们要打破附属品的观念,所以称他为中心小学。中心小学是师范学校的主脑,不是师范学校的附属品;中心小学是师范学校的母亲,不是师范学校的儿子;中心小学是太阳,师范学校是行星。……总之,乡村教育的生路是:我们要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师范,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教师,从活的教师产生活的学生、活的国民。”[8] 不难看出,“乡村实际生活”乃是陶行知乡村教育改革的根本出发点,“教学做合一”则是其最基本的教学方法。与通常的学校不同,陶行知要求指导员和学生要滚打在一起,把教室改为生活室,注重与实际生活的密切联系。夏孟文回忆说:“生活室除阴雨天,写字、作文在校内活动外,主要活动场所是稻田、菜园里。……我们还要邀请农友在田间用实物讲解,我们边做、边教、边学,既是老师,又是学生,师生打成一片。”[9]在这样的学校里,教师和学生都是以“做”事为中心,并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出现,学校与社会、生活与教育仿佛完全融为一体,呈现出朝气蓬勃、生机盎然的景象。 二、从东部的“山海工学团”到西部的“育才学校” 正当陶行知和他的同道者大力推进乡村教育改革之时,正当晓庄学校的实验创新精神越来越引起国内外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之际,却遭遇莫名之殇,于1930年4月12日被国民政府南京卫戍司令部强行查封。对此,陶行知不顾安危地开展护校活动,声称:“晓庄的门可封,他的嘴不可封,他的笔不可封,他的爱人类和中华民族的心不可封。”[10]然而,书生的护校行动终究敌不过残暴的专制屠刀。陶行知被迫深夜出走上海,继而东渡日本。数月避难之后,他毅然回国,先是被史良才特聘为《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常以“不除庭草斋夫”抨击时弊。与此同时,他提倡科学教育,编写《儿童科普丛书》,努力求索中国教育改革的出路。 “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民族危机愈演愈烈,陶行知开始谋划着一种有别于常规学校的新型教育组织——工学团。在他看来,以读死书和死读书为特征的传统学校已经走到尽头了,他在《古庙敲钟录》中设想创办一种融“工场、学堂、社会”为一体的全新办学形式,称:“工是工作,学是科学,团是团体。……它是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一个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11]设立工学团组织的更重要原因,还在于它是陶行知乡村教育整体改革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人子弟寻找合理人生的“救命圈”,是国难深重境遇中民族教育变革的创新之举。经过实地考察,陶行知决定将工学团的总部设在上海沪太路孟家木桥附近的一所古庙中,立名“山海工学团”,其字面意思是指该工学团位于宝山与上海之间,而深层含义则是暗指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已危在旦夕,号召国人打破学校与社会的壁垒,办学不忘救国,激发国人的爱国热忱,唤醒国人的爱国情操,随时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收回我东北失地。 1932年10月1日,孟家木桥儿童工学团率先成立,实际上也是“山海工学团”诞生的标志,陶行知推荐马侣贤为团长,立即开始招生,初期招收24名学生,后增扩了一倍多。陶行知强调,工学团要努力冲破长期封闭的传统学校生活习惯,以最敏捷的方式对广大民众子弟实施最普遍的“六大训练”——普遍的军事教育、普遍的生产训练、普遍的科学训练、普遍的识字训练、普遍的民权训练、普遍的生育训练,以期养成理想的国民,实现理想的社会。山海工学团除践行“半工半读”外,还通过“即知即传人”的“小先生制”之方法创新,以促进普及教育的大面积辐射。1934年1月28日,陶行知在山海工学团召集了当时17处工学团共316人参加普及教育总动员大会,正式提出“小先生制”,并进行庄严的授旗仪式活动。平心而论,在当时中国农村经济普遍破产和传统“小成人”观念根深蒂固的情境下,实行“即知即传人”的“小先生制”,不仅充分肯定了儿童自身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独立意识和生活能力,而且暗涵唤醒中华民族“少年精神”的深意;同时也是其生活教育理论——“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的本土化实践。陶行知曾自豪地说:“小先生制是一根根流动的电线,这一根根电线四面八方伸展到社会底层,构成一幅生活教育网、文化网,把学校与家庭构成一体,彼此可以来往,可以交通。”[12] 不难看出,工学团及其“小先生制”,是陶行知乡村教育改革探索的进一步延续,是其特定时期“生活教育理论”本土化、基层化的独特创造。因为生活变化了,教育便不能不发生变化,并强烈地表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 从1936年7月11日离开香港,到1938年8月31日回到香港,陶行知远赴亚、非、欧、美,进行长达两年多的各种形式的抗战宣传。回国之后,他本有诸多为政做官的机会与际遇,但仍然心系教育。1939年6月15日,陶行知借北碚温泉北泉小学,主持召开了育才学校的第一次筹备会,对该校的创办缘起、经费预算、招生情况、课程安排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与商议,并决定暑期在北泉小学开办“夏令共学会”。其后,陶行知的同道者和追随者——方与严、马侣贤、王洞若、帅昌书、戴伯韬、孙铭勋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育才学校的实际筹建和后续工作。其中,方与严为校务部主任、马侣贤为总务部主任、王洞若为研究部主任,师昌书为生活指导部主任,实行简约化管理。 1939年7月20日,“夏令共学会”如期开幕,有难童学生30余名,见证了开幕式盛会,这一天也就成为育才学校的纪念日。陶行知在开幕式上做了重要演讲,吴玉章、冯玉祥、邹韬奋、沈钧儒、邵力子、章乃器等著名学者,亦先后前来演讲,育才声名陡然鹊起。至8月份,学生已增加到71名;第二年,学生有168名。其后学生数不断攀升,“至抗战结束的6年间,育才学校已为4500名成人和儿童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13]育才学校何以声名鹊起,其办学特点与其“生活教育”有何内在关联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其一,把握时代脉搏,顺应抗战国势,契合建国需要。在长期的普及教育运动和全民抗战的特定历史时期,陶行知深切感受到许多难童的教育需要,他说:“创办育才的主要意思在于培养人才之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者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够发展,就必须给予适当的阳光、空气、水分和养料,并扫除害虫。”[14]他明确表示,不是要培养“小专家”、“人上人”,而是对普及教育的丰富和生活教育运动的新发展。因为从中华民族解放和复兴的政治高度出发,育才不只是要对“具有特殊才能的儿童之公育,予以充分的试验”,而是“根据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抗战建国需要,用生活教育之原理与方法,培养难童中之优秀儿童,使之成为抗战建国之人才”。[15] 其二,重构人才教育,实施分组教学,兼顾基本教育。与常规的“人才教育”做法——“先准备普通的基本教育,然后受专门的高等教育”不同,陶行知主张“不作这样严格的时间上的划分,我们选拔具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在开始时便同时注意其一般基础教育与特殊基础教育。前者所以使儿童获得一般知能及优良的生活习惯与态度;后者所以给予具特殊才能之儿童以特殊营养,使其特殊才能得以发展而不致枯萎,并培养其获得专门知能之基础”。[16]为此,陶行知依据学生自己的特长和偏好,划分为若干教学小组——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自然等,一时难显其特长者可先入普通组,再视其实际发展状况而定。与此同时,陶行知聘请了许多社会名家鸿儒先后前来实际教学或开设讲座,如贺绿汀、章泯、艾青、孙铭勋、翦伯赞、田汉、何其芳、吴玉章、邓初民、周谷城、郭沫若、夏衍、周扬、程今吾等。一时间名师云集,争奇斗艳。 其三,汲取传统元素,强化集体生活,提倡创造教育。陶行知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有过很沉痛的批判,但他并不排斥传统教育的合理因素。他说:“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的指标。尤其是目前抗战建国时期,我们需要智仁勇兼修的个人。……育才学校不仅是以智仁勇为其局部训练之目标,而是通过全部生活与课程以达到智仁勇之鹄的。”[17]然而,儿童的“个人完满发展”离不开火热的集体生活,为抗战建国而奋不顾身的集体精神更离不开集体生活的熏染和培育。陶行知说:“集体生活是儿童之自我向社会化道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为儿童心理正常发展所必须。”[18]需要指出的是,陶行知关注集体,同时并不忽视儿童的特殊才华与个性创造,他说:“教育不能创造什么,但他能启发解放儿童创造力以从事于创造之工作。”[19] 其四,贴近生活世界,突显社会活动,激活校外教育。与晓庄学校一样,陶行知继续践行其“生活教育”的理念,反对把教育局限在狭隘的学校课堂。规定每周星期五下午为学校的“社会活动”日,学生们不仅送教下基层,与农民同甘共苦,而且也从底层社会和民间生活习得学问的深厚资源。社会活动并非学生单方面地服务社会;同时也是学生向社会、向民众学习的极好机会,相互补充,协调共进。师昌书写道:“育才学校的学生,本‘社会即学校’与‘即知即传’的原则,真正做到当群众的学生,又当群众的先生。”[20] 育才学校一路走来,其办学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可谓有目共睹,但其办学过程之艰辛困苦,却往往为后人所淡忘。其实,陶行知从当时全国振济委员会争取到的有限“开办费”在学校正式开办之前就已经用完,他不得不到处募捐化缘,即便学校一度将三餐改为两顿,也是举步维艰。然而,陶行知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而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昂扬的奋斗精神和不挫之志,他号召大家学学武训的行乞办学精神。1941年6月,他在《育才二周岁前夜》一文中写道:“最近几个月我们是过着别有滋味的日子,每日与米赛跑,老师跑在米的后面。……怎么办?从前武训先生以一位‘乞丐’而创办了三所学校,我们连一所学校也不能维持,岂不愧死?”[21]在他看来,学武训要学其“真精神”,其真意乃在于为伟大的抗战建国而积蓄能量、履行职责。他说:“我们所要学的武训的真精神,配合新时代之需要,普及新义学,以增加抗战建国之力量,这便是我们的责任。”[22] 育才学校先后得到南洋华侨社会、美国援华会等社会组织的大力资助,也得到宋美龄、孔祥熙、冯玉祥、张治中、图楚南、周恩来、邓颖超、卢作孚、穆藕初等诸多名人政要和企业家的帮助,但学校办学的经济危机始终困扰着陶行知及其同仁们。当友人劝他放弃这过于艰辛的办学之路,“何必抱着石头游泳”时,陶行知辩解道,自己是“背着爱人在游泳,越游越有劲”。[23]事实上,正是凭借着一股异乎寻常的顽强毅力和乐观精神,陶行知得以在困难重重的战争环境中把“育才”办成一所闻名全国乃至世界的重要学校,培养了大量的仁人志士和杰出人才。据学者统计,“育才学校从1939年开办到1949年陶行知还健在时,共招收学生410人。他们后来的去向,据不完全统计,去延安革命圣地的有22人,去中原、华北、苏北、皖南、浙东、云贵等革命根据地的有76人,……总计有140多人走上直接的革命工作岗位,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强。此外,有许多同学也在不同的条件下为人民服务,不少人在艺术、科学、文教部门经过长期磨炼,成为出色的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24] 三、“生活教育”的思想来源与独特创造 不可否认,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源自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受到其生活教育理论的多方面影响;但与杜威不同,陶行知并没有照搬杜威教育理论,而是在火热的实践中进行方向性改变,注入了其对当时中国现实国情的经验感受和理性判断,以及对本民族优秀文化教育传统的有机吸收,完成了具有浓厚本土特色的理论重构和独特创造。 杜威教育哲学的理论基础是其著名的“经验论”。杜威认为,人的机体与环境,“以某种方式起着相互作用的事物,乃是经验”。[25]在他看来,离开了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就不可能获得“经验”的结果。杜威强调,“教育就是经验的改造或改组。这种改造或改组,既能增加经验的意义,又能提高后来经验进程的能力。”[26]有鉴于此,教育必须从固守传统回归到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世界之有效改造,“教育者的主要责任,不仅要了解周围条件形成实际经验的一般原理,而且也要认识到在实际上哪些周围事物有利于引导经验的生长。最主要是,他们应当知道怎样利用现有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从中吸取一切有助于形成有价值的经验的东西。”[27]很显然,杜威“经验论”是针对脱离实际生活的传统教育而立言,他明确指斥“传统教育”崇尚“上面的和外部的灌输”,漠视儿童的生活经验,无视周遭环境的剧烈变化,“有计划地回避这个责任”。[28] 杜威的“经验论”对传统教育之负面价值有着十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但需要指出的是,其“经验论”不可能逾越其特定时期的美国历史境遇及其立场。作为杜威的弟子,陶行知固然认同其“经验论”反传统教育的合理性,并以此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作了十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但经过长期的本土教育实践探索,陶行知对“谁”之经验,以及经验的历史广度和厚度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说:“我们必须把历史的教训,和个人或集团的生活联系起来。……倘使一个人停留在自我或少数同伴的生活上,而拒绝广大人类的历史教训,那便是懒惰不长进,跌在狭义的经验论的泥沟里,甘心情愿的做一个小泥鳅。”[29]在这里,陶行知明确反对“狭义的经验论”,主张把“生活教育”与更加广大的人民大众生活和民族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使“经验”获得新的内涵意蕴。同理,陶行知对杜威起步于“困难感觉”的“思维五步法”也渐生狐疑,指出其五步法“好比是一个单极的电路,通不出电流。他没有提及那思想的母亲,这位母亲便是行动”,[30]提出由“行动”入手,继之以“困难”、“疑问”、“假设”、“试验”,方能产生正确的思想。这一思维路径同样与杜威的“思维术”异趣,显示出其浓厚的辩证唯物主义色彩。 与“经验论”相呼应,杜威在教育理论上先后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等一系列主张和命题。对于杜威的一整套教育理论,陶行知曾经十分信服,但经过多年的教育实践历练,特别是经过创办晓庄实验师范学校之后的理性反思,他逐渐有了新的认识。1929年5月19日,陶行知在晓庄学校寅会上明确指出:“‘教育即生活’是杜威先生的教育理论,也就是现代教育思潮的中流。我从民国六年起便陪着这个思潮到中国来,八年的经验告诉我说‘此路不通’。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才悟到‘教学做合一’的道理。……实行‘教学做合一’的地方,再也不说‘教育即生活’。他不再耐烦把学校变成社会的缩影,他要伸张大自然大社会里去活动,他要我们在生活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没有‘教育即生活’的理论在前,决产生不出‘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但到了‘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形成的时候,整个的教育便根本的变了一个方向,这新方向是‘生活即教育’。”[31]在这里,陶行知既肯定了杜威教育理论的启发,但同时也指出照搬该理论的“此路不通”,并和盘托出其理论转向:“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与其“经验论”的哲学相应,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注重的是教育与当下生活经验、生活过程的联系。他说:“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32]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教育理应充满朝气蓬勃的生活气息和童真乐趣。应该肯定,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凸显了教育与儿童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对于批判脱离生活实际、故步自封的传统教育具有重要价值。但杜威将“简化的社会生活”直接搬运到学校中来,这样的“生活”还是真实的生活吗?对此,陶行知明确指出,这样的“生活”乃是精雕细琢、刻意修饰的“假生活”。与之相反,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是十分广阔的,他说:“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的场所。”[33]值得注意的是,陶行知在肯定生活是教育本源的同时,极力主张“我们要前进的生活来引导落后的生活,要大家一起来过前进的生活,受前进的教育”。[34]在他看来,这种“前进的生活”首先是与下层民众及其欲求联系在一起。他说:“我们这里主张生活即教育,就是要用教育的力量,来达民之情,顺民之意。”[35]他还特别指出:“生活教育是下层建筑。……它不是摩登女郎之金刚钻戒指,而是冰天雪地下的穷人的窝窝头和破棉袄。”[36]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更是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声称:“教育没有独立的生命,它是以民族的生命为生命。唯有以民族的生命为生命的教育,才是我们的教育。国难教育是要教人救民族之命,则教育之命自然而然的得救了。”[37] 杜威的另一个重要主张是“学校即社会”。他认为,学校就是缩小的社会。在他看来,这样缩小的社会当然不是简单化地照搬现实社会,而是经过教育者优化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它“简化和整理所要发展的倾向的各种因素;把现存的社会风俗纯化和理想化;创造一个比青少年任其自然时可能接触的更广阔、更美好的平衡的环境”。[38]这样的学校比起仅仅将学校视为“传授某些知识、学习某些课业或养成某些习惯”的传统学校而言,显然具有巨大的进步。但陶行知经过多年的观察和沉思之后,发现需要进行根本的理论改造。他说:“学校即社会,就好像把一只活泼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捉来关在笼里一样。他要以一个小的学校去把社会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吸收进来,所以容易弄假。社会即学校则不然,他是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去,使他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界里去。”[39]这样一来,学校与社会的隔阂才真正打通了。与此同时,学校的实际范围也扩大了。陶行知说:“马路、弄堂、乡村、工厂、店铺、监牢、战场,凡是生活的场所,都是我们教育自己的场所,那么,我们失掉的是鸟笼,而得到的倒是伟大无比的森林了。”[40]很显然,这样的学校已经“冲开了校门”,但绝非要取消学校,而是不满脱离社会、孤芳自赏的传统学校,要求将“社会的中心”与“学校的中心”密合在一起,办人民大众所真正需要的学校,其自己倾心所办的晓庄学校和育才学校即是明证。 杜威还有一个主张是“做中学”。杜威反对静听式的传统课堂教学方式,认为儿童天生具有某种活动的兴趣和本能,学校当然要善于创造可供学生表达兴趣的活动环境,让其“做中学”,这样不仅有助于其自己的健康成长,而且能够借此与社会保持良性的协调互动,有助于适应不断变革的工业化社会现实。对于“做中学”的反传统教育价值,陶行知深以为然,他回国之后即极力倡导将习惯意义上的“教授法”改为“教学法”。此后,他进一步提出“教学做合一”的整体贯通主张,并强调“教”和“学”都是以“做”为中心。他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41]值得肯定的是,陶行知所强调的“做”,其内涵更加广阔而丰富,他特别强调“‘做’含有下列三种特征:(一)行动;(二)思想;(三)新价值之产生。”[42]可以看出,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主张,不仅凸显了“行动”的本源价值,批判了传统教育中“劳力”与“劳心”的分裂现象,而且也否定了杜威拒斥“行”为思想母亲的“思维术”及其狭隘的活动本能观,从而表现出与时俱进的大时代观和大教育观。当国难来临之际,陶行知即号召师生要共同研修一门十分重要的功课——“救国教学做”或“民族解放教学做”,称“先生要在救国的行动上教救国,学生要在救国的行动上学救国,这样才是真正的救国教学做,这样才是真正的民族解放教学做”。[43] 综上所述,陶行知吸收了杜威思想的合理内核,但同时颇能结合特定时期的中国境遇进行创造性的实践探索和理论重构,提出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生活教育”说,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杜威”,[44]实现了民族教育学的本土建构,为后世中国教育学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