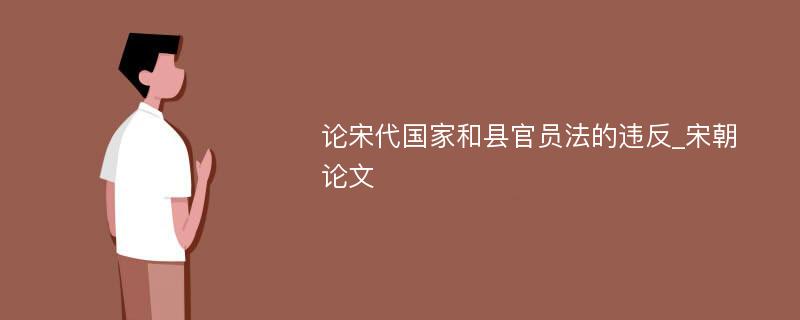
略论宋代州县公吏违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州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代州县公吏违法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正如叶适所言:“(吏胥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为甚者。”(注:《水心别集》卷一四《吏胥》)事实也确实如此,和前代相比,宋代州县公吏违法,已明显地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对此,宋人已有很多议论,近年来,不少中外学者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对宋代公吏违法的原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所有这些对笔者都有很多的启发。在此基础上,笔者不揣浅陋,也就宋代州县公吏违法现象,简要地来谈谈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一
关于宋代公吏的范围、职责,史学界已有不少论述,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本文毋庸赘述。不过为了述叙方便,本文将乡役人也纳入讨论范围。
宋人苏洵说:“夫州县之吏,位卑而禄薄,去于民最近,而易以为奸。”(注:《嘉祐集》卷九《上皇帝书》)所谓“易以为奸”,只是笼统而言,具体来说,公吏违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违法占田,隐产逃税。
宋代实行“不抑兼并”、“田制不立”的政策,使宋代的土地兼并尤为突出。公吏虽然位卑职低,但也往往利用职权乘机占有大量土地。如南康军前都吏樊铨“置买膏腴,跨连邻境,庄田园圃,士大夫有所不如”。(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一《南康军前都吏樊铨冒受朝廷爵命等事》)徽州都吏潘宗道“违法强买同分人见争田产,”当有司意欲使之退田还人,他却“阳为责退之辞,阴行谋筭之计。”(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一《都吏潘宗道违法交易五罪》)又如绍兴十五年九月三日虞祺言:“典卖田宅,出于穷窘,遂将田产破卖。多是乡豪、权贵、公吏之家典买。”(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六四)由于一些公吏负责催征赋税、攒造户口和租税帐簿,因而除了兼并土地,他们还利用手中的职权隐产逃税,如乾道元年三月三日户部言:“浙西所管营田官庄共一百五十九万余亩,内有未承佃六十七万余亩,内有未承佃六十七万余亩……多是州县公吏与形势之家通同管占,不行输纳租课。”(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二九)他们或者勾结本乡保正,“借令别人诈作卖地人名字,赴官对会推割,嘱托乡司,承认些少税役,”(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六五)或者勾结主管人吏,“不曾催纳入常平仓,上下蒙庇,官司无缘得知。”(注: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九九《约束侵占田业榜》)其隐产逃税的方式,也可谓是花样百出。
(二)、枉法受赃,倚势敲诈。
这是公吏聚财的主要手段之一。明刻本《名公书判清明集》(以下简称《清明集》)中有许多这方面的实例,如州吏黄德采取“酷虐吊打”、“因事受赇”、“恐吓欺骗”等各种手段先后诈取钱、会一千六百多贯。(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一《罪恶贯盈》)弋阳县余信到处搜刮,“既有无名钱,又有自寄钱,又有比呈展限钱,又有保正每月常例钱,敲锤骨髓,怨声彻天。”(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一《违法害民》)由于公吏的职责宽泛,凡攒造簿册、催租,摊派,捕人缉拿等基层事务所不涉,因此,他们枉法受赃、倚势敲诈的机会颇多,由头百端,最为常见的则是以下二种:
其一,里正、户长、乡书手、耆长等,他们作为宋代乡村基层政权的头目,封建政府赋予他们催驱徭役、征收赋税、监督镇压广大农民的职责,他们得以乘机重催白敷,胁取财物,敲诈勒索。欧阳修曾指出:“兵兴以来,公私困弊者,不惟赋敛繁重,全由官吏为奸。每岁科率一物,则贪残之吏,先於百姓而刻剥,老谬之人,恣为群下之诛求。朝廷得其一分,奸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庆历三年九月癸巳条)又如庆历四年十二月四日臣僚言:“……又有至下之户,平日赂不及于乡胥,则每每乱行飞摊,令被和买,俟其陈理,则其费已数倍于供输,往往甘心出纳而不辞。”(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七十之九十)五等户簿是宋代征收赋税和派遣劳役的依据。在户簿的攒造过程中,大量的调查工作,以及制作文册等许多细致具体的事务也都是经由乡书手等完成的。特别是州县三年一次的推排物力,是不法公吏敲诈、受贿的良机。他们往往乘这个机会,枉法受赃,中饱私囊。如绍兴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中书门下言:“州县三年一次推排坊郭、乡村物力,多系坊正、保正副私受人户钱物,升排不公,守令信凭人吏藏匿等第文榜,洎至人户知得,并已限满,无缘陈理,”(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一)又如淳熙十一年七月十二日臣僚言:“所在长吏多不究法意,唯凭胥吏差保正副根括。凡田间小民粗有米粟耕耨之器,纤微细琐,务在无余,指为等第,凭此抄籍其供认。”(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六之二三)公吏的胡作非为,造成簿籍不正,户等不实,赋税不均,广大贫弱百姓深受其害,国家赋税收入也因此受到影响,对这种行为,王安石也曾一针见血的指出:“造簿不正,缘吏人受赂,置之下等。及至上等无人,则又不免纠取,纠取之时,又可取赂。”(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三,熙宁四年五月庚子条)可见,不法公吏的诈取钱财,是宋代簿籍不正、户等不实的最直接的原因。
其二,公吏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司法权,曲法受赃,敲诈无辜。如《清明集》卷十二载,士兵张震之妻“中夜为强有力者挟而匿之,”推吏蒋估由于受贿赂,“阴与匿亡之家表里为一,案内紧要人隐而不追,不过泛然行根捉,苟延岁月而已。”(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二《兵士失妻推司受财不尽情根捉》)一个多月还没有结案。同卷还提到,豪横方震霆,“欺骗取夺,无所不至,弋阳之民,怨入骨髓。”此等恶霸本该重惩,然而吏王守善、徐必显接受重赂,“纵令供帐坐狱,饮宴自如,更不根究申上。”(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二《豪横》)又如饶、信二州,经常是“系狱者动辄百十人,未见有狱空之时,”其实并非是当地的犯罪率高,“皆缘官司不以狱事为意,每遇重辟名件,一切受成吏手,一味根连株逮,以致岁月奄延,狱户充斥。”而推吏乐于所为,是因为“狱户充斥,可以骗乞。”(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一《治推吏不照例禳祓》)更有甚者,公吏滥用司法职权,残害百姓。吴势卿在他的判词中就愤慨地说:“近阅诸郡狱案,有因追证取乞不满而杀人者,有因押下争讨支筭而杀人者,有讨断杖兜驼钱而杀人者,又有因追捕妄捉平人吊打致死者。呜呼!斯民何辜,而罹此吏卒之毒。”(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禁约吏卒毒虐平人》)
(三)、玩弄权柄,欺上瞒下。
公吏作为政府机构的办事人员,本应“上不侵官,下不病民,以自治其事而听命焉。”(注:叶适《水心别集》卷一四《吏胥》)但实际上由于制度和人事上的种种原因,官员却常常“为吏所欺,为吏所卖”。(注:《陆九渊集》卷八《与赵推书》)其主要表现,一是慢令,即故意拖沓,怠慢公务或违背上级的命令。如《清明集》卷十一载胡势卿处理的一个案例:宁国州吏汤友、王琮“故违安边所录匣,是慢朝廷之令也。使所行下本司追解,非惟不伏解来,抑且不行回报,本司行移交驰于道,而二吏安坐于家,是无监司也。”(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一《州吏故违安边所录匣》)又如弋阳县吏杨宜、彭信,事事慢令,江东提点刑狱蔡杭指出:“如前此李镗等状,只任收到,及本司索回状后,并不见一字行移。今来遣下格眼,系最紧切各件,其中三令五申,非不严切,已逾一限,更不缴回状词,蔑视上台,未有若此之无状者。”(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一《慢令》)二是涂改文书。如《清明集》中提到配吏郑臻、金彬、吴恭三人流毒一县,当得知有司将要处理,他们上下勾通,四处打点,甚至私自拆开文案,“藏去县丞所申,并假作缴案申状,”企图逃避惩处。(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一《受赃》)有的吏人则受人之嘱“假作批朱。”(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一《假作朱批》)象这种“郡县胥吏揩易簿案,”(注:洪迈《容斋三笔》卷十一《吏胥侮洗文书》)涂改舞弊的事例在宋代的有关文献中可以说是十分常见。
公吏违法的事例还有很多,但主要的是以上几个方面,其中又以借各种名目的敲诈勒索最为常见。如果将公吏的违法和品官违法作一个比较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一些不同之处。宋代品官违法的表现,最主要的是兼并土地,隐产逃税,经营商业、手工业、放高利贷,役使兵士等。其中的后两项,是一般的公吏难有所为的。此外,品官违法相对较为隐蔽(当然,在很多时候,品官违法之所以隐蔽,往往是他们自己不出面,而是借公吏之手所致);而公吏由于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以及文化背景和品官相去甚远,因此,他们违法更多的是采用诸如敲诈勒索等直露、粗劣的方式,这也是宋代社会对公吏违法反应强烈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
对于宋代公吏违法的原因,宋人就已有不少议论,如司马光言:“府吏胥徒之属,居无廪禄,进无荣望,皆以啖民为生者也。”(注:《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二五《论财利疏》)王曾言:“士人入流,必顾廉耻,若流外,则畏谨者鲜。”(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0四, 天圣四年春正月已亥条)王十朋言:“师帅之任,鲜或循良,昧者以胥吏为耳目,怠者以胥吏为精神,贪者以胥吏为鹰犬。”(注:《梅溪先生文集·奏议》二《轮对札子》)陆九渊言:“公人之所以得志,本在官人不才。”(注:《陆九渊集》卷五《徐子宜书》)叶适言:“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注:《水心别集》卷一四《吏胥》)等等。应该说,上述议论,都触及到宋代公吏违法原因的一个侧面,综合起来,基本上能得到就宋代士大夫而言的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但是,由于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以上议论的一个共同之处是都未触及专制主义封建制度的本身,以及宋代的时代特征。从这一意义上讲,宋人所论及的某些方面仅仅是果,而不是因。今人讨论这个问题时,则大多在宋代士大夫的认识基础上进而从官僚政治腐败、统治者的姑息放纵、儒家“仁义”治天下的主张等方面去寻找宋代公吏违法的原因。对于上述分析,笔者也深以为然。但基于以下两个理由,本文试图换一个角度,来谈谈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第一,今人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大都是将公吏违法放在广义的“官吏”概念下进行讨论。在宋代,统治阶级内部可以分为官员、吏员、公人和役人等不同的阶层,虽然他们都代表着封建国家行使各自的统治职能,但由吏以下的几个阶层和官之间却有着身份性的差别,其文化背景、产生方式、统治职能等,也各有不同。因此,尽管官、吏在利用职权违法时相互利用,狼狈为奸,但他们违法的原因、方式以及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是有所不同的。第二,宋朝作为我国封建社会中的一个朝代,既有封建社会的共性,也有其时代的特征。而上述提到的造成宋代公吏违法的诸多原因中,有的是宋代所特有的,有的则是与我国封建社会相始终的,如果对以上两个方面不加以区分,难免令人有“个别等于一般”的感觉。
我国的封建社会经过唐末五代的社会变革,进入宋代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新特点。对于宋代公吏违法问题,也应该放入这一总的背景中去进行考察。比方说,和前代相比,宋代政治体制具有官少吏多和吏强官弱这两个明显的特点,这和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化是密切相关的。宋代商品经济发达,与此同时,宋代政府又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所有这些,都是不同于前代的特定社会环境,也是宋代公吏违法活动远甚于前代的外部诱因。(注: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作为一种外部诱因,对官吏违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蔡襄说:“臣自少年入仕,于今三十年矣。当时仕宦之人,粗有节行者,皆以营利为耻,虽有锥刀之资者,莫不避人而为之,犹知耻也。今乃不然。纾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也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懋迁往来,日取富足。夫贪人日富,而居有田宅,岁时有丰厚之享,而清廉刻苦之士,妻孥饥寒,自非坚节之士,莫不慕之。”(《蔡忠惠公文集》卷一八《国论要目·废贪赃》)再加上宋代实行“不抑兼并”,允许贫富拉开差距的政策,所有这些都刺激了人们对财富的追求。苏洵在谈到南广川峡的情况时说:“其地控制南夷氏蛮,最为要害,土之所产,又极为富伙。明珠大贝,纨锦布帛,皆极精好,陆负水载,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关讥门征,僦雇之费,非百姓私力所能办。”(《嘉祐集》卷四《衡论·重远》)品官在这方面显然占有优势,以胥吏的政治、经济地位,当然不能和品官相提并论,但由于他们掌握一定的职权,一般贫民百姓自然远不能与之相比。)当然,对于一个“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者而言,仅仅是外部的诱因并不足以改变其操守。由于任何时代和社会,都存在着个人人品素质的差异,因此,排除诸如个人人品素质等这些非宋代特有的因素来探究造成宋代“官人不才”和公吏“畏谨者鲜”的原因,也许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
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主要表现,大略有宰相权力的分割;调兵权和统兵权的分离;地方州郡长官权力的削弱;官、职、差遣的区分等等。但仅仅从以上几个方面来认识宋代中央集权的强化,仍有不足。由于进入宋代以后,门阀政治的影响已经荡然无存,士族地主对地方政治的垄断成为历史,政治权力的分配方式也由封闭转为开放,中央政府对地方上的控制明显加强。同时,在技术上对地方行政组织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到既集权于中央,同时又要保证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的政权组织系统正常的运转是十分重要的。宋代的官吏制度,正是这种集权政治要求下的产物。
我们知道,宋代的政治制度中,官制和吏制是不同的两个组织系统,各自的职能范围各有分别。因此,他们任选方式和取舍标准也有很大的不同。官员的任选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关于宋代科举制的情况,学术界论述颇多,这里没有必要再重复叙述。需要指出的是,科举制中最主要的进士科的考试,自唐朝以来,就基本上是诗赋和经义两大内容,并不包含任何专门化知识。对于这种选官方法,宋代就已经有人提出了批评。如刘彝指出:“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注:《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他的老师、北宋著名的教育家胡瑗,则身体力行,本着“明体达用”的宗旨从教育入手,试图改变不重实学的风气。(注:《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一些不满现状的执政者,如范仲淹、王安石等,甚至有过全局性的改革举措。但总的来说,整个两宋时期,学用脱节的现象始终是存在的。对于那些仅以诗赋是否做得漂亮、儒家经典是否熟悉为标准选拔出来的仕宦,要他们胜任处理繁杂的日常行政事务,显然是不现实的。当然,宋代最高统治者出于集权的目的,也并不需要他们这样做,而是逐步完善吏制,通过吏人来处理各级政府机构的各类日常事务性工作,既可分散官员的权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员专门知识上的不足。可见,宋代中央集权的强化,以及与之相适应和政治体制本身,就决定了官在处理地方日常事务方面对吏的依赖。可以说,这是造成宋代“官人不才”的制度原因。
宋代吏员的任选,有子弟承袭、州郡推荐、自愿投名、吏员保引、公开考选等各种方式,真宗以后,考选是主要的选吏方式。由于吏的素质好坏,对统治机器能否正常运转具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宋朝最高统治者大都比较重视吏制建设。从宋初开始,通过有关法令法规的陆续颁布,逐渐形成了比较严格的吏员任职资格规定和任选方法。除了在年龄、品行、经济地位、身体状况等方面有相应规定外,在专业要求上,主要是能写会算,熟悉律文疏义;同时还要有一定的阅读、表达能力。这些都完全是出于事务性工作的需要。在此基础上,为了保持政权机构运转的稳定性,吏与官的任职方式也有所不同,官是任期制,任期一般不超过三年,吏则是常任制,常常数十年在任,甚至可以传袭子孙。
由上所述,官和吏的职能分工是十分清楚的,在各级统治机构中,官主要起着决策指挥、组织协调的作用;吏则主要是起着操作执行、按章办事的作用。宋代统治者正是通过由不同的产生方式和任职方式而形成的官、吏两个不同的行政组织系统,来保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庞大的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人们往往批评宋代的“官人不才”、“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等等,殊不知这种机制虽然弊端很多,但从集权的目的来看,却是颇为有效的。然而,这种对中央集权有效的机制的另一面,却是在制度上大大增加了公吏违法的可能性。
三
宋代的州县公吏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阶层,一方面,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使他们处于封建国家统治机构的底层,受到官的歧视甚至是欺压。另一方面,他们又掌握着一定的职权,直接面对被统治者,行使封建国家的统治职能;此外,所谓胥吏“非饥寒无业之徒,则驵狡弄法之辈”,(注:胡太初《昼帘绪论.御吏篇》)“胥徒皆少年无赖之辈,”(注:王柏《鲁斋王文宪公文集》二十《王梦得墓志铭》)其来源比较混杂,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和士大夫相比,更少封建道德的自我约束,因此,在“不抑兼并”而商品经济又高度发展的环境下,极易产生违法行为。尽管宋代品官违法的程度绝不逊于公吏,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违法行为都是官、吏的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但正如宋人所言:“民畏吏,吏困民,民吏相仇,而不足以相德。”(注:《嘉定赤城志》一七《吏役门》)公吏这种直露、粗劣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影响则更为直接。以致于宋代士大夫对其议论纷纷。一些勤于政事的官员甚至把“防吏如寇”(注:《斐然集》九《应诏荐监司郡守奏状》)作为为政之要。
为了维持政局的稳定,从宋初开始,朝廷就通过刑政建设和立法活动,加强了对贪赃枉法行为的惩治。但实际上在办案过程中对官、吏往往区别对待,轻重差别是很大的。以下仅以《清明集》中的有关内容,略举数例:
1.张知县、李县丞权县日,与县吏程全、王选同谋“擅创方印,印卖虚钞,作弊入己。”案发后,对张、李两人,办案者蔡杭(久轩)以“本邑贤厚贵寓曾谓其明敏可任,”而作出“人材难得,不欲玷其素履,姑免申奏”的判决。对程、王两人的判决,一个是“决脊杖十五,配一千里。”一个“决脊杖十二,编管一千里。”(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二《虚受钞》)
2.饶州推官舒济,“蔑视官箴,肆为攫拏。如本州抛买金银,则每两自要半钱,鉟销出剩,自袖入宅。提督酒库,科取糯米,受纳受糯米,官税之外,自取百金。”所有这些违法之事,舒济都是以“配吏吴杰为腹心,受成其手。”但蔡杭对舒济的处理是“对移”了事,而对吴杰,则是“决脊杖七十,於原配州上加刺配一千里,”并“籍没家产。”(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二《对移贪吏》)
3.崇安知县,“不理民事,罕见吏民,凡有词诉,吏先得金,然后呈判,高下曲直,惟吏是从。他如醉后必肆意施用酷罚,以为戏乐,又非理不法之事,有难载之纸笔者。”对这样一个淫秽贪酷的县官,办案者的处理,只是“载念知县历事已多,不应怙终如此,且与开自新之门,对移本县主簿。”而县吏叶祐、王嗣因“不能辅正知县,反利其淫昏,以为奸利之地,各决脊杖十五,编管五百里军州。”(注:《名分书判清明集》卷二《知县淫秽贪酷且与对移》)
除了以上所举数例外,官人如违法,或者“宜其不识,且免具析,”(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杖赵司理亲随为敷买丝》)或者“谆谆告诫,今后不宜如此。”(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催苗重叠断杖》)或者“如再有犯,定将重作施行,决无容恕。”(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责巡检下乡纵容随行人生事》)或者“姑书之,以告来者。’(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任满巧作名色破用官钱》)类似如此宽厚的处理,在那些“名公”的判词中比比皆是;而对吏人违法,或杖或配或流或编管,一般都作出相应的惩处。虽然在恩赦频繁的宋代,他们仍有获得减免的机会,但在判罚时,官、吏有别还是非常明确的。
可见,所谓“仁义”、“忠恕”、原则,主要还是限于品官的范围,这也是官本位的封建等级社会治小不治大,治贫不治富的具体表现。如果再考虑到官、吏违法的相互依存,互为条件,那么,不论那些“名公”的主观动机如何,他们对公吏违法的惩治,不过是将公吏当作替罪羊罢了,其客观效果则是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社会的视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