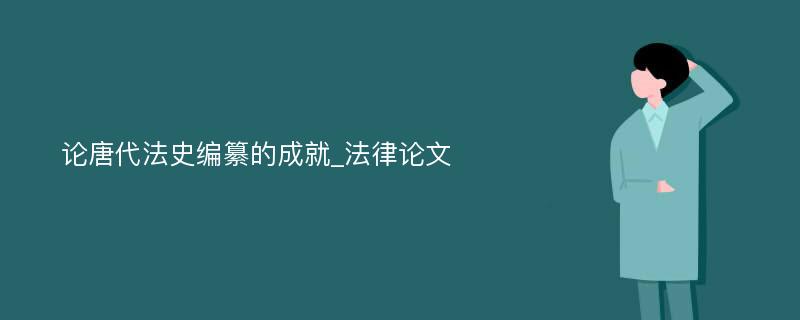
论唐代法律史的编纂成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成就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9 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5)02-0198-05
唐代史学家对法律史学展开了三次较全面的总结,第一次是在修撰《隋书》和《晋书》时从史志的角度对唐以前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总结,第二次是在编订《唐律疏义》时对注释法律进行了总结,第三次是杜佑编写《通典》时从制度通史的角度对法律制度史和法律思想史的总结。本文试就此探讨唐代总结法律史学的理论特点。
一、《隋书》、《晋书》刑法志的编纂成就
《隋书·刑法志》和《晋书·刑法志》对唐以前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总结。《汉书》创立刑法志后,直到唐代以前只有《魏书》撰有刑法志,其他正史都没有刑法志。刑法志的编纂尚未引起史学家、法史学家的重视。但自隋志及晋志之后,刑法志成为正史不可或缺的专篇,此后历代正史中除《新五代史》没有立《刑法志》外,其他正史都有,这与隋志和晋志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从通史的角度看,两篇刑法志勾勒出了唐以前法律制度的相因性。但两志又有明确的分工。隋志重在描述从梁律到隋律的相因关系。先看《梁律》,蔡法度将“齐武(帝)时,删定郎王植之,集注张、杜旧律”进行损益,而成为《梁律》。表明《梁律》是直接继承《晋律》而来的。陈朝时《陈律》,“篇目条纲,轻重简繁,一用梁法”,表明其与《梁律》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再看北齐律,它也是上承汉魏律发展起来的。“齐神武、文襄,并由魏相,尚用旧法”,这种沿用魏律的作法,一直到武成帝河清三年修成《齐律》十二篇,《新令》四十卷,才有所改变,不过《新令》依然“大抵采魏、晋故事”,表现了很大的因袭性。其后的隋律则直接继承了《北齐律》。《隋志》称隋律“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1](卷25)事实上,隋律不只继承北齐律中“十恶”的内容,而是将其主体都继承过来了,故程树德称:“隋氏代周,其律独采齐制而不沿周制”。[2](P393)这样通过对隋志的梳理,从南齐律直至隋律就有了一个大致的沿袭脉胳,此后学者多有论述补充,大抵不出其右。
《晋书·刑法志》则重在对晋代以前法律制度的总结。第一次明确提出从《法经》到《晋律》的继承关系。李悝在魏国变法时著《法经》,此后《法经》如何流传,如何对后世法律制度产生影响,班固撰《汉书·刑法志》也没有提到,特别是没有说明《法经》对汉律的影响。晋志指出:
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其后(曹魏)……傍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其序略曰:……旧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条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终,非篇章之义。故集罪例以为《刑名》,冠于律首。
……
(晋律)就汉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类,正其体号,改旧律为《刑名》、《法例》,辨《囚律》为《告劾》、《系讯》、《断狱》,分《盗律》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因事类为《卫宫》、《违制》,撰《周官》为《诸侯律》,合二十篇。
这段论述从两个方面说明了从《法经》到《晋律》的继承关系。一是从时间的角度看,从《法经》到秦律、再到汉律,再由汉律而为魏律、为晋律,他们之间有明确的继承关系。二是从内容上看,《法经》为六篇,汉律在此基础上增加三篇而为《九章律》,魏律为十八篇,晋律为二十篇,尽管在篇名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但都是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总之《晋书·刑法志》是第一次明确李悝著《法经》,并明确其是中国封建法律的渊源。这一思想被后来的《唐律疏义》所继承,该书称:“魏文侯师于(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商鞅传授,改法为律。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兴》、《厩》三篇,谓《九章之律》。魏因汉律为一十八篇……晋命贾充等,增损汉、魏律为二十篇”。[3](卷1)此后这一思想被《通典》[4](卷163)和《唐六典》[5](卷6)所继承,《法经》在制订约一千年后,其作为封建法制的渊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被确定下来,最终为人们所接受,这是《晋书·刑法志》的突出贡献。
从史料的采撷角度来看,两篇史志也是各有侧重,形成了不同的特点。隋志重在从历史的角度总结法制与国家兴亡的关系,对法制作用的认识与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晋志重在对立法思想与执法思想的总结,对律学的发展更为关注。
《隋书·刑法志序》在末尾说:“若乃刑随喜怒,道暌正直,布宪拟於秋荼,设网於朝胫,恣兴夷剪,取快情灵。若隋高祖之挥刃无辜,齐文宣之轻刀脔割,此所谓匹夫私仇,非关国典。孔子曰:‘刑乱及诸政,政乱及诸身。’”这里隋志是说实行残酷的刑罚,只是匹夫私仇,但最终的结果如同孔子所说是危及政权,危及自己的生命。隋志在后面的行文中多有论及。刑罚酷乱的结果只能是生死国灭。梁元帝“素苛刻,及周师至,狱中死囚且数千人,有司请皆释之,以充战士。帝不许,并令棒杀之。事未行而城陷”;陈后主“信任谗邪,群下纵恣,鬻狱成市……百姓怨叛,以至于灭”;北齐时“大理明法,上下比附,欲出则附依轻议,欲入则附从重法,奸吏因之,舞文出没。至于后主,权幸用事,有不附之者,阴中以法。纲纪紊乱,卒至於亡”;北周立法“大略滋章,条流苛密,比於齐法,烦而不要”,加上“宣帝性残忍暴戾……帝荒淫日甚,恶闻其过,诛杀无度,疏斥大臣。又数行肆赦,为奸者皆轻犯刑法,政令不一,下无适从”;杨坚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乃命盗一钱已上皆弃市”。他继任者炀帝“乃更立严刑,敕天下盗已上,罪无轻重,不等闻奏,皆斩……帝以盗贼不息,乃益肆淫刑”,终至“百姓怨嗟,天下大溃”。与《隋书·刑法志》之前出现的《汉书·刑法志》、《魏书·刑法志》相比,隋志留意于总结法律制度与国家兴亡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这是《隋书·刑法志》在记述刑法制度上的一个新的特征,也是对以往《刑法志》的发展。
晋志十分关注对当时丰富的立法和执法思想的总结。详细记录了张斐《律注表》的内容,集中反映了张斐在立法和执法上的思想。在立法上张斐主张要区分20种犯罪概念,对总结我国古代立法思想和指导后来的立法工作有重要的意义。在执法上张斐也提出:“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体守也”,应当“随事轻重取法”“或随事以尽情,或趣舍以从时”,也就是说对于处理案件时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罪行轻重。刘颂紧随其后提出,“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6](卷30)的著名思想。这些思想的出现,反映了两晋时期,我国立法和执法思想达到了较成熟的地步,而这一总结对《唐律疏义》具有重要的影响。
二、《唐律疏义》的编纂成就
《唐律疏义》永徽四年颁行,为中国封建法律的集大成之作。《唐律疏义》在编纂上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律疏的法典化,将私人注律最终排除在注律之外,完成了律疏的官方化与正规化。
私人为律作注解在汉代时十分兴盛,史称董仲舒作《春秋折狱》,开引经决狱和以经解律之先河。史称东汉时,“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此时律注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作律的多为经学家,因此他们都是以经解律。其弊端主要表现为:“律令本注烦杂”、“言数益繁,览者益难”,面对这种情况,曹魏时“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但又造成“但取郑氏,又为偏党,未可承用”。[6](卷30)这种局面的出现,表明以经注律已严重束缚了律学的发展。
为摆脱经学而使律学有自己的注释,西晋时出现了杜预和张斐对《泰始律》的注释,开创了古代注律的新局面。杜预和张斐的注律成就被晋武帝所认同,杜注“诏班于天下”,张注也被武帝认可,与《晋律》视为一体,具有法律效力。杜预与张斐的注律成就无疑对《唐律疏义》起了重要的启发作用。
《唐律疏义》中的律疏是在历代私人注律的基础上一次大规模的官方注律,有效地吸收了前人注律的成就,一方面避免了私人注解的混乱局面,另一方面继承了杜预和张斐的注律成就。史称:“(永徽)三年诏曰: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证,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监定”,[7](卷162)于是长孙无忌编定律疏,在永徽四年奏上,“十一月丑……颁新律疏于天下”,[8](P47)由于《律疏》是官修诏颁,因此具有极大权威性,“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8](P1454)《律疏》从一开始就不仅成为“明法”考试的依据,而且成为与《唐律》并行的法典。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有效避免了律文的多种解释,防止出现歧义。
《律疏》在编纂上的另一特色是使法律问答这一形式成为注律的基本方法。法律答问这一形式起源较早,商鞅在论述中就已指出“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吏、民欲知法令,皆问法官”,法官只能据法回答,不能随意增减,“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9]这是较早有关法官应回答法律问题的论述。从云梦秦简中的《法律答问》来看,商鞅的这一思想是被执行了的。《法律答问》内容共有187条,多采用问答形式,对秦律某些条文、术语以及律文的意图作出明确解释。但从全篇来看,《法律答问》侧重于对执法实践中的一些问题从出回答,如“甲盗牛,盗牛时高六尺,系一岁,复丈,高六尺七寸,问甲何论?当完城旦”,又如“或盗采人桑叶,赃不盈一钱,可(何)论?赀徭三旬”。[10](P153-155)此后董仲舒作《春秋决狱》也是以问答的形式来对具体案件作出回答,不过他不是依据法律条文而是春秋经义来解答,如: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抬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4](卷69)从历史上来看,这此问答都在现实中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史称:“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11](P1612)表明了这些问答在实践中的意义。董仲舒之后引经注律之风盛行,直至东晋私家注律之风始衰,[12](P180)但“法律答问”这一形式,在《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中都未著录,到《唐律疏义》将其作为主要注律形式来看,应是对这一形式的重大发展。一方面《律疏》中的答问基本上摆脱了依附经学解律的作法,同时也不局限于象秦简《法律答问》主要对具体法律问题作出解释。在注重解释法律条文的同时,也重视对一些法律问题的源流作出说明。《唐律疏义》将答问这一形式作为基本的注律方法后,后起各朝均将其作为官方注律的基本形式,《宋刑统》就是采用议和问答两种形式解释律文的。
《唐律疏义》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十分关注法律条文的简约。进入阶级社会后,奴隶社会的法律是比较繁复的,史称“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条三千”,西周时:“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13](卷5)。进入封建社会后,法律条文经历了由简单向复杂,再向简约的过程。战国时李悝制《法经》,只有六篇。到秦建立全国统治后,专任刑罚,因此,“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14](P243)后人评价说:“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15](P472)表明秦时法律条文已十分复杂。汉初废除了秦朝的苛法,刘邦始以三章之法御民,但“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16](P1096),萧何乃参照秦律,“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16](P1096)叔孙通又作《傍章》十八章。汉武帝时又在此基础上增加张汤的《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的《朝律》六篇,共合计六十篇。《汉书·刑法志》此时“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九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至此汉朝“法网浸密”。东汉基本继承了西汉的法律,史称“后汉二百年间,律章无大增减”,[17](P2872)鉴于汉律的苛重,后世屡有更作,曹魏制律十八篇,《晋律》断为二十篇。《北齐律》最终定为十二篇,史称“法令明审,科条简要”,隋《开皇律》即以其为蓝本,定为十二篇,史称其“自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1](卷25)但隋朝享国日短,加上隋文帝立法废法,《开皇律》在隋朝影响有限,但它的巨大影响带入了唐朝,唐律在形式上保留了十二篇这种结构。不过这与唐太宗追求简约的思想也是分不开的,唐太宗说:“用法务在宽简”、“国家法令,惟须简约”[18](卷8)。《唐律疏义》可以说就是继承了历代追求法条简要的思想以及唐太宗要求法令简约的精神下制定的,因此唐律条文定为五百条(现存《唐律疏义》为五百零二条),此后《宋刑统》律文502条,《大明律》律文460条,《大清律》律文436条,基本上都保持了简约的形式,这与《唐律疏义》追求条文简约是分不开的。
三、《通典》的编纂成就
杜佑在编撰《通典》时从典志体通史的角度对法律史做出了总结,明确了法律制度在政治制度结构中的地位,为法律史学在典志体通史中的地位作了逻辑性的说明。他明确指出: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
刑罚作为食货基础之上的一个具体职官职能被确定下来,而且刑罚是一项重要职能,与教化密切相关。因此,在典志体通史中给予其足够的重视也是自然的事。这是自刑法志成为专志以来,从理论上阐释其存在必要性的重要论述,也是法律史编纂理论的重大发展。
杜佑还从通史的角度写了一部简明的唐代建中三年以前的中国古代刑法制度史。《汉书·刑法志》、《晋书·刑法志》、《魏书·刑法志》和《隋书·刑法志》对不同时期的刑法史都有所总结,但由于体例所限,都没有作贯通古今的总结。杜佑则以“会通”思想为指导,第一次实现了贯通古今。这从《刑法志》前三卷的编目上可体现出来,《刑制上》记黄帝、虞、夏、殷、周、秦、汉、后汉、魏的刑法制度;《刑制中》记晋、东晋、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北周、隋朝刑法制度;《刑志下》记大唐建中三年以前的刑法制度。杜佑记载了从传说的黄帝以来,直到他生活的年代历朝的刑法制度。这种安排,固然与历代正史刑法志为其提供了史料分不开,但主要还是与杜佑在记载典章制度方面的认识有关。综观《通典》全书“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4](李翰序),很好地反映了作者的“会通”思想,刑法史的总结就是在这种“会通”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
《汉书·刑法志》、《魏书·刑法志》、《晋书·刑法志》、《隋书·刑法志》都是后朝人对前朝法律制度的总结。杜佑不宥于此,开展了对本朝法律制度的总结,开创了当代史学家总结当代法律制度的先河,这也是史学家总结法律制度史的新动向。杜佑对唐朝法制总结有两个鲜明特点。
一是以简明的文字记录了唐代法制的变化发展过程。高祖“起义至京师,约法十二条……及受禅,又制五十三条格”,立法简便易行,属草创阶段。太宗时,“据有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於隋代旧律,减大辟入流九十二条,减入徒者七十一条”,“以定令千五百九十条”,“又删武德、贞观以来敕格三千余件,以为格十八卷”,法制初具规模。高宗永徽初“分格为两部,曹司常务为《留司格》,天下所共者为《散颁格》”,“四年,有司又撰《律疏》三十卷,颁行天下”,“麟德二年,重定格式行之。仪凤二年,又删辑格式行之”。武太后时又有“垂拱格、式,识者称为详密”,这是唐代法制重要发展时期。开元初,“玄宗又令删定律令格式令,名为《开元格》”,“六年,又令删定律令格式,名为《开元后格》”。到开元二十五年对唐律进行全面总结,“总成《律》十二卷,《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开元新格》十卷”,同时还撰《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这是唐代法制完善时期。此后,直到建中三年没有大的立法活动,仅就个别具体问题进行补充。[4](卷165)
二是精详。杜佑把《格式律令事类》中的部分内容详细节录下来。从篇幅上来看,这一部分内容约占《刑制下》整卷的5/8。从体例上看,这是杜佑在记载刑法制度时唯一节录具体法律条文的地方,杜佑对这段法律条文进行了详细注释。一方面他对于封建法制中最重视的五刑、十恶、八议等条款逐条进行了注释;另一方面对一些易引起误解的法律条文进行了解释。
杜佑还将有关法制的言论从法制史中分离出来,编成相对独立的部分,撰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简明的法律思想史。这是法律史编纂上的一次创新,标志着法律史编纂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杜佑《通典》之前的四部正史《刑法志》都一方面记载了刑事法律制度,同时记载了大量有关法律制度的诏令、论议。如关于肉刑问题,《汉书·刑法志》详记汉文帝废除肉刑的诏令和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具体更定肉刑的奏言。而《晋书·刑法志》中记载言论的部分更是占了绝大部分篇幅。在《魏书》和《隋书》中也是以这种方式编写刑法志的。这样固然保存了大量的史料,但这也使关于制度史的记载条理不清楚。杜佑改变了刑法志这一做法,将有关言论从中析出,一方面使关于法制的记载更清晰、简洁,一方面也使大量宝贵的思想资料保存下来。尽管杜佑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思想史的意识,也不可能进行法律思想史的编撰,而且在史料的组织上也无明确标准,显得比较粗糙,但他这一划分,已有了明确将有关法制的言论与法制本身相分开对待的意识,对于法律史来说是有重大意义的,它对我国古代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史料的保存有重要的影响。
唐代法律史学在编纂方面的成就与当时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成熟是密不可分的,也与法律史学自身的成熟相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