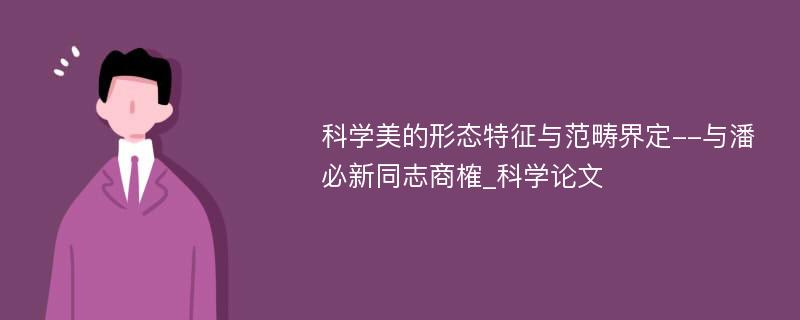
科学美的形态特征和范畴界定——与潘必新同志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畴论文,形态论文,特征论文,同志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科学美的认同, 在当代科学共同体中已经是一种不争的事实。20世纪以来,爱因斯坦重申了“我同意昂利·彭加勒,相信科学是值得追求的,因为它揭示了自然界的美”(《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04页)。杨振宁则把牛顿运动方程、 爱因斯坦的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等比作“造物者的诗篇”,说明“学物理的人在了解了这些像诗一样的方程的意义以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而又十分复杂的”。(《美与物理学》,见《中华读书报》1997年9月17 日)当代混沌学和分形几何所呈现出的绚丽多彩、气象万千的非线性自组织的世界图形,更给人提供了直观的科学美的形象。
其实,科学美的观念早在近代科学的形成过程中就已出现,并一直伴随着整个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发展。受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开普勒认为“数学是美的原型”(S.钱德拉塞卡:《莎士比亚、牛顿和贝多芬》,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当他把行星绕太阳的转动和一根振动弦进行比较时,发现不同行星的轨道有如天体音乐一般,构成一种宇宙的和谐,所以他以行星运动的第三定律来表达乐曲“和谐的序曲”的主题。
《“科学美”质疑》一文(作者潘必新,见《哲学研究》1997年第12期)对于科学家心目中的这种科学美如何纳入传统美学体系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众所周知,任何美(审美价值)在形态上都需具有可感知的形象性和情感激发作用。该文作者认为,科学美并不具有这两种审美特质,因此与传统美学体系是不相容的。对于这一点,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而文中所提的一些问题,确是探讨科学美所应回答的。
一
传统的西方美学是把艺术作为研究的中心,但是许多美学家和哲学家也并未忽视在艺术领域之外同样存在审美价值。德国美学家玛克斯·德索在谈到审美对象时指出:“假如我们从自然的审美对象转向人类自己设计的范围——除了艺术之外——我们便发现审美需要强烈得几乎遍及一切人类活动。我们不仅力争在可能范围内得到审美愉快的最大强度,而且还将审美考虑愈加广泛地运用到实际事务的处理中去。人们主要的精力,在理性与工艺活动中始终都偏向于呈现出一种审美的形式。”(《美学与艺术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还进一步说明:“艺术与科学既不同而又互相关联;它们在审美的方面交会。”(《美学原理
美学纲要》,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英国哲学家罗素说:“数学,如果正确地看它,不但拥有真理,而且也具有至高的美,正像雕刻的美,是一种冷而严肃的美”。(《我的哲学发展》,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3 页)这些表明,他们都肯定在艺术美之外也有科学美的存在。
尽管科学是诉诸于人的理性,而艺术诉诸于感觉和情感,但是两者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却应该符合美学的基本规定。不能简单地将科学美视为理性美,把艺术美视为感性美,因为审美活动是感性与理性相互交融统一的过程。科学美作为一种审美范畴,是完全可以纳入整个美学体系之中的。
对于科学美产生的疑惑,首先是虑及它能否成为一般人的审美对象。众所周知,美作为一种价值关系的存在物,是以行为主体与审美对象的互动作为存在前提的。任何审美对象的存在必然对应于特定范围的审美主体,离开了它的审美主体,它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说来不是对象, 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之一的确证”。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9页)对于科学美的审美主体说来,要想获得数学或物理世界中科学的美感,他就要具备相关的数学或物理学知识,以便在对其意义的领悟中产生相应的审美意象。这一点对于科学美或艺术美说来,情况是完全一样的。盲人不会去欣赏绘画,他们无法理解光和色彩的世界意味着什么。同样,“科盲”对于科学一无所知,科学美当然不能成为他们的审美对象。
任何审美对象都是依靠它所具有的审美特质,才取得自身的审美价值。这些审美特质首先是可感知的形象性和由一定意义蕴含所产生的情感激发作用以及给人的愉悦感。
科学美是否具有某种可感知的形象性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随着文化的发展和人类心理功能的进化,人的感知方式逐步多样化,不仅存在直观的方式,也产生出间接的感知方式。这就使科学意象获得了它特有的形象表现。
显而易见,自然科学是探索自然界运动规律和内在结构特性的,它并不停留在直观的外在现象层面,而要深入到事物的内部结构和运动中去。不论是研究宇观范围的天体运动,还是研究微观范围的原子物理,都要借助一定的观测或实验设备。利用望远镜可以观测星空中的天体,利用显微镜可以观测细胞和微生物。这是对人类感官能力的一种延伸和扩大,但它们还是直接与人的感官连系在一起的。然而,在原子科学领域,粒子加速器等试验设备则超越出人类的感官,它是借助其他物理媒介间接地展示出不可直接感知的世界。
科学成果有它特定的形象性,它们是由科学意象的符号化构成的,如定性的科学模型或定量的数学表达式。前者如卢瑟福的原子模型、电子的波粒二象性图象、湍流或生物的分形几何图,都是从特定角度揭示其物理内涵的近似代表物;后者如麦克斯韦方程组、牛顿力学公式等,它们是以数学结构表述与其相关的物理内涵,以数量关系表现出不同质的特性。后者在科学形象的构成中具有普遍的作用。
海森堡指出:“理论物理的数学符号也就是这个客观世界的符号,物理学家借助于这些符号就能描述世界未来的事件。”(戈革:《尼耳顿·波尔——他的生平、学术和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0页)当一种有效的符号把陈述结构与表达的内涵丰富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时,它便能获得一种审美的形式。例如麦克斯韦方程组表明:变化着的电场和磁场是以光的速度传播的,而光也是一种电磁波。由此,光、电、磁便统一在电磁波之中。它不但证实了牛顿的设想,说明不同颜色的可见光的区别只是波长或频率的不同,而且有效范围还延伸到红外线和紫外线的整个领域。同样,爱因斯坦根据时空性质推出的质能公式E=mc[2],以数学符号的简洁性揭示了自然背后物质运动的一大奥秘,说明了整个世界质量与能量的转化关系。这些表达式无不闪烁着科学美的光辉。
上述科学美的审美形象并不是直观的。这种情况,在艺术领域也有类似之处。语言艺术,例如文学便是通过语言符号的媒介作为物化的手段,其艺术形象也具有间接性。它要依靠审美主体对语言的解读和转化,才能形成艺术形象。当然,文学语言虽然是概念性符号,但它却具有较强的表象性和情感色彩,所以容易激发人的想象力,产生如临其境、如视其形的效果。由于语言媒介与思想的直接联系,也使语言艺术所形成的意象具有了更加丰富的精神内涵。这一点,与科学美以数学符号取得它的形象表现力可以相比拟。
总之,科学活动中也有形象思维,它是意象形成和想象力发挥的基础,而想象力又是促成科学创造活动中直觉形成的一种因素。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规律,……要通向这些规律,并没有逻辑的道路,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爱因斯坦文集》第1 卷,第102页)
那么,科学美是否具有情感激发作用呢?诚然,科学研究具有非拟人化的特点,它要排除个体感官和情感因素对于实验和观测结果的影响。科学符号虽然不是人的情感的表现,但是当人在观照和反思它时,仍会唤起情感甚至激情。科学理论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同时又是人的思想创造。科学所呈现的世界图象的那种和谐、简洁和秩序感,作为人的理智成果和逻辑力量的展示,可以唤起人的审美感受。这是一种思维性的情感,它体现了情感与思维的契合关系,由于理性思维的参与而使情感具有更大的容量和更深的思想内涵。在这种审美愉悦中还会夹杂着“一种庄严感、一种神圣感、一种初窥宇宙奥秘的畏惧感”(杨振宇语)。
二
科学美所展示的世界图象与艺术美所展示的自然图象,其形态特征有共通性。
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是以哥白尼日心说和牛顿力学的提出为标志的。牛顿完成了近代物理学的第一次大综合,把万象纷呈的自然界通过力学的纽带编织成一幅统一而和谐的图画,以科学定律的简单性反映出自然界运动的某种客观规律。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认为,自然哲学的任务不仅要揭示出宇宙的结构,而且要揭示出我们在宇宙中看到的一切秩序和美从何而来。在这一科学的世界图象中,宇宙犹如精巧设计出来的一架巨大的钟表装置,它服从于决定论的因果联系。
然而,现代物理学和非线性科学的发展,使人类的自然图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狭义相对论否定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念,量子力学打破了严格的决定论和主客体的绝对二分,非线性科学对复杂系统进行整体性和动态性研究,推翻了还原论的简单性世界观,说明非线性关系才是系统各层次和各部分之间普遍存在的关系。爱因斯坦在提出狭义和广义相对论时,从逻辑简单性原理出发,以最少的逻辑公理构筑起整个理论大厦,发挥了解释、预言和发现新规律的功能。他进一步提出了对称性,即变换不变性原理,在狭义相对论中应用了洛伦兹变换不变性,在广义相对论中又把对称性提升为物理学的普遍原理。“一种对称性的发现比一种特定现象的发现意义重大得多。像旋转不变性和洛伦兹不变性这样的时空对称性,统制着整个物理学。”(阿·热:《可怕的对称》,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81页)
对于形式特征的发现和运用,在艺术和审美领域也形成了一系列形式美的法则。对称便是各种结构形式对应关系的表现之一,同样在艺术中是达到平衡的重要手段。黑格尔指出:“要有平衡对称,就需有大小、地位、形状、颜色、音调之类定性方面的差异,而这些差异还要以一致的方式结合起来。只有这种把彼此不一致的定性结合为一致的形式,才能产生平衡对称。”(《美学》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79 年版, 第174页)达·芬奇的油画《最后的晚餐》、 拉斐尔的油画《雅典学院》都是采取了对称的构图,但人物的安排却充满变化,给人造成突出的张力效果。相反,戈雅的蚀刻画《马德里斗牛场的横祸》则采用不对称的布局,画面左侧一片空白,由此来强化悲剧效果。
其实物理学的定律是以非线性为开端的。开普勒对天体轨道的研究就是对非线性系统的研究。其后人们在水流实验、声光衍射和电声实验、气象预测中遇到了一系列非线性现象。由于非线性的数学处理十分困难,在经典物理学中便使用近似和简化原则来看待各种复杂现象。到本世纪80年代混沌学的研究表明,世界的本质是复杂的,而非线性正是这种复杂性的根源。
在几何学上,分形便是复杂非线性关系的一种表现方式。无标度特性系统具有层次的自相似性结构,它是层次变换下的一种不变性,也是一种对称性。根据简单性原则,分形几何为研究自然界形形色色的复杂结构提供了十分简洁的工具,使原来认为是“病态”的“怪物”,呈现出新的秩序和奇妙无比的美。它在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以及经济学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在动力学上,系统各层次间的非线性关系表现为“折叠式”操作,这种关系导致混沌。然而在这些“紊乱”现象的背后却有着惊人的规律性,它是随机性与确定性的统一。混沌理论把表现的随机性和系统内在的确定性机制结合在一起,从混沌中发现了秩序和大自然形成的奥秘。在集合论中,非线性关系表现为不同元素对集合从0至1连续阈的隶属度,从而产生了模糊数学。模糊数学反映了客观存在的真实状态和人的思维中概念的模糊性,可以更真实地模拟人脑的模式识别和判定事物的模糊特性,广泛用于人工智能和自动控制中。传统的数理逻辑是二值逻辑,非此即彼,它人为地将各种判断绝对化了,而无视事物状态所存在的差异和变化。
当代科学形态注重对事物整体性的相互联系和动态过程的展示,它为人们呈现出一幅朦胧与明晰、确定与非确定相统一的世界图景。这与传统的审美形态特征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审美是对于对象的整体性观照。审美的整体性特征,正如司空图在《诗品》中针对“雄浑”风格的形成所说,“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人对作品形象的审美感受正是寓于“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从而使人在具有“韵外之致”的意境中获得自身的审美意象和体验。对此,杜夫海纳也曾指出:“一所茅屋之所以迷住艺术家的眼睛,是因为它与半野生花草、空旷的小山谷、橡树的浓荫浑然一体,十分和谐,茅屋是作为自然的要素而不是因为它是茅屋而取悦于人的”(《审美经验现象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页)。
艺术结构中也充满简单性与复杂性相互交替的情况。有人说民族器乐《二泉映月》的旋律结构与混沌学对湍流现象揭示的相空间奇怪吸引子轨迹相类同。湍流中有不同尺度的漩涡相互嵌套、互相贯穿,其相空间奇怪吸引子呈现出连续的回线,它们无限延伸而永不相交,却始终包围在一块有限的面积内。《二泉映月》的乐曲从头至尾浑然一体,时时处处体现着发展层次和变化,它的“天问”给人一种永恒追问的苍茫感。同样,巴赫的钢琴曲《音乐的奉献》,以卡农的技巧构成了首尾相接的变调,用复杂的赋格实现了不同层次的自相缠绕,其中隐藏着数学的规律性,即哥德尔定理所揭示的自我相关的数理逻辑中的怪圈。
艺术形象的模糊性具有明显的不确定特性,从而唤起人的丰富联想和梦幻般的诗情。正如王维在《汉江临眺》一诗中所说:“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这是一种从有限到无限、从明晰到朦胧的含蓄美,使人在形象的感悟中“浅深聚散,万取一收”,而艺术的表现力正是在于那种“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语)。传统诗论中所说的“诗无达诂”,齐白石提出的绘画之妙在于“似与不似之间”,都是对审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阐释,“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饮酒》五)。
三
要确立科学美这一范畴,需要将它与自然美、艺术美等审美范畴加以明确区分。在这些审美范畴之间,肯定既存在联系也存在本质的区别。正是这种联系使它们能纳入整个美学理论的体系,而它们的区别则是它们各自构成不同范畴的根据。
“自然”这一概念是与“人工”相对应的,自然物便是指非人工制作物。自然物只有进入人类社会生活的视界才有审美价值可言。自然美重在外观形式,它是以物质形态的感性特征来引发人的审美感受的,这种审美特质或来自色彩、质感、形状等物质属性,或来自比例、均衡、反差、对称以及和谐等结构性要素。它与人的审美心理的契合根源于两者的异质同构性。在内容上,它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比较间接或隐晦。作为一种环境因素,人们往往外在地赋予它们某种寓意或象征。在自然美的背后,隐含着美与真的联系,它是以善为中介对自然规律性的一种观照。
艺术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具有反映社会现实以及表现和建构精神世界的双重功能。与社会现实的第一性存在相比,艺术是第二性存在(意识形态的反映性)。艺术美是艺术品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如果说自然美和社会美是第一性的现实美,艺术美便是第二性的反映美。艺术是通过对现实生活中个别的、偶然的和具体形态的模写去反映和表现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真实。因此艺术形象的结构本质属于特殊性范畴,它处于个别性与普遍性之间。艺术美重在形象的情绪感染力和内涵表现性。它的背后反映出美与真或善的联系:它或是以真为中介的对社会目的性的观照,或是以善为中介的对社会规律性的观照。
科学美与自然美具有根源上的联系:从世界统一性的角度上说,科学美是自然美的一种折射。正如海森堡所说,“自然美也反映在自然科学的美之中”(《精密科学中美的含义》,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2年第1期)。 因为两者的共同基础源于自然界自身的和谐和秩序,只不过一个表现在外部现象上,一个表现在内部结构和运动中。因此,科学美的本质也反映了美与真的联系。另一方面,科学美与艺术美也有共同点,它们都是第二性的反映美。然而,由于两者的反映方式不同,形成两者形象的结构本质的不同。科学反映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它所涉及的是普遍性范畴,而艺术反映则是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表现,它涉及的是特殊性范畴。这就使得科学美的面貌给人一种冷峻感,它是以数理符号作为表现媒介的;艺术美却充满情感色彩和个性的表现。
研究美与真的联系,是探讨科学美的本质的核心所在。真善美的统一或同一,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但是作为一种价值标准或尺度,真、善、美各有其自身的质的规定性。这就是说,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直接等同的关系,真的不一定就是美的,美的也不一定就是真的。济慈在《希腊古瓮颂》中曾经写下了“美就是真,真就是美”的诗句,它成为表述审美直接性的著名格言。在这里“美与真的同一性,是纯粹审美体验的直接含义,因此也是对艺术进行思考的一个永恒的命题”(卢卡契:《审美特性》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63页)。然而,这种文学表述并不能取代具体的美学分析。
德国数学家W.克鲁尔在《数学的审美观照方式》一文(见《数学智者》第9卷第1期,纽约英文版)中指出:有两种不同的数学家,一种是把数学美作为自己研究的基本要求,对于论证和表述的明晰性和引人入胜十分看重;另一种则把数学的价值只是放在其定理的无以辨驳的确定性和逻辑的不可置疑上。这两种态度的不同,直接影响到他们研究的取向。后一种数学家,包括德国数学家D.希尔伯特,为了追求理论的确定性,把算术视为最可靠的基础,往往将问题还原到更简单的逻辑系统中,下苦功夫在复杂而无吸引力的工作上,献身于数学的基础性研究。而侧重审美取向的数学家,对这种基础研究的兴趣不大。他们不仅注重新定理的发现,而且在论证的组织上要使每一个定理必然导致下一个定理,以致使读者在详细验证之前,在一瞥之中就会认定这是再好不过的结果了。例如因式分解a[2]-b[2]=(a+b)(a-b),便可以给人以极大的美感。
库默尔和戴德金便是这种审美取向的数学家。他们确信,代数数具有与基数整数结构同样简单和美的结构。从审美理想出发,他们创造了通用理想数论。若没有一种审美理想,很难设想会在数学中引入这种理想数和理想因子。在戴德金发现了通用理想数论主要定理之后若干年内,他并没有把它出版,尽管他有逻辑无误的论证。因为这个论证在他看来还不够明晰,还不能满足他的审美要求。所以对他说来,不仅要发现定理,而且同时要发现一种恰当的表达方式,使之能满足数学的美感要求。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数学形式的审美表述赋予了极高的价值。
另一位数学家克罗内科曾经用拉丁文写下了一个对仗句:
Nos mathematici sumus isti veri poetae
Sed quod fingimus nos et probare decet
(我们是数学界的真理诗人,
但我们的创造还要经验证。)
上述例子可以说明,真虽然是科学美(数学美)的前提,但科学上真的并不一定就是美的。同样,由于科学真理具有相对性,一些过去认为具有科学美的成果,今天可能暴露出在真理性上的失误和局限。例如莱布尼茨的数学论证,虽然今天已经失去了数学的有效性,但它作为特定时代的科学成果,仍不失学术的伟大意义和审美的魅力与风采。
科学中美与真的联系,它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美可以引真。为什么审美观照方式可以促进科学创造;形式美为什么可以成为科学家的一种直观判据,有助于科学的发现,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只能留待他文了。
责任编辑注:潘文见本专题1998年第2期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