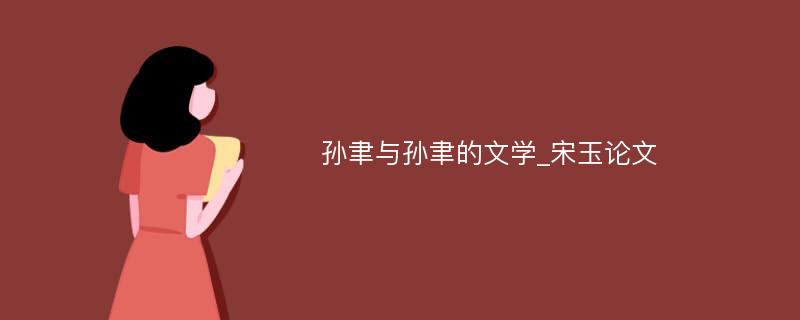
宋玉的文学与文学的宋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宋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1)05-0153-06
一、多面体的宋玉
宋玉的文学,归功于宋玉的创造与接受者的喜爱。两者同样重要:如果宋玉的文学没有那么广阔而有趣的话题,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接受者蜂拥跟进;如果宋玉的文学没有那么出色的质量,就不会有接受者绵延2000多年的欣赏热情。
文学的宋玉,同样归功于宋玉的创造与接受者的再创造。没有宋玉多层次多侧面的自我表达、自我描绘,以及游戏君王、贬损同辈、漠视女权、俗化女神、谈政治、谈女人、谈性欲……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赞美或憎恶。有趣的是,宋玉的文学正是在后人千变万化的趣味和情感的激烈争执中,其青春的活力才没有衰竭,艺术的生命才不致枯萎。
宋玉创造文学,也被文学所创造。真正享有这种待遇的文学家屈指可数:庄周、宋玉、司马相如、李白、杜牧、柳永、苏轼、秦少游、唐伯虎、徐志摩、林徽因等。
在某种意义上说,不被遗忘才是真正的活着。他们活在自己的作品里,更为难得的是活在别人的作品里,活在别人长长短短、或浓或淡、或褒或贬、或文字或口头的无休无止的话题中。
无限的多面就接近于圆体。宋玉的形象并非扁平、单一,而是比较丰满、接近浑圆:是宫廷的,也是民间的;是高洁的,也是世俗的;是真诚的,也是矫情的;是写实的,也是编造的;是欢乐的,也是感伤的;是澎湃的,也是冷静的;是嬉戏的,也是严肃的;是肤浅的,也是深刻的;是轻浮的,也是沉重的;是可赞的,也是可批的;是可爱的,也是可怕的;是好斗的,也是温情的;是正面的,也是反面的……惟其如此,宋玉形象才可能比许许多多正襟危坐、非礼勿言的圣人君子更具文学的魅力,更得接受者的青睐,更容易成为喜爱者、厌恶者、敌视者共同的传播对象。
二、“登徒子”之谜:“官名”+“子”
关于“登徒子”,现有三说:其一,“登徒”是复姓,“子”是尊称,登徒子犹如孔子、孟子。其二,“登徒”即“左徒”,楚国官职名称,“子”是后人因为不明“登徒”本义而添加。其三,“登徒”是楚国外交部门的官名,“子”是尊称,《战国策·齐三·孟尝君出行五国》有“臣,郢之登徒也”一语可证。笔者1993年即主张“登徒”是楚国官名,“子”是尊称:
“登徒”是楚国上大夫官名,“子”是尊称,颇疑“登徒子”即景差,因不便直呼其名,故以官名代之,以“子”尊之。①
但直至目前,一般人只愿采取第一种说法。但这一说明显缺乏文献证据,也就是说先秦叫做“登徒某”或“登徒某某”的,目前可以说一个也没有发现。第二种说法虽然仅限推测,但颇具启发性。经过近20年的研究,笔者认为第三说更加符合事实。
既然根本没有人姓“登徒”,同时又与“郢之登徒”的楚国官名相冲突,严格说来,主张“登徒”是复姓,应当是不能成立的、错误的。只是传统的惯性力量太大了,多数学人还不太情愿、不太习惯接受“登徒子”就是“官名”+“子”。说来真怪,没有一点佐证的说法,居然会被沿袭如此之久而浑然不以为非。习惯之糊弄人,一至于斯!当然,也与笔者当年没有举出古代“官名”可以+“子”的证据有很大关系,不能将全部责任往外一推了之。
1993年之后,笔者留心古籍中有关“官名”+“子”的例证,果然有所发现,证实当初猜想不误。2003年,笔者趁编写高等学校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两汉诗歌部分的机会,在注释辛延年《羽林郎》的“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后文还有“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时指出:
金吾子:对执金吾的尊称,犹战国末楚人称登徒(官名)为登徒子。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亦载:“至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执金吾:羽林军中的高级军官。掌巡逻京师,汉初称中尉,武帝时改称执金吾,地位与卿同。金吾本是一种铜棒,汉代卫戍京城的武官手执金吾巡夜,故名。[1]
“执金吾”可以省称“金吾”,依此,也可推测“登徒”乃“左登徒”、“右登徒”的省称之说是准确的。王莽时的“史通子”与“金吾子”、“登徒子”一样,皆是“官名”+“子”的模式,大约与今人所谓“部长先生”、“总理阁下”没有本质的区别。虽然汉代的“史通子”、“金吾子”晚于战国的“登徒子”,三者不具备时间的同步性。但它们是同一地域、同一民族、同一文化系统中时间距离仅有100-200年左右的职官称谓②,具备前后关系的趋同性。因此可信度比较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莽本是博学并实行复古之人,东汉著名学者桓谭批评他“嘉慕前圣之治,而简薄汉家法令,故多所变更,欲事事效古,美先圣制度”[2],既然“欲事事效古”,那么,他对“史通子”的任命(命名),就绝不会于古无征。
再有一个理由,就是西汉学者包括王莽见到的战国职官的材料,也可能比后世学者多得多。因为教材只是针对学生发行,一般学者不屑问津,也难以问津,致使极少有学者知道可以将“登徒子”、“金吾子”、“史通子”联系起来考虑。
此外,桓谭还介绍了一位叫做“张衡”的学者被封为“阳城子”:“阳城子姓张名衡,蜀郡人,王翁(王莽)时与吾俱为讲学祭酒。”[3]这位“张衡”,不知是否就是葬于南阳的著名辞赋家、科学家、《两京赋》和《归田赋》的作者,有待进一步考证,但“阳城子”显然属于一种官职或封号。以上对“登徒子”之谜的解说,想必已能成立,但“大夫登徒子”则极为少见,还需再费笔墨。
按《小言赋》开篇云:“楚襄王既登阳云之台,令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并造《大言赋》,赋毕而宋玉受赏。”《大言赋》开篇则云:“楚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游于阳云之台。”注意《大言赋》“宋玉”之后没有“等”字,所以在阳云之台进行大小言游戏的始终是楚襄王和他的三个大夫。两文的排名顺序极有讲究:小言时景差在前,大言时唐勒在前,任何时候宋玉都排在最后。唐勒在前时没有“大夫”二字,景差在前时特地冠以“大夫”之称。这一变化说明宋玉相当小心,不能得罪任何一人,但又必须突出景差更为高贵的贵族身份(景差与楚王同姓)。“大夫登徒子”之称,应该是由“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变化而来:“大夫”是三人共有的平级官职,“登徒”及其它官职则是“诸大夫”具体担任的次一级职位。再举一个不一定非常匹配的例证,即彭德怀元帅曾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贺龙元帅曾任“副总理兼体育部长”、陈毅元帅曾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如在国际交往活动中,可称陈毅为“副总理外交部长先生”。如此,“大夫登徒子”就不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怪名怪物了。
三、“悲哉!”——第一个妙用惊呼语调作诗文发端的文学家
不妨说,年轻时的宋玉是一个情绪型的诗人、作家。遇到刺激,一定会惊叫、高呼、呐喊,藉以减轻内心的压力与伤痛。遇到攻击和伤害,一定会绝地反击,不留情面,用词尖刻,入骨三分,瞅准机会,认准死穴,一招毙命,让对手臭名昭著,一(遗)臭万年!当然,他也会花言巧语,强词夺理,自我文饰,自我贴金,自我保护。
不幸的是,登徒子没有看透宋玉这个功力不凡的语言杀手的厉害,贸贸然趁宋玉偶然不在楚王身边之际,私下里对楚王说宋玉这个青年长相太漂亮,说话太动听,(平时还会弹琴和唱歌)对少女少妇太有魅力,本性又特别好色,千万不要带他出入后宫。潜台词是,以前您让宋玉这个好色之徒出入后宫,说不定已经……这可是要人脑袋的阴狠毒招③。谁知楚王太喜欢宋玉了,同时也想看看宋玉这小子如何表态,顺便也提前给他一个实实在在的警告。再见宋玉之时——当时还有一个国际贵宾“秦章华大夫”在座,楚王就迫不及待地将登徒子的话原原本本地加以转述。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清楚了,在宋玉的语言利剑之下,登徒子果然“死”得很惨很难看!虽说在1958年,浪漫诗人毛泽东在读宋玉作品时动了恻隐之心,曾经两次想以翻天覆地的伟力,试图为“两千年不得翻身”的登徒子平反昭雪,认为登徒子堪称婚姻模范[4]——其实毛泽东的内心是极为喜欢宋玉的,宋玉的那把“倚天之剑”,他就“抽”去挥舞了一回,将巍巍昆仑“裁为三截”。——但广大国人和多数学人并不知道还有这等最高指示,即使知道,心下是否完全认同也很难说。所以直至今日,“登徒子好色”或“登徒子是好色之徒”的印象和结论,依然铁板钉钉,是一桩“读书人都知道”的常识中的常识。写到这里,宋玉是可爱还是可恨,我似乎也有点说不清了。不过,我倾向于宋玉是可爱的,他只是将一场“自卫反击战”打得过于漂亮而已。
将《登徒子好色赋》这桩广受楚国“高层”关注的公案牵扯进来,是想让更多的人具体领教宋玉语言的冲击力、杀伤力、威慑力、征服力:激烈的情感,激烈的语言,如天雷贯耳,如天剑击地,一旦出口,或者出手,所向披靡,不可抗拒,不可翻案,悠悠千载,威力如故。
《九辩》首章,最能见出宋玉的情绪喷涌,惊呼连连、不可抑制:
悲哉!
秋之为气也!
萧瑟兮,
草木摇落而变衰。
僚慄兮,
若在远行,
登山临水兮,
送将归。
后边,紧接着又是一连串简短而急促的呼叫:
泬廖兮……
寂漻兮……
惨凄增欷兮……
怆恍懭悢(音旷朗)兮……
坎廪兮……
廓落兮……
惆怅兮……
2000多年过去了,我们已经无法完全明白这些极为拗口的惊呼与叫喊,到底包含了多少痛苦、多少愤懑、多少挣扎、多少不平、多少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的、激烈的情感。《九辩》作为200多句、1500多字的长诗,估计没有几个人能够一口气读完,也没有多少人能够记住它总共说了些什么。但是,开头一句“悲哉!秋之为气也”,让绝大多数人过目不忘,精神为之一耸,明确知道它表达了什么。因为它实在太独特了!
后来有几个作家兼诗人学习《九辩》的高唱发端,学得很像,也都写成了名篇。散文一是江淹的《别赋》,二是李华的《吊古战场文》,三是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诗歌则是李白的《蜀道难》。《别赋》第一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吊古战场文》首句:“浩浩乎”。《祭十二郎文》的开篇:“呜呼!吾少孤……”④《蜀道难》的第一、二句是:“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如果单就诗歌而言,李白之后,好像已经绝唱了。当然,现代诗人多的是“啊!啊”,可惜,名篇再也见不到了。
四、解构神圣:女人、性欲、政治权力与民间叙事的多重语义
如果想要更为清楚地认识宋玉的某些迷离惝恍的侧面,一定要认真地、深入地解读宋玉文学的民间性。因为那些精彩的语言,缤纷的形象,奇异的情节,可能不少就源于民间传说、民间笑话,不一定完全是真人真事。民间文学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一旦要对某些不太符合老百姓胃口的正统观念、权威人士、神圣事物进行解构,往往先从女性、性欲、性事着手,言在此而意在彼,利用多重语义增加叙事的深度,利用“色”彩增加叙事的有趣性、可听性、可记性和可传性。以现代民间话语表达,就是多多少少都要带一点“色”、“黄”、“荤”。
先看《高唐赋》所言之“巫山神女”:
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王问玉曰:“此何气也?”……玉曰:“昔者先王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⑤
请注意这里的核心句:“妾巫山之女也”云云,文字与下述5种古代文献存在极为明显的差异。
第一,“昔先王游于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台。闻王来游,愿荐枕席。’王因幸之。”(《文选》卷31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之十一“尔无帝女灵”句李善注引《宋玉集》)
第二,“我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台。”(《文选》卷16江淹《别赋》“惜瑶草之徒芳”句李善注引宋玉《高唐赋》)
第三,“我夏帝之季女也,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台。……闻君游于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唐·余知古《渚宫旧事》卷3《周代下》引《襄阳耆旧传》)
第四,“我帝之季女也,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台。……闻君游于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399《人事部40·应梦》引《襄阳耆旧记》)
第五,“宋玉所谓天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阳。”(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34《江水》)
对比今本宋玉《高唐赋》“妾巫山之女也”,五种文献同时具有“帝之季女”、“夏帝之季女”、“天帝之季女”以及“未行而亡”两大信息。从唐人李善两次引文——《宋玉集》、《高唐赋》来看,都有“帝之季女”、“未行而亡”两句,可以肯定古本《宋玉集》一定不缺这两句。今本所无,应是后人——现存《高唐赋》收入今本《文选》,主编是萧统,梁朝的一位太子、级别最高的后备干部——加以删除。
“帝之季女”,不管是“夏帝之女”,还是“天帝之女”,均表明身份高贵,年龄幼小。“季女”即最小之女、最末之女。“未行而亡”,即未嫁而亡,依然处女,表明纯洁。巫山神女,最初可能是精心挑选并精心养护,然后在祭祀仪式上献给巫山神灵的纯洁少女。献祭完毕,即隆重地安葬于巫山,更往后则是立庙于巫山。后世送去和亲的,难道不都是一律身份高贵的纯洁少女吗?偶尔有出身不太高贵的,也要加封之后方能送出。至于西门豹治邺之前献给河神为妻的,不也是纯洁的少女吗?国外民族学方面的例子就更多了。这一点跟国家政治、跟国土安全有关。巫山是楚国门户,巫山失守,楚国就无险可据。祭祀巫山、守护巫山,对楚国而言是头等大事。后世对此有所疏忽的楚王,理应让巫山神女前来“发蒙”(《高唐赋》)——受一点传统文化、国防知识的启蒙教育。同时“思万方,忧国害”(《高唐赋》),才不枉神女远古献祭神灵的牺牲、后来“自荐枕席”的苦心。这本身也是双赢的事业:巫山无虞,国泰民安,就能保证年年向神女献祭,至少是常常献祭;巫山落入敌国之手,国灭民殃,祭祀中断,就会断送神女的国家级的享祭。献祭为何单单选用少女(处女)?前文说是为了纯洁。纯洁,就意味着献祭者(君王,酋长,族长,大巫)或献身者(少女)对神灵的真诚、虔诚、崇拜和忠心。
宋玉笔下的人间少女,至少有两位具有向宋玉“自荐枕席”的自我牺牲的意愿。一位是他家乡的盖世美女,出现在《登徒子好色赋》里。另一位是他出差住宿时遇见的店老板的美丽女儿,出现在《讽赋》里。年轻的宋玉虽然身在朝廷,服务国家,服务朝廷,但对哺育他成长的家乡还是满怀记忆、爱恋、信任和感激的。在他无端地、突然地受到政敌攻击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家乡,就是家乡那些独特的民间文化资源,那是他最拿手的反击敌人的秘密武器。而他最熟悉的,莫过于长时间暗恋他的温情脉脉的邻居女郎。经过别出心裁的极具宋玉特色的语言包装之后,“东家之子”成了全天下、全楚国美少女星空中最耀眼的巨星。只要宋玉说她“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所谓“好色”的指控,就立即不攻自破了。与东家之子相比,外乡的“主人之女”完全是另一种性格,另一种形象:出奇的大胆,出格的大胆,坦诚唱出“君不御兮妾谁怨”的歌声。当然,从女权主义角度看,这是宋玉的栽赃,是宋玉的心事与想象,是宋玉的歌声而非少女的歌声。宋玉开始弹奏的《幽兰》《白雪》之曲——幽静、寒冷的曲调——没能让少女的情欲之火冷却,反而激情燃烧,盛装丽服,抽钗解发,挑逗宋玉。宋玉赶紧弹奏更为幽冷的《秋竹》、《积雪》之曲——大面积冷色调的“秋竹”比“幽兰”更能使人冷静,体积更大的“积雪”也比“白雪”寒冷得多,但这一切都不能熄灭少女愈发高涨的激情烈火,坚持唱出在“玉床”上“横自陈兮君之旁”。这一冷热相抗、雪火互拼的心理博弈的场景,堪称古今一绝。当然也与宋玉的极端矫情、超级自恋、自我崇拜交织在一起。
宋玉常常一不小心,就将一种刻意隐藏的自命不凡、同时也是真正不凡的身份和意识显露出来——美少女们“愿荐枕席”,就是突出的一例——暗中比拟君王待遇,尽管宋玉最终拒绝了、放弃了这种待遇。
但这两个超级美少女的出场,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帮助宋玉解构神圣:两个披着神圣外衣的同僚,假借神圣的名义,干着一点也不神圣的阴暗卑鄙的勾当——背后放冷箭。前一人是大夫登徒子景差,楚国世袭的贵族,宋玉曾经的朋友⑥,楚王身边的高级干部,一个也许很不对老百姓胃口的“神圣人物”,前文已有介绍,此处本来应该直接跳过,考虑到要将他与后一人——唐勒(也有学者认为此君才是登徒子)进行对照,所以还是照录俩人背后攻击宋玉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语:
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词,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王以在之言问宋玉。玉曰……(《登徒子好色赋》)
楚襄王时,宋玉休归。唐勒谗之于王曰:“玉为人身体容冶,口多微词,出爱主人之女,入事大王,愿王疏之。”玉休还,王谓玉曰:“为人身体容冶,口多微词,出爱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讽赋》)
“短宋玉”和“谗之于王”没有差别;“体貌闲丽,口多微词”和“身体容冶,口多微词”完全相似;“又性好色”与“出爱主人之女”不同,前者抽象,后者具体。不过,两者貌似相近,但却差别不小,而且最容易被人忽略:“又性好色”是本性如此,一贯如此,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有证据可以成立,无证据也可成立,证据不实照样成立——这是一种非常恐怖、极难对付、具有百分之百杀伤力的流言蜚语;至于“出爱主人之女”,倘若属实,确是一次失足,但也许还在“可以教育好的青年”之列;“愿王勿与出入后宫”与“愿王疏之”差别巨大:前者隐有杀机,后者只是建议。“入事寡人,不亦薄乎?”可以理解为“在朝廷为寡人工作,不是有欠庄重吗?”说明楚王比较清醒,不搞偏听偏信,一定要亲自向宋玉调查所谓“出爱主人之女”的指控是否属实。
两篇文章的命意和效果具有天壤之别:在《登徒子好色赋》中,因为登徒子告阴状说宋玉“好色”的话,经过楚王在外事活动的场合进行转述,使得宋玉在国际来宾的眼里丢尽了颜面,所以必须狠狠还击、十倍百倍还击!也让登徒子这家伙的名声在国际舞台上臭不可闻!结果不仅登徒子本人惹火烧身,堕入污池,万劫不复,而且近乎“灭门”——辱及登徒子夫人和五个儿子:真惨!他们以后如何在高干家属圈子中混呢?对于登徒子之妻的极端丑化,显然出于极度夸张和部分杜撰。反观《讽赋》,宋玉并没有对唐勒进行穷追猛打,更没有给唐勒及其家人带来任何灾难性后果,连楚王也被宋玉临场虚构的、如何摆脱“主人之女”步步进逼、紧紧纠缠的“惊险”故事迷住了,连连惊叹:别说了!别说了!要是处在那样的情景中,寡人早就成为她的俘虏了……连楚王也做不到的事,宋玉成功做到了,宋玉不是比楚王还要神圣,至少也和楚王一样神圣了吗?
《好色赋》和《讽赋》显然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重罪重惩,轻罪轻饶。区别对待,很讲政策。差异如此之大,读者诸君不妨想一想:登徒子、唐勒——他们会是同一个人吗!
两场貌似神圣的“检举揭发”,两位神圣之人——背地里假惺惺向楚王奉献忠心,实质上是借着捏造的罪名,打击排挤尚未结婚的年轻同事的所谓高级老干部,就这样以丑剧、笑剧和闹剧告终。神圣,就这样被“色”彩“艳”丽的笑话解构了!
然而,在解构别人神圣的同时,宋玉用他变幻莫测、风情万种、擅长民间性叙事的欢乐话语,也将自己“守身如玉”的“神圣”——对楚王、对楚国的洁白忠贞轻轻松松地建构成功了!“当在政治上欲打击某人时,就尽力搜寻他在私生活上‘腐朽糜烂’的证据并加以宣扬,反之要表彰某人时则去找出一堆他个人道德纯洁崇高的‘先进事迹’……”[5]这种将政治上的节操与个人生活中的道学态度直接联系起来的思考问题的方法,虽说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万古不绝,但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则非楚国文学中的登徒子、宋玉莫属。
由登徒子所谓“好色”引发的事件,并没有到此结束。宋玉如此盛赞东邻少女的盖世风采,如此大言不惭地在道德上自我“美容”和自我“广告”,固然可以化解和撇清“好色”的指控,但这样做不是没有风险的!倘若其他大夫追问:既然你的东邻少女是个风华绝代的世界小姐,宋玉你为何不首先推荐给咱们英明的楚王?三年时间不算太短,宋玉你从不汇报更从不推荐,你的忠心何在?倘若楚王真有兴趣,派人侦察索取,而东家之子又并非天下绝色,或者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东家之子,宋玉你又如何交差?这不是犯下了欺君之罪吗?可见凭空虚构的文学“证据”和肆无忌惮的吹牛实在太冒险了!
如果连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宋玉还有什么资格继续留在楚王身边工作?还有什么智慧可以继续对楚王进行政治讽谏?换了其他人,也许会一筹莫展。不过宋玉处理起来,依然轻松自如。他首先让国际友人秦章华大夫把自己臭骂几句:
今夫宋玉盛称邻之女,以为美色。愚乱之邪臣,自以为守德,谓不如彼(登徒子)矣。且夫南楚穷巷之妾,焉足为大王言乎!
意思是刚刚宋玉盛称他的邻家少女,以为美色。这个头脑愚笨、思维错乱、心术不正的家伙,自以为谨守道德,没有登徒子那么好色。其实,南楚小城穷巷子里的姑娘,有什么值得向大王夸耀的呢!(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宋玉这个乡下野小子的脑袋可能进水了)
你看,秦章华大夫几句发言,小骂帮大忙,立即将宋玉使劲的吹嘘和可能的困境彻底解构了:“东家之子”一旦和“南楚穷巷”捆绑在一起,其美色度马上直线下滑,几近于零!然后,秦章华大夫再将他“少曾远游,周览九土,足历五都。出咸阳,熙邯郸,从容郑、卫、溱、洧之间”所见的各色美女介绍一番,她们不仅“华色含光,体美容冶”,而且“扬诗守礼”,比那个只会死爬楼梯登墙偷窥一言不发毫无求爱技巧的乡下小姑娘的综合素质高到天上去了!
宋玉就这样跳过了自己在不经意中挖下的巨大陷阱,在文学中成了语言角斗场上的东方不败——
于是楚王称善,宋玉遂不退。(《登徒子好色赋》)
一场本来惊心动魄的政治角斗,双方都拿女色做进攻的利器或防御的坚盾。在快速闪过一张张美女和仅有一张极其丑陋的女人面容之后,角斗停止了,沉寂了,烟消云散了,你不得不惊叹:神了!
但有一些语言战场上创造和使用的独家利器流传了2000多年,风流俊美的宋玉、好色变态的登徒子、美到极点的东家之子、丑到极点的登徒子之妻、口多微词、又性好色、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他们(它们)在后世的礼教社会中虽然上不了大雅之堂,但却久久风行于广大民间。解构的是一朝一代一时一事令人生厌的政治阴谋,建构的却是千秋万代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欢乐语汇……
宋玉创造文学、创造形象、创造符号、创造话语,也用文学创造自己、美化自己、保存自己、宣扬自己、传播自己。哪些是文学的宋玉?哪些是宋玉的本真?哪些是文学的幻影?哪些是历史的原形?这恐怕又是未来几千年的话题。
注释:
①详见赵明:《先秦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93页。
②“执金吾”,汉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由“中尉”改置。
③“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词,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此类告密的信息隐有杀人的动机,请参阅《战国策·齐策三》所记孟尝君事:“孟尝君舍人有与君夫人相爱者。或以闻孟尝君曰:为君舍人,而内与夫人相爱,亦甚不义矣,君其杀之!”诸祖耿编撰:《战国策集注汇考》(增订本),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575页。
④据说,林纾有一次讲授韩愈《祭十二郎》文,以凄楚哀抑的声调,朗读头一句“呜呼,余少孤”五个字,其声呜咽,似闻啜泣。学生中有身世之感者,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讲解这五个字,林纾费了一小时还没有收束,连上四堂才讲完这一篇。
⑤引文据吴广平编著:《宋玉集》,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50页,为便于读者查阅,以下宋玉作品的引文均出自该书。
⑥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卷一《人物》:“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冢。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景差惧其胜己,言之于王,王以为小臣。”指明景差是宋玉友人而且“惧其胜己”。但更早的两条西汉的资料——韩婴《韩诗外传》卷七第十七章、刘向《新序·杂事第五》,均未点明宋玉友人是景差。从时间上说,韩、刘更接近宋玉、景差;从空间上说,习凿齿与宋玉、景差生活在同一地域。从史料的真实性看,各有优长与缺点。笔者认为,韩、刘之记明显带有为尊者讳的官方倾向,所以没有点出贵族景差之名;习凿齿之记则带有更多的民间记忆与评价,所以扬宋抑景,借屈原抬高宋玉,说宋玉“始事屈原”(此说已为当今学者否定),但绝不讳言景差曾是宋玉友人并且“惧其胜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