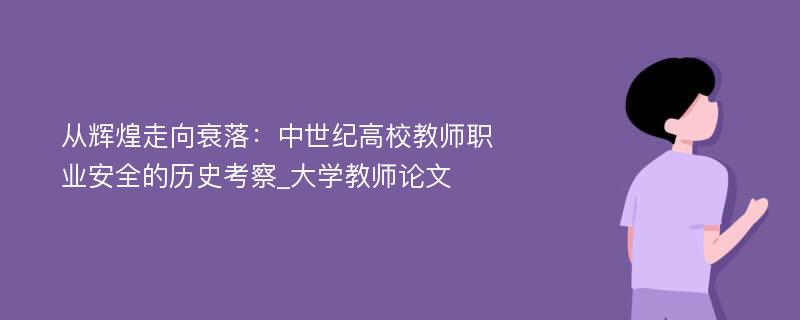
从辉煌到衰微——中世纪大学教师职业安全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师职业论文,辉煌论文,历史论文,纪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学教师一贯具有知识分子品性中的个人独立性和批判性,“在许多国家,对政府和社会进行严厉批评已经成为高等院校里的一种生活方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可能有这种情况。”[1](P283)事实上,这种“生活方式”早已有之,并非形成于当代,在国家之间也并无太大的区别。但问题是,这种不同寻常的“生活方式”往往会招致被批评者的不满和嫉恨,而这些被批评者又经常是政府或社会中的强势群体或个人,因此,毫无遮拦的特立独行很可能会给大学教师的职业安全带来威胁。历史上,以各种理由或借口解聘、开除甚至迫害大学教师的案例并不鲜见,它常常令教师们大失所望,但这种伤害并没有导致教师们的退缩,相反,激起了他们抗争的信心、决心和行动。这种伤害和抗争还同时带来了一个积极的效果——它促成了被伤害者思考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进而争取了许多特权(privilege)。
一、大学特权的形成条件
(一)中世纪城市自治传统
中世纪西欧城市的文明对今天的西方国家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看来,“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到,逐渐自乡村的最终破产中脱颖而出的城市,实在是高级历史所普遍遵循的历程和意义,我们便不可能了解人类的政治史和经济史。故而,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2](P353)与此相类似,要理解大学和大学教师种种特权的形成,也必须追溯到中世纪的城市以及城市中的大学。
美国社会学家波齐(Gianfranco Poggi)认为,“在中世纪的西方,城市的发展不只是生态学那种独特的定居……而且还是政治上的自治统一体。这种自治权常常通过反对勒索他们的敌对势力、对付来自领地统治者及其代表或封建势力,或者是来自西方的明白可见的阻力而取得。”[3](P40)到11、12世纪,西欧的城市随着人口的增加和贸易的频繁而日渐繁荣,城市不仅仅是生态学上那种独特定居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在教士、贵族两大传统阶层之外,新兴的市民阶层逐渐形成。
“市民”(burgenses)这个词“于1007年第一次出现在法兰西;1056年出现在佛兰德尔的圣奥梅尔;后经莫泽尔河地区(1066年出现在于伊)传入神圣罗马帝国。”[4](P93)当市民阶层队伍逐渐壮大,并且凭借众多的人员和富裕的经济而获得力量之后,对于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向往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他们所要求的首先是人身的自由……其次他们要求赐予一个特别法庭……再次他们要求在城市中建立治安……最后他们要求相当广泛的政治自治和地方自治。”[5](P105)经过各种曲折和努力,甚至是暴力冲突,大约到12世纪,基本的城市自治制度逐渐形成——“每个城市都是一个自治的市民社会,各自制定法律、自行征税、自管司法、自行铸币,甚至根据各自需要结成政治联盟、自行宣战或媾和。”[6](P174)
在中世纪,市民身份是一种权利的象征,城市居民只有获得了市民身份才能参加市政活动,出任城市官员,参与城市管理。而城市居民要获得这一身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例如,13世纪意大利西拿的市民特指拥有规定量的财产、居住在城市当中,并证明有能力从事城市活动的人们。但在中世纪大学形成之初,来自欧洲各地的师生们并不拥有大学所在地的市民身份,“著名的教师居住的城市享有自治权,外地学生不在国王的保护之下。市民和欧洲的学者们常常有争执,总是可能发生暴力行为。直到14世纪初期,大学的历史还充满了有关打斗、凶杀、骚乱和酗酒闹事的记载。”[7](P93)因此,为了有效地保护自己,作为学者行会的大学也试图团结起来争取更多的自治权利。
(二)教会、王权与大学的关系
在日尔曼民族征服西罗马帝国后的社会动荡期中,以罗马教会为首的基督教会利用自己的文化和政治统治经验,成功地使蛮族征服者和整个西欧皈依基督教。随着10世纪城市的复兴,新型经济和社会思想的变革动摇了中世纪初期既定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观念,教会与世俗王权之间,及其各自内部越发激烈的政治纷争导致了政治权力多元化的进一步扩散。而政治纷争与权力多元化的结果就是,任何一方绝对权力的滋长与蔓延得到了强有力的抑制,各种力量对社会组织的单向控制力大大削弱,大学遂成为政治力量争取的对象用以抗衡其他各方。
在中世纪大学诞生之前,修道院或教会学校是当时唯一教授读写能力的地方,因此,教会对包括大学在内的学校教育的控制根深蒂固。“主教们愈是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们就愈是想要捍卫自己的统治拒绝臣民的要求,并且愈是想要将臣民保持在专制独裁和家长式的制度之下。”[4](P107)而在世俗王权看来,大学不仅给他们的王国带来财富和声望,同时也是对大小官吏进行教育和培训的场所,因此,“他们希望像对自己领地上的居民那样,对自己王国里的城市大学成员行使自己的权威。”[8](P61)在中世纪权力斗争当中,无论是为了巩固对大学的控制,还是企图渗透对大学的影响,均遭到了大学不同程度的反抗,而各种政治力量纷纷通过“特许状”(charter)这一独特的政治法律文件确立起自己与大学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特许状所规定的自治程度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有所不同,现存的最早注明为公元967年的法兰西城市特许状,仅仅给予居民免受奴役的自由。而大学通过特许状,师生可以不再负担许多封建义务,并逐渐拥有独立的司法权等众多自治特权。事实上,特许状并非是完整细致的法律条款,在更多情况下,它只是提出了解决问题、协调关系的主要原则和方法。但是,在特许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大量惯例和不成文的习俗与规定给大学对自由的诠释和对反叛的辩护提供了更大的话语腾挪空间。因而,特许状成为大学自由与独立的象征,使拥有者备加珍惜。
二、辉煌的时代
在凯伯尔(Pearl Kibre)看来,中世纪大学与教师的特权是“一种自由,一种由国王或教会赐予社团或个人的与普通法相符或超越普通法内容的自由。”[9]这些特权大多数名义上是授予大学的,但最终都落实到教师(部分涉及学生)身上,对于维护中世纪大学与教师的自治地位和自由传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本文中仅讨论与大学教师职业安全有关的特权。
(一)作为一种合法身份的生存特权——城市居留权
中世纪城市传统的合法成员只有教士、贵族和市民,并非所有人都能成为城市的合法居留者。因此,从进入城市的那一刻起,大学师生们就要和各种各样的困难作斗争,但首先遭遇的是,他们所聚集的城市并未准备收留他们,他们被视为动荡的根源,常常被当作不受欢迎的人。“各大学在它们出现的城市里,由于它们成员的数量与质量,是一种令其他势力感到不安的力量的表现。”[8](P60)因此,要获得城市生活的合法身份,最重要的事情是与土地的所有者——主教、修道院或者占有土地并执掌司法的伯爵与领主达成居住协议。
公元115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 Barbarossa)在进驻意大利时,接受博洛尼亚大学部分师生的请求,颁布了“证据的常例”(Authentica Habita)这一文件,在文件中腓特烈一世不但肯定了知识的价值,而且对那些为了追求知识而远离家乡的人表示了钦佩,给予到博洛尼亚学习的师生(主要是日尔曼籍)在城市中居住和自由活动并不受该城法律管辖的特权。而城市有责任、有义务为大学教师提供适合于居住和不受干扰地进行教学活动的场所。①至此,大学教师可以合法地成为城市中的一员以法令的形式被明确,并为后来出现的大学在处理其成员与城市的关系中所援引而成为一种惯例。中世纪城市也被形象地分为三部分:“第一,商人、手工业者和普通百姓,名为大城;第二,宫廷周围的贵族和大教堂,名为旧城;第三,大学生和教员们,名为大学。”[8](P66)
以教学与写作为业的中世纪大学教师诞生在城市而非乡村有其历史必然性。只有交通便利、贸易频繁的地点才最有可能发展成为新兴而繁荣的城市,而只有城市才需要掌握知识的大学教师参与当时法律制度的完善、宗教文化的发展、医疗技术的传播并为此培养后继人员。然而,相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大学师生是外地人,甚至是外国人,他们并不熟悉或者有时索性并不考虑所在城市的规章制度与风俗习惯。在城市居民眼中,城市既因为大学师生的加入而变得更具活力和生气,也由于大学师生的“肆无忌惮”而越发混乱与无序。城市居留权的获得,首次从法律与制度上明确了大学师生也是城市当中合法成员这一社会事实,合法身份的确认为大学教师出于知识传播与发展的需要安全地、不受歧视地来往于中世纪城市之间创造了条件。
(二)作为一种自治组织的法律特权——独立司法权
中世纪城市享有高度自治权,而城市自治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在城市当中存在着各种各样自治的行会组织。中世纪行会事实上又是一个立法团体,各种各样的行会都订立自己的制度用以规定入会条件、成员身份、工作时间与标准、竞争的规则与保护等等。与其他行会组织所不同的是,大学在同样享有内部治理的自治权利的同时,积极争取到了处理与外界关系时至关重要的特权——独立司法权。
在正式颁布的“证据的常例”中规定,如果有人由于商业方面的问题要对学生起诉,学生有权选择传唤起诉者到大学教授面前或者到本市的主教面前进行陈诉,而大学教授与教会主教对这类事件均享有审判权[10](P170),换句话说,大学可以设立自己的特别法庭,以审判与大学师生有关的案件,这一规定同样为后来的大学所援引,成为要求政治力量授予大学独立司法权的依据。例如,在牛津师生的积极争取下,英王亨利三世(Henry Ⅲ)于1244年开始,就不断赋予大学教师广泛的司法权,大学教师可以审判任何牵涉大学成员的诉讼案件,内容涉及债务纠纷、房屋租赁、食品买卖、马匹租用等诸多方面。[11](P92)而在剑桥,1381年大动乱中城市居民抢走并焚烧了皇室特许状等文件。动乱之后,皇室恢复了大学的特权,并宣布成立大学民事法庭,享有独立司法权。[12](P43)但在法国,巴黎大学由于与教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从属于教会司法体系的管辖,自身缺乏独立的司法权。尽管如此,1200年,由于与市民之间的严重冲突,巴黎大学师生求助于国王,国王“奥古斯都”菲利普二世(Philip Ⅱ Augustus)随即颁布敕令规定,凡涉及大学师生的案件必须交由教会法庭审判,世俗法庭无权干涉[13](P295),同样对大学师生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
自学者们从欧洲各地聚集一堂并最终形成大学那一刻起,大学就是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而存在于中世纪城市。一旦与所在城市居民发生纠纷而又被城市法庭加以审判,显然对大学师生不利。总体上说,中世纪大学无论是与教会或世俗王权还是与城市中的市民阶层相比,应当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要想在冲突中切实维护大学师生的正当权益,唯有获得对冲突进行裁决的司法权,至少要取得对冲突的一方——大学成员——进行内部审判的权利。如果说城市居留权给了大学教师某种合法地存在于城市的身份,那么独立司法权则是保障这种身份的所有者在城市中自由地活动而不必担心稍不留神的冒犯可能带来牢狱之灾的严重后果。然而,独立司法权也为另一种情况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即大学教师也很有可能因为持有纯粹的学术性不同观点而遭受“自己人”的审查甚至不公正的对待,而外界很难干预。尤其当这种审查染上浓重的政治色彩并事实上为外部势力所控制时,将会对大学教师的职业安全构成严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威胁。
(三)作为一种学术职业的文化特权——教师资格和学位授予的专一权
在鲍尔生(Friedrich Paulsen)看来,教学权、考试权和学位授予权是中世纪大学最主要的特权之一,而这些特权都是宗教权威——罗马教廷赋予的。[14](P4)众所周知,在中世纪,获得大学学位意即获得了教师资格,但由于大学教师是教士,大学教学从属于教会管辖,因此在中世纪大学成立之初,获得学位具备教师资格之后,还要得到由教会中负责教育事务的“总监”②颁发的授课许可证(Licentia docendi),方可开门授徒。
从公元9世纪开始,“由于商业消失,城市生活的最后痕迹随之消失,那些残存下来的属于城市居民的东西不复存在,这时,已经如此广泛的主教的权势变得无与伦比。从此以后,城镇完全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4](P40)然而,主教的权势遭到素有自治精神的大学教师强烈抵制,在教师们看来,大学总监只有形式上对教师的任命权,而无教师资格的审核权。“1213年在巴黎,大学总监事实上失去了颁发执照即授课许可证的特权。这一权力转移到大学教师手中。”[8](P60)而到1219年,为了覆灭地方主教再次干预授课许可证发放的企图,争夺对大学的控制权,教皇贺诺利斯三世(Honorius Ⅲ)出面明确宣布,只要学生达到了标准,不管巴黎总监是否同意,大学均可以授予其授课许可证。显然,这个决定大学是乐于接受的,它确认了这一权利应当归属于教师。
1292年,教皇尼古拉斯四世(Nicholas Ⅳ)颁布训令规定,巴黎城内任何学生通过学习考试合格后,都可以获得在他们所学领域进行教学活动的许可证,并且在其他地方也享有教学权利而无须另外的考试和审查[15](P401-402),这就是所谓的“教授通行律”(jus ubique docendi)。由于中世纪大学是国际性的,师生的流动非常频繁,“教授通行律”实施的目的实质上在于确立巴黎大学在基督教世界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垄断国际性大学教师授课资格的授予。随后,一些老牌的强校如博洛尼亚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等,也纷纷获得了国际性大学教师授课资格授予的特权。
事实上,学位与教师资格授予权属于大学是一种早已有之的惯例,或者说是一种一直被承认的大学特权。关键是教皇对这一特权不受地方主教的约束,并不受地域的局限所进行的形式上的认可,这种认可实际上既否定了地方主教对大学学术事务的控制,又反映了教皇通过某种类似“资格认定”的方式与世俗力量在不同领域对大学控制权所开展的争夺。然而,教皇的行为并非是无私的或者是对学术事务自治理念的认同,其目的只是为了让大学臣服于罗马教廷,遵从教廷的政策,并把教廷的控制与观点强加给大学,因而其行为充其量只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和策略。身处这种拉拢和利诱,大学并非不知道,再加上一旁虎视眈眈的世俗势力,大学最终还是选择了投入教皇的怀抱。“面对时常是专制横暴的地方政权,大学肯定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成功地扩大了视野,增加了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影响,但是它也屈服在一再对它表示慷慨大度的那另一个权力之下。”[15](P430-432)更何况这种形式上的认可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为大学教师的流动创造了条件。
(四)作为一种权利主体的政治特权——争议权
相对于城市中原有成员而言,大学教师合法身份的获得相对较晚,并且要得到真正认同尚需一定的时间,因此极易受到侵犯。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世纪大学的历史就是大学与所处环境中各种力量进行博弈以争取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的斗争史——“在劳动关系里,的确在历史的特定阶段中……不以‘斗争’即不足以形容其真相”[16](P437),而斗争的前提就是要获得争议权。在现代劳动法理论中,争议权一般被称作劳动斗争权、集体行动权,中世纪大学行使争议权的集体斗争方式主要有两种:罢课和迁校,并且这两种方式经常结合在一起使用。
1209年在牛津,一名学生由于偶然的原因杀害了一个妇女,引发愤怒的市民在英王的同意下蛮横地绞死两名大学生,牛津师生集体罢课,并随后全体离开牛津,剑桥大学由此而得以诞生。1229年在巴黎,国王的警察因学生们和市民发生冲突而使用暴力,巴黎大学大部分人员参加罢课,并撤往奥尔良。有两年之久的时间,巴黎几乎没有再开任何课程,一时间巴黎的精神生活几乎陷入瘫痪。不仅如此,这次罢课和迁校所造成的混乱还使得主教被剥夺了对大学的管辖权。而在博洛尼亚大学,王权与教会竞相争夺对大学的控制权,争夺尤其集中体现在对大学教授的任命上,这种对大学学术事务直接的强制性干预同样引发了大学师生的强烈不满,师生们以罢课的方式加以对抗,继而迁至维琴察、阿罗佐、帕尔多瓦、西耶那等地重新发展。这些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231年,教皇格雷高里九世(Gregory Ⅸ)通过著名的被称为大学“大宪章”(Magna Charta)的教谕——《知识之父》(Parens Scientarium),规定当巴黎大学师生受到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非法逮捕等情况时,大学可以立即中止授课[17](P35),实际上是承认巴黎大学师生享有罢课权。在1355年的英格兰,国王明确支持大学并宣布,牛津地方长官和60名议员每年一度要到大学教堂去赎罪,而大学可以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市政委员会。[12](P43)
在勒戈夫(Jacques Le Goff)看来,大学之所以在这些斗争中取得胜利,首先靠的是大学的团结和坚定。但实际上,这种“团结和坚定”背后的动因是大学师生在遭受城市居民、当局和教会的排斥、挤压、强行干涉和利用后的不满与抗争。然而,对于这种旧秩序的反抗,个人的力量毕竟相当弱小,因此大学师生必须团结,团结基础上的集体反弹对于权利的维护和主张才更有实现的可能。并且只有当整个组织的权利得到了确认和扩展,组织中的个人才能获得更为自由的生存空间。“在中世纪……如果有人想行使自己的权利,那么他必须成为合作群体中的一员,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从共同体或合作群体中获得自己的权利;共同体的作用是维护这些权利免遭侵犯或抹杀。如果他脱离社会群体,那么他就不再是社会成员;他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不能得到任何人的保护,一点权利也没有。”[8](P226)由此,采取集体行动、在集体行动中保护个人的权利成为中世纪大学成员的必然选择。而中世纪大学没有自己的校舍,也无须费用很大的图书馆、实验室和其他设备,为迁移创造了极其方便的条件。
事实上,中世纪大学教师们不是革命性的,也并非仇恨旧制度,只是希望社会给予一个与他们生活方式相协调的位置,即便有时诉诸暴力,也只不过是迫使对方让步而已。但是,应当看到,争议权是大学教师保障自身职业安全“最后的武器”,没有罢课权与迁校权的协商和谈判无异于集体行乞,不会得到任何积极的回应。
三、走向衰微
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大学特权的性质和形式发生了微妙变化。例如,在1397年的博洛尼亚,法学家学会的新章程规定,每年博士学位只限于授予一个博洛尼亚市民时,博士们的儿子、兄弟和侄甥都不计在内。由此他们反而有更多的位置可以得到。在1409年的帕多瓦,博士的儿子必须被允许免费参加各项考试。[8](P110)显然,至少从文化与职业的角度说,传统的为整个大学社团成员所享有的种种特权正在向为社团中某个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方向演化,高级学位事实上的可继承性标示着大学教师越来越浓重的贵族化气息,中世纪大学的知识品性和文化水准逐渐走向衰落。
与这种衰落相伴随的是大学特权的衰微。随着15世纪以来大学浓厚国际化色彩的逐渐褪却③,世俗国家力量日渐强大并越来越重视对大学的控制,大学与王权、教会之间的关系天平发生了缓慢的倾斜,原先对保障职业安全有着重要作用的种种特权要么被王权或教会以各种借口加以废止,要么在实践中难以像中世纪那样得到彻底的落实,进而成为一纸空文。
例如,从16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社会进入了激烈的变革期,宗教改革中世俗王权战胜了宗教势力。罗马天主教权威在大学中失去统治地位,传统的修道院制度也被迫解体。为了加强对大学的影响,国王亨利八世(Henry Ⅷ)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将从修道院没收来的财产捐赠给牛津和剑桥大学,并于1540和1546年在两校设立了5个钦定教授席位。对大学的进一步控制发生在1549年爱德华六世(Edward Ⅵ)执政期间,信奉天主教的大学教师被驱逐出大学。而在玛丽女王统治时期的1555年,由于天主教的复辟,大学清查所有的教师,要求教师被允许从事教学之前,必须经过主教对其宗教信仰的考察和任职资格的批准,如果在宗教信仰上有问题,将会被立即开除,并用天主教徒加以取代。到了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新教又被恢复为国教。1559年皇室法令规定,除非经过品格和正统思想的考察并得到主教的许可证,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教学工作。这个规定成为1571年教会法的一部分。[12](P73-74)在激烈的政局动荡中,牛津和剑桥大学不得不屈从于强大的国家力量,在处理对外关系上逐渐丧失了一贯持有的独立自主性。种种特权在国家机器面前不堪一击,大学在某种程度上沦为统治者在文化和精神领域实施控制的工具。
巴黎大学的情况有些特殊。由于百年战争和教会的大分裂,巴黎大学外籍学生人数逐渐减少直至变成了一所法国人自己的大学。但直到15世纪中期之前,巴黎大学不仅是法兰西国王的“大公主”,也是教会的第一所学校,并在神学事务中扮演国际仲裁人的角色,享有非同寻常的崇高地位和学术声誉。查理六世(Charles Ⅵ)时期,在巴黎发生了卡博什党人的暴动,巴黎城一度成为英国国王的首都。然而,最令人遗憾的是,部分留在巴黎的大学教师最终屈服于英国人的意志并发动了臭名昭著的对奥尔良少女贞德的审判。巴黎被收复之后,被占领期间的“叛徒”行径使得巴黎大学失去了国家和社会的信任。1437年,查理七世(Charles Ⅶ)撤消了巴黎大学的税务特权,并迫使它为收复蒙特里奥而征收的“资助”提供资金。作为进一步的惩罚,1445年,巴黎大学的法律特权也被撤消,大学被置于议会的管辖之下。[8](P130-132)即便如此似乎仍难解心头之恨,1499年国王又颁布了限制大学特权使用范围和防止特权滥用的诏书,巴黎大学最终失去了罢课权。[15](P430-432)国家试图渗透对大学的控制固然使得大学特权逐渐削弱,但过分地介入宗教和世俗事务、并在其中摇摆不定乃是巴黎大学最终自食苦果的主要原因。
大学特权的衰微同时预示着大学教师独立的时代、独立而自由地献身于教学与研究的时代就此结束,“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学术自由”和“科学自由”曾经是学术界前进的旗帜,是团结学者并使他们成为一支统一的战斗队伍的神话。[1](P104)然而,神化破灭了,大学教师越来越深地卷入了世俗的纷争,忽略了知识的探求,进而在16至18世纪一度无所作为。也正因为如此,在当代人们越来越怀念中世纪大学教师的教学与研究自由。与此同时,失去特权保护后的大学教师职业安全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学术不断地遭遇政治与经济的诱惑与压力,但其中不少以放弃知识的中立和价值、转向对政治与经济的献媚和屈服为结局。由此,完善制度,保障职业安全,成为不得不重视的一个问题。
注释:
①有关中世纪博洛尼亚大学种种特权的详细考察请参阅Pearl Kibre.Scholarly Privileges in the Middle Ages[M].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4。
②“总监”是大主教的下属,受大主教委托管理大学事务,在13世纪一般称为“校董”(scholasticus)。
③主要原因是许多新大学的建立,如1383年重建的维也纳大学、1385年的海德堡大学、1388年的科隆大学、1389年的布达佩斯大学、1402年的维尔茨堡大学、1405年的都灵大学、1409年的莱比锡大学、1413年的圣安德鲁大学、1419年的罗斯托克大学、1425年的卢汶大学、1431年的普瓦捷大学、1432年的卡昂大学、1441年的波尔多大学、1444年的卡塔尼亚大学、1450年的巴塞罗那大学、1451年的格拉斯哥大学、1452年的瓦朗斯大学、1456年的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和弗莱堡大学、1459年的巴塞尔大学、1460年的南特大学、1464年的布尔日大学、1470年的萨拉戈萨大学、1476年的美茵茨大学和蒂宾根大学、1477年的乌普萨拉大学、1478年的哥本哈根大学、1483年的马略卡大学、1489年的西奎恩札大学、1494年的阿伯丁大学、1499年的阿尔卡拉大学、1500年的巴伦西亚大学等等,这些新大学大多是在封建王侯和教皇的参与下建立的具有公共性质的大学,比较注重从本民族招生,甚至从本地区招生。
标签:大学教师论文; 巴黎大学论文; 中世纪论文; 大学论文; 西欧中世纪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政治论文; 基督教论文; 辉煌集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