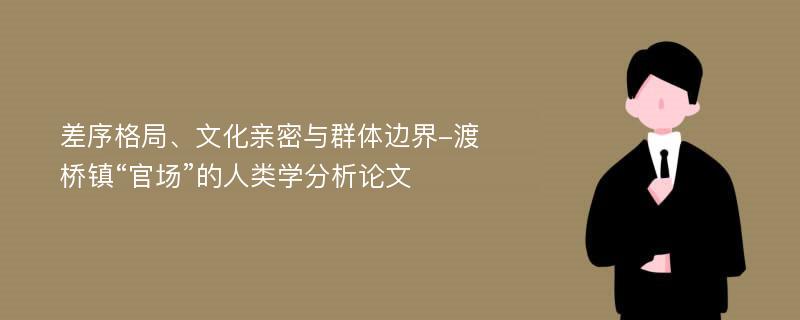
差序格局、文化亲密与群体边界 〔*〕
——渡桥镇“官场”的人类学分析
谭同学
(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 为争取资源、分摊风险和开展工作,乡村基层官员常以私人关系划分内外、亲疏有别的群体边界。其中,亲属关系存在但作用有限,战友、同学、老乡和拟制亲属关系更常用。称其为有限度的“派系政治”,比“家族政治”更切中实质。这些嵌入基层“官场”的私人关系,具有多重“差序格局”的社会文化特征。它们形成“文化亲密”,隐性地为内部人提供亲近感与信任,给外人划定界限。
〔关键词〕 基层官场;派系边界;差序格局;文化亲密
一、引 言
为理解乡村社会治理转型, 2007年11月至2016年8月,笔者一直断断续续在南岭中段南侧的渡桥镇做田野调查(2008年夏2个月、2009年夏3个月,其他为短访),其中,跟不少镇干部有深入交流。以镇干部为中心,上及县领导,下到村干部,构成了他们日常所说的乡村基层“官场”。镇干部们毫无疑问生活在,但又绝不仅仅生活在此“场”中,每个人还有自己的私人关系网络。同样毫无疑问,这两种公、私性质不同的关系网络,并非截然分开,而常有重叠之处。调查深入后,即可接触到一些“表里不一”的“秘密”。例如,无论以正式制度、组织框架而论,还是从“外人”角度看,基层“官场”都属于典型的科层制,有下属、分管领导及机构、制度。但是,这只是其“表”。其“里”,镇干部只有在关系紧密和私下场合,才会摊开来说事。从“里”看,农技(机)、林业、水利站站长,未必“是”分管“农林水”的副镇长的“人”,反倒可能与另外某位领导“站”一条“队”,属于一个“小圈子”。这种微妙的界限,绝不仅仅是私下场合说说而已,而会广泛体现在基层政治运行中。如遇此情况,下属对分管领导的决策、管理,可能阳奉阴违,影响基层行政效率乃至方向。
采用SPSS 17.0进行统计分析,对两次测试的成绩采用(x-±s)描述,比较进行配对t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意义。计算学生对课程的满意百分比。
整个样品呈灰色,主要由球状鲕粒和胶结物构成,鲕粒呈规则的球状,直径约40mm。核心基本位于球心位置。鲕粒和胶结物点稀盐酸起泡剧烈,可判断均主要由方解石构成。值得注意的是,鲕粒的表层,及部分层理间含有泥质,在标本上呈褐色。
当然,科层制本身可能就会隐含“失灵”的风险。正如韦伯早已指出,科层制中“为追求权力而追求权力”的成员,有可能会将行政手段置换为私自目标。〔1〕王亚南在论述传统中国官僚制时,更具体地指出,“成见一旦与利害关系结合起来”即会“锢蔽”官员,〔2〕形成官僚主义。华尔德的分析则表明,即使在“大集体”时期的工业企业中,以“依附”为特征的关系也依然存在。〔3〕当代科层制研究,制度学派关注制度不清晰而造成的组织混乱,〔4〕行动学派则强调组织成员自我建构权力的影响,〔5〕角度虽不同,但聚焦则均在科层组织本身。我们这里无意介入此类讨论,但想指出,除科层组织内部制度、行动者因素之外,其所处环境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文化因素,对塑造其运行逻辑,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以中国乡村基层行政为例,孙立平和郭于华曾敏锐地指出,乡村社会中的人情可能成为基层权力实践的资源。〔6〕以此为基础,吴毅进一步指出了基层政治实践中的“媒”与“擂”,〔7〕也即人情加权力、恩威并重的技术性策略。刘能和笔者曾关注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差序”特性,及其对基层科层制实践的影响。〔8〕而冯军旗则用一般人难得一见的某县委组织部“秘密”材料,试图说明县域政治中一些重要家族主导了基层“官场”的人事任命、官员升迁等事宜,并尖锐地称其为“家族政治”。〔9〕
本文尝试结合田野调查材料,对此现象再做些讨论,以期能更深入、准确地理解乡村基层政治,及其赖以存在的社会文化逻辑。
二、基层“官场”中的多重差序格局
在乡村基层调查较深入后,不少干部会在私下场合,谈及“圈子”“站队”“谁是谁的人”之类从正式制度视角看属于“政治不正确”的事情。笔者在渡桥镇触及此类话题,首先是从镇规划办干部程成信开始的。其基本履历为:1950年生于渡桥程村,1965年初中毕业,1970年参军后在部队入党,服役期满后于1974年回程村任大队民兵连长,1992年任村支书。
1996年,程成信在程村靠镇政府和集市的位置,张罗出售数千平米地基给农民建房,深得驻村镇干部、时任镇委副书记兼副镇长方立正的赏识。1998年,将程成信招录到镇规划办,即是方立正的主意,首先代表镇领导找他谈话的也是方立正。此后,在招干考试,尤其是在面试中,程成信能顺利过关,也与其帮助分不开。对此,程成信回忆道:“方书记前前后后帮我打了不少招呼,不然我这初中文化的底子,荒废了那么多年,肯定考不上。不过,也正因为这样,我进镇政府,大家就把我看成是他的人,是站他这一队的……基层都这样啦,桌子上谁和谁是上下级关系、谁管谁是一回事,桌子下谁是谁的人,又是另外一回事。你直接管的下属,站队的时候,不一定跟你站在一起。摆到台上,谁也不会说的,但大家都心知肚明。不过,面子上的功夫也很重要。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把站队的小圈子表现得太明显。相反,要让人觉得,四面八方的关系都还过得去。较劲只能暗中较的啦。”
正式上班后,作为土生土长的干部,程成信在镇政府新街道建设征地的工作中,表现出了优势。镇委书记、镇长好几次在党政联席会议上表扬过他。在私底下聊天时,方立正也夸奖他:“算是给我长了脸”。几乎同时,根据县国土局要求,渡桥镇开始编制第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于渡桥镇规划办与国土所合署办公,在他人看来,就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该项工作也成了程成信的中心工作之一。但在这项工作中,他几乎成了“文盲”,而国土所的陈金华是中专毕业生,比他“专业”得多。
当时,陈金华和一个排位比较靠后的副镇长肖某走得比较近,算是“站”一条“队”。但是,“这种小圈子还几乎冇向心力”,因为肖某“在镇里完全说不上话”。除此之外,陈金华在县里并没有可靠的关系。程成信则算是进了方立正的“小圈子”,而方立正在镇里是有实权的“三把手”。因此,陈金华虽对程成信的工作水平不屑一顾,却又没办法。对此,程成信说:“当时,我觉得他有点书生意气,懒得去跟他计较这些。他能干,那就多干点啦,我乐得清闲。”
1999年下半年,渡桥镇党政班子换届。在通常情况下,方立正将顺理成章地接替镇长职位。但出人意料,镇委书记、镇长均被调走后,方立正也被调往邻镇任镇长。新的镇委书记、镇长全部从外地调入,其中镇长与陈金华是中专校友。镇规划办、国土所的局面马上变得对程成信不利。对此,他回忆道:“新镇长是他(陈金华)的同学。估计原来关系其实也一般,没见有多少来往,不是学一个专业的。但现在在一个地方工作,又都是外地人,可能觉得还是同学比较值得信任吧。第一次见面喝酒,镇长就主动跟他喝酒。他也终于‘醒目’了,马上就打得火热,站到他那一队去了。”
在工作中,新镇长经常“鼓励”程成信加强“学习”,暗示其文化水平不够。不过,程成信说,新镇长做得也不算过分,毕竟涉及到处理一些本地的事务,他还是比较得力的。程成信自己则开始试图努力地跟新镇委书记拉近关系,但是他发现:“要真正取得一个陌生领导的信任,不是那么容易的,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原来(和)方书记打交道时间长,可以掏心窝子。新的(书记)不行,他是个谨慎的人。不是说你简简单单拿钱开道,多送点礼就行的。没有信任,礼送得太多了,反而不敢收啦,谁知道你有没有做手脚。”
农村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事关下一代的成长和发展,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教育工作,必须从思想上提高认识,从制度上加强管理,从措施上进行深化,切实形成学生心理健康成长的机制和环境,把农村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做实做好。
罗衫咬起嘴唇,久久没有说话。天已很晚,城市里弥漫起浅紫色的薄雾。不断有汽车从薄雾里穿过,灯光似乎透过厚厚的毛玻璃,世间一切,变得模糊不清。
很不凑巧,程成信在新局面下还没有稳固地“站”好“队”,人生的关键时刻却到了。2000年初,渡桥镇规划办主任兼国土所所长许某办理提前内退手续,职位出现空缺。这对程成信、陈金华都很重要,它不仅意味着是一个正股级的干部岗位,而且是公务员编制。结果,镇领导把这个机会给了陈金华。据程成信说,在当时的渡桥镇,公务员编制和事业编制待遇已略有区别,此后差别更大。更何况,此时国土所还变成上级垂直管理的机构。陈金华从此主要以国土所所长身份活动,其工资待遇与县国土局其他正股级干部一样,约为程成信的2倍。
但是,程成信后来主动退缩了。原因是他了解到,肖某在更高一个层次“站队”时,和县政府办主任是一个“圈子”,他们原来是战友。而渡桥镇镇长和县委组织部长有亲戚关系,他们是一个“圈子”。程成信“担心水太深”,就没深交,免得肖某和镇长两个“圈子”不和,“神仙打架、小鬼遭殃”。此外,程成信说自己一直摸不透新镇委书记的态度,所以更加不敢冒冒失失行动。他对此感叹道:“人家都说,搞政治,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话当然是对的,但也不全对。就拿我们基层来说,一个小小的镇,甚至一个县,都是一个小圈子,大家都熟悉。根据利益变化重新选择站队当然很正常,但你如果经常换来换去,站不同的队,名声就会坏掉。人家觉得没法信任你。谁知道你哪天会不会调转枪口,变成一个‘反动派’。所以,真正站队的时候,其实也没多少选择。你如果跳来跳去,可能哪个队都站不进去。”
良渚的鸟崇拜集中在鸟卵崇拜上。这主要体现在良渚玉器的兽面纹中两只眼和鸟纹中的鸟身,均很像鸟卵。鸟是卵生动物,一鸟能产很多卵,相比于哺乳类动物,鸟的繁殖能力强得多。且鸟有翅膀,能飞,远较哺乳动物神秘。也许,在良渚人看来,鸟就是神,或是神灵的使者。这样说来,良渚人崇拜鸟,包含有生殖崇拜和灵物崇拜两个方面的内涵。
程成信也曾与副镇长肖某“走得比较近”,自新镇长到位后,陈金华即与肖某“走得比较远”了,于是肖某有意主动向程成信示好。对此,程成信说:“当时换届,他(肖某)也算是升了一级,还是副镇长,但原来排名比较靠后,这个时候排在副书记兼人大主席后面,也算是‘四把手’或者‘五把手’了。(他)有事没事叫我去他办公室喝茶,有时候晚上叫我去陪他下象棋,其实我下象棋技术很差的。有时候出去办事,也喜欢叫上我。开会时,找机会表扬我。总之,有点叫我站他这一队的意思。”
毋庸置疑,正是更为深层的制度原因主导了儒家对女性的角色定位,裹挟于其中的女性是男性中心的宗法制度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受害者与牺牲品,因而对儒家女性观的反思离不开对基于儒家伦理的制度设定的批判。时至今日,封建君主制与家族制度早已崩解,“三纲”论与“三从”“四德”说备受质疑,传统的家庭伦理也受到冲击而处于重构之中。在此形势下,儒学要在当代社会复兴就必须在自我批判中正视并回应女性主义的挑战,实现现代转化。
程成信还分析过办公室其他人“站队”的情况。1998年他进镇政府工作时,办公室名义上共有5个工作人员,国土所、规划办各2人,另有许某兼任主任和所长。国土所除陈金华外,另有25岁的小伙子李哲文。规划办除程成信外,还有一位中年妇女曾某。
李哲文从某名牌大学毕业后即在国土所工作,事业编制,此时已被借调到镇党政办公室写材料达3年之久。在程成信看来,李哲文的文凭、能力都不应该那么长时间被埋没,只能天天写材料,地位几乎就跟打印室的合同工差不多。究其缘由,就是李哲文比较清高。据说,他到渡桥镇后,不仅不懂得“站队”,还很快就得罪了书记、镇长及方立正,也即渡桥镇几个主要“圈子”都被他得罪了。程成信对此评价道:“这样不行的。开始可能是刚毕业,书呆子气,以为别人只是中专生或大专生,自己是名牌大学正规本科生。结果,还没适应社会,就被人摁倒在地了。但后来,交往多了,我觉得是性格问题,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难得成熟起来,或者说思想上成熟了,但因为性格原因,在行动上做不到。领导换了几茬,都没解决站队的问题。办公室所有的同事,别人都升了,就他一直是个写材料的‘专业户’。”2005年,方立正调回渡桥镇任书记,镇长也由外地调入。据程成信说,方立正与此镇长勉强可算“站”一条“队”,他们都是县城某几个石材老板的好朋友。虽然他们在政治上还有别的“圈子”,但并不冲突。镇长与李哲文是大学校友。在镇长调和下,李哲文担任了镇党政办公室主任,级别上算正股级,但主要工作仍是写材料(2009年,李哲文在另一个担任某领导秘书的同学的协助下,终于调往县政府某局工作)。
规划办的曾某,因年龄已达40多岁,不再思进取,其丈夫为市农业局某科长。曾某在渡桥镇基本上不“站”任何一条“队”,处理人际关系时“和稀泥”,跟谁都不冲突,也不深交。曾某在工作上常应付了事,需实干的则全部丢给程成信。但因其家庭背景虽不硬也不软,加之在渡桥镇一副“老好人”形象,包括程成信在内的所有同事,一般也不去得罪她。至于办公室的“头头”许某,其丈夫为某镇人大主席。在渡桥镇,许某也不“站”任何一条“队”。许某在工作上表现平平,但书记、镇长均对她比较客气。程成信说:“大家心知肚明,她就等着内退,没人去拉她站队,也没谁会去故意得罪她。” 程成信还提到,人们常说的通过贿赂领导,跟领导“站”成一条“队”,得到提拔的现象,也确实有。但如果不是最后被查处了的话,一般都没有直接证据(2012年,广东省发起“三打两建”活动,渡桥镇有1人因行贿被查处)。
在乡村基层政治中,“官场”之“场”,是一个高度实践性的概念。它由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看不见、摸不着,但“内部人”在实践中却清晰地知晓其边界。在这一特性上,它与布迪厄说的“场域”〔12〕极为相似。此场域有其独特的“惯习”〔13〕,不仅有当代科层制研究者所分析的基于制度算计、建构权力的共性,也有与多重“差序格局”社会文化密切相连的个性。诚然,只要科层制由具体的行动者,也即活生生的人来执行,从绝对意义上说,就不可能避免其将“私”的关系嵌入“公”。但“私”的关系不是抽象的,相反,总是或多或少带有具体的社会文化特性。从渡桥镇田野材料看,基层官员嵌入“官场”之“私”的关系,总体上带有鲜明的“差序”特征。若更进一步细究,则因“人伦”或工具性色彩厚薄不同,而混合成多重“差序格局”。
2005年,方立正回渡桥镇任书记,对程成信而言自然也很重要。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他感叹“最终还算是站队站对了”。确实,此后程成信在办公室的日子好过多了。方立正曾含蓄地跟陈金华说过几次,对程成信这样的老干部、本地干部,要多爱护,很多工作,这样的干部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陈金华也早已不再将程成信视作竞争对手。于是,在选择驻村时,两人同在一个小组,负责程村。不过,关于程成信想转成公务员的想法,方立正明确予以了拒绝,理由是“公务员逢进必考,没办法操作”。
三、派系政治中的私人网络及其限度
从程成信及其周围镇干部“站队”的情况看,很显然,私人关系网络不仅嵌入在基层政治当中,而且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私人关系中的确有亲属,但绝大部分则并不是。从“人伦”色彩厚薄看,有部分关系(尤其是亲属关系)可谓费孝通意义上的“差序格局”,也即根据“人伦”关系设定他人与自己的远近,“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0〕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关系与利益算计有关,可谓“工具性差序格局”,也即这种“社会联系是自我中心式的,即围绕着个人而建立起来……人们建立关系时考虑的主要是实利可图,所以亲属和非亲属都可以被纳入格局之中”。〔11〕这两种性质很不相同的“差序格局”,并不截然分开。除个别直系亲属之外,同学、战友、老乡等关系既有“人伦”色彩,同时也有利益上相互利用的性质。镇干部基于“站队”需要,将私人关系网络嵌入到正式科层制中。而若细究,则私人关系网络又具有多重“差序”的性质。
可是,镇干部为什么必须“站队”呢?程成信表示,原因是“别人都站队,你不站队,孤掌难鸣,遭人欺”。2010年8月,已与笔者较熟悉且即将调离渡桥镇的副镇长文质彬,在一起吃夜宵的“私下”场合,曾给出更有“理论水平”的答案:“如果不想升迁,不站队当然也可以。如果想升迁,站队、进小圈子,提拔的机会就多点。否则,你就算干得好,上面也未必知道啦。或者,(上面)就算知道,在干部任命、推荐进修、组织外出考察等等有好处的事情时,人家对你的成绩也可能会装作不知道。再说了,工作干得好的人,毕竟不止你一个啦。当然了,领导也有主动拉下属站队的需要,要不然就是一厢情愿,站队也就站不成。领导之所以有需要,是因为你(领导)在工作中不可能亲自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但是,单纯靠制度要求下属去做,人家(下属)未必真心实意、百分之百尽力地给你去做。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私人圈子里的人才会尽力啦。再一个,尤其是在基层,现在好多工作都是‘打擦边球’,是‘变通’的,甚至是违规操作的。如果不是‘自己人’,你敢信任他(她),交给他(她)去办吗?这还不用说那些干违法勾当的人,他们就更加需要私家班底。”
注释:
1998年,渡桥镇政府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除了镇干部全员出动加班加点催收税费之外,还聘请了若干“协税员”。这些“协税员”,大部分都是人们常说的“烂仔”(小流氓)。“多管齐下”之后,渡桥镇税收进度略有加快。但按照税收“双过半”的要求(6月底前需完成当年税收的一半),6月中旬,渡桥镇仍有近100万元的缺口。于是,镇委班子会议决定,全体干部“主动出击”,到县城和城郊等税源充足一些的地方去“拉税”。“拉税”的手法主要以减免税收的方式,诱使一些企业将地税交至渡桥镇地税所。原本每个镇干部都有任务,但后来实在完不成的,镇领导也没办法。最后,镇委书记和镇长不得不亲自出马,找到城郊镇的领导“买税”。城郊镇早已远远完成上级分配的税收任务,故有余力划拨了60万元税收额度,算在渡桥镇名下。作为回报,渡桥镇支付城郊镇5万元征税“工作经费”。据说,因为两个镇委书记关系“铁”如“兄弟”,这笔交易才能达成且价格这么便宜。
针对近期我国西南旱情进一步发展、抗旱减灾形势严峻的情况,经中宣部同意,水利部组织,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科技日报、农民日报、中国日报、中国经济导报、第一财经日报、中国水利报等媒体记者3月26—29日深入云南、贵州等省区开展“西南抗旱行”集中采访报道活动。
从以上材料不难看出,从基层“官场”“内部”视角视之,编织“小圈子”,直接原因与政治资源的稀缺性有关。若无升迁之欲望,一个平凡的基层官员也可不“站队”。而一旦不“站队”、不进“小圈子”,即使有工作能力、有政绩,并且上级领导从私人渠道也完全能得知这些信息,但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理性化的科层制也可能让他们精心“过滤”掉这些信息,对之“视”而“不见”。何况,那些选择了“站队”和进“小圈子”的人,就未必没有能力和政绩。同样从“内部”视角看,那些未能纳入某个派系的基层官员也未必就是道德上“善”。相反,他们更可能是性格或能力对“官场”而言有缺陷,如过分“书生气”、不够“醒目”,或者无能。
不管是因为基层官员为争取稀缺政治资源的需要,还是因为领导为充分调动下属工作潜力去实现“公”的治理目标而发展“私”,派系都是一种便捷的、人格化且充满弹性的选择,与理性科层制不一致。因此,派系只能私下“做”,而不能公开“说”。既然派系不能在正式制度下公开运行,形成和维系派系的便不可能是理性科层制本身,而是私人关系网络。它们可以是亲属,更常见的则是战友、同学、老乡、校友或朋友。由于理性科层制哪怕是形式上为“公”,首先限制的便是亲属关系,所以在基层政治实践中,亲属关系客观上虽然能起些作用,却很难膨胀到几个重要家族主导县域政治的地步。对此,正如文质彬在笔者调查时所言,“县里的主要领导一般都是外地来的,不太可能允许这种情况存在。否则,他们的政令如何出得了办公室?再说,地级市的主要领导和组织部不可能对下面县里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也不可能坐视不管。如果真有这种情况,只能说县委、县政府甚至市委、市政府出大问题了。”
更有悖论意味的是,从“内部”视角看,官员们之所以将“私”嵌入“公”中,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为了把“公”搞好。理性科层制,不仅可能被上级用来对下属的能力和政绩“视”而“不见”,也可能被下属用来对付上级的治理之策。上级为了把工作做好,仅靠正式命令,可能还不够,还需要有“私”的交情,才能让下属“真心实意、百分之百尽力”去完成任务。也即,上级领导为了“公”而发展“私”。正如渡桥镇官员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所遇到的,相当一部分工作属于原本没有条件,而强行要求完成的。没有吸引投资的条件,而“不得不”以土地、环境容量为代价,强求“发展”。没有足够的税源,而不得不通过“拉税”“买税”“请烂仔”“协税”,完成高额缴税指标。这些“难以承受之重”的任务,都只能通过“打擦边球”或者“变通”,甚至违规操作才能“搞定”。既然上级需要下属完成正式制度所不能完成的治理任务,除了正式制度的上下级关系以及激励之外,“私”的关系网络成为一种选择,也就在“情理”之中。这种“私家班底”一旦变得相对固定,即成了不同的“派系”。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派系虽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基层官员积累政绩,争取政治机会,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助其克服不确定性。由此,不少渡桥镇干部相信“官运”之说。如程成信曾坦言:“之所以慢慢相信了这些(‘官运’)说法,一方面是因为好多次被提拔的机会,都眼睁睁看着擦肩而过,我觉得,好像再怎么努力也很难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于是,(我)就开始觉得有些事情,不信可能也不行。另一方面,我发现,在渡桥(镇)干部中相信‘官运’的人不在少数,可以说比普通老百姓还普遍,比普通老百姓还诚心诚意。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是不明说。”文质彬还举了一个例子为证:在该县一个重要的镇,辖区内某企业请人清理沼气池,因操作不当导致4人甲烷中毒身亡,其镇长按惯例本将很有可能升至副县长,却因此“重大安全事故”被免职,数月后调任文化局副局长。
四、结 论
第三,针对第三个问题,上述统计结果表明,语速修改、受试的听力理解水平和听力测试题型之间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对于较低中等听力水平班级,语速降低能够明显促进其在短对话中的听力理解;而对于较高中等听力水平班级来说,较慢语速会显著提高其在长对话和短文中听力理解的成绩。
在基层“官场”的多重“差序格局”中,亲属无疑是最“自然”的私人关系网络。因此,家族关系也便在基层政治中容易与科层制相伴生。但是,自然的、真实的亲属关系毕竟数量有限,更多的是拟制的“亲属”关系(如关系近的基层官员以“兄弟”相待)。而且,真正能达到真实亲属一般信任程度的拟制亲属关系,也同样不多。基层官员想在短期内取得一位陌生领导充分信任,十分困难。反过来,在明确知道有领导想拉自己“站队”时,信任同样也是个问题。信任不够,则可能因担心“水太深”而选择退缩。由此,在基层“官场”中,家族关系渗入政治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它只是建立和维系派系的多种关系之一。较之于拟制亲属关系,有信任基础的战友、同学关系,甚至围绕某个大老板而形成的共同利益关系,更常被用来建立和维系派系。视其为“家族政治”,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很显然,将之称作“派系政治”,才更切合其实质。
除了亲属,对基层官员而言,藉其他关系网络而成派系,蕴含了双重悖论。一方面,派系既是“不得不”选择,又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虽是“主动”选择,选择余地却又有限。一旦做出选择,就有某种“路径依赖”〔14〕,其后虽然还可根据利益需要而调整,但频繁更换派系,将会失去所有派系的信任。而且,派系毕竟是隐性的,基层官员还得根据正式制度完成基本的乡村治理工作。再者,在通常情况下,还得根据个人交往道德,尽可能地维持与所有人哪怕是表面上的良好关系。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基层派系政治也有其限度。更何况,派系虽可帮助基层官员增强竞争力,降低风险,但在“压力型体制”〔15〕下,基层责任大而权力小,派系并不能让他们从根本上摆脱,哪怕是“背黑锅”的“责任”风险。以至于,“官运”之说在乡村基层“官场”竟然颇有市场。
说到底,在乡村基层政治中,派系的形成,乃是官员尝试用“差序”的私人关系网络,克服科层制下工作开展、机会竞争、责任分摊等方面的不确定性风险。从“内部”视角看,它为“内部人”提供一种彼此心知肚明、无需亦不能言说的亲近感和稳定的合作预期。但从“外部”视角看,派系隐性存在,一旦被公开在“外人”面前,就会造成“尴尬”,甚至可能招致正式制度的惩罚。这种由社会行动者基于特定文化形成的内外亲疏有别的认知,赫兹菲尔德称之为“文化亲密”〔16〕。不管是基于真实还是拟制的亲属关系,抑或是战友、同学、老乡等关系,总之派系为“内部人”提供了一种或多或少有些“温情脉脉”的亲近、亲密感,以应对“冷冰冰”的科层制给个体官员带来的压力。在乡村基层“官场”中,实践性地构成“派系政治”之“文化亲密”的,是不同程度混合了“人伦”与工具性色彩、多重“差序”的文化和社会关系网络。
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派系政治”与“家族政治”虽只有两字之差,但对乡村基层政治运行逻辑的判断却有本质区别。若要作对策思考,其视角与举措无疑也应很不相同。“家族政治”的判断,认为基层“官场”中的“小圈子”主要是少数家族垄断政治资源和机会。循此逻辑,从治理角度说,应对之策当是在干部选拔中防范、打击基层中的少数精英家族。“派系政治”的判断根据则在于,基层“官场”中的“小圈子”不仅(甚至主要不是)源自亲属关系,更常见的情况是依赖战友、同学、老乡甚至纯粹利益同盟等非亲属关系,而形成具有“文化亲密”感的隐性群体边界。其目的也不仅是为“私”争取更多的政治资源和机会,也常用于应付压力型体制下开展“公”的工作所需。与此相对应,治理之策理应是优化基层政绩考核、干部选拔机制,并在基层日常政治运行中加强政务公开、民主决策与管理,防范、打击基于亲属或非亲属、具有利益输送性质的任何“团团伙伙”行为。
下属想与领导拉近关系,以获得更多政治资源和机会,当属不难理解。但如果上级领导没有必要与下属发展“私”的关系,则这种“小圈子”根本不可能形成。文质彬解释的精当之处,正是对后者的概括。其所分析的情形,在渡桥镇日常治理中,可谓比比皆是。例如,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渡桥镇水利站、财政所、计划生育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增加了约2倍。这部分人员的工资绝大部分靠镇政府自筹,政府急剧增加的开支与极其有限的收入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同时,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口号下,几乎所有村委会均出现了亏空,渡桥镇政府也债台高筑。而雪上加霜的是,1995年起,渡桥镇开始面临税费任务倒算的局面。每年能收缴多少税费并非根据实际情况而定,而是由县政府提出数字,渡桥镇必须将之作为“一票否决”的任务完成。上级提出的税费指标年年攀高,而渡桥镇的经济并没有出现同步增长,以至于完成税收任务越来越吃力。
通过长期与企业合作沟通,结合专业教学经验以及与学生沟通。想要真正形成长效的校企合作,将工学结合的培养方式落到实处,就要解决企业、学生、教师参与积极性的问题。而从上面的经验分析来看,最终需要的是找到各方的共同利益点。通过不断调研与走访本专业最终梳理出各方需求对形成多方共赢的工学结合培养模式进行实践,目前已取得一些效果。
〔1〕〔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56页。
1998年下半年,渡桥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政府征地并搞好“三通一平”,然后以比城郊镇低得多的地租,甚至是零地租,引进20余家石材企业。为此,刚到镇规划办工作的程成信,被镇领导找去谈话好几次,被要求“千方百计”地发挥好本地干部的优势,协助镇领导做好征地工作。他对此曾回忆道:“刚工作那一年压力太大了,先是要‘拉税’。下半年匆匆忙忙要征地,(老百姓)要价高,(镇)领导又不愿多给钱,就靠我们去跟别人(老百姓)攀交情、讲道理,甚至连哄带骗加威胁,得罪了不少人。除此之外,这些地基本上办不了用地手续,严格说都是违法的,我们搞业务的,也有点担心国土部门查啦。”
〔2〕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6页。
〔3〕〔美〕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65-268页。
〔4〕March J.G,“Bounded Rationality, Ambiguity and the Engineering of Choice”,in March J.G.ed., Decisions and Organizations ,Cambridge,MA;Oxford,UK:Basil Blackwell,1989,pp.266-294;Cohen,Md.,etc.,“A Garbage Can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Choic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72(17);Meyer John W.,etc.,“Institutional and Technical Sources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in Meyer John W.etc.ed., Organizational Enviroments ,Beverly Hills:Sage,1983,pp.45-67.
第四,树立矿业新型发展观,培育绿色发展意识。重塑矿山企业文化,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和行业道德行为,使企业既重视矿产资源等有形资产,又重视发展理念、企业文化等无形资产,彻底改变其“重资源开发,轻环境保护”的传统观念[26]。
〔5〕〔美〕彼得·布劳、马歇尔·梅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马戎、时宪明、邱泽奇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77页;〔法〕米歇尔·克罗齐耶、埃哈尔·费埃德伯格:《行动者与系统——集体行动的政治学》,张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0-31页;〔法〕埃哈尔·费埃德伯格:《权力与规则——组织行动的动力》,张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9-116页。
〔6〕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镇收粮的个案研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1),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第21-46页。
用锹捯7~8次,在捯拌中,依据混拌土的干湿度,适当用喷壶,喷5.5~6.5升水,搅拌均匀,达到手捏成团不滴水,落地混拌土自然散开为宜。
〔7〕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614-615页。
作为一种有机质和营养元素较为丰富的材料,农作物秸秆一直是土壤中养分和有机质的来源之一。在试验过程中,秸秆覆盖还田一年之后,土壤中的有机质、全氮以及全磷等营养成分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增加。在此基础上,秸秆覆盖还可以更好的提升土壤中酶的活性,使土壤中有理的微生物数量增加,为作物提供更加优质的生长条件。
〔8〕刘能:《等级制和社会网络视野下的乡镇行政:北镇的个案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89-229页;Tan Tongxue,“The ironies of ‘political agriculture’:Bureaucratic rationality and moral networks in rural China”,in Hans Steinmüller and Susanne Brandtstädter ed., Irony, Cynicism, and the Chinese Stat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6,pp.84-100。
〔9〕冯军旗:《中县干部》,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10〕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五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34-336页。
〔11〕李沛良:《论中国式社会学研究的关联概念与命题》,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编:《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1页。
〔12〕〔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邓正来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2页。
〔13〕〔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80页。
〔14〕〔美〕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钟正生、邢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
〔15〕荣敬本、崔之元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16〕Herzfeld Michael, Cultural Intimacy ,New York:Routledge,2005,p.3.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09.008
作者简介: 谭同学,社会学博士,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研究得到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资金支持。
〔责任编辑:刘姝媛〕
标签:基层官场论文; 派系边界论文; 差序格局论文; 文化亲密论文;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