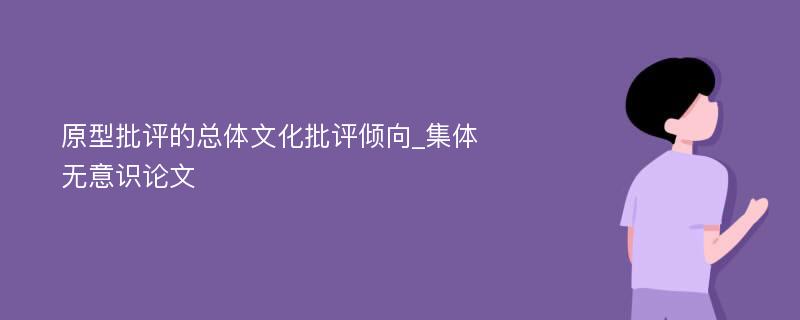
原型批评的整体性文化批评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原型论文,倾向论文,性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0)05-0067-08
原型批评是本世纪最为重要的西方文学批评流派之一。不少批评家认为,原型批评曾一度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和精神分析批评在西方文论界起过“三足鼎立”的作用。然而批评界过去对原型批评的研究有简单化的倾向:批评家们过于注重弗雷泽的人类学理论(主要是其神话理论)和荣格的精神分析学(主要是其“集体无意识”学说)对原型批评的影响,忽视了对其他方面影响的研究,因此批评界或称它为神话—原型批评,或将它划为精神分析批评领域。其实,弗莱的原型批评是诸多复杂因素的产物。除了它的心理学基础和神话因素之外,我们认为,在文学观念上,弗莱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社会历史观的影响,其原型批评呈现出一种整体性文化批评的倾向;在方法论上,原型批评还吸取了奥斯瓦德·斯本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的“历史有机(循环)发展论”和早期结构主义的一些东西;此外,原型批评虽是以反对新批评的面目出现的,但在某些方面仍带有“文学自足论”的痕迹。
原型批评的理论基础
一般认为,诺思罗普·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有两条根,一条是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的人类学,另一条是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精神分析学。笔者认为,弗莱的原型批评主要是建立在荣格的精神分析学,尤其是其“集体无意识”学说和原型理论之上的,而弗雷泽的人类学理论(主要是其神话理论)只是弗莱原型批评理论的切入点或外壳,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只是表层的、导入性的,就像弗洛伊德通过梦发现人的无意识领域的内容,进而建立起他的精神分析学说一样,弗莱通过神话发现了文学中的“无意识的结构”——“原型”——而建立起他的原型批评。笔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般人只看到了弗雷泽和荣格的理论对弗莱的影响,而没有注意到弗莱在建立其原型批评时对他们的理论采取了不同的借鉴“角度”,用罗伯特·德纳姆的话说,即“离心的角度”(centrifugal perspective)和“向心的角度”(centripetalperspective)。(注:参见罗伯特·D·德纳姆编:《诺思洛普·弗莱论文化与文学》(Northrop Frye on Culture and Literature,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第25页。)所谓“离心的角度”,笔者认为弗莱只是借用他人的一些概念或模式而实质指向不同;而所谓“向心的角度”,是指弗莱不仅借用他人的概念或模式,而且在内容实质上,指向也是基本相同的。笔者认为:对弗雷泽,弗莱采取了“离心的角度”,而对荣格,弗莱则采取了“向心的角度”。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詹姆斯·弗雷泽的有关理论。詹姆斯·弗雷泽的人类学理论的影响主要来自他的12卷巨著《金枝》。在此书中,弗雷泽考察了原始祭祀仪式,发现许多原始仪式虽然存在于一些截然不同的、完全分隔开的文化之中,但却显示出一些相似的行为模式和信仰。弗雷泽引用了大量资料来解释、说明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情况。弗雷泽在此书中公开宣称,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探究并解释存在于“金枝国王”这一奇异习俗之后的动机和目的。所谓“金枝国王”习俗,根据弗雷泽的考察,是指居住在内米湖畔的古意大利人如何进行王位交接的奇异习俗。根据这个习俗,王位继承人要从一棵圣树上折断一根树枝,然后在一对一的搏斗中杀死老国王,然后才能继承王位。
弗雷泽认为这个习俗是从远古时代传下来的。根据他的考察,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原始部落里,人们对他们的部落首领抱有一种神奇的看法:认为只要他强壮而有生殖力,他们的部落就能团结在一起,他们的食物供给就有保障。如果他年老多病而身体衰弱了,那么庄稼也会如此。因此,当他们的部落首领精力衰竭后就应该被杀死,可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把他的力量继承下来。弗雷泽认为,从这一习俗中发展出了许许多多的宗教,而所有这些宗教的中心人物都是一位以青年男子形象出现的神。他代表各个季节中的繁衍,尤其是农作物的丰产丰收。因此人们把他的躯体和血液与农作物的两种主要产品——面包和酒——等同起来。这种宗教的核心便是祭奠这位神的死亡与再生。这位神在希腊被称为“狄俄尼索斯”,在叙利亚被称为“阿多尼斯”,在埃及被称为“俄西里斯”,在小亚细亚被称为“阿提斯”。这种吃神的“肉”,喝神的“血”的仪式也成了许多宗教的“相同的模式”。
弗雷泽还认为许多古代神话和祭祀仪式都与自然界的季节循环变化有关。自然界的万物春华秋实,一岁一枯荣,生生死死,年夏一年,使远古人类联想到人的生死繁衍,便产生了人死而复生的想法,创造了许多死而复生的神的神话传说。我们东方也有人死了再转世投胎的说法。正如张隆溪先生所说:“这种关于神死而复活的神话和仪式,实际上就是自然节律和植物更替变化的模仿。”(注: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三联书店,1986),第57页。)
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发现了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中的神话和祭祀仪式的相似性。也正是弗雷泽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和发现才对于弗莱具有启发意义。弗莱曾研究过弗雷泽,认为弗雷泽是一位知识极其渊博的学者并受到过多方面的影响;如《圣经》研究专家罗伯逊·史密斯(Robertson Smith)的理论,即在原始社会中,祭祀仪式先于神话而存在:人们先把他们的信仰表现出来,然后再为它们想出理由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弗雷泽。弗莱认为弗雷泽虽是一位社会人学教授,但他从未做过任何真正的实地考察工作,他的研究主要是在图书馆和书斋里进行的。因此,对弗莱来说,弗雷泽的《金枝》与其说是一部人类学著作,不如说是一部古典学术研究著作,或者说是一部可供文学批评家参考的知识性著作。这种对于弗雷泽的著作和理论所采取的“离心的角度”的做法,正如弗莱本人在《无意识的象征》一文中所表述的那样:
我没有能力把《金枝》作为人类学的著作来讨论,因为我是一个文学批评家;关于人类学,我并不比其他任何人知道得多。……我倒要说《金枝》看起来与其说是一本为人类学者写的书,倒不如说是为文学批评家写的书更合适。(注:德纳姆编:《诺思洛普·弗莱论文化与文学》,第88页。)
罗伯特·德纳姆也说:“弗莱看弗雷泽的《金枝》,就好像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或一部多卷本小说。”(注:德纳姆编:《诺思洛普·弗莱论文化与文学》,第25页。)
弗莱还认为《金枝》的主题是以祭祀仪式表现出的社会的无意识象征,从这一点上说,它与心理学是相关的。他指出:
《金枝》并不真的是关于人们在原始野蛮时代的所作所为,而是关于人类的想象在试图表现它对于最大的秘密,即生、死和来世的秘密时的活动。换句话说,它是一部研究社会的无意识象征的书。它与弗洛伊德、荣格和其他心理学家关于个人的无意识象征(如做梦之类)的心理学著作相一致并相辅相成。令人惊奇的是,弗雷泽的模式与心理学模式是如此吻合。(注:德纳姆编:《诺思洛普·弗莱论文化与文学》,第89-90页。同时参见该书第100页。)
弗莱借用米尔西·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对“金枝国王”习俗的分析将弗雷泽在《金枝》中所阐述的观点与荣格的心理学理论进行了比较:
神圣的国王被神奇地认为是大自然力量的化身,因此,他的死和复活象征着从黑暗、寒冷、不结果实到新生的自然界的循环。国王复活的方式有两种:在部落里,制造一个躯体,把他的神性传给一位继承人,因此他的继承人就不会被认为是一个不同的人,而是同一种力量以新生的形态的继续。荣格的探索与此相似:自我下降到无意识的底层,与它在那儿发现的黑暗和混乱的力量搏斗,最后作为“个体”,以获得新生的原来的生命归来。(注:德纳姆编:《诺思洛普·弗莱论文化与文学》,第101页。)
弗莱认为,死亡和再生的主题是弗雷泽和荣格的共同的主题,只是出发点不同而已。弗雷泽从社会祭祀仪式方面去研究,而荣格则从心理学的“变形象征”方面去研究。
总之,弗莱没有把弗雷泽的著作和理论当作是纯人类学的,而只是从一个“离心的角度”,即文学的角度去研究后者的著作和理论,虽受到某些启发,但并没有形成理论;只是当他接触到了现代心理学,尤其是卡尔·荣格的心理学理论之后才真正形成他的原型批评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家莱维-施特劳斯在探寻各种制度、各种文化、各种习俗下意识中的结构时指出:
假如……心的无意识的活动是在于把形式加在内容之上,如果这些形式在所有的心中——不论古今,不论原始人或文化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必须把握住隐藏在各种制度、各种习俗之下的无意识的结构方式,再找出一个可通用于各种制度、各种习俗的诠释的原理。(注:克劳德·莱维-施特劳斯:《结构人类学》(Structural Anthroplology,trans.Clair Jacobson and Brooke Schoepf,Basic Books,1963),第22页。)
弗雷泽只让弗莱看到了不同文化背景中存在着相同的神话和祭祀模式这一现象,而未能向他揭示隐藏在这一现象深处的无意识的结构和产生这些相同模式的“原始意象”;而荣格则用他的“集体无意识”学说和原型理论为弗莱找到了存在于文学中那些反复出现的意象之下的“无意识的结构”,为他提供了阐释这些意象结构方式的理论基础。
当然,弗雷泽的许多理论和观点对文学研究也确实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较早运用他的理论的是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默里发现莎士比亚剧中哈姆雷特的故事与古希腊英雄俄瑞斯忒斯(Orestes)的故事有许多绝非偶然的相似之处:他们两人都是老国王的儿子,老国王被皇族中某个亲属谋杀了,而后这个亲属篡位做了新国王并娶了王后,即他们的母亲作妻子;然后哈姆雷特和俄瑞斯忒斯又都受到神示去为他们的父亲报仇,最后他们不仅杀死了篡位的新国王,而且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他们的母亲的死亡。默里深入考察了哈姆雷特和俄瑞斯忒斯两个故事的发源和神话模式,前者出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传说,后者为古希腊神话,两者不大可能会相互影响或相互模仿。因此,默里认为两个故事之后是“我们可以称之为金枝国王的世界范围的仪式或习俗故事”,(注:吉尔伯特·默里:《诗歌传统》(The ClassicalTradition in Poet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7),第228页。)换句话说,就是弗雷泽所说的“老国王被新国王、新国王又被后来的新国王所杀”的循环模式。因此默里相信,某些故事和情景“深深地植入了民族的记忆之中,可以说是在我们的身体上打上了印记”。(注:吉尔伯特·默里:《诗歌传统》(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n Poet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7),第238-239页。)
实际上,默里使用的“民族的记忆”的比喻就有着心理学的含义,只不过他不是心理学家而未作深入研究而已。这种“民族的记忆”的心理学含义由卡尔·荣格发掘了出来。卡尔·荣格曾是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作为一位心理学家,荣格在临床研究和广泛阅读的基础上,从神话以及他的病人的梦和幻想中,发现许多现象似乎源自原始社会的集体经验而不是个人的经验,因此他相信所有的人不仅都有着“个人无意识”,而且也都具有一种“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这个术语是荣格创造的。所谓“集体无意识”,用荣格的话来说,即
并非由个人获得而是由遗传所保留下来的普遍性精神机能,即由遗传的脑结构所产生的内容。这些就是各种神话般的联想——那些不用历史的传说或迁移就能够在每一个时代和地方重新发生的动机和意象。(注:荣格:《心理类型》(伦敦:1924),第616页。)
换句话说,“集体无意识”是指人类自原始社会以来世世代代普遍性的心理经验的长期积累,“它既不产生于个人的经验,也不是个人后天获得的,而是生来就有的。”(注:荣格:《卡尔·荣格主要著作选》(The Basic Writings of C.G.Jung,ed.Violet Staub de Laszlo,Modern Library,1959)第287页。)这是一个保存在整个人类经验之中并不断重复的非个人意象的领域。罗伯特·戴维斯和罗纳德·施莱弗认为:“集体无意识既属于人类,(在意识层次之下)也属于个人,包含‘原型’,或曰人类经验的基本模式和形式,如‘母亲’、‘再生’、‘精灵’、‘骗子’。”(注:罗伯特·康·戴维斯和罗纳德·施莱弗:《当代文学批评:文学和文化研究》(Contemporary LiteraryCriticism: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Longman Inc.,1989),第278页。)
荣格把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称为“原型”(archetype)。根据荣格的解释,原型是“自从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普遍意象”,(注:《卡尔·荣格主要著作选》,第288页。)是在人类最原始阶段形成的。原型作为一种“种族的记忆”被保留下来,使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先天就获得一系列的意象和模式。尽管这种理论显得有些神秘,但荣格觉得没有其他方法能够说明为什么那些处于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之中的个人的头脑中会存在或出现相似甚至几乎完全相同的意象和模式。譬如,荣格注意到,在一个新教牧师的梦中和在非洲部落的传说中都把水当作是无意识的象征。另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就是荣格在1906年治疗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向荣格叙述了他的幻觉,其中包含着一些奇怪的象征图形。而人们直到1910年才首次在写在古希腊纸莎草纸上的文稿中译解出一些相似的象征图形来。因此,荣格认为,原型理论不仅可以解释诸如此类的例子,而且可以解释弗雷泽发现的神话和祭祀仪式的相似性,因为神话是从原型这种普遍模式中产生的。
正是通过解释和揭示原型与神话以及神话与艺术的关系,荣格把他的原型理论扩展到文艺领域。荣格认为,原型是人类长期的心理积淀中未被直接感知到的集体无意识的显现,因而是作为潜在的无意识进入创作过程的,但它们又必须得到外化,最初呈现为一种“原始意象”(Primordial image),在远古时代表现为神话形象,然后在不同的时代通过艺术在无意识中激活转变为艺术形象。这些原始意象,即原型,之所以能够遗传下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艺这个载体,因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们不断地以本原的形式反复出现在艺术作品和诗歌中;也正是因为如此,荣格说,在文艺作品中,“一旦原型情境发生,我们会感到一种不寻常的轻松感,仿佛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运载或超度,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注:荣格:《心理学与文学》(三联书店,1987),第121页。)
在文艺研究中,荣格不同意文学艺术即幻想的观点,不赞成把治疗精神病的精神分析方法直接运用于文艺研究。因此,弗洛伊德从“个人无意识”的角度去解释文艺现象,而荣格则用“集体无意识”理论去解释。荣格认为文艺作品是一个“自主情结”(autonomous complex),其创作过程并不完全受作者自觉意识的控制,而常常受到一种沉淀在作者无意识深处的集体心理经验的影响。这种集体心理经验就是“集体无意识”。虽然读者不能直接在文艺作品中发现集体无意识,但却能通过在神话、图腾和梦中反复出现的原始意象发现它的存在与意义。因此,批评家可以通过分析在文艺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叙事结构、人物形象或象征,重新构建出这种原始意象,进而发现人类精神的共相,揭示艺术的本质。
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一样,荣格的以“集体无意识”学说为核心的心理学理论对文学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早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的是莫德·博德金(Maud Bodkin,1875—1967),她在1934年发表的《诗歌中的原型模式》中便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及原型理论运用于诗歌研究,在诗歌中某些反复出现的意象、象征和场景中发掘出由来已久的原始意义。比如,博德金在此书中用了整整一章去讨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1772—1834)的《老水手》一诗。她认为这首诗的艺术效果在于它与《圣经》中约拿的故事同属一类,表现了“再生”这一原型:约拿不服从神命,乘船逃走,惹得海上风浪大作,被众人扔进大海,被一大鱼吞入肚内三天三夜,而后他在鱼肚里向神呼救许愿,又被鱼吐出来抛在岸边获得“再生”。老水手也像约拿在海上航行,起初他充满仇恨与罪恶,并杀死了一只信天翁而招致一连串的灾难,全船水手全部死亡,他也已无力动弹,在等待死亡。这时他明白了自己的罪过,便开始祈祷,于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把船推向岸边使他获得“再生”。
尽管有少数像莫德·博德金这样的批评家在弗莱之前就曾尝试在文学批评中使用原型模式,但是原型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或手法并产生巨大影响是诺思罗普·弗莱的功绩。毫无疑问,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和原型理论以及早期批评家在文学批评中运用原型模式的实践对弗莱有着极大的影响。如罗伯特·德纳姆所说,“在评论荣格的《无意识的心理》时,弗莱形成了一种批评观点,后来这种观点——有些地方原本不动地——进入了《批评的解剖》一书中对象征原型阶段的阐述。”(注:德纳姆编:《诺思洛普·弗莱论文化与文学》,第26页。)当然这并不是说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完全是荣格式的,因为弗莱不仅强调文学批评必须与其他学科,如人类学和心理学,独立开来,而且在建立其原型批评理论的过程中,弗莱虽以荣格的原型理论为基础,但却把对原型的定义从心理学的范畴移到了文学领域。原先的原型是一些零碎的、不完整的文化意象,是投射在意识屏幕上的散乱的印象。这些意象构成信息模式,既不十分模糊,又不完全统一,但对显示文化构成却至关重要。现在对弗莱来说,原型成了文学意象,一个原型就是“一个象征,通常是一个意象,它常常在文学中出现,并可被辨认出作为一个人的整个文学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注:诺思洛普·弗莱:《批评的解剖》(The Anatomy of Critici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第365页。)譬如,弗莱认为,有些常见的自然景象,如大海、森林等,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就不能被认为是“巧合”,相反,这种反复显示了自然界中的某种联系,而文学则模仿这种联系。因此,一个关于大海的故事就可能有一个潜在的原型模式。
通过转化、运用原型理论,弗莱把一部作品构织成一个由意象组成的叙述表层结构和一个由原型组成的深层结构,并通过原型的零乱的提示去发掘出作品的真正含义。弗莱认为原型不仅可以包容而且可以贯穿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情节和背景的发展过程;一些表面上没有联系的文本组成部分和描写细节构成了一个或多个原型模式,而这些模式又可以反映作品的叙述和意象表层之下的内容。
这种原型的移位对于弗莱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他试图发现文学的“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也就是说,去确定文学领域的组织结构。弗莱说:“所谓原型,我是指一个把一首诗与另一首诗联系起来因而帮助使我们的文学经验成为一体的象征。”(注:诺思洛普·弗莱:《批评的解剖》(The Anatomy of Criticism,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57),第99页。)而原型批评的目标之一就是不仅发现作品的叙述和意象表层之下的原型结构,而且揭示出连接一部作品与另一部作品的原型模式,最终“使我们的文学经验成为一体”。而且弗莱认为,人们不可能到文学之外去完成这一任务,不可能用其他领域——无论是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领域——的概念来结构文学。相反,人们必须用归纳的方法来考察文学本身。而弗莱的考察结果显示,文学的结构是神话式的,不同类型的文学构成“一个中心的、统一的神话”的不同方面,而在各类文学的具体作品中,人们可以发现相似的原型和模式。
从表面上看,弗雷泽的神话模式理论和荣格的原型理论似有相似之处,但他们的根本区别在于:弗雷泽只是在神话中发现了相同的模式,而荣格则说明了这些模式是怎样保存下来的。正如荣格解释了自从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原型”是怎样保存在整个人类经验之中并不断反复的,原型批评的兴趣也在于探寻文学中某些反复出现的意象的由来已久的原始意义以及它们是怎样保存在文学经验之中的。正是从这一层意义上说,笔者才认为弗莱的原型批评是以荣格的心理学为主要理论基础的,才同意罗伯特·康·戴维斯和劳里·芬克提出的“精神分析学……是原型批评的理论之父”(注:罗伯特·康·戴维斯和劳里·芬克:《文学批评与理论:从古希腊至当代》(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y:TheGreeks to the Present,Longman Inc.,1989),第571页。)的观点。如果说弗雷泽的理论对原型批评有所影响的话,那就是弗雷泽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发现了相似的神话模式,这对弗莱从整体上考察文学中反复出现的意象有所启发;此外,弗雷泽的那种春夏秋冬季节循环变化与远古神话和祭祀仪式有关的理论对弗莱的原型批评也有所影响。
原型批评的整体性文化批评倾向
弗莱的原型批评是一种独特的批评方法。首先,弗莱的文学观是一种“整体文学观”。弗莱认为文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自主自足的体系。在《文学的原型》一文中,弗莱把艺术和自然作了比较,认为文艺批评家应像自然科学家把自然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那样,把艺术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来进行研究。众所周知,原型批评是作为对新批评的一种反驳而兴起的。弗莱认为,新批评对于文艺作品的“细读”只是解释了个别的、具体的作品,作为一种微观研究,它虽然对发现文学艺术的个别现象和规律有益,但却忽略了文学作品之间的联系,忽略了文学的广阔的结构性,因而不能发现文学艺术的普遍形式和规律。弗莱主张将一首诗或一部作品放在它与作者的全部作品的关系中去考虑。放到整个文学关系和文学传统中去考虑;也就是说,批评家还必须对文学进行宏观研究,必须找到一种更大的范式,去发现和解释文学艺术的总体形式和普遍规律。这种更大的范式就是原型。因此,弗莱的原型批评实质上是把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批评模式。当然,弗莱在阐述其原型批评理论时并未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分开,尤其是在其代表作《批评的解剖》一书中,他从五个层面——从微观到宏观——对文学进行了分析,即字面层面、描述层面、形式层面、原型层面和普遍层面。在《批评的解剖》中,弗莱分析或评述了几百部作品,然而他的兴趣并非要“细读”这些作品,而是要通过分析这些作品去研究文学作品的类型或“谱系”,并通过这种研究去发现潜藏在文学作品之中的人类的文学经验。弗莱正是从整个文学现象出发,通过对文学的整体研究,建立起他的原型批评理论的。
其次,弗莱认为文学是循环发展的。弗莱从前人的理论中,尤其是从生命和自然界的循环运动中得到启发,认为文学的演变也是一种类似的循环。人生有生有死,自然界有日出日落/春夏秋冬的交替更迭。弗莱根据自然界里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变化规律,归纳出四种原型:
1.黎明、春天和出生方面,这是传奇故事的原型,狂热的赞美诗和狂想诗的原型;
2.天顶、夏天、婚姻和胜利方面,这是喜剧、牧歌和田园诗的原型;
3.日落、秋天和死亡方面,这是悲歌和挽歌的原型;
4.黑暗、冬天和毁灭方面,这是讽刺作品的原型。(注:参见王宁等编:《弗莱研究:东方与西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161页。)
弗莱使用这种原型体系去阐释文学的形态。对弗莱而言,有四种类型的文学或四种叙事模式,每一种叙事模式又是一种更大的模式的一部分。这种大的模式,与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或者神话英雄的出生、死亡和再生相似:春天与传奇相对应、夏天与喜剧对应、秋天与悲剧对应、冬天与讽刺对应;然而冬天过后又是春天,讽刺达到极点又会出现喜剧色彩。文学由神话开始,经历传奇、讽刺等阶段后,又有返回到神话的趋势。因此,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呈现出一种循环状态。
正是弗莱的“整体文学观”和“文学循环发展论”使得他的原型批评呈现出一种整体性文化批评倾向。近年来,随着弗莱研究的深入开展,我们发现,文化批评的成分在弗莱的批评理论中,尤其是在其晚期著述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统观整个原型批评理论,我们认为,原型批评呈现出一种整体性文化批评的倾向。这是因为,第一、弗莱的原型批评是以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和弗雷泽的神话理论为基础的。我们认为这两种理论本身就含有相当多的社会文化的因素;而且弗莱的理论兴趣更在于阐释原型的文化含义。弗莱把文学当作大文化语境中的一个整体,使用原型去挖掘文学意象的原始意义,发现文学的原型“概念框架”。第二、我们认为,弗莱在建立其原型批评理论时曾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精神分析学和神话理论的影响之外,还主要受到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即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尤其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历史批评)和奥斯瓦德·斯本格勒的“历史有机(循环)发展论”。弗莱本人曾在《历史形态》一文中指出:“对现代思想的综合是我们时代的点金石,而且任何这种综合如果不是由历史哲学所构成,就必定包含这种历史哲学。马克思和斯本格勒就代表了这个领域里最杰出的现代成就。”(注:德纳姆编:《诺思洛普·弗莱论文化与文学》,第76页。)
虽然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存在着“经济决定论”的缺陷,但进入20世纪之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都抛弃了这种庸俗社会学的理论,拓展了批评的视野,从对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文学艺术与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转向对社会、历史和文化(包括文学艺术)进行整体性研究,尤其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这种整体性研究更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主要方法之一。这种研究方法对20世纪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弗莱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是另一种被广泛采用的、扩大了的历史透视法,而且从内在属性上说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种。”(注:诺思洛普·弗莱:《批评之路》(The Critical Path,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3),第19页。)虽然弗莱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外部研究方法且有一定局限性,但他承认“没有人能够或者应该否认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注:诺思洛普·弗莱:《批评之路》(The Critical Path,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3),第18页。)实际上,原型批评与文化历史批评就有相互重叠的地方,历史批评家称之为历史背景的东西,原型批评家常称为神话原型。这两种批评均承认文学有一种潜在的模式,而且这种模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文学作品的形态。所不同的是,对历史批评家来说,这种模式产生于或者就是历史本身,而对原型批评家而言,这种模式就不那么容易被辨认,它往往存在于文学意象之下,存在于人类的信仰和行为之下,其源头要追溯到史前史、神话或者书面文学产生之前的传说和故事中,譬如美国文学中的“美国梦”主题,对历史批评家来说,是一个产生于19世纪美国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的文学模式,而对原型批评家来说,则是一个永恒的人类理想的地区性文化表现形式,有着悠久的历史意义。
至于斯本格勒的影响,主要是其“历史有机(循环)发展论”的观点。斯本格勒认为,历史的基本形态既不是单个事件的混乱组合,也不是稳定的线性发展,而是一系列他称之为“文化”的社会发展形态。这些文化像有机体一样成长、成熟、衰老、死亡。他举例说,西方文化的春天在中世纪,夏天在文艺复兴时期,秋天在18世纪,冬天则随着法国大革命而开始。而在此之前的古典文化也经历了相同的阶段。荷马时代的英雄相当于中世纪的骑士英雄,古希腊城邦时代相当于文艺复兴时期,雅典的全盛时期相当于巴赫和莫扎特时代,而亚历山大时代则相当于拿破仑时代。这种观点无疑与弗莱的文化史中平行阶段的理论及其原型季节循环模式十分相似。弗莱承认斯本格勒为他的《批评的解剖》中第一篇文章的“模式概念提供了基础”。
总之,弗莱对西方文学的发展及其历史层面进行了整体研究,对西方文学的原型发展——从史前祭祀神话直到当代讽刺文学——作了“原始结构主义”(protostructuralist)的解读,进而在文化整体之上竖立起单一神话的结构,其目的就是为了给文学批评提供一个整体的原型“概念框架”,建立起一种整体性的批评体系。弗莱曾经说过:“我想要的批评之路是这样一种批评理论:首先,它可以解释文学经验的主要现象,其次,它将就文学在整个文明中的地位引出某种观点。”(注:诺思洛普·弗莱:《批评之路》(The Critical Path,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3),第14页。)罗伯特·康·戴维斯和劳里·芬克也指出:“他的方法是把整个文学作为一个文化结构整体,包括诗歌、戏剧和散文的全部作品。”(罗伯特·康·戴维斯和劳里·芬克:《文学批评与理论:从古希腊至当代》,第656页。)
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在60年代对文学批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中世纪文艺复兴研究方面。然而自70年代以后,他的理论与方法随着结构主义批评的兴起而逐渐失去其影响。近年来文学批评界虽有人试图从其他角度对原型批评进行重新阐释,但其整体性文化批评倾向及其对当前西方颇为盛行的文化批评的启蒙影响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在此稍作论述,以期引起批评界同行们的兴趣,共同开展研究。
□
标签:集体无意识论文; 心理学论文; 弗雷泽论文; 荣格论文; 原型批评论文; 原型模式论文; 批评的解剖论文; 象征手法论文; 神话论文; 金枝论文; 无意识论文; 人类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