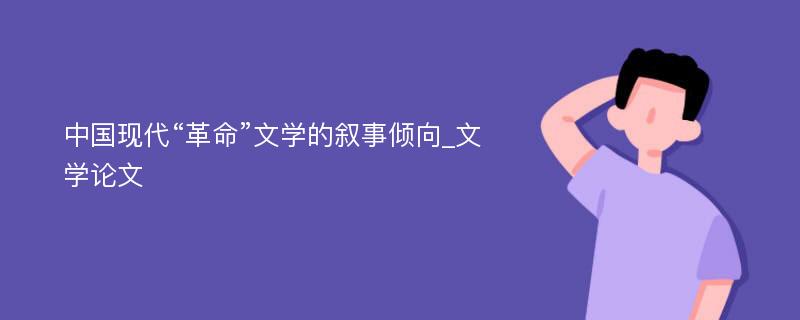
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叙事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倾向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叙事“时段”的隐义发掘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大多被笼罩在一种革命的氛围中,这里所说的“革命”不是一般的思想意识,也不是有具体主张的理论宣传,而是在作品情境中体现出的情感倾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中国现代的许多作品在“时间”的意识上被寄予了象征的含义,事件在时间轴上具有了特定的价值指向,由此彰显了它的“革命”意向。
谁都知道,中国现代有一股强大的反传统思潮,过去的、传统的、旧有的东西往往都被人从反方面去进行理解。可是为了达到求新竞进的目的,人们还需要一些具体言说模式、具体的事件安排方式,当人们在文学中企图把自己的意象表现出来时,手段与目的常常不能像想像的那样和谐。在现代具有革命倾向的叙事性文学作品中,理论上摒弃了“过去”的辉煌,但在实际的创作中为了达到否定现实的目的又不能不提供与现今对照的参照系,过去与将来成为最直接的价值联想,怎样对待过去和将来成为人们不能逾越的叙事“事件”。
在现代文学的具体文本中我们能看到的一种事件安排定向性是“过去”比现在好。《春蚕》中的老通宝在祈盼丰收时,把现在与过去做了对比:“记得自己还是二十多岁少壮的时候,有一年也是‘清明’边就得穿夹,后来就是‘蚕花二十四分’,自己也就是在这一年成了家。那时,他家正在‘发’”[1](p.76),以至到了《秋收》时老通宝还念念不忘“三十年前的‘黄金时代’”[2](p.111)。“黄金时代”里发生的事件给作品意义解读上带来的是什么呢?勤劳、节俭、诚实、努力,只要好好工作,就会得到好的回报。“现今”时代的人们也没能忘记这一点,“林老板,你是个好人。一点嗜好都没有,做生意很巴结认真。”这样的林老板“放在二十年前,你不发财么?”[3](p.54)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林老板,最后破产、自杀。《丰收》、《多收了三五斗》等大量描写丰收成灾的作品,之所以让人警醒,原因都在于现实没有给人们提供可能的出路,天道变了,过去的法则,现在不灵了。多多头“知道单靠勤俭工作,即使做到背脊骨折断也是不能翻身的”[1](p.89),“规规矩矩做人就活不了命”[4](p.123)。立秋也“……总是懒懒地不肯十分努力做功夫,好象车水种田,并不是他现在应做的事情一样”[5](p.614)。《上海屋檐下》黄家楣的父亲甚至迁怒得更远:“这个世界是变啦。咱们年轻的时候,天上打闪,总有雷的声音的,可是变了民国,打闪也没有声音啦。”虽然作品告诉我们,黄老头自己耳聋,雷声在他那里失去了震慑力,但在黄老头的话语方式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社会”的一般心态,否则黄老头也不敢杜撰这一“故事”。“今不如昔”可能有更深远的社会历史文化蕴涵,“九斤老太”意识,一般说来都是保守的负向价值体现。然而在具有革命倾向的文学叙事中,“过去”还承担了与“现今”不一样的“责任”,它主要不是一种实际的存在,而是对现实不满的心里寄托,在质疑现实的视野上,过去被人赋予了若干亮色。
如果说对“过去”的叙事是顶着极大的压力、在不被觉察的情境下与反传统的社会时代思潮发生了背忤,那么对“黄金子铺的地”的未来向往却是名正言顺的选择[6](p.590)。这里有两种关于未来的叙事在中国现代具有革命倾向的文学事件安排中被使用着:第一,未来是一种朦胧的目标,在知与不知的情境中焕发出了少有的光彩。瞿秋白在《饿乡纪程》的绪言中说,“我亲爱的同伴们呵!请等着,不要慌。阴沉沉,黑魆魆的天地间,忽然放出一线细微的光明来了。”[7](p.4)这光明所指任人都明白是什么,他的同伴们也同样对此抱着无尽的期待:
汽笛一声声催着,
车轮慢慢的转着。
你们走了——
走向红光里去了!
新世界的生活,
我们羡慕你们受着[8](p.33)。
如果说,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使》,有力排众议,敢为天下先的味道,在思想意识上召唤着“赤潮澎湃”的“二十世纪历史的事业之第一步”[9](p.200),那么蒋光慈的《鸭绿江上》则向人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未来的具体场景。苏维埃“十月革命”事件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叙事中的一种关于未来的驱之不去的憧憬。在中国当时的境遇中,苏维埃的实际情况是一个方面,人们通过传播渠道得到的心里期待又是一个方面。正像胡也频的作品名称显示的那样,《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到莫斯科去》,这是人们的一种坚定的信念,连传统的“旧社会”都可以被人目为“黄金时代”,更何况从未见过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和“理论”的“天堂”?我以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叙事中的理想,不仅与理论和事实相关,更与人们对现今的不满相关,在这个背景下只要与现今作对、与现今相抵牾都可以被作为有意义的事件使用着。第二,在具有革命倾向的文学叙事中,有时“未来”虽不可预期,也不妨先行“出走”,最坏也不过是现在所承受的,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出走的题材是中国现代文学叙事中的一大门类。田女士离家出走了,萧涧秋在乡党的围攻下逃走,觉慧从家庭的专制中出走去了上海。不仅是有为的青年转走他乡,就是农妇花金子、小姐愫芳也不甘寂寞,纷纷离家出走。江霞大哥离别江霞时说:“老三,你放心!家事自有我问。你在外边尽可做你自己愿意做的事,不过处处要放谨慎些!”[10](p.224)出走就一定会好吗?并不,鲁迅就曾探讨过“娜拉走后怎样”,在他看来出走的前程不一定光明。同样道理现今也不一定像想像的那样坏。“把最近的过去说成是‘黑暗的’(这个过去必然结构着现在),同时设想着‘光明’的未来必至无疑(即使这个未来是先前某个黄金时代的复活),这涉及到一种革命的思想方式。”[11](p.27)正因如此,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出走的事件不在作品开头,那样它将引发对未来的思考;也不在“中腰”,在“中腰”需要对出走前和出走后都有所交代;只在结尾——它不管后来会什么样,只是关注对出走前的意义阐释。我以为这是与中国现代文学出走母题意向相关的事件安排法则。毛泽东对“革命”的“破”与“立”有一种见解,在他看来“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出走就是“破字当头”的体现,它只关注对现实生活秩序的破坏,它是革命的情绪、革命文学叙事的标准事件安排方式。
过去不错,将来更好,只是现今不如意,这是革命文学叙事时段隐含意义的体现,其目的是为了否定现在。然而在文学作品中“现今”不能是一个空洞的存在,它要有具体的对象物和可被理解的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社会特定意识形态时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2](p.47)现今社会也是现今权威的社会。对统治阶层和统治势力的反抗,是任人皆知的中国现代革命意识体现,有关情况我们可以不赘。可在文化领域,在伦理和道德层面,现今被生活中的权威把持的意向,于社会群体意识中,它往往体现为习尚,于个体生活中,它暗示的就是“家长”。正如诺思罗普·弗莱所说,“主人公愿望的反对者,当不是父亲时,通常也是与父亲所处的已确立的社会有密切联系的人,也就是年事较长、财丰钱足的敌手。”[13](p.194)现代中国文学的“革命”叙事在父与子的冲突中,让否定现实的革命情结找到了取之不尽的描写素材,思想意识通过生活情境的推演变得丰满起来。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一般说来,老年人都不如传统文学中表现得“好”。家庭的长者,家庭的权威不能得到肯定,因为他们身上映衬的是现存生活秩序,肯定了他们,就是肯定了“现在”。不仅周朴园、高老太爷等是社会负向反面价值的体现者,即使是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受压迫”的家长,为了维持革命文学叙事的话语逻辑一致性,也受到了连累。保守、落后、不能寻找新出路是他们的共同特征,老通宝、云普叔是证。“父与子”的冲突,在这个视野上有了几种可被选择的类型:周冲与周朴园、觉慧与高老太爷,属于“正反”的对垒;多多头与老通宝、立秋与云普叔属于“道路”的抉择;至于李杰回到家乡,组织农会,打倒土豪劣绅,属于“造反”……一切都在说明一个道理:“现在是革命的时候了,老子管不了儿子。”[14](p.323)不但老子管不了儿子,还要儿子去“教育”老子,因为道理很简单,老子代表过去,儿子代表现在,革命就是现在对过去的违逆。
二、革命“词汇”诠释
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叙事,在时间段的调用上反映了自己的倾向,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时段”是对流程的概括,“流”需要“水滴”的供给,它在文学中需要具体实例的滋养。就像语法分析建立在词汇的基础之上一样,革命文学的言说逻辑也需要具体的革命“实例”——也要有革命“词汇”来作自己的表达工具。
财富是一个诱人的字眼,古往今来,没有的希望得到,得到的希望更多。正因如此,社会的自然法则产生了调控和制约的机制。传统中国社会均贫富的理想、仗义疏财的豪举,在一定意义上缓解着人们的心理紧张。可是20世纪前半叶,阶级剥削理论、社会主义理想,使得财富在向社会发展反方向的策应中越走越远。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对下层民众的体恤,让得不到财富的心理愈加不满,最终把财富推向了被告席。《丰收》里的何八爷能够为所欲为,因为他有地、有钱。《为奴隶的母亲》中的举人能“典”别人的妻子,满足自己的私欲,还是因为他能拿出钱。《五奎桥》中的周乡绅能够阻挡农人的正当要求,“乡绅”的地位非常重要,能够成为“乡绅”的人一定有钱。有钱才有势,有钱、有势才能仗势欺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铁证。为了改变穷人的处境,让穷人变富,站在穷人的立场上还说不出口。鲁迅早就提醒过人们,“人一阔,脸就变”。在革命文学理论观照下,人们杜绝了通过财富获得改变命运的企图,老通宝的梦想破灭是一例;《骆驼祥子》也告诉人们,“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15](p.211),不服输的祥子最后成为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15](p.228)。在这个视野中,没有办法的办法,让人们不得不转而憎恶财富、诅咒金钱。钱,“你这魔鬼,你这残忍的东西,你这世界上一切黑暗的造成者啊”[16](p.160)。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叙事中,财富和金钱缺少正面的光彩。虽然文学本有“世界大同”的趋向,但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革命使得社会“大同”的期望更多地从反面体现出来,人们不是希望通过“变”富而获得实利,而是通过避开金钱寻找新的出路。与“出走”题材意志相一致,对财富的诅咒着眼的是对现实的否定,至于实现自己真正所要达到的目的,还不在革命文学叙事的视野之内。
财富之恶的心理趋向连累了对有钱人的看法。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现代的实际社会生活中,许多与家国民族大业有关的壮举是由广义的有钱人干的,起码不能说他们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但在文学中,有钱或可能有钱的人都不如实际生活中有钱人所受到的“待遇”那么好。与中国传统文学相比,仗义疏财的豪侠不见了,温文尔雅的贵公子没有了。与外国的古典文学比,缺少了令人神往的绅士风度,减弱了忏悔、博爱的精神。这些都是有钱、有地位、有势力的人才能做、才配做、才能够赢得的声誉。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这些都被过于彻底地清除出人们的可能视野了。在时尚意识里,获得钱的手段是剥削,有钱不会是好人。这是阶级斗争思想、社会革命理论的表现。在文学中穷人不坏,坏人不穷。《窦娥怨》中张驴父子样的穷酸恶徒不见了,《水浒》中的屠夫和市井无赖销声匿迹。鲁彦所写的《阿长贼骨头》可能是不多见的刁民题材小说,但与《赌徒吉顺》、《为奴隶的母亲》的情感意向一样,作品中有缺点的穷人之所以有缺点,不在于他们的个体行为,而在于社会的畸形。
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私有财产在中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土地改革是四五十年代才开始有条件进行的社会变革,但其思想根基早在20世纪初的社会变革中便弥散开来。革命文学为它造足了声势、做齐备了思想意识宣传。生活在同一块黄土地上,为什么我不如人呢?江霞大哥想:“真的,刘家楼,吴家北庄,他们该多有钱!想起来也实在有点不公道!”[10](p.224)社会上有有钱的,有没钱的,这就不公道吗?“他们”的有钱和“我们”的无钱,可以有不同的思考逻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提供给人的是一种学习效法的榜样,“我们”可以像“他们”那样去致富。但是在中国现代社会,社会的不公平和阶级压迫,阻绝了走这条路的可能,社会意识鼓励的是“彼可取而代之”的造反心态。抢大户、抗租、抗税都是革命的行为。“偷两个瓜算什么,其罪就值得挨一次痛打么?为什么肚子饿了,没有吃瓜的权利?为什么瓜放在田里,而不让饿肚子的人吃?”[16](p.149)偷两个瓜,不应该遭“打”;肚子饿了,就应该吃“你”的瓜;瓜放在田里,任何人都可以吃。如此的道理,换一个社会环境可能讲不出,可在现代革命文学的“词典”里,它有根有据,仿佛天经地义。当“革命”群体让胡根富用两百块钱赎回了自己后,还觉得不够劲,“‘妈的,便宜了他!’癞痢头后来可惜地说道,‘他家里该多末有钱啊!听说白花花的银子埋在地窖里也不知有多少!’”[14](p.333)从这个意义上说,“吃瓜”实在是个典型表述,它是以小见大的样板,用“文学写真”袒露了革命的心理和情感趋向。
与“吃瓜”理论比起来,革命文学词典中“土匪”和“强盗”的特殊语误,更需要人们去细心辨析和厘定。“有许多土匪比所谓文质彬彬,或者耀武扬威的大人先生们好得多!倘若你以为当土匪是可耻的,那么,请你把土匪的人格低于大人先生的人格之地方指示出来!”[16](p.136)“土匪”的意念是什么,到底什么人是土匪,变成了“见仁见智”不能确定的议题!革命者往往以土匪自况,郭沫若有名的自由体长诗叫《匪徒颂》,其中就把“倡导社会改造的狂生,瘦而不死的罗素呀/倡导优生学的怪论,妖言惑众的哥尔栋呀/亘古的大盗,实行波尔显威克的列宁呀”作为自己心仪的对象。“兵”本来是维护政权、保卫国家的工具,可是由于政权的腐败,与政权联系在一起的人都可能沾有“匪气”。“那里现在驻扎着一连兵,这兵比强盗差不多,或者比强盗还要作恶些。”[16](p.141)到底谁是强盗谁是土匪,在革命文学叙事中大多需要人们从反面去认定,是一个需要人们换位思考才能明了的用语。
三、领导者“职位”的派定
叙事学理论不仅研究文学叙事,也研究历史叙事;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中的故事与文学中的故事一直有扯不断的因缘。《史记》中的若干篇什,一方面是“太史公”秉笔直书的史实记录,一方面也是优美的纪事散文,中国《古代散文选》中有多少脍炙人口的作品摘自《左传》、《国语》、《史记》?与此相联系,中国古代的小说也往往有史实的影子,《三国演义》、《水浒传》是证,甚至神魔故事《封神榜》、《西游记》也请出了历史真实人物出场。叙事学研究避开了“事实”而专注叙述的手段,注视的焦点是“叙述内容或故事的组织情况,即‘故事’(fabula)在‘情节’(sjuzhet)中的各种实现方式所依托的结构”[17](p.7)。历史通过事件的配置显示出关系和意义,叙事作品也要通过事件的配置显示出关系和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有了某种相通的特性。
中国历史和文学叙事在政治统治和集团利益上都有一类“智多星”式的人物出现:贤相或军师者是也。中国历史上开疆辟壤的元勋,个性都显得有些模糊,比如汉武帝,远没有张良、萧何有名气。相反倒有不少草包皇帝,不但末代皇帝有一个算一个,个个无能,开国皇帝也往往不如手下的大将、军师性格丰满。当然这里有多方面原因,也不可一概而论,但从整体上看趋向不错。为什么会如此呢?皇权的神秘和讳莫如深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领导者的才能也不都体现在自己有多大能耐上,而在于会使用人。使用人者才能大而不显,被使用者必须显示出自己的才能才会被使用。中国的文学性叙事深深懂得这一点,有意识地宣扬和尽情涂抹了这一趋向。诸葛亮、徐茂公、吴用,一个比一个神,有时颇有功高盖主之嫌,与他们比起来刘备、李世民、宋江算得了什么?深入地析理这一“文学”现象,不是我们的题旨,只要我们承认有这样的趋向也就足够了。我们指出这一点的目的是要说明: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叙事在领导“职位”的派定上与此发生了某些迁移,在情节事件配置的背后潜隐了事关“革命”的重大意义。
在现代中国文学的“英雄传奇”和“草莽聚事”型作品中,军师型人物的称谓发生了改变,政治委员、政治指导员、地下革命者和党代表等,称呼不同,作用却大体相当。与传统文化中此类人物类型相比,他们的作用更加突出,不但运筹帷幄得到了群众的拥护,而且也让“队长”、“司令”心悦诚服,仿佛与名义上的“一号人物”发生了“交叉换位”。如果说《红色娘子军》中高瞻远瞩的党代表洪长青是男性,恰如万花丛中一棵伟岸的青松,多少还有些男性主义的色彩,从而在叙事逻辑上遮掩了政治的含义;那么在《杜鹃山》、《洪湖赤卫队》中,柯湘、韩英则以女性的身份,出生入死,勇敢而有决断,在本是男性一统天下的战场上,叱诧风云,力挽狂澜,这就不完全是事件的真实而是情感意识的需要。她们的自然身份并不重要,社会赋予她们“职位”的符码意象起了决定作用。这一趋向在四五十年代以后取得了支配地位,但隐含的价值冲动早在20年代中期以后带有革命倾向的文学叙事中便显露出来。《田野的风》中,李杰是进入农民运动组织的知识分子,他与农会主席张进德的关系颇为微妙。名义上张进德是主席,李杰是一个重要的参加者,可实际上处处李杰起决定作用。在乡村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之时,李杰有了某种预感:
“李杰感觉到这种××的势力蒙着一种面幕……他深深地为着这种感觉所苦闷着。……正在兴奋着的何月素,是不会相信他的。……有一次他曾向张进德略略提及一下,可是张进德很不在意地说道:‘管他呢!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14](p.369)
两相对比,张进德与李杰的政治敏感程度孰高孰低,一眼就看得出来。在革命的队伍遇到暂时困难之时,还是李杰能够站出来进行形势分析,化解群众的疑虑:
“李杰首先向会场做了个详细的报告。他说,政局有了大的变动,一些假革命的叛徒们抛弃了革命的政策。他说,阶级起了分化,资产阶级投降了帝国主义…..土豪劣绅们连合一起……最后他说,这是必然的结果,没有什么可失望的,今后只有我们自己的努力……会场如驯服的巨兽一般躺着,静听着报告者的有时令他们不能明了的语句”[14](p.375)。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职位”派定不让李杰当“一把手”而让他当“副职”呢?现实的理由是:革命是工人、农民的造反,工人、农民一般并没有多少理论和知识可以炫耀,但革命毕竟不是聚众闹事,理论、知识、目标、理想,决定着革命的素质,世界范围内的“左倾”文化思潮,也与“主义”、“思想”密不可分。这样事实上就存在一个革命主体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主体者当然是一把手,不管实际情形如何,革命的叙事必须与革命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这就是我们反复看到的李闯、雷鸣等憨态可爱、勇猛有余,然而不堪大任,既没有传统叙事中刘邦、刘备、李世民等的“用人”的谋略,当然也缺少一把手的权威和霸气。然而如果我们仅仅从革命主体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关系角度解说现代革命文学叙事的领导“职位”派定价值取向,还不能完全把握时代的脉搏,在这里还有一个深潜其下,与现代中国革命联系更紧密的思维逻辑在制约着这一选择。共产党是中国现代革命运动的思想轴心,可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几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共产党都是“副手”,是“在野”性质的政党。周恩来在抗战时期出任的就是国民政府第三厅的副厅长,北伐战争以来,共产党人入阁所担任的绝大部分职务都是“副职”。在野的处境也决定了在野者对自己能够胜任的社会位置的叙事选择。如果我们把现代革命文学叙事与当代文学的有关表述做一对比,对现代革命文学叙事领导“职位”派定意识的取向理解得会更深刻。改革开放以后,反腐倡廉题材的叙事,在有关“领导者”的观念意识中有一个共同点:干坏事的都是副职,一把手肯定是好人;或者用替代的方式来表达这一意向:干了坏事的单位领导,最终要由能制约他的上级领导来处罚——他还是附属的角色。因为在主流意识形态看来,当代社会的主导意识倾向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个别人身上,“个别”与“少数”的“典型”应该是不起主要作用的“副职”。以此反观现代革命文学叙事,名义上的一把手的乏力与多种“副职”承担者的有为,同样是主导社会意识建构的需要。所谓30年代国共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与“军事”比起来,“文化”已早早地在有关“革命”的文学叙事中取得了胜利。
中国现代社会和中国现代文学充斥着一股挥之不去的革命情结,它是推动中国现代社会向前发展的原动力。这种革命的情绪和革命的意愿,在文学中不仅是由作者和作品人物用语言直接表达的,如果那样它的深厚历史韵味将大大降低,作品个性化因素会起到一定作用,把它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视角来研究的意义就涣散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倾向在作品言辞、故事结构、人物行为等显而易见的层面之外,还在作品的潜在述说逻辑、人物角色布置以及富有特色的语汇、词义的选择上表现出了超出作者个人明确意识的普遍社会倾向,由此才显出了“革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诱人魅力,不管是坚定的革命者,还是不断被批评、改造的同路人,他们都在最基本的立场上站在了一起。我们研究“革命文学”倾向的意义在这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不能绕过“革命”的原因也在这里。通过以上的探讨己可以证明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