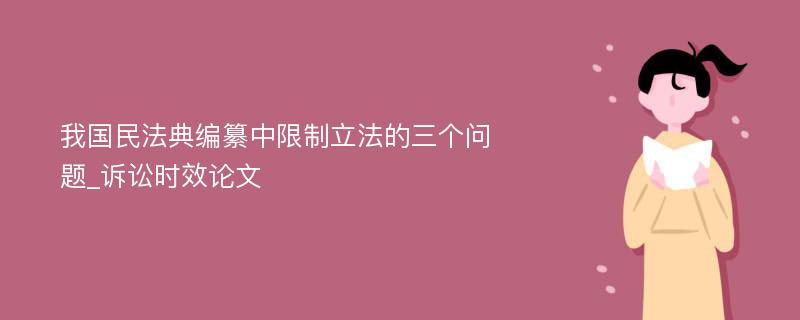
我国民法典编纂中时效立法的三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法典论文,时效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效是民法上的重要制度,直接关涉到当事人的权利保护。在我国未来民法典中,时效特别是诉讼时效应当如何规定,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试就时效立法的三个问题提出拙见,以期为民法典的制定有所助益。 一、时效立法模式的选择 (一)比较法考察 在域外民法上,时效通常包括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我国《民法通则》仅规定了诉讼时效,通说认为其在性质上属于消灭时效。①在民法典中如何处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的关系,涉及时效的立法模式问题。对此,域外民法上有三种立法例: 一是统一立法模式,即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在民法典中统一加以规定,并设立时效通则(一般规定)。因民法典编纂体例的差别,统一立法模式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潘德克顿式民法典中,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统一规定于民法典总则编。例如,《日本民法典》在第一编(总则)第七章规定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并设置了时效总则。在法学阶梯式民法典中,因不存在民法典总则编,故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统一规定在民法典的某一部分。例如,《奥地利民法典》在第三编(人法和财产法的共同规定)第四章(消灭时效和取得时效)规定了消灭时效和取得时效,《西班牙民法典》在第四卷(债与合同)第十八集(时效)规定了取得时效(占有和其他物权的时效)和诉讼时效,《阿根廷民法典》在第四卷(物权和对人权的共同规定)第三编(因时间的经过而取得或丧失物权和对人权)规定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智利民法典》在第四编(债的通则和各类合同)第四十二题(时效)规定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菲律宾民法典》在第三编(取得所有权的不同方式)第五题(时效)规定了取得时效(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时效)和诉讼时效。 二是分别立法模式,即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分别规定于民法典的不同部分,不存在时效通则。这种立法模式也因民法典编纂体例的差别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潘德克顿式民法典中,消灭时效规定于总则编,取得时效规定于物权编。例如,《德国民法典》在第一编(总则)第五章(消灭时效)规定了消灭时效,在第三编(物权法)第三章(所有权)第三节(动产所有权的取得和丧失)规定了取得时效;《俄罗斯民法典》在第一编(总则)第五分编(期限、诉讼时效)规定了诉讼时效,在第二编(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第十四章(所有权的取得)中规定了取得时效;《韩国民法典》在第一编(总则)第七章规定了消灭时效,在第二编(物权)第三章(所有权)第二节(所有权的取得)中规定了取得时效;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在第一编(总则)第六章(消灭时效)规定了消灭时效,在第三编(物权)第二章(所有权)中规定了取得时效。在法学阶梯式民法典中,消灭时效和取得时效分别规定于民法典的不同编章。例如,《法国民法典》在第三卷(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第二十编规定了消灭时效,在二十一编规定了取得时效;《意大利民法典》在第三编(所有权)第八章(占有)中规定了取得时效,在第六编(权利的保护)第五章(消灭时效和失权)中规定了消灭时效;《埃塞俄比亚民法典》在第三编(物)第七题(个人所有权)第一章(所有权的取得、移转、消灭和证明)中规定了取得时效,在第四编(债)第三章(债的消灭)中规定了诉讼时效;《埃及民法典》在第一编(债或对人权)第一分编(债的一般规定)第五题(债的消灭)第三章(非经履行的债之消灭)中规定了消灭时效,在第二编(物权)第二章(所有权)中规定了取得时效。 三是混合立法模式,即在民法典总则编规定消灭时效和取得时效的一般规则,在其他编具体规定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例如,《越南民法典》在第一编(一般规定)第九章(时效)就时效的种类、计算、中止、中断等一般规则作了规定,在第二编(财产与所有权)第十四章(所有权的成立、终止)中规定了取得时效,在第三编(民事义务与民事合同)中有关民事合同终止、非合同损害赔偿责任等部分规定了诉讼时效。 从上述立法例可以看出,无论是哪种立法例,基本上都是将取得时效作为物权的一种取得方式加以规定。这表明,取得时效主要适用于物权制度,对其他制度鲜有适用。 (二)学说争议 从我国立法实践来看,因现行法并没有规定取得时效,故尚无法判断采取了何种立法模式。但有学者指出,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民事立法深受苏俄民事立法模式的影响,故《民法通则》采纳了统一立法模式,但未规定取得时效。②在我国编纂民法典过程中,时效应当采取哪种立法模式,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认识。 2002年《民法草案》采取了统一立法模式,于第八章规定了时效,并分设二节规定了诉讼时效和取得时效。③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亦采取了统一立法模式,于第八章“时效”中分别就一般规定、诉讼时效、取得时效、除斥期间、失权期间、或有期间作了规定。④有学者认为,时效制度有统一的功能和目的,其效力均为发生权利的得丧,可以抽象出两者的共同规定,如期间中止、不完成、重新计算等,因此,将诉讼时效和取得时效统一规定于民法典总则编是可行的,可以避免立法的重复或准用的争议。⑤也有学者认为,取得时效与诉讼时效均以一定的事实状态的存在和一定的期间经过为前提,均导致权利变更的法律后果,因此,为了保持民法典的完整性,应在立法上将同属于民事法律事实的取得时效与诉讼时效统一归于时效制度之下。⑥ 也有学者主张采取分别立法模式,在民法典总则编规定消灭时效,在物权编规定取得时效。⑦其主要理由在于:第一,取得时效是物权的取得方式,只能适用于物权,因此,采取统一立法模式,将取得时效规定于总则编,不具有普遍适用性。第二,统一立法模式并不符合各国时效立法趋势。尽管目前仍有国家采取统一立法模式,但分别立法模式已成为世界时效立法趋势。第三,从我国实际来看,分别立法模式是我国的立法传统。第四,梁慧星教授、王利明教授负责起草的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均分别规定了诉讼时效和取得时效,这足以表明我国学者的立场。⑧ (三)本文主张 笔者认为,时效立法模式的选择,首先应当解决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否承认取得时效问题。因为若我国未来民法典不承认取得时效,讨论时效的立法模式就没有实际价值。在我国制定《物权法》的过程中,学者们对是否应当规定取得时效存在很大的争议,因此最终《物权法》对此没有规定。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国民法就不承认取得时效制度呢?在民法上,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是时效制度的两个重要支柱,缺乏取得时效制度,消灭时效的制度价值将会大打折扣。同时,取得时效是各国民法的通行制度,也为学界所公认。所以,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规定取得时效制度当无疑问。⑨那么,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采取何种立法模式规定消灭时效和取得时效呢?笔者认为,混合立法模式导致时效分散规定于民法典的不同部分,特别是如果把消灭时效的通则与具体规则规定于民法典的不同章节之中,不仅会破坏时效的整体性,也不利于法律的适用。因此,混合立法模式并不可取。而对统一立法模式与分别立法模式的选择,笔者倾向于分别立法模式,即在民法典总则编规定诉讼时效,在物权编规定取得时效,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分别立法模式符合时效立法的发展趋势。时效制度早在罗马法时期就已存在,且因取得时效的产生早于消灭时效而采取分别立法模式。但至中世纪时,罗马法将两种时效制度统一,从而形成了统一的时效制度,⑩并一直影响至今。在自然法发达时期所订立的民法典,如《法国民法典》《奥地利民法典》承袭了统一立法模式。(11)在近现代民法上,受《法国民法典》影响较大的民法典基本上都采取了统一立法模式,如西班牙、阿根廷、智利、菲律宾、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加拿大魁北克等。但应当指出,《法国民法典》在时效立法上原采取统一立法模式,其第三卷(取得财产权的各种方式)第二十编(时效与占有)统一规定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但在2008年修订时放弃了统一立法模式,而改采分别立法模式。《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也采取分别立法模式,于第三卷(债及相关权利)第七章(时效)规定了消灭时效,于第八卷(物的所有权的取得和丧失)第四章(通过持续占有取得所有权)规定了取得时效。而且即使在采取统一立法模式的国家如奥地利、日本,民法理论对该模式也大都持反对态度,并于民法理论上分别阐述消灭时效和取得时效。(12)可见,在时效立法上,分别立法模式已经成为当代各国的立法趋势。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顺应这种立法趋势,采取分别立法模式,在民法典总则编规定诉讼时效,在物权编规定取得时效。 第二,分别立法模式符合民法典的逻辑构造。从各国民法典的编纂体例来看,有法学阶梯式民法典和潘德克顿式民法典之分。前者基本上由人法和物法两部分组成,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民法典;后者由总则与分则组成,如德国、日本等国民法典。我国学者通说认为,未来民法典应当采取潘德克顿模式,设置总则和分则。在这种民法典模式中,民法典总则编是否应当规定取得时效是值得讨论的。民法典总则的功能是通过“提取公因式”的逻辑方法将分则中的共同规则抽象出来,用以指引分则中的具体规则,因此,只有适用于民事基本制度的共同规则才适宜规定于民法典总则编,而诉讼时效就具有这种属性。因为诉讼时效不仅适用于债权请求权,也适用于因人格权、物权、继承权受到侵害而产生的请求权。从各国民法规定来看,取得时效主要适用于物权的取得。当然,取得时效也可适用于其他权利,如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承租权等。(13)就此而言,似乎将取得时效规定于民法典总则编也无可厚非。但是,取得时效适用于物权之外的其他权利是极少发生的。因此,即使将取得时效规定于民法典总则编,其也主要适用于物权取得。与此情况类似,善意取得主要适用于物权的取得,也可以适用于债权、票据权利的取得,但各国民法典也是将善意取得规定于物权编,而没有因其适用于物权之外的其他权利而规定于民法典总则编,如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民法典。可见,从民法典的逻辑构造来看,取得时效并不是民法的共同规则,其主要适用于物权的取得,不符合归入民法典总则的要求。(14) 第三,分别立法模式符合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的本质属性。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虽然都是时间因素对民事权利所产生的影响,但两者在目的、规制对象、构成要件、法律效果等方面都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无法从消灭时效和取得时效中抽象出一般规则。既然两者在性质上各异,自不能以统一制度,规定于一处。(15)正如德国学者所指出的:“将二者(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归于同一学术理论框架之下在今天不再被视为有所裨益的,因为他们受制于不同的规则。”(16)日本学者我妻荣也曾指出: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虽然都是时效制度,但在援用、放弃、中断等具体规定上、处理上有很多差异是不能否定的,将两者分别处理是适当的。(17)因此,即使民法典统一规定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其实际上也是各自独立的,只是形式上的统一而已。正如有学者评价《法国民法典》原时效立法采取的统一立法模式那样,其统一立法仅仅是形式的,而实质上还是分别制。因此,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采取分别立法模式。(18) 尽管我国未来民法典在时效立法上应当采取分别立法模式,但考虑到我国编纂民法典不可能一步到位,学者普遍认为应当先制定民法典总则。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过渡的处理办法,即在制定民法典总则时先统一规定诉讼时效和取得时效,待民法典整体编纂时,再将取得时效移至物权编。这样处理,可以较早地弥补时效立法的缺陷,为司法实践提供法律依据。 二、诉讼时效名称的取舍 (一)比较法考察 从域外立法例看,就消灭权利的时效如何称谓,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是称为消灭时效,这是多数立法所采用的名称。例如,《法国民法典》第2219条规定:“消灭时效是指因权利人在一定时间内不行使而引起某种权利消灭的一种方法。”《德国民法典》第194条规定:“向他人请求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请求权),受消灭时效的限制。”《意大利民法典》第2934条规定:“权利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未行使的任何权利,均基于消灭时效而消灭。”日本、阿根廷、智利、我国台湾地区等民法典,也以消灭时效称之。 二是称为诉讼时效。例如,《俄罗斯民法典》第195条规定:“诉讼时效是被侵权人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提起诉讼的期限。”《西班牙民法典》第1961条规定:“诉讼时效依据法律确定。” 三是分别称为诉讼时效和消灭时效。例如,《美国路易斯安那民法典》将时效分为取得时效、诉讼时效和消灭时效三种。诉讼时效是指在一定期间内不提起诉讼而被禁止诉讼的时效(第3447条);消灭时效是指在一定期间内未行使权利而导致非所有权的物权消灭的时效(第3448条)。(19)从性质上看,《美国路易斯安那民法典》中的诉讼时效相当于大陆法系上的消灭时效,而消灭时效与大陆法系上的消灭时效并不相同。 四是分别称为免除民事义务时效、民事案件起诉时效、要求解决民事事件时效。《越南民法典》将时效分为取得民事权利时效、免除民事义务时效、民事案件起诉时效、要求解决民事事件时效(第155条)。免除民事义务时效是指当期限届满时,义务人可以免除民事义务的时效;民事案件起诉时效是指当期限届满时,起诉权丧失的时效;要求解决民事事件时效是指当期限届满时,要求有关机关解决民事事件的要求权丧失的时效。从性质上看,《越南民法典》中的免除民事义务时效属于消灭时效,而民事案件起诉时效、要求解决民事事件时效与俄罗斯民法上的诉讼时效相当。 从上述立法例来看,关于消灭权利的时效的称谓,主要有消灭时效和诉讼时效之分,这也是我国学者的观点分歧所在。 (二)学说争议 我国《民法通则》采用了诉讼时效的名称,但未来民法典究竟应采用何种名称,理论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用诉讼时效取代消灭时效是不科学的,将“诉讼”和“时效”嫁接到一起造成了程序法和实体法不分的逻辑矛盾。(20)诉讼时效本质上属于消灭时效的范围,是从消灭权利的角度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的可能性和司法机关所应遵循的原则;诉讼时效的用语明显体现了诉讼法上的法律后果,带有一定的公法色彩,而诉讼法上的法律后果只是对私法效果的反射而已。因此,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摒弃诉讼时效的名称,回归消灭时效的名称。(21) 第二种观点认为,诉讼时效的概念尽管有其缺陷,如时效并不仅仅在诉讼中采用,在仲裁和执行程序也采用,但比较而言,采取诉讼时效更为妥当。这是因为,我国立法一直采用诉讼时效的概念,从法的延续性角度而言,如无重大理由不宜抛弃,以保护法律的稳定性和民众对法律的一贯理解。同时,采用诉讼时效的概念可以避免使人误以为时效届满就是使请求权消灭。(22)从消灭时效与诉讼时效的关系上看,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诉讼时效“不过是消灭时效的另一种表达方式”(23)而已。 第三种观点认为,诉讼时效和消灭时效的名称均不可取,应当采用“抗辩时效”的名称。一方面,消灭时效本质上为实体法性质,并兼具程序法性质,因此诉讼时效的名称与民法典的概念体系不符;另一方面,在我国,诉讼时效届满产生债务人永久性抗辩权的效力而非消灭权利,因此,将诉讼时效改称为“抗辩时效”才更符合消灭时效制度的法律性质。(24) (三)本文主张 笔者认为,尽管诉讼时效的名称给人以程序时效的印象,但无论是诉讼时效还是消灭时效,其都具有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双重属性。因此,单就名称本身无法作出选择。从民法理论与立法上说,一个法律名称的选择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而非单纯逻辑推理的结果,如我国法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基于以下因素的考虑,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继续采用诉讼时效的名称,而非消灭时效或抗辩时效。 第一,从法律名称使用的习惯上看,诉讼时效的观念已经为公众所接受。(25)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民事立法上一直使用消灭时效的名称,(26)目前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仍在使用之。但在新中国成立后,民事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一直使用诉讼时效的名称。例如,早在1954年9月,《司法部、铁道部联合指示经由铁路运送货物的赔偿案件货主提起诉讼的时效及司法管辖权的决定》中就已使用了诉讼时效的名称。直到1986年4月,《民法通则》以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诉讼时效在法律上的地位。可以说,无论是在审判实践中,还是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诉讼时效已为立法、司法及社会公众广为接受。因此,从社会成本上说,将诉讼时效改称为消灭时效是不妥的,不利于保护法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第二,从消灭时效的客体上看,其范围远大于诉讼时效的客体。在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民法上,关于消灭时效客体的规定并不相同。例如,有的立法规定,权利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未行使的任何权利均因消灭时效而消灭(《意大利民法典》第2934条);有的立法规定,债权及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未行使而归于消灭(《日本民法典》第167条);多数立法将消灭时效的客体限定为请求权,不包括其他权利,如支配权、抗辩权、形成权等,如德国、瑞士、我国台湾地区等。这里的请求权主要是债权请求权,不仅包括一切债的关系所发生的请求权(第一次请求权),也包括因原债务不履行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第二次请求权)。(27)也就是说,就请求权而言,消灭时效既适用于原权中的请求权,也适用于原权受到侵害时请求保护的权利,即救济权中的请求权。(28)就诉讼时效的客体而言,按照我国现行法的规定,诉讼时效只适用于救济权中的请求权,而不适用于原权中的请求权。因此,如果将诉讼时效改为消灭时效,就不仅仅涉及名称的改变,还必须在适用对象上进行重新设计,即将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扩大到原权中的请求权,但这种改变与我国的现实传统未必相符。例如,基于民间借款习惯,当事人往往不约定偿还期限,债权人通常也不主动催要。在这种社会现实下,“如将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改为请求权,则依现行法普通诉讼时效期限为2年的规定,自债权成立之时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就等于规定当事人之间不定期债的期限只能是2年。即使将诉讼时效的期间延长为3年或5年,这也相当于要求此借贷期限不能超过3年或5年,否则法律不予保护”,这样的处理显然是不合适的。(29) 第三,从消灭时效和抗辩时效的效力上看,其名称与效力也并非完全相符。一方面,从消灭时效的效力来看,概括起来有四种立法例:一是抗辩发生说,德国、瑞士民法等采取之;(30)二是实体权利消灭说,日本、韩国、埃及民法等采取之;(31)三是胜诉权消灭说,俄罗斯民法采取之;(32)四是诉权消灭说,埃塞俄比亚、智利、菲律宾民法采取之。(33)在我国,关于诉讼时效的效力,《民法通则》采取胜诉权消灭说,但司法解释改为抗辩权发生说。(34)可见,只有在采取实体权利消灭说、胜诉权消灭说及诉权消灭说的情况下,称为消灭时效才能名符其实;而在采取抗辩权发生说的情况下,时效届满并没有消灭什么权利,只是产生抗辩权。同时,在实体权利消灭说、胜诉权消灭说及诉权消灭说的情况下,往往也会产生债务人抗辩权,因此,称之为消灭时效也名不符实。对此,梅仲协先生就曾指出:“消灭时效之完成,仅足使义务人取得时效抗辩权,得拒绝其应为之给付,而同时权利人之请求权即减损其力量……定为‘消灭时效’,殊属未妥。”(35)另一方面,从抗辩时效的效力来看,时效届满使债务人取得抗辩权。就此而言,称之为抗辩时效应无问题;但从债务人取得抗辩权而言,抗辩时效称为取得时效也未尝不可。同时,从程序法上说,一旦债务人行使了时效抗辩权,则债权人的权利将得不到保护,即失去了通过法律保护的权利,也就意味着胜诉权的消灭。从这个意义上说,称之为消灭时效也是可行的。再者,从取得时效来看,时效届满后产生物权取得的效力,如果原权利人要求返还,占有人可以时效进行抗辩。从这个意义上说,取得时效也可以看成是抗辩时效,只是消灭时效的抗辩结果是债务人无须再履行债务,而取得时效的抗辩结果是占有人取得物权。可见,无论是消灭时效还是抗辩时效都存在一定的名不符实问题,因为这类时效产生的效力是多方面的。 第四,从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衔接关系上看,诉讼时效不宜改称为消灭时效。在大陆法系民法上,消灭时效制度通常适用于权利保护的全过程,不仅适用于当事人起诉前的权利保护,也适用于判决确定后的权利保护。也就是说,执行阶段的请求权也适用于消灭时效。对此,有的国家规定,经生效判决确认的请求权适用新的消灭时效。例如,《德国民法典》规定,普通消灭时效期间为3年(第195条),而经生效判决确认的请求权的消灭时效期间为30年(第197条)。有的国家规定,经生效判决确认的请求权,其消灭时效重新计算。例如,《葡萄牙民法典》规定,起诉将导致时效中断,因此,经法院判决确认的权利,其消灭时效重新开始计算(第326条);但若原权利的消灭时效期间短于普通消灭时效期间的,判决确认的权利受普通消灭时效期间的约束(第311条)。但是,在我国现行法上,诉讼时效并不适用于执行阶段,在判决生效后,权利保护适用执行时效。《民事诉讼法》第239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83条规定:“申请执行人超过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执行人对申请执行时效期间提出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不予执行。被执行人履行全部或者部分义务后,又以不知道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请求执行回转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见,执行时效在性质上属于消灭时效,也会发生时效抗辩的效力。因此,如果将诉讼时效改为消灭时效,就需要采取像大陆法系民法那样,将执行时效纳入民法上的消灭时效制度之中。但由于我国法一直将诉讼时效与执行时效分立,若将诉讼时效改为消灭时效,就须将执行时效纳入诉讼时效,而这并无可能,也无必要。(36) 三、诉讼时效期间的确定 (一)比较法考察 从域外立法例来看,各国和地区关于消灭时效(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存在很大差别。例如,《法国民法典》规定了两种消灭时效期间:一是普通消灭时效,期间为5年(第2224条);二是特别消灭时效,期间分别为5年、10年、20年、30年(第2225~2227条)。《德国民法典》规定了三种消灭时效期间:一是普通消灭时效,期间为3年(第195条);二是长期消灭时效,期间为10年(第196条);三是最长消灭时效,期间为30年(第197条)。《意大利民法典》规定了三种消灭时效期间:一是普通消灭时效,期间为10年(第2946条);二是短期消灭时效,其种类繁多,期间从1年至5年不等(第2947~2953条);三是推定消灭时效,期间从6个月至3年不等(第2954~2956条)。《日本民法典》规定了两种消灭时效:一是普通消灭时效,期间分别为10年和20年(第176条);二是短期消灭时效,期间分别为1年、2年、3年、5年(第169~174条)。《俄罗斯民法典》仅规定了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第196条);对于特殊诉讼时效期间由其他法律加以规定,期间可以长于或短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第197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规定了两种消灭时效期间:一是普通消灭时效,期间为15年(第125条);二是短期消灭时效,期间为5年(第126条)、2年(第127条)。 综合上述各国和地区的立法例,诉讼时效期间有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短期诉讼时效期间、长期诉讼时效期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之分,其中短期诉讼时效期间和长期诉讼时效期间属于特殊诉讼时效期间。 (二)学说争议 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类型,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普通诉讼时效期间(2年)、特殊诉讼时效期间(1年)和最长诉讼时效期间(20年)(37),《合同法》《产品质量法》《环境保护法》《保险法》《票据法》《民用航空法》等单行法就不同的请求权又规定了不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而形成了复杂多变的诉讼时效期间类型。(38)那么,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如何规定诉讼时效期间的类型呢?对此,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民法典应当规定普通诉讼时效期间(3年)和最长保护期间(20年),特殊诉讼时效期间无须规定。(39) 第二种观点认为,民法典应当规定普通诉讼时效期间(3年)和长期诉讼时效期间(10年),但无须规定短期诉讼时效期间和最长诉讼时效期间。(40) 第三种观点认为,民法典应当规定普通诉讼时效期间(3年)和最长诉讼时效期间(20年),无须规定短期诉讼时效期间和长期诉讼时效期间。其主要理由在于:在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短期化的趋势下,没有必要规定更短的诉讼时效期间。同时,在仅将诉讼时效适用于债权请求权且时效期间的起算采取主观标准的前提下,也没有必要规定长期诉讼时效期间。(41) (三)本文主张 笔者认为,诉讼时效期间的确定需要考虑以下四个因素: 其一,时效的立法宗旨。《德国民法典》在消灭时效的《立法理由书》中指出:“消灭时效之要旨,并非在于侵夺权利人之权利,而是在于给予义务人一保护手段,使其毋需详察事物即得对抗不成立之请求权。消灭时效乃达到目的之手段,而非目的本身。”(42)《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规定的消灭时效制度,系基于以下三项基本政策的考量:(1)保护那些因“时间混淆力”而越来越难以对抗诉讼请求的债务人;(2)时间的流逝意味着债权人对自己权利的漠不关心,相应地也使债务人产生其不会再主张权利的合理信赖;(3)消灭时效阻止了关于陈年旧账的漫长诉讼。因此,时效制度旨在从一个非常特殊的角度来维护法律的确定性。当然,在法律的确定性与债权人正当利益之间必须维持平衡。(43)可见,诉讼时效的立法宗旨主要在于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保护义务人利益、稳定法律秩序。(44)基于这一立法宗旨,诉讼时效期间类型的选择,既要便于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也要给予义务人充分的保护。因此,诉讼时效期间的确定不宜过于复杂,期间的长短须适当。 其二,时效期间的立法发展趋势。消灭时效制度的功能之一在于防止诉讼耗费金钱、久拖不决,因此,时效制度必须尽可能地简单、明确、统一。如果消灭时效规则本身引起过多的、特定案件中时效是否发生的争端,这样的规则是让人难以容忍的。(45)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在比较法上,消灭时效期间出现了统一化的趋势,特别诉讼时效期间日趋减少。(46)例如,《德国民法典》在修订之前,在普通消灭时效期间外,就日常生活行为规定了短期消灭时效期间,但《德国债法现代法》在缩短普通消灭时效期间的同时删除了短期消灭时效期间的规定。德国民法这种改革的原因,主要在于时效期间的多样性(不同长度以及起始时间)以及不同时效期间之间存在着许多价值矛盾。(47)同时,在统一实体法的背景之下,《欧洲合同法原则》和《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仅规定了普通消灭时效期间(3年),例外的情形只有一种,即经判决确认的权利的10年消灭时效期间,意在简化普通诉讼时效期间。(48) 其三,时效期间的起算标准。从立法例上看,消灭时效期间的起算主要有两种标准:一是主观标准,即时效从受害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可以行使或权利受侵害时开始起算。例如,《法国民法典》第2224条规定:“对人诉讼(债权诉讼)或者动产诉讼,时效期间为5年,自权利(持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可以行使权利的事实之日起计算。”《俄罗斯民法典》第200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当事人获悉或应当获悉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二是客观标准,即时效从请求权可得行使之时开始计算。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935条规定:“消灭时效自权利可以主张之日起开始。”《日本民法典》第166条规定:“消灭时效,自权利可以行使时起进行。”《西班牙民法典》第1969条规定:“关于诉讼的各种时效,在无另外特别规定的情况下,自可以行使之日起计算。”当然,各国民法采取的上述标准并不是绝对的,通常也会根据具体情形兼采另一个标准。同时,时效期间的起算标准通常也与普通消灭时效期间的长短有关。一般地说,普通消灭时效期间较短的立法,期间起算标准通常采取主观标准,如法国、俄罗斯,时效期间分别为5年、3年;而普通消灭时效期间较长的立法,时效期间起算标准通常采取客观标准,如意大利、日本、西班牙,时效期间分别为10年、10年(20年)、30年(20年)。 其四,时效期间类型之间的协调。从域外立法例来看,凡是普通消灭时效期间较长的立法,大都以短期消灭时效期间给予配合。例如,《意大利民法典》规定的普通消灭时效期间为10年,同时又规定大量的1年至5年不等的短期消灭时效期间以及6个月至3年不等的推定消灭时效期间;《日本民法典》规定了10年和20年的普通消灭时效期间,同时又规定了1至3年的短期消灭时效期间。相反,凡是普通消灭时效期间较短的立法,大都以长期消灭时效期间予以配合,例如,《法国民法典》规定了5年的普通消灭时效期间,同时又规定了最高30年的长期消灭时效期间;《德国民法典》规定了3年普通消灭时效期间,同时规定了30年最长消灭时效期间。 从我国现行法的规定来看,《民法通则》规定了普通诉讼时效期间(2年)、特殊诉讼时效期间(1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20年),而且在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和特殊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上采取了主观标准,即“诉讼时效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第137条第1款),(49)而在最长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上采取了客观标准,即诉讼时效“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第137条第2款)。综合上述四个因素,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简化诉讼时效期间的类型,在已有时效立法传统的基础上,以较短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再配合以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具体来说,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规定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此外再规定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即可,不必规定短期诉讼时效,因为在普通诉讼期间短期化的趋势下,没有必要再规定更短的诉讼时效期间。如果确有必要规定某种短期诉讼时效期间,可以由其他法律加以规定。 关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世界各国立法呈现出越来越短的趋势。(50)例如,在罗马法中,普通消灭时效期间为30年。(51)法国、德国民法典于制定之初继受了罗马法的规定,将普通消灭时效期间规定为30年。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通讯日趋发达,人们的权利观念也日趋增强,30年普通消灭时效期间已显得过长。因此,法国、德国在修改民法典时均缩短了普通消灭时效期间。例如,《法国民法典》将原30年时效期间(原第2262条)缩短为5年(第2224条);《德国民法债法现代化法》将原30年时效期间缩短为3年(第195条)。其他国家在民法典中也在不断缩短消灭时效期间,如瑞士、荷兰、希腊、俄罗斯等。(52)但是,我国现行法将普通诉讼期间规定为2年,通说认为这一期间过短,对权利人的保护是不足的。(53)因此,在我国,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不但不能缩短,而且还应当适当延长。从国际经验来看,关于普通消灭时效期间,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其界定在2至6年之间,这已经成为共识。(54)例如,《欧盟产品责任指令》《欧洲合同法原则》《欧洲民法典示范草案》均将普通消灭时效期间规定为3年。笔者认为,将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规定为3年是合适的。在采取较短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况下,期间起算标准应当采取主观标准,即应当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关于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各国立法规定不一,有的规定为20年(荷兰、阿根廷等),有的规定为30年(法国、德国等)。我国现行法规定为20年,且期间起算标准采取客观标准。笔者认为,在现代社会,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规定为20年足矣。 ①参见王利明:《我国民法典重大疑难问题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梁慧星:《民法总论》(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46页;徐国栋:《民法总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94页。 ②参见朱岩:《消灭时效制度中的基本问题》,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2期,第157页。 ③参见杨立新主编:《中国百年民法典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616页。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http://www.civillaw.com.cn/zt/t/?29169,访问日期:2015年6月20日。 ⑤参见温世扬、廖焕国:《民事时效立法简论》,载王利明、郭明瑞、潘维大主编:《中国民法典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页。 ⑥参见王鹏:《论取得时效制度及其立法例》,载《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15页。 ⑦参见汪渊智:《我国民法诉讼时效制度之构想》,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第58页;刘保玉、王仁印:《论取得时效的制度构建》,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2期,第50页。 ⑧参见汪渊智:《我国民法诉讼时效制度之构想》,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第58~59页。 ⑨因取得时效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故我国未来民法典规定取得时效的具体理由,本文不予讨论。 ⑩参见汪渊智:《我国民法诉讼时效制度之构想》,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第58页。 (11)参见朱岩:《消灭时效制度中的基本问题》,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2期,第157页。 (12)参见朱岩:《消灭时效制度中的基本问题》,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2期,第158页。 (13)参见[日]近江幸治:《民法讲义Ⅰ·民法总则》(第6版补订),渠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8页。 (14)参见房绍坤:《关于民法典总则立法的几点思考》,载《法学论坛》2015年第2期,第12页。 (15)参见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1页。 (16)朱岩:《消灭时效制度中的基本问题》,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2期,第160页。 (17)参见[日]我妻荣:《新订民法总则》,于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402页。 (18)参见李永军:《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8页。 (19)例如,用益权因用益权人或以其名义行使的人在10年期间没有行使而消灭(第621条),地役权因10年不行使而消灭(第753条)。 (20)参见刘彤涛:《关于诉讼时效名称问题之检讨》,载《中国司法》2006年第10期,第99~101页;赖怡芳、王晓丽:《德国新债法时效制度变革及其启示》,载《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34页。 (21)参见许中缘、屈茂辉:《民法总则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79~480页。 (22)参见王利明:《我国民法典重大疑难问题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页。 (23)尹田:《我国诉讼时效之立法模式评价》,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2页。 (24)朱岩:《消灭时效制度中的基本问题》,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2期,第179页。 (25)参见郭明瑞:《诉讼时效的效力问题》,载《法学》2008年第9期,第77页。 (26)参见《大清民律草案》总则编第七章第一节、《民国民律草案》总则编第五章、《中国民国民法》总则编第六章。 (27)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页;黄阳寿:《民法总则》,台湾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378~379页;郑冠宇:《民法总则》,2012年自版,第443页。 (28)参见郭明瑞:《诉讼时效的效力问题》,载《法学》2008年第9期,第73页。 (29)参见郭明瑞:《诉讼时效的效力问题》,载《法学》2008年第9期,第77页。 (30)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95条、《瑞士债务法》第127条和第142条。 (31)参见《日本民法典》第167条、《韩国民法典》第162条、《埃及民法典》第374条。 (32)参见《俄罗斯民法典》第195、199条。 (33)参见《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1845条、《智利民法典》第2514条、《菲律宾民法典》第1139条。 (3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中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第3条规定:“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19条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35)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 (36)参见高圣平:《诉讼时效立法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学论坛》2015年第2期,第33页。 (37)关于《民法通则》规定的“20年期间”的性质,理论上存在着最长诉讼时效说、除斥期间说、最长保护期限说、最长期限制说等不同的主张。参见霍海红:《“20年期间”定性之争鸣与选择》,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38)参见高圣平:《诉讼时效立法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学论坛》2015年第2期,第32页。 (39)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4页;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第184、185条。 (40)参见梁慧星(课题负责人):《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0、41页。 (41)参见高圣平:《诉讼时效立法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学论坛》2015年第2期,第33页。 (42)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43)参见[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英]埃里克·克莱夫:《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全译本1~3卷),高圣平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999页。 (44)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0页;梁慧星:《民法总论》(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44页;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28页。 (45)参见[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英]埃里克·克莱夫:《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全译本1~3卷),高圣平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2页。 (46)参见高圣平:《诉讼时效立法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学论坛》2015年第2期,第32页。 (47)参见[德]汉斯·布洛克斯、沃尔夫·迪特里希·瓦尔克:《德国民法总论》(第33版),张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7页。 (48)参见高圣平:《诉讼时效立法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学论坛》2015年第2期,第33页。 (49)有学者认为,我国法采取的是主客观标准。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45页。 (50)参见[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英]埃里克·克莱夫:《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全译本1~3卷),高圣平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3页。 (51)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页。 (52)参见朱岩:《消灭时效制度中的基本问题》,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2期,第167页。 (53)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39页。 (54)参见[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英]埃里克·克莱夫:《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全译本1~3卷),高圣平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3页。标签:诉讼时效论文; 法律论文; 民法典论文; 债权请求权论文; 债权诉讼时效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取得时效论文; 抗辩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