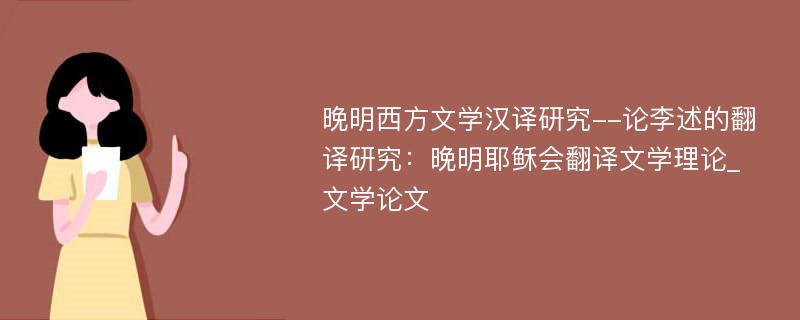
晚明西方文学汉译研究的扛鼎之作——评李奭学著《译述:明末耶稣会翻译文学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耶稣论文,明末论文,文学论文,之作论文,汉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6-6101(2013)-03-0143-5
明清间以天主教传教士为主要介质而展开的中西文化交流,在最近的20余年时间里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探讨的触角日益繁密而深广,人们发现,早在三个多世纪以前,传教士在引入天主教义的同时,也把西方的天文、数学、机械、水利、地理、医学、生理以及哲学、逻辑、伦理、文学、音乐、美术等几乎所有的知识类别全都带到了华夏帝国,其中,西洋火炮改变了明清之际国运鼎革的走向,①而翻译的西方天文学则以“崇祯历书”之名融入了中国百姓的寻常日用;不仅如此,借助新发掘的材料我们还知道,号称闭关锁国的有清一代,其实直至乾隆晚期仍然对西方存有较深的了解,即使在最封闭的嘉庆中期(宫廷及钦天监的耶稣会士此时被驱逐殆尽),中西间的商贸往来也未全然断绝。康、雍、乾三帝的身边始终活跃着传教士的身影,他们又都偏好西方的器物:康熙帝即位十余年之后,在养心殿专辟造作处,仿做各类西洋物品,他甚至多次表达对于西洋舶来之钟表的鄙夷。他所言确乎不虚,因为养心殿的瑞士籍耶稣会士乃当时世界最顶尖的钟表制造师;他拥有的各种西方奇巧,充盈而繁杂,让见过大世面的俄罗斯公使也惊诧不已。②至于乾隆皇帝,他不惟喜好西洋的钟表、玻璃、望远镜、眼镜、锦缎、建筑、美术、音乐、家具灯饰、犬马家禽等器物,③而且更曾酷嗜南美“淡巴菰”(烟草),并佩戴法国贵族常用的假发来让郎世宁等刻画描摹;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王致诚(Jean D.Attiret)、艾启蒙(Lgatuis Sickeltart)、安德义(Joannes D.Saslusti)等绘制的《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均远达欧洲制成铜板雕刻,可以说,中西间的交往在乾隆中期是相当畅通的。于此可见,真正的封闭并非器物往来的断绝,而是心灵与精神世界的“自我迷醉”与“拒绝变更”,它阻断了国人眺望世界的视线,导致对于“他者”的“视而不见”和“听若罔闻”。
在上述所有已然得到开掘的论域中,有一个论题堪称特别,这就是西方文学的汉译及其研究的问题。在我国学术界,除了明末耶稣会士金尼阁(Nicholas Trigault)等人翻译的文学经典《伊索寓言》(主要见于《况义》、《天主实义》、《七克》等书)及高一志(Alfonso Vagnone)翻译的西方修辞学《譬学》得到过一些重视(如周作人、戈宝权等人之关注《况义》,汉学家许理和之研究《譬学》)之外,其他部分就极少有人注意。可以说,持续时间达200余年的明清中西文化交流所蕴含的文学交往史实,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一直就是个“盲区”。④而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李奭学先生算是一个例外:他20多年来全心用力于此,在这一领域的开拓、耕耘以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在全球范围内也堪称空谷足音、独领风骚,尤其是在所谓“宗教文学”或“基督教文学”层面涉及的西方文学作品之汉译研究方面,他的许多探索,仍然可称“孤明先发”。因此,其《中国晚明与西方文学——明末耶稣会古典型证道故事考诠》(台湾“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公司联合出版,2005年;简体修订本由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出版)甫一问世,便获如潮佳评,两年后更使著者获得中央研究院最高学术荣誉——“深耕计划奖”;7年之后,李教授又推出力作《译述:明末耶稣会翻译文学论》(以下简称《译述》)。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赞誉此作“在一个几乎是独自开拓的领域内”,对晚明基督教翻译文学“作出了全面深入的探索,是一部廿多年内罕见的学术力作”[1:封底]。就晚明西方文学之汉译研究而言,李氏此著的确堪称扛鼎与奠基之作。它向这一巨大“盲区”所投射的,虽然常常是“孤明”之光,但也足以让我们清楚看到,晚明东传的西方文学(翻译文学)不仅自身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提醒我们,至少近代中西文学交流史理应重写。这里,笔者不怕谫陋,试就《译述》一书之方法路径与观点见解等作一归纳,不当之处,祈著者及学界同仁给予批评指正。
笔者以为,《译述》之最独特而又讨巧之处就在于采用了“翻译文学研究”的切入视角。这一视角,不仅把晚明入华的一些“译作”(表现形式多样,除了“授”、“述”、“口授”、“口译”、“口说”、“译述”之外,还有“演”、“译义”、“达辞”、“译叙”、“创译”甚至“撰”、“撰述”等⑤)从天文、数学、神学、哲学等译述中区分出来,并获得了新的“文化身份”(文学)和新的“知识”蕴涵,而且还使得著者在西方文学中译史上相对容易地发现了众多的“第一次”,如:中国第一次集成的欧洲歌词集子、第一次出现的欧洲传奇小说、第一次译出的欧洲上古与中世纪的圣传、第一次翻译的欧洲修辞学专著、第一次移译的欧洲灵修小品集、第一次中译的英国诗,等等,著者对它们都有深入的探讨。可以说,单就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第一”而言,《译述》的学术史价值就不容小觑。此以第一首中译“英”诗为例:钱钟书先生在1950年代曾提出,威妥玛(Sir 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与董恂合译之美国诗人朗费罗(H.W.Longfellow,1807-1882)的《人生颂》(A Psalm of Life)乃首见中译“英诗”与“西洋诗”,时在1864至1872年间;2005年,沈弘与郭晖推翻钱说,以为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1796-1857)所译密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论失明》(On His Blindness)才是最早中译的英诗,时在1850年。李奭学先生则通过对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637年译《圣梦歌》的细致寻绎与辨析,指出第一首中译“英”诗应当追溯到晚明,这样一来,最早中译“英”诗的时间一下子便上延了两百余年[1:311]!对于其他众多的“第一次”,李教授本人大都拥有学术制高点与话语权,故迄今为止学界对此少有异议。笔者以为,中国学界若再撰写中西文学关系史或西方文学翻译史之类的著述,则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及《译述》之类的优秀专题研究成果,是断然不可回避的。
其次,晚明耶稣会士的“文学翻译”,很少一对一的“完璧重现”,而常常夹译夹述,甚至改译、改写,这样一来,“底本”的寻找便格外困难,若非精通西方上古及中古文学便无由措手。如利玛窦(Matteo Ricci)的《交友论》,中国学者本以为是利氏应建安王朱多之约而自撰之“作”,后经德礼贤(P.M.D'Elia)、方豪以及米涅尼(Filip Mignini)等人钩抉沉隐,众人方才明白,原来此著大多出自多明我会修士莱申特(Andre de Resende,1498-1573)《金言与示范故事集》(Sententiae et exempla)以及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的著述,属于“译作”(尽管也包含一些改译与改写)。而《译述》的重头工作之一,就是在翻译文学领域接着方豪等人“讲”,将中译之西方文学一一回置于西方文化语境之下予以考辨和诠解——不过,结果往往不是找出某个精确的对应“底本”,而是一个包含了诸多衍本的“底本簇”或“底本的家族系谱”。如龙华民(Nicholas Longobardi)译《圣若萨法始末》,李教授虽然认为其所本之《巴兰与约撒法》(Barlaam and Ioasaph)主要出自《圣传金库》(Legenda aurea)的拉丁文系统,但此外,它另有至少60种不同译本以及不同文类的改写本,而《巴兰与约撒法》本身译自六七世纪乔治亚文的《巴拉法里亚尼》(The Balavariani),正是后者才使本属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的故事,在流传中成为天主教的“圣传”;再如艾儒略译《圣梦歌》,自云系“粗述圣人伯而纳一梦”而得(《圣梦歌·序》,明崇祯十年版抄本,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朗编号:6884),故有人称此作乃艾氏自撰。但《译述》遍考群籍,不惟在众多的“身体与灵魂之辩论诗”中找出《圣伯尔纳的异相》、《菲利普的异相》、《福尔伯特的异相》或《冬夜寂静时》为“研究者遍寻不获的《圣梦歌》的原本”[1:317],更指出,此原本所祖的《身体与灵魂的争辩》其实最早出自当时位居边陲的英格兰或不列颠,是一首“英”诗[1:315-317];再如1632年高一志译就的首部西方修辞学专论《譬学》(上下卷),其中有近600条格言范例,其出处虽然汗漫难考,但《译述》将其譬喻方法一一考出,并结合文中例言予以分析、诠释和总结,⑥这对于今日修辞学史的重新反思与认知,意义相当重要。
《译述》在考出“底本”之后,往往意犹未尽,于是对译作中诸多“意象”或“典故”又作出进一步的溯源和解析。如利玛窦的《西琴曲意八章》所云“(上帝)使日月照而照无私方”、“肩负双囊”、“观他短乃龙睛,视已失即瞽目”等,《译述》将其置于西方典籍之中予以考索,所指明的出处,除开《圣经》之外,更有《沙漠圣父传》、《伊索寓言》以及贺拉斯的《歌谣集》,使译作中乍看不甚了了的意象或“说法”均得到明确的诠解;⑦此外,《译述》还对译本中一些看似寻常、而且中土早已有之的概念予以浓墨重彩的阐析,读过之后我们便会发现,原来传教士在以中译西的诸多概念里已悄悄塞进了许多异质的蕴涵。如“圣人”一词:它在宋明理学的语境中几乎专指孔子,然而在利玛窦、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高一志等人的译述中,“圣人”却指天主教圣徒。高一志所译《天主圣教圣人行实》收录74位圣人行传(包括“圣女”12人),这些人之所以堪称典范,主要的衡量指标在于,在“三绝”(绝财、绝色、绝意)之后均能皈依基督,追寻“永生”;不过饶有趣味的是,《行实》以相当多的篇幅表现了在趋向成圣的过程中圣人们与欲望(特别是情欲)的抗争。《译述》指出,这是一种“神圣的不完美”(holy imperfectness)[1:212],与宋明理学之圣人观迥异。再如“梦”一词:《译述》先将“梦”置于希腊、罗马及中国传统之中辨析其蕴涵,再指出天主教高唱“圣梦歌”,其鹄的在于,通过“梦中的异相”或“灵肉的辩诘”让人领悟“人生在世之日,惟一天主鉴之;谢世之日,唯一天主判之,有永赏永罚之报”的天学“正道”,与国人常借“人生如梦”来寻求解脱与达观态度的在世立场有较大差异。⑧除了“圣人”与“梦”之外,《译述》还对“灵魂”、“情”、“任”等概念用墨甚多,并力求在蕴涵辨析中彰显中西文化与观念的差异,显示出上佳的哲学与神学涵养。
再次,《译述》的“翻译文学论”,其基本性质属于所谓“译介学”或文学翻译的文化研究,换言之,不是针对耶稣会翻译的各种现象(正译与错译、直译与意译、全译与漏译、增删与改写、忠实与叛逆,等等)来作语法与语言上的评判或纠正,而是以上述现象为客观事实来进一步探讨其文化成因与发生机制。有人将耶稣会士的翻译譬喻为“文本的诠释性外科手术”(exegetical surgery on their texts),他们随手使用“诠释的工具箱”(toolkits of interpretation)来对“原本”进行切割、改造、填充甚至移植、生造,很少做全然忠实的移译[1:26-27]。而支配这种“手术”的力量,因“手术”与“翻译”往往都在“静默”中完成,故《译述》借用斯皮瓦克(C.Spivak)的术语,称之为“静默的暴力”(violence in silence)。在《译述》看来,耶稣会翻译文学中随处可见的改写、改编、衍述、填补、删削以及文体上的归化等现象,均可以斯皮瓦克之“翻译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来探析与诠释。实际上,《译述》着墨最多者正在于此,著者出入于历史与神学、考证与论辩之间,把研究的译本还原到特定的时空情境之中,在洞悉译者彼时所处之复杂环境与人脉交往的同时,又对照原本,掌握改窜与增损之诸关节点,最后以神学、哲学、文化等各种知识予以透视观审,使潜藏于译本之下的深层成因与动机一一水落石出、明白彰显,显示了极其深厚的学术功力和知识涵养。因篇幅之限,以下仅择取改译、改写与归化等个案简述如次:
改译与改写现象。李教授指出,晚明耶稣会士在翻译时常常奔窜腾挪,改换攻击的靶子,将矛头指向佛道二教,“翻译”因此也成为意识形态间无声角力的战场。利玛窦、庞迪我等在早期护教著述里引述西方典籍,偶用此类伎俩,而龙华民的《圣若萨法始末》则在译作中直接改窜腾移,如“死神的号角”、“小鸟之歌”等故事,最初的灵感源头本属梵文本《五卷书》,在流衍之中它们曾先后被用于攻击希腊、北印度及埃及人的宗教信仰,至此则枪头一转,被龙华民用来打击佛教,“日暮焚香,求神庇佑”的“信望佛者”,被视为以“假”为“真”的偶像崇拜;说罢“小鸟之歌”等故事,龙华民更借若萨法之口,将“福音书”中著名的“撒种之喻”引入译本,这种做法便非一般的改译与改写,而是堪称改编与创作了。金尼阁踵武其后,也曾播弄此种“翻译的政治”,在《况义》之中,把偶像崇拜者的“神像”全都改写成“佛教”加以讥嘲。⑨
归化现象。《译述》注意到,阳玛诺(Emanuel Diaz jr.)译《轻世金书》一反原作(即耿稗思[T.à Kempis]之《遵主圣范》[Imitatione christi])的简洁易懂,而采用晦涩难读的“《尚书》体”,而艾儒略译《圣梦歌》则采用七言诗体,等等,这些都属于文体上的归化;此外,有些西方词汇,如“龙”(dragon),本来就有负面含义(是“魔鬼”的化身),但在中国却是吉祥之物,故高一志等在翻译时也采用归化的方式来处置:要么在“龙”之前加上“毒”字,要么就干脆避开,译之为“巨蟒”、“蝮蛇”,⑩这种情形则属于修辞上的归化。除开这些形式上的归化,更有神学与思想上的归化,如利玛窦把“Deus”(拉丁文“天主”)译为“天主”,并以之与中国上古文献的“上帝”相匹配的做法就是显例。著者对此认知有清楚而深入的了解(可参阅其《中国晚明与西方文学》一书),但也许是因为学界之相关论述已相当丰赡,故《译述》对此着墨不多。无论如何,不管归化的表现形式有何种差异,其动机却大抵相似,即,都是试图通过主动附会译入语文化来减少传教的阻力。
最后,还有必要再强调《译述》在材料引证上的特点。笔者曾著文论及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问性质,必然要求学者掌握数种外国语言。(11)在汉语学界,凡于此大有所成者大抵如此。笔者以为,即使把李奭学教授的系列著述置于近百年中外关系史的脉络之中来考量,他也堪称其中之佼佼者。以《译述》为例,此书征用外语文献达450种左右,语种除学界常用之英、法、德、日诸文之外,更有古希腊文、拉丁文以及中古法语、中古英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等。原文材料的直接使用,不仅裨益于学术视野之拓宽、史识与哲思之深化,而且更能增进义理见地之公信度。《译述》行之有效地体现了这些优点,它的成就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①陈寅恪先生曾指出,西洋火器本为明之所长,后竟转为明之“厉阶”,此事“实为明清兴亡之一大关键”(详见氏著《柳如是别传》上册,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59页;牟润孙先生也较早便指出这一点,认为徐光启苦心策划制造的新武器,大部分辗转落入满人手中,成为明与后金之战争中胜负转变的重大关键。详见氏撰《明末西洋大炮由明入后金考略》,收入氏著《注史斋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31页)。陈、牟二人之后,研究此一专题的成果不少,其中尤以黄一农先生为翘楚,其曾著专文多篇以究其原委。
②参见[意]马国贤著《清廷十三年》,李天纲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99页。
③参见鞠德源:《清代耶稣会士与西洋奇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1-2期,第3-16、13-23页。
④许理和甚至认定,除《譬学》之外,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就没有翻译过其他西方“文学”。详见《译述》第20页。
⑤详见该著第16页。
⑥详见该著第255-309页。
⑦详见该著第35-58页。
⑧详见该著第343-355页。
⑨详见该著第80-89页。
⑩详见该著第226-229页。
(11)详见拙文《评〈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第171-1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