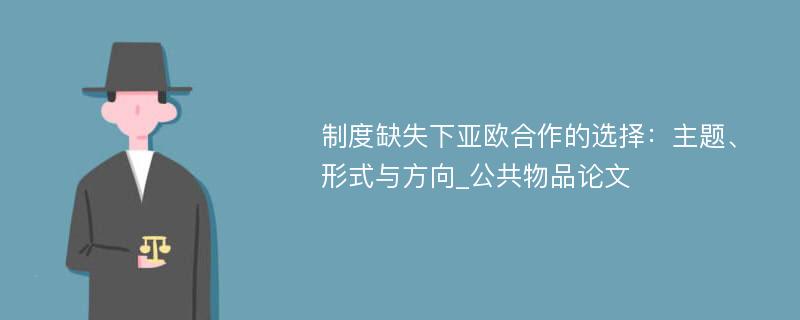
制度匮乏下亚欧合作的选择:议题、形式和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欧论文,议题论文,匮乏论文,形式论文,方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6年首次召开以来,亚欧会议(ASEM)至今已走过15年的发展历程。作为冷战结束后建立的亚洲与欧洲之间重要的跨区域合作方式,亚欧会议的非制度化现象、合作议题和方式等一直备受学界关注。近年来,随着全球公共问题的凸显,亚洲和欧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共同威胁;同时,随着亚洲新兴力量的崛起,亚欧力量对比已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新成员的加入,成员数量进一步增加。这些变化既增加了亚欧对合作的需求,同时也加大了合作的难度。尽管缺少制度安排、保障和约束,亚欧会议迄今仍是亚洲与欧洲之间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政府间论坛,因此,亚欧会议的存在具有某种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这种合作模式也面临探讨新议题、调整合作方向、提升合作水平的新要求。在制度匮乏的现状下探讨亚欧如何实现有效合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国际制度的两种类型和国际合作的条件
制度是国际合作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国际制度的产生是由于“行为者希望避免独立决策”;一旦国家之间产生共同的而非单个的决策行为模式,国际制度就形成了。① 行为体之所以具有避免独立制定政策的需要或动机,是因为其在单纯的自我利益驱使下进行的互动会使各方陷入共同利益的困境或共同背离的困境,这两类困境构成了国际制度形成的基础。为了避免行为体出于个体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导致次优结果,合作性国际制度得以形成;为了避免出现行为体最不希望的结果,协调性国际制度应运而生。这两类制度模式有着各自的生成逻辑,契合不同形式的合作。
合作性国际制度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其出现和维持依赖国际公共物品的充足供应。在霸权稳定论者看来,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转需要某个国家承担“公共成本”,为国际经济合作提供某种“稳定器”。② 集体行动研究的集大成者奥尔森强调,正是国际公共物品充当了“稳定器”的角色。霸主为国际社会提供国际公共物品,从而成为国际社会的领导者。而在霸主衰退之后,国际合作的持续和国际秩序的维持则依赖于霸主创设的一系列国际制度,这种合作即所谓的“霸权后合作”。③ 可以说,合作性国际制度产生和存续的根源是霸权国的存在及其提供的国际公共物品和创立的国际制度。
协调性国际制度则建立在避免共同背离的基础上,其建立只需要行为体进行政策协调,形成惯例和标准。惯例的形成和标准的确立不像国际公共物品那样依靠体系中的霸主提供,行为体可以通过各自调整政策来避免遭遇共同厄运。因此,解决共同利益困境的国际机制在于霸权和霸权后合作,即依靠强权的领导及其提供的国际公共物品;而解决共同背离困境的国际机制在于行为体的协调,即依靠惯例或标准。
合作的出现是由于“行为体通过政策协调过程,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其他行为体实际或预期的偏好”。米尔纳将合作产生的路径归为三种形式,分别是默契型合作(tacit)、协商型合作(negotiated)和强制型合作(imposed)。④ 默契型合作不需要行为体进行交流沟通或达成明确的协议就可以实现,这种合作纯属巧合,在国际关系中是鲜见的。协商型合作需要行为体经过详细明确的谈判过程而形成,国际关系中的大多数合作都是通过这一路径建立的。强制型合作由强势行为体推动,强权在迫使他者改变政策的同时,如果自身也能调整政策以实现共同利益,合作便可以产生。如霸权稳定论中的霸权合作,是由于霸主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并承担其成本,从而推动了合作的形成。概而言之,除了巧合这种偶然情况,合作主要由霸权主导或通过行为体协商产生。
战后大多数国际合作是在霸权的主导下形成的,在霸权衰退后则由霸权创建的制度来维护,而在霸主缺位和制度匮乏之下的国际合作如何产生和发展,则是亚欧合作需要回答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冷战后没有霸权参与且缺乏现成国际制度的合作诉求越来越强烈,美国地位的下降与地区性协议重要性的上升呈正相关关系。冷战后一些区域、次区域组织发展的现实,尤其是亚欧会议本身的发展,都说明霸主缺位和制度弱化条件下的国际合作是可能的;另一方面,亚欧会议也引出如下问题:塑造此类合作的要素是什么?这些要素会形成怎样的合作模式?行为体如何进行合作?什么样的制度对霸权缺失和制度匮乏下的合作更加有效?
阿克塞尔罗德认为,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理性行为体之间的合作是可能的,而促进合作的最有效策略是“一报还一报”(tit-for-tat)。⑤ 根据阿克塞尔罗德和基欧汉的研究,有三大因素影响合作,即利益互惠、未来预期和行为体数量,这三个要素同样也有助于理解合作的成败。⑥ 首先,利益互惠可以诱使行为体进行合作,但互惠未必导致合作,在经济领域也不例外。在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型中,行为体的利益冲突越大,选择背叛的可能性就越大。合作产生的共同利益不能消除行为体对相对收益的关注和由此引起的分歧。其次,对未来的预期可能促进合作。如果预期收益会超过当前收益,那么背叛的可能性就会减少,合作的机会则会增加。国际制度体现和影响着行为体的预期,因为制度确立了规则、准则和对破坏规则行为的制裁或报复。制度创造预期,从而增加了合作的可能性。最后,行为体数量也会影响合作的质量和成败。行为体的数量越多,对不合作者或背叛者实施惩罚和报复的难度就越大。
斯通等学者设计了一个由多个国家贡献公共物品的多次博弈模型来研究国际合作,就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对国际合作的影响做了定性分析,涉及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包容性和排他性,以及合作的机制化等问题。⑦ 他们提出,第一,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之间存在替代性,合作范围越广则深度会受影响,合作越是密集则范围必然狭窄。第二,权力分配对国家如何选择合作具有深远影响。权力分配和国际合作的复杂关系表现为:强大的领导国会形成范围较小和公共物品丰富的联盟,并建立排他性机制,因此霸权往往选择排他性合作;而相对弱小的领导国会选择建立更宽泛的和公共物品较少的联盟,这样的联盟更倾向于开放性的多边合作。第三,制度是一种投资,制度通过界定明确的规范、惩罚违规者和提供公正的司法程序来推动博弈的进展。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影响国际合作和国际制度的成败与效果的主要因素有:利益互惠、未来预期、行为体数量和权力分配。利益互惠和未来预期直接关系到能否形成合作,但是利益互惠不能消除行为体对相对收益的关注,特别是在高政治领域。而脱离现实的过高收益预期同样不利于合作,除非有制度的保障和约束,否则既不能避免、更无法惩罚合作中的欺骗行为。因此,利益互惠和未来预期只是合作的必要条件,不能充分保证合作的程度和质量。行为体数量通常决定合作的难易程度。权力分配则决定合作的主导者。行为体数量和权力分配这两个要素结合起来决定合作的特征和性质,如是松散还是紧密,是开放性的还是排他性的,是论坛的形式还是机制的形式,以及制度供应是充分还是匮乏等。下文将运用这四个要素解释亚欧合作中国际制度匮乏和合作不足的原因,并分析制度匮乏条件下亚欧合作的可能性。
亚欧合作的现状及其原因
中外学者普遍认为,亚欧会议存在制度匮乏、“虚多实少”、“松散”等问题。⑧ 目前亚欧合作的程度不高,实质性成果较少,作为亚欧合作三大支柱的政治对话、经贸合作和社会文化交流等领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合作虚、机制弱”的现象。
首先,政治对话最缺乏相应的国际机制。亚欧会议为成员国提供了一个论坛,供成员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以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随着交流的深入,政治对话的议题从务虚到务实,从人权、价值观扩展到环境、能源、非传统安全、国际金融秩序等领域,各方已在打击恐怖主义、移民与跨国犯罪、保护环境等问题上形成共识。⑨ 但是,亚欧政治对话既没有成员提供的公共物品,也不存在合作性国际制度。即使是在第二届亚欧峰会上正式通过的作为亚欧合作一般原则的亚欧合作框架(AECF),也只是一份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政治文件。⑩ 在一些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上,亚欧政治对话也没有制定出相应的规范、惯例或标准之类的协调性制度。比如,亚欧尚未在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上形成共同接受的标准,在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和改革方面也没有形成可操作的方案。由此可见,亚欧政治对话既缺乏合作性国际制度,也缺少协调性国际制度。
其次,经贸合作缺乏自身的多边贸易机制。目前,亚欧会议成员国的经贸合作仍主要依靠世界贸易组织建立的多边贸易体制规则,至今仍未建立跨区域的多边贸易制度,亚欧会议在创立之时作为亚欧经贸“多边协调工具”的预期功能也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亚欧之间、特别是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摩擦频频发生,欧盟与东亚国家也尚未就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达成协议,而且近年来,国际贸易大环境中存在一些不利于亚欧签订多边自由贸易协议的因素,诸如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失败,双边贸易协议备受推崇,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等。双边自由贸易协议正逐渐在亚欧会议成员中占据一席之地,如欧盟致力于与日本、韩国和印度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中国已同东盟建立双边自贸区等。亚欧会议成员对排他性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偏好,在根本上有碍跨区域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相对而言,社会文化交流是亚欧合作中制度化程度最高、合作成果较为显著的领域。常设机构——亚欧基金会(Asia-Europe Foundation)(11) ——也是亚欧会议唯一的实体机构,负责开展亚欧间的学术、文化和人员交流活动。亚欧基金会下设《亚欧杂志》(Asia Europe Journal),推动亚欧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多学科和跨文化研究。亚欧会议成员通过了《亚欧会议文化与文明对话宣言》,制定了亚欧文化合作中长期计划。为亚欧成员讨论敏感问题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对话平台。此外,亚欧会议成员还以自愿捐款的方式成立了旨在帮助亚欧国家加强能力建设,提供技术援助和克服金融危机的亚欧信托基金。
综上可见,亚欧会议在制度匮乏条件下的合作现状是:政治对话最缺乏国际制度;经贸合作仍在依靠世贸组织的多边机制,跨区域多边自由贸易机制尚未形成;社会文化交流的合作成果最丰,已具备一定的制度基础,但尚不足以“溢出”带动整个亚欧合作制度化。虽然非制度化、非正式和松散的特征始于亚欧会议创建之时,有其历史渊源和传统原因,但仍有必要对制度匮乏与合作程度低给出理论解释,从而为提升亚欧合作水平找寻路径。
根据影响合作的四个因素,目前亚欧会议制度匮乏、合作程度低和成果少的原因在于:利益互惠的推动力单薄,预期收益目标空洞,没有霸权的参与并先天缺乏合作性国际制度,成员数量众多增加了协调性国际制度的成本。
第一,利益互惠的溢出效应不足。虽然亚欧经贸交往越来越密切,但都弱于各国与美国的贸易联系。亚欧贸易还容易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制约,如人权问题、环保标准等,亚欧贸易摩擦时有发生。因此,亚欧经贸互惠尚未对其他领域产生外溢效应,不足以提升合作的质量和推动机制化建设。
在不直接涉及经济关系的议题上,利益互惠更加稀缺。在环境、气候变化等共同威胁面前,由于成员的发展程度不同,利益诉求存在显著分歧,因此难以找到利益互惠的契合点。利益互惠尚未从共同威胁中剥离出来,成员只能在避免共同厄运的层次上展开协调,难以上升到为谋求共同利益的合作。
第二,在战略和经济上制衡美国的预期收益目标空洞。亚欧会议的建立是冷战后世界经济新秩序呈现“三极结构”的结果。(12) 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三大经济体中的北美已经和东亚建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美国也与欧盟在新跨大西洋进程(New Transatlantic Agenda)下形成新的跨大西洋关系框架,相比之下,欧盟和东亚的联系最弱。(13) 在跨大西洋联盟主导的世界经济中,欧盟有在地缘经济上被边缘化的潜在担忧,这一忧虑成为欧盟推动亚欧会议的主要动机。在1994年制定的《亚洲新战略》(New Asia Strategy)中,欧盟明确表达了纠正三大经济体之间关系不平衡、加强自身在亚洲的经济存在的意图。东亚国家也有借助欧盟平衡美国在东亚影响的强烈愿望,认为通过亚欧会议可以帮助本地区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外交关系的多元化,减少经贸上对美国和日本的过度依赖,(14) 欧洲单一市场还会为东亚国家提供巨大商机。由此可见,推动亚欧合作的共同利益诉求是在战略和经济上平衡美国和加强世界经济体系三边结构中的最弱环节。(15)
倘若推动亚欧合作的预期战略收益是制衡美国在东亚的超强影响,那么,除非建立政治同盟,否则这种合作恐难实现双方期待的战略目标。而东亚地区要真正步入区域政治合作进程,还有很大距离。(16) 在亚欧尚未建立跨区域自由贸易区的前提下,预期经济收益只能依靠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的规则得以保障,而且难以屏蔽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排他性双边贸易协议的消极影响。事实上,欧盟和美国已于2007年建立了跨大西洋经济理事会。(17) 此外,东亚和欧盟也难以在经贸方面避免美国带来的消极影响。一旦美国爆发经济危机,欧盟和东亚国家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成为美国政府滥印美元和操纵美元贬值的直接受害者,甚至被迫为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买单”。在这种情况下,制衡美国的预期收益目标不免显得不切实际。
第三,亚欧成员力量对比状况限制了制度的形成。亚欧会议的成员由欧盟及其成员、东盟及其成员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组成,成员中没有具备超强权力优势的国家,因此亚欧合作先天缺乏霸权的参与,也没有霸主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创立的国际制度。成员之间权力分散,没有绝对的权力中心,缺乏核心国家领导合作,自愿式合作就成为亚欧之间重要的合作路径。此外,成员间力量对比差异大也使得他们在重要和敏感问题上存有分歧,难以采取集体行动。
第四,成员数量众多,增加了制度形成的难度。成员的多少与辨别合作中的欺骗行为、防范欺骗和惩罚欺骗的难度有关,成员越多,欺骗行为越难以识别,愿意充当“警察”这一角色的成员越少,而大多数成员更倾向于“搭便车”。(18) 亚欧会议成立之初有26个成员,随着欧盟和东盟的扩大,以及其他国家的加入,2006年亚欧会议成员达到45个。2010年,随着俄罗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加入,亚欧会议成员已扩大至48个。成员众多增加了集体行动的成本,成员众多和力量分散这两个条件结合在一起,则进一步制约了亚欧合作的质量和机制化程度,不仅使合作性国际机制难以形成,而且还会削弱协商性国际机制的效果,导致亚欧合作的松散化和弱机制化。
综上,预期收益和利益互惠对亚欧合作性国际机制的推动力不充分,缺少强权和权力分散决定了亚欧合作缺乏明确的主导者,力量差异悬殊和成员众多削弱了亚欧集体行动的效率。这些原因导致亚欧会议虽已运作了15年,但仍处于机制弱、程度低和成果少的状态。
制度匮乏下亚欧合作的未来:议题与方式
与亚欧对话创建时相比,当前亚欧所处的国际环境已有所改变,参与亚欧合作的成员规模扩大,亚欧实力对比发生重要转变,影响亚欧合作的条件已不同以往。
第一,亚欧面对的共同威胁在增加。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和全球公共问题的凸显,亚欧面临三大共同威胁的挑战,即国际金融秩序、非传统安全、能源与环境。在经济方面,虽然在2008年北京第七届亚欧峰会上,规范国际金融秩序已经或为热门议题,但是亚欧面对的这一共同威胁在过去两年中并没能得到有效缓解,以至于在2010年召开的布鲁塞尔第八届峰会上仍是会议重要议题。当欧洲尚未走出金融危机之时,欧元区又遭到主权债务危机的侵袭,欧元在2010年6月大幅贬值,11月欧元区经济再度出现危机。亚洲虽然在经济恢复中表现出勃勃生机,但却存在经济过热的潜在危险。在非传统安全方面,海盗问题一直是威胁全球贸易安全的重要因素,亚欧贸易主要依靠海上运输,随着亚欧间贸易量的增长,共同打击海盗将成为亚欧对话的重要议题之一。在环境与发展方面,2009年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尚未形成积极有效的措施,能源消费与环境保护这对矛盾仍是可持续发展的制肘,而随着亚洲发展中大国对能源需求的持续增加,能源消费、环境保护既是这些国家的发展瓶颈,也是亚欧需要共同面对和解决的难题。
在共同威胁之下,尽管新的合作需求不断产生,但合作的需求不一定导致合作行为。即使在共同利益之下,合作也只不过是行为体的多种选择之一。共同威胁更不足以催生合作性国际制度。在共同威胁之下,行为体别无选择,不得不采取某种形式的合作防范最坏结果,以免遭遇共同厄运,协商往往是最普遍的选择。成员交流协商的作用就在于加强对威胁的认识和理解、交换立场和观点、减少分歧和冲突。但事实上,亚欧成员在诸多共同威胁问题上,如减排标准,尚未形成一致的利益。
第二,亚欧实力对比正在经历着重要转变。欧洲经济在遭遇2008年金融海啸后又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复苏迟缓。而亚洲经济在复苏中展现活力,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实力的上升直接改变了亚欧的力量对比。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GDP增速一直保持在8%以上,(19) GDP总量现已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20) 虽然亚欧之间权力分散,没有绝对的权力中心,总体上仍存在明显的实力差距,但总体趋势却是,亚洲新兴经济体日渐成为代表亚洲经济发展的主流和与欧方合作的主力。
此外,根据2009年12月通过的《里斯本条约》,欧盟将形成新的行动机制和新的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个代表欧盟的单一法人将会加强欧盟的谈判力,使其在世界舞台上更有行动效力,成为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更加有形和具体的合作者。(21) 从长远来看,欧盟在外交上形成一个声音,对于推进欧亚合作应该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新成员的加入带来新的合作需求,但也会增加合作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第八届亚欧峰会吸纳了三名新成员,其中澳大利亚和俄罗斯都是能源、资源大国,新西兰则在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富有成功经验,他们的加入至少会增加能源资源及环境合作的可能性。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的重要地缘政治地位或许会为改善欧亚贸易运输安全带来乐观前景,但其规避“双钥匙”原则以第三方身份加盟的方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亚欧会议关于成员资格的规则。另一方面,虽然亚欧会议扩容的长期影响尚有待观察,但是成员规模扩大将直接降低该组织对话协商和集体行动的效率。
三大因素——共同威胁日渐凸显、亚欧力量对比变化、规模扩大,既对亚欧合作提出了新要求,也增加了合作的难度。根据影响合作的四个基本条件和当前三大现实因素,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有助于推进亚欧合作的合作领域、议题安排、模式选择、合作方式等。
首先,鉴于亚洲新兴国家日益成为与欧方合作的主力,亚欧需要在应对共同威胁的前提下,在低政治领域中寻找容易产生利益互惠和实现预期目标的合作议题。
正如前文所述,亚欧会议在政治领域的预期目标目前仍不切实际,而且政治合作本身对制度化的要求很高,在制度匮乏的情况下,亚欧难以在政治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诸如规范国际金融秩序、非传统安全、环保减排等问题难以在政治层面取得制度上的突破。而以欧方主导的对亚洲援助已不符合亚欧力量对比的现状。2010年5月26日在雅加达召开的亚欧工作会议上,这个问题已引起重视——“亚洲成员发展差异巨大,亚洲的变化引起对欧洲援助亚洲这一合作方式的反思,欧洲显然不能将中国和柬埔寨同等对待。”(22) 亚洲受援国显然不能代表当前亚洲的实力现状和发展趋势,援助合作也不适合继续作为亚欧合作的主要内容,欧洲国家更应把合作的对象转移到能真正代表亚洲发展主流方向的新兴国家。
因此,目前亚欧合作在经济领域最具取得突破和进展的空间。一方面,亚欧在贸易和技术合作上已取得一些成就,具备加深合作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旨在解决具体问题的非政治领域的合作不直接影响国家的核心利益,亚欧成员可以在制度匮乏的背景下,在技术层面找到管理共同威胁的某种利益契合点,确立务实可行的合作目标。比如减排问题,行为体虽难以在排放标准上达成一致,但在具体的节能方法或技术运用上能够找到某种共同利益,产生可预期的利益互惠。此外,发展经贸技术合作有助于扩大利益互惠,对其他领域的合作将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有鉴于此,欧方应与亚洲主要经济体优先在经济领域展开务实的经贸技术合作。
其次,制度模式的选择。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本文认为,设立常设机构和秘书处等设想与真正实现亚欧合作的国际制度之间存在很大差距。虽然常设机构和秘书处是成立国际组织的要件,但是建成国际组织不等于形成国际制度。国际组织不是制度本身,国际组织和制度可以相互独立,每一方都不依靠另一方而存在。比如联合国是一个国际组织而不是制度,因为联合国既不存在对成员国独立政策决策的限制,成员国也没有形成限制和协调共同行动的共同期望。(23) 就亚欧会议而言,设立秘书处不能改变制度匮乏的现状,本文所思考的正是在制度匮乏的现实面前亚欧合作的制度模式取向。
亚欧需要在合作型制度和协调型制度之间,以及奖励和惩罚机制之间做出选择。除了没有强权及其创造的国际制度这一先决条件外,目前亚欧合作在三大支柱领域也都缺乏成熟稳定和可预期的共同利益,因此,形成基于共同获益的合作型国际制度的时机远未成熟。在共同威胁严峻的背景下,以遏阻共同背离为基础的协调型国际制度更符合亚欧合作的现有条件。协调型国际制度的目的是避免出现最坏结果,协商对话机制有助于成员间的沟通和理解,减少分歧误解。协调只需要成员制定共同标准或规范,而不需要成员调整各自政策采取集体行动,也不需要充当稳定器功能的超强国家。虽然成员众多会增加协调的成本和代价,但与提供公共物品比起来难度要低得多。因此,没有强权主导的亚欧合作仍将需要协调型机制。
“一报还一报”是无政府状态下促进合作的最有效的策略,促进合作的方式包括奖赏和惩罚两种。由于亚欧会议成员数量较多,成员中缺少愿意充当“警察”的国家,很难对欺骗行为进行惩罚,因而亚欧合作的拓展和深化更需要奖赏机制而不是惩罚机制。
最后,在合作方式的选择上,应在强制与协商、排他与开放之间选择有效的合作方式。由于亚欧合作十多年来一直处于无强权参与和制度匮乏的状况,合作既无依靠强权推动的条件,也少有成员自动达成默契的可能,因而合作最适宜在协商中产生。又由于成员众多,增加了协商的成本,加之成员的力量分散,因而比较适合采取灵活开放的多边合作形式。
有学者在研究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时指出,在当前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区域性公共物品可以按照“受益人支付”的原则产生,由相关国家共同提供以满足共同需求,其优势在于可以直接反映不同类型国家的需求。(24) 这种谁受益谁支付的区域性公共物品的供应路径,对于亚欧跨区域合作颇具借鉴意义。参照“受益人支付”的原则,亚欧合作可以采取由选题倡议国组织承办,其他成员自愿参加的方式进行合作,从而确保议题选择的有效性,降低沟通成本的无谓消耗。因此,灵活松散、开放自主的多边合作既是亚欧合作的先天条件使然,也将是保持其活力的长期特色。
综上所述,制度匮乏是亚欧合作的基本特征,弱机制也是亚欧会议成立的前提条件,一味追求亚欧合作的制度化反而会脱离现实。鉴于共同威胁增加和成员力量对比变化,亚欧合作需要超越援助模式,以欧盟和亚洲主要经济体为主导,优先在经济领域寻找合作议题,开展灵活务实、开放自主的多边合作,构建协调型合作机制。
结语
从全球力量转移的角度来看,弱机制的亚欧会议自然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和长远意义。自两极体制瓦解后,世界格局一度陷入“单极”的状态。而随着美国地位的相对下降,全球力量对比逐渐从“一超多强”向多极化方向转化。尤其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力量对比变化加速,力量中心东移的轨迹趋于明显。在这一过程中,陆续出现多种跨区域、区域性和次区域等多边合作形式,其数量之多超过冷战期间。这种现象表明,力量变化和重组正在全球范围展开,其中,没有美国介入或参加的多边组织也不断产生,这更预示着世界需要学会适应真正意义上的霸权之后的国际合作,即在美国无力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和已有国际机制失灵的情况下探索国际合作的新路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欧合作开创了没有美国参加的跨区域多边合作的典范。
对于中国来说,弱机制的亚欧会议恰好给中国学习国际规则制定、培养负责任大国治理能力和积累经验提供了宽松灵活的试验场。中国正在以一种“软身段”姿态致力于低级政治议题的合作,比如在水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而“软身段”实则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哲学一脉相承,“弱机制”也正契合了中国“软身段”的行事作风。借用陆权论权威麦金德的警言,“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了世界”,我们可以说,治理好欧亚合作,就能治理好全球事务。对于亚欧会议成员来说,亚欧合作不只是要面对当前的亚洲和欧洲,更要面对全球的未来。
注释:
① 阿瑟·斯坦:《协调与合作:无政府世界中的制度》,载大卫·A·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② Charles P.Kindleberger,“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Exploitation,Public Goods,and Free Rider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5,No.2,June 1981,pp.242-254.
③ 关于霸权衰退后国际合作的经典论述,参见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中译本,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
④ Helen Milner,“International Theories of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Strengths and Weaknesses”,World Politics,Vol.44,No.3,April 1992,pp.466-496.
⑤ Robert Axelrod and William D.Hamilton,“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Science,Vol.211,No.4489,March 1981,pp.1390-1396.
⑥ Robert Axelrod and Robert O.Keohane,“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World Politics,Vol.38,No.1,October 1985,pp.226-254.
⑦ Randall W.Stone,Branislav L.Slantchev and Tamar R.London,“Choosing How to Cooperate:A Repeated Public-Goods Mode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1.52,No.2,June 2008,pp.335-362.
⑧ 参见Sung-Hoon Park,“ASEM and the Future of Asia-Europe Relations:Background,Characteristics and Challenges”,Asia Europe Journal,Vol.2,No.3,2004,pp.341-354;潘光、王震:《亚欧会议机制化问题浅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4期,第8~13页;亚欧会议课题组:《对亚欧会议下一步发展的几点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0期,第17~22页。
⑨ 参见亚欧会议课题组:《对亚欧会议下一步发展的几点思考》,第17~22页。
⑩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University of Helsinki Network for European Studies,“ASEM in its Tenth Year:Looking Back,Looking Forward”,European Background Study,2006,pp.1-218.
(11) “Dublin Agreed Principles of The Asia Europe Foundation” .http://www.asef.org/images/stories/aboutus/080501_asef%20dublin%20principles.pdf
(12) Heiner Hanggi,“AS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Triad”,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Vol.4,No.1,1999,pp,56-80.
(13) Christopher M.Dent,“The Asia-Europe Meeting and Inter-regionalism:Toward a Theory of Multilateral Utility”,Asian Survey,Vol.44,No.2,2004,pp.213-236.
(14) 参见马缨:《亚欧会议十年进程回顾》,载《当代亚太》2006年第9期,第3~9页。
(15) Christopher M.Dent,“The Asia-Europe Meeting and Inter-regionalism:Toward a Theory of Multilateral Utility”,pp.213-236.
(16) 蔡鹏鸿:《亚欧区域合作进程中的制度化问题:差异与前景》,载《国际观察》2004年第6期,第15~19页。
(17)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OO7/may/tradoc_134654.pdf
(18) Robert Axelrod and Robert O.Keohane,“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pp.226-254.
(19) “GDP Growth in China 1952 2009”.http://www.chinability.com/GDP.htm
(20) “China GDP Surpasses Japan,Capping Three-Decade Rise”.http://www.businessweek.com/news/2010-08-16/china-gdp-surpasses-japan-capping-three-decade-rise.html
(21) http://europa.eu/lisbon_treaty/glance/index_en.htm
(22) Shada Islam,“A New Asia-Europe Partnership for Development”.http://eeas.europa.eu/asem/2010conference/does/visibility_en.pdf
(23) 参见阿瑟·斯坦:《协调与合作:无政府世界中的制度》,第45页。
(24) 参见樊勇明:《从国际公共产品到区域性公共产品》,载《世界政治与经济》2010年第1期,第143~1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