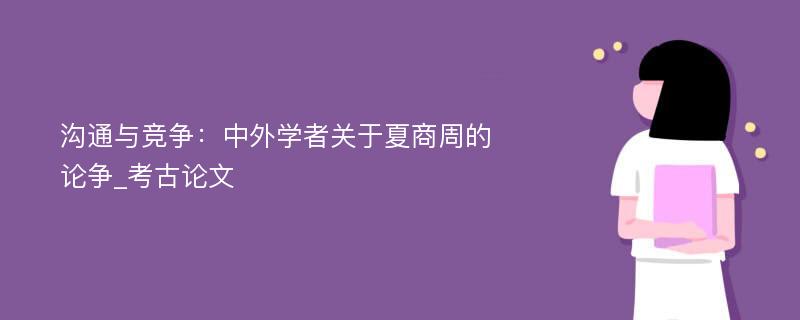
交流与争鸣:记中外学者关于夏商周年代的一场论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夏商周论文,论战论文,中外论文,学者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缘起
过去几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海外可谓毁多誉少。究其原因,一半是出于对工程的误解,一半是出于学术上的执着。有鉴于此,我在2002年4月4日~7日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亚洲学会年会上,组织并主持了一场题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交流与争鸣(Xia-Shang-Zhou Chronology Project:Exchange and Debate)”的小组讨论会,从国内外邀请了六位专家学者参与研讨。另外,因大会只配给小组两个小时的时间,恐有言犹未尽之憾,故约请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在年会上主持另一场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较自由的圆桌讨论会。本文旨在介绍这次讨论会的来龙去脉,会上讨论的实况和评论中外学者关于夏商周年代学歧见的根源。
早在2000年秋冬,当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阶段性研究成果之际,即在海外引起过一场激烈的辩论,战场是“东亚考古学互联网”(East Asian Archaeology Network)的电子讨论组。这场论战的导火线是《纽约时报》记者Erik Eckholm所写有关断代工程的报道。这篇题为《中国:古史引燃今疑》(注:Eckholm,Erik,In China,ancient history kindles modern doubts,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0,2000.)颇具争议性的文章,是在11月10日即断代工程新闻发布会的翌日发表,引起了海外汉学家对三代年代问题的关注。不过,参加这场辩论的人大都不是专门研究年代学的学者,所以讨论的主题集中在一般性的问题,如夏代是否存在、二里头文化与夏代的关系、古史年代与政治的关系等(注:陈星灿、刘莉:《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网上讨论纪实》,《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1年第9期第16~37页。),并没有触及夏商周年代学的具体分歧到底在那里。
与“东亚考古学互联网”上的讨论不同,华盛顿的这场辩论,参加者都是年代学的专家。从中国来的四位与会者,李学勤是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仇士华是副组长,张长寿和张培瑜都是独当一面的成员,他们分别代表工程的四个主要研究手段,即文献、放射性碳素测年、考古和天文。美方的与会学者倪德卫(David S.Nivison)和夏含夷多年来一直研究商周年代,邵东方专攻《竹书纪年》,我本人除习中国考古学外,还对碳十四测年稍有涉猎。因此,在华盛顿的两场讨论都能切中年代学的主题,具体讨论了研究古史年代的方法、理论和断代工程的成果。
两场讨论会的宗旨是交流对夏商周年代学的看法。中方与会者代表国内学术界对三代年代学的看法,或许说得更准确一点,他们代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观点;美方与会者则代表海外一些反对意见。海内外学者在会上澄清了一些事实,摆明了观点,虽然没有说服对方,但消除了一些误解。两场讨论会都在激烈但友好的气氛下进行,是一次难得的学术争鸣。
二、过程
其实,召集中外年代学学者齐聚华盛顿面对面地辩论并不是我个人的主意。早在2001年的夏天,倪德卫就约请我组织这样的一场讨论会,他还亲临剑桥与我商量;其中还得到艾兰(Sarah Allan)的帮助与支持,讨论会才能顺利召开。
这次中外辩论最大的特点是开诚布公,观点鲜明,坚持己见,但又互相尊重。早在开会前的两个多月,论文和圆桌讨论会的问题就已内部流通,所以双方都可以按对方观点组织和调整发言,讨论因此很有针对性。
首先举行的是4月5日下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交流与争鸣”的小组讨论会。发言的次序和论文题目如下[这组文章将在美国的《东亚考古杂志》(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发表]:李学勤,《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和成果》;张培瑜,《文献中夏商周天象和年代信息的分析研究》;倪德卫,《三代年代工程:两种定年方法》(The Three Dynasties Chronology Project:Two Approaches to Dating);邵东方,《关于今本〈竹书纪年〉的争议和三代年代的关系》(Controversy on the "Modern Text"Bamboo Annals and Its Relation to Three Dynasties Chronology);张长寿,《沣西的先周文化遗存》;仇士华,《碳十四年代测定与夏商周年表的关系》。
圆桌讨论会是在4月6日晚上举行,由夏含夷轮流提问,各位学者作答。两次讨论会各有近百人参加,会上都留有少许时间让听众提问或者发表意见,台上台下热闹非常。
三、论争
无论在小组讨论会或者在圆桌讨论会上,讨论都很热烈。总结其争论的主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断代工程的成果是否受政治影响
这个问题不论汉学专家还是一般公众,都颇感兴趣。海外新闻媒体曾对断代工程发过两次影响较大的报道,首先是Bruce Gilley在《远东经济评论》发表《中国:民族主义发掘未来》(注:Gilley,Bruce,China:nationalism.Digging into the future,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July 20,2000.)一文,之后有上述《纽约时报》的文章。这两篇报道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政府提出、组织并拨款资助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目的是证明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倡导民族主义,培养爱国思想。所以两篇文章都提到工程考订夏代距今已有四千多年,是民族主义在作祟。
倪德卫却从另一个角度评论断代工程与政府的关系。他认为西周年代学还有很多基本问题未能取得共识,断代工程匆匆发表一张不成熟的年表,是受政治影响所至。更遗憾的是,这样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竟然是在中国政府的权威领导下出现。这样一来,不单让中国政府的权威承担不必要的风险,还鼓励非专门从事年代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博物馆人员、学生和记者等,不经思考地接受这个年表。任何年代学的研究成立与否,都应该通过严格的论证,不能依靠政府权威。
为此,李学勤在私下讨论和公开发言时,都明确地指出工程一直贯彻“政府支持,专家负责”的原则。断代工程虽然有政府背景,但年表中的每一个年代,都是专家们独立探索的结果,政府并没有暗示某个年代要如何定,专家们的意见也没有受政府左右。
(二)整合文献与考古材料的困难
如何整合文献与考古材料是断代工程在方法论上的一项挑战,这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李学勤承认整合文献与考古材料的困难。他说:“各个时间所遗留的材料和信息,在性质和数量上互不相同,研究这些时期所能采用的方法手段也不一样。怎能把有关的研究结果综合起来,形成前后一贯互洽的年表,相当困难”。面对这项挑战,李学勤指出断代工程采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办法。他说:“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方法的特点,是把与年代学有关的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天文学和科技测年技术等学科结合起来,进行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工程的各个课题和专题,都尽可能要求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承担”。
断代工程的研究途径,不外从文字材料(包括古代文献、甲骨文和金文)和考古(包括碳十四测年)出发。工程根据夏、商及共和以前的西周这几个历史阶段的不同情况,分别确定了以下的具体目标:“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倪德卫则提出历史文献定年与考古测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手段,是难以整合的。考古的绝对年代是通过碳十四测年技术获得,透过累积性的工作,一步一步接近真实的年代。我们可以说:“这是目前的结果,我们希望以后能做得更好”。他还指出,碳十四测年的结果永远是不完美的,现在的成果可以为将来打下基础。依靠文字材料定年则不一样,所定出的年代只有对或错,如果错了,惟有推倒重来。
(三)碳十四年代数据拟合后的可信度
碳十四系列数据拟合是一种崭新的校正程序,拟合后不单使日历年代的误差大大缩小,可信度也可大大提高。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系列数据法是今后考古工程碳素测年的典范。
邵东方引用了蒋祖棣的看法,指出断代工程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只取一个标准差,因此夏商周年表的碳十四拟合数据只有68.3%的信度。在自由提问时,有听众提出类似问题。可见海外学者对碳十四系列数据的拟合普遍还欠认识。对此,仇士华作了全面的回答。
仇士华指出,最理想的系列样品是来自树轮可清数(就是从树皮往内的年轮清晰可数)的原木,如有50个或以上的年轮,则可象建立树轮校正曲线一样,每10轮取一个样品,连续取五个或以上的碳样,测出其碳十四年代数据。因为我们知道两个相邻样品的真正年代相距是10年,当综合考虑这五个测年数据,一些不互洽的、矛盾的年代的可能性因此减低。这个新的概率,或称为后概率,是利用贝叶斯数理统计法得出的。经过与树轮校正曲线拟合,国际上有实验室能把木头生长的年代定准到误差不超过±5年,而这个数字的后概率差不多达到百分之一百(注:Kojo,Yasushi,Robert M.Kalin,and Austin Long,High-precision"wiggle-matching" in radiocarbon dating,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21,pp.475-479,1994.)。对于按文化分期或地层连续的系列样品,在相邻时间间隔上,虽然不象树轮系列那样规整,但在时代上的早晚次序是明确的,也同样可以拟合,虽然获得的日历年代误差与可信度不如原木。
在碳素测年这个问题上,倪德卫指出所测定的年代并不是历史事件的年代,而是测定与事件相关的含碳物质,如棺木、人骨、兽骨等,所以碳十四年代与历史年代之间有不确定的因素。仇士华承认碳十四测年要与考古工作紧密配合,考古遗存与历史事件的关系全靠考古学家的考订。
(四)对今本《竹书纪年》的不同看法
中外年代学者对西周的年代有很多歧异之处,其关键是对今本《竹书纪年》(下称《今本》)有不同的看法。李学勤指出,《今本》开始出现肯定不在明代,但经清代以来学者分析,其中实有不少后人加入的材料和观点。断代工程虽然没有专门研究《今本》的专题,但曾请四川大学的陈力对《竹书纪年》进行研究,并在工作中参考了他的研究报告。海外学者以夏含夷和倪德卫为代表,则认为《今本》中的年代是目前最早的年代记录,虽然共和元年前的年代不一定都准确,但批判地分析《今本》中的年代,有助得出正确的年代。断代工程忽视了《今本》的材料实欠妥当。邵东方的论文,主要是介绍海外学者与陈力对《今本》的研究和《今本》年代对西周年代学的意义。
在当代汉学家中,夏含夷对《今本》的研究,可谓不遗余力。夏氏对《今本》的考证,不是从西周以后的文字入手,而是从同期的铭文切进。他发现,《今本》中有不少人名、地名和事件,都在金文中得到佐证(注:Shaughnessy,Edward L.,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Bamboo Annal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6(1),pp.149-180,1986.),例如《今本》中关于宣王五年命吉甫伐猃狁的记载,跟兮甲盘的铭刻暗合,尤其是“五年”这一时间上的细节,从未见于其他文献;穆王时的毛公班和迁,与班簋中征讨东方诸国的毛公班及其儿子譴应为同一人。会议中邵东方特别介绍了夏含夷发现《今本》西周早年一片长达40字的错简,这片竹简是从成王挪到武王末年,这样就把武王逝世为克商后的第三年延长为第六年。
倪德卫据《今本》得出西周行“二元制”的结论(注:Nivison,David S.,The dates of Western Chou,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3(2),pp.481-580,1983.)。西周盛行三年之丧,所以西周诸王往往出现两个元年,第一个元年是新王即位之年,第二个元年是新王守丧完毕、正式登基之年。战国时代的史家,在整理史料时作了修订,排除了第二个元年。这就是为什么《今本》中文王在位52年,其他文献中文王只有50年。倪德卫认为利用“二元制”的理论梳理《今本》中的纪年,便可把三代的年代很好地排列清楚。“二元制”的理论,后来更被夏含夷发挥得淋漓尽致(注:Shaughnessy,Edward L.,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Inscribed Bronze Vessel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
牵一发而动全身,倪、夏二氏深信《今本》的史料价值,他们得出的西周年表自然和断代工程得出的西周年表大相迳庭。会上倪德卫具体指出夏商周断代工程赖以推定西周王年的七个支点中的第二个支点“晋侯苏钟与厉王三十三年”有欠妥善。据雷学淇考证《今本》,厉王在生仅三十七年,在位年数最多是十八年(断代工程认为厉王在位共三十七年)。那么晋侯苏钟的“唯王卅又三年”所指的只能是宣王,并非厉王。善夫山鼎应为宣王晚年时器,其铭云“唯王三十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如果从公元前827年(断代工程认为这一年是宣王元年)算起,宣王三十七年便是公元前791年,与月相历日不合,符合“正月初吉庚戌”日历的年份应为公元前789年,而宣王元年则是公元前825年。
张长寿在圆桌会议上对晋侯苏钟的问题作了回应。他引用上海市博物馆馆长马承源的研究成果,认为苏钟上的四个干支历日,中间的两个是刻错了,如果把这两个干支颠倒过来,便能符合厉王三十三年的历日。倪德卫的说法则要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他的两元论要成立;第二,《史记·晋世家》把晋侯的世系弄错了,献侯和穆侯的父子关系要颠倒过来。张长寿认为断代工程采用马说,只要符合一个条件便能成立,是比较倪说更能令人信服的。
(五)学术道德的问题
有学者提出断代工程存在“学术上的不忠实”问题。断代工程存不存在学术道德问题,中方与会代表作了令人满意的答复。
这是在圆桌讨论会上,夏含夷向张培瑜提出的问题,原文如下:“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食是《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道。然而,在中国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食及其对西周断代的意义(注:方善柱:《西周年代的几个问题》,《大陆杂志》第51卷第1期第15~23页,1975年。)。一些海外学者觉得工程和《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能不能说明一下”。
张培瑜说明了懿王元年天再旦可能是日出之际的日食最早是刘朝阳提出的,后来方善柱把这一天文现象论证为发生在公元前899年。断代工程组织到新疆观看一次在日出时的日食,确有“天再旦”的效果。经过天文计算,把懿王元年天再旦确定为公元前899年4月21日。各种宣传报道和简本没有说明国外学者的工作,是有不尽妥当之处,将来的正式报告必定说明。
李学勤则补充说,《简本》限于篇幅和形式,未能把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但是并不存在学术道德问题。对此《简本》特别有如下的说明文字:“本报告为向社会公布阶段成果所用,为求简明,未能一一注明引用他人之说的出处,有关内容将在《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阶段成果报告·繁本》中全面反映”。经此一说,相信误解应可冰释。
四、评论
综观这次在华盛顿的辩论,确是有益的学术交流。作为主持人,从一个考古工作者的角度,觉得有如下的问题值得思考。
海外学者对断代工程与中国政府的密切关系感到疑虑是可以理解的。宋健一再旗帜鲜明地指出爱国主义教育是政府发起断代工程的初衷之一(注:宋健:《超越疑古,走出迷茫:呼唤夏商周断代工程》,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而在80年代以前中国政治干预学术有前车可鉴。政府在断代工程中的角色,很难不让大家担心,并对研究成果的严肃性产生疑问。
然而,通过几年来对断代工程的观察,我以为工程推行的过程说明中国的政治和学术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海外学者不应用20多年前对中国的认识来看今天中国的学术环境。再者,我们不能以断代工程得到政府的资助便认定工程成果会受到政府影响。后现代主义史学正确地指出任何历史研究都是有政治立场的。试问哪国的历史研究是完全中立、没有价值判断的?又试问哪国政府对本国历史研究与考古发掘的资助一点也没有政治考虑?反省考古工作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是近年来欧美考古界的热门课题,研究认为民族主义和考古工作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前者对后者既有负面影响,也有正面促进(注:a.Kohl,Philip L.,and Clare Fawcett,eds,Nationalism,Politics,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b.Diaz-Andreu,Margarita,and Timothy Champion,eds,Nationalism and Archaeology in Europe,London,UCL Press,1996.
c.Meskell,Lynn,ed,Archaeology Under Fire,London,Routledge,1998.)。所以,重要的是三代年表的发表纵使看起来有民族主义的效应,年表的得出却是严肃学术行为的结果。当然新的年表经政府宣扬,自然有了权威的地位。不过,《简本》谨慎地指出,这只是阶段成果报告,为今后的工作留有很大余地。
就以美国来说,20世纪30年代政府组织了很多大型的考古项目,出版了大量高水平的报告,我们没有因为它们的政府背景,弃而不用。不过,倪德卫的话也有道理,断代工程的年表是要通过严格的学术标准才能成立,不能因政府的关系而得到权威性的待遇。
如何整合文献与考古的研究是断代工程的最大难点,倪德卫在这方面的观察十分精警。就以武王克商为例,传统的说法有四十四种之多,年代从公元前1130~前1018年,时间跨越122年(注:北京师范大学编:《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考古学家作了大量的发掘工作,采集了数十个含碳的系列样品,碳十四专家作了很大努力改进试验室的精度,才把克商之年定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之间,年代跨度缩短了四分之一,筛去三分之二的说法。然而,如何推定具体的克商之年则全靠文字材料的考据了。假使没有考古对克商之年的推定,光靠文字材料似乎也可得出同样结论。如果说碳十四测年验证了文字的考据,三十年的区间则嫌宽松。关于克商之年的考订,《简本》依文献提出了三个方案,公元前1046年、前1044年和前1027年,以公元前1046年一说为符合条件最多的一种,故定为武王克商的首选之年。如何选定这三说,因它们都在考古所定的三十年区间内,所以都可以接受,就显得无能为力了。看来碳十四测年本身的局限还难以对历史年代有太大的作用。话得说回来,断代工程远在起动之始,鉴于早商和夏代年代湮远,文献稀少,主要依靠考古的手段,专家组为它们定下“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和“基本的年代框架”等目标(注: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确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透过断代工程的机会,中国的碳十四测年技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取样到校正等各个工序都作了系统的研究,仪器也得到更新,系列样品能拟合出误差较小的日历年代。最好的结果是在郑州商城一个水井井框取得的原水碳样,拟合得出公元前4000±8年的结果。我把仇士华的论文所公布的拟合数据梳理了一遍,120个常规数据拟合结果的中数是±35年,大大地提高了单个数据一般为±80年的误差。这些新的误差较小的绝对年代将为考古工作者带来重要的启示。例如二里头三期的年代被定为公元前1610~前1564年,四期被定为公元前1560~前1529年,偃师商城一期则为公元前1600~前1486年(注: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二里头与偃师商城两遗址在绝对年代上的重叠很值得我们深思。
五、后感
中外年代学家在华盛顿的这场交流与论战消除了一些对断代工程的误解,但是双方在学术见解上的分歧并没有完全解除。与会代表亮明自己的观点,也直接听到对方的意见,为今后的继续交流奠定了基础。会后李学勤指出中方有意筹办一次关于夏商周年代学的国际会议,预先向美方代表发了口头邀请。
张长寿在圆桌会议上提出公元前899年(懿王元年)和前841年(共和元年)这两个西周年代支点是大家的共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求同存异。看来张长寿的良好愿望只能是一厢情愿。因为对西周年代两种不同的重建,关键在于对《今本》有不同的认识,要解决与会年代学家之间的分歧,只能从《今本》入手,到底《今本》所载的年代对西周年代研究有何价值。看来一场关于《今本》的辩论在所难免。
李学勤指出,断代工程的工作繁重而艰巨,五年的时间还是太短促了,目前的报告只能是“阶段性成果”。《简本》在出版说明中也明确表示,“它(简本)还不是三代年代学研究的终极目标,而是三代年代研究步入新阶段的标志。我们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考古新材料的不断出土,随着更多的研究者投身到年代学研究中来,未来的三代年代学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加接近真理的结论”(注: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真理是越辩越明的。
附记:本文写作期间,得到艾兰、仇士华、李学勤、陈星灿、邵东方、张培瑜、张长寿、夏含夷和倪德卫等诸位先生的指导和帮助,谨致谢忱。错漏之处,自是笔者个人负责。
标签:考古论文; 夏商周论文; 公元前2000年论文; 夏商周断代工程论文; 政府工程论文; 竹书纪年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李学勤论文; 代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