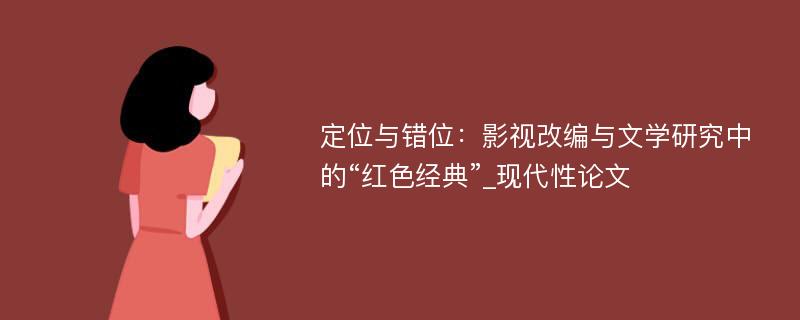
定位与错位——影视改编与文学研究中的“红色经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色论文,经典论文,影视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饶有意味的错位
建国初期十七年表现革命斗争题材的文学作品即所谓“红色经典”的影视剧改编热,方兴未艾,《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红旗谱》、《苦菜花》等已经播出,还有一批剧目在制作过程中。做出这种选择,有着各种现实的形势制约和利益考虑,比如说,清官戏充斥荧屏所招致的批评和限制,当代生活题材创作在选材和吸引观众眼球上的种种困惑,以及表现红色历史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和《长征》等所引起的热烈反响;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红色经典”作为一种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其潜在价值也被人们认可和看重。然而,就已经播出的作品而言,这类改编并不尽如人意,有的剧目如《林海雪原》,还遭到观众和杨子荣亲属的强烈批评。影视剧的制作者本来希望,能够借助于共和国初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这些作品的熟悉和追忆,讨巧卖乖,赢得广泛的观众和较高的收视率,但是,对于如何唤起观众的情感记忆,其敏感点何在,制作者们却没有作出准确的判断,因而产生了某种有意味的错位。
这样的尴尬是从影视剧制作上表现出来的,而问题却未必应当向影视界去追索。影视剧制作者遭遇的难题,也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大难题。与“红色经典”受到社会青睐相应和的是,对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文学(通称为“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也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大热点,相关论著日渐增多。研究者的初衷是以当下的学术眼光为这些作品重新定位,发掘这些作品的内在蕴涵。但是,在怎样给这些作品定位的问题上,他们却始终有些犹疑不定,左右为难。新潮激荡的1985年,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位学者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研究架构,影响乃至改变了其后学界研究的思路和进程。但是,在他们以“启蒙现代性”为主题词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描述中,却有意无意地用新的一元论定式取代先前的以革命和阶级斗争为主题词的文学视野。“目前的基本构想大致有这样一些内容: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最后,由这一概念涉及的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注: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12页。)在这样的宏观概括中,充满了历史新生和胜利欢乐的、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种巴赫金所言的狂欢化特征的新中国初期十七年文学,显然是被遮蔽了的,是无法整合进去的。21世纪之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一批学者撰写的《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采用的是“反思现代性”的视角,可以说是与当年的钱理群等人恰成对照(注:“启蒙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是近年思想界和文学研究界的关键词。据笔者在国家图书馆网站上所作的简略检索,近年来以“现代性”及其相关问题作主题词的硕士、博士论文有60余部,同类型的出版物则多达近200种。关于这两个词汇的相关阐释,参见陈晓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导言”,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版。),但是,关于“红色经典”的问题,他们同样感到棘手。该书主编陈晓明将“十七年文学”融进了他所描述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不断激进化、不断通过断裂的方式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过程,以保持文学进程的连续性:“中国现代性一直是以断裂的方式展开,这些断裂给社会的组织结构、秩序规范、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都产生剧烈的冲击。”“在现代性不断激进化的历史进程中,20世纪的中国文学始终是激进变革的先驱,它既是一面镜子,更是历史最内在的躁动不安的那种精神和情绪。在那些剧烈的变革时期,在那些猛然发生的历史断裂过程中,文学都在扮演一种推波助澜的角色。”(注:陈晓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第12页。)在这样的描述中,对“十七年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关系,是以不断断裂和激进化之轮廓加以整合的,但是,在具体论及“红色经典”的代表作《红旗谱》时,作者却以作品中阶级斗争状态并不尖锐和人际关系描写的人性化、乡土情怀的抒情性为例证,从“非激进化”的意义上为作品遭到的“非文学化”的指责进行辩解。从1985年至今,时间过去近二十年,学术视野和理论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对以“红色经典”为其主要组成部分的“十七年文学”的评价上,却仍然难以给出明确的说法。另一方面,在具体作品的再解读上,从陈思和标举的“潜写作”和“民间”视角,到黄子平拆解的“革命”、“历史”、“小说”,从境外的唐小兵,到内地的李杨、蓝爱国,都在做出积极的努力,揭示那些被誉为“红色经典”的作品的渊源流变和被人们所忽略的某些蕴涵(注:参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版;黄子平《灰阑中的叙事》,上海三联书店2000版;董之林《追忆燃情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版;唐小兵《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版;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版;蓝爱国《解构十七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版。)。但是,无论是借助于所谓“大传统”、“小传统”的区分,还是采用一种反思革命乃至追溯革命的态度,无论是使用阐释学的方式,还是接受福柯后结构理论的影响,在边缘处求索、发掘曾经被主流话语遮蔽的某些元素,这些再解读在关注文本自身的时候,对将作品还原于当时的社会语境和文学潮流,对作品的主导倾向的确证,却大都有所忽略,因而也存在明显的缺失。
如陈晓明所言,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特征,就是它与革命历史、社会现实和众多读者的期待心理的相互激荡。这是特定时代的文学生产的规定性。离开了这一点,对“红色经典”的再解读(许多时候会导致过度阐释),以及通过当下的影视手段,试图在作品和观众之间建立一种新的互动关系,激起作品与观众之间的情感呼应,恐怕难以实现。要想高屋建瓴地评价“红色经典”,专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尚且如此困窘,我们的影视作品又如何能揭开个中之谜?与之相关联,我们如何去认识“红色经典”在美学风貌和艺术风格上的独特的规定性?在此,笔者试图廓清一些问题,为逼近和解决问题的核心做一些外围清理工作。
二、现代史诗品格的建构
重新评价“红色经典”,首先需要确认其创建现代史诗品格的艺术范式的成就。
新中国的建立,新时代的展开,对文学反映迅速变化的新生活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学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表现中国社会主义开创阶段的社会现实,从文学样式到语言风格,都没有多少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和继承。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一直是在艰难的探索和积极的进取中进行的。换言之,它是从寻找范式、建立范式到拒绝和放弃范式、进而寻找新范式的过程。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在论述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形成时指出:一个时代的文学也好,一种文学类型、一部作品也好,都取决于三个互相联系、共同作用的因素,即作家的个性、最广义的现实性(作家把握现实的方式)以及艺术传统,三者有机地形成文学的结构。文学的发展,首先是文学结构的革新,“传统结构循序渐进的变化,最终不能产生新型文学作品。新型文学作品必以其全新的、完整的结构异军突起,在本质上与属于前一时期的作品迥然不同”(注:《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版,第120页。)。在我看来,普实克的这段话对文学范式的内涵作了较为明晰的规定,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当代文学因面对新的社会生活而探索新的文学范式所付出的艰辛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伴随着历史的跌宕起伏、潮流更替,中国当代文学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寻找、建立和更替种种范式。尽管在现实生活和文学追求中,曾经有过种种挫折和失落,作家仍然以巨大的激情去寻求适应于时代的最佳范式。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繁弦急管式的变动,又催促着文学艺术范式的急剧变化。建国初期的“现代史诗”和“乡村喜剧”,80年代初期的“改革文学”和“寻根文学”,都是其典型的表现。时至今日,这种创建新范式的努力和渴求,似乎不那么强烈了,但是“家族史小说”、“官场小说”、“情感婚恋小说”、“青春叛逆小说”等,仍然可以看到各自所遵循的范式的存在(注:关于中国当代文学艺术范式兴衰更替的详尽分析,参见笔者主编《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主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版。)。
在这样的视野中,“红色经典”的价值,首先就在于它建立了具有现代史诗品格的文学范式,并且为后来者们提供了继续前进和深化的路径。“红色经典”尽管风貌各异,但其共性就是具有现代民族史诗的规模和气魄,比较充分地层现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壮阔风云,为革命斗争的主体、觉醒而起来奋勇投入伟大斗争的民族大众,树立起文学的丰碑。同时,作品所具有的宏阔的时空结构,以及作者进发出来的火山爆发般的激情,也构成了这些作品的重要特色。广而言之,从清末民初的民主与帝制之争(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大革命时代的风起云涌(欧阳山《三家巷》、《苦斗》),红军时代的艰苦卓绝(梁斌《红旗谱》、王愿坚《党费》和《七根火柴》),抗战八年的血肉长城(冯德英《苦菜花》、知侠《铁道游击队》、刘流《烈火金刚》),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摧枯拉朽、风卷残云(杜鹏程《保卫延安》、吴强《红日》、曲波《林海雪原》),都在表现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方面,在文学范式的创建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尽管从更高的文学史意义上来说,它们还不过是现代史诗的雏形或者初稿。冯雪峰在为《保卫延安》所写的序言中就热情洋溢而又恰如其分地写道,杜鹏程的这部作品“够得上称为它所描写的这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有名的英雄战争的一部史诗的。或者说,从更高的要求说,从这部作品还可以加工的意义上说,也总可以是这样的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以这部作品所已达到的根本的史诗精神而论,我个人是认为它已经具有古典文学中的英雄史诗的精神;但在艺术的技巧或表现的手法上当然还未能达到古典杰作的水平”(注:冯雪峰:《论〈保卫延安〉》,见杜鹏程《保卫延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版。)。此后,在《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菜花》等作品中,这种对现代民族史诗的追求,仍然是激情充盈、成就斐然的。虽然较之《三国演义》、《水浒传》和《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前者的艺术成就还相去较远,但是草创之功却是不可湮没的。这些作品所具有的宏大的斗争场景,壮阔的时代风云,决定民族和个人命运的重大冲突,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具有大型结构和大型容量的表现方式,无疑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
对史诗性一宏大叙事的否弃,是当下的流行。在后现代主义的重镇利奥塔那里,现代性及其宏大叙事遭到强烈的质疑,文学中史诗性的追求也受到拒斥。但是,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看,史诗性和宏大叙事,仍然是一个顽强的存在。另一位被中国学者指认为后现代主义大师的杰姆逊,反诘利奥塔的反宏大叙事理论说,“事实上,利奥塔和德勒兹一样,自己就在很多方面是个不折不扣的现代派,总是满怀激情地期待着真正的、激进的、原汁原味的新事物的出现”,“声讨种种宏大叙事(及其‘萎缩的小矮人’,即神学)是相对容易的事情,但完全抛开宏大叙事去思考问题就不那么容易了。我已在别的地方论述过我的这一观点,即利奥塔的反宏大叙事本身就是一种大叙事……我想推出一种更强硬的正式的结论:对现有叙事模式的拒绝和排斥总是在呼唤一种被压抑的历史内容的叙事性复归。尽管它摆出反叙事的姿态,但其反叙事立场本身却产生了另一种叙事,虽然它总是在争论中把这个新的叙事小心翼翼地遮掩起来”(注:杰姆逊2002年7月28日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所作的演讲《现代性的神话》,引自“终点论坛·批评之路”网站。)。是的,哪吒劈山救母是伟大的英雄,雄阔海力举千斤这何尝不是伟大的壮举,虽然说,他们的动作的作用力是逆向而行的。说到80年代以来直到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在《黄河东流去》(李凖)、《红高粱家族》(莫言)、《古船》(张炜)、《白鹿原》(陈忠实)、《尘埃落定》(阿来)、《第二十幕》(周大新)、《英雄时代》(柳建伟)、《水乳大地》(范稳)等作品中,宏大叙事和史诗品格,仍然是作家的激情追求。甚至,在莫言笔下的最英雄好汉也最王八蛋的余占鳌那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苦菜花》中的草莽英雄柳八爷的精神血脉的传承。
那么,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谈论“红色经典”的史诗性呢?苏联文艺理论家波斯彼洛夫,在论述文学潮流中的史诗性作品的特征时这样说:
我们根据有关作品的一些共同的、历史的不断重复的题材的特点,从其他各种体裁中划分出这一组民族历史的体裁。这些特点就在于歌手、说唱家、作家、诗人,在自己时代或历史过去的社会生活中所关心的,主要是整个民族社会的形成,这种形成或者是在与其他部族或民族的外部冲突中实现的,或者是在全体社会阶级之间、在广大人民群众与国家政权之间等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这就是这一组体裁作品的特殊体裁内容,这就决定了这类作品的冲突的特点:它们建立在政治冲突的基础上,而个人关系(“私情”)在作品中只能起次要的辅助作用。(注: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三联书店1985版,第318-319页。)
波斯彼洛夫认为,这类具有规模宏大的形式的作品就是民族史诗。在讨论史诗性作品时,他的视野足够开阔,他从古希腊的《伊利亚特》、中世纪的《罗兰之歌》一路考察到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他所描述的“整个民族社会的形成”,也包括了从古至今各民族的形成,包括近代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由此看来,20世纪中华民族的艰难蹒跚而又坚忍不拔的步履,也正是现代意义上的“整个民族社会的形成”,即中华民族的现代转型。波斯彼洛夫揭示的这一民族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两种剧烈冲突,民族冲突和阶级冲突,在现代中国都同时地存在。由鸦片战争以来古老帝国的分崩离析一败涂地引发的民族危机意识,国家变革的诉求与焦虑,国内各利益阶层、集团和各种政治势力的互相角逐,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鲸吞瓜分、勾结争夺……统统交织在一起。而后,经过漫长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消灭了国内反动派,在战争中高度动员和整合起来的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和平建设的新时代。这是“红色经典”产生的历史场域。“红色经典”尽管在艺术性上有种种不足和缺憾,但在表达这一民族历史题材上,却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那些从常规的人物形象着眼,认为“红色经典”缺少对个人命运和感情生活的关注的批评失之皮相,为什么在影视剧作品中着力加大其个人感情戏的努力难以得到观众认同。就像在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和《苦菜花》中,制作者试图为单色调的杨子荣等增添个人的感情生活,甚至为杨子荣添加什么情人和儿子的时候,就会让人感到,这是“戏说乾隆”式的搞笑把戏,这不会给英雄增添多少凡人生活色彩,相反却会使作品变得不伦不类,画蛇添足(注:对杨子荣形象的任意增改,还在于改编者没有察觉,这一类作品不是致力于圆形人物的形象塑造,而是在诸多人物身上采用互补方式,每人只突出其性格的某一方面,类似于诸葛亮的智,张飞的猛,宋江的义,李逵的莽。在《林海雪原》中,杨子荣感情戏的阙如,是由少剑波与白茹的爱情戏加以弥补烘托的。)。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艰难孕育过程中,社会整体分裂为两个生死相争的敌对阵营,民族的和阶级的命运的大搏斗,千百万人投身其中的政治斗争和残酷战争,以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的巨大数字为标识的累累伤亡,在这样的宏大背景下,个人的命运和情感,亲情和婚恋,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在宏阔的时空中进行的残酷战争,许多时候都会要求人们服从战争的最高需要,对儿女情长的排斥,对个人的欲求丰富性的压抑,都有其必然合理性;相反,在深山老林中进行的剿匪战斗,在齐鲁大地上展开的抗日斗争,无论作品中的人物是否有自觉的意识,在很大意义上,他们都首先是作为酷烈的环境下奋战不已的民族大众的一员,乃至作为战争的工具而存在的。这些作品,不是以展现人物的丰富性格见长,而是强化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对历史重大事件的驾驭能力。就像《伊利亚特》中的阿喀琉斯一样,尽管他是天下第一勇士,当他因为希腊联军首领对被俘女奴的分配不公心怀不满拒绝出战时,他对于正在进行的特洛伊战争就一钱不值。波斯彼洛夫指出,不同于那些塑造社会性格的风俗描写体裁,史诗性作品是以描述历史风云和重大事件为着力点的。“民族历史题材的作品通常描写一次过去的事件。并且这些作品的主要主人公在这次事件的进程中,总是起着某种主导作用。他们常常用自己的行动,促成或引导这些事件的发展,这种行动是根据他们的社会历史性格特点而来的”(注: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三联书店1985版,第321页。)。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和战争,是简化的艺术,一切与胜败无关的东西,如波斯彼洛夫所说的“私情”都必然会缩减到最弱最小的程度。为“红色经典”中的人物增添个人私情,不但是可怜无补,还往往会损害作品的血脉气韵,个中缘由也正在这里。
三、在写实与传奇、典范与通俗之间
对“红色经典”的又一点误解,是在再评价和再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对其所独具的传奇性的漠视。有的论者将同属于“红色经典”的《红旗谱》和《林海雪原》对立起来,用前者贬抑后者,对后者的传奇性色彩深表不屑;在电视剧中,制作者也无法处理作品中的奇崛特色,相反地,在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和人情风俗的添加中,将作品的英雄传奇湮没在一地鸡毛的琐屑之中。
“红色经典”具有明显的仿真写实特点。作品所描写的历史事件,民族的和阶级的大规模斗争和战争,都确有其事,而且为时不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则从最终胜利的宏观情景上确认了这些作品的可印证性。与此同时,这些作品的作者,与其说他们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文学梦而写作,不如说他们是充溢着胜利豪情和对牺牲战友的悼念之情欣然命笔的。《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参加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解放前夕的反蒋斗争,并被投进白公馆、渣滓洞牢狱,是吃人魔窟的见证人,是红岩下的幸存者;《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出生于北平一个大学校长兼大地主的家庭,为了脱逃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她离家独立谋生,在河北香河县做过小学教师,还做过家庭教师、书店店员,在迷茫和求索中走向革命;《苦菜花》的作者冯德英从小就生活在作品中所描写的革命家庭,感同身受,记忆犹新;曲波担任过牡丹江军分区部队的团副政委,亲自率领一支小部队,转战于林海雪原,与许家父子、座山雕、谢文东等匪军周旋竞逐。他们出于亲历者的激情而写作,许多作者并没有做好必要的文学准备,甚至也没有多大的文学抱负,因此,在死打硬拼地写出他们的处女作以后,也就没有多大的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但是,这些作者的独特优势,就是他们都是作品中描写的斗争和战争的亲身经历者和战斗者,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也往往以现实中的人物作原型(如《林海雪原》中直接用其姓名的杨子荣、高波,《红岩》中可以和纪实作品《在烈火中永生》两相参照的英雄们),加上在场者的切身感受和身份证明,从感性层面上先在地保证了这些作品的真实性乃至部分的纪实性。
同时,这些作品又都具有着较强的传奇性。这种传奇性,从表现内容来说,是和那些创造战争奇迹的英雄们相伴随的。战争是人类的巨大灾害,又是改造历史的巨大铁腕。战争将人类的心灵和情感压缩到了极致,一切为战争而存在;同时,战争又给人们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个性提供了空前辽阔的舞台,将生命的潜能、情感的蕴藏、智慧的运筹发挥得淋漓酣畅,荡气回肠。更何况,如前所述,现代中国的内忧外患,波诡云谲,革命进程的以弱对强,转败为胜,这又给人们提供了多么丰富的机遇和选择,造就了多少叱咤风云的时代英雄!就像波斯彼洛夫援引黑格尔的话所说的,英雄传奇是个人化了的史诗。民族、阶级、国家在剧烈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中形成的历史,依靠的是全社会的群体、无数人民大众的集体力量,因此,一切游离于这个历史潮流之外的个人浮沉、儿女恩怨便都显得微不足道。但是,从广大的人民大众之中是不断地产生出他们的领袖人物、他们的英雄豪杰的——譬如说,被称为荷马史诗的两部叙事长诗,《伊利亚特》刻画的是希腊联军与特洛伊人的决战,是两个民族的命运搏斗,是群像式的;《奥德赛》则是记述奥德修斯在战后返回家园时一路上的冒险和奇遇,带有浓重的个人化色彩,即所谓个人化了的史诗,是史诗的一种变奏。它们具有同一的精神内涵,是同一种创作激情的产物。
对于“红色经典”的传奇性来说,它还有个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接续和继承的问题。中国文学传统中从来是不缺少传奇因素的,中国的四大名著,都是无奇不传的。《水浒传》、《西游记》无须赘言,《三国演义》中赵子龙的神勇无敌,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周公瑾的才调无伦,曹操的阴险狡诈,都堪称为神奇卓绝。《红楼梦》的第一个评点者脂砚斋,一再以现身说法的方式证明作品中的场景和情节的亲在亲历,但是,作品的另一个层面上的奇异灵动,也是掩抑不住的:被炼石补天的女娲遗落的那块通灵宝玉,“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的虚虚实实,太虚幻境的玄虚缥缈,甄府贾府的相映相生,“风月宝鉴”的境由心造,都具有一种超现实的灵光。“红色经典”的作者,偏巧大都是在民族民间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古典文学和民间传说的传奇性,天然地融入他们的精神血脉之中。李杨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中这样写道:“随着50年代末期以《红旗谱》、《青春之歌》为代表的‘成长小说’的兴起,(以《林海雪原》为代表的)‘革命通俗小说’便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注: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第3页。)这一说法显然是不确切的。以传奇性见长的“革命通俗小说”,和李杨所说的“成长小说”,不是互相取代,而是互补互生的。一方面,传奇性极强的《林海雪原》,并没有因《红旗谱》的问世而被放逐,它在60年代前期接连被搬上电影银幕和戏剧舞台,后来的《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等更将这种英雄传奇发挥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红旗谱》中豪情侠胆、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朱老忠,闯荡过关东、见识过外面的大世界,也在骨子里继承了中国古代传奇英雄的神髓,他比起死守乡土、循规蹈矩的严志和,更多一些放纵不羁的血性,更多一些敢做敢当的英气,也更多一些开阔深邃的胸襟。他的口头禅,“出水才见两腿泥”所蕴含的乐观气息,不也凸现出河北平原上英雄汉子的奇情异彩吗?所谓奇者,言常人不能言,行常人不能行也。林道静第一次出场,令火车上的众旅客称奇惊艳,是不是奇?她在人生道路上,多次遇到种种危机,却都得以在风云际会的时代浪潮中化而解之,由一个弱女子成长为坚强的时代战士,兼具爱国救亡和阶级斗争的双重使命,是不是奇?许云峰挖通了逃身的地道,自己不用,留给后来的战友,齐晓轩足智多谋,利用敌人的疏忽,化解狱中《挺进报》被破获的危机,江雪琴目睹丈夫的头颅挂在城门洞口,忍住悲痛,继续战斗,还不足以令人拍案称奇吗?
不过,李杨指认“红色经典”的通俗性和大众化,确实是很有见地的。不但《林海雪原》等作品的通俗性创造了发行和阅读的纪录,就是《青春之歌》和《红旗谱》,《红岩》和《苦菜花》,在50-60年代的时代氛围中,也是深受普通读者欢迎、流传甚广的(笔者在60年代初期最早读到的《青春之歌》,就是在乡村度暑假时从一位喜欢读书的青年农民那里借到的)。在那样的年代里,阅读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几乎是占据首位的,更为重要的是,“红色经典”与时代精神、与众多读者之间,是“不隔”的,是息息相通、非常容易产生相互呼应的。由此产生“经典”和“通俗”的交织:所谓“经典”,是指它们在表现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历史上创造了文学的典范,即前面所说的范式;所谓“通俗”,是指在艺术表现方面,它们都注意了作品的情节性、可读性,注重了民族文学传统的承接,因而容易被普通读者接受和理解。但是,当下的影视剧改编,在这种“革命通俗小说”与时下市场化时代的、商品化色彩很浓的通俗文学—影视作品之间,怎样实现良性的沟通和转换,却是很值得研究思考的。比如说,当年的“红色经典”的读者,是宁愿保留原汁原味的青春记忆,还是甘愿接受新一代影视人对记忆的修改和重写?在没有对观众心理作出较为准确的把握时,与其自以为是,为什么不事先做一些观众调查呢?有一个现成而饶有意味的例子:90年代以来《红灯记》重现舞台,也曾经恢复过一个阿甲等当年执导的原始版本,以取代后来的革命样板戏的版本,始料不及的是,对后一个版本记忆更为深刻的众多观众,却仍然要顽强地维护自己的记忆,演出者只好又还原到样板戏的版本。这种局面意味深长,值得后来的人们深思。尽管说,《新白娘子传奇》、《春光灿烂猪八戒》和《月光宝盒》等戏说和改写类作品,也得到了部分观众的认可,但是,这和“红色经典”的改编,毕竟不是一回事。“红色经典”作为一代青少年成长时期的人生教材,它在那一代人的精神构成上,起了很大作用,今天的再开发再改编,也应当把这一点放在首位。
标签:现代性论文; 文学论文; 红色经典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青春之歌论文; 苦菜花论文; 保卫延安论文; 红岩论文; 烈火金刚论文; 伊利亚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