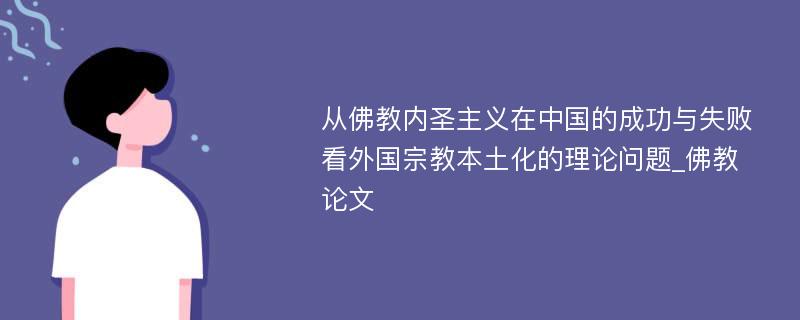
从佛教景教传播中国的成与败看外来宗教本土化的若干理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景教论文,佛教论文,本土化论文,中国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学的理论研究表明:一种自我封闭的文化不可能保持其活力,只有通过与外界的接触和交流,才能获得继续发展的动力。从历史上看,文化交流的形式多种多样,宗教传播是其中的重要形式。一种宗教传入异质的文化社会中,双方能否进行实质性的交流,外来宗教能否完成其本土化,所取决的因素相当复杂,这些因素包括外来宗教自身因素,外来宗教与本土社会关系因素,也有外来宗教传播过程中方法论因素等等。
代表着印度古代文明和精神价值之一的佛教在两汉交替之际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碰撞、冲突、融合中,逐步转型,最终完成了中国化进程。景教也是一种外来宗教,其文化传统属于基督教文明,在唐朝初年传入中国,令人遗憾的是景教传入中国仅200余年便告夭折,未在当时中国社会留下深刻的影响。 佛教在中国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最早的也是最完整的经验,而景教在中国传播则提供给我们失败的教训。本文试图对佛教、景教传播中国进行多个角度、多个侧面的比较研究,以期在外来宗教本土化的理论方面获得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一、外来宗教的传教动机问题
作为世界性宗教,佛教传教的内在推动力早在佛陀在世时就已具备。英国当代宗教学者弗兰克·惠林说:“佛陀在他的领悟中接受了一个超越现实、不可抵抗的异像,并且感到非将这个异像超越正常的社会和政治界线进行传播不可,而且这个异像被千百万人在所谓的佛教运动中所传播、所改变,并且创造性地当地化。”(注:[英]弗兰克·惠林:《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传教移植的比较宗教研究》,原文译自瑞士《国际传教评论》,1981年10月号,日内瓦,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办,转引自《世界宗教资料》1983年第3期,第17页。 )佛教初传中国的历史表明:佛教向中国传播是以一种自觉的、主动的和平方式进行的,是纯粹意义上的宗教传播。而中国人接受佛教主要出于探索真理、寻求精神解脱的纯文化动机,这在历代赴印求法的高僧身上有充分的体现。可以说,佛教传播中国基本上摆脱了政治上的功利主义影响,而中国人也以一种超功利的文化态度来接受印度佛教。佛教初入中土为两汉之际,统治者对佛教的信仰只是为了去灾得福,求得个人的幸福,基本上没有从政治上加以利用。只是到了两晋时期,对佛教的利用才逐渐加强,但这始终不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主要方面。中印文化交流中忽视政治功利性的倾向,使得中国佛教徒能真正做到为法捐躯,自觉传法,理解印度文化,最后加以融合、创新。
景教是在被判异端后转而向东方寻求发展的,其间受到当地统治者的迫害,可以说景教传教在许多情况下是迫于外界压力下的。景教在唐初进入中国,史料(注:中国史籍中关于唐代景教的记载,主要见诸《唐会要》卷49、《册府元龟》卷546、卷971、 卷975 、 《全唐文》卷727、《新唐书》卷112、《旧唐书》卷18以及宋代人宋敏求的《长安志》卷10。此外佛经《大正新修大藏经》、《贞元释教目录》等当中也有若干片断的记载。)表明:当时的统治者对景教进行利用从未间断过。从唐太宗邀请景教士在宫中译经,到允许景教传播天下;从官员对景教士的重用,到武宗灭佛时对景教的殃及无不显示唐王朝对景教的利用。从景教士的活动看,初入中土的景教士将活动的重点放到宫廷中,他们为欲邀宠,或造奇器异巧进呈皇上,或参与政务,做了许多与传道无太大关系的事务,这些概与景教的商人身份有关系。有许多学者认为,景教是叙利亚和波斯商人的宗教,从事商业活动是景教徒的特点。景教发源地叙利亚及安条克,爱德萨、尼西比斯等地均为商业繁盛之地,其信徒有不少商人。进入波斯后,景教不得从袄教徒中争取改宗者,其信徒多为受袄教教义歧视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景教徒未曾享有国教特权,他们必须从事各种职业以谋取自给自立,这样集商业传统、工艺技巧于一身的景教徒便很快成为成功的商业社团。景教士可以经商,商人也可任圣职,传教和经商并行不悖,至伊斯兰教时代,虽有穆斯林商人的竞争,但因商路大开,景教通过商人往东传遍各地。值得注意的是,景教教会的兴衰几乎与东西商路的兴衰紧密相关,现今考古发掘的景教遗物,分布范围远比文献记载的要广,大概对于景教商人,必是利之所至,无远勿届。景教传入中国,是以商业为先导的,无论是借从商传教,或借传教从商,传教的纯粹性都会大打折扣,进而影响景教本土化在中国的自觉开展。
从佛教与景教的传教动机中,我们得到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只有摆脱文化交流中的各种功利性倾向,才能使文化获得真正融合的可能。
二、外来宗教传播的时机选择问题
宗教在异质文化中传播,应该选择在适宜的社会环境中,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必须是被传播的客体(接受国)有所需,而传播主体(外来宗教)又能满足这一需求。这里所讲的社会环境主要包括接受国的对外环境,社会环境和思想环境。
第一,接受国的对外环境。
代表古代印度精神价值的佛教和代表西方基督教传统的景教是在汉唐两代分别传入中国的。汉唐两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的盛世,在当时世界历史上都占据重要地位。因为它们的影响,世界各国称中国人为汉人、唐人。当汉王朝强盛之时,只有西方的罗马帝国可与之匹敌。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方世界出现了4、5百年的经济停滞和文化衰败时期,后经过法兰克王国、查理曼帝国的缓慢恢复,直到10世纪以后才有了新的发展。中国的情况则与之不同,汉王朝结束后虽也出现过3、4百年的分裂,但社会的发展却是持续向前的,“在中世纪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注:[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429页。)7世纪初建立的唐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更是空前繁荣。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向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多的物质保障和心理上的安全感。当时只有穆斯林的阿拉伯帝国可与唐朝相比,但它在当时世界上的影响是不及唐朝的。
强盛的社会表现出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势。汉唐时期经济发展、国家强盛、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中国的长安、洛阳等地在前汉、后汉两个朝代都出现了四夷宾馆会萃,殊方异物聚合的情景。班固在《汉书·西域传·赞》中写道:“(孝武之世)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马充于黄门,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于是广开上林,造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兴造甲乙之帐,落络以随珠和璧。天子负黼衣,袭翠被,冯玉几,而处其中。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各。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鱼抵之戏,以观视之。”可以说,这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唐时更是如此,贞观二十一年(647)三月,唐太宗“以远夷各贡方物,珍果咸至, 其草木杂物有异于常者,诏皆使详录焉”(注:《册府元龟》卷970, 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分册,第11400页。)。至于史书所记来自外国的物品, 名目繁多,不胜枚举。(注:请参阅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下编:对外贸易。[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一章,大唐盛世。)对汉唐吸收外来文化的气魄,鲁迅先生评价道:“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驰使,绝不介怀。”(注:《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01页。)
对外来文化开放的态势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自西汉以来外来文化越来越多地进入华夏大地,以至于有记载写道:“(东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注:《后汉书》志13《五行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分册,第3272页。)至唐代“长安胡化极盛一时”(注: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1页。),洛阳也是“家家学胡乐”(王建的《凉州行》)。当时的胡风之盛,在元稹的《法曲》中可见一斑:“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决不只是简单的拿来,而是在吸收中有消化,在发展中有创造。以中国与佛教的关系为例,在接受外来佛教文化过程中中国并没有被全盘佛化,相反却出现了佛教的华化。
佛教、景教都是在开放的历史时代进入中国的,这是二者表现一致的地方,此为外来宗教本土化的前提条件,具有规律性。但在开放内容方面二者略有不同,主要表现为两汉时期的中外交往是在比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中进行的,张骞通西域主要出于“断匈奴右臂”的政治目的,加强中外文化交往并不是统治者自觉的行动,而是发展政治势力过程上带来的一副产品,结果导致了对外来宗教政治功利性倾向的弱化,这种情况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反倒成全了外来宗教,汉代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可能受益于此。与汉代不同,唐时的对外交往是在统治者对外政策指导下的自觉行为,它有着很强的功利性,当外来文化有利其统治,便采取积极促进的政策,反之,仇外心理则给予外来文化以毁灭性打击。景教在唐代的命运受到了这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二,接受国的社会条件。
人们对宗教的需求有其心理学基础。一般情况是,宗教往往盛于动乱之世,其原因在于动乱之世易使人们产生恐惧感和依赖感,在古代人们选择摆脱恐惧、寻求依赖的最常见的途径是借助宗教帮助,以获得心灵的安慰。陈垣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中,对宗教与社会现实环境的关系作了这样的表述。他说:“人当得意之时,不觉宗教之可贵也,惟当艰难困苦颠沛流离之际,则每思超现境而适乐土,乐土不易得,宗教家乃予以心灵上之安慰,此即乐土也。故凡百事业,丧乱则萧条,而宗教则丧乱归依者愈众。”(注: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卷6, 本书先收入《辅仁大学丛书》(1940年8 月)。 解放后, 科学出版社(1959年),中华书局(1962年)先后出版。)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能够迅速发展,与汉末至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现实环境有密切关系。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情形严重,失去土地的人们被迫流亡他乡。为缓和阶级矛盾,王莽宣布实行改制,改制非但没有减轻人民的负担,反到成为统治者掠夺财富的一种手段,最终导致了绿林、赤眉起义的爆发与东汉政权的建立。东汉初期社会生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东汉中期以后外戚和宦官交替控制中央政权,广大人民无衣无食,被迫起来反抗。到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被镇压后中国又陷入三国鼎立的纷乱时期,中经西晋短暂的统一,又陷入“五胡十六国”更大的动荡之中,战乱遍地,民不聊生,“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底—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页。 )两汉交替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以其通俗的天堂地狱,业报轮回之学说,与中国固有的方术迷信有机结合,为苦难人生指示了一条简单、方便的解脱之路,因而信佛者甚众。从根本上讲社会的黑暗为佛教传播提供了温床。对此梁启超先生论述道:“季汉之乱,民疾已甚,喘息未定,继以五胡。百年之中,九宇鼎沸,有史以来,人类惨遇,未有过于彼时者也。一般小民,汲汲顾影,旦不保夕,呼天呼父母,一无足怙恃。闻有佛如来能救苦难,谁不愿托以自庇。其稔恶之帝王将相,处此翻云覆雨之局,亦未尝不自怵祸害。佛徒悚以果报,自易动听,故信从亦渐众。”(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51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页。 )这种社会现实与景教初传中国时唐之“贞观之治”及开元盛世形成鲜明的反差。
唐朝建立以后,统治者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不仅稳定了封建社会秩序,提高了大唐王朝的威信,而且也使封建地主政权日益巩固和发展。尤其在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期间,国家政治比较清明,经济有较大的发展,民族关系得到改进,社会秩序安定,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出现了历史有名的“贞观之治”,表现为“天下大稔,流散者威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注:《资治通鉴》卷193,《太宗皇帝》上之中,唐纪9,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分册,第6085页。)这里虽有夸大事实粉饰太平的成分,但多少能反映出贞观时期的社会状况。唐高宗即位之初,依然执行唐太宗的“治术”,政策法令照旧,“永徽(唐高宗的年号)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注:《资治通鉴》卷199, 唐纪15,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分册,第6271页。)。唐玄宗统治的开元年间是唐王朝的全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发展时期。唐玄宗统治时期唐朝积聚了丰盈的物质财富,“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聚粟帛,动以万计。”(注:《资治通鉴》卷216,唐纪32,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5分册,第6893页。)长安洛阳地区的国家粮仓积如山,甚至达到了“陈腐不可较量”。总之8世纪中叶以前唐王朝国力强大, 社会秩序比较安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在社会条件方面,景教发展的机会较佛教要差得多。时机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该宗教传播的效果。景教在中国初传的失败不能不和其没有适宜的社会环境有关。
第三,接受国的思想环境。
为什么要接纳外族宗教?从接受学的角度来分析,首先必须有这种需求,而外来宗教恰好能满足这种需求。一般说来,本族文化尤其是民族的精神生活处于一种危机状态,人们无法解决现实存在的种种矛盾,对本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念(宗教、道德、制度、风俗)发生怀疑、失望以至绝望,期望得到新的拯救时,易使人追求新的(与自己的传统不同的)价值真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民族的宗教能够以某种新的方式给人们带来生命存在的文化前景,能够安抚人们的心灵,唤醒人们伦理道德意识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它自然而然地就会在本民族得到流传,得到人们的自觉接纳。这样,本民族文化就会借外族宗教的激励而获得新的活力,现实中的社会问题和精神矛盾以新信仰的价值系统为依据得到发展机会。
佛教景教传入中国所面临的思想环境不尽相同,表现在佛教对汉代以来中国思想发展有补缺作用,而景教在这方面则显得苍白乏力。
所谓佛教的补缺作用第一个含义是指,它填补了汉代儒学衰落所形成思想空隙。从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的方针后,儒家学说便成了汉代的统治思想,与之相辅的是对儒家经典进行烦琐考证和牵强解释的经学。汉末以来黄巾起义、三国争霸、群雄割据、权奸起伏、经学的谶纬化以及儒家学说对乱世的无能为力,使人们本能地产生对儒家理论的厌倦。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经世主义不再具有往日的吸引力,独尊儒术的思想信条逐渐被人鄙弃。儒学的衰落在中国的思想界形成了一种空隙,为佛教的传入创造了一种千载难逢的时机。佛教的出现以其独有的出世思想,不仅填补了因儒学衰落所形成的思想空间,同时在与方兴未艾的玄学的交汇中,给中土人士开立了一种新的安心立命之道。
所谓佛教补缺作用的第二个含义是指,它又弥补了汉文化形而上领域缺失和彼岸世界图景模糊两大缺陷。在汉民族思想发展史上,周代以前曾有过较为发达的国家宗教。但是古代宗教从周初开始便走上了人文主义的发展方向。周代崇尚德政,敬德保民等观念,一改商文化重鬼治轻人治的倾向,反映了周人开始对天命观念的动摇和对人事的注意。以后又经过春秋战国疑天、怨天(注: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论语·宪问》,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6页。)、骂天思潮的冲击, 古代文化中理论与宗教逐步分离,传统宗教走向了重礼仪而轻理论的世俗化方向。而士大夫阶层则走上了理性主义道路。孔子提倡“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注: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论语·宪问》,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3页。 )荀子讲:“唯圣人为不求知天”(注: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荀子·天论》,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0页。)。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使中国士大夫很早便摆脱了宗教观念的束缚,但也造成了汉文化形而上领域缺失和彼岸世界图景模糊两大缺陷。西汉时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搞经学研究,但仍然无补原有的缺失。从终极关怀的角度着眼,汉代谶讳迷信虽然发达,但关于彼岸的一些问题并没有解决,宗教遇到了无神论思想家的尖锐挑战。比如关于灵魂的问题,灵魂不死的观念三代就有,但古代宗教相对简单,关于灵魂消翕归宿的问题并没合理解决。到了理论思维比较发达的汉代,王充便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计今人之数,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辄为鬼,则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注:(东汉)王充:《论衡》,《论衡·论死》,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16页。 )佛学的理论多集中于人生痛苦与解脱,在这个问题上佛教作出了自己独特的价值判断,其中的一些理论如“轮回”、“业报”、“因缘”、“因果”、“三世”等等说教,正是中国固有文化所欠缺的。佛教的传入,解决了中国文化这方面的难题,灵魂不死,业报轮回,因果报应,天堂地狱,解脱涅槃,佛教将人生与死后的问题比较圆满地连结在一起,满足了中国人对自我存在于彼岸世界的思考。
与佛教东传初期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一些变化不同,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滞迟缓慢发展的渐变积累,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期滞迟缓慢发展的渐变积累。历史没有提供总结和建立新的理论体系的社会条件,也就没有将总结和建立新的理论体系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不仅如此,在景教传入之前中国的儒释道三学已有高度的发展。中国先哲的思想体系与佛教思想之合流,其理论思辩足以和基督教(景教)思想相媲美,因而不需要对它们的学说进行调整或填充,此时中国文化的传统渗透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法的各个方面,它是吸取外来文化的母体。与景教风貌极不相同的中国文化,极大地制约了中国景教文化及它的具体发展方向。
唐朝前期社会繁荣而开放,虽然思想界也显示多元共容的文化格局,但这并不等于说各种文化因素都处于平列对等的地位,其中为主的只有儒、释、道三家。它们在当时的中国思想舞台充当主角,当势力弱小的景教进入中土时,已经没有插足这一事局、并向社会施加重要影响的机会,它能做的只有侧身三教其间左右依傍,作为一个观众注视着三家在唐代意识形态领域里各显神通了。
总之,外来宗教通常选择在开放的社会,当接受国民族精神生活危机,外来宗教自身对接受国传统文化具有补缺作用时,则其本土化成功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三、外来宗教本土化的方法论问题
外来宗教本土化的方法论问题属于一个实践范畴,具体操作起来涉及到十分广泛的文化内容,一般说来必须正确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是经典的译释问题。
高级宗教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有一整套日渐繁密而系统的神学体系,虽然灵异神迹是宗教吸引信众之不可或缺的手段,宗教的传布却必然是以教义的传布为中心,而教义的传布则要以经典的传译为前提。
西来佛僧传教的一个重要活动就是从事佛教经典的翻译。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得以在中国传播发展,同佛经的翻译密不可分,译经活动长期以来成为中国佛教传播运动的中心事业。两汉交替之际在中国内地流传的佛教经典,仅有口授的《浮屠经》和《四十二章经》。西汉哀帝时(前2年),西域高僧、 大月氏使者伊存传授佛典《浮经》于汉博士弟子景卢。(注:《魏书》卷114,《释老志》十,第二十, 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分册,第3025页。)虽然《浮经》较为简短, 而且伊存和景卢之间也仅仅是口口互译,但这毕竟是佛教传入中土的最早记载。大量翻译佛教典籍直到2世纪中叶才出现。2世纪中叶以后西域各地不断有高僧大德进入中国内地,他们同汉族士人一起共同承担翻译佛经的任务。
从译经的内容看,初期所译佛经大致分安译和支译两大系统:安译即安世高系,是小乘佛教,重修炼精神的禅法,比较接近神仙家言;支译即支娄迦谶系,是大乘佛教,宣传空宗般若学理论,比较类似玄学。阐述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小乘经典的流通,为广大下层群众信教创造了条件。
从翻译的水平来看,最初在汉地翻译经典、传授信众的基本是西域来华的僧人,或者是迁居汉地的西域胡人的后裔。如东汉初年明帝时印度僧人摄摩腾与竺法兰。由于外国僧人对于汉语掌握得不好,常常出现翻译不确切的情况。因此在摄摩腾之后,逐渐改为外来僧人与汉族人二人对译。由于合译的梵客华僧在语言条件、知识结构和文化素质等方面的差异,译经的质量受到影响,所以这段时期所译诸经,后人往往加以重译。随着佛教的发展,对于内容丰富、翻译质量高的佛经需求更加突出。在外来僧侣中既能忠于原著的结构和文意,保持佛经特点,又能曲尽其意、正确表达的,可以以竺法护、鸟摩罗什为代表。罗什翻译了大乘佛教的《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以及《成实论》等重要论书,对后世影响深远。高水平的佛教译经的出现,不仅保证了中土佛学之士系统准确地掌握佛理,也使得大量士人研究佛学成为可能,导致南北朝时代众多佛教学派的出现。鸠摩罗什这个外来的译经大师,以他大、小乘兼备,对般若、中观学说备得其解的深厚佛学功力,开辟了中土佛经翻译、佛学研究的新纪元,至唐玄奘时译经水平和佛学发展达到极致。
与初传佛教相类似的是景教士进入中土以后也从事过经典的翻译工作。
关于景教译经的数量目前已知。发现于敦煌的《尊经》末尾有段附文,这段附文写道:“谨案诸经目录,大秦教经都五百州部并是贝叶梵音。唐太宗皇帝贞观九年,西域大德僧阿罗本届于中夏,并奏上本旨。房玄龄、魏征宣译奏言。后如本教大德僧景净译得卅部,卷余大数具在贝叶皮夹,犹未翻译”。这说明景净在当时已译成汉文30部,应当说,唐代景经的翻译数量是很有限的。
唐代景教经籍翻译从阿罗本来到长安以后就开始了。现已发现的景教文典除景教碑以外,还有7篇,它们是《序听迷诗所(诃)经》、 《一神论》、《宣元至本经》、《大圣通真归法赞》、《志玄安乐经》、《三威蒙度赞》、《尊经》。经学者的研究,《序听迷诗所经》、《一神论》、《宣元至本经》、《志玄安乐经》属经文,其余为颂文。译述于初唐的是《序听迷诗所经》和《一神论》,译述于中晚唐的是《宣元至本经》和《志玄安乐经》。上海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翁绍军先生在对前后期译经的类型进行了仔细比较,得出:前期景教文典呈原典化传述类型,后期则呈本土化类型,基督教教理呈现逐渐淡化的变迁和取向。(注:翁绍军:《汉语景教文典诠释》,三联书店1996年版,导论部分。)笔者同意这个结论。
引进外来文化离不开语言翻译,语言与文化呈相依相存的关系,文化渗透于语言的各个层面,特定的文化反映在特定的语言之中。翻译既是在进行两种语言的转换,同时也是在进行着两种文化的转换。将外来宗教经典翻译为本土语言,这是外来宗教本土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外来宗教的流传过程中,经典的翻译水平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们对经典的接受程度。由于不同的经典代表不同的文化,如果生搬硬用原来的语言、词汇,地外来经典不加以本土化的加工,不改变其“外邦之物”的形象,人们读起来费劲,念起来拗口,思考起来不与本土思维习惯相适应,必然阻碍人们接受外来宗教。所以经典概念、范畴的本土化问题十分重要。初入中国的佛教非常重视经典的翻译,在历代佛经翻译家的努力下,佛经的翻译质量不断提高,这种提高也体现在佛教对自身义理特性的坚持上,这一点犹为可贵,也犹为重要。而景教的译经水平从初期的原典化传述转向后期的本土化传述,则导致了其教法义理逐渐暗淡湮没,这一点不可不视为唐代景教失败的重要原因。
第二是外来宗教和价值与本土精神价值结盟问题。
外来宗教在异质文化土壤中生存和发展,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交流和融汇现象。当外来宗教进入本土后,由于不可能全部被接受,它必然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其过程存在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只有同本土的类似的或相适应的精神价值结成联盟,表明自己对本土文化传统的认同,外来文化才能存在和发展。否则它的精神形象对于本土来说仍然是异己的。另外对外来宗教来讲,还要处理好认同本土文化传统与坚持自性的关系。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盟就是一个典型实例。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属于印度文化,有其独特风格和个性。初入中土的佛教也面临中华文化价值不认同的严峻挑战,但佛教并未故作坚持、永不合流的高傲姿态,而是积极地、谦卑地把自己作为本土文化价值的附会者和迎合者,它最初附会与迎合的是传统的道家思想。为了适应中国文化,佛教不仅在宗教术语的译名上采用道家概念,在生活态度上也以一种超然世上、看破红尘的方式而与道合。在这里佛教借用中国人熟悉的黄老之学等一些概念对佛教教义作迎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使之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相亲和而趋向“一致”,如果不利用道家的思想媒介作用,佛教那些深邃而广泛的内容,很难在当时直接为中国文化吸收和消化,佛教的思想意境正是通过道家之说而为中华民族所理解和接受,这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当佛教渡过了最初的艰难岁月后,便逐渐由形式上的依附转向内容上的独立,东晋时期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明显化就体现了佛教坚持本宗义理的独立意识。从最初的依附,到成长过程中的独立,最后融为中国思想文化之中,佛教成功地完成了它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由此看来佛教在中国传播总体上不是采取同中华文明相冲突的走向,而是采取了相交融、相嫁接、进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一部分而又不失佛教本色的一种文化走向。从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特点看,佛教这种传播既不是简单的空间移动而无变化,也不是变得面目全非,以致有陌生之感,而是既保持了佛教的基本信仰和基本生活方式,又发生了部分中国化变化,获得了佛教的和中国的双重品格。如果采取象景教那样的传教策略,一味地同中国传统文化相妥协、相调和,在依附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以致丧失自身的独立性,那么最终失去的将是这种宗教本身。
第三是关于文化载体阶层的作用问题。
所谓文化载体是指文化的主要传承者。文化环境对于外来宗教特征的改迁作用是潜移默化的,这种影响又是通过信仰该宗教的士大夫知识层而发生作用的,就佛教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关系而言,历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僧侣是承担佛教中国化的主要角色,是佛教中国化的代表。这些人大部分具有厚实的儒学文化基础,然后又接触、学习、研究佛教哲理、教义,这种知识形成的层次、程序和结构,必然深刻地影响整个社会对佛教的理解和接受,也促使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在考察魏晋时期佛教迅速发展的原因时,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信徒,如汉魏时期的严佛调与朱士行,以及晋代的道安、支遁、慧远和僧肇。这些中国僧人大都受过中国文化与学术传统的熏陶,道家之崇尚自然、儒家之重人事的理性精神在其思想中影响至深。他们的出现一改汉魏佛教神仙方术之风,而致力于佛教义理的探析与理论的建设。受魏晋玄风吹拂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深奥圆融的佛理产生兴趣并发生思想上的契合。特别是晋室南渡之后,知识分子中亲佛者骤然增多,如王导等与帛梨密多罗“披衿到契”,交往甚密。(注:释慧皎著:《高僧传》卷1,收入《大正藏》第50页,第327页。《大正藏》由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1990年初版。)殷浩精研《小品》。(注:《世说新语·文学篇》,转引自徐震萼:《世说新语校》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4页。)何充“性好释典, 崇修佛寺”(注:《晋书》卷77,《何充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30页。),其弟何准“唯诵佛经”(注:《晋书》卷93,《何准传》,中华书局1974 年版, 第2416页。)等等。魏晋以后大量知识分子投身佛教的研习,不仅使佛教的社会品位得到提高,同时也使得知识分子阶层逐渐成为佛教的主要社会基础,并进而带动了一批最高统治者亲佛,如晋元帝、慧帝、明帝、恭帝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与佛教的结合中走了一条成功之路。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景教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发展的有限性。
唐代知识分子在景教徒中所占比例很小,此推论的理由有3 :其一从景教碑引文中判断,归信景教之人,多为被施以救济之人,其中包括“馁者”、“寒者”(注:见景教碑文。)以及无力医病、无力安葬之人,此阶层自然是生活没有保障的贫苦之人;其二,从现存的景教文献来看,除《景教碑》、及《三威蒙度赞》等,堪称上乘之作外,其它如《序听迷诗所经》、《一神论》、《志玄安乐经》等文笔均极为拙劣。就文笔典雅的景教碑来说,虽说作者是景净,但也很有可能借汉人之润色而成。在《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中有景教碑的撰述者景净曾与梵僧接触,两人共译佛经一事的记载。文中说:“法师梵名般刺若……泊建中二年(782),届于上国矣。至贞元二祀(786)访见乡亲。神策正将罗好心,即般若三藏舅氏之子也,悲喜相慰,将至家中,用展亲亲延留供养。好心既信重三定,请译佛经,乃与大秦寺波斯僧景净,依胡本《六波罗密经》译成七卷。时为般若,不闲胡语,复未解唐言:景净不识梵文,复未明胡释教,虽称传译,未获半珠。图窃虚名,匪为福利。”(注:转引自(英)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4页。)当时的般若法师不懂唐言,而景净亦不识梵文,两人既合作译经,非有汉人从中作语言助手方可进行,因此,景净必然要与晓通语言的汉人进行接触,在此过程中,求助汉人将其所译之景经进行润色,是极有可能的。景净得以汉人接触,是件幸运之事,但这种合作很快因圣上的干涉而中止。《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又接着说:“录表闻奏,意望流行。圣上濬哲文明,允恭释典,察其所译,理昧词疏。且夫释氏蓝大秦寺,居止既别,行法全乖。景净应传弥尸诃教。沙门释子弘阐佛经。欲使教法区分,人无滥涉,正邪异类,泾渭殊流。”(注:转引自(英)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4—75页。)由有典雅如景教碑之名作少有出现,也可证明有学问的汉人景教信徒较少;其三,在唐代的文献中,景教与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发生直接交往的记载极少,不曾象佛教那样留下了一部《理惑论》供人们研究,也是景教徒中缺少知识型人才的一个旁证。
近几十年来,在学术界,特别是西方的社会学家和史学家,对知识阶层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研究,兴趣浓厚。通过对比佛教、景教初传中国与知识阶层的关系,我们有理由认为:知识阶层在接受外来文化(包括外来宗教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这种作用“无论作何估价都不会太高。要知道,外来文化流传中国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国传统价值与帝国政治,而士大夫知识阶层正是传统价值之最有力的维护者和社会文化之承袭者。在君主权威的阴影下,他们或许从未获得过真正的政治主体的地位,但他们无疑是影响帝国政治中有能量与活力的阶层,对帝国政治的运作乃至君主的意志具有深刻的影响力。何况作为传统之唯一合法的解释者,他们还持有这种极为有效的武器,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传统导向的社会中,个人对群体,群体对传统的依附乃是绝对的,即使君主也不能例外,正是这个能量极大的社会阶层从根本上影响着官方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深刻制约着外来文化在中国的发展。事实上,两千年来,佛教传法中国所遇到的主要抗力并非来自民众,而是来自士大夫知识阶层。只要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佛教同士大夫阶层的契合,在佛教传播中国的过程中,该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注:刘莘:《论汉晋时期的佛教》,载《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
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证明:任何一种外来文化的移植,首先必须在本土文化精英(知识分子)中取得认同,使它成为本土文化精英的自觉事业,不然,它必将仍然长期处于文化表层,而在文化深层结构中无立足之地,处于被批判、被阻碍、被排斥、被挑战的地位。(注:参见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457页。)景教在中国唐代流传的断档,与没有取得广大知识分子阶层的认同有重要关系。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一种文化的命运,归根到底决定于历史、时代、阶级和群众的需要。在外来文化的传播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关键性作用固然不可少,但上层人士和平民百姓则最终决定着文化的命运,这是因为上层的统治权力可将任何外来宗教控制在自己手中,而宗教在民众中的传播,也可保证外来宗教获得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最广泛的社会影响。所以说外来宗教和价值只有成为人民生活中的通俗的、日常的存在,才能获得真正的立足。同时它也应该贯通本族文化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甚至及于个亚文化系统,只有如此它才能在异族当中生存下来,并不断走向稳固。
四、结语
外来宗教在异质文化环境中传播、成功地完成其本土化,是需要一定条件支持的。除了宗教自身具有无功利思想意识的传播,还要对传播时机进行选择,处理好传播主体与被传播客体之间的关系。佛教本土化的成功与景教的失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即: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程度。外来宗教想要在本土文化中长期存在下去,在经典的译释,宗教文化在本族各个社会阶层中的贯通等问题上应当注意其方法的运用。
在外来宗教本土化理论研究中,除上述所论外,我们还有必要强调以下两点:
第一,一种外来文化若能成功地在一国传播和发展,还要取决于这种文化自身的素质,就是说,它必须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一方面能够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正确解决传播过程中与接受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来顺应或同化接受国民族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还必须保留自身的特点,充分利用时代和社会提供的各种条件来发展自身。
第二,文化交流的实质,就是不同文化间的互利和认同,对异文化的忽视、藐视以至敌视,则是缺乏文化交流意识的表现,不符合文化进化的大势;同样在异文化面前盲目地形成对本土文化的否定态度,也是一种不正确的文化心态。
标签:佛教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文化论文; 唐朝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汉朝论文; 本土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