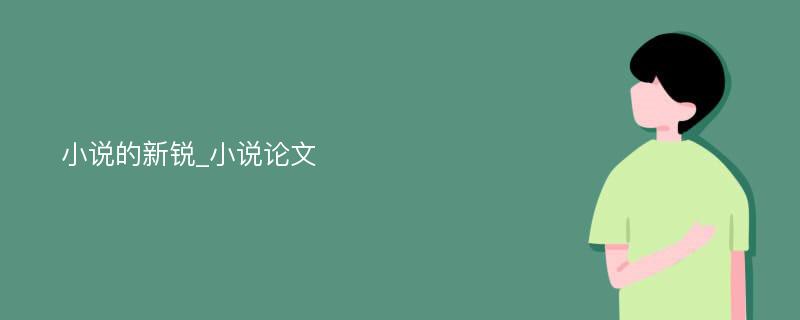
长篇小说的新与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篇小说的繁荣与影视剧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文学基础,为银幕和荧屏增添了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
进入新世纪,由于作家们普遍看重长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市场化运作的相对成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都在以稳中有升的姿态持续发展。2005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大致上也是在这样一个基本态势下开局和收尾的。
从总体的阅读感受上看,较之于往年的长篇小说创作,2005年间出自于文学名家的作品先后联袂而至,数量显著增多;且许多新作都在选题,立意和写法上,表现出不少新的努力和新的变化。还有,就是包括了这些名家新作在内的长篇小说写作,在观照现实和看取生活上,视角更为切实,视野普遍下沉,更关注“过去时”的历史演进和“现在时”的日常现实,在人物塑造上,作家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社会下层的普遍平民和蓬门荜户的市井百姓,使得许多“小人物”不仅纷纷进入作品,而且成为挑梁唱大戏的主角。在显现题材和题旨取向的同时,重在讲故事的,侧于写断面的,着力写意向的,纷纷登场亮相,表现出作家在表现生活的丰富性和叙事手法上的多种可能性。
乡土谣:是牧歌又是挽歌
这些年,乡土题材写作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一直没有间断。但在叙事手法和写作态度上,较之以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小说的内容构筑不一定以故事为主,而是一种细琐的事象和连缀的片断,向乡村生活的原生态逼近;而作家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描写对象,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味地铺锦列绣,莺歌燕舞,而是以一种惆怅的情绪、反思的态度,既抒写其前所少有的新变,又哀叹其不该逝去的恬静,把作者的怀恋与困惑一股脑地端了出来,让人们在阅读中进入对当下乡村现实的沉思与反思之中。
年初,阿来拿出了新作《空山》。作品以细节化的现实图景,深切叩问一个小人物和一个小山村的悲辛命运。卷一《随风飘散》,写小男孩格拉,如何因人言而被虐杀;卷二《天火》,写藏乡机村怎样为激进的时世所摧折。无论是写格拉的冤屈,还是写机村的颓势,阿来都没有在事件本身上花过多的笔墨,而是把笔力放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和不可遏制的压力,人们情感上和精神上的艰难承受与痛苦变异的过程。事实上,经由精雕细刻的细节描画和从容不迫的叙事节奏,人们看到了那种由小到大、由外到内的外在打击,是如何在机村人的精神世界激起回响,撞出创痕,并在人生的被改变和命运的被改写中,发出无声的哀叹与无言的抗争。与这种注重心理状态的细切描画相适应,作者的语言是温和的,情感是内敛的,这种哀不放声,怒不形色的写法,更加加重并深化了作品的情感底蕴,使得整个作品有一种雄浑沉郁的情感的力量在暗中运行,而且以其“于无声处听惊雷”般的内力,隐隐地感染着人,深深地撞击着人,让人们更多地从人之常情、事之常理的角度,去同作者一样诘问和思量一个少年被戕害和一个村庄被折损的蹊跷命运。
著名作家余华携新著《兄弟》在上海书展签名售书 南山摄/CFP
凹的《秦腔》,则动用了他一直珍藏在心底的关于家乡的积累、记忆与困惑。作品在时代大背景和社会大变革中,写了农村的新旧交替与农民的游离土地。一边是新兴商品经济不可阻挡的强劲冲击,一边是传统村社经济的江河日下与日益解体,农民们在忙活家常生活的同时,无不对目下的出路与今后的前景感到惶惶然、茫茫然。关于村社文化的式微,关于秦腔艺术的衰落,都使作品带上了浓得化不开的悲剧氛围。作品像是借用苍凉而悲怆的“秦腔”,在为现代乡土文明的悄然变异吟唱一曲悠深致远的挽歌,让人惆怅,引人深思。因为语言表述的方言化和叙事的“鸡零狗碎”,《秦腔》这部作品不是很好读,这也跟作者原先只是作为个人笔记而写作,没有过多考虑读者的接受有关。可能也与作者在叙述视角上的常态的、变态的和奇异的多向复合不无关系。
与上述两部作品明显不同,毕飞宇的《平原》,是以清新引人的乡土故事取胜的。在这部长篇新作里,作者以充满乡土质感的丰沛感觉和丰饶细节,讲述了苏北乡村少年端方在一个特定年代里的充满坎坷的生存状态与成长经历。作品给人深刻的印象或唤起人们沉重记忆的,是“文革”期间弥漫于日常生活的乡村政治,以及无处不在的政治权力对农人的有形无形的制约——包括应有的尊严、自发的爱情、当兵的夙愿。在这里,无告与无奈交织在一起,让你权且活着但又活得惆怅而憋屈,让你怀有理想但总是得不到真正的实现。因而,那些生长于和成长于“平原”的普通农人的人生,其实并不平坦和顺遂。在如何把作品既写得好看,又耐得起咀嚼上,《平原》无疑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小说文本;在揭示乡村生活在现代以来的如何走向了政治化,以及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和几代农人的成长方面,这部作品无疑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文本。
一直醉心于现实题材的刘醒龙,推出了潜心六年写就的长篇三部曲《圣天门口》。作品的时间跨度从上个世纪的初期到晚期,将近一个世纪,人物谱系有雪、杭两大家族,国、共两大势力,围绕两大家族和两大势力也称得上纵横交织、林林总总。小说虽然头绪繁多、故事繁杂,但纠结于雪家、杭家的世代相争的主线索的不同政治力量的斗争、不同文化信仰的较量,以及串结其中的情爱纠葛婚恋恩怨,主要揭示了崇尚暴力与暴力革命在推进历史的进程之中显而易见的双刃性:它一方面通过集权的方式、极端的手段加速了政治目的的实现,使传统的乡间走向了现代化、革命化;一方面又以血腥的争斗和惨烈的后果,把人际关系简单化,把社会生活粗鄙化,从而使传统乡间的人文伦理和田园梦想日见稀薄,甚至风光不在。作者在这样一个主干故事中描述的鄂东地域的区间革命史和乡间演变史,是让人荡气回肠的,又是蕴涵氤氲的。由这样一个悲壮又悲怆的“天门口”沧桑演变构成的历史长叹,是激人猛醒的,又是引人长思的。
平民谱:小人物背后的大历史
在2005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不少作者纷纷将艺术目光移向社会生活的底层民众,投向日常生活中的寻常百姓,以小人物的生死歌哭和悲欢离合书写时代的曲折演进,状写社会的浑重背影,使得其作品在“以小见大”之中,更富于严谨的现实主义精神,也更具有亲合大众的人民性。而那些出身微贱、性格鲜明的“小人物”,通过作者的文学打磨和艺术提炼,成为靠近大众经验又富于平民情趣的个性化典型和艺术化结晶。
余华的以“文革”为背景、以刘镇为场景的《兄弟》,正是以普通的乃至底层的两个破碎的家庭重组为一家人的种种遭遇,写了“小人物”在特殊年代里的异常艰难的生存状态。好不容易从破碎的婚姻走到了一起的宋凡平和李兰,刚刚有了家庭的些许温馨,因为出身地主家庭,宋凡平被“红卫兵”无情地批斗致死;出院回家的李兰把丈夫擦洗干净,躺在他的身边睡了最后一个晚上;之后,为了给丈夫守孝,7年没有洗头,在临终前终于进了一次澡堂,一洗白了头。一边是冷漠与冷血,一边是温情与温馨,普通平民就这样在最无情的年代守护着少有的爱情,生发着难能的友情。两个并无血缘关系的孩子李光头和宋钢,就这样由相识、相依,走向了相亲、相靠。作品中,由武斗和暴力构成的社会环境的冷酷,由理解和爱怜构成的家庭生活的温热;宋凡平和李兰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给予对方的人格尊严,以及他们不顾一切地对这种尊严的自我维护,都让人感动感奋,起恭起敬。
顾坚的长篇新作《元红》,是一部好读又耐读的作品,主人公就是一个名叫丁存扣的苏北水乡的小农民。作品围绕小存扣由从9岁到35岁的人生历程,从他懵懂无知的童年,写到情窦初开的少年,又由他意气风发的青年,写到弃教经商的中年。他由小到大一步步的悄然成长,他与众多女性温婉的情感纠葛,以及贯穿其中的美好与苦涩、快乐与悲怆,都由密密扎扎的细节串结起枝繁叶茂的故事,写出了“小人物”颇为不易的成长经历,也写出了“小人物”亦喜亦忧的人生滋味。作者那几乎是顾不上梳理的倾诉,忘记了择选与顾及的描述,使得人物在一种接近天然的环境里“疯长”,反倒让人读来淋漓痛快,感觉格外真实;又因为故事的悲喜交错、人物的“长”“短”杂糅,作品让人时而欣忭,时而焦虑,总是在既愉悦又忧伤的情绪里徜徉和激荡。
东西在他的《后悔录》中着力描述的“后悔者”曾广贤,既是生活中很不起眼的“小人物”,又是近年来小说人物中最具个性的“这一个”。他一直对性萦绕萦怀,做梦都想得到性,甚至因为强奸罪坐了8年牢,但实际上却没有经历过一次真正的性。为自己一不小心将父亲的情事“泄密”,父亲遭受残酷迫害,30年不和他说话,母亲死于非命,妹妹失踪。因为一次幼稚荒唐的行为,被当作强奸犯捉拿归案,身陷囹圄8年。出狱之后毫无心理准备地一脚踏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准备跟真爱自己的两个女人中的一个结婚,因过分谨慎,把两个女人全错过了。等到一切明白过来时,已经人财两空,为时已晚。小说在一个人如何用一生来犯错,又用一生来后悔的故事中,淋漓尽致地描写了一个与女人没有情分、与时代没有缘分的背运者,总是使自己的想望与欲求在现实中频频落空的悲戚一生。曾广贤的《后悔录》,因“后悔”全是与最基本又最重要的与爱和性与自己的擦肩而过,整部小说在不动声色之中让人为之嗟叹,为之惊愕。“小人物”的人生如何失意和失落,这在某种意义上既是个人的问题,又是社会的问题。
王安忆在2005年推出的长篇新作《遍地枭雄》,也颇令人意外。一贯以女性形象为主角的王安忆,这次不仅推出了一个男性主角,而且此人还是一个边缘性的“小人物”——出租车司机韩燕来。在上海当出租车司机的他,因为在一个圣诞夜被专门抢劫倒卖汽车的三个劫匪劫持,由此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问题是他在被迫同他们一起亡命之后,渐渐地与他们越来越投合,他数次放弃了报警和逃脱的机会,反而在劫匪卖了桑塔纳之后怀揣分得的卖车款,跟着他们踏上了“游历”之路,并一起经历了再劫车和杀人,最后躲到了大王老家一处深山里废弃的钨矿,直到被警方抓获。经由这样一个蹊跷异常的故事,作者给人们道出了一个人从善到恶,由好到坏的偶然、简单与容易,以及此岸到彼岸、枭雄与英雄的一念之差和一步之遥,更由对韩燕来由出租车司机转换为劫匪同伙矛盾的心理过程的探悉,揭示了他因为身份低下和感觉失落在心里积存的莫名的愤懑和改变现状的渴望,这样的一个心态实际上和那样一个遭遇的暗合,使得韩燕来由劫持感到了某种快感,他把自己的被劫持当成了一场人生的游戏。作者在这里,以敏感又悲悯的文学的情怀,在揭露人性真实的同时,显然也对边缘性的“小人物”给予了一种善意的心理抚摸,寄予了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
王蒙在接近年底推出的名为长篇小说实为系列小说的《尴尬风流》,其主人公“老王”也是一个平民化乃至民间化的知识分子形象。300个小故事的写作本身在自由潇洒中饱带了王蒙的个人印记,作品的文体超越了通常的小说,像是文学性的小品,又像小说化的“二人转”,还有些象“情景喜剧”。王蒙式的睿智、幽默、深邃与忧思,都尽显其中。这样的以平民“小事”折射生活日常的故事,以凡人“心绪”碰撞读者“心智”的作品,引人读解,更耐人品味。
成长颂:苦涩与快乐一齐诉说
成长的主题,以前主要表现在少儿类题材作品的创作之中。但在2005年,“成长”却为不同的作家所共同关注,并以他们各具其妙的人物和故事,演绎了“成长”的丰饶主题和无尽内蕴。
偏重于少儿题材写作的曹文轩推出了小说《天瓢》。与以往的小说创作相比较,这部作品不仅超出了他惯常的题材范围,而且让人有两个意外。一个是作品里写到的许多雨,一个是作品里刻画的两个人。小说从开首到收尾,通篇是各式各样的雨,写雨的肆虐,雨的滋润,雨的朦胧,雨的暧昧,雨的裨益,雨的恶果;这里,雨是超常的,又是日常的;既是自然的,又是神秘的;既阻遏着人,又成全着人;既捉弄着人,又诱惑着人,永无止息又花样翻新。这样,雨便作为一种象征,构成了负载人的命运之舟的自然的又是历史的一条长河。而作品所主要表现的两个人物——杜元潮与邱子东,因在“整”与“被整”上相互较劲,经历彼此勾连,人生相互纠缠,把纷繁的世俗生活凝结于两个人物,又把复杂的个人命运浓缩到两个人的一生,这在别的作品中很少见到。而杜元潮之所以与邱子东在后来较劲不已,盖因童年时代受尽他的欺侮,包括玩耍的被凌辱,女友的被抢夺;成年之后的他要一一清算童年时期的旧账,并在相互较劲中彻底占据上风。童年的伤痛其实一直影响着他,甚至主宰了他成人之后的继续“成长”。
杨志军的长篇小说《藏獒》给2005年的书坛送来一波雪城高原的劲风蒋韵的长篇新怍《隐秘盛开》,以卓富诗意的文笔和通体浪漫的叙事,抒写了一个女性在情感上默默守护的暗恋,其实也是从情感的角度书写女性的成长。女主人公潘红霞,自幼性情恬静,品格坚贞,她用全部生命去爱竖笛姐姐,却发现那神仙一样的竖笛姐姐心里,其实并没有她的位置。后来考取大学,毕业留校,结婚离婚,生病旅行,几十年里把对一个男同学的暗恋,作为重要的人生目标在内心呵护着、发展着,到生命最后时刻,在从巴黎自助旅行去西班牙的路上,将这秘密交付给陌路相逢的年轻女子米小米。而米作为这场暗恋的信使,将潘的故事写成书,并代她拥抱了那男同学。故事忧伤之至,主题浪漫之极。在这个感人的故事里,单相思是那样的苦涩,又是那样的甜蜜;从少女到成人,都一直悬空着的爱恋,使她只好把非常态当作了常态。这其实也是爱恋上的另一种补偿、情感上的另一种表现和人生中的另一种风景,而这就是不能没有爱又难以实现爱的一类女性(也应该包括一些男性)的隐秘成长史。
冯唐的《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写一个十五六岁的北京男孩的苦涩童年和艰难成长,作品里,社会生活的沉闷,家庭环境的窘迫,与学生的好奇,少年的好动,以及老师的刻板、家长的严厉,与“老流氓”孔建国的平易和亲切,构成了极大的反差。在一个人的成长中,肃杀的环境所起的反作用,严苛的父母与师长所起的负作用,所谓的“坏人”可能起到的好作用,都由真切的故事和顽皮的语言娓娓道来,让人在意料之外的阅读之中获得情理之中的感受。作品充满那个时代独具的和冯唐特有的“灰色幽默”。冯唐的小说,一般都有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比故事更好的,是“痞”中见“真”的叙事语言;而比语言更好的,是“真”中见“妙”的艺术感觉;这几样东西凑到一起之后,就自然而然地以冯唐式的精妙与精彩,使得作品既快人心目,又耐人把玩。
属于“80后”的春树写于2005年的长篇新作《2条命》,也是典型的“成长”小说。作品所主要描写的遇断和好孩子楠楠,你可以看作是不尽相同的两个少女,也可以看作是同一个少女的AB面;一个人物的两种命运,或两个朋友的境遇反差,使得作品在表现青春人生与人性上更见深刻与凌厉,也使作品在折射社会生活现实上更显丰富与浑厚。
新锐女作家章元的《20后没有初恋》,以当下时代为背景,以现代都市为场景,也给人们描绘了一个在青春中爱恋,在爱恋中成长的故事。主人公南北是一家报社的记者,很有朝气,又颇有才气,但在情感上却总不顺遂,一个出色的男人看上了她,她看上的却是另外一个男人;而她看上的男人,又看上了别的女人。在这依次错位的爱的马拉松中,所有的人都爱有旁骛地死死坚持着,又都心有不甘地苦苦追寻着,当明白了事理与是非时,又都身心疲惫,失却激情。作品在一个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故事中,揭示了当下社会在情爱方面潜藏的问题,那就是观念的开放和现实的松动形成的性与爱的分离,情与欲的游移,反倒给置身其中的人们造成了许多迷乱与迷惘,使得人们常常因误读和误解而进入种种误区。这部被媒体称之“F世代”的发轫之作的小说,实际上从反思的视角写了新一代人的在自由旗帜下的不自由,在成熟幌子下的不成熟。他们还在“成长”之中,他们需要继续“成长”尤其是以活跃不羁的青春心性面对着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世的时候。
面对近千部长篇小说这样一个巨大的文学存在,以上的在几个倾向性话题下选择的作品及其所做的简括描述,无疑是挂一漏万,很难全面的。既如在2005年间,特色明显又影响甚大的杨志军的《藏獒》、冉平的《蒙古往事》,因很难归入以上的几种倾向之中,就未能予以提及;而在直面当下现实写官场方面,陆天明的新作《高纬度战栗》,范小青的新作《女同志》,较之以往都以新的开掘而表现出新的力度,也因超出了以上几种倾向而未做论说。因而,至少把这样一些力作连同本文中论及的作品汇集起来,才谈得上对2005年长篇小说“以点带面”的巡礼。这是要特别指出来并提请读者在阅读中加以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