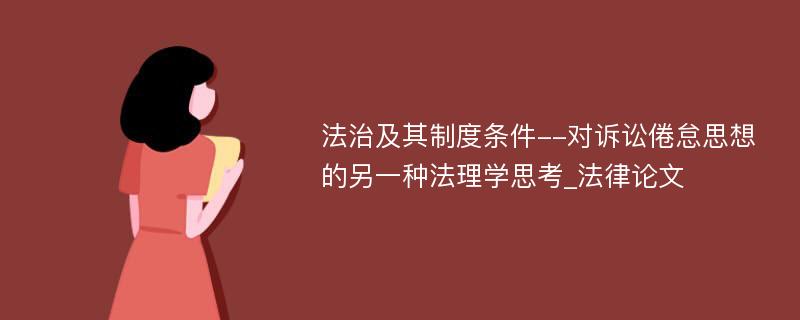
法治及其制度性条件——对厌讼思想的另一种法理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理学论文,法治论文,条件论文,思想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缘起:对有关厌讼思想的经典理论的质疑
差不多在每一部论及中国传统法律意识的经典和非经典的著述中,基于厌讼思想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标志性地位,作者们几乎都毫不例外地谈及了古人(乃至今天的中国百姓)的厌讼思想,而且同时都不约而同地对厌讼思想产生之根源作了尝试性探求,然而或许是因为受到先哲和同行中已有定论的潜移默化式的影响,那些有心于寻求事实真相的学者们却无法突破既有知识的束缚,以寻求一个新的致力点,不自觉地把前人的结论作为真理以承继下来,而他们的工作也就注定只能是粉饰前言。(注:关于这一点加达默尔有其精辟的论述:“我们总是在希望和恐惧中被最接近我们的东西所影响,并且在这样一种影响中去接触过去的见证,因此反对轻率地把过去看成是我们自己的意义期待”。转引自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页。 又如笔者曾听西方一位著名学者说过,前人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后人研究的一种束缚和压力,使后人的研究空间变得越来越来小。)对于厌讼思想产生之原因的经典性描述是:“传统社会中的厌讼(避免采用诉讼方式来处理纠纷)的倾向是由人们的法意识决定的,而这种法意识的特点在于缺乏权利的觉悟或者说是缺乏对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的正确理解……随着现代法意识的不断形成和发展,人们将会更加强烈地意识和主张权利,因而将会把诉讼或者说审判制度作为实现权利的手段,而更加频繁地加以利用。”(注:[日]川岛武宜著:《日本人的法意识》,转引自川著:《现代化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第2—5页。 有关此论断还可参见李培玉:《论传统诉讼意识的特征以及当代中国的影响》,《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何勤华:《泛讼与厌讼的历史考察》,《法律科学》1993年第3期; 张中秋著:《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等文献的相关论述等。)然而,只要我们稍微有一点怀疑权威的勇气,暂时忘却脑海中已有的经验或定论,那么,我们的许多疑意和追问便会在不知觉中产生:厌讼是否就意味着对法的无知,而法知识的普及是否就必然地导致诉讼活动的蓬勃兴起?厌不厌讼与法意识及权利意识之间是否存在着直接性的必然关联?如果对于前面的疑问我们所能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导致古人厌讼思想的产生以及今人依然普遍对诉讼缺乏情感上认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在法治的现代化进程中,当我们有必要去改变这种厌讼观念时,(注:许多中国法学者认为,厌讼思想是现代化法制建设的一个不利因素。)作为法治建设的旗手,我们应该而且能做些什么?所有的这些疑问,对于一个有学术责任心和社会使命感的学者,便不应该只作为一个念头在脑海中稍纵即逝,而有义务和必要去作深一层的理论探讨。正是有鉴于此,笔者才开始了这样一种不讨好(注:之所以说这是一个不讨好的思考历程,是因为作者在本文的写作中,有时也不自觉地受前引加达默尔所说的那种“影响”,以致使笔者的思考固步不前,甚至怀疑起这种思考本身的存在意义。)的思考历程,而本文的写作亦紧紧围绕这种思考历程而展开。
二、求证:法意识与厌讼或健讼思想之间的逻辑思辨
(一)厌讼并不意味着法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淡薄
厌讼思想的一个比较全面的含义是:人们不愿意或不积极主动地用司法审判的方式来解决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纠纷。笔者认为无论是直观地从厌讼思想的固有含义中,还是根据既有的大量学术论著中关于厌讼思想、少讼行为的论述,都无法令人信服地推导出厌讼思想的产生是因为或主要是因为人们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淡薄,是出于对法律条文规定的普遍性无知。相反地,从少之又少的案例记载中,(注:我国是个成文法国家,因此很少有专门的案例汇编,哪怕在古代偶有记载案例律文的官方正史中,以及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也向来是“载事不载诉”。)我们不时看到父子之诉、兄弟之争、夫妻邻里的纠纷出现于公堂上,以及今人为告状不惜倾家荡产,多年甚至几代人不懈怠的现象(注:参见《中国青年报》1999年3 月有关《京城有这么一群上访者》的报道。),我们固然不能就此认定古代和当今的中国老百姓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有多浓厚,但同样我们更无法推出人们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极度淡薄,进而把其归为厌讼思想的产生之根源。而从经验上讲,我们把人们之所以不诉诸于法律以解决纠纷的某种主观因素称之为“厌讼思想”,必然要以人们知道相关的法律规定,知道自己的法定权利被侵害为前提,并且知道可以诉诸法律来保障自己的权利。否则的话,如果人们不知道这种纠纷可以通过司法审判加以解决,不知道这种诉讼被提起的可能性,又何来在主观上的讨厌呢?这一点在逻辑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正如苏力先生所说的人们有意识地去避免用法律诉讼来解决纠纷,首先是人们对相关法律已经有了一个相当的感性甚至是理性的认识(注: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49页,以及《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之第2节。 )“法律规避所证明的并不是行为人对法律的无知和非理性,而恰恰证明了他们的理性(注: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以及《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之第2节。)”。由此看来, 厌讼思想的形成不是因为或至少不是主要因为人们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的淡薄,也不是因为人们对法律的不知。
(二)、健讼未必就等于人们法意识的普遍提高
与厌讼并不意味着法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淡薄这一命题相对应的是“健讼也未必等于人们法意识的普遍提高”。一个现代化的法治社会固然要求既有的法律得以良好的贯彻,法治的一个基本含义是“任何事情都必须依法而行”(注:[英]威廉·韦德著:《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依法办事必须作为一种理念构成人们法律意识的主要部分,然而问题在于,我们绝不能就此简单地断言:现代化法治社会必然要求人们凡事必须通过司法诉讼加以解决,更不能逆向而言之,以为健讼就意味着人们法意识的普遍提高。比如:在古代中国社会,一方面厌讼思想占据着整个传统法律文化意识的主流;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各种诉至法院的情词中“看到中间多系户婚田土等事,虽有一二地方重事,又多繁琐牵扯,不干己事”(注:《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一,转引自张中秋著:《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7页。 )形成“累讼不休……结而复起”最终导致“告评成风”。(注:康熙《徽卅府志》。)时至今日,旧有的厌讼思想虽然还没有在老百姓的观念中加以剔除,然而类似于一元钱电话费、三毛钱入厕费等等的琐小官司却时见报端,(注:请参见《南方周末》、《民主与法制画报》等报刊的系列报道。)亦有为一百多元承包费而连续上访15年的不厌讼之人。(注:参见庄会峰:《上访老户息诉罢访的启示》,《民主与法制画报》1999年3月19日第14版。 )面对这样的悖论,笔者以为一种较为接近的解释便是:法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悟程度如何与人们是否厌讼或健讼没有直接意义上的必然联系。在法尚不为众知的古代社会,老百姓亦有可能把诉讼作为解决纠纷的主要选择,而在今天的法制化社会中,支撑人们有兴趣去打类似于“一元钱官司”的动力亦不必然在于当事人的法意识和维权意识高程度的觉悟。因为毕竟支配一个人某一行为的主观意志目的动机,有时它不是单一的,甚至不那么单纯。(注:苏力先生曾用华君武先生的一幅漫画作为这种心态的注脚。画的是一个人趴在凳子上,亮出屁股,对旁边一个手拿鸡毛掸子的人说:“你快来打我,一打我就出名了”。)而包括我们法学界在内的许多人在评断这种行为的时候显然过多地掺入了自己的主观意愿,以致难免有感情用事之嫌,从而使整个舆论导向产生偏颇。记得当此类官司发生之后,我们中的多少朋友以为这是多年来普法教育、法制建设的硕果而为之欣慰,额手相庆。因为在我们看来这种“健讼思想”已经昭示了人们法律意识、维权意识的普遍提高。然而,现实终归是现实,理想也毕竟只是理想,二者之间的差距并不会因为部分人暂时性的忽视而不复存在。事实上,正如当事人所说的:“(我)‘以身试法’设计制造官司,本意不在提倡打官司……若能创造一个案例载入最高法院公报,或者编入教科书的附属教材,应是人生快事。”(注:丘建东:《我为什么好打官司》,《南方周末》1999年3月12日第7版。事实上,丘建东更是获得了媒体的关注和政论的褒奖,大大提高了知名度以及其他物质上的利益,参见同版记者评语。)由此看来,隐藏在当事人这种行为背后的主观想法并不是我们法学界的理想,至此,我们只能尴尬地说:“我们多情了”。(注:当然,笔者无意就此否定多年来法制建设所取得的已有成果,而只是分疏相关的因果关系以使有些问题及其结论更接近于事实的本身面目。)
如果前面的分析还算大致正确的话,那么在此我们就可以说:厌讼思想产生的原因并不象人们长期以来想当然式的推定,它似乎与人们的法意识以及维权意识的觉悟程度没有直接意义上的必然关联。那么,到底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厌讼思想的产生以及如此根深蒂固地存在下来呢?
三、答案:制度性条件的欠缺,厌讼思想产生的根源
(一)政府的政策性限制和社会的舆论性谴责
在我国古代社会,统治者为便于统治,客观上需要老百姓都能安事生产,尽可能少地给政府制造麻烦。然而在他们看来官司词讼无疑会给社会生产带来不安稳的因素,进而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于是政府无一例外地要求地方官员能够尽量减少当地的诉讼,以当地讼例的多少作为衡量该地方官员之政治业绩的重要标准。因此,在此种传统法律和传统文化下所培养出来的官吏们无一不以“无讼为尚”,视争讼为“刁讼”、“刁民”予以严厉打击。海瑞在《督抚条约》中明示“本院到处即放告,江南刁风盛行,非系民间疾苦,官吏贪毒,实有冤抑而官司分理不当者,不准。……江南刁风盛行,事诚可忍,……江南刁讼日盛,治之诚有本焉。然江南刁讼入人极深,非借法度辅德礼则又不可……。”(注:《海瑞全集》上册,转引自张中秋著:《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第343页。)被老百姓们誉为“青天”的海瑞大人况且如此, 更何况那些贪吏和庸吏乎?封建时清官循吏不仅以调解、劝谕、教化诸方式来代替判决,有时更是采取“拖延、拒绝、设教唆词讼罪”等方式(注:参见,马作武:《古代息讼之术探讨》,《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以达到息讼止讼的目的。 清代有一份《劝民息讼告示》可见一斑:“钱债、田地、坟山、一切口角细故原是百姓们常有的,自有一定的道理,若实在被人欺负,告老成公道的亲友族邻替你讲理,所以和息也就罢了,断不可告官讦讼……就算有十分道理也要忍气,牢牢记住本官的话,只要投告亲族和息,就吃点亏总比到官较为便宜”(刘衡《庸吏庸言》)。而更有甚者,乃至以立法的形式公然剥夺了某些诉讼主体的诉讼权利。例如规定“父子将狱,是天上下也”(《国语·周语中》);(注:转引自肖永清主编:《中国法制史教程》,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以下。)
“子告父母,臣妾告主是谓非公室告,勿听”“主擅杀,刑,髡其子,臣妾告主是谓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有罪”(《秦律》)(注:转引自肖永清主编:《中国法制史教程》,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以下。),从中可以看出,“以卑告尊,以幼告长”都是为法律所不允许,在两汉时期更是以“干名犯义”罪加以严惩。(注:转引自肖永清主编:《中国法制史教程》,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以下。)这样一来无疑会使古代的诉讼较之正常情况为数要少了许多,而这一本来可能出现而事实上又没能出现的诉讼案件显然不是因为“下”、“卑”等诉讼主体对法律缺乏了解、知道法律的相关规定而不得以忍气吞声。
而也正是因为政府在政策上的严加限制,司法行政官员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横加劝阻,一方面致使诉讼行为在量上大大减少;另一方面,政府的这一政策同时又引导着社会舆论的导向,致使人们对周围的诉讼事件及其当事人缺少一种同情式的理解,相反“谓之好讼,顽讼,缠讼,纵不把其看成黠而且悍者。亦不认为是安分良善之人”(注:梁治平著:《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6年版,第八章。)给社会带来了“终讼之凶”,这样无疑会使提起诉讼的当事人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有时极可能会迫于这种压力而不得不放弃诉讼,进而厌倦诉讼。(注:例如,苏力先生在《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一文中,在分析了秋菊的处境(为家人和乡邻所不理解)后,不禁疑虑:“在这之后,在下一次类似的纠纷中,秋菊还会再次诉求正式的法律吗?”)笔者以为这种政府的政策性限制和社会的舆论性谴责,是古代人们“厌讼思想”产生的制度性根源之一。
(二)古代诉讼制度之于原告的过重负担
在我国封建社会,虽然普遍地实行纠问式诉讼结构,法官根据职权主动追究犯罪。然而,由于官府追究犯罪的能力明显不尽人意(这一点笔者在下文将有详述),所以一大部分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还是需要被害人向有关部门递交诉状以提起诉讼。在诉讼的过程中,除呈诉状外,原告还应尽可能地拿出被告的犯罪证据提供给政府。如唐律规定:“诸告人者,皆须明注年月,指陈实事,不得称疑。违者,笞五十”(注:《唐律·斗讼》。)。否则的话,原告不仅因此面临败诉的风险,还可能因证据不足而难逃诬告之谦。根据规定“诬人”要反坐,反坐者,即其诬告他人之罪罪之。即使法官相信告人者无主观恶念,亦因错告而构成“告不审罪”必须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在古代侦查手段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案件的侦破、证据的取得,对于一个平民百姓显然难乎其难,几近不太可能。所以当一个人在向官府提起诉讼之前,他(她)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投诉行为所即将带来的风险。如此一来,除非拥有足够之证据胜券在握者,不然的话,哪怕他有天大的冤屈也只得忍气吞声,打落牙齿往肚里咽。
此外,“胥吏衙役无不以讼案为生财之道,一打官司就索取种种规费(陋规),以清代为例,原告需交纳挂号费、传呈费、买批费、送稿纸笔费、出票费、铺堂费(即开庭费)、踏勘费、结案费、和息费,如果是命案,并有命案检验费等等。(注:瞿同祖:《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历史的考察》,《中外法学》1998年第4期。 )而且到了公堂,无论被告、原告抑或证人一律得长时间跪在县官面前。而在“有罪推定”盛行的年代里,问官审案动辄用刑、逼取口供。如《魏书·刑罚志》规定“从今断狱,皆依令尽听讯之理,量人强弱,加之拷掠。”被告自是刑讯逼供的对象,然原告亦难能幸,一旦被告“限满不首”,则要“反拷告人”。(注:《唐律·断狱》中有“诸拷囚,限满而不首者,仅拷告人”的规定。)
还有,虽然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直诉朝庭,然而,当事人不服判决的,原则上还是不能上诉,如果坚持上诉的,则要“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之长”(《周礼·大司寇》)(注:转引自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现代化》,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页。)在古代司法审判技巧极度落后,加上司法腐败猖獗, 穷苦庶人本已难能获得一个公正合理的判决。而不服判决也就成了经常而正常之事,求助于上诉,以求能有一平反之期,然在未卜上诉吉凶之前,先要忍受筋骨之苦,“以立肺石三日”,这对早已身心憔悴的受害人(包括原审的原告和含冤的被告)无疑是雪上加霜。于是乎,能有精力与财力付诸上诉者为数亦是锐减。同时由于对上诉制度的失望,更使许多人对当初诉讼的提起热情大减。
正是基于这种不尽合理的诉讼制度之于原告的过重负担,致使许多原告因无力承担举证责任,高额的诉讼费用,以及承受不了(从生理上和心理上)这种“立肺石,跪公堂”之屈辱,遭受不起拷讯的皮肉之苦而不得不放弃诉讼。已有过这种诉讼经历的,更是会有“一朝被蛇咬”的恐惧与厌恶。所谓“屈死不告状”,不是心中没有冤屈,不是不知道可以告状,只是通过对诉讼制度的体验和了解,认为诉讼制度的不合理代价以及处理结果的难遂己愿,也就只能敬而远之。
笔者以为,这是厌讼思想产生之制度性根源之二。
(三)、司法模式效能的低下,是促使人们厌讼的又一制度性原因。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地方司法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结合在一起(分为省、府、县三级),由知府、知县执行地方司法审判权。府台大人和县令也就是偌大一个县、府中唯一的法官。因法官在人数上的缺乏而形成的力量的单薄,致使每一个地方官员的工作量都是严重超过了其正常工作能力所能承载的范围。这在一方面,自然地造成诉讼案件的相对泛滥(由于厌讼思想的影响,古代社会诉讼在绝对数量上是不多的,而相对于法官的承办力而言又显得绝对膨胀,这也是古代官府极力息讼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由于案件的积压,造成诉讼效率和效益的大大降低,一件情况十分简单的案件却往往要经年累月地搁置下去,使当事人长时间得不到满意答复,同时由于时间的延误,致使原告的举证更是难上加难,而法官由于力不从心,也必然会出现类似于“草菅人命”的情况,从而造成冤假错案,进一步削抵了司法的效能。
其次,就侦查技术而言,古代显然不同于今日,在我们今天看来十分容易弄清的案情,或许在当时会显得扑朔迷离,而案件的最终解决有可能离实质正义相去甚远。而由于交通、通讯等客观条件的欠缺,更是使当事人每打一次官司必然会伤筋动骨。为了一件小小的纠纷而不远千里地上县府,赴京城(那时县府衙门的设置显然没有今天基层法院的高密度,更不会有派出法庭之类的),何况那时尚无法律援助之制度,律师亦是奇货可居,偶有一二讼棍亦极尽落井下石之能事,讹诈高额费用。对于原告而言,因诉讼而支出的费用有时会不堪重负,哪怕最终胜诉也会是“赢了官司,输了金钱”。而正所谓“争财曰讼”“因财争控”,当事人提起诉讼原本就是“因财”而来,却最终落得个“冤仇日结,卒至两败俱伤,废业伤财,竟至得不偿失。”(注:钟祥:《审理寻常词讼》,载《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刑政》。)诉讼制度不能使当事人的受损权利得到救济,反而使其“尚受其殃”(注:钟祥:《审理寻常词讼》,载《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刑政》。),这无疑背离了当事人提起诉讼的初衷。
我们说“在一定意义上,立法和与之不可分离的司法和执法都是一种经济活动,而经济活动就是寻求社会资源的最优化”(注:苏力:《市场经济对立法的启示》及其注⑨, 《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司法诉讼作为国家对一种受损权利(权力)的公力救济手段,其设立之目的应该是也必须是使受害方得到最有效的补偿(从精神上和物质上)。然古代诉讼制度由于司法模式效能的极度低下,“卒至(当事人)两败俱伤”,而使原告“不但废时失业,抑且荡产倾家”“竟至得不偿失”“尚受其殃”。于是乎,难怪宋儒朱熹要“劝谕士民乡党族姻所宜亲睦……且委曲调和,未可容易论诉,盖得理亦须伤则废业……终必有凶,切当痛戒”(注:《朱文公文集》卷一百,转引自梁治平著:《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八章。)。笔者以为,大智有如朱子者却厌讼至此,当不能责其乏维权之法意识(注:引文中的:“盖得理”当可推知,朱子对法律有相当认识,知道某行为在法律上得理,更况乎朱子之博学当对法律之领域有所涉及。),而实在是古代司法模式效能之低下迫使其作出“厌讼”这一无奈之选择。
此乃厌讼思想产生之制度性根源之三。
综览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厌讼思想的产生之根源在于制度性条件的欠缺,致使人们无法通过诉讼行为实现预期的诉讼目的,“以和为贵”的儒家礼治文化固然极大程度地影响着人们对人际关系的看法,但是这只能说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尽量坦城相处相互谦容,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纠纷产生的可能性,然而,诉讼是以纠纷的既存为前提的,纠纷一旦产生就已经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以和为贵”的默契,而人们避免用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只能说明当时诉讼方式的不合理性,因为它作为一种法定的解决纠纷的方式,不仅不能使纠纷得以顺利解决以恢复人们之间原有的和谐,反而进一步破坏了人们之间的安宁,使纠纷更大程度地破坏了人们所寻求的那种“自然秩序中的和谐”(梁治平语),而造成“一场官司十年仇”的尴尬结局。厌讼现象实际上是人们对于司法审判制度和法律运作效果的极度失望,息事宁人抑或用其他的非诉讼手段以解决纠纷,源于司法难以实现立法时所期望保护的社会正义,而致公众对司法崇高信念的失落。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汉相晁错会慨叹:“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注:《汉书·食货志》。)当然,本文的写作意图绝不仅出于此。因为,对一种古代社会现象的纯粹分析,显然缺乏现实的建设性意义。“以古为鉴”当以能“知今之兴潜”为要义。因此,面对历史我们需要反思……
四、反思:法治的实现及其制度性条件
现代化的法治社会,客观上要求人们在法律规范下决定自己的行为,也必然要求人们通过法律的手段解决自己的纠纷。然而,人们在作出自己的行为选择时必然要寻求一种最佳的途径,而在中国现存的法律程序结构中,从法律运作的效果来看,那种调解和私了的处理方式“恐怕反倒比允许法学素养不高的审判人员进行自由心证和拥有判决确定力的严格形式主义的审判更多些可测性,更少些压抑感”(注:季卫东:《法治与选择》,《中外法学》1993年第4期。)。更何况, 在判决生效后的“执行难”几乎已成经验之谈。这更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司法诉讼寻求法律保护并不是解决纠纷终南捷径(注:参见,郑永流、马协华著:《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的现实变迁——来自湖北农村的实证研究》第五节,《中国法学》1992年第1期。)。 上海的一位资深律师更是感慨:“一位律师的高明之处在于不打官司就能解决问题”(注:陶武平先生的一篇随笔,载《青年一代》1998年第12期。)一位以打官司为其职业特征的法律工作者之“高明”处不在打官司以解决问题,反而在于不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法律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对立法者的嘲弄,更是我国法治进程固步不前的症结之所在。
“中国的法制不能长此以往了”(注:季卫东:《法治与选择》,《中外法学》1993年第4期。)这样的呼声显然已不是什么危言耸听。 笔者认为如果我们仍然把法治的最终实现寄望于立法层次上的片面追求和法律知识填鸭式的灌输,把法制改革的重点仍滞留在令行禁止和权利义务量的设置上,而对“具体制度的建设长期忽视,那么所谓的根本性改革,充其量只能获得一些表层的效果。(注:贺卫方:《司法改革中的上下级法院关系》,《法学》1998年第9期。 )”“有法可依”对于法制化固然重要,然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法律对公民权利在量上的规定并不逊色于现代的西方法律,从位居其高有如国家主席到地位之低有如市民乡夫,他们并非找不到主张权利的依据,而实在是无法运用这种依据,在于这些实体权利缺乏赖以实现的现实条件和客观环境。有法律并不意味着有法治,只有立法产品(法律)在社会的运行中产生正的社会效益,(注:有关法律运行的评价,请参见姜丛华:《论法律运行的实现——法律在社会中实现的机制与评价》,《浙江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2期。 )真正使法律保护成为人们权利最有力且最有效的保护手段,人们才有可能在情感上和行为选择上对法律的实践效应予以认同,也才有可能使“法律能在实践中产生法治效应,才能使主体自救型人格既成为社会的深刻需求,亦成为主体的自主选择(注:谢晖《拯救还是自救——法治人格精神要素分析》,《学习与探索》97 年第4期。)”才能“培育起我国法治的人格精神基础”(注:谢晖《拯救还是自救——法治人格精神要素分析》,《学习与探索》97年第4期。 )。从而从根本上摒除人们传统观念上的厌讼情结(注:例如,据报道,广州日升大厦业主在向延期交楼的开发商追讨权益时,由于手段不同,结果迥异:诉诸法律者获得高达73万元巨额赔偿,接受私了的仅得几千元至万元的补偿。业主们无不感慨“用法不用法,就是不一样”。(曾胜泉:《“私了”与“公了”结果迥异》,《钱塘周末》1999年4月 30日第2版)此类案例可视为法制建设的成果, 亦是作者上文立论的实施基础。)。
然而,在中国建立一套实现现代化法治所必需的制度性条件体系,这个创造过程显然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注:由于意识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厌讼思想必然会反作用于制度性条件的安排。表现在:一方面,它大大降低了官府(制度性条件的创设者)去创设制度性条件的热情(因为从古代官府劝民息讼的行为本身来看,厌讼思想显然同样根蒂固地存在于他们之中。)另一方面,它又必然导致老百姓(制度性条件的承受者)对制度性条件的创设和增大制度运行的难度。),对此作为法治的建设者,我们不应只是消极地等待,而需要一种积极的“积薪”式的努力。当然,在主观努力的决心之外,还存在着客观努力的方式选择的问题。本文作者以厌讼思想的根源为契引,不惜笔墨地去论证厌讼思想产生的理性根源在于古代乃至今天诉讼制度之于原告的过重负担,在于司法模式效能的过于低下,意在昭示,制度性条件之于法意识的培养,之于法治建设所需的人文基础的决定性意义;更在于昭示,创造制度性条件的努力方向在于司法模式效能的提高,在于法律运行的保障制度的完善。显然,一份判决的有效执行之于老百姓对法律信仰的提高要远比几堂普法教育来得近于功效;而把一部法律完全地贯彻执行之于法治的实现要远比制定十部闲置的法规来得意义深远。
能说明这一点是本文的写作用意。
当然,或许是作者对厌讼思想的经典理论缺少系统的把握,亦许是本文的思路之切口过于简单、细小,而使本文的思考难以深入以致难能有一更高的理论意义。然而,笔者深有同感于一位学者的治学态度:思考的实践若能开放出一些较具理论意义的问题,并透过这些问题使人们能够对那些原本被视为当然而不被质疑的现象以及潜藏于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追问,一定比那种对繁复问题做自以为是的简单回答或者干脆把这些问题搁置起来而不做任何反思和批判的作法更具意义。因为这才符合作为知识分子的自由思考的原则。(注:[美]E ·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重译本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