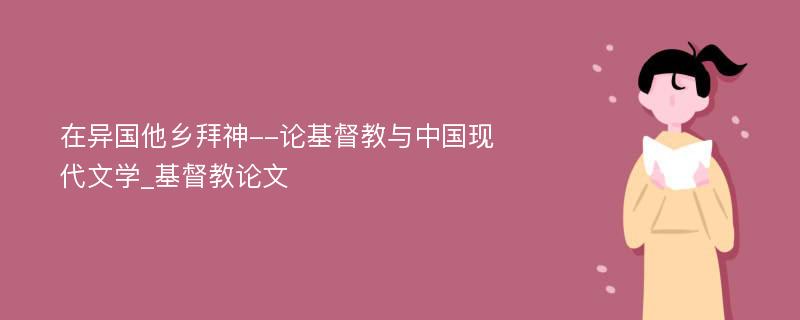
遇到异乡的神祇——论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论文,现代文学论文,异乡论文,中国论文,教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诠释基督精神的方式
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基督教文化所扮演的角色并非无足轻重①。从胡适、陈独秀、鲁迅开始,到郁达夫、郭沫若、田汉、周作人、许地山、冰心、穆旦等等,直接或间接受到过基督教文化影响的现代作家简直不胜枚举。人们不禁要追问:基督教文化这种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外来强势文化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哪些异质性的精神资源?这种精神资源又从何种层面上丰富了现代文学创作的审美内涵?但遗憾的是,当前研究界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研究的这个基础性问题,回应始终含混。本文认为,研究界在这根本问题上的暧昧情况与研究界流行的“索隐法”、“护教解经法”这两种研究方法是有密切关系的。
“索隐法”乃是当前中国最常见的一种关于基督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模式。在这种研究模式中,研究者们竭力从作家的个人经历、文本中寻找一切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线索,并往往放大这些线索对创作者的影响力。他们一般不重视这些线索具体的内容与历史背景而乐于通过索隐的方式来证明这些线索总是隐秘地见证了作家基督徒式的感情。不可否认,“索隐法”对于考较基督教与现代文学的源流关系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但过分执著于寻找文学创作中宗教影响的痕迹,却常导致研究者过度阐释甚至是完全地曲解文本,也就无法对基督教在现代文学的影响力做出令人信服的估量。
马佳关于鲁迅《复仇(二)》的解读是一个典型的个案。虽大量运用了象征、隐喻等含蓄的表达手法,但鲁迅借用耶稣被钉十字架故事来怒斥现实的黑暗、诉说先行者内心悲凉的题旨还是比较明确的。但马佳为了证明基督教文化对这位中国现代最伟大作家的影响力,却把它完全当成鲁迅表达其基督精神的一个文本。像“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们的身上,比钉杀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血腥”②之类表述,鲁迅明明是针对现实黑暗而言的,马佳却认为,这是鲁迅对于基督被钉十字架事件的一个强烈的精神回应:“被钉死的基督是孤独的人之精神,是人类的痛苦。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钉死的是他们未来的前途与希望。”③不仅如此,马佳还进而发挥道:“然而死后的耶稣会复活,会复仇,会悲悯人类的前途。复活的基督将是真的猛士:‘他屹立着……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我们通过《复仇》(二)中死去的基督以及日后的复活,重振雄风的过程,依稀可以看见鲁迅的身影和精魂。”④按照马佳的引述,人们很容易得到这样的一个印象:鲁迅即使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他某些核心的价值立场上也是非常同情于基督教的,并且他非常擅长于利用某些包含基督精神的意象来表达情思。但令人遗憾的是,马佳的这种论证是相当不规范的,是很难成立的。《复仇(二)》不但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这篇文章(包括鲁迅所有的文章)也没涉及什么耶稣的复活问题。马佳所引“他屹立着”并大大加以发挥的这段文字,则出自鲁迅另一篇文章《淡淡的血痕中》,与基督教感情也毫无关系。
虽然马佳式的读解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个案,但当前不少论说在谈论基督教文化对作家影响时实际上采取的就是这种“索隐法”的思路。许多优秀的持人文立场的研究者为强调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价值,有时也有一些“索隐法”的议论。
“护教解经法”则是另一种很有市场的研究模式。它强调文学创作最终的价值取决于其表现的基督教意识的深刻程度。据此,它容易得出如下的结论:中国作家中感悟到基督救恩崇高的已经很少,将之作为表现主题的就更少了,因此中国从根本上说没有什么伟大的文学作品。这种完全从基督教立场来判断文学作品价值高低的思维方式,很像是习用了基督教史上那些护教论者的思想方法,因此称之为“护教解经法”。
刘小枫是这种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他在其《拯救与逍遥》中提出过这样一个著名的观点:虽然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剖析人类灵魂的大师,但鲁迅因为缺乏基督信仰,他的作品最终便只剩下了“阴毒”、“阴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却因为涉及了基督信仰问题的思考而总是散发出一种救赎的热力⑤。虽然,除了刘小枫,很少研究者彻底地以“护教解经法”的理路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基督教影响问题,但这种研究方法在研究界仍有着深刻的影响。显然,根据“护教解经法”的价值理路,人们很难对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的影响作用问题作出深入的研究。因为在这种思想方法中,核心问题是宗教问题,而所有与宗教相关的问题预先又被设定成一个是不是符合基督教价值的问题,这样的逻辑设定,就容易使得研究偏离正常的人文向度。
因此,如果要真正深入地研讨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的价值意义,我们需要摒弃“索隐法”和“护教解经法”这两种习见的研究模式,从艺术自身的价值立场出发来思考问题。
首要的一点,我们不能按照当前习见的方式,在一个简单的层面上不加区分地讨论基督教文化对于现代作家创作的影响。尽管许多现代作家的创作都曾受到过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但他们从基督教文化中汲取营养并将之转化为创作上重要的思想资源的角度、立场其实是有很大不同的,这种不同至少体现在他们对基督教文化的吸收和利用方式上存在着外在借用和内在化用两个不同层面。中国毕竟不是基督教国家,有些中国作家对于基督教文化资源的利用,的确是从比较简单的外在修辞策略(比如说主题的创新、题材的新鲜、表述的趣味性)的角度来考量的。这和西方作家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对中国作家而言,我们如果不承认某些作家可能只是外在地简单借用某些基督教的词汇或典故,而是执意要从这些简单借用中论证他们与基督文化内在的亲和性,就容易落入“索隐法”的窠臼。
另外,在研究那些从内在尺度的方面来融会基督精神的作家时,我们也要注意到这种融会是有多种形态的。像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展现的那种思维模式,混淆信仰的不同类型,把神的信仰当作对基督教的神的信仰,把艺术创造中的包含基督教元素的宗教性思考完全等同于基督教式的神学思考,恐怕是过于简单了。
二、神坛外部的写作
虽然有不少现代作家注意到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冲击性影响,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这种崭新的异质性的外来思想资源的利用,却基本停留在外部的层面上。就是说,这些作家无意将基督教式的思想感情化入自己整体性的艺术构造系统中,他们大多只是为题材的需要或某种修辞策略的需要,在作品中加入一些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内容。作家们的这种“无意”绝不是一种刻意的漠视而是一种真正的无意识:基督教那种独特的价值立场与思想情感基本上没有进入作家的视界。中国现代作家对于基督教文化外在层面的利用,大致可以分为俗世的批判和修辞借用两种类型。
所谓俗世的批判,就是指作家站在俗世的立场,对有关基督教文化的各种现象展开批判。就俗世批判这种创作类型来说,它倒并不一定是外在于基督教精神的。作家完全可以站在俗世的立场深入至基督教价值的核心来批判它对于人的现实生存的虚妄性,或者又可以借此考察神性与人性的背离等等,像《十日谈》、《巨人传》以及易卜生的许多作品都是这种“俗世批判”的标志性作品。但中国作家的俗世批判一般都不包含这种深层次的价值观照与反思,他们往往只是站在一个世俗的中国人的立场,对基督教各种扞格于中国现实生活的现象、对于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表里不一的现象,进行揭露性的描写。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俗世批判的一个基本特征。
巴金的《田惠世》(《火》第三部)是一部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按照巴金的本意,“在这本小书中,我想写一个宗教者的生与死,我还想写一个宗教者和非宗教者的思想与情感与交流。”但巴金自承:“可是我不曾写出来,或者可以说是写得不好。”⑥事实的确如此。巴金在描写田惠世这位虔诚教徒在抗战时期的悲惨遭遇时,始终没有把笔墨探入这位虔诚者的心灵深处来描写他的生与死、爱与恨的体验,他只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来记录这位信者的各种不幸:他历经事业、生活的各种磨难,爱子还死于日寇的轰炸。在这种叙述中,原本宗教性的生死、爱恨主题让位给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俗世立场:我们可以非常尊重田惠世的人格,但站在战时的中国人的立场,却不能不认为他的信仰在现实中是软弱与无稽的;中国人得救的希望,不在田惠世信仰的那个天国,而在“如今一般年轻人朝夕向往的那个圣地”⑦。巴金很清楚自己与基督教价值的疏离性,他说:“读了这本小说,说不定会有人疑心我是一个基督徒,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⑧
沈从文的《建设》、《绅士的太太》、《蜜柑》、《平凡的故事》,老舍的《老张的哲学》、《二马》以及胡也频的《圣徒》等等,大体也可以归入俗世批判类。
中国现代文学对基督教文化的俗世批判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是其意识形态属性。近代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史是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史与殖民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西方列强发动的对中国的多次侵略战争中,许多传教士曾经扮演过很不光彩的角色。这一点让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深受伤害,当他们在作品中涉及中国与基督教文化相遇的问题时,这种伤痛记忆就转化成为了一种内在的抵制情结。他们自然地从国家、民族的立场上将基督教定性为一个文化侵略者的角色。萧乾在《皈依》中怒斥那些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咱们祖上没缺德,你敢莫非信那二毛子!”⑨可谓是自觉从意识形态的立场抗拒基督教文化的最强音。田汉的《午饭之前》、臧克家的《罪恶的黑手》、郭沫若的《双簧》等都表现了这种鲜明的意识形态的立场。沈从文的《建设》其实也包含了相似的观念。
中国现代文学从外部对基督教文化资源的利用还有一种重要的类型便是基于修辞策略的借用。这种“修辞策略的借用”是指作家有意识地运用某种基督教文化特有的精神资源来表现某种新鲜的艺术趣味或价值指归。既然作家注意到了基督教文化特有精神资源与新鲜的艺术趣味或价值旨归,当然不能说是他对于基督教文化毫无内在的体认,但在此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借用相对于其整体的艺术构造来说,是局部性的、次要的。就是说,作家不是从某一饱含基督教文化特质的精神资源中洞觉到了艺术问题,而是在表现某一艺术思想过程中意识到某些基督教文化的资源能够增进表达的效果因而在修辞层面上调动了这些资源,有时他们只是在表面装饰性的层面上来利用这些文化资源以取得某种奇观化的效果(毕竟对20世纪上半叶绝大部分的中国读者来说,基督教文化是陌生和异质性的)。
现代文学对基督教“修辞策略的借用”主要有借境、借情、借事、借典等几种方式。所谓“借境”指的是作家意识到基督教的某种文化元素与其整体的艺术境界追求有内在的契合性,因此他在作品中有意引入了一些具有基督教风格的环境、氛围的描写来烘托、加强这种艺术境界的展现。曹禺《雷雨》的“序幕”、“尾声”可谓是运用“借境”手法的典型范例。在《雷雨》中,曹禺试图表现的是“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他还试图进一步探讨这斗争背后的“主宰”因素:“这主宰,希伯来的先知们赞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运’,近代的人撇弃了这些迷离恍惚的观念,直截了当地叫它为‘自然的法则’。”⑩“序幕”一开场空旷孤寂的充满基督教风格的大厅以及若有若无伴随着的巴赫《B小调弥撒曲》等等强有力地烘托了曹禺的这种艺术理念:在这种氛围中,我们尤能体会命运的无常和人的渺小、易受伤害的特质。应当说,《雷雨》的“序幕”、“尾声”中种种基督教情境的塑造,是紧紧围绕着“命运”的“残忍”和“冷酷”这个主题展开的,本身并无独立地表现基督精神的意味。这一点从《雷雨》文本构造的特点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日后曹禺因为种种原因消去了这“序幕”、“尾声”后,我们仍然能够从其保留的文本中感受到某种希腊悲剧的特质,但有关基督教精神的消息,我们便再也不能感觉分毫(11)。曹禺在《日出》开篇连引七段《圣经》中的文字,其手法也可归入“借境”之类,他借此强化剧中的社会批判主题。
作家借用基督教文化的某些特点来渲染、加强作品的感性情调,这便是所谓的“借情”。这种手法在言情类的小说中尤其常见,作家以突出基督徒宽容、坚忍、博爱的精神品格来为一些老套的爱情故事增添新的阅读趣味。徐訏的《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小说描写了“我”与一个巨豪家女佣海兰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结局却是海兰为成全自家的小姐白蒂对于“我”的爱而毅然服毒自尽了。尽管小说的最后部分比较有力地突出了海兰的宗教情怀和基督徒式的牺牲精神,不过从整体上看,最后的这些描写仍然是比较突兀的,以至于让人感到,海兰的自杀不是这个角色内心基督教情感喷涌的结果,而是小说家利用基督徒式的牺牲精神为常见的爱情传奇增添别样情致的刻意安排。
虽然在艺术上多有可挑剔之处,但《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借情”手法的运用相对来说已显得比较细腻和生动了。现代文学中大部分运用“借情”手法的作品,只是运用某种基督教文化情调的笔法,来起到煽情、伤情或忏情的局部效果,像张资平的《约檀河之水》、《双曲线与渐近线》,郁达夫的《迷羊》、《南迁》、《马樱花开的时候》,徐舒的《风萧萧》等等大体都可归入此类。
所谓“借事”,指的是以艺术化的笔法直接改写《圣经》或基督宗教故事。这些“借事”类的作品有些颇有题外的讽喻之意,如茅盾的《耶稣之死》、《参孙的复仇》等,明显讽刺当时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但有些作品,如徐志摩的《人种由来》、《卡尔弗里》,向培良的《暗嫩》等,既无明确的现实所指也无深沉的宗教寄托,作者似乎只是出于题材的新鲜感而改写了《圣经》的某些故事。
所谓“借典”,指的是创作者行文中信手借用基督教的某些典故来传达自己的情思。当然,这种借用往往只是借其大意而已,与基督情感没有什么深入的联系。殷夫的《东方的玛利亚——献母亲》、李金发的《屈原》、沈从文的《篁君日记》等是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沈从文的《篁君日记》明显借用了《圣经·雅歌》的意象和抒情笔法(12),只不过沈从文所歌颂的,是甜美的肉体之爱,与基督教感情并没有什么关系。
三、神圣元素的融合
从内在精神层面来化用基督教文化的现代文学作品,大致也可以分作两种类型,一种主要是从人文的价值立场来审视基督精神的价值意义(或是其缺憾),并试图将这种对基督精神的人文审视转化为艺术创造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种则主要是从信仰出发,试图建构具有基督精神灵韵的艺术作品。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自觉地从人文的立场来谛视基督教价值意义的作家不算多,但他们取得的成就却比较引人注目。这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视角就是从人文的角度来考察神对于人的意义。穆旦的创作是其代表。早在20世纪40年代,王佐良就已经指出:“穆旦对于中国新写作的最大贡献,照我看,还是在他的创造了一个上帝。……诗人的皮肉和精神有着那样的一种饥饿,以至喊叫着要求一点人身以外的东西来支持和安慰。”(13)穆旦从未否认人的价值之终极奥义,然而现实的黑暗,对人性软弱的洞察以及其对于现代人存在荒芜性的体验,使得他又以诗人的敏感去质疑人是否能够为自己寻得一个终极的灵魂居所。因此,穆旦在其诗作中常常以一种呻吟的笔调感叹人的局限和神存在的必要。在这类诗作中,穆旦对于基督教神学种种独有的观念如“神恩”、“神是人的得救希望”、“神的国度的至福与充盈”等等简直是信手拈来,并使之成为了其“祈神”叙说有力的情感支持。不过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到,穆旦的“祈神”叙说绝不是为人们祈祷一个基督教意义上的神,这个神其实是人在终极探求过程中对于超出人类的那个大者的一个命名。这个神可以是一个反基督的神:“主呵,让我们和穆罕穆德一样,在他沙漠的岁月里/让我们再说这些假话做这些假事时/想到你”(14);也可以是一个充满了俗世意味的自由的神:“我歌颂肉体:因为光明要从黑暗站出来,/你沉默而丰富的刹那,美的真实,我的上帝。”(15)
冯至的诗风虽与穆旦大有不同,但他们在诗中对基督教文化的化用方式,那种对于神人关系思考的价值立场却颇为接近。冯至的《夜深了》、《残馀的酒》、《窗外》、《永久》、《“最后之歌”》都展现了某种基于人文立场的对于神的祈愿。叶灵凤《拿撒勒人》中的有关描写也可以归入这一类。
中国现代文学中,还有一种融会基督教精神的人文视角也很值得注意,这就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考察基督教对于人生尤其是中国人的人生的价值意义,鹿桥的《未央歌》、无名氏的《野兽、野兽、野兽》是代表性作品。这其中,鹿桥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未央歌》尤其值得注意。《未央歌》有不少关于基督徒感情的传神而深入的描写。小说在描写女主人公蔺燕梅对基督教的体认感情的部分,某些笔触生动而深入地传达了基督徒特有的痛苦体验以及他们对救主的热爱与寄托之情。苏雪林的《棘心》虽是一部描写基督徒皈依之路的自传体小说,但在这方面的手笔远不如《未央歌》。当然,对于鹿桥来说,类似的文字并不是为了简单地向读者展示基督徒的特殊感情。他试图通过这种基督徒的感情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描写,凸显蔺燕梅的文化人格,将她的这种文化人格与书中另外几位具有标志性意味文化人格的主角余孟勤(儒家文化的代表)、童孝贤(道家文化的代表)、伍宝笙(兼有儒、佛的情怀)形成比照,并进而描写他们在精神境界上融会的情况。书中写到蔺燕梅与余孟勤相爱而不能相合,最后反而与童孝贤产生了心灵的契合感。这绝非无的放矢,而是具有某种文化象征意味的。
现代文学作品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创作类型是从信仰出发来建构具有基督精神灵韵的艺术文本。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虽然很少有真正的基督徒,但却有不少作家在其精神求索的某一个阶段曾特别注意到基督信仰某种独特的感人力量。他们试图在作品中表现这种信仰给予人的慰藉以及对人的拯救作用。朱自清的《自从》、梁宗岱的《晚祷》,庐隐的《余泪》,郭沫若的《落叶》,陈梦家的《一朵野花》,艾青的《一个拿撒勒人的死》,石评梅的《罪恶之迹》,王统照的《微笑》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型的作品。但这些作品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它们一般只是着意于描写基督信仰、基督式的博爱对于人的精神的抚慰作用,但很少有人深入挖掘基督教信仰迥异于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质并把它们彰显为具有基督教美学风格的新意象、新主题。
在从信仰出发来融会基督精神的文学创作中,有一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不少现代文学作品在表现基督信仰的同时,也融进了其他宗教的独特的神学精神。这是中国文学吸收宗教元素时一个比较具有民族个性的特点。像许地山的《缀网劳蛛》就是这样。这部小说的主题虽然是宣扬基督教的宽容与博爱精神,但在结尾处,却借主角尚洁的口作了一番极有佛教式宿命论意味的表白。按照小说中的说法,最终决定人命运的,并不是基督的启示,而是天地间一种更为扑朔迷离的神秘力量。许地山这样的描写,虽未颠覆文本主体的价值立场,却给小说增添了一些与基督教精神完全异质的内容。冰心的许多作品也是如此。她的《超人》、《繁星》、《春水》中的大部分篇什,《往事》之十,《寄小读者》中的大部分,在表达某种基督教情感的同时,也都融进了佛教、印度教、中国本土宗教的许多精神理念。
注释:
①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论著有马佳的《十字架下的徘徊》(〔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杨剑龙的《旷野的呼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王本朝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许正林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②鲁迅:《复仇(二)》,《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第179页。
③④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第13页,第13页。
⑤参见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修订版。
⑥⑦⑧巴金:《火》,《巴金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14页,第611页,第614页。
⑨萧乾:《栗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版,第21页。
⑩曹禺:《〈雷雨〉序》,《曹禺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版,第14页。
(11)有关“序幕”、“尾声”的氛围塑造只是起到烘托命运主题的作用,曹禺本人有非常清楚的论说,可参见《〈雷雨〉的写作》 (《曹禺全集》第五卷,第10页)。
(12)可参见《圣经·雅歌》第2章第1节、第2节、第16节。
(13)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穆旦诗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版,第123-124页。
(14)穆旦:《隐现》,《穆旦诗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页。
(15)穆旦:《我歌颂肉体》,《穆旦诗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页。
标签:基督教论文; 基督教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拯救与逍遥论文; 雷雨论文; 穆旦论文; 读书论文; 未央歌论文; 耶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