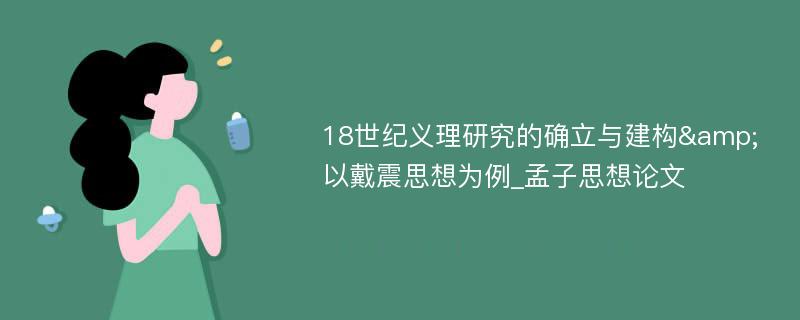
十八世纪义理之学的确立与建构——以戴震思想为例的个案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理论文,为例论文,个案论文,之学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2)04-0039-06
18世纪中叶是我国历史上的所谓“乾嘉盛世”,考据学成为这一时期学术的主流。但当一般学人沉湎于考据之学而难以自拔之时,戴震则超越时贤,自觉确立和构建了其义理之学思想体系,成为当时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本文拟以18世纪乾嘉考据学为叙述背景,对戴震在自觉确立和建构其义理之学思想体系时所遵循的两条基本原则及理论表现形态做学理上的说明。
戴震义理之学确立之基本原则
(一)“由训诂而推求义理”原则
从经学的角度来看,经典诠释者们一开始就预设了一套“真理系统”,认为在儒家经典中隐含着一种绝对普遍的真理,戴震称之为“道”、“义理”。每个人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对经典的训释而发掘、阐发经典背后隐藏的“道”或“义理”。这种“真理预设”的思维方式,对于打破传统束缚、解放思想起到了积极进步的作用,但由于它往往是以寻求经典背后的“义理”为目的,容易流于断于己意的弊端。为了避免出现这一流弊,戴震建立义理之学所采用的原则,是试图将义理之学置于严格的考据学基础之上。如果把戴震义理之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做一划分的话,戴震前期确立的治学原则就是“由训诂而推求义理”,后期确立的治学原则则是“执义理而后能考核”。戴震前期的治学原则,能为当时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最普遍的看法如章学诚所言,戴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知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1]戴震作为在当时被广大学者认可的著名考据学家,对当时几乎所能涉及到的学问都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研究,我们从戴震留下的宝贵思想资料中大多数是关于文字、音韵、考据、训诂、名物制度、天文、地理等,就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戴震作为考据学家这一不争的事实。但是,戴震并没有局限于为考据而考据,并没有把考据作为终身的目标,而是仅仅把它作为一个过程、一个手段、一个前提。其目的就是从文字考据出发,借助正确的推论方法,来寻求文字背后的“义理”,同时为自己的义理之学寻找“经言”依据,以作为阐扬自家“义理”的根本立足点。戴震弟子段玉裁鉴于当时一般学人对戴学的不理解,特别指出:“先生之治经,凡故训、音声、算数、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恶是非,以及阴阳气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实。盖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成。用则施政利民,舍则垂世立教而无弊。浅者乃求先生于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间,惑矣!”[2-1]具体说来,戴震之所谓“义理”,不同于程朱之所谓“义理”。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界定:从经学的角度来看,“义理”是儒家原典背后所显示的价值意义,“由训诂以求义理”,实即由训诂求古经中之义理。训诂明而古经明,古经明而义理明。就是说,它必须通过“以字通词,以词通道”的途径来获得;从对待传统的角度来看,“义理”是破除“株守先儒而信之笃”后的理性精神,它必须通过寻求“十分之见”的方法来获得;从人性自身的角度来看,“义理”是“情之至于纤维无憾”的真情表露,它必须通过“体情遂欲”的方式来获得。这样,戴震所谓义理与程朱所谓“得于心而具于天”的义理尽管在文字、形式上相同,但在内涵、本质上却有了根本的区别。
戴震还针对宋儒只重“义理”而不重史料甄别的弊端,认为“义理”不但存在于儒家经典之中,而且还存在于典章制度之中。他说:“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在乎典章制度者是也。……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3]可以说,戴震的这一思想是对清初顾炎武“通经明道”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戴震早年确立的“闻道”思想并非空穴来风,它与继承、借鉴前贤时哲的思想有关,但更主要是批判、抨击程朱理学的结果。尽管戴震在早年就形成了“闻道”的思想,但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所从事的只是为其“闻道”所做的“小学”方面的积累工作。他后期的“闻道”思想更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如果说戴震前期“闻道”之思想侧重于阐明“圣人之道在《六经》”,在于强调古贤圣之道的话,那么,戴震后期“闻道”之思想则侧重于强调古贤圣之道与“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有机结合,在于一种新义理之学思想体系的自觉建构。戴震对其自觉建构义理之学体系所形成的一系列思想原则和方法是随着对程朱理学由崇信而怀疑、由怀疑而批判逐渐完善起来的。因此,戴震关于义理之学思想的提出,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进步意义。
那么,戴震是如何从考据训诂中来推求其义理的呢?戴震认为,宋儒也以寻求“义理”作为最终价值目标,但是,宋儒之“义理”并非构筑在坚实的训诂考据基础之上。宋学者黄震说:宋代经学的最大特点,就是“摆落训诂,直寻义理”。而戴震提出的“由故训以明义理”,恰恰是与宋儒针锋相对的。如此,宋儒之“义理”便可随意解之,求“义理”,也无需经过语言文字的工夫就可“径至”而达到。对此,戴震指出,宋儒所谓“谓大道可以径至”的方法,对寻求“义理”是十分有害的。他说:“谓大道可以径至者,如宋之陆、明之陈王,废讲习讨论之学,假所谓‘尊德性’以美其名,然舍夫‘道问学’则恶可命之‘尊德性’乎?未得为中正可知。群经六艺之未达,儒者所耻。”[4-1]在戴震看来,“尊德性”必须以“道问学”为基础,没有“道问学”,“尊德性”何以能存在?同样,求“义理”也是如此,他认为求“义理”不可“径至”,而必须从研究“本经”入手,循序渐进,从而达到闻“道”、求“义理”的目的。
戴震还认为,宋儒之解经,还常常援袭释老之言,给人们认识宋儒之真面目造成了极大困难。“宋以来儒者皆力破老释,不自知杂袭其言而一一傅合于经。遂曰‘六经孔孟之言’。其惑人也易,而破之也难,数百年于兹矣。”[5]戴震还以朱熹之注“四书”为例来指斥宋儒解经之谬。他说:“朱子四书注:《大学》开卷说‘虚灵不昧’,便涉异学;云‘以具从理而应万事’,尤非‘理’字之旨。《中庸》开卷‘性即理’也,如何说性即是理?《论语》开卷言‘学可明善以复其初’,‘复其初’出《庄子》,绝非孟子以扩充言学之意。”[6-1]
他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4-2]戴震认为,所谓“义理”存之于古经和典章制度之中,通过严格规范的语言文字、训诂考据工夫,就可发掘和体察古经和典章制度背后的“义理”。戴震是把义理之学建构在扎实的考据训诂基础之上。他在给方希原的书信中,就提出:“古文之学……在今日绝少能者,且其途易歧,一入歧途,渐去古人远矣。”[7-1]“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乎闻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笃,如南北朝人所讥,‘宁言周、孔误,莫道郑、服非’,亦未志乎闻道者也。”[8]“后之论汉儒者,辄曰故训之学云耳,未与于理精而义明。则试诘以求义理于古经外乎?若犹存古经中也,则凿空者得乎?呜呼!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是故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二,守讹传谬也。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9]“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薄训诂之学。夫文字之未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未能通,妄谓通其心志,此惑之甚者也。”[10]通过戴震对宋儒的批判可以看出,如果抛开经典仅凭主观臆想来解释经典,人人皆可“凿空”得之,将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人们治经的目的,无非是要认识和体察经典背后的价值和意义。戴震还认为,学者读经,不但需要知道文字的本义,而且还要知道文字在使用过程中的意义。因为“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从宜辨。”[4-3]“六经字多假借,音声失而假借之意何以得?故训、音声相为表里。故训明,六经乃可明,后儒语言文字未知,而轻凭臆解以诬圣乱经,吾惧焉。”[11]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义理明,只有把经典训释者对经典的理解与经典背后的义理在认识层面上达成共识与默契,才算得上真正懂得了经典的精蕴。贤圣的义理并非空漠虚理,而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古代的典章制度之中。认真考释用文字所记载的典章制度,从语言文字入手从而掌握故训、推求义理,就对义理的把握有了经学的前提和逻辑推理的方法。戴震说:“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3]如果把故训与义理割裂开来,就不可能达到推求义理的目的。一句话,戴震试图通过回归原典、通过语言文字,把一切的价值规范都建构在对原典的收集、挖掘及诠释上,并揭示原典之中及原典背后的价值涵义。在这里,戴震揭示的治经必须遵循的逻辑程序是:字——词——道;或,文字——语言——圣贤之心志。
戴震强调寻求“义理”首先要“明经”、“通经”,但要做到“明经”、“通经”是十分困难的,宋儒的根本错误之一就是背离儒家经典,不知语言文字而胡乱解经,章学诚曾引述了戴震说过的这样一句“狂言”:“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12]戴震这种以为当时许多所谓“学者……不曾识字”的议论,很明显是针对程朱理学家而发的。不识字就不可能达到寻求“义理”的目的。戴震说:“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布置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4-3]在戴震看来,若不懂得这些具体学科的知识,就谈不上“通经”,更谈不上“明道”。与这一治学观点相一致,戴震谈了自己在这方面曾有过的困惑,“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即不敢读‘关关睢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15]可见,戴震对经学的研究,遍及当时的各门学科。广博精审的知识,为戴震提出的“义理之学”构筑了扎实可靠的基础。
(二)“执义理而后能考核”原则
戴震的“由训诂而推求义理”原则在当时得到了一般学者的广泛认同,但他后期的“执义理而后能考核”原则都受到了来自考据学内部及理学家的指责和反对。当时以为戴震之“义理”与程朱之“义理”皆出一途,是“空谈义理,可以无作”。对戴震的义理之学,时人也多“莫能名其为何等学”。在乾嘉时期的学术界,对“义理”的定位问题曾有过激烈争论。姚鼐认为“天下学问三事,有义理、文字、考据之分”。戴震也把学问分成义理、考证、文章三部分,他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7-2]三者之中又有轻重主次之不同。戴震把义理称为“源”、“大本”,认为义理居其首,义理之学综赅天下之大道。“明义理”是为学的最终目标,段玉裁在《戴东原集序》中又对戴氏的“学问之途”做了详细说明,“其(指戴震)言曰:‘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又说:“玉裁闻先生之绪论矣。……执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2-2]还有一段类似的文字,见于段玉裁写的《戴东原先生年谱》中。段玉裁说:先生初谓:‘天下有义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吾于三者皆庶得其源。’后数年又曰:‘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义理又何源哉,吾前言过矣!’[6-2]在这里,戴震已明确把“义理”作为一切之根本。执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表明“义理”在价值上要优先于考核、文章。基于这一前提,戴震批评当时能文章、善考核者,都是一群不善闻道者,他说:“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乎闻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笃,如南北朝人所讥:‘宁言周、孔误,莫道郑、服非’,亦未志乎闻道者也。”[8]
戴震已经开始从单方面强调“以训诂求义理”向“训诂与义理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可以说,戴震“以训诂求义理”到“执义理而后能考核”,是他经学思想的一次巨大转变和质的飞跃。戴震曾就“义理”与“考核”之间的内在关系,做了一个十分贴切和形象的比喻。他说:“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就误以为轿夫为轿中人也。”[2-1]戴震这一时期的“义理”既不同于程朱之“义理”,也有别于前期治学提出的由训诂而推求之“义理”,而是一种“自得之义理。”(注:戴震族人戴祖启在致其子函中,曾记戴震临终有言:“生平读书,绝不复记,到此方知义理之学可以养心。”理学家以此推断戴震晚年对己之主张已有悔过之意。实则不然。焦循之论最为确当,指出“其所谓义理之学可以养心者,即东原自得之义理,非讲学家《西铭》、《太极》之义理也。”[13])戴震提出这一主张,恰逢其《绪言》完成之际。据王茂先生考证,戴震确立义理为考核、文章之源,当在完成《绪言》之际,这一时期也正是戴震思想对程朱理学由怀疑转向批判的时期。这是戴震从早年提出“闻道”以来,首次从一名考据学家转化为哲学家的尝试,也是戴震首次自觉建构其新义理思想体系的尝试。以后的十年中,戴震不断强化这种意识,一点一滴地为构建自己的义理之学思想体系寻找历史、理论和方法上的支持。到“正人心之要”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完成,标志着戴震已完成了由音韵训诂到探讨义理的思想转换,表明戴震已经建构起了一套完全不同于程朱理学系统的新的义理之学思想体系,也标志着戴震已经在思想观念上和价值目标上完全超越了当时的社会、当时的考据学者,成为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并确立了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因此,戴震在考据训诂方面的成就只是他整个思想学说的一个构成部分,其最重要最能体现戴震思想特色的是他义理之学方面的成就。
戴震义理之学的理论表现形态
以上我们对戴震义理之学思想确立之前提及原则方法做了一番梳理。通过这番梳理,戴震与程朱理学在“义理”问题上有了泾渭的分明。那么,戴震一生所孜孜以求的“义理”在理论上具有怎样的结构,在形态上具有怎样的表现呢?
众所周知,在中国早期思想文化中,一直存在着天道与人道两大系统。《周易》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来形容这两大系统。道家文化侧重于天道系统,而儒家文化则侧重于人道系统。这两大系统在中国早期文化中便呈现出“合一”的趋向,但在宋明以后则逐渐出现分离。尤其在宋明理学那里,不但天道系统与人道系统互相分离,天道系统超越于人道系统,可以脱离人道系统而独立存在。程朱又把天道系统划分为理气、道器、形而上与形而下等许多子系统,并认为空漠虚无之“理”存在于气之先,“理”成为产生一切、决定一切的终极精神实体;至于人道系统,程朱把它划分为理欲、心性、情欲等,并认为天理是主要的,人欲则是微不足道的,因而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无论是天道系统,还是人道系统,在程朱理学看来,都过分夸大和强调了“虚”的一面,其表现形式就是在本体论层面上承认有可以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在哲学层面上把追求义理之学作为最终的价值目标。戴震从形式上接受了程朱把天道与人道二分的思想,这是戴震反击程朱的一种策略。戴震说:“道有天道、人道。天道以天地之化言也,人道以人伦日用言也。是故在天地,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谓道;在人物,则人伦日用,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气化之不可已,是为道。”[14]简单说就是“天道,阴阳五行是也;人道,人伦日用是也。”[15]但戴震又指出,天道与人道各有其运行规律,它们之间不是相互隔绝、相互冲突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包融的。可以说,戴震的义理之学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丰富、深化和发展。与程朱在思维方式上相反,戴震认为,一切“虚”的东西必须以具体事物为存在的基础,它只能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而不是相反。在戴震的思想系统中,注重征实、注重实事求是、注重科学方法成为其思想的最大特点。
戴震的义理之学思想,除了在其经学或自然科学及其他领域的论著中有所涉及外,主要体现在他有关义理之学思想的18篇论著中。这些论著(包括文章和书信)按时间顺序篇次如下:《法象论》、《与是仲明论学书》、《与姚孝廉姬传书》、《答郑丈用牧书》、《与方希原书》、《原善》三篇本、《读易系辞论性》、《读孟子论性》、《原善》三卷本、《孟子私淑录》、《绪言》、《大学补注》、《中庸补注》、《孟子字义疏证》、《与某书》、《答彭进士允初书》、《丁酉与段若膺论理书》、《丁酉与段若膺书》。戴震的义理之学思想经历了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反映在其论著中,就是一个不断思考和修订、不断补充和完善自己见解和结论的过程。于是,对戴震义理之学著述孰先孰后、“孰为定本”的问题,在戴震弟子段玉裁与戴震学友程瑶田之间曾有过争论[16]。在戴震的所有义理之学著述中,如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对《读易系辞论性》重视有加。对该文在戴震思想中的重要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读易系辞论性》一文是戴震义理之学从元气自然观通过“人性”向社会政治、伦理领域过渡的一篇重要文章,该文所涉及的一些概念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奠定了戴震整个义理之学的基础。因此,王国维说:“戴氏之学说详于《原善》及《孟子字义疏证》,然其说之系统具有《读易系辞论性》一篇。”王国维认为这篇文章集中体现了戴震义理之学的精神实质,“由此而读二书则思过半矣。”[17]
戴震的义理之学的确是一个不断补充、修订、完善的过程,我们在研究戴震义理之学时,应牢牢把握戴震的这一思想特征。在戴震不同时期的义理之学著作中,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就是同一段话、同一个命题、同一个概念,往往出现在不同的著作中。若不认真琢磨、理解,很容易把它们等同起来。其实,这些概念、命题尽管或在用法上形若相似,或只是更改了其中的几个字,但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譬如说,《原善》中的概念范畴和语言表达方式,多见之于《法象论》、《读易系辞论性》及《读孟子论性》中。有的前后语言风格及表达形式完全一致;有的则根据思想的变化,对前期的思想或命题做了修改和补充;有的前后含义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因此,我们对戴震义理之学进行研究和探讨,首先要确立辩证发展的观点,把他早、中、晚期的观点区别开来,从中寻找戴震义理之学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同时也要避免对戴震各时期著作不分先后、平等对待的倾向,从而把戴震的义理之学思想说成是一个混乱的自相矛盾的体系。通过对戴震义理之学思想的分析,我们从戴震在建构其义理之学时一种独特的学术现象中——如《原善》有前后两种版本,《孟子字义疏证》也有前后两种版本——可以窥见戴震自觉建构其义理之学体系的执著与追求。通过前后两种版本的修订和补充,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戴震义理之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脉络。如《原善》三篇本和三卷本,在写作时间上相差10多年(1753-1766年),在这10多年中,戴震的思想观点发生了重要变化。从戴震思想发展的内在线索看,《读易系辞论性》、《读孟子论性》两文恰恰为由篇本到三卷本的中间环节。戴震在三卷本自序中说,他在《原善》三卷本中,采取“援据经言,疏通证明”、“比类合义”等方法,阐述了天道性命之学与经书之奥旨,力辟宋明儒者“习所见闻,积非成是”之弊[18]。《原善》三卷本是戴震第一部系统阐述自己义理之学思想的重要论著,也是戴震从早期唯心主义理本论向唯物主义气本论转变的中间环节。尤其是戴震在《原善》三卷本中以对现实政治的揭露和抨击作为结尾,更加表明了戴震的义理之学不单纯是一种思辨的学问,而有其鲜明的政治色彩。也就是说,戴震义理之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他的理论落实到了政治批判的层面。再比如,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在写作形式上综合了《原善》、《孟子私淑录》及《绪言》的思想,但在理论层次上,《孟子字义疏证》发展和超越了以前所有的认识观点,不但把对程朱理学的批判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从理论的批判深入到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戴震通过对《孟子》“疏证”的形式,以自问自答的体裁,从《孟子》中选出11个概念范畴予以重新疏证和诠释,在诠释目的、体例、方法等方面超越了以往的注经解经方法,在思想的深刻性上以及方法论的运用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因此,我们认为,《孟子字义疏证》虽然披着孔孟的外衣,但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却达到了当时理论思维的最高水平,可以说,《孟子字义疏证》是戴震义理之学的代表作,而此前的所有义理之学论著,只是向义理之学趋于成熟和完善的各个逻辑环节和发展阶段。另一方面,戴震的义理之学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有一个相当严谨完整的逻辑结构体系。这一体系由三部分组成:即天道、性、人道。每一部分又由若干不同的概念范畴构成,如天道系统之道、气、理、神、化、器,人性系统之性、命、才、知、情、欲,人道系统之仁、义、礼、智、权、善等逐一加以定义和界说,然后通过一定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把这些概念范畴贯通起来。各个范畴和论点之间都存在着严密的逻辑层次和逻辑关系,其推理和论证也相当细密,戴震构建义理之学的方法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戴震的义理之学不但具有深厚的经学基础,而且具有较为严密完善的逻辑思想体系和成熟的思想内涵。这一思想体系是与程朱理学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戴震超越当时的考据学者,成为中国18世纪最伟大思想家的重要标志。戴震遂以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继承者和总结者,并且是开启19世纪近代启蒙思潮的关键性代表人物。梁启超对戴震之学给予了高度的赞誉,他评价说:“苟无戴学,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19]
[收稿日期]2002-06-18 [修回日期]2002-0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