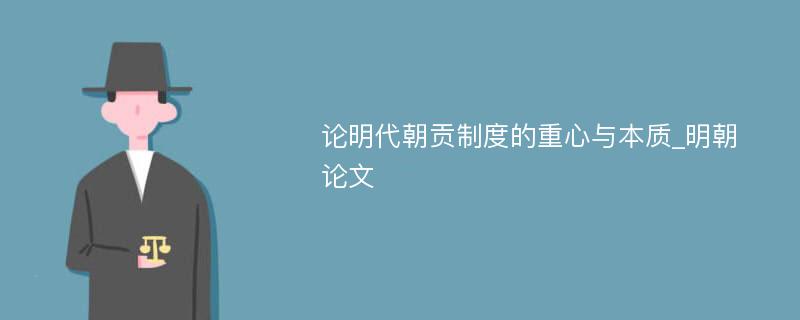
交邻有道,实为保土之方:论明代封贡体系的重心与本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重心论文,本质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1-0105-13
关于封贡体系的重心与本质,在中国古代本来是一个不需要过多思考与争论的问题。近年来中外学者对此展开论争实肇源于滨下武志、费正清和何伟亚对中原王朝传统政治观念后现代式的解构。其代表性著作便是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与《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陶文钊编选的《费正清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何伟亚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据滨下武志治近代亚洲经济史的思路来看,他实际上是认为,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的重心在于经济,封贡体系实质上基本就是朝贡贸易体系的代名词,朝贡贸易是朝贡关系得以维系的很重要的基础和基本特征之一,中国明清时期封贡体系的发展演变史体现于东亚地区就是一部区域朝贡贸易发展演变的历史。而费正清则对清朝对外关系中以厚往薄来为特征的贡赐贸易颇为注意,认为清代有借助属国、属部万邦来朝的盛况增强其在国内的政治威信的动机,“而威信是践行统治时至关重要的工具”。[1]“中国统治者通常宣称,他们准备牺牲经济内容以保持政治形式。他们一般不肯承认对于贸易的任何依赖,因此贸易只有从属于纳贡才算是合法。”[2]不难概括,费正清认为清代封贡体系的重心在于礼仪典制。何伟亚则对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噶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来华交涉通商事宜遭拒一事中的礼仪之争兴趣浓厚,并进而将该朝贡礼仪之争视为正在扩张中的东西方两大强国的遭遇与对撞。严格来讲,滨下武志、费正清和何伟亚的论说时段和对象是相对固定和明确的,其学说固有须待商榷之处,与本文的研究时段与对象并不完全契合,但国内学界对国外汉学之思潮、范式素来关注,风气所及,上下推展,动辄影响国内史学研究十数年乃至数十年,因而上述三位学者之学说思想又势必与本文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关联,即对封贡体系中的军事防卫、贸易往来、礼仪典制诸功能要素的层级地位如何排序的问题,该排序是判定封贡体系重心与本质的关键。虽然限于篇幅,笔者不能对上述三种论说详加剖析,但撮拾明代史事廓清明代封贡体系的重心与本质,或许能够对学界深入反思历代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的运行机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而国内学者对明朝封贡体系的根本性质的认识歧异,①更昭示出笔者深化此项研究的必要性。
一、封贡诉求的多元性与封贡政策层级差别的内在关联
笔者认为,廓清封贡诉求的多元性与封贡政策层级差别的内在关联是探寻封贡体系的重心与本质的关键。封贡体系固然有礼仪、秩序、往来贸易、军事防卫诸多功能,然诸功能在封贡体系肇建、维系中的地位并非等同,潮去岸显,水落石出,在失去地缘军事比较优势以后,封贡体系的原有格局出现松动、分化,其诸多功能自然不能同时保留,必遭受中原王朝剥竹笋式的层层政策抽离(这种现象笔者暂称之为封贡多元诉求的退行性选择),而于中原王朝的政策取舍之际,能保留至最后者方可堪称封贡体系的重心与核心所在。整个封贡体系的运转与维系也无不以此为依托和努力的终极目标。此种判断,于中原王朝强盛之时或稍难,于中原王朝衰微之际则甚易。明朝无疑是笔者寻找封贡体系的重心并作出最终判断的一个绝佳样本。
就明代封贡关系而言,表征天朝上国与其属国、属部、一般交往者政治、军事关系的仪制主要为封、贡。封与贡二者如唇齿不可分,天朝有封,而后属国、属部有贡,无封而贡者,天子可却其贡;受封而不进贡者,天子可遣使责之、索之。大明历史上册封而不允其贡者,惟万历二十三年正月明之待日本一例也,当时册封关白丰臣秀吉本为中日媾和中无奈之举,故不允其贡、市。贡则有诏贡、许贡、索贡、却贡、绝贡五种。此五者皆以天朝上国为其封贡秩序的主导者和核心。表征天朝上国与其属国、属部、一般交往者经济关系的政策,则为互市与民市。陆上对互市之管制有开市与闭市,沿海及外洋于互市之官制则有海禁、弛禁与开禁。各因时势以通权达变。诏贡、许贡、索贡、却贡、绝贡体现了明朝与其封贡体系成员政治关系的亲疏远近,互市之管制则是明朝对与其政治关系相对较近,于军事防卫方面又能互相信任的封贡成员主要是属国、属部实施的羁縻之术,而非单纯的经济政策。因而互市属于政治羁縻手段,互市与否由明朝视其与大明的军事安全冲突与否而定,但有丝毫窒碍之处则互市必不允行。因而,在明臣看来,“互市事至钜,必院、道熟议方敢上闻”,“奏请权尝在抚、按”。[3]
就明代封、贡、市政策实施的具体情形来看,终明一代,明政府在“封”、“贡”、“市”的政策实施中坚持以封贡体系的圈层划分为前提,特别是封贡体系中的贸易环节始终奉行圈层性差别政策。明代于属部普遍实行册封、通贡、互市政策,双方于封、贡之外兼开互市;于属国之素来恭顺者如吕宋、琉球、大泥则皆册封、许通贡并默许使臣从事一些附贡民间贸易但不允于明朝本土互市。如嘉靖九年十月,给事中王希文即言:“暹罗、占城、琉球、爪哇、浡泥五国,贡献道经东莞。我祖宗立法,来有定期,舟有定数,比对符验相同,乃为伴送,附搭货物官给钞买,载在祖训可考也。洪武间以其多带行商,阴行诡诈,绝不许贡。”[4]万历四十年以后明朝因防倭之需始允琉球市于福建外海小浧地方,于吕宋、大泥则仅允许福建漳、泉之民往市其国,“先是,吕宋澳开,华人始航海涉境上贸易”,吕宋因而才有机缘成为明朝与西洋诸国贸易的中介地:“吕宋,第佛郎机之旁小邑,土著贫,无可通中国市,其出银钱市汉物,大抵皆佛郎机之属。而和兰国岁至焉,于是红毛岛夷,始稍稍知与中国通矣。华人利其银钱,率一直而数倍售之;辄侦其船之至不至,酤一岁赢息高下,有守冬以待者。”[5]“漳、泉之商贩大泥、吕宋诸国者,岁数十艘,人不啻数千”。[6]对于封贡体系中的一般交往者如日本、佛郎机、和兰(荷兰)、西班牙等,明朝鉴于其武力强大、嚣悍难制、屡有侵扰则既不愿与之发生封、贡关系,亦不许在华互市。
可见,封、贡、市政策的圈层性差异实为明朝封贡体系中属部、属国、一般交往者在经济领域中的最大差异。明朝政府特意设置这种政策差别,通过对封、贡、市政策的灵活调控,尽力避免与具有强大的潜在军事威胁能力的西洋诸国发生官方往来,尽力阻止其留驻中国境土,以绝后患。
就前文所述贡、市政策的圈层差别与实际演化而言,明朝作为天朝上国的尊严与荣耀、天下之主的地位与声望显然与明朝对其封贡仪制、封贡体系秩序的维护与调控二位一体,密不可分。明初以来盛行的存祀主义以及明朝对安南的两次征伐虽然皆出于明朝维护其天下之主的尊严、稳定原有封贡秩序的愿望,但最终的事实却是:存祀主义让位于现实的地缘军事战略,自明初以来明朝政府就放下了存祀主义的包袱,于属国之内乱、内政力行其和平、中立政策;明朝对安南的两次军事行动最后也都以明朝的迅速抽身结束,特别是宣德二年明朝军政人员撤出安南一事,于此体现得最为充分。
因关乎主旨,笔者于此略述宣宗罢兵之情形。宣宗即位后,颇不愿劳中国以镇外夷,“虚内以事外”,宣德元年四月、宣德二年正月宣宗两次与阁臣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探讨单方面停战、从交阯撤兵之事,并假借太宗遗意直截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因黎氏弑其国主、毒害国人,太宗皇帝不得已有吊伐之师,初意但讨平黎贼之后即求前王子孙立之,盖兴灭继绝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孙为黎贼杀戮已尽,乃徇土人之请建郡县、置官守,非出太宗皇帝本心。自是以来,交趾无岁不用兵,一方生灵遭杀已多,中国之人亦疲于奔走甚矣。皇考常念及之,深为隐恻,故即位之诏施恩于彼特厚。昨日遣将出师,肤通夕不宁,诚不忍生灵之无辜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乐初使自为一国,岁奉常贡,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朕素志如此,本不系用兵之如何。[7]
虽然在宣德元年十二月,明朝再次派遣安远侯柳升率军往援交阯守将王通,“征剿交阯叛寇”,但次年正月宣宗仍坚持罢兵之议,对于反对停战撤兵的蹇义、夏原吉,宣宗则称,“蹇义、夏原吉拘牵常见,若从所言,恐中国之劳费未已。……联今欲成先志,使中国之人皆安于无事。”[8]这年五月,交阯方面明军请求增调广西土兵一万人入援,遭到宣宗的断然拒绝,宣宗“悉止之,令自为守”。[9]宣宗的态度对明朝交阯守军震动极大,恰好这年九月交阯叛军首领黎利至隘留关柳升军前,“乞罢兵息民,立陈氏之后主其地”,[10]交阯守军遂无战意,“交阯总兵官成山侯王通等大集军民官吏出下哨河,立坛与黎利盟誓,约退师,遂宴利,且遗利金织文绮表里,利亦奉重宝为谢。”[11]同年十一月乙酉,明朝遣使安南诏谕黎利:同意安南独立,明军将撤出安南。而王通遂于十二月“不俟朝命”,“率师出交阯”。[12]
考诸明朝历次强硬外交与对外争战,明朝基本上仅在涉及自身军事安全与王朝重大利益时始行干涉主义,必要时不惜以武力解决之,并辅之以贡、市政策的变化作为军事、外交行动的奥援。而封贡体系内外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传播更是借助天朝的有限赐予以及使臣的往来实现的,是中原王朝宣威于属国、属部的副产品。由此看来,尊严与荣耀、秩序与声望乃至王朝领土的扩张绝非明朝封贡体系的重心所在;文化交流与文明传播作为前者的副产品,在封贡体系诸功能中的地位自然更下之;明朝封贡体系的重心与本质显然在于其陆基国土防卫功能,因为明代贡、市政策的前提与初衷只与此国土防卫功能息息相关、时时相关,终明一代,终始如一,这种规律是对此种重心与本质的有力佐证。而有明一代与朝鲜、日本、佛郎机、蒙古鞑靼部封贡关系的曲折变化更是对此种重心与本质的四个力证。[13]
终明之世,日本、葡萄牙以及1580年吞并葡萄牙的西班牙人都未能与明朝建立起封贡关系,其在东亚、东南亚的贸易始终是以私商贸易的形式进行的,其贸易网络所以能够维系并扩大,仅得益于其以武力为后盾对明朝东南亚诸属国的蚕食鲸吞以及海盗式的商业经营,而始终没有得到明朝官方的正式认可、支持和保护。相比之下,明朝与北虏蒙古俺答汗所领鞑靼各部的边境互市自隆庆五年三月以来不仅顺利展开,并一直维系了整整70年(包括俺答汗时期的30年与其妻三娘子在位时期的40年)。这是蒙、汉双方共同推动的结果,特别是大学士高拱、张居正与边臣王崇古在两次廷议中力争的结果。自嘉靖三十年以来,鞑靼部为求互市屡次兴兵内犯,明军与鞑靼部相互争战20年,明臣已渐渐认识到许市则两利,不许市则两害。远非羁縻之术所能尽言,在张居正看来,仿照明朝与女真部族互市的开原事例,允其通贡,“因其入贡之便,官为开集市场,使与边民贸易有无,稍为之约束,毋得阑出中国财物及应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只要措置得宜于明朝北方边政将有五利:
敌既通贡,逻骑自稀,边鄙不聳,穑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复屯田,蓄吾士马之力,岁无调援,可省行粮数十百万,二利也;土蛮、吉能每借俺酋以为声援,俺酋既服则二虏不敢轻动,东可以制土蛮,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赵全等既戮,板升众心已离,吾因与虏约,有愿还者必勿阻之,彼既无勾引之利,而又知虏之不足恃,则数万之众皆可渐次招来,豊州之地可虚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孙情乖意阻,胡运将衰,其兆已见,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顿、呼韩之变,我得因其机而行吾之计,五利也。[14]
高拱事后的看法亦与此相似。[15]显然,明朝与俺达部实现封贡、互市,实为缓解当时的北疆军事危机之亟图。事实证明与俺达通贡是卓有成效的,高拱评价曰:“国家九边皆临敌,在山西宣大则有俺达诸部,在陕西三边则有吉能诸部,在蓟辽则有土蛮诸部。西驰东骛,扰我疆场,迄无宁岁。辛未,俺答率老把都儿、黄台吉暨吉能等,稽颔称臣纳贡,于是七镇咸宁。独土蛮獗强,犹昔建州诸彝与之声势相倚,时为边患。”[16]但鉴于蒙古部族军力的强大,明廷在与俺达汗进行通贡、互市的同时亦保持相当的戒心,高拱的思虑可为其代表:“封贡一节,本欲假此以修内治,待内治充实之后,其势在我,则任其叛服皆不足虑。若遂以此为安而高枕焉,则乱之道也。”[17]高拱奏请,“三岁遣近臣视塞,以八事殿最边吏,积饷、修险、练卒、锻甲、督屯、理盐、养马、招降,皆以数课计,治其功罪,绩最者同斩虏,废坏者仿失机。上嘉纳焉。”[18]
不过,相较之下,明朝基于军事防卫安全级别的判断不同对朝鲜、日本、佛郎机与蒙古鞑靼部封贡政策的巨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而这恰恰是明朝封贡体系服务于明朝的国土防卫需要、国土防卫功能在封贡体系诸功能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有力明证。至于嘉靖倭乱结束以后,明朝政府允许福建漳、泉滨海地区居民往贩东、西二洋,其政策调整的前提即是“漳泉滨海居民鲜有可耕之地,航海商渔乃其生业,往往多至越贩诸番,以窥厚利。一行严禁,辄便勾倭内讧”,并且最重要的是,“吕宋素不为中国患”,“华夷相安,亦有年矣”。[19]因此,嘉靖倭乱结束以后,闽人数万人得以前往吕宋等东南亚诸国经商并定居,“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20]纵观明后期葡人之灭吕宋、据澳门,荷兰之占澎湖、台湾,无不以请求与之互市、贸易为先导,继之以寻机对贸易所在国、所在地区展开鲸吞蚕食。明人与之绝市可谓颇有远见。至于万历二十一年潘和五率众反抗事件,万历三十年阎应龙、张嶷赴吕宋勘察、采榷金银事件分别引发吕宋的佛郎机人大规模驱逐、诱杀流寓当地的漳、泉商人,明朝对上述事件的善后处理基本上皆属搁置不问、不了了之,这不仅彰显出万历中期以后明朝对东南属国控制力的式微,更赫然表明明朝对封贡体系经济贸易功能的极端漠视,这在明朝对后一事件的处置意见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事发后,明朝负责处理交涉事宜的大臣徐学聚,虽然觉得此次事件“变出异常,法应讨罪”,但最终并未奏请派兵吕宋为死难的华商争取公道,明朝最终只是檄谕西班牙人天朝不再追究其擅杀之罪,西班牙人要停止仇杀华人,并将吕宋国内“所有漳泉遗民子孙,追敛各夷劫去货财赀送还郡”,“自此,商舶交易仍听往来如故”。[21]“时佛郎机已并满刺加,益以吕宋,势愈强,横行海外,遂据广东香山澳,筑城以居,与民互市,而患复中于粤矣。”[22]但与吕宋不同,葡萄牙夷人进入香山澳经商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明朝广东省香山县借其军事力量对付老万、曾一本、何亚八等倭寇、海盗有关,其性质是受明朝邀结来侨寓当地的夷兵,嘉靖倭乱结束后,香山澳葡萄牙人但行市易,且屡示好于明政府,但仍被纳入到广东政府的行政管辖和军事监管体系中,“内不许一奸阑出,外不许一倭阑入”,[23]加之其贸易伙伴主要是日本,明朝政府对这些留居、盘踞于此经商、传教的葡萄牙人,无论是蓄养倭奴、收容被日本幕府驱逐的日本基督徒,还是为抵抗中国海盗、荷兰进犯而私筑城垣以及单纯为传教活动之需修建教堂,都警惕有加,甚至为此多次动用武力强加干预,务令其复旧如初。显然在广东政府眼中,保证明朝对香山澳的有效控制远比每年获得葡萄牙人缴纳几万两税银重要得多。万历四十一年,广东海道副使俞安性又专门制定《海道禁约五款》对在澳葡萄牙人的活动行止加以钳束。[24]
二、明朝对其封贡体系各圈层成员的监控、防范与信息情报搜集
笔者认为,要充分关注明朝对其封贡体系各圈层成员的监控与防范、信息情报搜集问题,因为这恰恰是陆基国土防御功能对明朝封贡体系反向规约、塑造的具体体现和直接结果。
1.明朝对其封贡体系各圈层成员的监控与防范。基于历史经验的长时段累积,明朝君臣一方面努力在封贡体系内外特别是在属国、属部圈层中构建以中原王朝为核心和主体的国家陆基防御体系,另一方面又鉴于这种防御体系成效鲜微而对这一圈层特别是属国普遍存在一种政策安全上的担忧与怀疑,无不在军事、政治、外交领域加强对属国和属部的监控与防范,甚或必要时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而且其监控与防范还处于封贡体系规则的更深、更基本的层面上。简而言之,明朝的监控与防范可分为封贡体制中的常规监控与防范、对封贡体系特定成员的监控与防范两大部分,用前者以守常,用后者以遏巨变。对封贡体系特定成员的监控与防范,其种种事例情形在本文第一部分的论述中已约略有所体现,限于篇幅兹不赘述。这里重点讨论一下封贡体制中的常规监控与防范,细而言之,这种监控与防范又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加强对属国、属部、一般交往者(如日本、西洋诸国)所遣贡使的监控、防范,防其窥伺。明人已清晰地认识到其贡使往来,实有搜集情报之潜在危害。于慎行《谷山笔麈》即痛言:“金之破辽,犹不敢轻举伐宋也,及使者往返既数,道路险易、朝廷治否、府库虚实,渐得要领,而南侵之志决矣。中国底里不可使外夷知之。彼以纳贡为名,往返出入,或有密图山川、潜窥虚实,即平时贡夷,犹不可不备。”[25]因而,对贡使的防范极严密。“洪武开基之初,首重海防,迁海岛之居民,以绝其招引之衅;绝番夷之贡献,以塞其往来之途。……宣德年间,弃南、交而杜雷、廉之道。至如高丽通贡,不许泛海于登莱;琉球来王,示必严兵于福海。”[26]洪武八年,明太祖以“登、莱二州皆濒大海,为高丽、日本往来要道,非建府卫、增兵卫不足以镇之”,遂令“改登州为府,置蓬莱县”。洪武十七年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命延安侯唐胜宗镇辽东,他特地戒敕唐胜宗绝高丽一事,太祖曰:“旧岁今春,高丽之使水陆两至,皆非臣礼,暗行侮慢,明彰亵渎。……此夷自古至今未尝不侮慢中国搆兵祸者也,验古事迹,可与绝交不可暂交,况深交者乎!……今尔胜宗等出镇辽左,高丽必数有使至,其至者送来,勿令其还,以绝彼奸计。若纳其使而礼待之,岁贡如约则可,人亦不可久留辽东,或朝或归,速遣其行。”[27]“辽壤东界鸭绿,北接旷塞,非多筭不能以御未然,尔能筭有余则名彰矣。”[28]对此,明代著名学者严从简亦深以为然,曰:“四夷来王,虽中国盛事,然赏赐宴劳,其费颇钜。且使者频至,与华人情熟,窥伺机密,固当防其渐也。……我太祖严示禁戒,乃谨微之深意,岂特为厚往薄来惜此费而已哉。”[29]《明实录》亦称:“先是,四夷贡使至京师,皆有防禁,五日一出馆,令得游观货易,居常皆闭不出,惟朝鲜、琉球使臣防之颇宽,已而,亦令五日一出。”直至嘉靖十三年十一月,“朝鲜国王李怿以五日之禁乃朝廷所以待虏使,而己为冠裳国,耻与虏同,因礼部以请”,世宗才下诏弛朝鲜使臣五日之禁。[30]而对于贡使的种种非分要求,明朝政府也一律加以驳斥。如天顺年间,“琉球请岁一入贡,回回贡使乞道广东归国,皆以非制格之。”[31]此类事例极多,兹不赘举。
二是纠察本国泄密、通敌之官吏、民众与防制敌方间谍活动。《大明律》卷3《吏律二》对朝廷吏员漏泄军情大事作出规定:“凡闻知朝廷及总兵将军调兵讨袭外蕃,及收捕反逆贼徒机密大事,而辄泄露於敌人者,斩。若边将报到军情重事而漏泄者,杖一百,徒三年。仍以先传说者为首;传至者为从,减一等。”若私开官司文书印封看视者,杖六十;事干军情重事者,以漏泄论。若近侍官员漏泄机密重事於人者,斩;常事,杖一百,罢职不叙。; [32]《大明律》卷15《兵律三·关津》又规定:“凡缘边关塞及腹里地面,但有境内奸细走透消息於外人,及境外奸细入境内探听事情者,盘获到官,须要鞫问接引起谋之人,得实,皆斩。经过去处守把之人知而故纵及隐匿不首者,并与犯人同罪。失於盘诘者,杖一百,军兵杖九十。”还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段匹、细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驮载之人,减一等。物货船车,并入官。於内以十分为率,三分付告人充赏。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漏事情者,斩。其拘该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夹带或知而故纵者,与犯人同罪;失觉察者,减三等,罪止杖一百;军兵又减一等。[33]此外,《问刑条例》内也规定:“官员军民人等私将应禁军器卖与夷人图利者,比依军器出境;因而走泄事情者,律各斩为首者,仍枭首示众。”还规定:“官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往番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远充军。”[34]万历六年以后,海禁有所调整,民人可以至日本以外的诸番贸易,但需经由官府盘验、登记,亦令里甲行连坐法“互相稽查”,防其“通贼接济”。[35[
从法规、政策执行的实际情形来看,明政府对于涉及蒙古、女真、日本、安南、缅甸等诸属部、属国的敌方间谍以及本国的通敌者的确予以最严厉的惩治,反间谍活动可谓不遗余力。以蒙古为例。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宣府捕获虏谍张于库,诏升游击将军张嵩职一级,斩于库首,枭示。”[36]隆庆元年十二月,徐阶等奏陈安边诸事,语及叛入蒙古鞑靼部的赵全、周元等人,奏请“令各边总督镇巡揭榜于道,并多置木牌插于边外,晓谕华人之陷入虏中者……能计斩逆贼赵全、周元等亟首来献,升都指挥佥事,世袭指挥同知,仍赏回宅银一千两。……若赵全、周元能自悔罪率众来降,亦待以不死,仍计人口授职,一应有罪逃在虏中者或自归或率众来降各酌量宥罪行赏”。隆庆帝纳其议。[37]次年,在降人赏格诏中,又重申前诺,并补充说:“或能杀害(赵全、周元)不及斩首自身投降来报者,巡按御史覆实,如前例升赏。”[38]隆庆四年(1570年)十二月,俺答汗为换回先前逃入明境的孙子把汉那吉并推动蒙汉封贡、互市的和议进程,遵从明朝宣大总督王崇古“若赵全等旦至,那吉夕返矣”的约定条件,[39]将赵全、李自馨、王廷辅、赵龙、张彦文、刘天麒、马西川、吕西川、吕小老官等9名叛人解归明朝,隆庆帝随即命人“奏告郊庙,献正法”。[40]当然反间谍活动持续时间最久、情形最复杂、也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明代御倭战争。洪熙时,黄岩民周来保、龙岩民钟普福困于徭役,叛逃至日本,“倭每来寇,为之向导”。正统八年五月,二人又“导倭犯乐清,先登岸侦伺。俄倭去,二人留村中丐食,被获,置极刑,枭其首于海上”。[41]嘉靖初年,“大江南北皆中倭,漕艘几阻。……中国奸民利倭贿,多与通。通州人顾表者尤桀黠,为倭导。以故营砦皆据要害,尽知官兵虚实”。时任吏部考功郎中的郑晓“悬重赏捕戮之”。[42]嘉靖二十六年,副都御史朱纨巡抚浙江兼制福、兴、漳、泉、建宁五府军事,下令申严海禁,凡交结、勾通倭寇的滨海奸民包括“为倭内主”的闽浙大姓为其所获者,“不俟命,辄以便宜斩之”。[43]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亦称,当时以巡按御史裴绅之议,明廷敕令朱纨“严禁泛海通番、勾连主藏之徒”,朱纨乃下令禁海,“凡双樯余艎一切毁之,违者斩”。嘉靖时期之倭乱,实为“沿海诸奸民乘势流劫,真倭不过十之二三”。因此,朱纨在禁海的同时上言朝廷:“去外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群盗易,去中国衣冠盗难。遂镌暴贵官家渠魁数人姓名,请戒谕之,不报。於是,福建海道副使柯乔、都司卢镗捕获通番九十余人以上,纨立决之於演武场。一时诸不便者大哗,葢是时通番,浙自宁波定阳、闽自漳州月巷,大率属诸贵官家,咸惴惴重足立。”[44]朱纨死后,明廷于嘉靖三十一年七月又以佥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巡视浙江海道及兴、漳、泉地方。自此,至嘉靖三十三年三月调任山西巡抚之前,王忬一面整军经武,一面广行侦刺,“凡沿海大猾为倭内主者悉系之,按覆其家。自是倭不复知中国虚实与所从向往,而余艎在海中者,亦无以菽粟、火药通,往往食尽自遁。”[45]其后在朝鲜之役中,明军的反间力度更是表现在其《军令三十条》中:“前锋将领遇有倭中通士、说客至营或拏获奸细,即时解赴本部军前,听指挥发落。有敢私自放归及容隐不举者,副将以上按军法参治,副将以下斩。……各营将领有不严束兵士、谨防奸细以致漏泄军机者,自参将以下斩。……夜巡官军不小心巡缉,偷懒误事者斩。”[46]上述反谍条令不能不说有过于严苛之嫌。朝鲜之役以后,明朝对其宿敌日本的防范更是呈现出长期化、制度化的态势,“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47]
明朝封贡关系史上唯一的一个反间特例是善待丁南杰。嘉靖九年,广西副使翁万达“获安南谍者丁南杰,万达解其缚,厚遇,遣之去,怵以天朝兵威”。丁南杰所以不死,与当时翁万达的政见有关,当时朝廷就安南问题剿抚意见互不相让,战争一触即发,主持安南事宜的翁万达力主和平解决明朝与安南的封贡关系危机,在他看来“揖让而告成功,上策也。慑之以不敢不从,中策也。芟夷绝灭,终为下策”,正是出于这种大局考虑,丁南杰方得以安然释还回国。[48]
2.明朝对其封贡体系各圈层成员的信息情报搜集活动。在严密监控、防范的同时,明朝君臣对其封贡体系中属国、属部、一般交往者三个圈层的军事信息情报搜集活动也极为重视。无论域外水陆舆图的绘制,还是直接服务于特定战争需要的军事谍报,都在其努力获取的范围之列。因关乎主旨,这里以依略述一下。
一是明代对域外水陆舆图信息的搜集、汇总。这种搜集、汇总活动,实质上是元明朝代更迭之后军事地理信息的数据重建,主要集中于洪、永时期,并主要通过往来双方之间的使臣、商旅等的观察、问询、记录来获取。当时,明朝军力尚强,征伐四出,全国大部分地区归于一统,周边属国、属部、一般交往者与明朝建立封贡关系者逐渐增多,明朝封贡体系呈现圈层性扩张,明朝在其封贡体系中威望日增、影响日著,因而,明人这种搜集、汇总活动进展较为顺利。有时候属国为了表示对大明的事大之诚也会主动提供一些常规军事信息。但总体来看,这种搜集只能是借助一定的政治交往契机,渐次搜集、绘制、积累,时间跨度较长且没有统一的规制。检诸史料,其搜集、汇总主要包括如下诸事:洪武三年春,朱元璋“遣使往安南、高丽、占城,祀其国山川。……仍命各国图其山川及摹录其碑碣图籍,付使者还”。[49]洪武五年正月,琐里国王卜纳的遣使朝贡,“并绘其土地山川以献”。[50]洪武六年,暹罗新王参烈宝昆邪嗯哩哆啰禄遣使贺明年正旦,“贡方物,且献本国地图”。[51]永乐元年,御史尹绶受命出使真腊,“自广州发舶,由海道抵占城,又由占城过菩提萨州,历鲁般寺而至真腊。……绶归,凡海道所经,岛屿萦回,山川险恶,地境连接,国都所见,悉绘为图以献。上大悦。”[52]永乐十三年吏部员外郎陈诚出使西域诸国归,“上《使西域记》,所历凡十七国山川、风俗、物产悉备焉”。[53]为嘉其劳,三年后朱棣仍不忘将时任行在吏部郎中的陈诚晋升为广东布政司左参议。[54]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年),郑和等率军2.7万余人七次下西洋,由于郑和兼通戎务与外交,因而在与西洋各国发展商贸、增进友谊的同时,也附带对其所历东南亚、南亚、西亚23国凡四万余里之政情、山川、风俗、人物、土产、物候以及水道、气象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考察。虽然郑和当年出使“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但其通事、随从马欢所著《瀛涯胜览》、费信所著《星槎胜览》、巩珍所著《西洋番国志》、吴朴所著《渡海方程》却使明朝对西洋诸国的了解大为加深,郑和留下的出使水程尤为兵部库房珍藏的重要资料。[55]至明末,人们根据郑和下西洋时所用的海图针经又编绘成《郑和航海图》,该图共收航海所经地名500多个,成为我国最早的航海图,茅元仪所辑《武备志》更认为《郑和航海图》“列道里国土,详而不诬”,将其置于书末,“载以昭来世、治武功也”。[56]而明末清初舟师远洋航海所用的两种针簿《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更是大量吸收了郑和船队对东西洋水道长期探索的成果。
水陆地理信息的不断积累,为明人域内外舆图的绘制逐步奠定了基础。嘉靖二年,郑晓以进士授职方主事,“日披故牍,尽知天下阨塞、士马虚实强弱之数。尚书金献民属撰《九边图志》,人争传写之”。[57]万历四年,户科左给事中萧崇业、行人司行人谢杰出使琉球,归国后绘成《琉球过海图》,长二尺六寸,宽六寸半,附于二人所撰《使琉球录》中,共7页。这是明人首次绘制琉球图。[58]而万历七年钱岱重刻的元代朱思本《广舆图》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明人域外地理考察的总成绩,朱思本《广舆图》原本并不涉及域外部分,明人罗洪先、胡松、钱岱在朱图基础上陆续增补了《朝鲜图》、《朔漠图》、《安南图》、《西域图》、《琉球图》、《日本图》、《华夷总图》、《东南海夷总图》、《西南海夷总图》9幅域外地图。[59]万历三十年(1602年)利玛窦又指导李之藻绘制完成了《坤舆万国全图》,根据香港学者李兆良对该图的研究,②正是依据180多年以前即1423年以前郑和船队远洋航行获得的地理资料而非同时期欧洲的发现,利玛窦得以清晰地在《坤舆万国全图》上勾画出五大洲、四大洋的准确轮廓。[60]
二是对直接服务于特定战争需要的军事谍报的获取。至迟在成化十年余子俊巡抚陕西之时,针对时常处于军事紧张状态的蒙古、女真诸属部以及沿海倭寇、国内沿边地区重大兵变、民变等,还有后来的日本、缅甸、西洋诸国,明朝就已经开始着手创建塘报这种大型的沿边、沿海重大、紧急军情的哨探、分析、传递网络,相比于朝鲜之役中因时、因事而实施的间谍活动,明军沿边、沿海卫所、墩台及一线作战部队皆配属有大量的职业情报侦察人员——夜不收、尖哨,其规制颇为严密完整。嘉靖中期以后,蒙古诸部与明朝的冲突加增,明边军将领遂将“节年虏中走回男子熟知虏情者”[61]以及“边人惯习夷情者”[62]加以拣选、训练,其后或充通事,或充家丁,“与远近侦卒偕往偕来”,进一步增强了明军的情报侦察与军事渗透能力。当然明军间谍网络的效能发挥如何,不仅取决于其间谍管理体制是否完备,也取决于该间谍地域(属国、属部、一般交往者等控制的地理区域)与明朝的民间交往程度,如果该间谍地域商业辐辏、汉人在该地往来经商、居住者甚或汉人被掳者、逋逃入其地者甚多,与当地民众彼此熟稔,信息来源广泛,间谍活动借此掩护往往比较顺利,所获情报亦会较有价值。在明朝对蒙古、女真、沿海倭寇等中国境内敌对力量的长期预警、监控、战争中,明朝的间谍活动能成功显然与此不无关系。相比之下,在日本、缅甸、西洋诸国等敌对力量管辖、控制的地理范围内,由于明朝长期执行海禁政策,禁止私人海上贸易,禁止私人与外国势力相通,少数涉履其地者亦多被明朝视为叛国背祖、营私罔利之奸徒,归国无路,报国无门,则明朝间谍在该地域的间谍活动就会效能大减,很难获得有价值的重大情报。限于篇幅,这些内容笔者将另行撰文探讨,此处从略。
而且,随着明朝军队中后期的作战范围突破本国边界和陆地,向跨海和跨国作战延伸,明军的军事监控、侦刺的地域范围也在大为拓展、延伸,这在东北朝鲜之役、东南清剿倭寇和反击西方海盗的诸多战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在防倭、防日过程中,明军已逐步认识到沿海岛屿的重要性,万历二十三年福建巡抚许孚远奏请在福建海坛、南日岛、澎湖列岛,浙江陈钱、金塘、補陀、玉環、南麂岛屯田驻军,并特别强调了澎湖列岛的战略地位:“彭湖……遥峙海中,为东西二洋、暹罗、吕宋、琉球、日本必经之地。”期望明廷及早派兵屯驻彭湖诸岛,“且耕且守,据海洋之要害,断诸夷之往来”。[63]万历四十四年琉球咨报日本舰队进攻鸡笼(台湾),进一步使明朝认识到台湾在明朝海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今鸡笼实逼我东鄙,距汛地仅数更水程,倭若得此而益旁收东番诸山,以固其巢穴,然后蹈瑕何间,惟所欲为。指台、礵以犯福宁,则闽之上游危;越东涌以趋五虎,则闽之门户危;薄彭湖以瞷泉、漳,则闽之右臂危。即吾幸有备,无可乘也,彼且挟互市以要我,或介吾濒海奸民以耳目我。彼为主而我为客,彼反逸而我反劳。彼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而我无处非受敌之地,无日非防汛之时,此岂惟八闽患之,两浙之间恐未得安枕而卧也。[64]
但限于军费,明朝对沿海诸岛的经营、屯驻进展缓慢,自万历二十六年就开始实施的彭湖驻防实际上成为每年至多5个月的间歇性的季节性汛防,而鸡笼更是长期没有戍兵前往屯驻,这是天启二年至天启四年(1622-1624年)荷兰军队轻易进占澎湖、鸡笼的重要原因。直至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才率兵渡海收复澎湖和鸡笼,郡县其地,并长期驻守,当时距明朝政权在大陆倾覆已经17年了。[66]在常规性的海上巡哨之外,[66]实施跨海机动作战、依托岛屿加强陆防,海陆协同,这些都是先前的中原王朝自卫战争中所不曾出现的新特点、新趋向。
终明一代,尽管明朝统治者自开国以来就一直倡导“交邻有道,实为保土之方”,[67]奉行一种务实性的军事外交政策,重和平忌扩张、重内轻外,以期保境睦邻,但并未稍忘加强其边防武备,并未稍减对其封贡体系的监控与防范,其监控与防范可谓不遗余力、既周且备,较之汉唐宋毫不逊色;其军事信息情报搜集活动亦多可圈可点。同时,为了加强对封贡体系各圈层成员特别是陆上毗邻属国、属部的有效监控,有效应对封贡防卫危机,自明中期以后,明廷开始大力推进缘边地区军事管理体制的改革。明初以来,基于明朝与周边属国、属部、一般交往者的地缘格局态势与封贡关系,明朝封贡体系在地方布局结构上大致形成了七个次级封贡事务处理中心:一是以辽阳都指挥使司为中心,负责处理东北方面的封贡事务;二是以宣大为中心,处理北疆事务;三是以哈密为中心,处理西域事务;四是以河州、朵甘为中心,处理西番事务(藏务);五是以云南(初为沐氏,后为云南巡抚负责)为中心,处理缅务;六是以两广总督为中心,处理东南亚及西洋诸夷事务;七是以宁波、福州为中心,处理日本、琉球事务与海上联防。这七个区域中心虽各有其处置运行机制,但大体上都是围绕明朝的边防和海防展开的,奉命驻守于上述地区的军事主官一般都具有相当程度的临时决断、先斩后奏之权,与北京的礼部会同馆官员凡事皆请于皇帝及朝廷中枢大臣唯命是从的做事风格迥然不同。明朝政府的监控与防范政策也正是通过上述七个次级封贡事务处理中心区别对待、灵活实施的。这套明初颇见成效的机制在明中期却暴露出巨大的弊端,以北疆防御为例,万历十八年,王锡爵在其《论边事疏》中即痛批当时朝政、边政在防御蒙古问题上的三个反常态势:
自敌款二十年来,吏恬卒玩无复守战之备,一旦烽火乍惊,鸣镝内向,则当事者亡羊补牢亦犹未晚,而震怖忧惶止办呶呶追尤首事,此一反也。……武官爨下求安,专藉款关之利;文吏隙中观斗,争谈出塞之功,贾勇不在边境而在朝廷,御寇不以甲兵而以文墨,此二反也。……诸边以彼此支吾为熟套,以日月玩愒为良谋,转和慕效,翕然同风,遇缓急重难之事则隔垣内外便分尔我,如彻哩克一人在宣大则力保其无他,在甘肃则以之为诛首,犯边一事,在西人委东则曰尔何不招,在东人委西则曰尔何不战,皆逃责于己而嫁祸于人,此三反也。……而臣之所忧者,独恐将吏以忘战之久而畏事之甚,苟听要挟急图招抚,使外敌反持中国之权,武吏反袭文儒之论,则其患有不可言者。[68]
有鉴于此,明廷采取了两项措施以督促边臣大吏恪尽职守:其一,对各个次级封贡事务处理中心关涉的地方军事将领、朝廷主事大臣以重赏、苛法为其考课殿最之辅。如隆庆元年十二月敕令:“今后总督、镇、巡仍令各遵敕行事。遇有功罪,自总督以至副、参将、游、守、兵备,有司查照职任一体从公赏罚,著为定例,以杜推诿之私。”[69]万历三十年缅甸出兵十几万人占领云南蛮莫,万历三十二年又占领孟密、孟养,万历三十四年缅甸出兵30万人攻占木邦,负责缅务的云南巡抚陈用宾被下狱论死,陈案可谓首开督抚失地论死之先河。且愈到后来,明廷处置级别愈高,拟定罪罚愈重,“沦开、陷沈、覆辽、蹙广,仅诛一、二督抚以应故事,中枢率置不问”;“俺答阑入,而丁汝夔伏诛;沈惟敬盟败,而石星论死”;陈新甲主辽东议和事泄,被劾以“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专擅便宜者,辱国启侮……即日弃市”。[70]天启七年五月,工科都给事中郭兴奏言:“近年御奴(辽东女真)之兵,强半望风而逃,宜于蓟镇咽喉之处设标兵一营,令大将统之,号曰‘杀逃营’,使关内无逃生之路便决意死守矣”,熹宗纳其言,随即令于“蓟镇咽喉之处设立标营,统以大将,内卫外援俱可相资,防逃之法寓于其中”。[71]其二,一旦面临重大边疆军事危机时,打破各地军事管辖的行政界线,提高方面统帅的事权,以统一协调、调度各省主客兵的作战行动及户、工二部相关兵员的征集、粮饷武器的解运,“世宗朝倭之役,胡宗宪节制七省;今上(万历帝)御极以来,火洛赤之役,郑洛节制九边;播之役,李化龙节制,楚、蜀、滇、黔、闽、粤、浙、齐诸省俱听调遣。”[72]自熊廷弼经略辽东以后,明臣周如磐、官应震等亦屡倡“专用辽抚,赐剑许以便宜从事”,“经略事权不可不重”,[73]允许辽东方面统帅集权节制之议,熊廷弼、王在晋、孙承宗、王化贞、袁应泰、袁崇焕等皆获皇帝“赐剑”,以行临事应变之权。
然而成化以后,明朝农业经济的日趋衰微无疑对明朝的军力重振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使明朝最终陷于内外交困、军民吏俱疲的境地,无以自拔。迨至天启、崇祯时期,辽东战事日亟,天启七年,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封贡防卫体系鱼烂不堪,无所依恃:“奴子妄心骄气何所不逞,我欲合西虏而厚其与,彼即攻西虏而伐我之交;我藉鲜为牵,彼即攻鲜而空我之据;我藉款愚之,乘间亟修凌、锦、中左以扼其咽,彼则分犯鲜之兵而挠我之筑”;[74]崇祯二年,刘宗周痛陈,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养饥军而军愈骄,聚天下之军以冀一战而战无日”。[75]《明史》称:“自辽左军兴,总兵官阵亡者凡十有四人:抚顺则张承荫,四路出师则杜松、刘綎、王宣、赵梦麟,开原则马林,沈阳则贺世贤、尤世功,浑河则童仲揆、陈策,辽阳则杨宗业、梁仲善。是役(即驰援西平之役),(刘)渠与(祁)秉忠继之。” [76]上述诸总兵死于社稷,尚蒙明廷厚加恤典,而诸辽东统帅的命运波折则折射出明帝国封贡防卫体系收缩、衰微之际的无奈与悲哀。王化贞、袁应泰,本为庸才,其罢默迁调固不足议,而其他几位颇有军功、堪于任事的杰出将帅却因朝中党争和清议的干扰、攻击迭遭厄运:熊廷弼,两次被劾,天启五年(1625年)下狱枭首于西市并传首九边;毛文龙,崇祯二年(1629年)以糜饷、自大之名被斩杀于双岛;袁崇焕,因皇太极之反间计见疑于崇祯,崇祯二年被夺职下狱,次年磔于市;孙承宗,两次夺官闲住,崇祯十一年清军攻入京畿南面之高阳,孙承宗被俘自缢死;洪承畴,以文臣督师辽东,战守出于帝旨而不得自专,崇祯十五年于松山兵败被俘;陈新甲,松山兵败后受密旨主持辽东和议,旋以清议遭弃市。明朝政治之窳败姑置不论,仅就军事而言,辽东女真部族实令虚弱不堪的明朝耗尽了最后的一点元气,并直接导致两个恶果:其一,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乘明朝后方防守空虚之际纠集苗众于天启元年、二年相继叛乱,至崇祯十年其乱始定,川黔因之糜烂长达十七年;[77]其二,受辽东战事的牵制,对于崇祯十三年以后复起的李自成起义军的连续攻伐,崇祯帝无兵可调、无力自保,坐困于京城以待毙,可谓惨痛极矣。
综上,从明初以来封贡体系建构、维系的地缘环境的演变特别是明中后期封贡体系的加速式微来看,明朝政府在封贡体系中实施一系列严密的监控、防范措施与军事情报搜集活动,尽管有过于谨微之嫌,却也堪称基于历史经验的远见。多年来,当代史家论及西洋诸国如葡萄牙、西班牙等使华通商,每每认为是单纯的明朝统治者外交观念、海洋观念的落后与对世界形势的无知,中国以农立国,与西洋诸国以商立国固有不同,中国的海洋海权观念固然落后于西欧,至于相互了解,西洋诸国对中国的了解并不比中国对西欧的了解深刻。而西洋诸国的通商也并非是正常的平等的贸易,考诸16、17世纪西洋诸国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在全球商业贸易网络的拓展史,就是一部在地理大发现的进程中对所到之处的国家和民族进行武装殖民和以强凌弱的海盗式贸易的历史,就是当地国家与民族国土沦陷、人民备受欺诈与奴役的历史。西洋诸国早期的崛起与富足不仅植根于知识与技术的积累,也植根于对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残暴征服与掠夺。从明朝中后期起,其在东南亚的诸多属国如吕宋、满刺加等在政治、商贸等方面已经陆续受到西洋诸国不同程度的挟制或控制,中国在与西洋诸国进行有限贸易的过程中对此已有所了解,因而对其已无法完全信任,不能、也不再完全尽到封贡体系中一个天朝上国应有的保护与救援责任,也就可以理解了,明朝对其封贡体系成员的监控与防范越到后来越加强化也就不足为怪了。在地缘军事关系的不断演化过程中,这种针对封贡体系自身的防控政策在维护大明封贡秩序、保障大明国土安全方面功不可没。
三、结语
大量史实表明,终明一代,其封贡体系带有极其浓厚的自我本位色彩与浓重的服务于本朝本土防卫的印记。所谓“交邻有道,实为保土之方”,无疑应从这种角度加以理解和诠释。细观其交邻之道,不过是务实性军事外交的代名词。加之明军仅在明初70年堪称强盛,“天下卫所官军原额二百七十余万”,[78]“自宣德年间以后,老将宿兵消亡过半,武备渐不如初。”[79]因此,自仁、宣时期开始,明朝的对外政策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收缩态势,其封贡防卫体系的战略重点也重新转向陆上毗邻属国和缘边属部,其中蒙古、日本、缅甸、女真四者于明朝的军力、国力耗费甚大,特别是蒙古,自洪武初至于万历中,“北虏”的地缘军事威胁既久且大:“有明一代之边防,东起榆林西迄宁夏,首尾万余里,建碉设堡,转饷征兵,天下骚动二百余载,君臣上下,孜孜然,矻矻然,日不暇给者,皆所以防蒙古也。”[80]北方蒙古的长期侵扰是造成明朝前中期国力、军力衰弱的首要因素。如果没有蒙古方面的长期压力,明代中后期封贡体系诸诉求的退行性选择、封贡防卫的圈层性收缩现象可能都不会出现。但即便如此,明朝君臣仍然勉力在封贡体系的军事外交中纵横捭阖,在明朝现实利益至上的理念之下,所谓和平外交、存祀主义、中立主义、干涉主义皆各有其所、各尽其用,有明一代君臣于封贡体系之地缘军事价值的利用虽不及汉唐,亦颇有可采。至明中后期,明朝封贡防卫体系的圈层性收缩与封贡多元诉求的退行性选择日益明显,但仍不脱维护本土安全之要旨。[81]
至此,我们很容易发现学界从前以“字小”、“事大”来概括天朝上国与属国、属部的关系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那只代表了中原王朝统治者的一种理想和愿望。揆诸先秦时期的历史,属国对上国“奉正朔,求册封,定名分”尚且难以真正实现并长期维系,遑论那种单纯依靠信义和道德来维系的字小事大乎?斯事难矣!先秦时期地域不广、种族不多、国家不大,字小事大尚且如此,遑论秦汉以迄明清历朝实行之难哉!广而言之,历代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的构建亦皆与其维护国家利益、加强陆基国土防御的初衷唇齿相关、两面一体。而中原王朝的综合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的强弱变化在其封贡体系建构、维系、调适中都无可置疑地发挥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明初以来的厉行海禁以及嘉靖末年开始的开放杭州、澳门等少数口岸地区的海上贸易,并严控赴吕宋等东南亚属国从事私人海上贸易的闽广商民的有限开放政策,是明朝的封贡体系面对海上政治、军事形势变化的一种反应,那么自秦汉以后迄于清朝两千余年中原王朝封贡体系中的监控与防范,以及某些时期力图构建或者成功构建的军事联盟,则是中原王朝在如此漫长的时期内基于当时陆上、海上的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所作出的本能反应。封贡体系的内外形势与力量对比决定了封贡体系的时代特征与极强的政治、军事色彩。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更透彻地理解历代中原王朝封贡体系内部的复杂运作与演变,才能更清晰地描绘出华夷关系分合聚散的历史经纬。
注释:
①庄国土不赞成滨下武志将朝贡制度演绎为东亚国际关系的主要模式,对朝贡制度的实施范围和有效性一直存疑,并以东南亚作为例证,他认为明清时期对东南亚国家的海外政策基本上是自我封闭毫不作为,中国与相关国家不存在真正的宗藩主从关系,将东南亚国家纳入朝贡制度“基本上是中国统治者以及历代史官、文人的一厢情愿”。见庄国土:《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陈尚胜对庄说持反对意见,指出清朝所构建的封贡体系“具有谋求自身安全和边疆稳定的显著用意”,清朝在处理涉外事务时实际上已经摒弃了在海外世界扮演“天下共主”的理想,而专注于自身的边疆稳定和安全,使她的封贡体系具有周邻性和边疆防御体系的突出特征。这是国内学者对古代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相关研究的重要推进,但他对明朝封贡体系的重心定位则估计不足,认为明朝与清朝存在很大的不同,特别是明太祖、明成祖的封贡政策中长期抱有在海外世界扮演“天下共主”的理想。见陈尚胜:《试论清朝前期封贡体系的基本特征》,《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
②严格来讲,《坤舆万国全图》是李之藻对利玛窦1584年所绘《山海舆地图》的放大、重印。参见杨泽忠:《利玛窦与非欧几何在中国的传播》,《史学月刊》2004年第7期。
标签:明朝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嘉靖帝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历史论文; 清朝论文; 有道论文; 赵全论文; 唐朝论文; 白莲教论文; 专门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