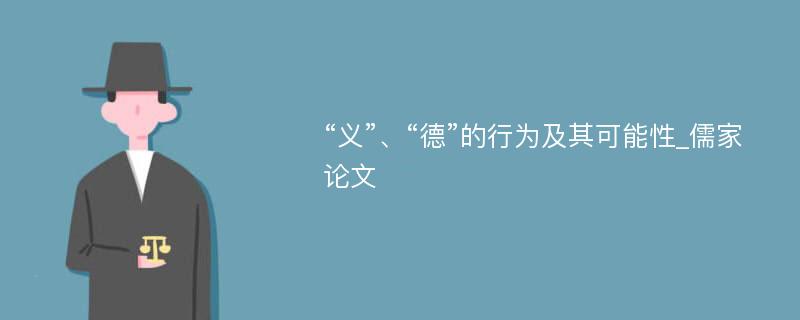
“义”之作为“道德辨别力”及其可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辨别力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115(2012)02-0025-06
“义”是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而前贤多注重“仁”、“礼”之发微,对“义”却不够重视。同时,与仁、礼相比,在先秦的典籍中,儒家之“义”究竟何指颇为令人费解。有感于此,本文拟对“义”的含义及其由来进行初步的探讨,同时也对其作用机制及其终极指向作一大概的梳理。鄙陋之处,祈望诸方家批评指正。
一、“义”:儒家的“道德辨别力”
对于儒家之“义”,人们往往将其视为外在的道德标准,如刘殿爵先生认为:“‘义’基本上是一个行动的特征,它在主体那里的运用是派生性的。……行动的正当性依赖于它们与环境具有道德适宜性,而与行为主体的品质或动机无关。”[1](pxxiii)但“义”如果是派生性的行为的品质,那么一个人对正当行为的践行并不必然保证他是个有“义”之人。据此郝大维先生和安乐哲先生表达了他们的不同看法,认为“义”是行为主体的品质:“说一个遵照‘义’的标准行事而与环境相合的人就是道德的人,这是相当误导的,没有独立于‘语境中的人’而存在的‘义’的原理。”[2](P122)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质”者有质干、本之意,“义”显然指人的内在德性,与上述的伦理标准之意截然不同。余纪元先生则极力寻求一种恰当的理解以容纳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及其各自的文本依据,他把“义”视为两个方面,即“适宜去做的”和“选择和实施适当之物的理智品格”,这两者是有内在联系的:“在前一种含义那里,‘义’是一种伦理行为的品质(让我们称之为‘外在之“义”’)。在后一种含义那里,它是行为者的理智品格(让我们称之为‘内在之“义”’)。这两个方面紧密相关,而且是互不可分的。正是由于行为者具有一种‘义’的理智能力,他才能得以在行动中达致‘义’。”[3](P250-251)
诚然,“义”既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伦理标准、规范或原则,也可以被理解为人的一种理性能力,不过后者更为根本,本文着重探讨后者并将“义”定义为“道德辨别力”。“道德辨别力”也可称为“价值判断力”,而以“辨别力”指称之则源自儒家自有的用词。荀子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即以“义”作为人之为人的规定性。而在《非相》篇中,荀子又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于此可见,“义”即等同于“辨”。竹帛《五行》曰:“不直不肆,不肆不果,不果不简,不简不行,不行不义。”可见由“直”层层外推可达到“义”,“义”以“直”为基础。而“中心辩(辨)然而正行之,直也”(《五行》),“直”指内心的判断及其行为。马王堆帛书《五行》之“说”解释道:“有天下美饮食于此,吁嗟而予之,中心弗迷也。恶吁嗟而不受吁嗟,正行之,直。”“不受吁嗟者,义之理也。”“义”显然指价值判断,但它要以“中心辨然”为基础,即要求达于明辨而中心弗迷。《中庸》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义”指的就是这种明辨的思想境界。通过博学、审问、慎思而达于明辨,到此一阶段,对人而言,只要笃行之即可。因而“义”指人的思想达到诚明通透、至辨无妄时所展现出来的人性能力。
“道德辨别力”具有如下三个意涵:首先,“义”并不是伦理中立的。一种中立的理性能力既可为善也可为恶,比如“勇”,而一个有“义”之人不仅能作出判断而且总是站在正确的一面。《荀子·议兵》曰:“义者循理。”“循理”使得“义”总是公正的、正当的。其次,“义”要求在同样是好的或者善的价值观之间进行选择。没有一种预先确立的价值体系能够解决所有复杂的道德问题,尤其是当所有的价值观就其自身而言都是善的,我们必须在其中作出选择。最后,“义”要求对情境的适宜性。“循理而行宜”要求行为不仅正当,还必须合宜。正当或公正是基本诉求,合宜则是本然归宿。正当的行为不一定合宜,合宜的行为则必然要求正当,故而《中庸》与郭店楚简《语丛三》直接以“宜”来定义“义”:“义,宜也。”总而言之,“道德辨别力”所做的乃是既正确又合宜的价值判断。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仁义的“内外”问题。《孟子·告子上》中孟子与告子对此有所争论。孟子认为仁义皆内,而告子认为仁内义外。告子以“长”与“白”为例,说明其“外”字之含义:“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我“长之”、“白之”乃因对方长、白而然,即取决于外在客观之意。而孟子反诘曰:“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在孟子看来,“长马之长”只涉及事实描述,而“长人之长”则关乎价值判断,而且这种判断乃自我主体所作。李大齐先生认为:“且推原孟子之所以谓义为内,因为他所认为义的那些判断,是价值性的,不是事实性的。价值的有无高下,其决定权却操在主观之手,不操在客观之手。”[5](P56)这正是孟子与告子争论之焦点所在,而站在局外看,实际上这是一事的两面。缺乏外在价值体系的参照,价值判断无以生成;而无心性主体的参与,又哪来羞恶的价值判断?
郭店楚简《五行》曰:“不变不悦,不悦不戚,不戚不亲,不亲不爱,不爱不仁。”“不直不肆,不肆不果,不果不简,不简不行,不行不义。”“不远不敬,不敬不严,不严不尊,不尊不恭,不恭无礼。”“变”通“恋”,帛书本即作“恋”,乃一种顾念不舍之情。“变”者“颜色容貌温,变也,以其中心与人交悦也”,“远”者“以其外心与人交”,“直”者“中心辩(辨)然而正行之”。可见,“直”介于“中心”与“外心”之间,“义”介于“仁”与“礼”之间。“仁”为人心之本然发动,“礼”为外在价值规范,“义”则兼涉上述二者,既指“内”又指“外”,是内外的统一体。
二、“义”之作为“道德辨别力”如何可能
在各种复杂的现实语境中,每个人都需要做出适合自己的判断,但如果每个人的价值判断都截然不同,社会将出现极大的混乱,因而在各种不同的“义”背后必须要有一个终极的理念或根本精神,此即“道”或“理”。贾谊《新书·道德说》曰:“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义者,德之理也。”“义”为“德之理”,而“道者,德之本”,则“义”以“道”为本。“道”和“理”有天道、天理之意,《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曰:“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但同时“道”和“理”也有人道、社会公理之意,此种“道”和“理”是历史生成的人类经验的凝聚,它是“义”的直接来源。《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曰:“《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诗、书、礼、易、乐产生于人的需要,是人类历史经验的凝结,当它经过一代代人的增删损益,其中所蕴涵的精义显然超越了个体的经验世界,已由经验而先验,在此称之为“历史理性”。就当下而言,个体需从“历史理性”中体悟其中内蕴之精义进而塑造自我的人性能力,使“历史理性”复由先验而经验,实现个体经验与“历史理性”的融汇,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曰:“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顺之,体其义而节文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者。”
史华兹先生认为:“对孔子而言,知识肯定始于由大量的殊相(particulars)(然而,殊相中也包括诸如一首诗的意义之类的东西)所组成的积累性的经验性的知识。然后,还必须包括把这些殊相关联起来的能力,其步骤是:首先与人们自身的经验,最终还必须与某种将思想过程结合到一起的‘统一性’关联起来。”[4](P90)传统典籍背后的精神,即所谓的“义之府”与“德之则”便是史氏所谓的“统一性”,后人在体会并运用这一先世流传下来意义之流的同时也产生了创造性的新的意义,从而使得传统的意义与时代化,生生不息。其中,个体与历史之“义”结合起来的能力至关重要。孔子不曾明言该如何产生这种能力,但《论语》通篇都在暗示并引导这种能力的产生,宋人认为“仁字难说,论语一部只是说与门弟子求仁之方”,“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仁之方也”。[5](卷二十四)孟子认为“义”为“心之所同然者”,即每个人都具有此种人性能力。顾立雅先生说:“那么,我们能做出决定说,任何人都应当具有和其他人一样的判断正义与真理的能力吗?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的。”[6](P165)每个人生来都是平等的,都具有培养成为君子的潜能,但是要成己成人显然还需要后天的不断努力。在此意义上,传统典籍与文化传统是不可或缺的。“义”的内在性指它需通过外在的知识逐渐内化并规制人心,由表而沉潜及里。具体地说,教和学是“生德于中”的必要条件,而教和学的内容则是各种传统文化,当然,最直接的一个资源就是“礼”。子曰:“不知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可见“礼”对人类而言是一个具有基础性的文化源流。当孔子自述“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时,他所学的主要内容必定是“礼”。学礼的目的是要有所“立”,即建立自我的主体性和主体意识,形成个体之“义”,这是“成人”的必然过程。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学、适道、立、权,层层精进渐至成人,其中的关键在于“立”与“权”。“立”者处经,“权”者反经而不离经。从理论上看,道德规范作为普遍律令,具有超越具体情境的一面,但以之应对特殊境遇则略显不足。在西方,从柏拉图到康德的理念伦理学主要注重道德律令的普遍性,对具体道德情境的分析则相对薄弱,直到现代的实用主义、存在主义以及境遇伦理学,才开始重视具体道德境遇的分析。而孔子认为“立”的更高层次是“权”,不仅重视普遍伦理,对特殊情境下的伦理应用也相当关注。孟子对此有明确的阐述:“执中而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荀子也认为应以“义”宗原应变,曲得其宜:“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以义屈信变应故也。”(《荀子·不苟》)
“义”作为伦理规范具有定然性和不变性,但实践领域的“行义”却无适无莫,并无规章可循,而需因时、因事、因人制宜。日人广常人世认为:“义又是调和礼的形式和精神(恭敬)的原理。……但孟子于尊重礼之余,对其形式本身加以反省,强调义为使行为切当的原理。[7](P83-84)“权”、“中”、“时”确实与“义”相关,不过严格地说,这些都是“义”即“道德辨别力”的实践表现。一个行为只有当它作为人的“理性能力”之表现时,才必然发于并作用于内心。如董仲舒认为“义”是用来自我规范的,他说:“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春秋繁露·仁义法》)在儒家,“循理行宜”具有非常之意义,它是“成人”的根据所在,荀子谓“义”为“德操”:“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荀子·学而》)
三、情理合一:“道德辨别力”的内在结构
《性自命出》曰:“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内之。”“始者”、“终者”之主词承上句而为“道”,此“道”指“人道”:“道四术,唯人道为可道也。”裘锡圭先生注曰:“‘内’似可读为‘入’。‘入之’意为‘使之入’。”[8](P182)基于此,“知情者能出之”意为“知情者能使之出”,“之”指“情”;“知义者能人之”意为“知义者能使之人”,“之”指“义”,只有知“义”才能使之深入人心。“始者近情”谓人道始发于人情,“情”之适度发抒乃“道之始”;此“情”之发展目标则为“义”,达至“义”则为“道之终”。
郭店楚简《语丛一》曰:“仁生于人,义生于道。或生于内,或生于外。”“生于外”意为通过外在规范而影响于内在的人心、人性,其重心不在外而在内。《性自命出》曰:“凡道,心术为主。”又曰:“虽有性,心弗取不出。”因而“义”自外入就是要习得“心术”,最终目的则是要影响于人性。“义”“自外入”、“生于外”的品格决定了学习外在规范的重要性,“学”者学习如何“用心”也。《性自命出》曰:“凡心有志,无举不可。……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学习的内容为“礼”或“理”,其载体则为诗书礼乐。《性自命出》曰:“道四术,唯人道为可道也。其三术者,道之而已。……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关于道之“四术”,李零先生以为指“心术”和下文的“诗”、“书”、“礼乐”三术。[9](P70)陈霖庆先生也认为:“从文义来说,‘四术’应包含‘人道’,其余的‘三术’并没有明言……思考‘人道’以外的‘三术’,很可能就是‘《诗》、《书》、《礼乐》’,这四者皆因人的需要而产生,而后再回头以它来教导人民,使人民心中生德。”[10](P167)道以心术为主,而人道为唯一可道之道,其他三术则是用来引导心术的生成,亦即引导人们如何去规制人性。以诗书礼乐为教,其目的为内在地生成相应的理性能力——“心术”亦即“义”。《性自命出》明确地说:“虽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贵。”只有具备此种理性能力方为儒家所贵,孔子也认为君子应“义以为质”。
毋庸多言,郭店楚简中“心”与“情”、“性”的关系遵照的是“心统性情”模式,所谓的“心术”是指“心”通过外在的“理”规制“情”从而形成“合情合理”的作用机制,此即“义”——它意味着“人道”主体的建立。“情”兼有情实与情感之意,在郭店楚简中更多的则是指情感。情感首先要真诚,《性自命出》曰:“凡学者求其心为难,……求其心有伪也,弗得之矣。人之不能伪,可知也。”“信”与“伪”相对,乃指情感之真诚,当孔子说“人之生也直”、“质直”时也是此意。然而真诚的情感只是人道之始基而非终极依归,即便是真诚的情感亦须受到规制,否则其流弊也大:“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论语·阳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谓真诚的情感须受“理”之约束并生成“义”,孔子谓“质直而好义”(《论语·颜渊》),《礼记·乐记》亦称“情见而义立”。丁原植先生认为:“‘始者近情,终者近义’,指人道的肇始必当切近于‘情’,而人道的终极必当归趋于‘义’,‘近’字的作用,不但强调这种必然性,也说明以‘情’、‘义’作为人道的准则。……人道肇始于人情,终极于义立,当是孔门思想发展的主导观念之意。这也是儒家人文价值规划的根基。”[11](P52)当“义”通过心的作用而对“情”予以规范,人逐渐扬弃其本然性与自在性而走向自由的存在形态。蔡仁厚先生以“义命分立”来表达此一命题,他说:“人一方面要承认‘命’的存在与限制,此一面是‘被决定者’,属于事象系列中的必然命题。而另一方面则尤需明‘义’而自我做主,此一面是‘自决定者’,代表自觉、自由式主宰性之肯定,属于道德世界中的价值创造之问题。人生之意义,不在‘命’一面,而在‘义’一面,其理甚明。”[12](P16)
“义”是情感与理性的交融。“性”指人的自然本质,“情”指人的始源展现,“义”指人道之建立,亦即价值主体之生成及其完善。因“义”之成,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做出合情合理的判断进而指导其具体实践。《论语·阳货》载:“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三年之丧”大概是古制,宰我却认为守丧一年就可以了。孔子尽管认为宰我“不仁”,却也把标准明确地定在“心安”上,根据己心之所“安”,每个人都可以在具体情境中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作为人之为人的规定性,“义”是与人同在的,它既不同于抽象的逻辑或先验形式,也有别于单纯的意识或本然的心理功能,而是理性规范对意志、情感的渗透与制约。历史形态中的“义”可以寄寓在典籍甚至制度中,但对实存的人而言,“义”是后天生成的并且对人来说是可控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理性对情感的绝对宰制,而是情感与理性的交融,《论语集释》引陆陇其《四书困勉录》曰:“情与理必相准。天理内之人情,乃是真人情;人情内之天理,乃是真天理。”[13](P926)
四、审美和谐:道德辨别力的终极指向
《论语·微子》载:“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人的做法大相径庭,而孔子皆许之为“仁”,可见孔子并不认为必须遵行某种固定的价值取向。私意、期必、执滞与私己皆为孔子所不取:“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在孔子本身,其行事既不严格遵循礼,亦不执着于某种“仁”。《论语·微子》相对于伯夷、叔齐、柳下惠、少连、虞仲、夷逸诸逸民,孔子自言“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他认为自己的行事具有相当之灵活性,较之上述诸者要高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孔子一味与时依违、与世浮沉,而有其根本精神——“义”在,他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皇侃“疏”引范甯云:“适莫,犹厚薄也。比,亲也。”无适无莫犹无可无不可,即既不专执于某种行为模式,也并不绝对地排斥某种模式;义之与比即根据具体情境选择适当的行为方式。孟子对孔子推崇备至,认为“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孟子·离娄上》)与势俱化是孔子优于伯夷、伊尹、柳下惠辈之处:“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孔子为“圣之时者”,其行自能合于“大人”之迹:“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上》)
“义”定义为“宜”,带有适宜、合宜之意,这种“宜”不仅指人情、人心与“理”之宜,还指自我与当下语境的切合,荀子曰:“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义之情也。”(《荀子·强国》)汉儒公孙弘认为“智”为“术之原也”,而“义”不仅要“明是非”,还要“立可否”(《汉书·公孙弘传》)。所谓“立可否”就是寻求一条适宜于语境的中适之道,是心性主体对历史语境和当前语境的判断与选择,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理》释孟子以理、义为“心之所同然者”曰:“举理,以见心能区分;举义,以见心之能裁断。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则,名曰理;如斯而宜,名曰义。”总而言之,“义”是自我本心对天理、历史理性及当前语境的综合考虑并臻至通融为一、谐和一致。对于其终极指向,本文称之为“审美境界”,在儒家则常以“乐”来表达。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诗言志,因诗可以激发心智情感;礼为行为之准则与依据,无礼无以立身;乐则使人性得以完成。郭店楚简《语丛一》曰:“礼生于庄,乐生于度。”音乐是节奏与度的理想结合与展现形式,完美的音乐对此必然会有所体现。故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叹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李泽厚先生认为:“‘度’是‘美’的基石,还不是‘美’本身。美是‘度’的自由运用,是人性能力的充分显现。”[14](P41)音乐承载着这种审美形式,所以以音乐启迪、塑造人性才有事半功倍之效,楚简《性自命出》曰:“凡学者求其心为难,从其所为,近得之矣,不如以乐之速也。”“成于乐”不仅指用音乐来帮助型塑人性,也指当人达至与音乐一般的审美境界时就意味着人性的完成,意味着人们能在伦理实践中俯仰进退无不一一合于至道。也正因为“义”以这种审美境界为旨归,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才要“义之与比”、“惟义所在”。
从根本上说,乐对审美境界的体现源自其对天道的体会与契合,《荀子·乐论》曰:“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荀子·解蔽》又云:“仁者之思也恭,圣人之思也乐,此治心之道也。”杨《注》:“思,虑也。乐,谓性与天道无所不适。”而“义”因为“循理而行宜”,故而也实现了对天道、对审美境界的映照。然而如何达至此种境界却非知性所可授受,它需要个体用心体会。《论语·阳货》载:“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道无言,徒以四时行、百物生示人而已;至道也非言语可及,故而孔子欲效法天道之无言,但令门弟子观之言动即可。诸弟子以为孔子意有所隐,孔子申辩道:“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可见子非不欲言,只是此道着实难说,故而颜回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卓立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以颜回之资尚力有不逮,可见这就是孔子之教的奥义所在。
而一旦达至审美境界,则能进退有序、动静从容,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学”者自洒扫进退至治国平天下,不一而足,但非人人皆有志于“道”;即便有志于“道”,未能建立自我的主体意识,亦不可行;主体意识确立之后,尚需揣度权衡、因应时势,从而超越任何具体的形限而从容中道。楚简《五行》认为“闻道而乐,有德者也”、“不乐无德”,帛书《五行》之“说”曰:“闻道而乐,有德者也。道也者天道也。言好德者之闻君子道而以夫五也为一也,故能乐。乐也者和。和者,德也。”“乐者言其流体也,机然忘寒(塞)也。忘寒(塞),德之至也。”“流”者如《礼记·乐记》之“流”:“乐胜则流,礼胜则离”、“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即变动不居、与势俱化之意。“乐”者“和”,即仁义礼智圣五行在人内心的圆融谐和,达于此种境界乃能“有德”,达不到的则是“无德”。“其流体也”是对“乐”(亦即“和”)的性质的定义,言其以仁义礼智圣五者和合为一从而超越任何具体的德性限制而与天地和同、生生不息之意。这一过程又称为“一”,《五行》曰:“‘淑人君子,其仪一也。’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君子慎其独也。”只有能为“一”,然后方得为君子。如何谓之“一”?据帛书“说”云:“能为一者,言能以多[为一]。以多为一也者,言能以[夫]五为一也。君子慎其独。慎其独也者,言舍夫五而慎其心之谓[也]。[独]然后一,一也者,夫五夫为[一]心也,然后德之一也,乃德已。德犹天也,天犹德也。”“以多为一”是使仁义礼智圣五行和而为一,“一”者“和”,“和”者“德”、天道也。该章最后总结“慎独”曰:“言至内之不在外也。是之谓独。独也者,舍体也。”达至“一”而能“乐”,自然“忘(无)塞”,从而为“德之至”。当“心”实现了对五行的融和与超越时,五行俱可舍而弃之,独此“心”可矣。依此而行则无往而不胜,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因此“德”才具有超越个人形体和任何具体限制之意味,楚简《五行》曰:“君子之为善也,有与始,有与终。君子之为德也,有与始,无与终也。”帛书“说”曰:“[君]子之为善也,有与始,有与终,言与其体始,与其体终也。君子之为德也,有与始,无与终。有与始者,言与其体始。无与终者,言舍其体而独其心也。”池田知久先生认为,“它是这样的哲学,不是只到自己的‘心’支配身体诸器官‘体’而已,而是有从人当中拂拭或排斥身体的物质的性质,通过解放来自‘体’的束缚,升华到一种世界精神或绝对理性,通过这些以获得人的真正的自主性。这是歌颂其主体性的哲学。”[15](P121)“体”有形体之意,但帛书《五行》中的“体”又指具体的德性规范。池田知久先生所谓的精神或理性固然实现了心对体的超越,更深层次上则体现了“和”对具体德性之限制的超越,而这才是孔子“成人”之道的最终理论归宿。
标签:儒家论文; 孔子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孟子·尽心上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论语·子罕论文; 君子慎独论文; 论语论文; 孟子论文; 人性论文; 国学论文; 荀子论文; 心术论文; 五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