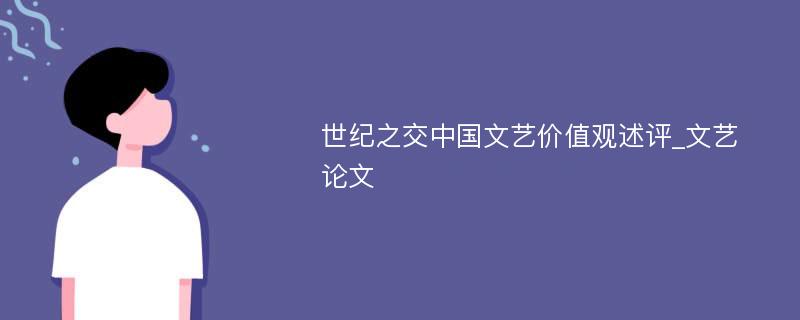
世纪之交中国文艺价值观的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中国论文,价值观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近几年中国的文艺理论讨论中,由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反感而引起了对二元对立思想方法的批判。的确,在一个阶段里,有人曲解了辩证法的矛盾对立学说,把矛盾对立双方绝对化的“非此即彼”,把人简单地分为革命和反革命,把文学史简单地归结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把作品简单地看作不是“香花”就是“毒草”,把理论看作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的等。在文艺界,从创作到理论都批“中间人物论”。这些观点曾经给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和文艺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对这种观点进行批判是完全应该的。恩格斯说过:“‘非此即彼’是愈来愈不够了”。“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35页)这一真正的辩证法思想说明了批判简单两点论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然而,我们发现,有人在批判这种机械的形而上学观点的同时,在回顾中国近百年的文论史时,却又重复了简单机械论的错误,把中国的文论表述分为“革命叙述”和“审美叙述”,认为前者始于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思维模式是从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去思考思想文化革命,再思考文学艺术革命。由“文学革命”而至于“革命文学”,并成为五四以来中国左翼文论的元叙述,什么“进步的”、“人民的”、“劳苦大众的”、“无产阶级的”,都由此而生。后者始于王国维,他受康德和叔本华的影响,推崇纯文学具有“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批评政治功利倾向,强调文学本质上是审美的、独立的、无外在目的、有自身规律。我以为,这种从总体上所作的概括,即使稍有偏颇,也不失为一家之言。问题在于,他们在作出这种概括之后,又认为这两种文论叙述是“水火不容”的:“审美文论”强调文艺自由,“革命文论”限制文艺自由,并得出结论:“九十年代前的中国现代文论史就是一部限制与反限制的历史”。(余虹《对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叙述的反思》)这种概括性的回顾等于否定了五四以来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否定了文艺冠以“进步的”、“人民的”、“劳苦大众的”、“无产阶级的”种种提法,而且不承认两种文论叙述的互补性和互通性。这显然是缺乏科学性的。
“革命”和“审美”都与文艺价值观有密切关系。我们不能不为之一辩。
价值是客观事物对人类的有用性,它以人为主体。谈论价值就不能离开人,不同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单就中国20世纪的文艺价值观而言,就不能不顾及本世纪中国人的处境,即此时的中国历史。因为任何文学艺术都是历史的产物,离开一定的历史背景去谈论文学艺术就无所依据。
中国是在义和团运动反抗帝国主义的呐喊声中和八国联军对中国人民的屠杀中进入20世纪的。当时的中国人民正处在深重的灾难中,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企图正在变为现实,民族存亡危在旦夕。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忧心,爱国的知识分子都在向西方寻求救国的道理。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实业救国论、学术救国论、文艺救国论以及中西学术体用之争,都未能改变中国的面貌。由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中国人民不得不选择了新的革命道路。先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以后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成了新中国。
应该说,在上个世纪之末,面对危亡的国家形势,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对国家前途之关心是一致的。年轻的、初出家门的王国维也曾在改良派报纸《时务报》当过书记、校对,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对时局十分关心,主张学习西方以图存。1898年3月1日在给许同蔺的信中就敏锐地看到:“各国兵舰云集于太平洋,其意实为叵测”。对于传言说“二年后日本不准再译西书”一说表示怀疑:“此事恐未必确”,怕的是有人以此为据拒绝学习西方,指出:“若禁中国译西书,则生命已绝,将万世为奴矣。”(《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3页)一片爱国主义拳拳之心,溢于言表。在此情形下,对文学的看法也不会有大的不同。后来王国维在罗振玉的影响下成为封建遗老,王、梁二人的政治观点开始相左,对文学的看法也有了区别。作为改良主义政治家的梁启超,着重从政治的角度去看文学;成了封建遗老的王国维则更重于学术,接受了康德、叔本华的哲学、美学思想,鼓吹起了非功利主义的文学主张。我这样说,决非贬低王国维的文艺思想,王国维的文艺理论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过去说“他提出的距离美学、超功利主义、文艺起源于游戏等,都反映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与文艺思想”(《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第885页),抹煞了其中的真理因素,是有失公允的。但把它提到至高无上的高度,认为只有这种说法才正确,就又有失偏颇。
实事求是地说,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确存在着革命文论和审美文论的区别。实际上,包括中国古代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文艺理论也都存在革命(或称功利主义)叙述和审美叙述的差异,不独近代中国。但并非如一些论者所说,审美文论就是绝对的真理,革命文论就是绝对的谬误,而是各有其是非。而且双方也都不是那么纯粹,革命文论也讲审美,审美文论也讲思想内容,即也涉及革命。梁启超鼓吹革命文论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大文中,把小说支配人道之力归纳为“熏”、“浸”、“刺”、“提”四字就是从审美的、艺术的角度谈问题的。他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他看到:“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而此蠢蠢躯壳,其所能触能受之境界,又顽狭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以其直接以触以受以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识想,不独利根众生有之,即钝根众生亦有焉。”“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焉不察者矣;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赫,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谓:夫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为甚。”这两段关于小说作用的论述,难道不是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从审美的观点看问题的吗?尽管如此,梁启超仍然是从政治作用的立场立论的。说他对文论的叙述是革命的叙述也符合实际。这就说明绝对的、纯粹的革命文论是根本不存在的。纯粹了,就与文学无缘了。
王国维对文论的审美叙述也是非纯粹的。他的非功利主义的美学观来自康德,而康德的非功利主义美学观本身就不纯粹。康德把美分为“自由的美”和“依存的美”:“前者不以对象究竟是什么的概念为前提,后者却以这种概念以及相应的对象的完善为前提;前者是事物本身固有的美,后者却依存于一个概念(有条件的美),就属于受某一特殊目的概念制约的那种对象。”(《西方美学史》(下)第17-18页)按照这个标准,只有一部分自然美是纯粹的自由美,而大部分自然美和艺术美都属于依存美,即依附于一定的内容意义和目的。可见,康德并没有把问题简单化。同样的,王国维也没有把问题简单化。他说文学的审美原质有二:“曰景,曰情”。这个景不仅是自然之景,还有“人生之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于是,文学和生活,和科学、历史就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在科学、史学、文学的三大类知识中:“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法理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性之效者,谓之文学。”只要文学兼有事理及其变迁之迹,就无法脱离特定的目的。王氏还把中国春秋以前的道德政治思想分为帝王派和非帝王派。中国的文学就是这两种思想的表现。受帝王派思想影响的北方文学,是“以描写人生为事”为主的现实派;受非帝王派思想影响的南方文学,是以写理想为主的浪漫文学派。“北方派的理想在改造旧社会,南方派之理想在创造新社会。”当理想不能实现时,就于文学中予以变相地表现。然北方人有感情而缺乏想象,南方人有想象而缺乏深邃之感情,只有“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的屈原,才将“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从而成就了一番伟业。把文学当做政治理想不能实现时的精神寄托,这本身就是目的。可见,王国维的美学观和文艺观也是不纯粹的、也有一定的功利色彩。
本世纪的两种文论叙述自梁、王始,大体也符合事实,此后确实有两种倾向贯彻在整个世纪文论叙述的始终。坚持革命叙述(或称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的理论家,除梁氏之外的所有改良派人物,几乎都是如此。他们之后又有辛亥革命时期的章炳麟,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李大钊等,此后还有鲁讯、郭沫若,而其集大成者乃是毛泽东。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文艺功利性的叙述可谓达到了高峰;坚持审美叙述的文论家,和王氏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写《“小说林”发刊词》的黄人(摩西),观点近似的有鸳鸯蝴蝶派诸君,之后又有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直到八十年代以后又出现了新的高峰。
在中国现代文论史上,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论家和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以胡秋原为代表的自由人、以苏汶为代表的第三种人、以林语堂为代表的闲适派的斗争了。这场斗争的实质看似以文艺的性质为中心,实际上是围绕着文艺价值展开的。斗争的背景是国内的军阀混战、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围剿、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步步进逼。斗争的焦点是文艺有无阶级性,是否为阶级斗争服务。梁实秋是主张人性论的理论家,他在《文学与革命》中所要求的是,文艺要“忠于人性;至于与当时的时代潮流发生怎样的关系,是受时代的影响,还是影响到时代,是与革命理论结合,还是为传统思想所拘束,满不相干,对于文学的价值不发生关系。”文学家的心目中,“不含有为某一阶级谋利益的成见”。“文学一概都是以人性为本,绝无阶级的区别。”因此,“革命的文学这个名词根本的就不能成立。”但是,他也承认,“在革命的时期当中,文学是很容易的沾染一种特别的色彩。”“伟大的文学家足以启发革命运动”。他所要争的是要给“描写失恋的痛苦,春花秋月的感慨”一席地位。实事求是地说,他所反对的是要求一切作家都去创作革命的文学,这一主张有其合理的一面。在正常的情况下,甚至是相当正确的。但在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条件下,这一要求就未必妥当了。胡秋原的《勿侵略文艺》声称“我是一个自由人”,反对将“政见与文艺结婚”,反对“只准某种艺术存在而排斥其他艺术”,认为“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在今天看来,其见解也有其可取之处。但他也承认,“中国既有普罗之存在,成长与斗争,自必然有普罗文学的存在,成长与斗争。”“阶级斗争尖锐的时代,急进的社会主义者与极端反动主义者都要求功利的艺术。这只要看苏俄的无产者文学与意大利棒喝主义文学就可以明白了。”(《阿狗文艺论》)把无产阶级文艺与法西斯文艺相提并论,其立场也就不言自明了。林语堂先生创办的《人间世》,提倡“小品文笔调”,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这在文艺大家族中也应有一席地位,但是,置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民族危亡于不顾,而热衷于提倡闲适的消遣,其文学的独立固然是保持住了,但文艺家的民族责任就显得淡薄了。正是因为如此,鲁迅才起而反对。他竭力主张文艺的阶级性,文学家要听从无产阶级的将令,把文学家的使命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责任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也从而成为了“民
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毛泽东,肩负着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重任,总结了五四以来文艺运动的经验,结合根据地特别困难的形势,充分肯定、高度评价了鲁迅关于文艺阶级性的主张及其文艺价值观,称他是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的“民族解放的急先锋”,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并且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更加响亮地提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就是有名的“工具论”。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家,他对文艺的着眼点当然是政治的。但是,从理论到实践,他从来没有忽略过艺术形式和艺术性。他强调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强调文艺批评中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并重,强调“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就是最好的证明。毛泽东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并非句句是真理。中国文艺状况后来出现的失误,既有理论本身的偏颇,更有别人错误理解或曲解所致,还包括他自己对自己观点的违背。
建国以后,毛泽东的文艺观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对文论的革命叙述当然也就占据了统治地位。审美文论的声音显得相当微弱,文艺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但作为次要的声音,审美叙述也不时发出声响。这既表现在何其芳对于典型问题的研究上,也表现在胡风关于文艺思想的抗争上,还表现在文艺界一部分所谓的右倾分子对文艺问题的看法上。因此,文论并没有停止发展,文艺创作也没有停止前进。只是到了六十年代中期直至文化革命结束,林彪与“四人帮”把本来就有些片面性的无产阶级文艺价值观推上了极端,终于走向了谬误。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我们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当被禁锢的思想解放了的时候,当封闭着的国门被打开,国外鲜为人知的学术思想大量地涌入国内的时候,作为对极左文艺思潮的反动,一种曾经被掩盖着的倾向也就应运而生。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怀疑革命文论的合法性合理性的论调,很自然地就出现了,把审美当做唯一的价值功能的主张成为了时髦。只有在此时,文学的独立性才成为“一个反政治理想限制”的理论命题而使文论的革命叙述与审美叙述“水火不容”。
这种情况的出现,据说根源在“革命”。“八十年代人们放弃文艺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并不是因为什么新的学理的提出,而是因为别的因素的介入而使人们重新咀嚼那已被遗忘的学理并开始信赖它。这一因素就是‘革命’在‘人’身上留下的现实‘伤痕’。准确地说,是‘革命信仰’的危机使‘革命’本身的合法性受到了怀疑。”(《对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叙述的反思》)这里说的再清楚不过,他们捡起来的并不是什么新的学理,而是早就被人们遗忘了的老调重谈。他们所说的“革命”并非只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指的一切革命。这一点可以从另一个学术权威的言论中得到证实:“我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就是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词、褒词,而‘改良’则是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理性的眼光看中国——哲学家李泽厚谈访录》)弄了半天,中国20世纪的历史竟是一段走错了的历史,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不是领导了中国革命的孙中山、毛泽东,而是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按照这些人的想法,中国现在不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应是仍由宣统皇帝统治的满清帝国。然而历史总是爱开玩笑,它给了搞改良的康、梁一个失败的结局,溥仪皇帝不仅被赶出了龙庭,而且尽管曾过了一阵伪满洲国的皇帝瘾,但最后还是在新中国的监狱里接受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新人。而孙中山却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被几亿中国人尊称为“国父”;毛泽东不仅建立了新中国,而且还顶住了西方势力的封锁和压力,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虽然目前经济上仍然落后,但毕竟已成为世界上无论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是举足轻重的大国。假如不是被这些理论家说得一无是处的“革命”,我不知道这些理论家们能否在这里发表此等高论。
回顾到此就可以告一段落了。从这一回顾中能够给我们以什么样的启示呢?我觉得,至少有以下几点:
1.文艺是多维的,不是单面的,文艺价值观可以有多种出发点。文艺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构成也不宜简单化。过去说,文艺只有社会意识形态性,这就只看到了一面;后来又说,文艺只有审美性,这是只看到了另一面。胡乔木说:“文学艺术是一种社会艺术现象——说文学是意识形态,只是就一个方面,就文学艺术观点而言,不能说整个文学是意识形态。这里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回忆毛泽东》之二,载《大地》94年第2期)这是一个谨慎的相当科学的论断。复杂性就是多维性。在我看来,和文艺有关的因素,自外而内地看至少有:一是可见的物质材料。艺术是艺术家心灵的创造,但必须有物质载体来负载,不然,就不能成为客观存在的艺术品。不同的物质材料产生的效果不同。正如马克思所说,大理石的物质特性是不在雕刻之外的。这不仅表现为绘画、雕刻、舞蹈、戏曲、电影、文学等有不同媒介材料的区别,还表现为同一材料内的区别,如雕刻有石雕、玉雕、木雕,绘画有油画、水彩画、粉笔画,戏剧有话剧、歌剧、舞剧,电影有故事片、动画片、科幻片,文学有不同民族的语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东西是给我们审美满足的物质基础;二是外在的技巧手段。雕刻的不同刀法,绘画的不同笔法等等。技巧既有可资学习的成规,又有无法学习的创造。这是构成艺术形式的基本条件;这两条虽然也在发展变化,但总的说来,它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不存在阶级的差别而可以为各个阶级所世代继承,因此,它是构成艺术形式审美本质的组成部分。三是文艺作品中的生活质料。包括自然景物和社会关系,这是构成大部分作品故事构架的材料,也就是恩格斯说的意识到的历史内容。艺术的源泉在生活主要就表现在这里。作家必须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原因也在这里。四是作家的思想。包括事件自身所蕴涵的思想意义和作家对它作出的评价和判断,这又是作品深度和导向之所在。五是作家渗透在作品中的感情。这是作品审美本质的重要体现。文艺是情感的产物,有无情感是区别文艺和非文艺的分水岭。作品中所描写的一切都应该是被感情浸透了的,否则就没有打动人的力量。思想感情虽然也有生活的根据,但毕竟不是生活本身,而是生活的派生物。这三项是构成思想内容的要件,是艺术意义和价值的主要构成因素,也是构成艺术审美本质的又一部分。按说,后三项都属意识的范畴,这该是决定艺术意识形态性的决定因素了,但也非完全如此。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的心理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与无意识,而潜意识#
无意识就不是意识形态。所以说“不能说整个文学是意识形态”的论断是有道理的。这五个构成方面,就是艺术的五个维度。不同的维度决定着艺术的不同价值。看不到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正确地认识艺术问题。
2.文艺功能的价值取向因时代而异,战争年代和和平时代有着重大的区别。文艺中的多个维度是有机统一而不能解析的,当作品作为一个完整的客观存在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时,哪一种价值发挥得最好,是因人、因地、因时而异的。文艺的阶级性问题曾经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其实,从实际出发,问题并不难解决。历史上的大量事实说明,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不放弃对文艺的利用,而作家也都不同程度的属于某一阶级。同时也有大量的事实说明,文艺也表现无阶级性的共同人性。包括许多主张文艺阶级性的作家也有非阶级性的作品。因此,各执一端的作法是永远也达不成共识的。从总的倾向上看,在具有审美功能的前提下,占据文艺史主流的作品都是有意义、有生活内容、有阶级性的作品。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代,各阶级都要求功利的艺术,并非如胡秋原所说,只有在资产阶级颓废的时代,急进的社会主义与极端反动主义者才要求功利的艺术。事实上,上升的资产阶级也要求功利主义的艺术。这只要看看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的文艺状况也就清楚了。人的需要是分为层次的,只有基本的需要满足之后,更高级的需要才能产生。美和艺术享受的需要都是高级的需要。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刻,广大群众生存和安全的保障尚且没有保障,就像鲁迅所说,饥区的灾民是不去种兰花的,他们哪有欣赏美的雅兴!所以在民族危亡之时,不去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而去鼓吹鸳鸯蝴蝶、花前月下,至少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醉生梦死的。类似的事例历史上曾经有过,南宋王朝偏安一隅,却不思收复国土,只顾歌舞升平,诗人林升就在《西湖》诗中抨击说:“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难道这是我们希望的局面吗?但是在温饱和安全问题解决以后,美和艺术的需求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所以,和平时期的人们更多的要求纯艺术的享受。今天对艺术消遣功能需要的猛增,既有艺术观念转变的原因,也有社会安定和生活水平提高后提供的新的条件。用今天的观点去否定战争年代的文论,显然是不公正的。更何况,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人民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对于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精神风貌需要表现,对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热情需要鼓舞,对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不良现象需要揭发和鞭鞑,这是我国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规定了的。假如一味地消遣和享乐,就会堕入有些人指出的“消费主义”的泥淖。中国的经济还相当落后,有相当一部分群众还没有解决
温饱问题,可是,大款和暴发户们却在挥金如土,政府的腐败分子们却在用公款大吃大喝、挥霍浪费,沉醉在高档娱乐场所中。在此情况下,如果单纯强调文艺的审美和娱乐功能,只能是那些把“真实的实在”当做“个人当下即刻的感受和享受”者的理论,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毫不相干的。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不看现实而单纯追求文艺审美功能的理论家,最容易走进人民的敌对阵营。号称本世纪文论审美叙述的祖师爷王国维,不是在北伐军胜利进军的枪炮声中自沉于昆明湖了吗?大讲人性的梁实秋、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也都破口大骂共产党而成了文化领袖鲁迅的死对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一历史事实也十分值得人们深思。
3.由上述两个结论推出的第三个结论是:凡在历史上存在过较长时间、有相当影响的学术思想,大概都既有其合理之处,又有一定的局限。黑格尔那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名言,未必一无是处。过去我们老是把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轻易地冠以“资产阶级”的帽子予以全盘否定,使得文论的审美叙述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结果在建国以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拒绝接受国外美学、文艺学思想,造成了我国美学、文艺学的单一局面,直到本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才醒悟过来,匆忙地急起直追。结果,对眼花缭乱的国外学术思想,有的生吞活剥,有的望文生义,甚至用作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理论武器。这个教训我们不能忘记。但是,在为审美叙述平反的同时,又把革命叙述完全放到审美叙述的对立面对彻底否定它,同样也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本文既称不上是系统的回顾,也谈不上进行全面的理论剖析。我只希望这种片断的回顾和从中得出的启示,能够为今后理论建设提供一点必要的参照。不确之处,望予批评。
标签:文艺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中国文艺论文; 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王国维论文; 读书论文; 革命论文; 古文字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