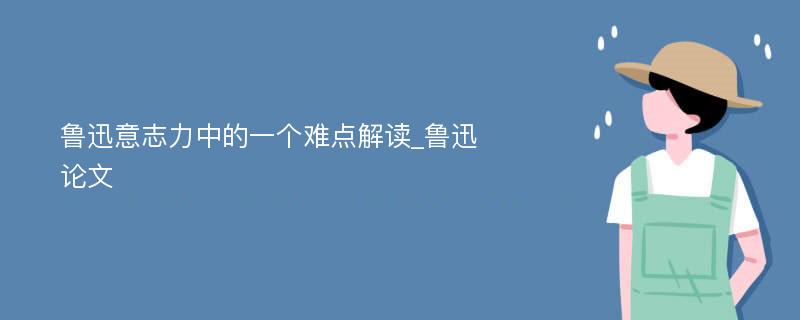
对鲁迅遗嘱中一个难点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遗嘱论文,难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先生在逝世前的一个月,即1936年9月,写下了一篇被后人当作遗嘱来读的著名杂文《死》,其中有类似遗嘱的七条,第五条是这样写的:
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1]( p.612)
文章发表后,即产生巨大的反响。以后的论家对此也特别重视;但是,对“空头文学家” 这一提法的来历却说得不多。其实,如果我们将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写的一段话对照起 来读,也许更耐人寻味。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初稿中是没有“空头”两个字的,为此冯雪峰 提出了修改意见:
关于第五条,我也说出了我的感觉,认为容易给人误会,好像一切文学家和美术家 ,他都看不起似的。他也同意改一下,还和我商量如何改,不一会儿就由他自己想出“空头 ”两个字来了。这“空头”两个字,他觉得很满意,在原稿上添上了,躺回藤躺椅上去以后 ,还笑着说:“这添得好。只两个字,就将这些人刻画得活灵活现了。这就是住在上海的好 处,看多了这类空头人物,才能想到这两个字。”[2](p.163)
冯雪峰这一段话是真实可信的,且活龙活现地画出了鲁迅的性格。但这一段回忆我们提出 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鲁迅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在逝世前留下的遗言中,只有一条是 关于文学的,而这仅有的一条,初稿中竟说是“万不可去做文学家和美术家”,鲁迅为何对 文学家和美术家说出如此不敬的话呢?这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呢?这就成了我们研究 鲁 迅遗嘱的一个“难点”,有必要对此作一番认真的解读。
一
以往的论家在研究鲁迅遗嘱时,尽管对“空头文学家”的阐述评论层出不穷,但是对“空 头文学家”这一词的产生过程往往避而不谈,这就很难解释鲁迅为什么会对“文学家”和“ 美术家”采取嘲弄态度。事实上,只有正视鲁迅遗嘱中的这个“难点”,才能窥见他那浩瀚 而复杂的内心世界,揭示他晚年文艺观中一个重要的层面,并在我们面前显示出一个真实的 、可信的鲁迅。
鲁迅晚年嘱咐自己的孩子“万不可去当文学家和美术家”,确实是一件叫人触目惊心的事 。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决心从事文艺运动,选择了文艺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方向。五四 时期,他首先以他的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以后又在战斗的硝烟中写下了大量的随感 录和论文,到1936年,他已为自己的民族和人民留下了35万字的小说、散文、散文诗,135 万字的杂文,辑录、校勘了80万字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翻译了十几个国家的文学作品300 余万字。鲁迅在美术方面作出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他自己办出版社自费印刷或与人合资 印刷的,就有《近代木刻集》、《引玉集》、《北平笺谱》等,并翻译、编辑了画史、画集 共18种,主办木刻讲习班一次,举办外国展览三次,写了美术方面的论文20余篇,给青年美 术工作者写信200余封,直到逝世前几天还抱病参观了木刻展览。他在文学、美术领域耗尽 了毕生的精力,树起了可观的丰碑,临终前却反对自己的孩子继承自己的事业,这该如何解 释?
一种解释认为,这话是鲁迅随口说说、随意写下的,并未深思熟虑,所以一经冯雪峰提醒 , 鲁迅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有些善良的研究者还在“倘无才能”上做文章,意思是说鲁 迅讲这话是受了限制的,是反对孩子无才能而硬做文学家,若有才能还是可以做文学家的。 但鲁迅晚年留下来的书信和别人的回忆文章又证明,类似的话他不止说过一次。日本友人增 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中回忆:“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做跟政治没有关系的工作,数学呀或者 别的什么都可以;关系到政治的工作,总是像穿着湿衬衫一样不愉快。”[3](p.29)1934年4 月,鲁迅在给姚克的信中说得更明确:“近颇自憾未习他业,不能改图,否则虽驱车贩米, 亦较作家干净,因驱车贩米,不过车夫与小商人而已,而在‘作家’一名之中,则可包含无 数恶行也”[4](p.385)。由此可见,不当文学家和美术家,是鲁迅晚年经常思考的问题,并 不是他兴之所至,随口说说的。
还有一种解释是鲁迅从事政治活动受到挫折,所以认为当文学家是没有用的。有的论者还 将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论曹植的一段话当作“夫子自道”:曹植说 文章是“小道”,鲁迅认为“大概是违心之论”,“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 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5](p.504)。确实,曹植身为文人,政治上是有抱负的, 曹操在世时他即与曹丕争宠,可是屡受打击,雄才一直无机会施展,最终以悲剧结局,因而 ,他有“文章是无用”的感叹是完全可信的。但鲁迅同曹植并不是一回事情。鲁迅早年是有 政治热情的,也直接从事过政治活动,但遭受到一连串失败后,认识到自己“决不是一个振 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6](pp.417-418),以后就同直接的政治斗争保持了一定距离,而 将思想文化战线当作自己的主战场。同时,他早在弃医从文时就立志以“改造国民性”为己 任,直到1925年,他还认为:中国的政治斗争,“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 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7](p.31)。他从事文学运动,完全是为了实现“立人”的理 想,是他终身奋斗的目标,绝不会有比当政治家低人一等的想法,对他说来,中年以后恐怕 也未考虑过政治上得志不得志的问题,因而,将鲁迅不要去当文学家之类的说法同曹植的话 来相类比,是不尽相宜的。
笔者认为,比较接近鲁迅自身的解释是:鲁迅在晚年之所以会对“文学家”、“美术家” 有一些大为不敬的“说法”,是因为他在从事思想文化运动三十余年后流露出来的一种绝望 心理的表现,是鲁迅品尝了以文化改造社会而不能成功的苦酒后产生的一种虚无情绪。这种 心理和情绪,在鲁迅晚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后来的研究者是不必回避、也不容忽视的。
本文强调鲁迅晚年的这种情绪,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这岂不是说鲁迅是个虚无主义者吗? 这不是周作人的观点吗?确实,周作人曾用“虚无主义者”来概括过鲁迅,他在鲁迅逝世后 五天就写道:“大约现代文人中对于中国民族抱着那样一片黑暗的悲观的难得有第二个人吧 ”[8](p.26)。对《大晚报》上海记者也表示,鲁迅“以前的思想是偏于消极的,现在变为 ‘虚无主义’者”[9](p.634)。把鲁迅说成虚无主义者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曹聚仁,他20世 纪50至60年代在香港出版的两本有关于鲁迅的书《鲁迅评传》、《鲁迅年谱》中,以朋友的 身份、平视的态度观察和描绘了鲁迅,其中有不少独到的见解,这给还处于思想禁锢状态中 的大陆学者以耳目一新之感。但是,书中多次说鲁迅带有“浓厚的虚无色彩”,在政治上, 他“不相信任何政党会有什么成就的”,“有了政治永远是一种骗局的看法”;而在艺术观 上,“他曾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却也反对为政治而艺术”[10](p.377)等等,这就值得商榷 了。周作人、曹聚仁不分政治观和文化观,不分虚无主义情绪和虚无主义者的区别,笼统地 认为 鲁迅是个虚无主义者的观点,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曹聚仁只看到了鲁迅和当时上海文化界 地下党领导人发生过矛盾,强调了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保持思想上的独立性这一面,而基本 否定他也是共产党阵营中的一员,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鲁迅晚年投身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 革命斗争,对革命的前途表示了热烈的希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鲁迅在政治态度 上的这种新姿态,是不是就说明了他心底深处就没有了一点绝望和虚无,特别是在文艺改造 社会的作用上,也就一定抱乐观、前进的态度了呢?若这样推论,恐怕也是一种简单化的倾 向。
二
为了说明鲁迅晚年文艺思想上的这种变化,简单回顾一下他的文艺思想、特别是文化价值 观的演变过程,也许是必要的。以一般而论,鲁迅文艺思想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
其一,早期。鲁迅早期的文艺观是在东京留学期间形成的。当时,其他民主革命家注意的 都是军事政治活动,准备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而鲁迅的思想比别人想得更深一些,他并没 有停留在反清这一点上,而是进一步看到了提高人民群众觉悟的重要性。他弃医从文,企图 以文艺来改变国民精神,因为那时在他看来,改造国民性的最好武器是文艺。辛亥革命后, 中国社会一天天沉入黑暗的事实,证明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为了打破这死一样的“铁屋子 ”,五四前后,鲁迅又一次发出了高昂的“呐喊”,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从“今索诸中 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6](p.100),到听革命前驱者之“将令”,鲁迅当时的文化价 值观是前进的、乐观的,充满了浪漫主义、英雄主义激情。
其二,中期。经过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鲁迅南下厦门、转辗广州,他对文艺社 会作用的估计发生了变化。他不断地对自己所坚持的思想文化方面的战斗作出了否定的评判 。1927年4月,他在黄埔军官学校演讲时说:“开枪打杀学生的时候罢,文禁也严厉了,我 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 的 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 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办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5](p.417)?其哀痛和绝望之情溢于言表。经过了1927年大革命及其失败的全过程,鲁迅对此的看 法更加明确。著名的《答有恒先生》往往被视作是鲁迅的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转变的标志 :“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被解释为“进化论”破灭了,这当然不无道理,但结合全文来 看,他自称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 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5](pp.453-457)。若把这些“破灭”解释成“以文艺改造世 界”观念的“破灭”,也许是合适的。此后鲁迅类似的议论发过很多。1929年5月,他说: “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 倘 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事实的出现,并不如文学家所预想”[11](p.1 34)。论者也往往将此作为鲁迅文艺观从唯心到唯物转变的根据,屡屡被引用,但是,从这 里透露出来的文化价值观的逆转,其中所包含着的长期从事文化运动的老战士的痛苦和惶惑 ,是否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呢?
其三,后期。对鲁迅最后十年的文艺观,一般论者总是概括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成为无产阶级文艺冲锋陷阵的战士。确实,20世纪30年代初,经过革命文学论争,鲁迅接触 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他又被推到了盟主的地位;同时,他同 瞿秋白、陈赓、冯雪峰这样的优秀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看到了实实在在的“中国的 脊梁”,这一切促使他的政治立场站到了中国共产党这方面来。但如果说《二心集·序言》 中 ,“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的宣言及由冯雪峰起草、经鲁迅认可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中,对毛泽东理论的赞扬能够表明鲁迅晚年政治态度转变的话,那么,鲁迅在20世纪30年 代的文化价值观则基本上同中期一样,并没有什么大的变更。面对国民党政权对进步的文化 事业的压迫和摧残,他只能抱“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态度;面对革命队伍内部的种种磨擦, 他又只能以“横站”的姿态应付腹背之敌;而面对多数人的社会心理和旧习惯势力,又不能 不感叹自己种种“启蒙主义”的努力只不过是一种“一箭之入大海”式的悲哀。在黑暗势力 如此浓重的情况下,鲁迅难道还会对文艺的价值作出多少高的估计吗?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6](p.159),这是鲁迅中年时期的人生体验。而到 了 晚年,最让鲁迅痛苦的是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却似乎看不出产生了多大的效果,以至 于对自己年青时代选择的事业发生了怀疑,终于说出了要自己的孩子不要去当什么文学家 、美术家的话。这样一条思想线索是符合逻辑的,也是符合鲁迅的个性心理特征的。周作人 不分 鲁迅的政治态度和文学观念,笼统地说鲁迅是“虚无主义者”,而曹聚仁说鲁迅的虚无主义 也主要是偏于政治态度上,这是有明显漏洞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正视鲁迅晚年在文艺价值 观上确有虚无的情绪,或者用一顶“虚无主义”的帽子随意否认鲁迅的一些独特的、超越他 人的深刻思想,则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鲁迅晚年在文艺价值观方面所表现的悲观主义情绪其实是比较多的,还可以举出另一篇文 章的例子来说明。1936年2月,鲁迅应日本《改造》月刊之约写了一篇杂文,题目就显得惊 心动魄——《我要骗人》。文中写道:鲁迅在电影院门口遇到一个为水灾灾民募捐的小学生 ,鲁迅给了一块钱,小女孩“非常高兴了,称赞我道,‘你是好人’,还写给我一张收条” 。可是鲁迅一想起这件事,“心情又立刻不舒服起来,好像嚼了肥皂或者什么一样”,他沉 思着:
……而其实,一块来钱,是连给水利局的老爷买一天的烟卷也不够的。我明明知道 着,却好像也相信款子真会到灾民的手里似的,付了一块钱。实则不过买了这天真烂漫的孩 子的欢喜罢了。我不爱看人们的失望的样子。[1](pp.485-487)
接着,鲁迅忏悔自己“骗她是不应该似的”,甚至觉得自己正在写的这篇稿子也是“骗人 的文章”,“如果这骗人的学问不毕业,或者不中止,恐怕是写不出圆满的文章来的”。其 沉痛心情力透纸背,读了叫人刻骨铭心。
由此不能不想到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鲁迅在此将中国四千年的文明史概括 为“吃人”,这成了人们经久不息的话题,但鲁迅在逝世前夕,却已经将这“吃人”改变为 “骗人”了。也许是鲁迅写得实在是太痛心疾首了,以至论家不敢正视鲁迅这篇题为《我要 骗人》的文章,无论是从研究的力度、还是从传播的普及面来说,该文都远远不如《狂人日 记》。但笔者认为,这是一篇特别应该注意的力作。当我们一再读这篇文章并为之感动的时 候,就时时会想到五四运动前夕,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下的战斗宣言:是他第一个揭示 了中国四千年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是他第一个提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厉声 诘 问;是他第一个高声疾呼“救救孩子”。这一切犹如一道道划破漫漫夜空的闪电,成了新文 化运动中高亢激越的时代最强音。但是曾几何时,在鲁迅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却从“救救 孩子”的呐喊变成“我要骗人”的悲号了。反对瞒和骗的文艺,强调中国要有“真的声音” ,这是鲁迅的一贯主张,但他晚年所悲号的“我要骗人”,确是坦露出了自己那流血的心灵 ,说明了鲁迅晚年思想的深邃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鲁迅是严于解剖自己的,当他在揭露别人是骗人的时候,同时还用解剖刀分析了自己,眼 见自己三十余年在文坛的奋斗见效甚微,他所热爱的祖国的面貌也并未见好转,反而一日日 地沉入黑暗之中;他所寄予希望的人民的意识同样也并未见清醒,且仍然一天天陷入愚昧之 中,更为痛心的是,甚至“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 净的人物的”。面对严酷的现实,他不禁怀疑自己是否也在“骗人”,或者如《我要骗人》 一文中所说:“为了希求心的暂时的平安,作为穷余的一策,我近来发明了别样的方法了, 这就是骗人”[1](pp.485-487)。就像五四运动时他在发问:“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 有?”到了1936年去世前夕,他实际上是在问:没有骗过孩子的人,或者还有?从“救救孩子 ”到“我要骗人”,正好勾勒了鲁迅从五四时期到逝世前夕的心路历程,描绘出鲁迅文艺价 值观的变化。正是顺着这一条思路,他不无忧虑地担心自己的孩子会不会也走上有意无意“ 骗人”的道路,所以,他在遗嘱初稿中写下了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当文学家和美术家的话。 笔者认为,将《我要骗人》同《死》连起来读,才能让我们真正理解不当“文学家和美术家 ”这一遗嘱的来龙去脉和深刻内涵。
三
承认鲁迅晚年思想中有虚无主义情绪,这同鲁迅对自己的剖析是一致的。鲁迅从来也不隐 瞒自己的思想中有虚无主义的色彩;但是,鲁迅却不是虚无主义者,他是轻蔑虚无主义的, 并一直在同虚无主义作抗争。在这方面,日本友人增田涉有一段很有价值的回忆。增田涉对 鲁迅说了一句近代丹麦文艺家勃兰兑斯的话:“一切贤明的人,在他们心胸的深处藏着虚无 的深渊。”鲁迅却不赞成,说:怕不能那样说吧。增田涉争辩道:虚无主义者也许是值得轻 蔑的,但虚无主义在人类复杂的精神里,却是有价值的。鲁迅听了后,又表示认同:“也许 是那样吧”。增田涉解释说:“也许他是因为嫌麻烦而那样回答吧”[3](pp.33-34)。
但笔者觉得,这不仅仅是“嫌麻烦”的问题,鲁迅前后不同的回答,实际上是反映了这位 大思想家内心的波澜,他理智上明白虚无主义的负面影响,但心底却无法摆脱虚无主义的阴 影,因而处于一种极度痛苦的心理状态之中。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多次说过这样的话:“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但是,鲁迅对此立 即又怀疑了,解释道:“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 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鲁迅在1925年说的这一段话,显然同1930年与增田 涉交谈时的思路基本一致。但是,鲁迅的伟大即在于:无论他轻蔑虚无主义者也好,承认自 己有虚无主义情绪也好,他都没有放弃反抗,就在同许广平探讨是否“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 有”的同时,鲁迅提出了“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7](pp.20-21)的命题,这“绝望抗 战”即成了鲁迅向一切黑暗势力反抗到底的宣言书。而到了1936年逝世前夕,鲁迅在文章和 谈话中又一次表露了虚无主义情绪的时候,他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终身不倦的孜孜追求;尽管 一生备受挫折、屡遭厄运,又遇腹背之敌、疾病缠身,但他仍然顽强、坚定地生活着,并准 备 用他最后的一击,奋力投身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去。稍稍熟悉1936年 鲁迅境遇和心态的人,都知道这实际上成了鲁迅去世前最悲壮的篇章。所以,我们透过 鲁迅不愿让儿子当文学家的遗嘱,看出了鲁迅的悲观主义情绪,但这绝不会影响鲁迅一代伟 人的形象,倒反而显示出这位大思想家深邃的眼光和广阔的思绪,后人不应该、也不会像周 作人和曹聚仁一样,随便给鲁迅作一个“虚无主义者”的结论的。
但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活动家的冯雪峰,对鲁迅的悲观主义情绪是非常敏感的。 据《回忆鲁迅》中记载,早在1929年前后,鲁迅和冯雪峰相交不久,冯雪峰就对鲁迅提过《 野草》中的情绪“阴暗”、“虚无”、“悲观而绝望”等问题,并对此作了讨论。冯雪峰认 为,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他在咀嚼着他的某些旧的思想和旧的感情,一方面更多地反映了 他的矛盾的心境,尤其可以看出他在分析着自己,并且否定着自己某些旧的思想”[2](pp.1 5-17)。所以,当鲁迅遗言中有不当“文学家或美术家”之类的话时,冯雪峰便立即在一旁 提醒:不要给人以看不起一切文学家、美术家的感觉。冯雪峰此时的潜台词是很清楚的,那 就是希望鲁迅要保持乐观主义情绪,不要给别人以“绝望”与“虚无”的感觉。当冯雪峰以 朋友的态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时,正如增田涉所说的那样,“对论敌彻底地战斗的鲁迅”, 在对手不同的情况下,“决不是始终执著的人”[3](pp.33-34),就接受了冯雪峰的意见, 加上了“空头”两个字,最终就成了“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的遗言。
当然,在20世纪30年代阶级斗争非常激烈的时候,冯雪峰担心鲁迅的悲观情绪会对革命实 践活动带来不利的影响,这应该说有他的道理所在。实际的革命活动家总是要拒绝一切可能 会给革命实践产生负面作用的东西,哪怕仅仅只是一种情绪、一种感觉,都是要极度警惕的 。冯雪峰同鲁迅在思想上确实存在着分歧,表现出来的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差异,但这说明 了什么呢?讨论这个问题时,笔者不禁想到了时隔半个世纪后的一件让人听了感到心酸的事 。1985年6月8日上午,鲁迅的忠实学生及传人胡风病危,当时已呼吸困难、喘息不停,女儿 晓 风附在父亲耳边轻声说:外孙要报考大学了,特来征求你的意见。弥留中的胡风竟然很清楚 地重复道:“不报文科!不报文科!”当天下午胡风就去世了,“不报文科”成了他最后的遗 言[12](p.399)。一生为文学奋斗而又为文学受难的胡风,弥留之际竟不愿自己的后代继续 走文学之路,不能不使后人为之喟叹。两代宗师、一对师生,为何时隔49年后留下的遗嘱竟 会一脉相承呢?这又不得不使我们承认鲁迅思想所具有的超前性和长久的生命力了。人们常 常认为,在变革社会和世界的过程中,乐观主义总是必需的,而悲观主义总是糟糕的;但是 ,人们在评价鲁迅某些观念为何显得偏激时,也常常会说另外一句话:深刻的片面性胜过肤 浅的全面性,深刻的悲观主义要比平庸的乐观主义高出一筹,在“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 ”之间简单地分一个是非,实在是太浅薄了。一味地陶醉在乐观主义之中,就会忽视前进道 路上的坎坷和波折,就会对突然而来的困苦和磨难缺少必要的思想准备。冯雪峰和胡风,在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都被称之为文坛上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冯雪峰对鲁迅虚无情绪的 警 觉性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这两位乐观主义者天生的天真、轻信、不知世 故、少有策略,使他们最后都无法摆脱悲剧的命运。
如果将胡风、冯雪峰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悲剧称之为“缺乏悲剧意识而造成的悲剧”,是 一点也不过分的。而被冯雪峰所警觉的鲁迅的“绝望”、“虚无”情绪,却显示了鲁迅对中 国历史和现实的深刻了解,对唤醒民众之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的清醒认识,这在中国现代 思想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甚至至今也没有失去它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