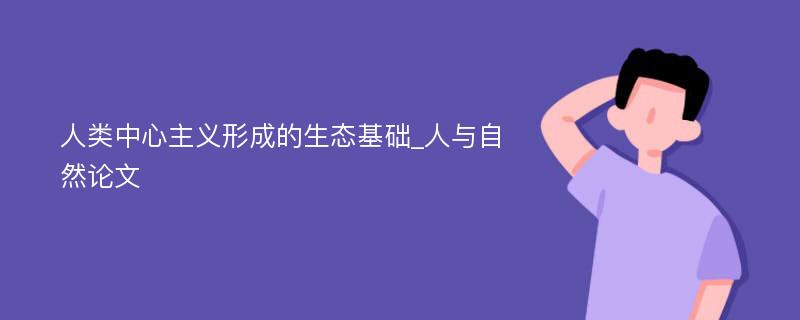
人类中心论形成的生态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人类论文,基础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B03
(一)“人是什么?”这是一个既古且新的问题,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人们就在不断地追问着,试图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但直到今天,似乎还没能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然而,人们可以从不同方面、角度对人作出不同的解释。如生物学把人理解为生命蛋白体的存在形式,经济学把人视为有理性的经济人,伦理学则把人理解为自尊、自觉的生命存在,等等。即便是在同一学科内,对人也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可以这么说,凡有一种有关人的学科或理论存在,就会有一种相应的对人的理解。用我国著名学者高清海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人是一切,又不是一切,人属于一切,一切又属于人”(《人与哲学》,《求是学刊》1995年第6期)。对人的认识,似乎只能通过归纳的方法来进行, 而不可以作出一个包容一切的结论。换言之,关于“人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只能说“人就是人”,除此而外,无法作出任何其他形而上的概括。有鉴于此,本文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来探求人及人之存在的本质,进而探讨人类中心论形成的生态基础。
(二)人本来是一种自然存在物。生命进化的过程表明:在距今大约30亿年的太古代,地球上开始出现生命存在物,然而这时的生命形式还是非常简单的。经过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一直到上新世与更新代交界时期(距今约200—300万年),生物逐步摆脱了古猿阶段,进入能人时期。这时,也就出现了早期的人类。与已往古猿不同,早期人类已能够制造并使用简单的劳动工具,而古猿则只是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能够制造并使用劳动工具,标志着人类已逐步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独立于自然并能积极改造自然的力量。
(三)人的产生,使人作为一种独特的类本质而成为“万物之灵”。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物质实体能与之相提并论。我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描述出人之优越于别的物种的特性,如人的大脑具有比其他动物更为复杂的组织结构,这也是人类能够进行思维活动的生理基础;人还具有社会性,人能够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实现个人所无法达到的目的。如若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来看待人之为人的特性,则人就表现为一个创造性的动物。人与其他动物虽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之中,并且都具有自然属性,但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人具有创造性,人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各种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相比较而言,动物则只能被动地接受外部世界所存在的事实。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曾以人的“劳作”来说明人的生存本质,“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圈。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就此意义而言,人的意义是在其创造性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人是一个自我塑造的过程,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个人类创造性活动的历史。
(四)人类创造性活动的动力来自于人类不断增长的需要。从生物个体来说,人之生存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的生理需求,即人的自然本能需要,这是保持生物个体和种的存在的自然前提。所谓“食色,性也”,实则蕴含了人的生理性要求的客观性公理,任何人都不可违背这一生命的自然法则。然而,人之存在并不仅仅表现为简单的自然生存需要,从根本上说,人之存在体现于文化存在的意义之中。只有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才能昭示出人的存在意义。当我们说某个人是“高尚的人”,某个人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人生”的时候,实则是依照一定的文化价值观作判据的。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特定社会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背景条件下生成的,受当下文化状况的影响。对不同的活动主体来说,他们所生活的这种文化背景有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当中已经包含了人们对自己生活条件和生存条件的价值判断,亦即价值优劣的肯定或否定。人们总是追求价值较高的文化存在,并在实现这种价值要求中肯定自我。同样是吃,原始人和现代人有着不同的饮食文化。即使是在同代人之间,人们所面临的文化条件也具有差异性,表现出某些方面条件的优劣,这也促使人们去不断追求更高、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生存条件。就这样,人们在不断地实现着自己的需要,同时又不断地创造出新的需要。人的意义就在这种不懈的追求中不断实现,不断深化。正如黑格尔所言,生命的本质“是扬弃一切差别的无限性,是纯粹的自己轴心旋转运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第117页)。由于人对生命本质的不断追求,使得人们总是不满足于现实的主体地位,在无限的追求中实现新的“人”的意义。
(五)满足人类需要的最基本途径在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任何一个生物物种的保存与繁衍,都必须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等的交换,通过交换而获得必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然而,人的保存方式不同于其他动物,人类不是仅靠本能而谋取生存资料,人对自己所创造的工具表现出很大的依赖性。工具作为人类获取物质资料的最基本手段已成为人自身器官所必不可少的延伸部分。而且,随着工具的发展,人类对工具的依赖性会越来越强。对于一个充满生存竞争(霍布斯所讲的“自然状态”)的世界,与其说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不如说是创造与本能、工具与工具之间的竞争。原始初民之所以尊崇自然,对自然表现出极大的敬畏心理(如他们制定了许多带有神秘色彩的规范和禁忌),实则是他们由于工具的简陋而缺乏足够的能力去改造自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无奈。近代中国之所以被动挨打,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生产工具的落后而造成的。
人类的全部本质物化于劳动工具之中。人的产生首先是以劳动工具的创造为标志的,人借助于劳动工具而获得了人之为人的实质意义,并在劳动工具的改进中使人的意义不断扩展。我们通常把人类社会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如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及后工业社会等,所划分的基本依据就在于人所创造的工具的意义。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其说是社会生产力提高的结果,莫如说是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更新使然。当代人类的技术发展已可以把人的意义扩展到地球以外的其他星球上(如月球),从而使人的生存意义与生存本质都得到了深化。
(六)从人自身的生产过程来看,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形成了一个朴素而又简单的观念,即人口的多寡与人群族体的兴旺休戚相关,因而每个族体都非常重视人口数量的增长。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社会生产水平的低下和人们思维能力的限制,人类抵御自然的能力还不够强大,社会物质资料的增长及部落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人口数量的增加。基于人类这种自我保存和自我发展的需要,人们对自然的生命繁殖力表现出强烈的追求与渴望,世界上许多民族至今所遗留下来的生殖图腾和生殖观念都反映了这种思维倾向。既已形成的这种人口生产观念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传承下来,延伸到后来的社会中而起作用。如“多子多福”的观念在我国直到现在仍然还有很大的市场。
当然,人口的增长是建立在物质资料增长基础之上的,只有当物质资料的生产能够为人口的生存、发展提供保证的前提下,人口的增长才更快、更有效。同时,由于人类医疗等有关人类健康的技术水平的发展,人类自我保存的能力也逐步得到扩展,人口增长的速度和人口增长的基数也越来越大。马尔萨斯曾以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物质资料呈算术级数增长的巨大反差为由,断言人类不同的族体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必然会发生战争。这种结论固然有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但他所揭示出的人口增长的规律却是客观的,这已为人自身的生产发展历史所证实。1850年世界人口约为10亿,1920年时已增加到20亿,到1981年已达到45亿,1992年世界人口超过了55亿。人口的急剧膨胀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压力,也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状态。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的需要,人们极力发掘自然界中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然而,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七)自人类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之后,人类便同自然界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没有工具、人们便制造工具,没有土地,人们便开垦土地。经过多少万年的不懈努力,人类逐步改变了完全依赖于自然的状况,使人的主体地位获得了提高。从远古时代天(自然)人浑然不分(在蒙昧时代的人类意识中,人与自然没有明确的界线,人们心中“我”的概念还不十分清楚)到现代人类“自我实现”的观念,证明了人具有巨大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人在自然面前可以有所作为。经过世世代代人们的不懈努力,人类创造出巨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如果说,在以简单的手工工具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中人还是微不足道的话,那么,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于机器大工业的作用,以及社会生产力中科技含量的增多,人类影响自然的能力不断增长,人逐步取得了自然与人的关系上的主导地位。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人们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现在世界上一年所创造的财富要比农业社会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总和还要多。人之所以高于其他动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的这种能动性决定的。在此基础上,人类不断生成和获得新的“人”的意义。
(八)然而,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所带来的意义并不都是积极的。随着人的主体地位的加强和人类理性的发展,人类逐步产生了一种盲目自大的认识和心理,仿佛人就是万物的主宰,人是宇宙中的唯一价值主体,世界万物都是为人利用的,万物皆备于人。在这样一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人类逐步建构出以“自我”(这里的“自我”是表示人的类主体)为中心的文化价值体系,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人的利益成为衡量人类行为的唯一尺度。这便是人类中心论的思想。
(九)从实践上讲,以人为中心的活动可以说是与人类自身的产生同步的。因为人和所有的其他动物一样,有一种利己(这种利己性是以种为单位的)的本能,他要生存,就得从外界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就得同其他外部竞争者作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生物物种得以保存下来。然而,人与其他生物不同之处在于:人是积极、能动的行为主体,他不只是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的变化,而且还可借助于劳动工具对自然施加影响。是否可以这样说,人类中心论是从制造最简单的石器工具开始萌发,又从人的自我意识的产生而逐步形成,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才逐步成为人与自然关系上价值观的核心的。
(十)无论在古代中国文化哲学或古希腊文化哲学中都可找到人类中心论的思想端倪。如中国历史上留传下来的“人定胜天”、“愚公移山”的神话和思想以及西方思想史上“人是万物的尺度”等都表现了人对自然的这样一种态度。可以说,人类很早就已产生了人类中心论的思想。然而,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中心论的思潮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上,人们往往把自己看成是微不足道的,人类中心论的思想还是被“天命观”和宗教神学观念所遮蔽着,如中世纪欧洲宗教神学把人看作是超自然的“上帝”的创造物,认为人在自然面前不应该有太多的奢望,人只能服从上帝对现有世界秩序的安排。
人类中心主义思潮的滥觞,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以近代工业革命为开端,整个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时,人们才真正认识到自己力量的伟大,人类社会也就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即“技术文明”时代。“知识就是力量”(培根语),人们相信技术可以做一切事情,人类借助技术的力量可以统治整个世界。由此,人们对技术的发展抱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确认技术可以为人类带来无限的可资利用的资源。技术被视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理想的参变数,人们用技术的发展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技术成为人道化和科学化的代名词。德国社会学家舍尔斯基指出:“技术不是以自己本身为基础的、和人对立的绝对存在,而是作为科学和作为劳动的人本身。在这里,人完全处在一种必然性之中,这种必然性把自身塑造成了自己的世界和自己的本质。”(转引自达夫里扬《技术·文化·人》,河北人民出版社,第145页)
(十一)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近代的泛滥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即商品经济社会的建立。近代资本主义的建立和发展,冲破了闭关自守和封建割据的状态,商品成为社会最普遍、最一般的客观存在。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商品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支配人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和源泉。人们更多地关注自身的物质利益,在现实的物质利益中审视人的价值和尊严,这客观上又促进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潮的蔓延。近代以反对封建禁欲主义而提出的“尊重人”、“重视人的价值”,实则是将人置于一种感性自然人的地位,把趋乐避苦视为人的本质,认为人都是只追求有利于自己的事物,人生的目的就是享乐。荷兰人道主义思想家爱拉斯谟曾经指出,人是自然的中心,人的自然欲望就是人的本性,因而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感官快乐。在这样一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人们极力追求物的消费价值,试图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寻找“自我”。用美国一位社会学家所说的话也许更能表达这种意思:“在过去,满足违禁的欲望令人产生一种负罪感,在今天,如果未能得到欢乐,就会降低人们的自尊心。”
(十二)然而,人能完全摆脱自然的约束而实现自我吗?换句话说,人可以对自然界为所欲为吗?现实的回答是否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以来充满矛盾的文化现象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人类一方面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又使人类生存的条件日趋恶化;一方面创造出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将人类置于毁灭性的危险之中。同时,工业化又使人变成机器的奴隶,加剧了人与人的劳动成果分离、异化的进度……最终还是造成了人的“自我”意义的失落。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在《论科学和艺术》一书中对艺术与科学的发展提出过诘难,在他看来,由于科学、艺术和文化同财富、奢侈密切相连,因而它们不仅没有给人类带来好处,反而带来害处;不但无助于敦化风俗,反而伤风败俗;不仅没能满足人的欲望,反而使人的贪欲急剧膨胀。由此,他得出结论:科学与艺术即整个文化并不能增加人的幸福,反而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而他主张“回复自然”。卢梭的这种思想固然有其复古主义之嫌,但他已经揭示出了人类文化所固有的矛盾现象。
由于人类过度地开发自然,并强调技术的绝对价值,最终造成了人类当前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难题,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口压力、沙漠化加剧、可耕地减少,等等,使人类所赖以生存的条件变得越来越坏。早在100多年前, 恩格斯就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
现代生态学理论已经揭示出人与自然是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而相互依存的,自然和人任何一方的存在必须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它们之间是一种互惠的利益关系,人类不应把自己的意志随意强加给自然界,而应平等地对待自然及自然的客观要求。对自然的过度利用,必然使人类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
(十三)平等地对待自然,并不意味着人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正是在人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才获得了“人”的意义,并使“人”的意义逐步扩展。问题在于,人类在对象性活动中如何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保持一种良好的互助互利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康德的认识是深刻的,他认为,人类的文化和文明并不是幸福本身,而是实现人的幸福的条件。就“人类文化的目标来说,也不是要使世俗的享乐得到实现,而是要使自由即真正的自律得到实现。这种自律并不在于人类对自然的技术性驾驭,而在于人类对自身的道德性控制”(参见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第160页)。
在人与自然之间,人是能动的主体,他既要在自然的人化过程中施之以人的影响,为人自身创造更好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条件,同时,人的创造性活动又必须被限定在合理的限度之内,使人类的行为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即既能够满足人类目前的需要,又不对未来的需要造成危害。
标签:人与自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