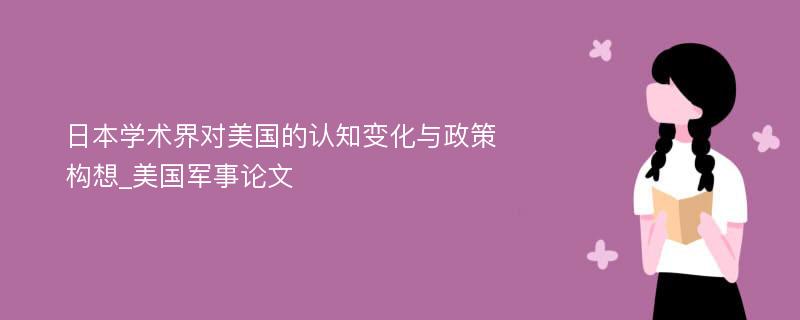
日本学界对美国的认知变化及政策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美国论文,学界论文,认知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日本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进入战略性的转型时期。一方面,日本政府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制订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强行推进安保法案等一系列措施,加速日本在军事上成为“正常国家”的进程;另一方面,日本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借此重塑日本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角色。是什么因素在推动日本的政策变化?日本国内的政治动态无疑是重要的背景,特别是以安倍晋三为首的右倾保守势力的崛起,为加速这一进程提供了政治动力。①然而,日本的战略转型绝不仅仅来源于保守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不仅仅出自安倍内阁的政治考虑,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政界、舆论界乃至学界正在形成的新的战略思维,其核心主张是:日本应该在军事领域发挥更主动、更积极和更具战略性的作用。这种新思维的出现不只是日本国内政治变化的结果,还与国际环境的深刻变革密切相关。其中,美国的战略转向与中国的崛起是两个关键的外部动力。本文将聚焦于近年来②日本对美国认知的变化及由此带来的战略思维的变化,以学界③的观点为主要研究对象,希望从一个侧面探索日本战略转型的动因和走向。 围绕日本对美国的认知及其变化,日本学界一直进行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例如,有学者整理和总结了从近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人的美国观,从比较文化的角度解析了日本人“崇美”和“排美”的历史。④有学者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社会中“亲美”和“反美”思潮的流变,指出日本民众之所以长期抱有稳定的“亲美”感情,深层原因在于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与战前以日本为中心的地区秩序之间存在很大程度的连续性。⑤有学者通过剖析日本人的精神构造和行为模式,指出日本人(包括精英)对美国的看法更多的是出于爱恨交错的情感表达,而不是基于对作为他者美国的冷静评价,其背后蕴含着与理想化美国的一体感和受美国背弃后的怨念。⑥有学者基于民意调查的数据,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舆论中的对美评价总体良好,但在“安保条约”、美军基地等问题上存在着挥之不去的受美国压制的感觉。⑦也有学者从意识形态或文明观的角度,分析了当代日本反美保守主义的思想内涵及其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兴起的背景。⑧还有学者指出,在日本精英的美国观中,同时存在着对美抗拒和对美依赖两个要素,这反映了民族主义冲动和现实政治约束之间的矛盾;而日本人之所以一直难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心理,除了受实力差距、地缘环境等客观因素限制之外,从根本上说是对日本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缺乏明确的认识。⑨还有学者从“忠诚与反叛”的视角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人对日美同盟抱有的矛盾心理,并指出近年来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强化日美同盟的动向可能引起与中、韩之间的安全困境,为此,日本应该审慎行事。⑩ 中国学界对日美关系的研究也涉及认知层面。有学者指出,美日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具有主从性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结成了师生关系,但日本又一直想要后来居上,竭力追求与美国平等竞争的地位。(11)还有学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美主日从关系至今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从文化心理学角度看,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亲子关系,是日本获得安全感的重要源泉。(12) 上述研究涉及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外交、思想和心理等多个层面,体现了这方面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过,总的来说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大部分学者探讨的要么是精英层面的思想,要么是大众层面的感情,对有政策含义的观点的研究并不多见;二是大多关注日本对美国的认知中长时段的、稳定的因素,着重分析形成此种稳定的美国观的原因,但日本对美认知中变化的一面研究得还不多。究其原因,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美关系在总体上的稳定,以及日本精英在很长时间里刻意回避敏感的对美政策讨论,也不愿在民众中挑起相关的争论。然而,随着近年来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特别是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迅速上升,日美同盟和日本自身的战略地位都面临重大挑战。在此背景下,日本国际问题研究者开始重新思考日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并试图提出新的政策选择。为了理解这一变化及其趋势,本文将重点关注近年来日本对美国的认知中与政策相关的讨论,着重考察日本对“美国衰落论”、美国的“转向亚洲”战略和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这三个新事态的反应,在此基础上对日本国内正在形成的战略新思维及其政策影响做初步的、总结和评价。 一、“美国衰落论”引发的远虑和近忧 近年来,日本对美国认知的变化,始于“美国衰落论”的冲击。和以往一样,最近一波“美国衰落论”也主要发端于美国国内,以2008年和2012年的两次总统选举为契机蔓延开来,绵亘奥巴马政府两届任期。日本多年来一直以日美同盟为外交基轴,自然对此反应敏感。日本的《中央公论》《文艺春秋》《世界》等综合杂志,以及《外交》《国际问题》等专业杂志纷纷刊登专题讨论文章,以“世界会无极化吗”“崇美主义的终结与世界萧条”“再见吧‘美国的时代’”“霸权国家美国的凋落”“美国衰落论的神话与现实”等为主题,从不同角度探讨美国实力的变化及其影响。在《国际问题》杂志于2011年实施的一次以学者为对象的问卷调查中,当被问及今后国际形势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什么时,不少人把目光投向了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其中代表性的回答有:受困于大规模财政赤字的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维持其在亚洲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影响力;美国霸权的持续衰退和世界秩序的多元化将如何演进;如何通过对秩序的管理,使美国即使在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还能维持国际秩序的稳定;美国能否恢复全球领导力;等等。(13) 在这些评论中,确有对美国实力的客观分析和真实疑虑。有日本学者指出,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外交失策,金融危机对美式资本主义的沉重打击,过度干涉引起的国家财政危机,以及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惊人崛起,都是不争的事实。(14)还有学者认为,美国社会和政治的两极分化日趋严重,民众对国际事务缺乏兴趣,态度变得内向。在此情形下,美国还能不能维持一个多元包容、充满活力的社会,能否以不同于20世纪的方式领导世界,让人感到怀疑。(15)而奥巴马总统本人公开宣布美国不是世界警察,撤回空袭叙利亚的计划,更是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留下了美国衰落的鲜明印象。(16)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表达疑虑的同时,大部分的日本学者都认为美国的霸权还不会被取代。他们的主要论据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从全球秩序的角度看,美国发挥的领导作用不可能由中、印等其他国家担当。2008年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但很快将中、印、俄、欧等国家和地区卷入其中,恰恰证明了美国影响力之大。(17)而且,中、印等新兴国家本身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即使有朝一日它们的硬实力能超越美国,在领导世界所必需的软实力方面还与美国相差甚远。(18) 第二,从美国自身的发展前景看,美国在人口、国土面积及吸引人才和自我变革的能力等方面仍保有优势。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可能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但由于劳动人口减少等原因,又将被美国反超,到2050年美国将再次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19)目前,美国只是需要一定时间调整内外政策,奥巴马执政期间可能会始终致力于这样的调整,甚至出现孤立主义的倾向,但不能轻视美国经过调整以后恢复国力的可能性。(20)因此,不能把美国在外交上的“不为”解释成“不能”,并以此作为美国衰落的证据。实际情况是,奥巴马政府把主要资源和精力集中在了国内问题的解决上。(21) 第三,从美国国内民意看,尽管美国民众中确实存在厌战情绪和内向态度,但还没有发展到期望美国霸权衰落或者单极秩序终结的程度。(22)“美国衰落论”一方面反映了美国民众中潜在的恐惧和不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不愿让美国跌落为普通国家的心理。美国人始终坚信自己的国家是例外的,即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是普世的,美国的霸权不可能落到其他国家手中。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历届美国政府,只有卡特政府接受了“衰落论”,并以此为前提采取了稳健的外交路线。但当前的美国社会几乎不存在这种可能性,信奉无限的进步和扩张仍是美国不变的政治正确性。(23)美国民众愿意接受的外交政策,依然是要么保持领导地位,要么回归孤立主义。(24) 第四,从“美国衰落论”产生的背景看,在美国历史上“衰落论”反复出现,而且模式相同。有日本学者提到,亨廷顿曾经总结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出现的五次“衰落论”,当前的“衰落论”可以被视为第六次。“衰落论”的三个基本要点是:(1)以科学、教育的衰退为背景,美国在经济上输给其他大国;(2)由于经济实力是国力的核心要素,经济衰退引发其他各种难题;(3)财富过度耗费在军事上,导致衰落。根据亨廷顿的结论,“衰落论”就是一方面相信这些论调,另一方面又竭力防止其变为现实的理论。由此观之,当前的“美国衰落论”反映的同样不是对未来的悲观,而是美国的又一次自我警醒、自我变革的呼声。(25) 总的来说,面对再度兴起的“美国衰落论”,日本国内的主流看法是:美国作为世界霸主的地位将持续下去;(26)当前美国正在经历考验,但“美国时代”不会终结。(27)基于这一判断,日本应该走的路自然是继续维持与美国的紧密关系了。事实上,在上述《国际问题》杂志进行的针对日本学者的问卷调查中,当被问及日本外交的方向时,回答最多的是强化、激活日美关系或者维持日美同盟。(28)另一项由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简称CSIS)所做的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在这项于2014年进行的以亚太国家和地区中有影响力的专家为对象的调查中,有接近80%的日本专家预测,未来十年,尽管美国的相对实力会下降,但美国仍将在东亚地区发挥领导作用,而且有85%的日本专家认为,这样的前景最符合日本的利益。(29)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问题上,日本的一般民众与学者持有相近的看法。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1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只有37%的日本受访者认为中国已经或最终将取代美国成为领导世界的超级大国,远远低于英(65%)、法(72%)、德(61%)等西欧国家,甚至低于美国(46%),到2015年,持此看法的日本受访者进一步减少到20%;相反,认为中国永远不会取代美国的日本受访者在2011年就有60%,到2015年则上升到77%,在全部22个受访国中高居首位。(30)专家与民众的意见表现出一致的倾向,反映了日本国内在看待美国霸权的问题上有相当程度的共识。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日本并不真的担忧美国的衰落呢?实际上,比起美国衰落的“远虑”来,美国当前的政策调整才是更触动日本人神经的。这种“近忧”的潜台词是,美国终究会恢复其实力和领导地位,但可能要经历相当长的调整期,在这期间如果美国从中东、亚洲等地区一步步后撤,甚至转向孤立主义,就会造成权力真空,引起地区局势的动荡,而对于在安全和经济上都严重依赖美国的日本来说,这样的前景显然是其不愿想象的。(31)换言之,日本更为担忧的是美国当前的政策调整会不会伤害到日本的利益。这种不安感和焦虑感,集中体现在日本对美国“转向亚洲”(32)战略的反应中。 二、对美国“转向亚洲”的期望和失望 美国“转向亚洲”战略的出台,在时间上恰好与中日围绕钓鱼岛紧张局势的升级相吻合。尽管日本官方始终没有明确将中国称为“威胁”,但在日本的精英舆论和媒体评论中,中国俨然已经取代朝鲜成为日本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在这样的氛围下,日本的不少学者自然希望美国的亚太战略能够助力日本,对抗中国。日本国际教养大学校长、中国问题专家中岛岭雄把“转向亚洲”直接视为21世纪版的“遏制”战略。(33)东京大学的美国问题专家久保文明也认为,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并计划扩至2500人,由于该地距离南海很近,又在中国导弹的射程之外,因而具有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意义。但他同时指出,在国内“小政府”意识形态的强烈冲击下,美国大幅削减国防开支已不可避免,未来不太可能在亚洲增兵。因此,美国必然要加强与盟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合作,日本如有意愿,应能担当大任。(34)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转向亚洲”战略本来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政策变化,从奥巴马政府在内政外交上的优先顺序看,经济是其更重视的方面。但在现实中,引起更多反响的是其军事政策,特别是被认为针对中国的部分。例如,日本防卫问题专家、后来担任民主党政府防卫大臣的拓殖大学教授森本敏认为,自“转向亚洲”以来,美国亚太政策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华政策,其背景是中国在东海、南海的“扩张”,特别是中国发展反介入/区域拒止(Anti-Access and Area Denial,简称A2/AD)能力对其他亚洲国家构成的威胁。美国的政策是一方面提出“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构想应对中国的上述能力;另一方面,利用与同盟国、伙伴国的安全合作,对中国采取含有接触色彩的、相对缓和的包围政策。而日本地处向海洋进发的中国与美国在亚太的军事部署之间,具有战略性地位,日本可以为美国的国防态势贡献什么,对美国的亚太战略和对华战略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森本看来,日本的“动态防卫力”构想和重视西南方面防卫部署的举措,能够对美国的“空海一体战”构想发挥有效的补充作用。(35)《朝日新闻》的编辑委员加藤洋一则更具体地指出,美国在冲绳部署MV-22鱼鹰运输机,是其重返亚洲战略的重要一环,由于该运输机的行动半径覆盖朝鲜半岛、中国台湾和钓鱼岛,美国此举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36) 然而,在美、日两国的防卫政策是否能够“无缝”对接的问题上,日本国内存在不同的看法。与森本敏的上述观点不同,加藤洋一认为,日本的“动态防卫力”构想和美国的“空海一体战”构想之间存在差距。前者针对的是不致发生武力冲突的“灰色地带”(grey zone),即中日围绕钓鱼岛的非武力争夺,重视的是提高威慑的可信度;后者的关注点是在发生真正的武力冲突时如何维持作战能力。这两种构想所针对的事态在烈度上明显不同。(37)日本防卫研究所的高桥杉雄也指出,虽然美、日都强调威慑,但威慑方式不一样。对美国来说,其在亚太地区的现有海空力量仍占有绝对优势,在短期内足以起到威慑作用,因而没有必要扩大可能刺激中国,同时也增加己方风险的前沿部署;而对日本来说,中国通过非武力手段在东海和南海争端中渐进地改变现状是最迫切的问题,因而,当务之急是加强包括西南诸岛在内的前沿部署及日美在这方面的合作。在高桥看来,前者可能减弱对中国的威慑力度,后者可能加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在战略上是相互矛盾的。(38) 可见,日、美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战略和战术考虑。对此,加藤洋一不无疑虑地指出,尽管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2012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宣布,到2020年,美国将把其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军力量的部署比例从50%对50%调整到60%对40%,但他在宣布这一计划的同时强调,美国重返亚洲不是对中国的挑战。在加藤看来,美国虽然在政治上对中国不信任,但在军事上难以维持迄今的压倒性优势,因而不得不采取温和的策略。尽管美国国内的保守派依然坚持制衡中国的立场,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也从起初的重视接触偏向了重视制衡,但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向对华强硬路线仍不可预知。(39) 从日本的上述反应中可以看出,尽管对美国“转向亚洲”的前景及其对日本的影响看法不同,但对美国在军事上制衡中国的期待却是一致的。不仅如此,日本国内在解读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意义时,也倾向于强调其地缘政治意义,而不仅仅是经济意义。2010年10月,日本政府就研究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首次表态之时,恰好是在中日发生钓鱼岛撞船事件后不久,由此可见,日本对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可能带来的安全利益的考虑。到2015年4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时更是明确表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超越经济利益的长期安全保障领域具有重大意义”,以此呼吁美国国会通过《贸易促进授权法案》(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简称TPA)。(40)事实上,早在2010年底,前外务省事务次官、后来担任日本政府新设的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的谷内正太郎就撰文强调,日本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意义不只在经济方面,而且涉及安全保障方面,日本面对中国军力的急速上升,在战略上的唯一选择就是维持太平洋同盟网。(41)几乎同时,曾担任外务省副报道官、后来又出任第二次安倍政权负责宣传的内阁审议官的谷口智彦也明言,对日本来说,讨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不应只看经济得失,而应关注日本的安全保障和国家特性问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可以和由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的菱形同盟相配合,构成海洋民主国家联盟,共同牵制中国的海上通道。(42)此外,庆应义塾大学的田所昌幸教授也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不仅有促进自由贸易的一面,而且有外交战略的一面,是美国介入地区事务的手段;对日本来说,在有美国加入和没有美国加入的两种地区经济秩序之间,显然应该选择前者。(43)前经济产业省经济产业审议官、三菱商事董事今野秀洋同样认为,日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兼具经济意义和地缘政治意义,后者毫无疑问是针对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呼应美国的亚太战略。但他同时强调,绝不能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冷战年代对苏联的遏制相提并论,现在的中国应该是接触而非遏制的对象。(44) 可见,一方面,日本对美国“转向亚洲”的战略寄予厚望,期待美国制衡中国;另一方面,又担心这一战略会因为美国削减国防预算或重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而变得有名无实。对此,《日本经济新闻》的评论员秋田浩之分析道,从财政能力看,美国目前的国防预算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低于冷战时期的7%-8%,所以美国只要有意愿,还是有能力实施其国防战略的;但问题是,与当年的苏联不同,中国现在已经是美国的重要经济伙伴,美国即使有财力,国内民众也未必会支持对亚太地区的持久军事投入,所以,美国对亚洲的介入可能会发生动摇。(45)实际上,不仅美国要顾及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美国的盟国也日益重视对华关系中的经济利益。加藤洋一以澳大利亚为例,指出在美国的盟国中也出现了怀疑美国能否维持优势或领导地位的声音。(46) 如果说美国的“转向亚洲”或者“亚太再平衡”(rebalance toward the Asia-Pacific)战略在提出之时因缺乏具体措施而让日本感到疑惑,那么,这一战略在实践中进展不顺,就更让日本感到失望了。上述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针对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日本受访专家的基本看法是:这是一项正确的政策,但缺乏资源、实施乏力。(47)日本共同通信社的评论委员长会田弘继对此揶揄道,日本和其他邻国本来指望美国“转向亚洲”能减轻它们对中国军事崛起的担忧,但这一战略很快改名为“再平衡”,似乎是出于对中国敏感性的高度谨慎;而大吹大擂出台的“空海一体战”概念除了五角大楼里一个传闻中“布满蜘蛛网的房间”之外,似乎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结果;甚至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新设的海军陆战队轮换驻扎基地,看起来也像是为了避开中国的力量投送。(48)《日本经济新闻》的总编辑春原刚也指出,随着国务卿克林顿和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的离任,从第二届奥巴马政府一开始,“转向亚洲”战略就失去了以往的势头,这至少意味着在白宫政治意志的层面上,“转向亚洲”几乎成了纸老虎。在此局面下,日本不得不担心美国在亚洲政策上领导力的显著下降。(49)事实上,在2015年“香格里拉对话”期间,美、日就暴露出双方在地区问题上的看法并不一致。会前,日本官方和媒体都预计美国会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展现强硬姿态,但与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会议开幕前就明言不会对中国说“硬话”,其主旨演讲也被认为是低调、平衡的,这让与会的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高木诚一郎感到失落。(50) 在日本分析家眼中,美国除了受到财政困难、民意内向、中美关系复杂性和中东局势恶化等因素的掣肘外,奥巴马政权自身的政治意志也颇成问题。《读卖新闻》在社论中指出,奥巴马总统在2013年的国情咨文中没有谈到亚太战略的内容和对中国的定位;2014年的国情咨文虽然提到了亚太战略,但语气冷淡,而且奥巴马连续两年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首脑会议。(51)久保文明教授分析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奥巴马本人缺乏信念,存在优柔寡断、不坚决表态、避免与对手冲突、在使用武力上犹豫不决等倾向。特别是约翰·克里接替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以后,对“转向亚洲”的关心减少了,对中国的顾虑增加了。在他看来,国务卿一换人就导致外交基调发生变化,这恰恰暴露了总统本人没有坚定的原则。(52) 总之,日本的分析家们虽然对美国霸权的未来并不悲观,但对美国霸权的当下却难掩焦虑。究其原因,在于近年来中国实力的上升和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激化,使日本对自身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感到前所未有的不安甚至威胁。而美国又恰在此时调整外交战略,名为“转向亚洲”,实际却已转向国内或仍留在中东。特别是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摇摆不定,甚至萌生退意,让日本深受震动。 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冲击 作为美国的盟国,日本长久以来一直面对“被卷入”或“被抛弃”的同盟困境。在21世纪最初的几年里,日本虽然支持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但主要担心的仍然是美国的单边主义,不愿意“被卷入”美国的战争。(53)但近年来,随着中美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和相互依存的深化,日本对“被抛弃”的担忧日渐明显。在日本看来,如果真的出现美国不能或不愿支持日本的情形,要么是因为美国实力相对衰落,无力施援;要么是因为美国更重视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无心相助。如上文所述,日本对前者虽有担心,但认为只是暂时的;而对后者则是深感忧惧,因为那意味着日本战略地位的根本受到动摇。 日本对中美接近的担忧由来已久。从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基辛格背着日本与中国和解,到90年代克林顿总统访华时不在日本停留,日本一直担心被美国的“越顶外交”抛在一边。但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日本所担心的,除了日美关系内部的摩擦之外,主要是在对华关系上落在美国后面,因为对于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日本的态度原本就是支持甚至更为积极的。然而,这种情况在21世纪初发生了显著变化。中日关系先是因历史问题、后又因钓鱼岛问题严重恶化。尽管日本仍然重视中国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也仍然不愿意看到中美发生冲突,但在中日关系恶化的形势下,美国站在哪一边变得至关重要。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感到了遭美国背弃的风险。 以美国对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政策为例,美国官方虽然反复宣称钓鱼岛处于日本的管辖之下,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范围,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但同时表示在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这让不少日本人感到失望和不满。2013年11月,中国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美、日虽然都表示不承认,但日本要求中方撤回,美国却没有这么做,还让各民航公司自主提交飞行计划,这令日方迷惑不解。(54)2014年4月,奥巴马访日,虽然在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了美国对钓鱼岛的安全承诺,但日本媒体立即注意到,他的发言与日本政府的期待有异。奥巴马不仅强调钓鱼岛问题的和平解决,要求中日双方避免挑衅,寻求合作,并采取建立信任的措施,而且还不忘向日方指明美国和中国也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55)对此,日本有评论认为,奥巴马的表现实际上就是无能为力。(56)日方还注意到,在2015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奥巴马在和习近平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赞赏中日紧张关系的缓和,并称美国也在推动同盟国与中国加强关系。在日本观察家看来,奥巴马是通过对中日首脑会谈的支持,公开否定了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57) 日本对中美关系反应敏感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近年来,每次中美关系中出现指向合作的新概念时,日本都如芒刺在背;而每次中美关系出现波折时,日本都如释重负。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发表演说,在对华政策上提出著名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概念,很快在日本国内引起不安。《中央公论》甚至以“美国抛弃日本之日”为题刊发专题讨论文章,指出在看似顺畅的日美关系背后,两国在美军基地、靖国神社和对华关系等问题上的分歧已开始显现,一旦首相小泉纯一郎离任,由小泉和布什建立起来的日美紧密关系将随之消失。有学者认为,“利益攸关方”一词已在美国2006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第二届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使用,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词,这使得中国可以借用美国的影响力对日施压;如果中日以美国为舞台围绕历史问题展开舆论竞争,会对日本相当不利。(58)但是,也有学者注意到,“利益攸关方”的概念既可以为对华强硬政策,也可以为对华温和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如果考虑到佐利克不久将辞职的前景,那么,中美关系可能再次陷入不稳定,所以日本不必担心被中美战略关系的强化排除在外,日本应该做的是比中国早一步承担起“利益攸关方”的责任。(59)还有学者从经济层面分析了中美关系变化对日本的影响,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相比于日本,美国自然会在经济外交上更重视中国,但日本经济有足够的规模和技术水准维持自身的增长,对美国来说可以成为平衡中国的力量,因此不必担心美国会无视日本,应保持冷静的态度。(60) 继“利益攸关方”之后,2008年和2009年美国方面又传出了有关“两国集团”(G2)和“中美国”(Chimerica)的说法。尽管这两个概念并非出自美国官方,但奥巴马总统上台之初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相当积极的态度,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了中美“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的构想。这让日本的观察家们感到中美关系“两国集团”时代正在到来。对此,日本国内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有观点认为,对美国来说,与中国的关系越重要,作为美国亚洲政策“基石”的日美同盟也就越重要。(61)原因是,美国对华外交有两面性,一方面尽量不与中国冲突,另一方面视中国为竞争对手,为此,必然要加强日美同盟的力量。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美国把东亚作为优先考虑的话,或许会重视日美同盟,但眼下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中东,在那里与中国的合作比与日本的合作更有价值。(62)还有专家对中美关系作了冷静的前瞻,认为日本应该学习的不是中美在表面上的“两国集团”动向,而是中美在暗地里的相互试探和高超的政治手腕。美国的对华战略是灵活运用“包容”和“警戒”两种手段的模糊战略,现在是把前者推向前台,将来任何时候都可能转向后者。(63) 随着2009年末以后奥巴马政府在对华政策上转向相对强硬,日本的分析家们又很快恢复了对日美同盟的信心。东京大学的北冈伸一教授认为,基于“两国集团”路线的中美合作论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曾一度高涨,但很快幻灭了,而日本的重要性相对来说正在上升。(64)前外务省事务次官薮中三十二也认为,美国提出“利益攸关方”论后,没有得到中国的积极回应,于是再次把目光投向日本,特别是2010年9月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表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使美日同盟的重要性再次得到确认。(65)等到2011年美国推出“转向亚洲”战略,日本对中美接近的焦虑进一步缓解。然而,也有日本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指出中美“两国集团”关系虽然是包含了一系列难题的同床异梦,但中美在经济、安全领域的战略对抗会继续受到抑制,即使局部出现摩擦也会限制在战术层面。(66) 然而,对日本冲击最大的还是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向。比起美方提出的“利益攸关方”“两国集团”“战略再保证”等说法来,日本对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倡议如临大敌。有日本学者注意到,中国早在2012年初就正式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但美方起初持谨慎和怀疑的态度;而从2013年秋开始,美国政府显示出了对这一概念的积极态度。在2013年9月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奥巴马总统在与习近平主席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称,两国就构筑“新型大国关系”达成了一致,首次公开接受这一提法。同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在一次演讲中更是明确提出,美国致力于将“新型大国关系”付诸实施(operationalize)。(67)对此,久保文明教授担忧地说,和此前的“核心利益”概念一样,直接使用中国提出的概念和词汇本身就有危险,更不要说将其“付诸实施”了。(68)《朝日新闻》前总编船桥洋一则指出,中国早晚要让日美同盟从属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他看来,过去中国之所以容忍日美同盟,是想借助美国的力量控制日本;如今中国想把“日本问题”也纳入“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与美国协商和共同管理,这当然会损害日本的利益。因此,日本的当务之急是,揭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假象,让中国的这一战略失去力量。(69) 日本为什么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反应如此强烈呢?原因有三点:第一,日本担心其国家安全利益受到直接的损害,因为中国每次说到“新型大国关系”,几乎都会提出中美应该相互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而中国政府已经表明钓鱼岛包含在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中,这就意味着要让美国尊重中国在钓鱼岛的主张,对此,日本自然要坚决反对;第二,日本感到在如何认识和应对中国的问题上,日美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扩大,美国虽然在安全上加强了对中国的防范,但在经济上把中国视作比日本更重要的伙伴,在朝鲜、伊朗、叙利亚等地区问题和气候变化、能源等全球问题上,美国都需要中国的合作;(70)第三,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如果美国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提议,那就说明比起强化美日同盟提升对华威慑力来,美国政府更热衷于推进与中国的合作,这实际上与美国的“转向亚洲”战略相矛盾,因为“新型大国关系”是以世界的多极化为前提的,而“转向亚洲”则终究是以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为前提的。(71) 可见,对日本来说,美国是接受“新型大国关系”,还是推进“转向亚洲”战略,既关系到主权和安全之争,也关系到国际地位和世界秩序之争,其影响非同小可。然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真的只是假象吗?如上文所述,确有日本分析家注意到了中美关系中战略协调和分歧管控的能力,但大多数意见仍然更多地强调中美之间的矛盾,这显示出日本对中美关系的战略性认识不足。 从上述日本对美国实力和政策变化的反应看,日本的担忧主要包括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从短期看,日本担心当前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会在亚太地区留下权力真空,从而弱化对中国的制衡与威慑,损害日本的安全利益;从长期看,日本担心中美战略关系会取代日美同盟,在未来的亚太国际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从而动摇日本几十年来通过追随美国而在该地区享有的优越地位。针对这两种担忧,日本学者提出了相应的新对策和新理念。 在短期方面,“活用”日美同盟成为不少人提倡的政策选择。(72)在日本看来,不论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如何变化,日本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而美国受到财政紧缩等因素的制约也无法单独实施其亚太安全战略,因此,强化日美同盟仍是日本对外战略的基轴。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日本不应该仅仅被动地承担美国所给予的任务,而应该主动地利用日美同盟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服务,同时利用自身所处的地缘政治位置配合美国的国防战略。为此,日本的一些防卫问题专家将中日钓鱼岛争端解读为中国挑战美国地位、推进“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的一个环节,提出日美应该就岛屿防卫加强能力建设,并制定详细的联合作战计划。(73)也有专家提出,应该配合美国的对华军事政策,构筑日本版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体制。(74)甚至还有人提出,可以重新考虑以往美国是“矛”、日本是“盾”的任务分担,让日本自卫队‘补充美国的攻击能力,比如,以日美合作为前提讨论日本保有对敌方基地进行攻击的能力等。(75) 与“活用”日美同盟相呼应,一些学者还提出了“日美+α”的同盟扩展战略。(76)在他们看来,日本应该加强与美国的其他同盟国、伙伴国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以配合美国将其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从“轴辐型”(hub-and-spoke)转变为“网络型”的战略。这么做既可以弥补美国投入的不足,制衡中国的力量,也可以扩大日本的地区影响力。(77)还有学者基于实力对比的预测指出,到2030年,美日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可能会略低于中国,为了制衡中国,有必要将其他国家纳入新的地区均势中来,这包括构筑美日印、美日印澳等多边安全架构,以及把“东亚”概念扩大到“亚太”乃至“印太”概念等的尝试。(78) 从长期看,不少学者认为日本应该探索认识国际体系的新范式,并寻找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新身份。在他们看来,国际秩序演变的趋势是:美国仍将维持其主导地位,但新兴国家的崛起必然带来国际秩序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在亚太地区可能最为明显。为了适应这一形势,有学者提出了“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复合体”的新范式。他们认为,国际体系正在走向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相互渗透、长期共存的新模式。这两类国家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因而合作的必要性极大;但在政治和安全上分歧明显,因而有可能发生对抗。(79)这将是一个保留了单极构造,同时包含若干自主势力范围的“单极—多极复合体”。其中,中美将在亚太地区形成两极体系,双方的竞争与合作将长期存在。(80)而维系这一秩序的机制主要是威慑和危机管理。(81)在这一新的秩序中,日本已经不能再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达国家的一员”“西方国家的一员”等身份为依据制定大战略了;而应该在“和平国家”身份的基础上增加积极性,以“发达的稳定势力”作为新的国家身份,在此基础上推动“大国协调”和“地区协调”。(82) 还有学者提出,日本应该构建“安静的威慑力”(quiet deterrence),作为应对亚太地区权力均衡巨大变化的新概念和新战略。其主旨是:一方面,加强日本自身的防卫能力和日美同盟的介入能力,构筑包括澳大利亚、印度、韩国和东盟等国家和地区在内的、贯穿印度洋和太平洋漫长海岸线的“海洋国家联盟”;另一方面,避免不必要地刺激中国,寻求与中国建立危机管理和战略沟通的机制。(83) 可以看出,上述政策建议和战略构想在事实判断和逻辑思考方面具有很大程度的共通性,这反映了日本国际问题研究者中正在形成的主流看法,而这样的看法与日本政界日渐兴起的战略新思维也相当地一致。正如美国的国际安全与日本问题专家理查德·萨缪尔斯(Richard Samuels)所指出的,进入21世纪以来,主张改变“吉田路线”的修正主义者已经取代传统的实用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成为日本战略讨论中的新主流,即便新的共识尚未形成,但至少新的话语已经产生,而变化的趋势是赋予日本更大的自主性和更强的能力。(84) 事实上,上述新思维和新话语中已经有不少转化成了日本政府的新政策。早在2010年民主党执政时期,日本政府就提出“动态防卫力”构想,取代了1976年以来的“基础防卫力”构想。而在当年的中日撞船事件之后,日本明显倒向了美国,此后在一系列安全问题上积极与美国合作。2012年底,以安倍晋三为首的自民党上台后,强化和加速了这种借力美国、制衡中国的战略,除采取增加防卫预算、增强军事装备及部署等强军措施外,在对美关系上通过更改宪法解释解禁了集体自卫权,与美国制定新的防卫合作指针,最终在国会强行通过了安保法案,使日本自卫队能够在更多的领域更加主动地配合美军的行动。与此同时,不管是民主党政权还是自民党政权,都积极地推动与菲律宾、越南、新加坡、澳大利亚、印度等亚太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安倍政权还推出“俯瞰地球仪”外交,遍访世界各国,以“远交近攻”的策略抵制在对日政策上日益强硬的中国和韩国,有学者称之为“安倍地缘政治学”(Abegeopolitics)。(85)可见,日本政府在自助、结盟和多边合作这三种基本的安全手段上都做出了敏锐的调整,表现在对美关系上就是:借美国之力以制华,强自身之力以助美。 需要强调的是,日本的这种政策倾向不仅代表了安倍个人或者自民党的政见,而且反映了存在于当前日本政界的相当程度的共识,安倍只是给这些新政策增添了民族主义的色彩。这种共识是:在美国倾向孤立、中国更趋进取的时代,日本必须警惕、机敏和主动作为。日本官方将这种新的政策倾向表述为“积极的和平主义”。因此,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日本防卫力量和日美同盟的强化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不过,日本的上述政策倾向能在多大程度上付诸实施并取得效果,还存在很多限制因素。一方面,日本在安全政策上变得积极主动,有助于美国在削减军费的情况下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地位,这固然能得到美国的支持;但另一方面,美国的利益是稳定地区局势,而不是帮助日本强军,因而在钓鱼岛问题上一方面表明作为盟国的承诺,另一方面要求日本保持克制,在历史问题上更是有意约束日本。所以,日本要“活用”日美同盟、让美国为其撑腰并非易事。而日本的同盟扩展战略和“远交近攻”的地缘政治外交也面临障碍。这表现在:安倍在历史问题上的倒行逆施严重损害了日本与韩国的关系,连美国也很不满意,以至多次施压;第一次安倍政权企图推动的美、日、印、澳“四国同盟”无果而终,而随着印度、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更趋紧密,在当前或未来要纠集针对中国的多边安全架构就更不可能了。即便是美国也不愿意在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中明确提及中国。同时,在日本国内,民意也不支持政府的新安全政策,声势浩大的反对安保法案的运动就是明证。在此背景下,日本的战略转型虽然方向明确,但步伐只能是渐进的。 更为根本的问题是,不论是日本学者提出的新概念,还是日本政府推行的新政策,都没能真正提供处理对华关系的良方。不管对美国还是对日本来说,中国问题在过去、今天和未来都是它们关系中的核心问题。(86)尽管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日本和美国在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国问题上的分歧,但相当一部分人仍然把中国看作威胁日本的他者,仍然把日本的身份定位在相对于中国的差异和优越性上。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所谓“安静的威慑力”或者“发达的稳定势力”在实践中就很难带来真正的安静和稳定,所谓“大国协调”或“地区协调”也无从建立。日本如果真要寻求战略上的自主性,那么,不论是在对美认识还是在对华认识上,都还需要有更理性、更包容和更长远的眼光。 *本文初稿曾提交《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感谢与会学者对论文提出的很多宝贵意见,同时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的细致审读和修改建议,但本文错误与疏漏之处完全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关于日本国内政治变化对日本安全政策的影响,参见Adrew L.Oros,"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Challenges to Japan's Postwar Security Identity:'Norm Constructivism' and Japan's New 'Proactive Pacifism'," The Pacific Review,Vol.28,No.1,2005,pp.139-160。 ②认知层面的变化往往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一定有明确的起始时间。本文重点讨论的是近年来日本对“美国衰落论”、美国“转向亚洲”战略和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等事态的反应,因而将研究的时间段限定为从2009年至今。当然,就具体过程而言,由美国实力或政策变化及中美关系变化引起的日本对美认知的变化可以追溯到21世纪初甚至更早的时期,本文在讨论部分具体问题时也会提及2009年前的变化。 ③尽管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能无视民意,但就影响力而言,精英的态度还是比大众的意见重要得多。因此,本文把研究重点放在对政策和舆论有影响力的学者的观点上。 ④亀井俊介『アメリカの心 日本の心』日本経済新聞社、1975年、亀井俊介『日本人のアメリカ論』研究社、1977年。 ⑤吉見俊哉『親米と反米——戦後日本の政治的無意識』岩波書店、2007年。 ⑥鈐木晟「日本人の対米観·序論——『阿闍世コンプレツクス』の視点から」『社会科学討究』1990年8月号、1-21頁。 ⑦西平重喜「日本人の対米観アメリカ人の対日観」『自由』1982年1月号、32-52頁。 ⑧伊藤述史「反米保守主義のアメリカ批判——戦後史評価の諸相」『アソシェ』第19号、2007年8月、141-151頁。 ⑨田所昌幸「反発と甘ぇの交錯——日本の対米観を考ぇゐ」『 アステイオン』第59号、2003年、105-121頁。 ⑩土山実男「日米同盟におけゐ『忠誠と反逆』——同盟の相剋と安全保障ディレンマ」『国際問題』2015年9月号、13-14頁。 (11)刘世龙:《日美关系的两个周期》,《日本学刊》2002年第3期,第30-31页。 (12)张建立:《战后日美关系的心理文化学解读》,《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4期,第35-49页。 (13)「国際情勢と日本外交の)課題」『国際問題』2011年4月号、26-53頁。 (14)小林陽太郎「オバマ7大統領とアメリカ文明衰亡論」『国際問題』2011年3月号、2頁。 (15)三浦俊章「アメリカぃまだに決着をつけられなぃ問ぃ」『外交』2011年9月号、53頁。 (16)春原剛「オバマ外交の現在」『国際問題』2014年4月号、5頁。 (17)中西寬「国際社会を待ら受けゐ均衡と軋轢の半世紀」『中央公論』2009年2月号、116-118頁。 (18)小林陽太郎「オバマ大統領とアメリカ文明衰亡論」『国際問題』2011年3月号、3頁。 (19)北岡伸一「主要国間協調の時代におけゐ日本の)責務」『中央公論』2009年2月号、106-107頁。 (20)中西寬「国際社会を待ら受けゐ均衡と軋轢の半世紀」、122頁。 (21)渡辺靖「米国衰退論をどぅ見ゐか——ブレマ一氏の論考を手掛かりに」『外交』2012年11月号、34頁。 (22)長山靖生「オバマ新政権への期待」『中央公論』2009年1月号、162頁。 (23)古矢旬「米国衰退論の現在——背後に潜む文明的問ぃ掛け」『外交』2012年11月号、54-58頁。 (24)梅本哲也「オバマ政権の世界観と米国の外交·安全保障政策」『国際問題』2013年3月号、51頁。 (25)会田弘継「『米国衰退論』は時代を画す——停滞の時代に繰り返されゐブ一ム」『外交』2012年11月号、27-28頁。 (26)孫崎享『これからの世界はどぅなゐか——米国衰退と日本』筑摩書房、2013年、243頁。 (27)松尾文夫、吉崎達彦、渡部恒雄「(座談会)オバマ新政権の布陣にみゐアメリカのかつてなぃ切迫感」『中央公論』2009年2月号、143頁。 (28)高原明生「回答を読んで」『国際問题』20n年4月号、54頁。 (29)Michael J.Green and Nicholas Szechenyi,"Power and Order in Asia:A Survey of Regional Expectations," A Report of the CSIS Asia Program,July 2014,pp.7-8,http://csis.org/publication/power-and-order-a-sia,2015-03-02. (30)Pew Research Center,"China Seen as Overtaking U.S.as Global Superpower," July 13,2011,http://www.pewglobal.org/2011/07/13/china-seen-overtaking-us-as-global-superpower/,2015-01-30; Pew Research Center,"People Think China Will or Already Replaced U.S.as Superpower," June 22,2015,http://www.pewglobal.org/2015/06/23/global-publics-back-u-s-on-fighting-isis-but-are-critical-of-post-911-torture/bop-report-17/,2015-07-30. (31)加瀨みき「中国にも同盟国にも国民にも舐められゐアメリカの暗ぃ世紀と暴走すゐ世界」『中央公論』2011年3月号、153頁。 (32)Pivot to Asia,又译“重返亚洲”。 (33)中嶋嶺雄「米中『新冷戦』と日本」『環』2013年冬季号、156-157頁。 (34)大野正美、久保文明、国分良成、田所昌幸「(座談会)『政治不信の時代』の外交」『外交』2012年1月号、39頁。 (35)森本敏「米国のアジア重視政策と日米同盟」『国際問題』2012年3月号、38、42頁。 (36)加藤洋一「米国の『アジア回帰』とオスプレイの沖縄配備」『外交』2012年9月号、100-101頁。 (37)加藤洋一「国際環境の変化のなかの日米同盟」『国際問題』2012年1·2月号、36頁。 (38)高橋杉雄「財政緊縮下の米軍と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の抑止態勢」『国際安全保障』2013年12月号、75-76頁。 (39)加藤洋一「米国の『アジア回帰』とオスプレイの沖縄配備」、102-103頁。 (40)《安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对二战表示“痛彻反省”》,共同网,2015年4月30日,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4/96671.html,2015-04-30。 (41)谷内正太郎「TPP参加は『強ぃ安保·経済』への分水嶺」『ウェツジ』2011年1月号、8-10頁。 (42)谷口智彦「TPPと『同盟ダイヤモンド』拡張中国への抑止力」『中央公論』2011年3月号、140-145頁。 (43)大野正美、久保文明、国分良成、田所昌幸「(座談会)『政治不信の時代』の外交」、41頁。 (44)今野秀洋「通商政策の転換——GATT/WTO体制からFTA·TPPへ」『国際問題』2015年1·2月号、42-43頁。 (45)秋田浩之「せめぎ合ぅ米中アジア太平洋勢力圏の攻防(下)」『外交』2012年7月号、110-111頁。 (46)加藤洋一「国際環境の変化のなかの日米同盟」、40頁。 (47)Michael J.Green and Nichdas Szechenyi,"Power and Order in Asia:A Survey of Regional Expectations," p.11. (48)Hiro Aida,"America Self-Contained?" The American Interest,Summer(May/June) 2014,pp.20-21. (49)春原剛「オバマ外交の現在」、7-8頁。 (50)郭丝露、赖竞超:《硬派防长柔软外交》,《南方周末》2015年6月4日。 (51)「オバマ演説『北の核』対処へ行動が肝心だ」『読売新聞』社説、2013年2月14日;「オバマ氏演説そっけなかった『アジア重視』」『読売新聞』社説、2014年1月30日。 (52)久保文明「オバマ外交のヴィジョン——ぁゐぃはオバマ外交にヴィジョンはぁゐか?」『国際問題』2014年4月号、2-3頁。 (53)Kenneth B.Pyle,Japan Rising: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7,p.352. (54)春原剛「オバマ外交の現在」、9頁。 (55)「日米首脳会談 アジアの礎への一步を」『朝日新聞』社説、2014年4月25日。 (56)水本達也「オバマが描くアジア太平洋の秩序——対中外交の理想と現実が交錯」『外交』2014年7月号、80-83頁。 (57)水本達也「『日中』『米中』首脳会談の評判——ワシントンの冷たぃ目」『外交』2015年2月号、88-89頁。 (58)吉崎達彦「劣勢、日中広報線戦争の挽回なゐか」『中央公論』2006年7月号、107-111頁。 (59)島村謙司「米国の対中新政策は日本素通りか」『中央公論』2006年7月号、126-134頁。 (60)齋藤進「やがて世界は覇権なき多極化を迎ぇゐ 迫り来ゐドル凋落と中国の重み」『中央公論』2006年7月号、146頁。 (61)坂元一哉「日米同盟の課題——安保改定50年の視点から」『国際問題』2010年1·2月号、25-26頁。 (62)岡崎久彦、孫崎享「漂流前夜 日米同盟の運命を徹底検証すゐ」『中央公論』2009年7月号、55-56頁。 (63)春名幹男「米中G2時代に求められゐ戦略なき日本からの脱却」『ェコノミスト』2009年9月15日、87頁。 (64)北岡伸一「日本外交の座標軸——外交三原則再考」『外交』2011年2月号、15頁。 (65)藪中三十二「中国の台頭がさらなゐ变化をもたらす」『中央公論』2011年10月号、90頁。 (66)茅原郁生「安全保障から見た米中関係——二○一二に向けたG2時代の行方」『海外事情』2010年6月号、34、42頁。 (67)加藤洋一「米中『新型大国関係』の虚実と日本——米『アジア回帰論』との矛盾を問ぅ」『外交』2014年3月号、105-106頁。 (68)久保文明「オバマ外交のウィジョン——ぁゐぃはオバマ外交にヴィジョンはぁゐか?」『国際問題』2014年4月号、3-4頁。 (69)船橋洋一、北岡伸一「対談『積極的平和主義と静かな抑止力』をめぐって」『外交』2014年5月号、88、94-95頁。 (70)田中均「東アジアの構造変動と新思考外交——重層的機能主義を」『外交』2014年1月号、123-124頁。 (71)加藤洋一「米中『新型大国関係』の虚実と日本——米『アジア回帰論』との矛盾を問ぅ」、104-107頁。 (72)「国際情勢と日本外交の課題」『国際問題』2011年4月号、39-41頁、長島昭久『「活米」とぃぅ流儀外交·安全保障のリアリズム』講談社、2013年。 (73)香田洋二「日本海洋戦略の課題——米中の安全保障政策·戦略と我が国の対応策」『国際安全保障』2014年6月号、34頁。 (74)永岩俊道「米国の対中軍事戦略と日本の対応——日本版『接近阻止·領域拒否戦略』体制の構築」『国際安全保障』2013年6月号、67-68頁。 (75)「敵基地攻擊能力 日米連携前提に保有の検討を」『読売新聞』社説、2013年5月18日。 (76)别所浩郎、伊藤隆敏、神谷万丈、添谷芳秀、山本吉宣「(座談会)国際情勢の動向と日本外交」『国際問題』2011年1·2月号、16-17頁。 (77)白石隆「膨張中国VS米新安保戦略——『海の帝国』再論」『外交』2012年5月号、38-46頁。 (78)神谷万丈「東アジア地域秩序の動向——リアリズムの立場から」『国際問題』2013年7·8月号、11-12頁。 (79)山本吉宣「新興国の台頭におもぅ——從属の逆転?」『国際問题』2013年1·2月号、3-4頁。 (80)山本吉宣「先進国一新興国複合体の秩序構築へ——日本外交の長期戦略」『外交』2012年1月号、27-30頁。 (81)納家政嗣「新興国の台頭と国際システムの変容」『国際問題』2013年1·2月号、14頁。 (82)PHP「日本のグランド· ストラテジ一」研究会事務局「『先進的安定化勢力·日本』のグランド·ストラテジ一一『先進国/新興国複合体』におけゐ日本の生き方—」PHP研究所、2011年6月、16-26頁。 (83)日本再建イニシアティブ日米戦略亡ビジョンプログラム『静加かな抑止力』日本再建イニシアティブ、2014年、24-25、66頁。 (84)Richard J.Samuels,Security Japan: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7,p.37. (85)Takaski Inoguchi,"The Rise of 'Abegeopolitics':Japan's New Engagement with the World," Global Asia,Vol.9,No.3,Fall 2014,p.31. (86)Walter LaFeber,The Clash:U.S.-Japanese Relations throughout History,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97,p.5.标签:美国军事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经济学论文; 太平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