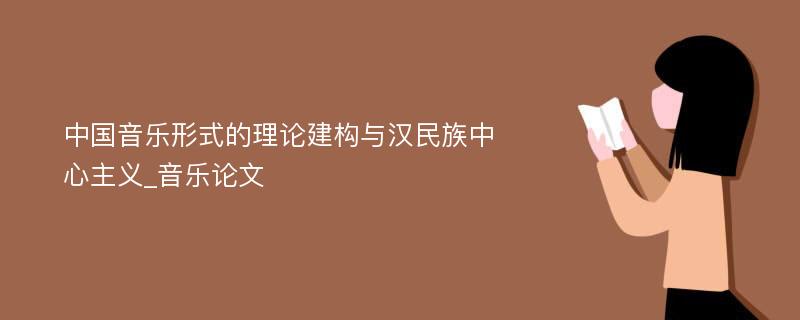
中国音乐形态理论建设与汉族中心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族论文,中国音乐论文,形态论文,理论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在近年发表的一篇中文文章中谈及后殖民主义理论时曾指出,中国学者们在学术研究中批判欧洲中心论、试图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同时,也应该注意不要走入另一极端、陷入中国中心论以至汉族中心论的泥潭。我在该文中提醒道:“在汉文化中熏陶或教育出来的学者们是否会循着汉文化的思路去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化或沿此思路去试图总结或创建少数民族的体系?比如说,学者们是否会将汉族体系认为是包括中国各民族在内的中国体系,并且试图用这样的体系来解释中国各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注:杨沐《当代人类学中有关音乐研究的几个问题》,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通过众多音乐工作者与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从20世纪中期开始,在中国大陆逐步形成了被统称为“民族音乐理论”的一整套分析描述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形态的理论,包括歌、乐种分类、音阶、调式、曲式甚至和声(注:以下举出数例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此类理论著述:黎英海《汉族调式及其和声》,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于会泳《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上海音乐学院1963年油印资料本,第一部分发表于韩钟恩主编《音乐人文叙事》年刊创刊号,1997年。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民族音乐概论》(音乐出版社1964年版)。赵宋光《论五度相生调式体系》(上海文化出版社1965年版)。高厚永《民族器乐概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江明敦《汉族民歌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李西安、军驰《中国民族曲式》(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版)。)。在20世纪后期又有学者在此基础之上构想出“民族音乐形态学”(注:如赵宋光《对民族音乐形态学的构想》,载《广州音乐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中国学者萧梅、 韩钟恩认为这一套体系之内其实包括了两种不同的路向,其一是循西方古典作曲技术理论的思维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音阶、旋法、调性、调式、曲式等方面的分析,虽然使用了中国术语,其本质是欧洲中心论的;另一是以中国传统乐学—宫调理论为主要依据,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音体系上的全面梳理,其性质是确认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的不同;而二者又都标以基础理论学科的名义,都只着眼于音乐本身即音体系的分析,都只为创作、表演服务,而基本上与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无关(注:萧梅、韩钟恩《音乐文化人类学》(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我在这一方面的看法与萧、韩稍有不同。我认为在上述理论体系中萧、韩所说的这两种路向固然能被大致分辨得出来,但其实它们又是错综纠结,并非在源、流两方面都是泾渭分明的。我认为这两种路向的存在与分野,是萧、韩二人以音乐人类学者应具的学术敏感而侦辨出来的,而那些纯音乐形态基础理论学者们自己却很有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至少,从这些基础理论学者们的著述来看,他们都认为自己所建设的是与西方体系不同的中国体系,在这一点上看不出他们之间有歧见或自认有学派之分,也看不出后者认为前者的思维本质是欧洲中心论的。如果把前者称为“民族音乐理论”派,把后者称为“民族音乐形态学”派,则从一些学者在近几十年间的教学与著述来看,他们其实可被看作是这两个“流派”的两栖学者。在努力建设中国自己的音乐形态学的数十年过程中,许多学者其实在起步时就是循着前一路向的,但其中一些人在其后多年的理论建设过程中逐步地越来越向中国传统乐学靠拢,然而始终并未完全与前者分野。同时,至今为止仍然有些著述其实是上述两“派”观点的大拼盘(注:例如杜亚雄《中国民族基本乐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这种情况,并不像萧、韩二人所说的那么简单,仅是“由于表层上的共同点,使得一部分原来从事‘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的人员,想当然地将自己转入‘民族音乐形态学’的研究队伍,从而掩盖了研究方法上的不同及研究成果(对象的确立)上的不同”。我认为,20世纪中期的“民族音乐理论”与后期的“民族音乐形态学”在方法与成果上虽有不同,但二者其实有着比“表层上的共同点”更深更复杂的渊源关系与共生关系。
本文的论题是中国音乐形态理论建设与汉族中心论问题。在对有关情况作过如上说明之后,我就暂不深究上述的“派别”是否存在,因为这跟我现在要讨论的汉族中心论问题的直接关系不大。相对于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上述“民族音乐理论”派也好、“民族音乐形态学”派也好,都可以被看作是属于一个阵营、一个体系。20世纪下半叶在中国大陆,这一套主要为作曲与表演服务的纯音乐形态理论体系不但被所有音乐院系的中国音乐形态理论教学所采用,而且也被几乎所有的音乐工作者和音乐学者应用于工作与研究中。比起早期学者原封不动地使用欧洲古典专业作曲技术理论来分析中国音乐形态的作法,这套体系被应用于汉族音乐分析应当说是历史性的进步。建设一套理论体系是很困难的巨大工程,我们不应苛求完善。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基本上是汉族音乐形态的理论却在中国学界被普遍地称为“中国民族音乐理论”或“民族音乐形态学”,并被使用于分析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表述这套汉族理论的著述大多数也被冠以“民族民间音乐理论”或“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之类的标题或书名,显示出包括这些论著作者在内的中国学者们相当一致地认为这种理论涵盖了整个中国各民族的音乐形态或是尚未注意到这种提法的误导性。虽然学者们都知道中国多民族多元文化共存的事实,但却似乎没有人意识到上述作法所隐含的大汉族主义心态。
纯音乐形态研究固然必要,而且也可以说它是音乐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部分,但是只从事纯音乐形态研究的学者往往和注重全方位视野的当代音乐人类学者在对音乐形态研究的认识与态度上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前者倾向于把音乐形态从社会及文化整体中割裂分离出来作单独的作曲技术性研究,而后者则强调在音乐形态研究中充分注意该形态的社会文化层面和内涵以及各者之间的关系。将音乐与社会文化隔离研究常易使人仅注意到外层形态的异同而忽略了深层本质上的不同,其结果是容易产生误导。在西方人类学研究的早期,有些学者没有意识到或有意忽略人类学与临床解剖学的本质区别、不研究社会和文化因素而仅从肤色和身体器官的物理结构来论定不同人种的精神与文化的性质,其结果是导出人种优劣论,为殖民主义者的侵略行径与希特勒灭绝“劣种民族”的行径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当今的纯音乐形态理论研究的路向与这种西方早期人类学研究的路向有些类似。其实在中国也已经有人看出国内纯音乐形态研究中的此类问题了。上述萧、韩二位学者就曾指出:“仅从音乐谈音乐(实质上是从音乐的音响层面谈音乐)是无法传达出以‘体认逻辑’为轴心,以认识‘自然/人文’的‘同和’为目的的中国民族音乐的真实内涵与精神的”(注:萧梅、韩钟恩《音乐文化人类学》(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的一些学者把实质上是汉族音乐形态的体系命名为“中国体系”,将其用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形态分析,例如将中国汉族的古典宫调理论用于维吾尔族音乐的形态分析;甚至更进一步,根据曲调形态的相似而将其他国家的音乐也划入“中国体系”(注:例如杜亚雄《中国民族民间的音乐体系浅析》,载《中国音乐》1984年第1期。杜亚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 载《艺术探索》1994年第1期。)。 这样的方法在注重纯音乐形态研究的学者中被普遍认可与实行(注:例如周青青《中国民歌》(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版)。),但注重社会文化内涵的音乐人类学者就可能追究:这样的应用与归类是否合理?这些不同民族以至不同国家中形态相似的音乐是否貌合神离、在表层相似的伪装之下有实质性的区别?这样的用法与归类是否会给二者的文化内涵研究造成误导?甚至:这样的用法与归类是否音乐研究中大汉族主义、汉族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的表现?中国音乐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批判欧洲中心论,但是对于本国学界中是否存在汉族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的问题则始终无人提出过。倘若有人因曲调与音阶形态相似而认为《孟姜女》曲调是欧洲中世纪教会密克索利底亚调式而不是汉族的徵调式,并据此认为在中国音乐中存在欧洲教会音乐体系,则早在60年代就会被认为是荒唐可笑;然而对于将汉族宫调理论用于维吾尔族音乐分析、或认为“中国音乐体系”存在于蒙古、北亚等地的做法,却直到跨入21世纪的今天还几乎没有人提出疑问或商榷。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者沈洽曾在1982年发表《音腔论》(注:沈洽《音腔论》,连载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1983 年第1期。),提出与上述体系在观念、 思路和方法上都迥然不同的一套分析汉族音乐形态的新理论。我认为这是一套符合当代音乐人类学思路的音乐形态理论,不带文化偏见与民族中心主义色彩。虽然沈洽在文中明确地将这一理论应用的范围界定在汉族的音体系之内,但由于此理论的本质是客观描述性的,路向是客位的而不是主位的,所以它对于分析存在“音腔”的其他民族的音乐也有实用意义。我认为这是一套重要的理论,它足以在音乐形态学领域引起革命性的变化。 然而遗憾的是, 近20年来它在中国音乐理论界与音乐学界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学者们虽然对它时有谈论,但却基本上无人将此理论与方法付诸实施,亦无人将其进一步发展完善。中国音乐形态学的主流仍然在上述“民族音乐理论”的渠道中流淌,不为所动。
中国的“民族音乐理论界”或“民族音乐形态学”界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基本上是纯理论案头工作者而不是立足于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研究者。这种案头工作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是由音乐工作者收集、整理、记录下来的谱面资料,这些案头工作者根据这样的第二手资料进行分析,试图从中归纳总结出民间音乐形态的规律,并以此规律为原则来建立起一套作曲理论。这样的案头工作方式本身无可非议。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案头工作所依据的谱面资料是否准确。倘若这些资料不准确或是错误,则据此得出的“规律”和“理论”就缺乏说服力。然而中国学界的情况,恰恰是从来没有人将这个关键问题提出来讨论过。那么究竟中国的音乐工作者对采录到的音响所作的记谱有多大的准确度和可信性呢?这是个很值得深究的问题。音乐形态理论和音乐记谱实践是互相影响甚至互为因果的两个环节。记谱者采取的记谱体系和最终呈现出来的谱面在相当程度上是记谱者根据某种理论对所记的音响材料进行了初步分析归纳的结果。上述路向中的情况是:形态规律的发现和归纳、形态理论的总结和建立都依靠记谱资料,而这些记谱实践所依靠的则是先前已有的形态理论以及据此理论发展出来的记谱方式;根据这样的记谱资料总结出来的规律和理论又反过来再指导了其后的记谱实践,而据此产生的记谱结果又再被作为更进一步的形态理论研究依据;如此反复循环不已。这样的音乐形态理论和音乐记谱实践二者间的关系有如“鸡生蛋、蛋生鸡”,与其说是谁生谁,不如说是二者互相影响或互相促进发展。我认为,中国大陆的音乐学者们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中努力建设发展汉族音乐形态的分析与理论体系,在此期间这形态理论的建设与记谱实践之间的关系,倘以“恶性循环”来形容也许有些过分,但至少不能说它们是良性循环的。我们不应否认中国音乐学界在汉族音乐形态体系理论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果,但是也应该思考: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音乐中是否存在不同于此的形态体系?倘若有,是否必要或有否可能归纳总结出适用于那些不同体系的分析描述方法或理论?然而这些课题却没有被深入探讨过,当然也谈不上此类方法或理论的建立。根据我多年来与中国各地音乐学者和基层音乐工作者接触中所了解到的情况,在分析少数民族音乐形态时,绝大多数基层音乐工作者应用的就是上述中国体系亦即汉族体系的理论,而没有充分意识到那有可能是张冠李戴。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记谱作业中就经常出现削足适履的情况。例如,某些实际演唱(奏)中的音高跟已知的汉族律制的音高很不相同,但这在记谱中却看不出来,因为有的记谱者认为那是演唱(奏)者“音不准”,记谱时就把它们“准确地”记成“应该是”的音符,而有的记谱者则是没能听辨出音高上的不同,而认为它们跟汉族音阶中的音高是一样的。不论是何种情况,其结果都是记谱时就以汉族的音阶和调式概念来分析记录,那些音乐中的音组织哪怕真是不同于汉族的音律、音阶和调式,也都统统被装进了汉族音乐形态体系的小鞋。在节拍、节奏方面的情况也是这样,一首民歌不论实际演唱是如何地自由或不规整,不少记谱者也都“理所当然”地把它按照西方体系的节奏、节拍或汉族体系的板眼给加以整理,对各音的时值予以增削,加上小节线,安排成了完全规整的带有拍号的小节,最终呈示在谱面上的结果其实是这些记谱者认为那音乐“应该是”的形态,而不是那实际演唱(奏)原来的形态。这样的记谱实践是在西方理论影响及汉族理论指导之下的实践,已经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如此产生的少数民族音乐记谱资料,是已经被按照汉族音乐形态修改过的;而据此进行的研究,所归纳总结出来的“规律”和理论,就仍然还是汉族体系的。这样归纳出来的“规律”和理论又反过来指导了再后的记谱实践,而这种实践又继续以上述方式为这种理论提供分析资料和“事实”依据。理论建设和记谱实践,就在这样的不良循环中不断发展、成型。于是几十年来,多民族中国的民间音乐的形态理论和记谱实践就只在汉族音乐形态体系之中反复循环,没能跳出这个“怪圈”。
中国有些音乐学者同意西方音乐学者中的一种说法:西方现行的所谓“基本乐理”实际上只是关于西方五线谱记谱法的说明(注:沈洽、邵力源《关于“通用旋律动态模拟器软件(第一版)的设计、研究报告”》,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这说的是西方音乐理论与记谱实践不良循环的“怪圈”。我认为在相当程度上同样的说法也可以用来形容这几十年间中国音乐学界通用的中国民间音乐的“基本乐理”和记谱。最近国内有学者提出,受了某一种音乐文化“格式化”训练的人可能在心理上受到这一特定音乐格式的影响,在听觉上用自己“受化”了的“格式”去“格式”感觉对象(注:沈洽、邵力源《关于“通用旋律动态模拟器软件(第一版)的设计、研究报告”》,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我对此很有同感。 用我上面的话来说,经汉族音乐文化和形态理论格式化训练或熏陶的音乐工作者,在记录不同文化的音乐时,就把音响听成记成了自己以为是或认为应该是的形态而不是客观的实际形态。举例而言,我曾对原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群众艺术馆为《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而准备的一百五十多首黎族民歌的记谱和原始录音逐一进行对照复核,结果觉得上述问题的存在相当严重。(注:沈洽、邵力源《关于“通用旋律动态模拟器软件(第一版)的设计、研究报告”》,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我从事黎族音乐研究已有20年,曾数次到黎区进行调查。根据我所听到的实际演唱,除了黎族中流传的汉族民歌(部分地区黎人称其为“客歌”)以外,相当多的黎族本族传统民歌的曲调是难以或不能以汉族的音阶、调式、小节、拍号或板眼的概念来限定的;如果以汉族的节拍节奏概念以及律制、音阶和调式体系为规范,这一部分黎族民歌的演唱都可以说是节奏和音高都“不准”。不仅民歌如此,黎族民间乐器与器乐的情况也是这样。海南与广州已高度汉化或西化的专业歌舞团体的音乐家们所用的经过改革的“黎族乐器”及其演奏不算,民间生活中实际存在的黎族乐器及其演奏的音大多是“不准”的。面对这样的情况,半个世纪之前学者们可能认为这是民间歌手乐手的演唱演奏“节奏不准音不准”,但在跨入21世纪的今天,音乐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已经有所提高,我们就不应贸然断言这是民间的唱奏“不准”,也不应忽视这一现象,而应认真研究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然而许多音乐工作者和研究者却在开始对黎族音乐进行记谱之前就已经接受了一个预设前提,即黎族音乐形态属于所谓“汉族体系”,于是忽略了民间存在的与此前提冲突的迹象。但当然,我对上述黎族民歌记谱的审听复核所依据的只是我个人的听觉,并非测音仪器,所以我只能说以上只是我自己的感觉和结论,却不能断言我个人的感觉与结论就一定正确。进一步的核实与论证,还需要同行们的共同努力。我认为一方面,在今后的调查研究中我们必须重视这些问题;另一方面,对以前已经完成的记谱与分析,似有必要对照田野录音原材料进行客观的全面复核,如有可能,最好是能使用合适的仪器或是电脑软件,例如不妨试用国内最近有人设计的“通用旋律动态模拟器”(注: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群众艺术馆编《黎族民间歌曲》,内部资料,油印本及盒式录音带四盘,1983年内部印行。)。当然,这样的复核工作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并非少数人在短时期内所能完成的;学者们甚至会认为这不切合实际或没有必要。当代中国音乐界都知道,中国大陆已经部分出版并正在陆续出齐的中国民间音乐几大集成是中国民间音乐采集记录的一项划时代的成果。中国大陆的音乐形态学者普遍将其中的记谱作为中国音乐形态研究的主要资料,但除了我本人的著述(注:Yang Mu:"Academic Ignorance or Political Taboo? ——Some Issues in China's Study of Its Folk Song Culture"《学术无知还是政治禁忌? ——中国民歌研究中的几个课题》,载Ethnomusicology《音乐人类学》,第38卷(1994年第2期)。)以外,我从未见过有人对这些资料的可靠性和可信性提出问题并进行研讨。我觉得,也许音乐学界的这种现象本身就已经是个值得我们思考并予以重视的问题。
除了上述汉族中心论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觉得必须提请学术界注意的,即对中国目前的纯音乐形态研究性质的认识。至今为止,中国的“民族音乐理论”或“民族音乐形态学”的主流仍是侧重于纯音乐形态研究的。广义而言,纯音乐形态研究可以被看作当代音乐人类学中的一个科目,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当今中国的这种纯音乐形态研究跟当代音乐人类学中的音乐形态研究在性质上的区别。我将它们列表示意如下:
中国"民族音乐理论"或
"民族音乐形态学"的主流
分析研究 第二手书面资料,包括:(1) 以现代演奏界通用的乐谱式记
所依据的 谱方法记录下来的谱面资料;(2)已有的音乐理论,例如现
主要资料 存的主要以汉族音乐为依据的中国古典乐学.
以对上述资料分析归纳的结果为基础,建立或发展出一整套
重点企图 作曲技术理论,例如音阶、调式、和声理论等所谓"作曲四
大件",用于指导音乐创作与演奏实践,而不在于要描述和
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
主要目的 1.为作曲和演奏服务;
2.为发展中国音乐服务.
二者的这些分野并不是绝对的、清晰划一的,二者之间既有
界属不甚分明的过渡类型与学者,又有交错相叠、互可通用
之处(故在此表中二者仅以虚线隔开).
性质路向 1.与中国古典乐学、西方传统音乐学中的音乐分析和作曲技
术理论属同一路向.
2.倘用于当代音乐人类学中的音乐形态分析描述,基本上应
被认为是"主位"(emic)路向且应用范围有限.
当代音乐人类学中的音乐形态研究
分析研究 第一手音响资料.通过田野工作采录民间演唱(奏)的实际音
所依据的 响,然后直接对这音响进行分析研究.
通过对上述资料的分析,发现、归纳、总结出民间音乐中实
重点企图 际存在的规律,不企图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用于指导音乐
创作与演奏实践的理论,而企图借此深入描述、研究包括音
乐在内的人类社会和文化.
主要目的 1.为分析、描写、研究音乐文化服务;
2.不以发展任何一种音乐为已任.
二者的这些分野并不是绝对的、清晰划一的,二者之间既有
界属不甚分明的过渡类型与学者,又有交错相叠、互可通用
之处(故在此表中二者仅以虚线隔开).
性质路向 1.与当代音乐人类学的总体思想属同一路向.
2.在当代音乐人类学的音乐形态分析描述中基本上可被看作
是"客位"(etic)路向且应用范围较广.
我指出二者的上述区分,绝不是要否定或肯定其中一者的价值、作用或必要性,而是要明示二者在性质上的不同。此二者的性质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但如果我们对它们的性质及其区别认识不清,那就可能成为一个问题。中国音乐学界的这种纯音乐形态的“民族音乐理论”或“民族音乐形态学”方法在音乐人类学研究中并非不可使用;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在音乐人类学研究中使用这种理论或方法时应该充分认识到它的上述性质和可能因此具有的局限性。倘使用得当它可以是一种好方法,但倘对其性质与局限性认识不清,就可能产生问题。例如,如果仅根据现今通行的记谱亦即第二手资料来作案头分析,得出的结论必定是中国音乐中不存在“音腔”现象,因为中国民间音乐中的“音腔”在目前通用的乐谱式记谱中是看不出来的,它只能从实际演唱(奏)的音响中听出来。在这一方面,沈洽的“音腔论”就在性质上有所不同;“音腔论”的得出,主要是依据实际音响亦即第一手资料,其路向基本上符合当代音乐人类学音乐形态分析描述的要求。
以上说的是中国大陆的情况,而在海外,当代音乐人类学界在音乐形态记录与分析方面也不见得就没有弊病或都不存在欧洲中心主义或某一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在西方国家,音乐人类学界现行的音乐记谱和形态分析的具体方法是五花八门,例如在记谱方面有的人使用“规范”的西方五线谱,有的人主张使用被记谱对象本身文化中已有的记谱法,有的人使用图表方式,有的人使用仪器如频谱仪、“记谱仪”或电脑,还有的人使用各种符号或是自创的其他方式,不一而足(注:中文出版物中有两部概论性著作中的有关章节提供了一部分海外信息,可资参考。见俞人豪《音乐学概论》第331—336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版);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第131—136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版)。)。在所有方法中,最通用最普及的仍然还是传统的由人工进行的各类乐谱式记谱法,其中最经常用的就是西方五线谱配上音乐人类学者们发明的用于记录非西方音乐的各种符号。我想提请同行们注意的是,现今通行的这些乐谱式记谱法的产生和普及是在录音、录像、电脑和多媒体媒介普及的年代之前,当时的出版物只有文字与乐谱的形式,如果没有乐谱,读者们根本无从想象作者所论及的音乐是个什么样子。但是这样的由人工进行的乐谱式记谱不可避免地会有偏差或带有偏向,而且每一个读者根据这样的乐谱想象出来的音乐形态仍然与该音乐的实际形态不尽相同,甚至会有严重歪曲。在20世纪末,人类世界已经进入高科技、多媒体的电脑时代。对于民间音乐的保存和介绍,已经可以比较容易地把录音、录像等原材料原状复制、出版、传播、保留。现今国际上的多媒体出版物已在日渐普及,而音乐人类学书籍出版时附以音响或音像的做法,正在逐渐成为趋势。读者们可以不依靠那些不一定可靠的传统乐谱式记谱而通过多媒体媒介直接得到相当于第一手材料的感受和认识。演奏界的情况不谈,全球的音乐研究界在这一方面今后的走向如何虽很难预言,但较大的可能性则是高科技、多媒体与互联网有可能使得以研究为目的的音乐形态记录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很可能将来通用的记谱不会使用今天通用的这类音符和谱表,而会使用高科技、多媒体的新方法。在音乐形态分析、描述和理论方面,将来也会因音乐记谱方式的变化而相应地产生变化。而在目前,西方的音乐人类学者们使用的音乐形态分析描述具体方法虽然五花八门,但共识还是有的,即无人会用汉族的调式体系来解释蒙古民歌或印尼甘美兰音乐的形态或是用汉族古典宫调理论来解释十二木卡姆或维吾尔歌舞的音乐形态,这似乎是比中国的某些民族音乐理论家在认识上略胜一筹之处。另一方面,在20世纪末的西方音乐人类学界,许多与社会、人文直接相关的研究课题成为热门,音乐形态研究也多被融合到人文与社会的研究之中进行,而纯音乐形态的研究则被冷落。这种倾向在中国其实也已开始,学术刊物中已越来越多地见到从社会和文化深层来探讨音乐形态的文论(注:例如戴嘉枋《从系统论看中国传统音乐单声体系的长期延续》,载《音乐研究》1991 年第4期;乔建中《“下四川”研究》,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年第2 期;李玫《中立音源流之猜想》,载《中国音乐学》1998年第3期。 )只不过这倾向尚未在中国国内的音乐形态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已。在中外交流尚不充分、海外学者在中国进行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尚有困难的情况下,西方学者对中国各民族音乐的了解毕竟比不上中国本土学者的了解程度,不论是通过调查分析归纳总结出中国各民族音乐形态的规律,还是企图建设发展出有关的理论,所依靠的主力应当还是更加了解情况的中国本土学者。但是这些工作不是某一个人以一朝一夕之功就可以完成的,它需要整个学界长期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