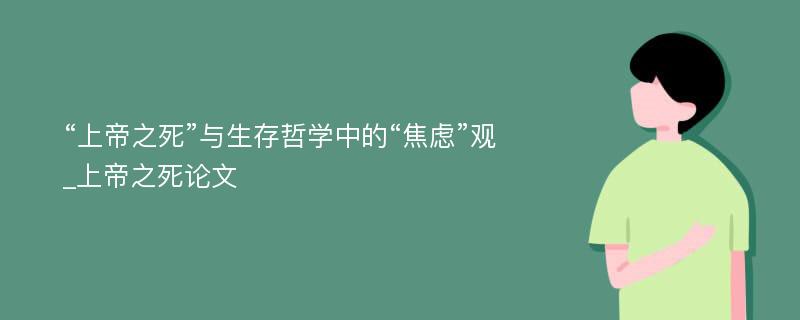
“上帝之死”与存在哲学之“焦虑”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死论文,焦虑论文,上帝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1)06-0038-08
“上帝死了”是由谁首先喊出的,是启蒙运动中的法国无神论唯物论者,抑或是德国哲人 尼采,这一历史性质的问题与本文的论题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上帝之死”对于整个西方 文化意味着什么,紧要的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精神中上帝成了被宣判的对象,这种时代 精神对于塑造、培植自己的哲学旨趣又有什么样的关联。有了这样的限定,我们便将上帝之 死这一命题的历史溯源搁在一边,而着重于其文化意义或功能的分析。这种分析可分为两个 相关的方面进行:一是“上帝”本身在西方文化中的意义或功能是什么,二是“上帝之死” 在西方文化中的意义或功能是什么。在这两个问题得到厘清之后,存在哲学的“焦虑”的语 境与相应的内涵也就会变得清晰可辨了:存在哲学的焦虑观无非是对上帝之死这一语境的一 种回应,在我看来这种回应准确无误地诊断出时代的症候,但并没有开出有效的药方。由此 , 本文依次讨论三个问题:(1)上帝之死的意义,(2)存在哲学的“焦虑”,(3)问题与出路。
一、上帝之死的意义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是在种种社会关系中获得自己的角色预期、身份定位及行为方式的 。做人就是尽自己的种种身份所承当的职责,扮演自己在社会中所担当的种种角色。戏台上 带着面具的演员之演出,无非是把人世间社会人的角色表演以一种夸张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 而已。不过与演员不同的是,当演员把自己的戏台上的面具扔掉后,他(她)仍不失是一个人 (或许应说是一个真实的人),一旦人把自己的社会角色扔掉的话,那么他(她)究竟还具不具 人性就成了一个问题。另一点不同是,社会角色的承担并不只是生硬地背诵预先准备的“台 词”,社会秩序与意义乃是通过种种社会化机制不断地“内化于”每一个社会中的人之中了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家庭、幼稚园、学校便是每一个人登上社会这个大舞台之前背诵“ 台词”(熟悉社会角色)的场所,监狱是对那些不愿按“台词”演戏而屡屡失范、越轨的人重 新培训的地方,而精神病院是那些无能记住台词更无能按台词演戏的人被隔离的地域。当然 由于人类文明长期的熏陶,任何失范者实际上首先都会受到他(她)自己的“超我”(良知)的 谴责。个人生存的社会环境是一个有序的意义结构,作为一个社会化的人处身其中便是“健 全的人”,而一旦因种种失范被排斥在外,便会有面临“疯狂”之险境。当然在一些所谓的 “边缘情况”下,如面临死亡等等,社会有序化的意义结构之“脆弱性”就会显露出来。死 亡向任何一种既定的人生意义提出了诘难,“假如给我几天光明”、“假如有来世”之类的 说法多少暗示了这一点。“死亡向社会提出了一个可怕的问题,不仅因为它明显地威胁人类 关系的连续性,而且它威胁着关于社会赖以生存之秩序的基本设想。”(注:贝格尔著,高师宁译:《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7月第1版,第30页。本论文的第一部分很多地方得益于贝格尔该书的有关分析,在此向该 书 作者(及译者)致谢。)
边缘情境将人们平 时习以为常的社会秩序撩在一边而暴露出它背后的混乱与无意义的背景。
正是在这里,上帝作为意义的终极依据与源头这一角色发挥了它自己的作用。“上帝”是 从无意义、混沌中创造了世界,或者说,“上帝”是宇宙秩序的立法者,是宇宙意义的神圣 化的象征。由此神圣化的宇宙秩序与意义,人的生命便始终被置于“具有终极意义的秩序” 之中,秩序的(无意识)“投射”色彩被(意识)抹掉了,宇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有秩序的。 还是引用贝格尔的话,“在人类建造世界的活动中,宗教起着一种战略作用。宗教意味着最 大限度地达到人的自我外在化,最大限度地达到人向实在输入他自己的意义之目的。宗教意 味着把人类秩序投射进存在之整体”(注:贝格尔著,高师宁译:《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第36页。)
。上帝这一超越者使人类活动内在的不稳定性以及社 会有序化意义结构的脆弱性被赋予了“最终的可靠性和永久性的外表”,社会秩序与宇宙秩 序挂在一起并得到了神圣化,原本的无意义、混沌被“神圣的帷幕”所遮盖。于是,即便在 一切边缘情境下,意义、合理性也同样存在。“死亡”现象也不能取消意义,相反,人类要 追求一种有意义的死亡,要有一个“好死”。何况,很多宗教还坚持“死亡”只是生命形态 的一种转变而已,死后还有另外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这样“今生之死”与“来世之生”又有 了一层意义的关联。如此,一切天灾人祸(如地震、战争)、一切死亡(如夭折、溺死)都获得 了某种“神圣的意义”,一切宗教的神正论说到底都是对人世间一切极端非理性的现象加以 理性化的辩明而已。“上帝”是一切价值与意义之终极依托,即是指此。
“上帝”的意义已明,“上帝之死”的意义也就不难厘清了。“上帝之死”不只是对某个 神 学命题(如“上帝存在”)的否定,也不只是某个无神论者(如尼采、马克思)的情绪宣泄,而 是整个西方文化中的“神圣的帷幕”被揭开的一个结果,是世俗化时代降临人世的象征。世 俗化过程是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活动摆脱宗教的控制的过程,表现在“上帝”这一神圣 之维上,便是“上帝”逐渐从这个世界中撤离出来。首先是经济领域的完全世俗化,“上帝 止步于工厂的大门前”便是对此的一个形象的写照。和经济的世俗化并进的是自然界的去魅 化,上帝由“创世主”而蜕变为钟表匠式的“设计师”,自然界成了一部上紧发条的钟表, 完全开始独立运转。洞察创世奥秘的不再是受到天启的神学家,而是禀有理性的科学家(注:卡西勒著,顾伟铭等译:《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尤第二章“ 自然和自然科学”,第35~89页。及杜布斯著,陆建华等译:《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和自然》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
。 从此,科学与技术联袂并进,“上帝”从自然领域退到道德领域(社会领域),康德视上帝为 实践(道德)理性之预设就反映了“上帝”的这一境况。不过甚至在康德之前,激进的法国无 神论者就早已决心把上帝从社会领域中赶出去,他们运用“自爱”、“自利”这一人性的自 然因素去解释人类社会、人类道德的形成与发展。而在康德之后,道德领域、社会领域的去 魅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在这一进程中德国的几个思想家功不可没,首先费尔巴哈高扬人 本主义的旗帜,将传统上帝创造了人这一命题颠倒为人创造了上帝:上帝不过是人自己投射 出 的“大写的人”而已。紧接着马克思将这“投射”的社会的、经济的背景给揭发出来,而叔 本华、尼采则从意志这一维度将文化中的一切所谓的神圣价值还原成人的非理性因素。德国 哲人这些神圣价值的“还俗”运动得到了日益强盛的达尔文主义的有力支持,而弗洛伊德主 义、行为主义尽管在学术理路上泾渭分明,但在神圣价值的自然化取向上却殊途同归。
经济领域的自足化、自然领域的去魅化、道德领域的自然化,使得“上帝”在社会秩序的 合理化论证中完全变成了一种“修辞上的装饰”而无实质性的意义。宗教变成了纯粹的个人 的“兴趣”与“爱好”,“上帝”、“佛”、“真主”等等像超市中不同品牌的商品一样, 任由现代的宗教消费者拣选。“信仰自由”以及“宗教多元论”的思想正是扎根于宗教超市 的土壤中的(注:近来有人批评希克的宗教多元论乃是植根于我们时代的超市文化,就是例证。见希克著 ,王志成、思竹译:《信仰的彩虹:与宗教多元主义批评者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年9月第1版,第38~39页。)。基督教本身也加入了世俗化的进程中,本世纪一度兴盛的世俗神学就是例证 。不仅如此,很多学者甚至认为世俗化的根子就在基督教里面,尤其是新教更是被认为是现 代世俗化这一曲戏剧的“彩排”(注:贝格尔在《神圣的帷幕》之第5~7章有较详尽的分梳,可参看。)。
如果说传统是靠“上帝”这一“神圣的帷幕”将原来混沌与无意义的深渊罩上一层价值与 意 义的表面,那么,现代哲学中“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就是对此表面的剥脱。事实与价值的 区别不只是一个语言分析的问题,从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来看,这个二分法折射的乃是世俗化 的时代精神。“价值”成了主观的领域,而“事实”则是无价值的领域。更激进的看法是事 实也不过是人的一种“虚构”,是权力意志的透视的一种“结果”,“一个事物的本质也仅 仅是关于这个‘事物’的意见”(注:尼采著,周国平译:《偶像的黄昏》,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52页。)。尼采的观点受到了后现代主义者的欢呼,无论是科学的 真理抑或是道德的标准都成了一种“诠释”。人成了价值之源,成了意义的主体。没有人, 一切就堕入混沌。这样,在现代意义上的主体的挺立的边缘,乃是无意义的深渊、无边无际 的混沌。这也是现代哲学主体性原则凯旋的结局。这一结局乃是我们把握存在哲学主旋律的 契机,存在哲学所张扬的“焦虑”即是对此境况的一种回应。
二、存在哲学之焦虑
有了上述的语境之分梳,存在哲学的“焦虑”观也就不难理解了。无论是陀思妥也夫斯基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切都是被允许的”的慨叹,抑或是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 》中荒诞感的抒发,都是这个“焦虑”时代的精神之表达。作为一种哲学范畴,存在哲学的 “焦虑”不应只在心理学、社会学等层面上去理解,而应从生存论的层面去把握。
1.海德格尔之“畏”。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对“畏”的讨论是在Dasein在世的 生存论结构之后进行的。Dasein之“Da-sein”(在-此)不能被理解为物理空间性的“这”或 “那”,而应在生存论上加以领会,它是一种“存在性质”而不是现成东西的属性。“在此 ”的“生存论建构”由三个统一的环节构成:现身情态-领会-言谈。在“现身情态”中展开 的乃是Dasein的“被抛状态”,这是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情绪”。生存论的情绪所展开的 就是在世之中的存在之整体。而任何现身都有其“领会”,“领会总是带着有情绪的领会” ,此生存论的领会所展开的乃是Dasein对“本己能在”的“筹划”,这种“能在”并不是漂 游无据的“为所欲为”,“Dasein本质上是现身的Dasein,它向来已经陷入某些可能性”, 因此,它所筹划的是其“向来所是的可能之在”,是“彻头彻尾的被抛的可能性”(注: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76 页。)。而任 何领会状态实际上都是“分解了的”,对领会状态的“勾连”就是“言谈”。现身情态领会 -言谈是Dasein在世之“在”的本质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却表现为两可-好奇-闲谈之“沉沦 ”样式。尽管海德格尔提醒我们,Dasein之沉沦于世并不是指先有一种“纯粹高级的‘原始 状态’”,然后由此状态而堕入“非本真状态”之中。“沉沦于世”乃Dasein本身的“生存 论规定”,“本真的生存并不是任何漂浮在沉沦着的日常生活上空的东西,它在生存论上只 是掌握沉沦着的日常生活的某种变式。”(注: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17 页。)但无论如何,“沉沦”是Dasein的“一种异化” ,在其中,最本己的能在对Dasein“隐而不露”,异化把Dasein“杜绝于其本真性及其可能 性之外”。沉沦于世就是“逃避”,就是逃避它本身。
沉沦的“逃避”与日常的因“害怕”而避走是两回事。怕总怕某个东西,因害怕而躲避可 怕的存在者,不过要躲到另外一种不可怕的、熟悉的的存在者那里去而已。因此,害怕的对 象 是确定的,人们对可怕者的可怕性是早有领会的。而“畏”之所“畏”不是任何世内的存在 者,“凡是在世界之内上手在手的东西,没有一样充任得了畏之所畏者”,“畏就根本‘不 知’所畏者是什么”,这就是说畏的对象是“不确定的”,它不是某个可怕存在者,也不是 某个阴森的空间本身,但“它已经在‘此’——然而又在无何有之乡;它是这样的近,以致 它紧压而使人屏息——然而又在无何有之乡”,“畏之所畏就是在世本身”。畏将所有 世内的存在者日常的意蕴给挂了起来,一切曾经令我牵挂的存在者在畏中“沉陷”了。“世 界”不再呈现任何东西,“畏剥夺了Dasein沉沦着从‘世界’以及公众讲法方面来领会自身 的可能性”,“畏使Dasein个别化为其最本己的在世的存在”(注: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25~227页)。“畏”使日常容身的意义 世界、“在家”安定、熟悉的生活套路崩溃了,Dasein因此“无家可归”、因此“茫然失其 所在”:“无家可归在畏的基本现身情态中本真地暴露出来;它作为被抛Dasein的最基本的 展开状态把在世摆到世界之无面前,在为其最本己的能在的畏中而有所畏。”(注: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30页。)
由此可见,“畏”是搅人不宁的东西,也正因此,它通常是被压抑的,Dasein沉沦于世实 际上是逃到世界之中,为的是掩盖“畏”的折磨。在“常人”之“在家状态”中栖身,也就 是为了克服“畏”之“无家可归感”。
2.萨特之“焦虑”。像海德格尔一样,萨特的焦虑理论也是从“焦虑”和日常的“畏惧”( 怕)的区别入手的。恐惧是对世界上的存在的恐惧,而焦虑则是在“我”面前的焦虑。前者 是对“超越的东西不假思索的领会”,而后者则是对“自我反思的领会”。例如,我走在悬 崖边一条没有护栏的狭窄小路上,我可能在石头上滑倒并跌进万丈深渊,小路上疏松的土壤 可能在我脚下崩塌,这种种周遭的存在可能性,时刻威胁着我的存在,这些可能性是外在于 我的,它们出现与否不是由我决定的,我是从处境出发把它把握为“诸超越物中可破坏的超 越物”,对之的“恐惧”因此而显现出来;而属于我的可能性的乃是在“反思的范围”内, 我留心路上的石头,尽可能远离路的边缘,这些行为是由我决定的,而不是由外面的原因决 定的,我完全可以否定它们,比如,我完全可以无视路况昂头阔步,毕竟没有任何“外部原 因”来排除这些可能性。这就意味着“反思的范围”只能给我一个“未规定的将来”,没有 任何东西能够迫使我采取某种行为。这样在我当下的存在和我的“将来的存在”之间就有一 个“虚无”插了进来:“我现在不是我将来是的那个人。我不是将来的那个人的原因首先在 于,时间把我同他分开了;其次在于我现在所是的人不是我将来要是那个人的基础;最后在 于没有任何一个显示的存在物能够严格规定我即将是什么。”是跳下深渊还是小心自救,完 全由“一个我目前还不是的我”决定,于是,“在我还不是的那个我不依赖于我正是的这个 我的严格意义下,我正是这个我本身依赖于我还不是的那个我”。我可以“玩弄”我的可能 性:将眼睛扫视一下深渊,想象跌进深渊的动作等等,此种“以不是的方式是他自己的将来 的意识”就是“面对未来的焦虑”。另有一种“面对过去的焦虑”,例如,一个赌徒决心不 再赌博了,而当他一走近赌桌,他的决心都“融化”了,他想起前一天下过的决心,而且现 在仍然认为自己不想再赌了,但在“焦虑”中他体验到的东西恰恰说明过去的决心是“完全 无效的”,或许决心还在,但“由于它是为我的意识而存在的,它又不再是我。我逃避了它 ,它未履行我叫给它的使命”(注:萨特著,陈宣良等译:《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1987年第1版,第64~66页。)。
焦虑突显的乃是意识的虚无化品格,是“我的可能性”。意识在人之“焦虑”中挣脱了一 切“内容”,包括“动机”也被清除在意识之外,意识中从来就没有什么动机,动机也只是 “相对意识而言的”。如此,焦虑将一切意义与价值领悟撇在了一边,而直面意义与价值的 基础:毕竟任何意义与价值都需要相应的基础,而在“存在”中是找不到这样的基础的,惟 有 我的自由才是各种价值与意义的“唯一基础”:“没有任何东西,绝对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 我应接受这种或那种价值,接受这种或那种特殊标准的价值”,“焦虑”之为“焦虑”,即 在于它将此自由开显出来,“我的自由之感到焦虑是因为它成为诸价值的基础而自己却没有 基础”。我不应该忘记给西蒙写回信,我今晚同皮埃尔有约会,我无权再对克洛德隐瞒真相 ,等等,所有这些平凡的日常价值,都是“从作为我在世界中对自己的选择的第一次谋划中 获得意义的”。当然我是出生在“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之中的,况且还有闹钟、告示、税单 、警察等告诉我如何如何生活,但通过“焦虑”,我才觉悟,原来我自己才是赋予闹钟意义 的人,我自己才是看到告示牌而禁止自己践踏花坛的人,等等。“我孤独地出现,并且是面 对唯一的和构成我的存在的最初谋划而焦虑地出现,所有的障碍,所有的栅栏都崩溃了,都 因意识到我的自由而虚无化了,我没有也不可能求助于任何价值来对抗这样一个事实,即 是我支持了诸价值的存在”,“在焦虑中,我既觉得自己是完全自由的,又觉得不能不使世 界 的意义通过我而到达世界”(注:萨特著,陈宣良等译:《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1987年第1版,第72~74页。)。
由此可见,“焦虑”的根子在于虚无化的自由的敞开:因为我是绝对自由的,所以一切所 谓的“价值”与“意义”都是通过我才存在的,所以我必须为自己的自由选择负责。“责任 ”、“价值”、“意义”等等悬于绝对自由的“我”,而我恰恰是“无”。存在的“荒诞” 与选择的“负担”在此“焦虑”中显现出来。于是,而有“逃避”焦虑、“掩盖”焦虑之举 动。向哪里逃避呢?向他人、向物、向决定论逃避,于是而有“不诚”(bad faith)之人生。
无论是海德格尔的“畏”抑或是萨特的“焦虑”,实际上都揭示了现代人的自由及其尴尬 。在前者那里,畏揭示出了在世本身结构(能在),在萨特那里,焦虑揭示出了虚无化意识品 格(绝对自由)。可以讲畏与焦虑使“迷失”于世界之中的本真人性返回它自己,然而自由的 境界并不是让人“安顿”的“化境”,相反,恰恰在这里,无家可归感、茫然失措感、荒诞 感悠然而生,搅人不宁,以致于获得自由的人最想做的往往就是“逃避”而重堕非本真状态 之中。问题出在哪里呢?
三、问题与出路
如上所述,存在哲学对“畏”、“焦虑”的揭示无非确立了人的自由的本体论的地位,然 而,与这种个体自由突显相伴而来的是一种无家可归的失落感。如果说传统的世界的意义是 由 “上帝”担保的话,那么,现在没有上帝的主体的“在世”便成了一种精神的流浪。“畏” 和“焦虑”说白了就是对人生“在世”的“在”本身的一种牵挂、一种自觉,因为上帝的缺 席,真实的个体不能再想当然地成为世界之中的“什么”(角色),种种的“什么”不过是外 在的社会(“常人”)加在个体身上的“套子”,而不再具有任何神圣的意义。不加反思地容 身于世界中的“什么”,在海德格尔那里是Dasein没于非本真状态,在萨特那里是自为的逃 避责任的“不诚”之举。如此,畏之所畏、焦虑之所焦虑不再是世界中的“什么”,而是在 世的“在”本身。“在”作为个体生存的“可能性”直面的乃是无意义的深渊,存在主义文 学所描写的“眩晕”与“恶心”就是对此境地的体验。而“在”本身毕竟只是“可能性”, 它要成为现实,就必须在“什么”之中,“在”总是要在世之中而在的。“在”和“什么” 便始终纠缠在一起。人的“在”是被“抛”进“什么”之中的“在”,这是一种“自由的被 抛”:“什么”的意义是由人的“在”筹划、投射、领会的,而任何一种筹划、投射、领会 都是在先前的“什么”之中进行的。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对自由与境况关系的描述对 此有精辟的阐发。无论如何,“在”和“什么”成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存在范畴,海德格尔强 调存在与存在者之间“本体论的差异”,萨特对“自为”与“自在”的区分也是着眼于此。 自由地去“在”成了现代主体的“宿命”,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在向“什么”筹划、 投射意义之际以何作凭据?换言之,在人的“在世”中,有没有一个“应该”如何在的问题 。对此,存在哲学给出了“消极的答案”试卷:“在”除了“自由地去在”之外,便再无任 何的规定,选择“什么”、“应该”选择“什么”完全是个体在世本身的事情。这一点萨特 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举那个年轻人的例子说得最清楚不过了(注:萨特著,周煦良、汤永宽译:《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4月 。“在”就是自 由 ,自由就是“在”,除此之外,无可奉告。
正因为“在”是自由的,所以个体就得为自己的在“什么”的选择负责,任何掩盖自由的 借口都没有合法性:世界之“中”没有一个“什么”可以限制“在”的自由,而世界之“外 ”,上帝已经死了。“在”的负担如此之沉重,这和《圣经》中说的“轻省的担子”形成了 鲜明的对照。自由面对自在这一无意义之深渊便无法感到“自由自在”了,所以,存在哲学 所 讲的“无”、“虚无”和东方哲学所讲的“无”、“空”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在后者中, 个体体验到的是空灵、宁静与在家感,而在前者中,个体体验到的是孤独、恶心、荒诞感, 是举手无措的茫然与尴尬。于是而有“逃避自由”、“逃避孤独”的现象出现,但逃到那里 去呢?逃到“世外”桃源吗?上帝死了,“世外”的“避难所”已经关闭。于是,只能向世界 之中的“什么”那里逃,逃向“领袖人物”、逃向“人群”,从而重获“安全感”、“归属 感”,法西斯社会的极权主义和民主社会的群氓主义便成了个体在世逃遁的“避难所”。法 兰克福学派对大众社会的批判印证了这一点。
“神律”不见了,“自律”又深受“畏”与“焦虑”之纠缠,逃向“他律”便成了一条“ 路子”,这是“神圣的帷幕”降下后,人本主义戏剧的一个情节。然而遁入“他律”毕竟是 以个体的泯灭为代价的,在“逃遁者”与向之逃遁的“威权者”之间,乃是一种“受虐”与 “施虐”的变态关系。这一点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曾花大笔墨阐发过的。设若个体乃具 有“存在的勇气”,而不向任何他律的东西逃遁,那么,这又如何避免布尔特曼所批评的“ 虚 幻的自由观”之虚无主义的结局呢?布氏指出,现代的自由观念,“不承认源于彼岸的准则 或律法”,这必然导致“一种拒绝承认绝对伦理要求和绝对真理的相对主义”,其结局便是 “虚无主义”(注:第1版。)
布尔特曼著,李哲汇、朱雁冰译:《生存论神学与末世论》,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12月 第1 版,第21页。)。
那么,如何克服存在哲学所揭示出的现代虚无主义的困境?(1)通过重新挖掘“神律”之维 吗?以蒂利希、汉思昆、麦奎利等为代表的基督教神学家希望人类会在“自律”中重新发掘 出一种新的“神律”,或者在人之向神圣之维的“投射”的结构中找到一种具有普遍性、先 验性的某种终极地位的东西,从而让上帝之维重新纳入人的在世之中(注:蒂利希著,尹大贻译:《基督教思想史》,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年版,第424~42 5页。)。或者(2)通过诉诸 “智的知觉”而挖掘“自律”中的“义理”吗?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儒家在回应存在哲学的 挑战 时,指责海德格尔与萨特的人性论是虚无的人性论,没有“义理承当”,只有诉诸“智的直 觉”等“逆觉工夫”才能为人性奠定实有的内容(注:牟宗三在《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一书中批评海德格尔的本真状态是“虚荡的”、“未 落实的”:“人诚然是不安定的,无家性的,不能以习气、堕性为家,人能勇于接受此一事 实,不蒙蔽自己,固然可显一真实性,因而也就是显示其实有性,但这样的真实性、实有生 恰正是消极的,虚荡的,并未正面真得一真实性与实有性。”(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 哲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61页)在《论无人性与人无定义》一文中,牟宗三又 批评萨特的存在人性论实际上是否定人性,是虚无主义(该文载于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 义》,台湾学生书局1971年修订版)。总之,在牟看来,海德格尔与萨特之失在于他们停留 于“情欲生命”的层面,而未上升到“仁体”、“性体本心”,因而最终是“无本无根”。 对牟宗三对海德格尔的批评,笔者曾有专文讨论其得失,参见《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与 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互参》,《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或者(3)通过强调责任感、相互间的信 任而克服原子论式的个体主义的局限性吗?以查尔斯·泰勒、麦金太尔等为代表的具有社群 主义取向的思想家将个体的自我实现与对传统的认同、社群的忠诚联系起来,而不是象个体 主义者将自我本真存在与沉沦的共在对立起来。或者(4)坦然接受后现代主义的模式,彻底 摒弃任何重建神圣之维的形上学的冲动,拒绝一切宇宙意义的宏伟叙事,完全安于生活各 个领域之内的平面化的意义安排,比如,周一至周五作为一个生意人在公共场所依照最大利 益原则搏杀,在周末则躲进教堂或酒巴忏悔或宣泄一番?至于所谓的终极关怀、统一的意义 等等则作为学究式的问题而被抛诸垃圾堆之中?于是谈论角色的分裂、谈论公共生活领域与 私人生活领域的分裂不再有任何的意义,因为原本就不存在什么统一?
人会不会在“畏”与“焦虑”的现象学所揭示出的“自律”中重获“神律”,或者逆觉到 “性体本心”,或者在社群与传统的归服中找到道德价值的“根”,或者坦然接受后现代主 义的模式,我想这一问题不单是靠某个神学家的神学探究、某个哲学家的理性探索就可以回 答的,上帝的重临与否也不是由神学家可以决定或预期的,世俗化的时代精神究竟会为哪一 种变数敞开空间,这只能在世俗化的进程中寻找答案。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思想便因此而无所 作为,能否在以上四种变数之间(“神律”取向、“内在”超越、社群主义、后现代主义)建 立某种新的综合,是完全值得当代思想界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注:德国汉学家卜松山(Karl-Heinz Pohl)在《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一文中曾试图就社群主 义与儒家思想作一比较与会通,见卜松山:《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刘慧儒、张国刚等译 ,中华书局2000年10月第1版,第47~74页。而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所谓“内在超 越”)的发掘与阐发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视为一种对西方文化神律取向的“回应”。至于具有 “颠覆”与“解构”性质的后现代主义,则可以通过适当的“转换”而充当前三种变数的“ 解毒剂”,起到预防虚假的神律(或不真实的集体主义)对个体生命尊严的践踏之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