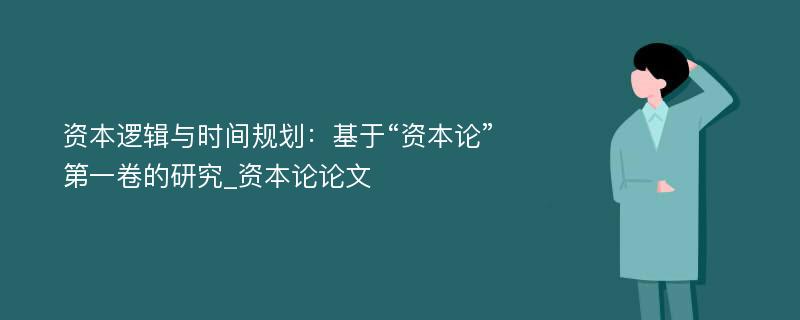
资本逻辑与时间规划——基于《资本论》第一卷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论文,第一卷论文,逻辑论文,资本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991年第10期的《哲学研究》上,刘奔先生发表了《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文,在国内率先提出了时间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揭示了时间范畴的历史唯物主义意义。(参见刘奔)之后,俞吾金先生从实践概念出发,并结合资本的运行过程,进一步讨论了时间范畴的哲学意义及其在马克思哲学中的理论地位。(参见俞吾金)这些研究打破了传统思路的束缚,形成了探讨时间问题的新的理论指向。在此基础上,按照自己近年的研究思路,笔者更愿意将马克思的时间概念与资本逻辑联系起来,从两者的关系出发来揭示时间范畴的现代哲学意义。
在过去的研究中,学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在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着从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转变,建立了以生产逻辑为基础的理论构架,《资本论》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成果。在这一思考中,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并不存在逻辑的转变。这也意味着从生产逻辑出发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资本逻辑批判的结论。但按照笔者的思路,这种逻辑恰恰是成问题的:从一般的生产逻辑出发,并不能得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逻辑,反而有可能陷入李嘉图式社会主义者的思路,即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时,提出不要资本家、但必须接受资本的解决方案。(参见仰海峰,2010年a,2010年b,2011年b)这意味着,对马克思思想的深度解释,必须以资本逻辑为核心来展开。同样,对马克思哲学中的时间范畴,也只有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才能作出清晰的阐明。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一段充满激情的文字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剧烈变化,揭示出现代社会的时间境域: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页)
传统社会中凝固化的时间被资本搅动起来,变成了吸纳一切的漩涡。这也意味着,时间已经从先验的存在状态转变为可控制的存在状态。这个过程是如何被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本质规定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此做出具体的分析。到了《资本论》,马克思则以商品生产为例,具体分析了资本逻辑与时间规划的内在关系,揭示出资本逻辑的时间境域。
一、商品的普遍化:物化时间的社会存在基础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论证了日常的此在处于一种计算化的时间境域中,这正是此在遗忘存在、沉沦于日常性的流俗时间:“流俗领悟所通过的‘时间’的种种特性之一恰恰就在于:时间被当作一种纯粹的、无始无终的现在序列,而在这种作为现在序列的时间中,源始时间性的绽出性质被敉平了。”(海德格尔,第390页)时间变成了一种线性化的、可以即时计算的东西,存在就在这种可计算性的时间中到场,成为存在者。在这个意义上,流俗时间规定了沉沦的此在。这种可计算的时间,从技术层面来说有赖于时钟的产生:“时钟如此造成的基本确定性既不在于指示时间的持续,也不在于指示时间现在的流量,而是在于持久地固定当即。”“当即是什么意思?比如,‘我当即看手表’。(……)我是否就是这个当即?其他人是否都是这个当即?如是,那时间就是我自己,所有其他人都是时间。”(海德格尔语,转引自斯蒂格勒,第252页)由时钟度量的时间成为工业化时代人们的存在境域。“‘人们’的手表以及一切钟表都指示与他人共同在世的存在。”(同上,第271页)
从海德格尔的论述来看,时钟成为时间的尺度当然是技术作用的直接后果,但这种流俗意义上的时间实际上早就被确定了,即早在人们面对太阳确定时间节气的时候,体现存在境域的源始时间就开始向平均化的时间滑落了。海德格尔的批评是一种思想史与文化史的反省。在这种反省中,技术的“座架”让所有的人都成为了无差别时间中的“人们”或“常人”。但这里的问题在于,从社会历史的意义上来说,时钟何以能够成为日常生活的时间度量器?在以循环时间为主要境域的农业文明中,即使时钟所度量的时间存在着,对人而言也并无根本的意义,因为农业生产无需精细到每小时、每分钟;只有到了工业文明之后,时钟才获得了社会存在的意义。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种农业文明的时间与工业文明的时间或许只有量的差异,但如果从马克思的论述出发,这种差异恰恰是根本性的。从社会存在或者说社会结构的变迁来说,商品的普遍化才是时钟所衡量的时间得以流行的基础。只有在这个新的社会存在基础上,物化的时间才可能成为一切存在的境域。
对马克思时间理论的上述新解读,将构成重新阅读《资本论》,并以资本逻辑为基础重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的开篇之句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版,第47页)早在氏族公社时期,商品就已经存在,因此,以商品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起点似乎不太合适。但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存在并不具有普遍性,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商品交换只具有从属的意义;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才得到普遍化。“直接的物物交换这个交换过程的原始形式,与其说表示商品开始转化为货币,不如说表示使用价值开始转化为商品。交换价值还没有取得自由的形态,它还直接和使用价值结合在一起。这表现在两方面。生产本身,就它的整个结构来说,是为了使用价值,而不是为了交换价值,因此,在这里,只有当使用价值超过消费的需要量时,它才不再是使用价值而变成交换手段,变成商品。另一方面,使用价值尽管两极分化了,但只是在直接使用价值的界限之内变成商品,因此,商品所有者交换的商品必须对双方是使用价值,而每一商品必须对它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版,第443页)也就是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并不构成社会财富的本质内容,它并不规定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才成为普遍化的存在。这是从量到质的根本性变化,而不是量的积累。商品的普遍化在社会存在的境域中形成了现代时间观念,即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当海德格尔将商品社会的时间观念与前商品社会的时间观念相等同时,从马克思的哲学来看,这恰恰是成问题的。量的变化带来的质的变化,导致了社会存在的重建。
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商品的分析,商品本身具有二重性,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前者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使用价值具有质的差别,交换则体现为一种使用价值与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商品交换的普遍化就是要将使用价值撇开,使不同的商品成为可以交换的对象,这时“它们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它们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1页)只有当一切都归结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时,商品之间才可能按照比例关系加以比较。从这个论述中可以看出,商品的普遍化是一个质性被抽离、质性的物变成了由量所规定的物的过程。在这种抽离中,不同质性的商品有了一个共同的内核,即抽象的人类劳动,这形成了商品的价值,交换价值不过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当商品之间进行交换时,它们的价值量根据商品所包含的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的量来计算,“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同上)商品交换的发展过程正是将一切都归结为可以由物化时间来衡量一切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存在从本质上来说是由物化的劳动时间规定的。商品交换的普遍化使物化时间的意义得以呈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当人们都被纳入到抽象劳动的过程中时,人们就从日常生活层面接受了物化时间的合理性,并通过商品交换强化着这种物化时间观念。
上面的论述表明,到了商品社会,其社会存在的本质规定是在物化时间的境域中实现的。从马克思的理论构架来看,以商品交换的普遍化为基础的社会,其内核是资本逻辑,这也意味着,资本逻辑与物化时间具有同构性。资本逻辑在其根本的规定上,决定了社会存在的自我抽象过程;这种自我抽象将物的质性抽离掉,使之成为可以比较的商品,这才是物化时间的社会存在基础。海德格尔所说的量化的时间,只是到了资本逻辑统摄一切的时代才成为社会存在的境域。
那么,在时间问题上,海德格尔与马克思有什么不同吗?他们有相同的地方,即两者都意识到现代时间的物化与量化,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视角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按照笔者的理解,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着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逻辑与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逻辑,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具有统摄地位。只有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生产逻辑,但如果从生产逻辑出发来类推或界定资本逻辑,恰恰无法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从马克思的双重逻辑的视角来看,海德格尔考察时间的起点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其关于时间的量化的论述,是从此在的沉沦状态——“烦”着手的,“寻视估算的烦忙首先揭示时间并形成计时,估算时间对在世起组建作用。寻视以烦忙的方式进行揭示;凭借计算时间,寻视的揭示让被揭示的上手事物与现成在手事物到时间中来照面。世内存在者于是作为‘在时间中存在着的东西’得以通达。我们把世内存在者的时间规定性称为时间内性质或时间内状态”。(海德格尔,第394-395页)用马克思式的话语来说,这里的烦忙就是指向对象的一种劳作,可以用生产逻辑来指称海德格尔关于烦忙的论述。按照马克思的视角,海德格尔并不关注资本逻辑,他关注的是生产逻辑,然后以生产逻辑来统摄他所生活的技术化社会。在海德格尔的这一思考中,资本逻辑所统摄的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并无根本的区别。而在马克思的思考中,这两个社会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以致无法以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逻辑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以资本逻辑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到达现代社会的根基处。可见,海德格尔关于时间的讨论,只有置于资本逻辑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历史性的说明。
二、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物化时间的计量
上面从社会存在论的视角讨论了量化时间的社会前提,这是通过分析商品及商品交换得到的理念。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与商品交换只是资本逻辑的现象界,资本生产的过程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所在。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在商品生产中,资本家关心的是以下两点:第一,生产出具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即生产出用来出售的商品;第二,要使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大于生产该商品所需要预付的价值总和,即生产出剩余价值。(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17-218页)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存在着两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两种形式都涉及对量化时间的规划与榨取。也正是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可计算的时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义才充分显现出来。下面主要分析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
以马克思所举的棉纱生产为例。假定劳动力出卖时的日价值为3先令,体现了6个劳动小时,这也是生产出工人每天平均的生活资料量所需要的劳动量。纺织工人1个劳动小时内把12/3磅棉花转化为12/3磅棉纱,即6小时把10磅棉花转化为10磅棉纱,这个劳动时间的价值量为3先令。假定10磅棉纱中对象化了21/2个工作日,其中2日包含在棉花与纱绽中,1/2日是在纺纱过程中被吸收的。这样,整个10磅棉纱的价值是15先令。这时,产品的价值等于预付资本的价值,永远也不可能生产出剩余价值。如果是这样的结果,资本家不如将这些钱挥霍掉。马克思接着指出,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但这只需要半个工作日就可以生产出来,而工人的劳动时间实际上是一天,按12小时计算,那么,有半个工作日是免费劳动的。根据上面的同样比例,工人劳动一天,除了生产出付给自己的工资3先令外,还有3先令被资本家拿走了。这个3先令就是剩余价值,它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即延长半个工作日得来的。
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体现了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在这个统一中,劳动过程的实质在于生产出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而价值增殖过程则体现出劳动的量的方面,“所涉及的只是劳动操作所需要的时间,或者说,只是劳动力被有用地消耗的时间长度”(同上,第228页)。这里,我们再一次遇到马克思思想中的双重逻辑问题,即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问题。而只有当资本逻辑统摄生产逻辑时,劳动的量的规定性才成为劳动过程的主导因素。只有当劳动的量成为主要因素时,劳动过程才可能按照量化的时间来计算、来比较,说它等于若干小时、若干日等等。复杂的劳动需要更多的生产费用,因此具有较高的价值。但复杂的劳动可以换算成简单的劳动,因此珠宝细工的劳动与简单的纺纱劳动在质上没有完全的区别。“在这两种场合,剩余价值都只是来源于劳动在量上的剩余,来源于同一个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的延长。”(同上,第230页)
以上所述虽然揭示了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源自于劳动时间的延长,即超出了补偿工资的劳动时间,但在具体论述中,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具体要素都被看作是量化的存在来分析的。比如在棉纱的生产中,关注的是物化在棉花中的具体劳动时间、支付劳动工资的具体劳动时间,然后计算出未付工资的劳动时间。按照这一思路,剩余价值似乎只是在最后半天才生产出来的。
这当然是认识上的盲点。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就曾指出,蒲鲁东想以等量劳动换取等量劳动,以同等劳动时间来对等同等劳动时间:“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的;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现在已经不用再谈质量了。只有数量决定一切:时对时,天对天;但是这种劳动的平均化并不是蒲鲁东先生的永恒的公平;这不过是现代工业的一个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版,第97页)也就是说,如果只看到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一种时间的延长,这只是从时间等量的角度来解决问题,而没有理解造成这种延长的背后原因,依然没有击中问题的要害。从价值增殖的视角来看,这种物化的时间是以本文第一部分所论述的商品普遍化为前提的,商品的普遍化实际上就是资本的普遍化。根据马克思的讨论,能够以时对时、天对天作为衡量劳动的标准,在其具体表现上就是以钟表时间为计量标准,这是以社会关系的全面资本化为基础的,在此基础上才有时间的全面物化。因此,如果不能从社会关系的资本化视角来分析剩余价值的形成,而只是作单纯的时间比较,并不能通达问题的本质。所以,马克思在完成了从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相统一的视角分析剩余价值的时间性后,接着就从资本的视角展开分析。这不只是问题的进一步细化,而是一种新的分析路径,就像以资本逻辑来分析生产逻辑一样。
在分析一般劳动过程时,马克思曾指出其有三个简单要素:“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08页)购买这些要素需要预付货币,从资本和价值增殖的视角来看,购买劳动力的货币即为可变资本,购买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货币即为不变资本。这样,适用于一切劳动的要素在资本主义社会就变成了价值增殖过程中的资本,因此,关于“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讨论,是一种视角的转换,而不是问题的细化。在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劳动一方面创造新价值,另一方面将不变资本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虽然这个过程有赖于追加劳动的特殊的有用性,但“他通过自己的劳动加进价值,并不是由于他的劳动是纺纱劳动或木匠劳动,而是由于他的劳动是一般的抽象的社会劳动;他加进一定的价值量,并不是因为他的劳动具有特殊的有用的内容,而是因为他的劳动持续了一定的时间”。(同上,第233页)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在同一时间内产生出双重结果:“新价值的加进,是由于劳动的单纯的量的追加;生产资料的旧价值在产品中的保存,是由于所追加的劳动的质。同一劳动由于它的二重性造成的这种二重作用,清楚地表现在不同的现象上。”(同上,第234页)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二重性,从根本上保证了从计量时间去计算剩余价值的可能性。
从价值增殖的过程看,劳动时间改变了事物的存在方式。对于劳动力而言,在现代社会,只有价值增殖意义上的劳动才能使劳动力得到存在与延续,人类最初的自我保存的本能变成了资本自我保存的工具。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尼采对人类自我保存观念的批判(参见尼采,第230-232页),这也构成了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的一个重要主题(参见霍克海默、阿多诺,第22-35页)。从不变资本的构成来看,原材料与附料随着劳动时间而消失,其原来的价值也随之消失,但这种消失是为了重生,并以新的使用价值的形式表现出来,原材料与附料的价值以及新加进的价值,都通过新的使用价值的载体而呈现自己。这是一种否定,但这种否定并不是全部抛弃,而是变形与重生。劳动资料如机器、厂房等,则在一定的周期内实现自身价值的转移。不能重新进入价值生产过程中的上述排泄物则成为废物。这种废物不仅包括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而且包括不能重新进入劳动过程的劳动力。从根本上说,与剩余价值生产相关的这种计量时间,是最合乎物的时间。这种物不是有其自身物性的物,而是处于剩余价值生产图景中的物,是可以按照计量时间来计算其价值的商品,是实现剩余价值的载体。
根据上面的论述,一定时间内的劳动的凝结成为价值的来源,新产品的价值可以用如下的公式来表述:产品价值=C+V+m。C即不变资本,V即可变资本,m为剩余价值。如果我们以12小时为一个工作日,其中6小时为支付工人工资的必要劳动时间,那么,m就为6小时劳动的凝结物的价值,而C的价值则在劳动过程中转移到新产品了。结合前面所举的例子,可以用具体的数字来表述上述公式:
30先令的棉纱价值=24先令(C)+3先令(V)+3先令(m)
这里的时间还是从计量的、可直接分解的意义上来理解的。按照这种解释就会产生一种假象,即只有在后面的6小时里才存在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在前6小时里,工人则在生产出自己的必要生活资料所体现的价值。正是根据这种计算方式,西尼尔在经过一番计算之后认为,英国棉纺业工厂主的纯利润及其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取决于“最后一小时”。如果以12小时为一个工作日,假如前11个小时都用以抵消已经消耗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那么这最后一小时才是创造利润的劳动时间,所以如果将这一个小时取消了,棉纺业就不可能获得发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58-264页)“最后一小时”的论证当然有其特定的背景,即与当时工人争取缩短劳动工作日的时间有关,而如果从计量时间的角度来看,这种算法似乎又是合情合理的。
这种算法当然是错误的。根据前面的讨论,在每一个单位的劳动时间内都存在着旧价值的转移与新价值的创造,这也意味着,在每一个单位的劳动时间内都存在着剩余价值的生产,价值转移与新价值的生产是同时进行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计量时间合乎资本逻辑的内在要求,但计量时间在一定的意义上又可能成为遮蔽资本逻辑的烟幕。剩余价值不是在最后一小时才生产出来的,它产生于生产过程的每时每刻。
三、工作日与物化时间的制度化
绝对剩余价值的多少,从时间的维度来看取决于劳动时间的长短,因此,延长或缩短劳动时间就成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的关键。对于资本家来说,作为资本的人格化的载体,“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69页),尽可能地延长劳动时间。但这种延长有其自身的界限:一是劳动力的身体界限,即工人需要一定的时间恢复体力;一是道德界限,即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这决定了工作日是在这两个界限之内变动的。假定工人为购买生活资料需要劳动6小时,工作日的长度是10小时,4小时是剩余劳动时间。对于资本家来说,或者将劳动时间再延长2小时;或者在工人的斗争下,将劳动时间压缩到8小时,这都没有改变剩余价值的生产的本质;但如果将劳动时间缩短到6小时,剩余价值就无法生产出来了,因此,6小时就是缩短工作日的下限。即使是无限地延长工作日的时间,也不可能超过24小时,否则工人就无法恢复劳动力。延长与缩短工作日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限度内展开的。
从历史上来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曾存在过通过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生产生活资料的情况,那么这种追加劳动时间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有什么区别呢?马克思做了如下解释:第一,除了在谋取独立的货币形式的交换价值的地方有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外,在追求使用价值的社会中,剩余劳动受需求范围的限制,这种生产本身的性质不会造成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的需求。因此,非资本主义生产中的追求超额劳动时间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存在着质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以商品交换的普遍化为基础,以资本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只有这时才会导致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第二,从剩余劳动时间的表现形式来看,也存在着差别。比如在封建徭役劳动盛行的地方,农奴为自己的劳动与为农奴主的劳动,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是分开进行的。从时间上来说,农奴在每周内有3天为自己劳动,还剩3天为农奴主劳动,这个时间是可以清晰划分的;而在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虽然上面的讨论将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也做了区分,但在实际劳动过程中这两种时间是无法分割的。从时间流失的空间境域来说,农奴为自己的劳动与为农奴主的劳动在空间上同样是分开的;而在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农奴劳动中的两个空间被整合在一起,这更便于提高一定时间内的生产效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72-281页;另参见仰海峰,2011年a)虽然这两种劳动形式存在着质的差异,但即使在农奴制时代,为了将追求剩余劳动合法化,统治者也曾以立法的形式将剩余劳动时间固定下来。马克思曾以多瑙河流域的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公国的“组织规程”为例,说明农奴为自己劳动与为农奴主劳动的时间比例。实际上,这种宪法性的强制规定是农奴时代将剩余劳动时间合法化的途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74-277页)当然,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当农奴的这两种劳动的时间比例被法律规定下来时,农奴也就无须提供更多时间的剩余劳动。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商品交换规律本身并没有规定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家可以在劳动力的身体界限和道德界限的范围内无限制地延长劳动时间,于是,延长或缩短工作日的斗争就成为工人与资本家斗争的一个主题。对于资本家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榨取剩余价值的做法,不仅工人斗争激烈,而且其危害也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并派出工厂视察员进行调查和监督。根据工厂视察员提供的报告以及政府的调查报告,这种延长劳动时间对工人带来了一系列的后果:第一,由于无限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对工人、特别是童工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根据1860年1月17日伦敦的《每日电讯》报道:“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呆痴,麻木得像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82页)长期的过量劳动使工人疾病缠身,甚至饱受折磨而死,这是早期工人未老先衰、过早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为了突破工人身体的界限,工厂主通过换班制度来保证机器生产的连续性,使工人日益成为机器生产的附件。比如桑德森兄弟钢铁公司在解释为什么要进行夜班生产时就指出:“凡是只在白天开工的工厂,都会遭受到这种由于机器停着不用而造成的损失。但是我们使用熔炉,损失就更大。”(转引自同上,第304页)这意味着工人晚上的睡眠时间正是保证机器运转的时间,这个时间不利用,机器、厂房、原料等也随之丧失了资本的性质。第三,长期的过量劳动使人精力难以集中,带来生产安全问题。马克思以火车司机、列车长、信号员的过量劳动造成事故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第四,由于过量劳动造成了工人身体素质的下降和死亡概率的增加,人口过剩就成为维持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一环。当工人人口的衰退无法在城市得到补充时,就只能从农村中吸取新鲜血液。在这个意义上,农村的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正是因为这些影响加上工人的斗争,政府的劳工法、工厂法等相继出台,对工人的工作时间进行限定。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主义初期,劳工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延长工作日,而不是像18世纪之后是为了缩短工作日。这个区别反映了另一个问题,即在资本主义早期,并不像斯密所说的那样,经济的发展不需要国家的干预;相反,恰恰是国家的干预推动了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参见李斯特,第31章)比如在1349年爱德华三世颁布的第一个劳工法,就以当时鼠疫猖獗、雇不到劳动力为由,强制规定工作日的长度,并强制规定了“合理的”工资。只是过了几个世纪之后,“自由”工人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按照日常生活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时缩短工作日才成为劳工法的一项内容。
当工作日的长度以法律的方式规定下来时,意味着工人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的妥协,这时与剩余价值生产相关联的时间也随之获得了法律的保证,剩余时间被合法化、体制化了。比如英国1850年的工厂法,“把受它约束的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人的工作日都纳入法律限制之内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340页)当工作日的长度被限制之后,工人体力与精神的恢复更快了,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工人在较短的时间内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限制工作日的长度获得了道德说教的意义。另外,对工厂法的服从也表明:工人是无法反抗资本的力量的。这就正如尤尔所咒骂的,“英国工人阶级洗不掉的耻辱就是,他们面对勇敢地为‘劳动的完全自由’而奋斗的资本,竟把‘工厂法的奴隶制’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转引自同上,第346页)其实,工厂法的实施也进一步表明,只有在现代时间的境域中,才能理解“自由”的含义。工人在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后才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大宪章,代替了‘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这个大宪章‘终于明确地规定了,工人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同上,第349-350页)应该说,从商品交换中对物化时间的度量到劳动力交换中物化时间的量化,再到物化时间的制度化,体现了时间的现代社会建构过程,也是资本逻辑规划的结果。
四、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与自由时间的解放意义
实际上,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缩短工作日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就只能增加劳动强度,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马克思的论述中,这就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时空间规划就显得非常重要。(参见仰海峰,2011年a)当必要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而日益缩短时,就会增加工作之外的自由时间,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可能性的条件。可以说,自由时间是人的自由发展的境域。
但这并不意味着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必然地会带来自由时间的增加,这个过程仍然是充满矛盾的辩证过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机器在现代生产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这是马克思在论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将分工、机器、大工业纳入进来的原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劳动时间具有双重效果:一是产生延长劳动时间的要求。机器的运转具有不需要休息的特征,因此依附于机器的劳动者最好也不用休息,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机器的生产职能。工人之间的轮流倒班解决了这一问题。二是迫使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增加劳动消耗,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更紧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虽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了、空闲时间增加了,但这是以劳动力的高度紧张为前提的。这一点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更为明显。
随着泰勒制的发明与福特主义的推广、劳动强度的加大和生产能力的提高,工人的空闲时间也增加了很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有了发展自由个性的“自由”时间。正如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讨论的,机械化的生产使人越来越成为机器的附庸,从肉体到心灵都被物化了。(参见卢卡奇,第145-154页)葛兰西同样意识到这一问题。他在论述泰罗制与福特主义时就指出:“泰罗的确极端恬不知耻地表达了美国社会的目的:在劳动者中间发展机器的和自动的技能至于最大程度,打破要求一定程度地发挥劳动者智力、幻想和主动精神的熟练和专业劳动的旧的心理生理关系,把一切生产作业都归结到它们的体力和机器的一面。”(葛兰西,第403页)为了缓解这种物化的肉体与精神,空闲时间成为工人的自我放纵时间,酗酒与性放纵成为工人缓解压力的方式。而对于福特主义的生产过程来说,“需要工作者‘合理地’花费更多的钱来维持和更新自己,并且尽可能地加强自己肌肉和神经的工作能力,而不是为了破坏和损毁它。于是反对酗酒这种破坏劳动力的最危险的原因就成了国家的职责。”(同上,第404页)另外,机械劳动的强化很可能会导致一种极端的情况,这就是后来者马尔库塞所说的,导致人的单向度发展。(参见马尔库塞)与这种单向度发展相一致的,就是在休闲时间里人沉迷于物化社会的各种消费与休闲规划中,这是福特主义之后、消费社会兴起时的一个重要问题,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的批判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讨。(参见鲍德里亚)当然,这些问题已经超过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直接问题域,笔者已在其他地方进行了探讨,这里不再多述。
因此,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并不必然地意味着自由时间的延长,这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但从另一个层面也可以设想,当工人可支配的时间增多时,即使这些时间已经被消费社会所规划,但还是为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的境域;即使是量的积累,也可能会造成质的变化,就像商品交换从量的积累导致其质的变化一样。但当这种变化降临时,它必须是社会存在层面的结构性转变,是一种结构性的关系转型。应该说,只有在这种结构性的关系转型中,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才会带来自由时间的增加。与此同时,必要劳动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马克思在论述共产主义社会时所说的,劳动成为一种需要,即成为体现人的个性与本质力量的需要。对于这种时间转变的节点,马克思设置了两个内在的条件:一是资本逻辑达到了自己的极限;一是无产阶级能够意识到自己就是改变这个社会的主导力量。这两个条件合而为一时,才可能导致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才能真正成为人的个性发展的时间之维。(参见马克思,第926-928页)这当然是一种文明样式的转变,只有在这一新的文明样式中,自由才会现实地体现出来。
标签:资本论论文; 剩余价值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交换价值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剩余价值规律论文; 逻辑分析法论文; 时间计算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逻辑与论文; 社会存在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