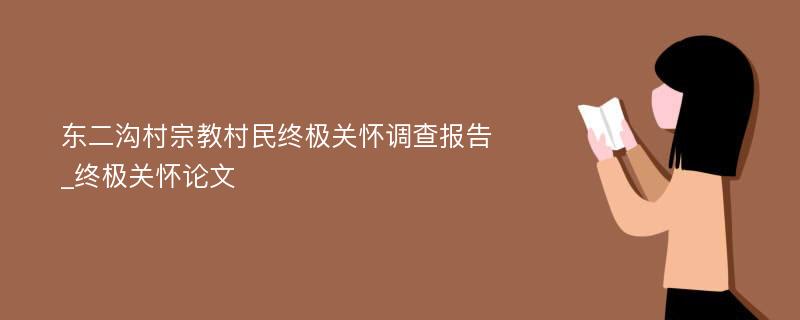
关于洞儿沟村信教村民的终极关怀的调查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调查报告论文,村民论文,洞儿沟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人所最终关切的自身的存在及其意义的“终极关怀”,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的一种内在的精神关切,但是精神的东西总是要外化为人们的行为取向和某种制度规范、风俗习惯。我们采用访谈方法,通过对一个比较典型的由天主教信徒组成的村庄洞儿沟村的调查,看一看“终极关怀”到底对人们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一、洞儿沟村概况
洞儿沟村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姚村镇。该村总人口为1196人,总户数为263户,信仰天主教的村民比例为100%。村民主要以务农为业,种植果树,农闲时在附近村子打些散工,做点石匠活儿。该村经济比较落后,村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不大,有50%的农户享受低保待遇。
洞儿沟村的天主教会是天主教太原教区的下属堂口。目前,该教区有神父一位,修女若干。洞儿沟村有教堂一座、方济各修道院一座(已废弃)及神职人员的住所、外来朝圣者的住所、食堂等。另有圣母七苦山,山上有“上天之门”、祭坛、圣殿。山上的原有建筑都在“文革”中遭到很大破坏,现在是“文革”后新建的,它们仿照巴黎凯旋门和北京的天坛、太和殿。登上“上天之门”的石阶,扶手上交替有狮子和天使的石柱雕刻,十字架及两边的卧龙立在“上天之门”和圣殿的顶盖上。洞儿沟村民居的门楣上写着“沐浴主爱”、“主赐安康”,“四海黎民沾主泽、三晋花鸟浴神恩”、“百顺风调主降祥、民安国泰天心顺”等等。也有把大大的“福”字倒贴在门上的农户。
“天使”和“狮子”共存,“十字架”与“卧龙”并立,“沐浴主爱”与“期盼福到”同在,这些都是中西文化结合后的产物,带有一定的地方特色。这也说明,就是像天主教这样纯粹西方来的文化形态,一旦来到中国,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本土的色彩。
二、教会·村委会·家族
作为一个天主教势力占优势的村庄,神学教会组织、世俗社区组织与传统家族组织的状况及其关系如何,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从中可以折射出村民对终极关怀的眷注。
(一)教会
洞儿沟村只有300年左右的历史,起初这里只住有一户人家。当村子定居有100多人的时候,传教者来到这里,教会力量由此巩固并发展。现在,教会在社会整合和公共福利方面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
1、社会整合
洞儿沟村基本上每天都有弥撒活动(除非神父外出),届时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走进教堂,念经、祷告。在婚配弥撒和“开圣体”等圣事活动中,村民们会在教堂里为两位新人和已满十二、三岁的孩子或新入教者做见证并祷告。在每年的圣诞节,村里还有台圣诞晚会,村民自己编演天主教题材的小品、相声、歌伴舞等节目,有时还会有知识竞赛、拔河比赛等。
洞儿沟村的教会有一个西洋鼓乐团。它是由一些村里的中年妇女组成。她们有自己的服装、乐器,生产生活之余从事排练活动。在教会的大型活动中,会看到他们的表演。这个鼓乐团也会像社会上其它的鼓乐团一样,出现在一些社会上的节日、婚礼庆典活动上,收取一定的费用。
教会的唱诗班也是由村民自己组成,村中的男女老少都可以参加。
洞儿沟村还有一个非固定成员的组织,叫临终组。全村划分为四片,每一片有一个临终组。临终组的任务是,为本组所在的片区的生命临终者读经,一直到下葬。
教会的辅祭员和读经员都是村里的孩子。男童到了一定年龄,可以报名当辅祭员,经教会选拔确定后就可以在圣事活动里辅助神父。辅祭员分三类:辅祭的、执蜡的、提吊炉的。在唱弥撒,也就是大型的弥撒活动中,通常需要两位负责辅祭的,两位负责执蜡的,一位负责提吊炉的。在日常的小型弥撒活动中,只需要两位负责辅祭的人员。男童一般到上中学的年龄,由于学业的负担,就不再做辅祭员了。读经员没有性别限制,经过报名确认后,就可以在天主堂内的读经台上为大家读经了。
2、公共福利
洞儿沟村天主教会主办了两个社会化组织机构:幼儿园和孤儿院。
幼儿园叫“小天使维礼幼儿园”,于1995年9月开始由村委会办。1998年的时候,在教会的大力资助下开始新建,1999年12月开始使用,2000年9月全部工程竣工,累计总投资100万元。改造后的幼儿园占地面积扩大到3600平方米,并且引进《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和《蒙特梭利教学法》,在2000年时,升级为“三星级幼儿园”。幼儿园对外村也是开放的,有专门服务外村儿童的接送车。幼儿园现有儿童180人,教师20余名。
幼儿园运作的主导力量是教会,园长和后勤处主任都是修女,其余老师是本村及外村的村民。幼儿园的立足点是为村里的儿童提供尽可能完善的培养和教育,收费只是象征性的,本村儿童20元/月,100元/学期,外村儿童140元/学期,远远低于同类幼儿园的水平,充分考虑了农民的贫困状况。教会每年贴补的金额大约为二、三万。
孤儿院的名字是“圣神启智中心”。于1994年开始收养弃儿,是非营利的民办机构,收养人数不定,近几年保持在40名左右。他们大多是小至初生婴儿,大到二十几岁的不同程度的残疾弃儿,如患有唇腭裂、脊柱裂、脑瘫等。这些孩子起初都是被遗弃在教堂或孤儿院门口,被孤儿院收留。孤儿院对弃儿实施语言训练、康复训练、引导式训练。力图增强他们的语言表达、自我照顾等方面的能力。
基于缺乏资金、弃儿需要家庭温暖等原因,教会出面联系上了一些外地教友,将弃儿寄养在了教友家。所以,目前孤儿院暂无孤儿。对于村里的孤寡者、老年人、久病者,教会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一些重大节日,神父、会长、修女等教会人员会去探望他们,给他们送钱、送食物、送衣服等。
由于洞儿沟村的贫困状况,教友的奉献能力比较有限,教会的日常运作及善举的施行会依靠上属教区的力量及外地教友的奉献。
(二)村委会
洞儿沟村的村干部是民主选举产生,请客送礼拉选票的风气比较淡,大姓家族对选举的影响作用也不是很明显。村民大会一般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村民参加,相对于周围村庄,洞儿沟村的这个比例较高。
洞儿沟村村干部的作风以及干群关系比较好。由于村子比较贫穷,村大队部还是教会给盖的,甚至村里欠的电费还得由村干部拿出自己的钱贴补。
教会和村委会,用村民的话说:一个关乎灵魂,一个关乎生活。二者彼此独立,少有矛盾,同时,作为教友的村干部十分尊重教会。村委会的村务公开,教会的账目一般是不公开的。
(三)家族
在中国的大多数农村,家族势力盘根错节,直接影响到农村的民主建设和社会面貌。而洞儿沟村村民却有一种其为上帝共同子民的观念。该村有四大姓氏:刘、武、张、段,但由于受天主教的影响,村民家里不留牌位,家族的观念在这里十分淡薄。
三、村民心态
人们的终极关怀常常表现为一种心态,而这种心态又最能从人们的婚丧嫁娶以及日常社会生活中体现出来。
(一)婚育生死观
洞儿沟村村民一般选择有同样信仰的人为配偶,如果是无信仰者也会在婚前或婚后动员其入教。另外,村民们一般要避免在同宗的五代之内的族人里择偶。
洞儿沟村的村民结婚有两套仪式,一是带有宗教色彩的“婚配”,二是具有世俗性质的“婚礼”。
“婚配”仪式是在教堂举行,它可以有两个时间,如果是当天举行婚礼的话,就是中午12点举行婚配仪式;如果不是当天举行婚礼,就是晚上6点举行“婚配”仪式。
具体的婚配过程如下:
婚配过程之前,在教堂的忏悔室里行告诫圣事,这样就获得了赦免,接下来就可以进行婚配圣事,领圣体了。
婚配过程开始:鼓乐团在前面,依次是神父和两位新人。神父将两位新人领到圣体跟前,神父本人站在祭台上,宣誓活动开始。宣誓内容是关于遇到困难、挫折,双方不离不弃,宣誓完毕后双方互赠戒指。在宣誓过程中有神父,男方、女方各请的一位同性,全场的教友会为他们做见证。
整个婚配的主体部分就结束了。然后,就是行拜谢礼和奉献礼。
世俗婚礼形式与其他地方一般群众的婚礼大致相同,一般是在家中举行。家里会有专门收礼金的账房,会用小汽车迎娶新娘等等。但是也会有一些天主教的痕迹,例如圣母像会置于家中的院子里(因为整个婚礼过程都是在院子里举行的),新人并不是一拜天地,而是首先向圣母像三鞠躬,然后才是拜父母。
由于婚配弥撒的举行就意味着双方对此婚姻的绝对忠诚,违背它就是在犯罪,会受到终极审判,所以,村里的离婚现象几乎没有。如果是双方实在感情不和,可以分居,但是双方均得独居,而且也不离婚。
在洞儿沟村,传宗接代的观念不是很浓,对于不能生育者,村民们也不会有什么不好的看法。基于对天主教教义的尊重,村民们不太能够接受计划生育政策,平均每户家庭会有3个孩子。
在洞儿沟村,神父在教友从病危到辞世,再到下葬的过程中的作用是明显的。神父会为教友送圣体、祷告,在死者的下葬仪式上,神父会为死者铲下第一铲土。到每年11月2日天主教的追思亡灵日的时候,神父会带领人家一同到教会陵园为已亡者祷告。整个村子不过清明节。
除了病危教友的亲人会陪伴在他身边外,临终组和一些其他教友会在这期间每天来为他念经祷告。在教友亡故后,人们也会用念经祷告的方式来追思他或者保佑他升天堂,而不是送花圈。
亡故教友的墓碑上刻着十字架、天使,亡故者的姓名表示依次是:姓氏、圣名、字。除了这些天主教的特色外,洞儿沟村的教友也会有些很传统的做法,比如,人死后门上要贴白纸;亲人披麻戴孝;三年守孝;年幼的在家停棺五天、年老的在家停棺七天。
(二)环境民风
洞儿沟村村民有植树造林的习惯,极少乱砍乱伐。他们通常不会把羊赶到山上破坏植被,这完全是一种为了下一代的自觉行为。守护圣母山的老伯也在长长的山路上种了许多的花草树木。
洞儿沟村没有村办企业,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受限,但即使这样,村民还是拒绝了某老板要在村里投资建焦化厂的计划。
洞儿沟村的治安非常好,村民们甚至有时外出都不锁门,偶尔有失窃的现象发生,但都是外村人所为。打架、邻里纠纷也少有发生。赌博的现象也几乎没有,据村长说,村里会打麻将的人不超过20人。同时,村民们普遍比较勤劳,很多外村人需要雇工时都选择洞儿沟村人。村民们大都有一种奉献精神。教堂里有奉献箱,村民可依自己的力量、意愿对教堂,对圣事奉献财物。这种奉献不强迫、不留名,只是让天主、神父知道。每年村民的奉献总额大约为1万元。
在对圣母七苦山建筑修葺的1992年到1998年之间,洞儿沟村村民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出钱出物出工,竭尽所能,另外依靠教会及其他地区教友的支持,共同完成了对圣母七苦山的重建、翻新工程。
洞儿沟村有许多为教会的日常运作奉献的教友。有一对60岁左右的老夫妻,他们的家在外地,两年前来到洞儿沟村,负责给教会做饭,平常就是给几位神职人员以及寄宿于此的教友做饭,逢到夏天朝圣者集中来访的时候,二老甚至会给一、二百人做饭,但是二老每月的工资总共只有200元。圣母山的守山者是位60多岁的老伯,看守圣母山8年了,负责整座山及山上建筑的卫生、安全,他的妻儿住在山下,平时独自吃住在山上,每月工资是400元。
一位50岁左右的妇女是个菜农,她除了在星期天休息外,每天都起早贪黑,很辛苦地赚钱,但她有时会把一些菜按进价卖给教会,以获得天主的保佑。
由于从小在天主教的环境下长大,一些村民到了一定年龄就决志要为圣事服务,读修道院,准备做神父或修女。目前,属于洞儿沟村村籍的在职的神职人员或者在读修道院的人共有十位,现在的天主教太原教区的主教就是洞儿沟村人。
洞儿沟村村民尽管仅依靠务农而生活水平比较低,但村民很少有远出打工的,通常只是在附近村里打些散工。这一方面由于山西人的乡土情结,另一方面是出于对远出打工可能会沾染上一些不好习气的担心。
教会的运作经费很多都依靠村外的力量;每年还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天主教教徒来这里朝圣,届时教会的老年组、祈祷组、礼仪组、唱经班等都会来负责接待朝圣者。
四、小结
洞儿沟村天主教会主办的幼儿园以及面向弱势者的福利给村民们带来了很多实惠;教会的运作、管理需要教友的广泛参与,这使得村民们形成一些组织成为可能。教会使洞儿沟村更加社区化。在天主教的氛围中生活,村民们有很多接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念经、祷告、听神父讲道,奉献、忠贞、勤劳等观念渐渐内化于心。另外,村民们参加的各种关于教会的组织使他们具有了一定的协作精神和凝聚力。
通过调查可以发现,宗教正是通过种种集体仪式,培植民众的“亲和力”、“聚议性”。宗教交流生活有利于提高世俗生活中民众的社会境界、道德自律、超越意识、公共秩序感。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可以发挥其可能有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