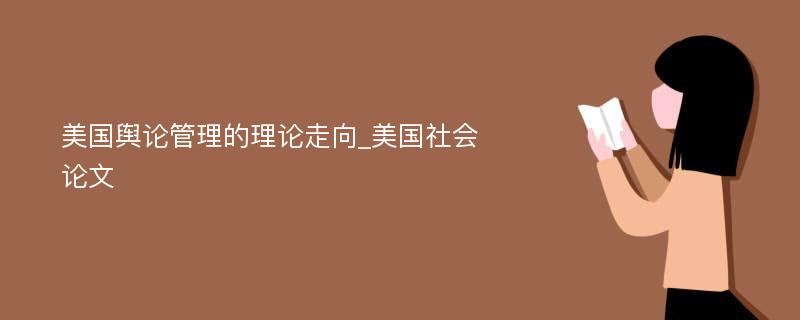
美国舆论管理的理论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动向论文,舆论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0)08-0095-06
言论自由被认为是美国的立国之本,相应地,美国的舆论民主制度也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典范。然而,正如许多美国文化批评家所指出,美国的社会舆论并非如人们所臆想的那样任凭意见市场的“自然进化”,它不仅一再被仔细“塑造”,而且在一定界域内加以“模式化”,其最好的明证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政府通过“制造”人民的“同意”,使美国在海外实施暴行的同时,还保持着世界上最自由国度的形象。然而,这种“形塑”舆论或“制造同意”的技术,实际上并非美国政府的新发明,它缘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国的宣传战以及美国大企业在20世纪初发起的公共关系运动,成为战后美国大政府时代以来的舆论管理和政府传播的主要内涵。
一、从宣传的衰落到舆论管理的登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时宣传引起了不同领域学者的关注,某些夸大宣传作用的著作引起了西方人对宣传的恐惧。正是在这个时期,“宣传”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获得了贬义,“宣传成为战后醒悟时期的一个替罪羊”①,被认为是不诚实的操纵。“一个词语出现了,它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发出了不祥的叮当声,这就是‘宣传’。……它通常是人们咒骂的对象,也因此成了人们兴趣的焦点、讨论以及研究的对象。”②
1927,拉斯韦尔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的宣传技巧》刊行时,评论家称其为“马基雅维利式的教科书,应当马上予以销毁”③。整整10年后,拉斯韦尔在美国《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书评文章中使用了“舆论管理”④(management of public opinion)一词,标志着“舆论管理”作为一个新的概念进入美国政治,同时也表明美国宣传分析的领军人物已经注意到了宣传的衰落。
法国学者马特拉认为,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主要贡献是指出“政府管理舆论的必要性”,美国大萧条时期的新政则促成了“在工业化社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国家为寻找‘走出危机’的策略而呼唤‘传播技术’的援助。舆论管理成为持续不断的研究对象。”⑤尽管在实践层面上清晰地区分宣传与舆论管理的差别并不容易,但一种理论关键词的变化,则必定预示着社会心理与现实的颤变,以及由此引发的学术转向。
20世纪20至30年代是西方宣传分析的黄金时期,代表着早期传播学的一种重要类型,然而,随着宣传一词在西方变成一个贬义性的概念,人们不再把政府诉诸宣传的手段和行为视为理所当然。二战后,随着“传播学”最终替代“宣传学”登上历史舞台,宣传分析被纳入到传播学研究的体系之中,与此相应,“舆论管理”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美国政治和学术研究的重要话语。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理解,战后美国大政府时代以来,“政治精英的组成人员在两个方面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一是擅长舆论管理的政客,一是为民事与军事服务的行政管理人员。”⑥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指出:“舆论管理,被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杰出技术,现在正日益成为政府和商界的日常生活。”⑦
这一时期,发端于20世纪初叶的美国大企业公共关系运动,成为战后美国舆论管理概念的重要来源。美国公关界人士于1960年代指出:“我们中间有些人认为,计算机将取代大众传播的作用,‘舆论管理’将应运而生,以取代长期被遗弃的‘认可工程’。”⑧这也就是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企业公关人员可以通过建立大规模的数据库,随时跟踪社会舆论的细微变化,进行分众和小众化的意见管理,获得传统的大众传播手段所不能企及的公关业绩。事实上,战后美国政府虽然不再使用显性的宣传手段,但并未放弃对公众舆论的“引导”和“塑造”,只不过变得越发隐形,成为今天人们所说的“舆论管理”的主要特征。一方面,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根深蒂固,人们对“观点的自由市场”的信念与生俱来、不言自明。因此,显性的宣传手段不仅在战后美国人的观念上无法接受,而且在实践上也注定不会取得满意的效果。另一方面,新闻传媒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商业化体制,也使美国政府无法直接诉诸宣传手段,不得不借助现代传播技术以及美国大企业的公关策略,在新闻、公共关系和公共管理之间寻找平衡的支点。
1980年代,美国政治和外交史学者希尔德勃兰特(Robert C.Hilderbrand)把研究的视角指向了美国国务院与新闻界,在成书于1981年的学术专著《权力和人民:1897-1921年对外事务中的舆论行政管理》中,希尔德勃兰特教授富有创见地论证了从麦金利到威尔逊等四届美国政府在舆论管理方面的不同凡响之处。对此,有评论指出:“自新政以来美国国务院各部门一直维持着‘公共信息’的有效运转,但我们对行政管理部门在此之前的所作所为却知之甚少,此书为我们填补了这个鸿沟。”⑨1985年,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W.Steele)的《开放社会中的宣传:罗斯福时代的行政与媒体》出版,不仅在全书架构上借鉴了希尔德勃兰特的经验,而且更为详尽地考察和总结了美国新政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对舆论管理的努力和尝试。
1990年代,美国学术界进一步廓清了舆论管理的概念,并对海湾战争中的舆论管理进行实证应用研究。1991年出版的《注意力之王》指出:“美国进步时代,是舆论管理和公众意见概念化的关键时期。这一时代的政治家通过公开信息,比他们的前辈们更加有效地影响选民。”⑩1995年出版的《单一民族国家的终结》写道:“我们不再为了仇恨做好牺牲的准备,军事首脑们已经接受了‘越战’的教训,把管理舆论和集合知觉,提高到与指挥战斗一样重要的位置。”(11)
进入21世纪,美国舆论管理研究呈现出密集的态势。2002年,锡拉丘兹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森(Anderson)指出:“就舆论管理而言,政治家们需要理解,一种统一的舆论如何能够促成某种特定的政策。”(12)2003年出版的美国知名学者论文集《考量布什政府》一书中,有作者认为:“舆论管理经常意味着为公民设定先入为主的框架,以使他们适应总统对政治事件或总统行动的预想。”(13)2004年,库乌(Meganv.Vandeker Ckhove)教授在一篇演讲报告中说:“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舆论管理是外交和公共事务官以及公共关系从业者的首要任务。”(14)
2005年美国“国会研究奖”(Congressional Research Award)资助的十个项目中,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候选人派利卡(Stacey Lynn Pelika)的《舆论管理:注意力公众、政治精英与政策制定过程》榜上有名。(15)派利卡在项目概要中写到:“社会精英领跑舆论的模式,大多基于党派身份认同和个人水准上的政治信息。此类模式忽视了‘注意力公众’对舆论和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导致学术研究者局限于低水平的‘手工操作’,不能很好地解释‘精英们’如何形成有利的公众舆论。因此,在我的舆论管理模型中,‘注意力公众’作为一个整体,在政策说服的精英战略中扮演中心角色。”(16)
二、批判与实证的两种学术取向
在不断推进的美国舆论管理研究中,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集纳了政治学、舆论学、管理学、公共关系学、历史学、社会学、新闻学和传播学等多学科素养,为人们提供了跨学科的研究视域。
然而,舆论管理的概念并非不言自明,直到20世纪末,美国社会学家埃里克斯·凯瑞(Alex Carey)依然为此困惑不解,他写道:“关于宣传的重要性以及谁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拉斯维尔的基本结论与希特勒的看法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后,在集权主义德国,希特勒法西斯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了舆论管理,而拉斯维尔也在美国着手研究民主制度下对舆论管理的需求。在西方世界,尽管集权主义宣传因其民主和人身自由的丧失而遭到全面谴责,但舆论管理在民主制度下却被普遍认为是非常不错的事情,差异何在?”(17)沿着这一思路,进入21世纪有美国学者提出:“政府领导人今天用‘舆论管理’或‘斡旋’代替了宣传,这是委婉的术语还是另有隐情?”(18)
显然,舆论管理毕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管理或行政管理,对舆论管理的研究也不同于态度改变的传播效果研究。舆论管理与舆论管理研究的终极交汇点,在于对民主制度和自由价值的理解和认识,因此,研究者在宣称坚守价值中立原则时,常常流露出某种程度的批判倾向。这种批判的研究取向,与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取向占居主流的美国舆论学和传播学学术传统相颉颃,成为美国舆论管理研究的重要分支。
在批判研究取向中,不少学者对美国民主制度所面临的威胁表示忧虑,有学者认为:“战时审查权力是可以用来反对国内不同意见的一件唾手可得的武器。这样,总统的舆论管理就从积极争取舆论转向消极地扭曲舆论,这对美国民主的未来而言,构成了不祥的征兆”(19)美国舆论研究的知名学者雅各布指出:“二十世纪,自由主义民主政体不再依赖于直接的行政统治,而代之以巨大的操纵舆论的能力,制造出广泛的意见一致以及对政府行为的热情支持。”(20)一些左翼知识分子,更是直接将批判的锋芒直指美国政府舆论管理中的反共意识形态以及权力与资本的共谋或相互渗透,如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S.Herman)和诺曼·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制造同意》,罗伯特·W.麦克切尼斯特(Robert W.McChensney)的《富媒体 穷民主》等,已经成为政治、新闻、传播和舆论研究的畅销著作。
与此相反,实证研究取向中的舆论管理是不带褒贬色彩的中性词汇。据考证,英语中的“管理”(Management)来自拉丁词Managgiare,原意是指“训练和驾驭马群”(21),后引申为管理。一般认为,管理就是有效地支配和协调各种资源并努力实现目标的过程。换言之,“凡处理事物及对人的指导,使其循序进行,以达到预期目的者,统称之为管理。”(22)从这个角度上说,把舆论管理简化为控制或钳制舆论的观念是不符合英语习惯的。
实际上,舆论管理概念的提出也是西方公共关系学与管理学长期磨合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管理学人际关系学派的横空出世,现代管理学不仅扩大了管理理论的人文内涵,也将管理的概念拓展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话语。差不多也在这个时期,美国现代公共关系之父艾维·李(Ivy Lee)的“公众应该被如实告知”原则被引进企业管理,而公共关系本身也被当代学者界定为一种管理职能。显然,如果把舆论管理看作与人际关系管理、绩效管理等概念相似的动态过程,那么,舆论管理应该包括宣传、反馈、疏导和控制等一系列环节在内的一种动态的意见管理。这样,舆论管理的概念避免了“宣传”在西方语境下的贬义,成为当代美国企业和政府借鉴现代传播技术及传播学研究成果的组织化行为。
因此,美国舆论管理研究的两种学术取向,内在于“宣传”和“管理”等概念的历史演变之中,又融入了学术界对美国战后大政府时代以来公共权力全面介入公众精神生活的不同理解。其中,拉斯韦尔1926年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给宣传下的权威定义本身就已经埋下了日后分歧的种子,他认为宣传“仅仅指通过重要的符号,或者更具体但不那么准确地说,就是通过故事、谣言、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的其他形式,来控制意见。”(23)在此,“控制意见”与“舆论管理”的联系是十分明显的,这不仅是因为从意见到舆论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而且在英语世界中,舆论的最初含义是指不确定的判断,直到18世纪末期,才获得了公众舆论的明确范畴,意指有判断能力的公众以印刷刊物为中介、在讨论和批判活动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权威意见。因此,在英语表达习惯里,“意见”不仅在很多情况下可以与“舆论”互换使用,而且“公众意见”不是对“舆论”的解释,而是一个名词的同义转换。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宣传作为控制新闻流动、管理舆论或操纵行为的手段,和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一样古老。”(24)拉斯韦尔在给宣传下定义之后断言:“宣传关注的是通过直接操纵社会暗示,而不是通过改变环境中或有机体中的其他条件,来控制公众舆论和态度。”(25)
由此看来,西方社会语境下的宣传主要是被当作控制舆论的手段来看待的,由此必然导致了今天的美国学术界在宣传和舆论管理的概念使用上,始终呈现出的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同时,舆论管理研究的跨学科特色,也使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在无形中形成了批判研究与实证研究互不搭界、自说自话的学术取向。
三、现实需求与历史经验的混合动力
管理的概念进入舆论和政治的交互视域之后,舆论管理成为美国政府“制造同意”的一张王牌。在美国,舆论作为影响政治生活和政府决策的重要变量之一,始终是参与式民主理论与公共决策理论的重要范畴。美国学者认为:“舆论同政府决策之间的关系,是有关民主政体与政治权力理论的核心。”(26)“对舆论分布状态的感知,不仅会影响个人立场、社会决策以及意见的公开表达,而且,会影响人们从事各种政治行动的意愿。”(27)
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不少研究者迫切需要了解,当政府管理之“手”伸向“观点或意见的市场”时,他们最为珍视的自由是否还依然存在?退一步讲,如果政府的舆论管理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那么这种管理的界限在那里?规则又是什么?一方面,随着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最好政府,最少管理”这一原则的隐退,美国民众要求政府公权力对经济以及社会生活“从摇篮到坟墓”加以全方位的干预,遵循“最好政府,最多服务”的新原则;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政府的过度干预和权力的专横、腐败,又不会放弃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这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种社会思潮的交替和演变反映到学术研究中来,不能不呈现为对政府舆论管理行为既肯定又疑虑的矛盾心态。
正如美国学者卡普斯(Cupps)所说:“越来越多的统计资料也表明并支持了以下观点,即那些自发的、无意识的、不加限制的、没有充分考虑相关规则的公民参与运动,对于政治和行政体系可能带来功能失调和危险。”(28)这与20世纪20至30年代“阿尔蒙德——李普曼共识”(Almond-Lippmann Consensus)可谓一脉相承。阿尔蒙德提醒人们“时时切记美国公众舆论的摇摆不定和爆炸性潜质”(29),李普曼则一再证明“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利益与舆论根本无法一致。并且,公共利益只能有一个特殊阶级来管理。”(30)因而他的《舆论学》刚一问世,就被杜威称为是对民主价值理念的前所未有的指控。显然,从传统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舆论观到现实主义、精英权能主义舆论观的演变,既为美国政府的舆论管理提供了理论支撑,也同时为学术研究带来了“鱼和熊掌”何以兼得的悖论式思考。不难理解的是,越是在众说纷纭的议题上,人们越渴望贡献出自己的一家之言。
与此同时,随着舆论测量技术的精细化和日常化,美国学术界的舆论管理研究获得了新的动力。因为,源源不断的数据和全方位的议题设置,既能使政策制定者在事前及时获得第一手材料作为判断的依据,也能使研究者在事后的对比和监测变得简单易行。赫伯特·席勒(Herbert I.Schiller)指出:“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民意管理的先进机制,深深依赖着民意测验与调查。”(31)金斯伯格(Benjamin Ginsberg)断言:“通过民意调查、媒体和公关手段,现代国家已经学到了许多操纵和管理舆论的方法。”(32)如果说舆论是影响政府决策的一个变量,那么在科学的民意测验诞生之前,严格意义上的舆论管理是不存在的。沿着这一思路,不少研究者试图精确分析舆论调查与公共政策之间的联系,并对美国政府操纵民意测验结果的作法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劳伦斯·雅各布(Lawrence R.Jacobs)和罗伯特·夏皮罗(Robert Y.Shapiro)的研究证实,尼克松政府采取一系列策略,迫使民意测验机构与其合作。这种合作包括:在民意测验结果公布之前就可以获得信息,使白宫能够采取措施扬长避短;促使民意测验机构选择有利于政府的问题和措辞方式;修改测验结果。(33)
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先驱赫伯特·席勒(Herbert I.Schiller)指出:“尽管民意测验是一项以科学方法形塑的工具,但它不可能是中性的构件。…它旨在为政府、政治、经济各界的政策制定与决策提供帮助。进行民意测验,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政策行动。”(34)因此,尽管舆论调查或民意测验对任何公共决策都是不可或缺的,但任何调查又是都不完美的。或者说,“调查往往也是能提供一种关于舆论的一时‘快照’。”(35)人们不熟悉的一个词、一个含蓄的短语或一个难以被人们完全理解的提法,都会使结果出现偏差,“给公众提出什么样的问题选择结构,将引导公众的议题态度和态度体系的变化模式。”(36)比如,用“福利”替换“帮助穷人”时,结果差不多截然相反——有一半的人认为花在福利上的钱太少了,但同时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用于帮助穷人的钱太多”。美国民意研究专家约翰·扎勒认为,这种“问题措辞效应”(question-wording effects)意味着不同的问题措辞方式会在统计学的意义上极大地影响公众对某一问题的支持率,使民意测验变为舆论的“临时建构”。(37)
此外,20世纪中叶,美国新史学兴起,认为美国社会从一开始就和欧洲不同,是一个相对平等的中产阶级社会,不存在鲜明的阶级分野和激烈的冲突;历史上的各种斗争都是在美国人共同的价值基础上、在美国宪法的框架内进行的;美国人向来保守,激烈的变革和美国无缘;所以一致性和连续性乃是美国历史的本质特征。(38)美国史学研究从“冲突论”到“和谐论”的转向,令美国舆论研究者大有茅塞顿开之感,他们在历史和谐与一致的背后,发现了美国政府通过舆论管理这一中介,广泛“制造”同意和共识的秘密。美国舆论研究著名学者劳伦斯·雅各布斯(Lawrence R.Jacobs)和罗伯特·夏皮罗(Robert Y.Shapiro)1989年撰文指出:“新史学不仅提供了公众信念、公众习惯和舆论趋向的证据,而且使研究并阐释舆论同政府决策之间的关联成为可能。”(39)新史学强调公众舆论在社会和经济结构演变过程中的作用,为舆论研究者重估舆论的功能和角色并重新考量舆论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价值,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契机。
结语
舆论管理是美国社会历史机缘与现实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舆论管理研究的终极目标,在于探寻舆论与管理之间的契合点和作用方式,以增进对于人自身及社会力学的理解。同时必须强调的是,舆论管理在美国数以万计的舆论研究文献中只是沧海一粟,而舆论管理本身又蕴含着复杂的社会互动机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或逻辑问题。因此,舆论能不能管理以及要不要管理等问题,必将在美国学术界继续争论下去。无论如何,舆论管理作为“决策层面的宣传技术”,不仅主宰了西方的公共领域,而且成为诊断美国政治的一个关键现象。
注释:
①【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页。
②(23)(25)【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张杰、田青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2、44页。
③【美】沃纳·J.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郭镇之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④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1,No.1.(Jan.,1937),pp.152-153.
⑤【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陈卫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⑥Talcott Parsons,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9.pp.177-178.
⑦(30)【美】罗纳德·斯蒂尔:《李普曼传》,于宾等译,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97、263页。
⑧【美】杜·纽萨姆、艾伦·斯各特:《公共关系与实践》,罗建国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⑨Elmer E.Gornwell,Book Review [Untitled],The Journal of America History.Vol.69,No.1(Jun.,1982).
⑩Gregory W Bush,Lord of Attention,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1.pp.112-113.
(11)Jean-Marie Guehenno,The End of the Nation-State,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5.p.122.
(12)Christopher J.Anderson,Consent and Consensus:the Contours of Public Opinion toward the Euro,Paper presented at the Year of the Euro,December,2002.
(13)Gary L Gregg,Mark J Rozell,Considering the Bush Presiden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2003.
(14)Meganv.Vandeker Ckhove,Domestic public diplomacy,public relations strategy and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Persian gulf war—implications for democracy,A thesis presented to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in mass communication,2004.
(15)该奖项由迪克森基金会(Dirksen Foundation)资助、迪克森国会研究中心(Dirksen Congressional Research Center)评审,自1978年至2005年已有337人获奖。http://www.dirksencenter.org.
(16)Stacey Lynn Pelika.,Managing Public Opinion:Attentive Publics,Political Elites,and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University of Wisconsin,2005.
(17)Alex Carey,Taking the Risk OUT of the Nation-Stat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7,p.1.
(18)Christopher J.Anderson,Consent and Consensus:the Contours of Opinion toward the EURO,http://www.Facing history campus.org.
(19)Sally Hunter Graham,Woodrow Wilson,Alice Paul,and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98,No.4.(Winter,1983-1984),pp.665-679.
(20)Lawrence R.Jacobs,The Recoil Effect:Public Opinion and Policymaking in the U.S.and Britain,Comparative Politics,Vol.24,No.2.(Jan.,1992) pp.199-217.
(21)曾仕强:《中国管理哲学》,台湾东大图图书公司1981年版,第18页。
(22)邵培仁:《媒介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24)Garth S.Jowett; Victoria O'Donnell,Propaganda and Persuasion,Sage Publication,Inc.1999,p.47.
(26)Lawrence R.Jacbos; Robert Y.Shapiro,Public opinion and the New Social History:Some Lessons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and Democratic Policy-making,Social Science History,Vol.13.No.1.(Spring,1989),pp.1-24.
(27)Dietram A Scheufele; William P.Eveland Jr.,Perceptions of‘Public Opinion’and ‘Public’Opinion Express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Spring 2001,Vol.13,p.25.
(28)D.Stephen Cupps,Emerging Problem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37,No.5 (Sep.,1977),pp.478-487.
(29)Gabriel A.Almond,The American People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Harcourt,Brace,1950,p.55.
(31)(34)【美】赫伯特·席勒:《思想管理者》,王怡红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28-129、128页。
(32)Benjamin Ginsberg,The Captive Public:How Mass Opinion Promotes State Power,New York:Basic Books,1986,p.224.
(33)Lawrence R.Jacobs; Robert Y.Shapiro,Presidential Manipulation of Polls and Public Opinion: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oll,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10.No.4 (Winter,1995),pp.519-538.
(35)【美】斯各特·卡特里普等:《公共关系教程》,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96页。
(36)William G.Jacoby,Variability in Issue Alternatives and American Public Opinion,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52,No.2.(May,1990),pp.579-606.
(37)John R.Zaller,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34-35.
(38)李剑鸣:《关于二十世纪美国史学的思考》,载《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
(39)Lawrence R.Jacbos; Robert Y.Shapiro,Public opinion and the New Social History:Some Lessons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and Democratic Policy-making,Social Science History,Vol.13.No.1.(Spring,1989),pp.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