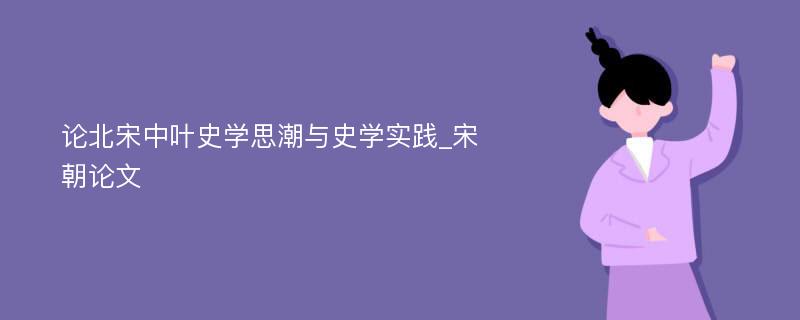
论北宋中期的史学思潮及其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北宋论文,思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2)02-0014-07
北宋中期,兴起于庆历之际的学术变革运动,使学者们得以逐渐摆脱经传注疏的束缚,整合儒、释、道三教思想,构建出具有新内涵的儒学,在此过程中,学者们既从史学中汲取了相当多的营养,同时也试图将其新的学术理念灌输到史学领域中去,以期在史学领域内确立儒家伦理纲常思想的主导地位。
一、试图以道德至上观冲击传统天命观
庆历以前的北宋学者在论及王朝兴亡之时常称说天命。如薛居正等称后唐之亡,“是知时之来也,雕虎可以生风;运之去也,应龙不免为醢。则项籍悲歌于帐下,信不虚矣。”①后晋之亡是“皇天降祸,诸夏无君。”后汉高祖得天下是“虽曰人谋,谅由天启。”②李昉等在编纂《太平御览》的过程中,对于历史上记载历代帝王神异事件的史料十分看重,“几乎达到凡有必录的地步。”③王钦若等所编纂的《册府元龟》中也到处充斥着天命意识,《帝王部》中表现得尤其突出。所谓:“为了麻醉人民,保持王朝的长治久安,于是利用阴阳灾异说,宣扬天命论神学史观,就成了历代统治者及其御用史家编写史书时常用的一种手法。这种天人感应的神学史观,充斥了《册府元龟》的《帝王部》,从《总序》到每一个《小序》,几乎个个都贯穿着皇权神授这一说教。”④
然而自庆历之际起,学者在思考历史时,更重视以经过改造具有新的内涵的道德理性来推演王朝的变迁,并认为决定人类历史进程的不是“天命”而是儒家所宣扬的伦理道德。
如欧阳修认为推行礼乐道德教化是治国的根本,所谓:“道德仁义,所以为治”。⑤因为人只有恪守礼义道德,有廉耻之心,才会安分守己,否则纵是祸乱败亡,也会无所不为。所谓:“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⑥所以礼义道德是治民之具,只有以礼义道德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统治者才能顺利推行其政治主张,“苟不由焉,则赏不足劝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⑦欧阳修同时认为不仅统治者要以礼义道德为治民之具,而且其自身也要具备崇高的道德品质,因为“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历朝历代都是“有德则兴,无德则绝。”⑧并以隋唐的历史为证,所谓:“考隋唐地理之广狭、户口盈耗与其州县废置,其盛衰治乱兴亡可以见矣。盖自古为天下者,务广德而不务广地,德不足矣,地虽广莫能守也。呜乎,盛极必衰,虽曰势使之然,而殆忽骄满,常因盛大,可不戒哉!”⑨
邵雍从“道”的角度论述了伦理道德的作用。他认为整个宇宙及万物衍生的过程都是由“太极”展开的,而所谓的“太极”就是“心”,就是“道”。所谓:“心为太极,又曰道为太极。太极,道之极也。”⑩因此道为宇宙之本原,天、地、人、物都受道的支配,所谓:“春夏秋冬者,昊天之时也。《易》、《书》、《诗》、《春秋》者,圣人之经也。天时不差,则岁功成矣;圣经不忒,则君德成矣。天有常时,圣有常经。行之正则正矣,行之邪则邪矣。邪正之间,有道在焉。”历史上王朝的兴衰都与是否推行以人伦之道有关,所谓:“至于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伦之为道也;三代之世乱,未有不乱,人伦之为道也。后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正人伦者也;后世之慕三代之乱世者,未有不乱人伦者也。”(11)
司马光认为主宰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儒家所宣扬的伦理纲常、礼乐教化。在司马光看来,人类社会有一永恒不变的“道”存在,它不随历史推移而发生变化。他说:“治乱之道,古今一贯”(12),道的实质即是儒家纲常伦理、礼乐教化。所谓:“孝慈仁义忠信礼乐,自生民以来谈之至今矣。”(13)司马光以此为指导,对三代至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进行了梳理,所谓:“昔三代之王习民以礼,故子孙数百年享天之禄”。到了汉代,“虽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犹尊君卑臣,敦尚名节,以行义取士,以儒术化民,是以王莽之乱,民思刘氏,而卒复之。”到了东汉末年,“曹操挟献帝以令诸侯,而天下莫能与之敌。操之心岂不欲废汉而自立哉?然没身不敢为者,畏天下之人疾之也。”自魏晋以降,由于统治者“以先王之礼为糟粕而不行,以纯固之士为鄙朴而不用。于是风俗日坏,入于偷薄。叛君不以为耻,犯上不以为非,惟利是从,不顾名节。至于有唐之衰,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帅者,朝廷不能讨,因而抚之。”视成功者为贤,失败者为愚,“不复论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于五代,天下荡然,莫知礼义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远者十余年,近者四五年,败亡相属,生民涂炭。”(14)
二程提出了“天者理也”的命题(15),而天理的具体内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所谓:“人伦者,天理也”(16)就是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和仁义礼智的道德原则,亦即是“礼”,程颐所谓:“礼,即是理也。”(17)具体而言,“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18)自然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也只有顺应了所谓的“人伦”、“礼”方才能够实现。所谓:“名分正则天下定。”(19)若“道不行,百世无善治。”(20)在程颐看来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不断出现纷争,就是由于人们行事违背义理所致,如对于唐朝,他说:“唐有天下,如贞观、开元间,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其原始于太宗也。故其后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才使肃宗,便篡。肃宗才使永王磷,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镇不宾,权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乱。”(21)
范祖禹将三代的兴废归于王者是否推行仁德之治,所谓:“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人心悦而归之则王,离而去之则亡。故凡有德则兴,无德则废。”(22)
当然,当时学者也并非完全不称说天命。如司马光声称:“天者,万物之父也。父之命,子不敢逆;君之言,臣不敢违。父曰前,子不敢不前。”认为“违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顺天之命者,天得而赏之。”(23)范祖禹所谓:“天人之际,相去不远,应如影响,不可不畏,能应之以德,则灾变而为福,异变而为祥。”(24)凡此种种,显见他们对天命还是在意的。然而他们在涉及探讨历史盛衰之变时,天命论色彩都大为减弱。对此的解释有二,一者应该与所谓的“神道设教”关系甚大,亦即学者们想以天命论来约束百姓,限制君主;再者新的学说毕竟是处于正在形成的过程中,所以许多学者在接受新观念的同时仍无法完全摆脱旧观念的束缚,不免在思想中出现新旧杂陈的现象。此不仅是司马光、范祖禹如此,可以说当时整个思想界都处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中。
二、尽力以伦理道德为准则评判历史是非
北宋前期,在对历史的评判方面多有以成败论是非者。如霍彦威等历仕后梁、后唐,薛居正等称:“夫才之良者,在秦亦良也,在虞亦良也。故彦威而下,昔为梁臣,不亏亮节,洎归唐祚,亦无丑声,盖松贞不变于四时,玉粹宁虞其烈焰故也。”(25)后汉张鹏因论国事被诛杀,薛居正等称“张鹏以一言之失,遽灭其身,亦足以诫后世多言横议之徒欤!”(26)冯道历官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中间还曾仕于辽。临难不赴,遇事依违两可,惟以圆滑应付为能事,然时人多称其贤,至谓与孔子同寿。所谓:“道既卒,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其喜为之称誉盖如此。”(27)入宋后虽有褒贬,但更多的是推崇与惋惜之意,如薛居正等所谓:“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所以饰终之典不得谥为文贞、文忠者,盖谓此也。”(28)
然自庆历之际起,学者们在判定历史之是非时,受新儒学思想的影响,大多能够做到在看成败得失之时重视伦理道德,或者说是义理为准则来评判史事的得失。程颐所谓:“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败,然后却看有不合处,又更精思。其间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今人只见成者便以为是,败者便以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败者煞有是底。”(29)
当时对唐代玄武门之变的评判,就生动地体现了学者们以伦理道德定是非的观念。如程颐秉持君臣名分,对李世民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所谓:“太宗佐父平天下,论其功不过做得一功臣,岂司夺元良之位?太子之与功臣,自不相干。唐之纪纲,自太宗乱之。终唐之世无三纲者,自太宗始也。”(30)与程颐一样,司马光也认为李世民是篡位,所谓:“君实修《资治通鉴》,至唐事。正叔问曰:‘敢与太宗、肃宗正篡名乎?’曰:‘然。’”(31)但他又从礼的角度出发,对玄武门之变有关各方的行为提出了批评,试图作持平之论,所谓:“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32)而范祖禹则对程颐之论予以深入阐发,评论也更加严厉,所谓:“建成虽无功,太子也;太宗虽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贰,父之统也,而杀之是无君父也。”(33)
对魏征的事迹的评价也是时人关注的一个焦点。如孙甫从魏征忠于太宗立论,对魏征评价甚高,所谓:“魏公以忠直称,历数百年而名愈高。”(34)司马光基本上赞同孙甫的观点,所谓:“管仲不死子纠之难而事桓公,孔子称其能不死,曰:‘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与征何异?”(35)程颐则从魏征与太子李建成有君臣之义的角度立论,对魏征背故主改事太宗持批评态度,所谓:“天下宁无魏公之忠亮,而不可无君臣之义。昔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36)范祖禹对魏征等建成故臣的评价与程颐基本相同,所谓:“今建成为太子,且兄也;秦王为藩王,又弟也。王(珪)魏(征)受命为东宫之臣,则建成其君也。岂有人杀其君而可北面为之臣乎?且以弟杀兄,以藩王杀太子而夺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禄而不死其难,朝以为仇,暮以为君,于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妇之从夫也,其义不可以不明。苟不明于君臣之义而委质于人,虽曰不利,臣不信也。”(37)
对于冯道,学者们根据自己对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解,纷纷发表新的看法。其中尤以欧阳修为代表,所谓:“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38)欧阳修的观点引起了学者们的强烈共鸣,所谓:“自为欧阳公所诋,故学者一律不复分别”。(39)如唐介认为冯道“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为纯臣乎?”(40)司马光认为冯道虽有小善,但因大节已亏,因此不足称许,所谓:“臣愚以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为女不正,虽复华色之美,织纴之巧,不足贤矣。为臣不忠,虽复材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何则,大节已亏故也。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41)二程认为冯道“更相数主,皆其仇也”,因此这是“不忠”,尽管冯道会辩解自己的行为是为了天下,不得已而为之,同样是不能原谅,所谓:“如以为事固有轻重之权,吾方以天下为心,未暇恤人议己也,则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42)
三、尝试以经学为指导来编纂历史
北宋中期,由于学者们普遍认同道德至上观,而这种观念的重要载体就是先秦经学著作,因此学者们对先秦经学非常推崇,故而在从事历史编纂的过程中,学者们往往以经学为指导或在经学的影响下撰写史著,从而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就。
首先,提倡《春秋》“笔法”。当时史书编纂方面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学者们纷纷仿效孔子以《春秋》笔法来著史。对于《春秋》笔法的看法,欧阳修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如他称:“夫据天道,仍人事,笔则笔而削则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援他说,攻异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传》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质诸人情,推至隐以探万事之元,垂将来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于《春秋》矣。”(43)又称:“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惟不没其实以著其罪,而信乎后世,与其为君而不得掩其恶,以息人之为恶”。(44)由于非常推崇《春秋》笔法,因而学者们在史学研究中大都有意识地加以借鉴。如尹洙曾仿《春秋》笔法一字褒贬之法撰《五代春秋》,其内容“全仿春秋”,(45)欧阳修亦以《春秋》笔法著《新五代史》,被章学诚认为“本纪笔削深得《春秋》法度,实马、班以来所不能及。”(46)范祖禹著《唐鉴》在叙述武周历史时,“窃取春秋之义”自嗣圣元年以至于中宗再次复位一二十年间不书武周年号,仍用中宗纪年。(47)同时由于重视“不没其实”与“书法不隐”,因此学者在著述过程中,往往遍考群书,采征宏富。如欧阳修修纂的《新五代史》,虽多据《旧五代史》旧本,然采证极博,不专恃薛本也。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亦是如此,为了把书编好,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搜集了大量的史料,并著《通鉴考异》。吴缜则著专书,以考订《新唐书》及《新五代史》之讹误。当时,在“不没其实”原则指导下,有益于褒贬劝戒的善恶之事都得到了充分记述。如武则天因以女主称帝,欧阳修在撰《新唐书》时,为其列本纪,目的是通过尊从《春秋》“不没其实”的手法“著其大恶。”(48)宋祁更是在列传的类传中对善恶之事大书特书。在列传中,宋祁把《忠义》、《卓行》、《孝友》三个类传依次排在类传之首。这三种类传虽然内容不同,但是突出的都是忠义思想。在强调忠君思想的同时,《新唐书》还对所谓乱臣贼子的恶予以揭露,以起到警醒统治者的作用。为此《新唐书》的类传新增了藩镇、奸臣、叛臣、逆臣四个类传。
其次,促进古史研究的繁荣。兴起于庆历之际的学术变革运动,使对经书的研究成为时代的潮流,由于经书所讲多为三代及上古之史事,故而对经书的研究也带动了学者们对古史的兴趣。刘敞开创的金石学研究,就与研经关系甚大。所谓:“嗟乎,三王之事万不存一,诗书所记,圣王所立,有可长太息者矣。独器也乎哉!兑之戈、和之弓、离磬崇鼎,三代传以为宝,非赖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孔子曰: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众不可概,安知天下无能尽辨之者哉!使工模其文,刻于石,又并图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终此意者,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乃为能尽之。”(49)论及三代,刘恕认为:“太史公云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咸不同乖异。历汉魏晋,去古益远。众言不本于经,夸者务为诡诞。”(50)因此刘恕对古史研究颇为用心。苏辙认为“古之帝王皆圣人也”,其道至善,然而春秋以下世道衰落,圣人之道无由而得,故司马迁虽著《史记》以记之,但是却不得要领。为了阐述圣人之道,苏辙遂“因迁之旧,上观《诗》、《书》,下考《春秋》,及秦汉杂录,记伏羲、神农,讫秦始皇帝,为七本纪、十六世家、三十七列传,谓之古史。追录圣贤之遗意,以明示来世。至于得失成败之际,亦备论其故。”(51)
再次,排斥符瑞怪异及佛老内容。在北宋中期,理学形成的过程中,学者反异端、排佛道的思想继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如欧阳修称:“郑惑谶纬,其不经之说汩乱六经者不可胜数。学者稍知正道,自能识为非圣之言。”(52)司马光“疾阴阳家立邪说以惑众,为世患。”(53)对于释老,学者们也大加挞伐。如孙复认为:“佛老之徒,横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绐我生民,绝灭仁义以塞天下耳,屏弃礼乐以涂天下之目。”(54)欧阳修称:“彼为佛者,弃其父子,绝其夫妇,于人之性甚戾,又有蚕食虫蠧之弊”。(55)司马光“不喜释、老”,所谓:“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也。”(56)
这种反谶纬排释老的思想在历史编纂上也有明确的反映。其有代表性的当属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新五代史》中,欧阳修对符瑞的抨击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不书符瑞。如在《旧五代史》中记载了朱温称帝前后出现的大量符瑞现象,而在《新五代史》皆被欧阳修一一刊落。其二是不设《五行志》。自班固《汉书》设《五行志》志五行、叙阴阳、记灾异起,后世史书大多设《五行志》仿效之。《旧五代史》即设有《五行志》,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则不立《五行志》,只立《司天考》以记天象及历法,“以备司天之所考。”(57)欧阳修的排抑佛道思想在《新五代史》中也有生动的反映,有学者将其进行全面梳理之后,指出:“纵观《新五代史》,没有一处对佛教进行称赞和肯定,显示出欧阳修对佛教的彻底批判精神。”又指出《新五代史》中欧阳修对那些“打着道教旗号或利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致家国败落的伪道士们”进行了“不遗余力地批判。”(58)此可谓不易之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妖异符瑞现象必欲悉数删之而后快,还是在修定长编的阶段,他在与助手范祖禹讨论修《资治通鉴》的原则时就称:“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59)对于释老则在书中采取批判态度。他称佛教“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劝诱愚俗。”(60)又利用古人之口驳斥释老,如载崔浩不好老庄之书,称:“此矫诬之说,不近人情。老聃习礼,仲尼所师,岂肯为败法之书以乱先王之治乎?尤不信佛法,曰:‘何为事此胡神!”’(61)还详细记载了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禁佛之事。此外《新唐书》在反对符瑞释老方面也作了很多工作。如宋祁撰《新唐书·方伎传》将《旧唐书·方伎传》中所有的玄奘、神秀、慧能、一行诸传皆删而不载。欧阳修在《五行志序》中对阴阳五行之学进行了抨击,所谓:“汉儒董仲舒、刘向与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范》为学,而失圣人之本意。”认为他们“取其五事、皇极、庶证附于五行,以为八事皆属五行”,是荒谬的。(62)
综上所述,北宋中期,为了强化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的至上性,学者们不仅竭力将其演绎为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而且还纷纷以其为准则评判历史人物事件的是非,同时又以其为指导思想对历史进行大规模地编纂或重构。通过学者们不懈地努力,使新的学术理念全面渗透进了历史领域。
注释:
①《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69页。
②《旧五代史》,第1340页。
③《旧五代史》,第1340页。
④仓修良:《从〈册府元龟·帝王部〉看其作者的神学史观》,《〈册府元龟〉新探》,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76页。
⑤《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14页。
⑥《新五代史》,第611页。
⑦欧阳修:《武成王庙问进士策二首》,《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73页。
⑧《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页。
⑨《新唐书》,第960页。
⑩邵雍:《皇极经世书》,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22页。
(11)邵雍:《皇极经世书》,第501页。
(12)司马光撰,王亦令点校:《稽古录点校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649页。
(13)司马光:《辨庸》,《司马温公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3页。
(14)司马光:《上谨习疏》,《传家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4册,第247页。
(15)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2页。
(16)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二程集》,第394页。
(17)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二程集》,第144页。
(18)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二程集》,第77页。
(19)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二程集》,第276页。
(20)程颢、程颐:《河南程氏粹言》,《二程集》,第1242页。
(21)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二程集》,第276页。
(22)范祖禹撰,白林鹏、陆三强校注:《唐鉴》,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6页。
(23)司马光:《士则》,《司马温公文集》,第313页。
(24)《范太史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0册,第307页。
(25)《旧五代史》,第860页。
(26)《旧五代史》.第1401页。
(27)欧阳修:《新五代史》,第615页。
(28)《旧五代史》,第1666页。
(29)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二程集》,第258页。
(30)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二程集》,第236页。
(31)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二程集》,第19页。
(32)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11页。
(33)范祖禹撰,白林鹏、陆三强校注:《唐鉴》,第21页。
(34)孙甫:《魏郑公谏诤》,《唐史论断》,学海类编第15册。
(35)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二程集》,第19页。
(36)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二程集》,第405页。
(37)范祖禹撰,白林鹏、陆三强校注:《唐鉴》,第24页。
(38)《新五代史》,第611页。
(39)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99页。
(40)魏泰:《东轩笔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9页。
(41)司马光:《资治通鉴》,第951—9512页。
(42)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二程集》,第73页。
(43)欧阳修:《石鷁论》,《欧阳修全集》,第880页。
(44)欧阳修:《魏梁解》,《欧阳修全集》,第299页。
(45)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第1987页。
(46)章学诚:《文史通义》,《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47)范祖禹撰,白林鹏、陆三强校注:《唐鉴》,第105页。
(48)《新唐书》,第113页。
(49)刘敞:《公是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37页。
(50)刘元高编:《三刘家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45册,第545页。
(51)苏辙:《古史序》,《三苏全书》(3),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51—352页。
(52)欧阳修:《诗本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第278页。
(53)司马光:《葬论》,《司马温公文集》,第301页。
(54)孙复:《孙明复小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0册,第176页。
(55)欧阳修:《本论下》,《欧阳修全集》,第291页。
(56)《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769页。
(57)《新五代史》,第706页。
(58)张明华.《〈新五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128页。
(59)司马光:《答范梦得》,《传家集》卷63,第582页。
(60)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447页。
(61)司马光:《资治通鉴》,第3761页。
(62)《新唐书》,第872页。
标签:宋朝论文; 欧阳修论文; 欧阳修全集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司马光论文; 二程集论文; 唐鉴论文; 新唐书论文; 新五代史论文; 中华书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