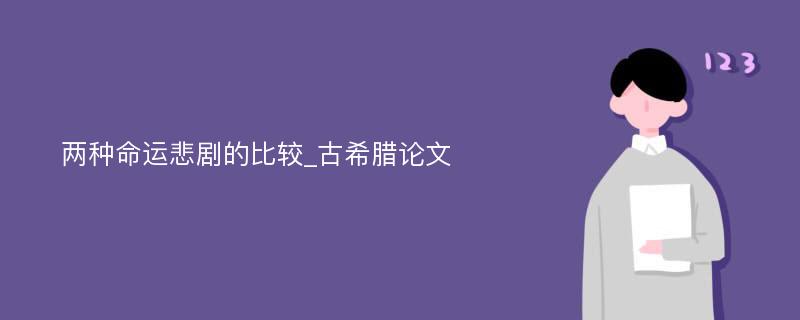
两种命运悲剧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悲剧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元杂剧与古希腊悲剧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二者产生的年代相距遥远,但却拥有相近的戏剧形式——命运悲剧。笔者认为,诞生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两种命运悲剧均包蕴着十分丰厚的文化内涵,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将帮助我们认识戏剧艺术的某些规律,并引起我们对中西两种文化的思考。
一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文学不能不是某一种思想倾向的体现者”。(注:《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547页。)尽管我国元代与古希腊的社会形态不同, 但艺术家在体现某种思想倾向时却可以选择相近的艺术处理方式,两种命运悲剧的创作实践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首先,中西作家都认为,“命运”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而且都将命运理解为先天注定的灾难、困厄和死亡。为阐释命运的不可抗拒的威力,他们往往在戏剧的开场和过场以独特的方式加以暗示。
古希腊作家或以神谕的方式告诉观众,或用先知的预言暗示观众,戏剧主人公则全然不知。戏剧主人公们一味地按着自己的意愿行事,试图挣脱某些束缚,但却事与愿违,他们愈是挣扎,就愈加难逃命运的罗网。如埃斯库罗斯的三联剧《俄瑞斯忒斯》借用神话故事反映父权制战胜母权制、法治精神战胜血族复仇观念。当时,古希腊作家不能按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来理解这场社会变迁,只好将其解释成神的诅咒或命运的捉弄。《阿伽门农》的开场就是“守望人”寓意深长的暗示:“这个家料理得不象从前那样好了”,继而在进场歌中十二个长老回忆事情的缘起和先知的预言,发出了不祥的警告。欧里庇得斯笔下《希波吕托斯》主人公的命运在开场时即由神注定,究其死因则在于他高傲,怠慢了恋爱和美神阿佛洛狄忒。悲剧性的冲突是由爱神的挑唆引起的,所以她要借费德拉对希波吕托斯的一段恋情惩罚希波吕托斯。这样,主人公无论怎样反抗,也不能逃脱神预先设下的“命运”的陷阱。
元代作家多以“占卜”的形式将灾难告之主人公,主人公闻讯后即作苦苦挣扎,以求躲过灾难,结果却无济于事。《朱砂担》、《盆儿鬼》、《生金阁》、《魔合罗》等反映黑暗现实中好人受难的悲剧都是这样。如《魔合罗》中李德昌长街市上算卦得知自己有“百日灾难”,千里之外可避,便立即赶赴南昌做生意,可就在返家途中身染重病,委托高山老汉给妻子捎信,竟被堂兄李文道中途截获,李德昌终被李文道毒死。目睹这些发生在异族统治下的人间惨剧,元杂剧作家尚不能从社会制度本质的高度去分析,只能把主人公的坎坷踬蹇与上天的冥冥主宰联系起来。可见,元杂剧作家的命运观念是明显的,他们同古希腊作家一样承认命运的存在,相信命运的威力,在无法解释现实中某些社会现象时,便把命运理解成“先天注定”的,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其次,两种命运悲剧都描写了悲剧主人公不甘认命、与命运奋力抗争的过程。中西作家如此相类的艺术处理,意在突现命运具有伤天害理的邪恶性质。
古希腊作家把悲剧主人公描写成同命运苦斗的英雄,杰出的代表当属《俄狄浦斯王》中的俄狄浦斯。在其降生之前,父亲就得知儿子将会“杀父娶母”的“神示”,为此,他刚刚出世时,父母就命仆人将其丢进荒山,仆人不忍相弃,将其交予邻国王后作养子。俄狄浦斯长大后知道了所谓的“神示”后,便以顽强的个人意志对抗着命运的安排。尽管在其抗争中厄运犹如狭路上的冤家时时相逢,但在命运挑战面前,俄狄浦斯却不乏斗争的勇气。
元代命运悲剧的主人公在得到某种预示后也不甘心听任命运的捉弄,却都想方设法争斗一番。如无名氏的《朱砂担》叙写王文用卜卦得知自己将有百日血光之灾后,借故做生意外出躲避。百日将满返乡之时,被强盗铁幡杆白正于途中缠住。王文用先在十字坡店中灌醉白正后逃走,又在黑石头店中再次设计潜逃,几度周旋后还是躲不过恶人的暗算,王文用惨遭杀害,就连他的父亲、妻子也未能幸免。显然,元杂剧作家着力表现的是命运的伤天害理,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
此外,两种命运悲剧还不同程度地笼罩着超自然的神秘色彩。古希腊作家多借助于神力,元杂剧作家则善用占卜,二者都将个人意志行为置于一种超越现实力量的主宰之下,使其无力与命运对抗。借助于神力的古希腊悲剧重在表现神祗具有不可超越的力量。《阿迦门农》一剧不时穿插着神示和预兆,导演着阿迦门农一家互相残杀、报复的惨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一剧的冲突双方都是神,普罗米修斯本来是一个小神,埃斯库罗斯将其创造成一个意志力无比坚强、极具勇敢与牺牲精神的伟大神祗,但在与宙斯的冲突中,宙斯更显示出超越现实的威力,最后,在为人类的生存与进步而斗争的正义事业中,普罗米修斯蒙受到巨大的灾难和痛苦。
至于元代命运悲剧所用的占卜则夹杂较多的迷信成分。我们知道,以占卜来推断人生之祸福本身就是迷信行为,于是,剧作中由占卜显示出来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就不那么具体、有形了。如武汉臣的《生金阁》叙写郭成偶得一梦,经占卜后才知自己有百日血光之灾,郭成躲灾不过,终遭恶人杀戮。这里,人们感受到的已不是神祗的威力,而是无形的不可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遣着善良人的命运,使其抗争无能为力,这正是元代命运悲剧的神秘性之所在。
二
古希腊命运悲剧与元代命运悲剧毕竟是诞生在不同社会文化土壤中的不同质的戏剧,在题材、人物、结局等方面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
(一)戏剧题材的传奇性与现实性
古希腊命运悲剧的题材或采用上古的神话传说,或选取史诗中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的神性居主导地位。正如黑格尔所言:“原始悲剧的真正题旨是神性的东西,这里指的不是单纯宗教意识中那种神性的东西,而是在尘世间个别人物行动上体现出来的那种神性的东西。”(注: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第285页。) 古希腊悲剧作家正是以传奇性的故事来折射现实,剧中表示的人与神的冲突或神与神的冲突,实质上是从人与命运的冲突这一独特的角度去审视人生、社会、历史和宇宙的真相。如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所表现的是氏族道德的传统开始与国家及其法律的冲突,既然冲突不可避免,也就只能把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理解成为新的命运,无论神与人都逃脱不了它的神秘力量。《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则借喻主神宙斯对普罗米修斯的疯狂迫害来揭露和谴责专制暴君的专横和残暴。
由于中国从古到今都不存在古希腊那样一群全民信奉的神,而相信善恶昭彰、因果报应的道德逻辑,元代命运悲剧便完全取材于现实,戏剧冲突的双方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描写的事件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事件。虽然剧中设有占卜,鬼魂复仇的情节,但这只起某种神秘的作用,并不直接表现为冲突双方的对峙。《朱砂担》中的王文用以占卜得知自己有“百日之灾”,虽然令人感到神力的秘不可测,但直接与王文用对抗的却是现实生活中的强盗白正。王文用被害后,其父也受株连,王父的阴魂到地府状告恶人,正义却不得伸张。这非但没有肯定神力,反而在亵渎神力。这就说明,元代作家不像古希腊作家那样坚信神的存在,而是借助神灵来宣泄自己对黑暗现实的困惑与无奈。神灵并不圣明,全然不为善良人做主,这分明是在影射元代官府窳败衰朽的现实,地曹判官本身更充溢着元代滥官污吏所具有的某些“人气”。
(二)人物抗争的主动性与被动性
古希腊命运悲剧的主人公顽强地与命运搏斗,表现出积极主动的战斗风貌。《俄狄浦斯王》中的俄狄浦斯得知自己日后注定要“杀父娶母”的神示后,便开始了主动抗争的历程。他毅然抛弃王位继承权,离开科任托斯,逃亡异乡,途中杀死了拉伊俄斯,沦落于忒拜城郊。凭着超人的智慧,俄狄浦斯解开妖兽的谜语,拯救了忒拜人,被尊为王。拉伊俄斯的寡妻嫁他为后,从此便精心治理城邦,深得人民的拥戴。这一切,展示了一个敢于主动向命运挑战的精神境界。尽管他所做的努力反倒促成了厄运的降临,但他仍不失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强者。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则以其强有力的反抗精神使希腊诸神“悲剧式地受到一次致命伤”。(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57页。) 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以其抗争的主动性表现了他们在厄运面前的昂扬斗志,由此迸发出的悲剧美的火花显得格外耀眼夺目。
同古希腊命运悲剧相比较,元代命运悲剧的主人公缺乏古希腊命运悲剧主人公那种敢于赴汤蹈火、向命运挑战的主动性,反抗的强度较弱。《生金阁》、《魔合罗》、《朱砂担》等剧的主人公都通过占卜得知大难临头,并且无一例外地以躲灾的方式进行被动的抗争,结果,不但灾难未能躲过,还株连了亲人。《荐福碑》中的张镐与上述几剧人物情形略有不同。几经周折后张镐自叹命运乖蹇,去龙神庙避雨时以掷珓问卜前程,连掷三次都是下下,气得他大骂龙神,还题诗否定龙神,可惜这种否定龙神的抗争精神随着荐福碑被雷雨击碎而消失了,走投无路的张镐竟然触槐自尽。元代命运悲剧的主人公在反抗中表现出来的消极被动性,削弱了戏剧冲突的激越性,审美效果也不及古希腊命运悲剧那样震撼人心。
(三)结局的毁灭性与圆满性
依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所言:悲剧只应有“由顺境转入逆境”这一种,其结局一定是悲惨的。古希腊命运悲剧的主人公经过一番抗争,其合理要求得不到实现,往往以悲剧主人公惨遭失败作结。普罗米修斯因触犯主神宙斯被铁链锁住,囚禁在高加索悬崖的绝壁上,俄狄浦斯得知自己“杀父娶母”后悔恨地弄瞎双眼而逃亡异地。这种毁灭性的结局显示了古希腊命运悲剧在正义与邪恶的冲撞中所产生的崇高美感。
元代命运悲剧的结局却与古希腊命运悲剧大相径庭。虽然也揭示了主人公反抗命运的失败,但结局却拖着光明的尾巴。在《朱砂担》、《生金阁》、《魔合罗》之类的公案戏中,作家们都请出神灵、清官为受害的主人公平反冤狱。《生金阁》中的秀才郭成死后化作无头鬼魂向包拯陈述冤情,最后包拯严惩了权豪势要庞衙内,其妻李幼奴被封为贤德夫人,死去的郭成“特赐”进士出身,这一结局,不但生者受到封赏,死者的灵魂也得以告慰,原本凄惨的故事戴上了理想的光环。《荐福碑》中的张镐穷愁潦倒,几近绝境,可作者偏偏令其于生死攸关之时巧遇范仲淹,获得理想的归宿。当然,元代作家为这些命运悲剧安排圆满的结局只是相对地弱化了原来的悲剧气氛,并不能改变人与命运冲突的实质。
三
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页。)两种命运悲剧虽然诞生在不同质的社会形态中,但二者都是当时社会存在的反映,都能揭示当时社会的某些特质。从两种命运悲剧的比较中,我们获得了许多深刻的启迪。
我们看到,两种命运悲剧都诞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即社会面临着剧烈的变革与动荡的挑战,新的社会秩序亟待建立的时代。在中西社会发生历史性转折的关头,中西戏剧家能够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以深邃的目光透视着社会、人生的真相,以命运悲剧的艺术形式表现这场震撼人心的历史变迁,其可贵的艺术创作实践是发人深省的。
古希腊是一个特殊的悲剧时代,发生过一系列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变革,例如民主战胜专制、国家取代家庭、女权让位于男权等。这些牵动人心的剧变,既需要人类付出一定的代价,也激励人们去积极探索,大批命运悲剧就在这沉重的社会精神压抑下孕育而成。同样,元代在我国封建史上也极具悲剧色彩,地处北疆的元蒙统治者挥师南下,给传统的封建儒家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崛起的草原文化同悠久的农业文化的撞击中,社会上的许多秩序都被打乱,朝政混乱黑暗,法律严酷,冤狱丛生,就连知识分子本身也是穷困潦倒,仕进无路,不得不奔波于平民市井之间。一些命运悲剧就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应运而生。中西历史发展的进程表明,当社会急遽变迁的时候,也是人们的思想极易产生困惑的时候,这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中是难以解释的,就是那些有着较高认识能力和文化素养的艺术家们也不易理解。这样,他们自然要从人与命运冲突的视点来洞察社会、直面人生。尽管中西戏剧家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但他们由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困惑与不理解是相类的。因此,在经受社会变迁的洗礼之后,他们选择了极为相近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对不可思议的力量即“命运”的观点,揭示人与命运抗争的真谛。两种命运悲剧的创作实践启发人们认识到:艺术家只有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才能做到以自己的艺术创作反映时代的某些本质,在社会变革时期尤其如此。
中西作家在历史剧变的激流中作出了极为相近的艺术选择,但两种命运悲剧所产生的美感却存有差异。这说明,中西悲剧从其成熟之日起就表现出不同的悲剧精神,并影响着本民族的审美趣味。
所谓悲剧精神,是指人面对不可避免的生命苦难与毁灭时所表现出的强烈自我保存的生存欲望,敢于同毁灭的必然性进行殊死抗争的勇气。在这种表现中,人的价值和人格力量得到最大程度的提高,显示出超常性与崇高性。如前所述,古希腊命运悲剧中对峙的双方始终处于尖锐的、不可退让的矛盾之中,显现出惊心动魄的崇高性美感,它使读者或观众受到精神的陶冶和心灵的震动,美感效应强烈。这种高蹈激越的悲剧精神已在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影响了西方民族的审美趣味,形成了西方的悲剧传统。与古希腊命运悲剧相比较,元代命运悲剧问世要晚十六、七个世纪,在此之前,中华民族虽然不乏悲剧精神,但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又产生了某些特殊性和复杂性,以追求中和之美、欣赏娴静之态、创造和谐优美的意境为审美趣味。因此,即使在异常黑暗年代中诞生的元代命运悲剧也承袭了这种审美追求,较少西方那种敢于撞个鱼死网破的富于个性的抗争行为,而是以善恶相报的圆满性结局给人以精神的慰藉。这种独特的审美趣味一直为后世作家所孜孜追求,成为我们民族的悲剧传统。
黑格尔说过,戏剧是一个已经开化的民族生活的产品。世界戏剧史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人类日益丰富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主宰着戏剧艺术的兴盛和发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物质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们总会渴求着新的艺术样式的降生,人类一系列艺术形态则在这种艺术需求中成熟。正是基于这种艺术需求,中西戏剧家才分别以卓越的艺术创造写下了中西戏剧史上极富魅力的一页。两种命运悲剧的创作实践雄辩地证明:需要,乃创造之母。任何艺术形式都是人类需要的产物。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的社会主义时代,人们的审美需要自然要跃上新的层次,这种高层次、高品位的审美需要已为戏剧艺术的拓新、拓深提出有意义的课题。我们深信,在中西文化信息交流频繁的现代社会中,戏剧家只要能适应人民大众的审美需求,就一定会培育出雅俗共赏的艺术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