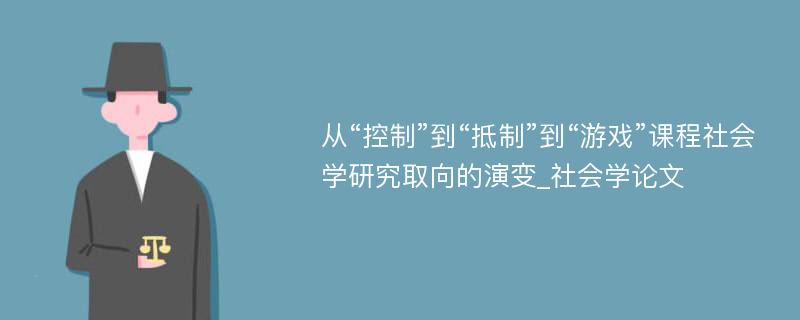
从“控制”到“抵制”再到“博弈”——课程社会学研究取向的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到论文,取向论文,社会学论文,课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9)03-0168-05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外对课程理论和课程实践的关注,基本上集中在工具理性的层面上,即集中于对怎样的课程是好课程,怎样设计、编排好课程,怎样制定和编写课程标准、课程大纲、教科书等技术问题的探讨,而对到底“谁”的知识是“法定的”和“值得传授”等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对课程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权力之间关系的探讨很少触及,这种把学校当作工厂,把学生当作产品的工厂模式,抹杀了课程的社会本质,忽视了对课程价值属性的审视。课程社会学的研究打破了这一局面,它并不停留于对课程内容选择或课程编制作技术上的考究,而是侧重去挖掘课程与权力、课程与政治、课程与社会控制的内在关联和深层根源。纵向上看,课程社会学的研究取向经历了一个从控制到抵制再到博弈的流变,即早期的课程社会学集中于研究国家是如何实现对课程的控制并通过对课程的控制进而实现对社会的控制的,“控制”是这一时期研究的主旋律,而这之后的研究似乎将关注的目光集中在社会力量是如何对国家的控制进行抵制的,而近期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国家的控制与社会的抵制之间展开的课程博弈。
一、“控制”——早期课程社会学研究的主旋律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课程的形成与其说是根据对学生、社会及学科的研究结果而对知识进行价值判断与类型划定的技术过程,不如说是根据政府决策层的价值取向而对知识进行价值判断与类型划定的社会过程。因而,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课程领域展开了广泛的“概念重建运动”,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科学化课程开发范式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并形成了以麦克·扬(Young)、布迪厄(P.Bourdieu)、伯恩斯坦(B.Bernstein)为代表的新教育社会学流派和以阿普尔(M.W.Apple)、吉鲁(Giroux.H)、鲍尔斯(S.Bowles)、金蒂斯(H.Gintis)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流派。其代表著作包括麦克·F·D·扬的《知识与控制:教育社会学新探》,阿普尔的《意识形态与课程》、《教育与权力》、《官方知识》、《教师与文本》、《民主的学校》、《文化的政治学与教育》、《权力、意义与认同》、《教育的“适当”方式:市场、标准、上帝与不平等》,伯恩斯坦的《阶级、符码和控制:朝向教育传播理论》(第三卷)、《论教育知识的分类与构架》,鲍尔斯、金蒂斯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布迪厄与让-克劳德·巴塞朗合著的《教育、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吉鲁的《新教育社会的再生和抵制理论:一个批判性的分析》、《意识形态、文化与学校教育与课程》,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等。
这其中影响比较大的研究有麦克·扬的知识与控制理论、布迪厄等的再生产理论、伯恩斯坦的语言代码理论(language code)、阿普尔的意识形态理论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这些研究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倾向于将课程理解为一个充满了权力斗争的场域,由此揭开了课程这个黑箱,把课程中内嵌的权力关系暴露在世人面前。
可见,早期的课程社会学研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打破了课程知识完全“客观中立”、“价值无涉”的神话,指出课程内容的选择、课程内容的编制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操作与实践的过程,学校课程设置的目的也并不仅仅在于促进儿童个体本身的发展,它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统治传播与渗透的媒介,是国家实现社会控制的主要载体,是谋求政治合法化的工具等,由此,课程与权力、课程与意识形态、课程与政治、课程与社会分层、课程与社会控制等成为课程社会学探讨的焦点,揭示课程的社会控制功能成为此时课程社会学研究的主旋律。
二、“抵制”——对“控制”的矫枉与过正
应该说,早期新教育社会学流派和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流派的许多著作和观点,如扬的《知识与控制:教育社会学新探》以及阿普尔的《意识形态与课程》等系列著作,几乎都集中地揭示和批判了国家对课程的控制,这对我们全面而深刻地审视课程,尤其重新反思课程的客观性和中立性等提供了新的视角。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开始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这种“控制”的研究取向其实已经走向了极端,即此时的研究在批判课程完全“客观中立”和“价值无涉”的基础上确实非常深刻而精辟地集中揭示了课程的价值倾向和社会属性,但将教育完全看作是社会再生产的手段,将课程完全看作是国家单向介入和控制的结果,这实质上走向了极端,它忽视了课程形成和实施中的多元介入,忽视了社会控制背后的斗争和反抗,忽视了社会各种力量追求和行使课程权利的努力,也忽视了目前世界各国在不断追求民主和平等的整体趋势下完全让课程成为社会控制的工具所面临的风险。换而言之,支配集团借助于课程来实现社会控制,但权力、支配集团、意识形态对课程的介入和控制,是否就意味着被支配集团会完全屈从于被支配的命运而不作任何斗争和抵制呢?课程,作为官方知识的载体,非官方知识或者地方知识是否就完全失去了进入课程的可能,或者它们会主动放弃这种机会和可能?显然不是,“课程……是互相竞争的种种力量之社会产物(Apple,1982)”[1]。和国家一样,其他社会力量也力图使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在课程中得到平等表达。在这种情形下,各方力量,基于不同的考虑,站在不同的立场,都力图在课程中占有一席之地。于是,课程社会学研究的焦点开始从前期关注国家对课程的控制转向其他社会力量对国家控制的抵制。
严格地说,早期课程社会学研究在集中对“控制”进行批判的同时,其实已经开始模糊意识到了潜伏在“控制”背后的“抵制”,“控制”取向的研究开始慢慢修正。如阿普尔,他起初是“控制”研究取向的主要代表人物,到20世纪80年代初也开始从“控制”走向“抵制”。在其早期著作《意识形态与课程》中,基本上沿用了再生产理论的观点,认为学校的教学内容与社会不严等的社会结构是相对应的。学校就像社会的镜子,需要什么样的驯服工具,学校就培养什么样的工具人。而在其后期著作《教育与权力》和《教育中的文化与经济再生产》中,阿普尔修改了他关于教育过程的概念。他说,仅仅认为学校再现了社会生产关系这未免过于简单。尽管学校肯定会出现再生产,但这种再生产理论未考虑到学校生活的复杂性以及存在于学校中的斗争和矛盾,也贬低了教育制度中人的自由和自我决定的重要性。“工人阶级的学生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副产品,屈服于权威教师和学校……学校也是一个竞争场所,它不仅以结构矛盾和意识形态矛盾,而且以学生集体的抵制意识为特征”[2]。金蒂斯(Giroux)的著作《教育中的理论与抵制:一种对抗教育学》(Theory and Resistance in Education:A Pedagogy for the Opposition)中也体现了从“再生产”向“抵制理论”的研究转向。在金蒂斯看来,“抵制”表明了对抗教育学(oppositional pedagogy)的可能性。
对“控制”取向批判最为彻底的,当数保罗·威利斯。他反驳的理由是:在“控制”取向看来,资本主义的学校教育不过是实现“阶层间相对关系再生产”的一个工具并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精英和底层各自所处的结构位置早已注定了他们各自的整体命运:那些在结构位置上处于优势的学生得以维系父辈的地位或实现向上流动,而处于弱势的学生则被淘汰出局,成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所需要的“简单一般劳动”(Bowles & Gintis,1976)。这意味着学校成为了“资本要求怎么做,它就怎么做”的场所,而学生们则成为了仅仅接受结构性因素决定的沉默者和被愚弄者。威利斯并不这样认为,他在(学做工)中就形象地刻画了以“抵制”为核心的工人阶级男性的“反学校文化”,他以民族志深度描写的方法记录了学生尤其是来自社会底层学生通过“抽烟喝酒、逃学旷课、挑战教师权威、觉得学习无聊乏味,却对打工挣零花钱兴趣盎然”甚至“自我放弃向上流动的资格(self-disqualification),自愿从事工人阶级的体力劳动”等方式对国家试图灌输给他们的知识系统进行的反抗。阿普尔也指出,学生并不仅仅是学校试图传播的思想的“载体”。相反,学生“以经常有悖于学校盛行的规范和态度的方式进行创造性活动”。“许多学生干脆不上学校所开设的一切课程。他们尽可能冷落数学老师、历史老师、职业课和其他课程的老师。他们也尽量拒绝接受严守时间、穿戴整齐、服从指挥以及在经济生活中其他更加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方面的隐形教育。这些学生的真正任务就是等着下课铃响。”[2]
如果说,“控制”的研究取向是自上而下关注社会宏观经济、政治、文化等对课程内容的影响,揭示和批判政治、权力、国家等对课程的控制,那么,“抵制”取向则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来关注学校、教师和学生等不利群体对课程内容或社会控制的抵制。也可以说,“控制”取向所强调的是国家、政治和权力等对课程的决定性影响,而“抵制”取向则认为,课程的形成并不可能是国家单向介入和控制的结果,国家的介入、课程的社会控制不可能一帆风顺,社会的其他利益集团和群体也会站在自身的角度对课程施加一定的影响,包括对不符合自身利益倾向的国家控制进行抵制。既然,课程的形成既不可能是国家自上而下单向介入的结果,也不可能是社会其他力量自下而上不断集中的反映,这实际暗示着课程社会学研究的新取向,即课程最终是博弈后妥协的结果,是整个社会各种利益集团相互斗争、权衡后的体现。
三、“博弈”——课程社会学研究的新路径
教育,无论是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统治地位的巩固,还是个人的完善,其重要程度都是不言而喻的。它是一项影响广泛而深远的社会事业,“显然,任何起如此重大作用的社会事业是不会被允许在某一政体下任意游荡的。拥有权力和影响的团体与个人在必要时刻,将会尽最大努力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塑造一个体系,并使课程设置得以在技术与科学上符合自己特殊的需求”[3]。课程理所当然地就成为了“拥有权力和影响的团体与个人”的必争之地。换言之,社会的各个利益群体,都试图站在自身的立场来判断与决定什么知识可以进入课程,什么知识不能进入课程,什么知识必须学习,什么知识是无关紧要或根本不需要学习等权力展开争夺。于是,课程成为了“各类知识与应当传授知识之间冲突的发源地,是谁的知识是‘法定的’和谁有传授知识的法定权之间冲突的发源地”[4]。“不同的集团在此基于自己社会的、文化的和宗教的目的,竞相致力于建立自己的霸权。”[5]所以课程的形成,不仅是国家介入的过程,也是不同利益集团争斗的过程,国家介入的过程充满了斗争。“某一社会文化结构内部的阶级和阶级分子未必与控制经济结构的经济和经济分子相同,文化和政治制度有其自身的历史和自身的需求,他们所追求的这些需求受到经济动力规定的限制,但他们确实具有相对的自主权,因此我们不应期望经济上的支配群体在任何时候都很容易把自身意识形态的利益强加于课程之上,国家文化结构中以及一般地说国家内部的阶级分子,有其自身利益要追求,这些利益可能与支配群体利益一致也可能并不一致,因此就会产生冲突[6]。
如此看来,围绕着课程,至少形成了两股相对抗的力量,一方面是强势群体强力对课程知识进行控制,力图使课程能够成为官方知识的载体,成为传播支配集团身份文化的主流载体;而与此相对抗的是,社会其他群体也试图使自身的知识和文化进入课程,他们对支配集团的控制极力进行抵制。围绕课程的博弈由此而展开。因而,近年来关于课程社会学的研究都特别关注国家和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侧重对课程的形成进行动态的分析,如阿普尔主编的《教科书政治学》中选用了大量类似于“来自朋友的一些帮助:出版商、抗议者以及得克萨斯州教科书政策”的研究;艾沃·F·古德森的《环境教育的诞生——英国学校课程社会史的个案研究》;米查林尼斯·泽姆伯拉斯的《塞浦路斯科学课程为实现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平衡而展开的斗争》(The Global,the Local,and the Science Curriculum:a Struggle for Balance in Cyprus,2002);单文经教授的“美国中小学历史课程标准争议始末(1987-1996)”等。类似的研究近年开始大量涌现。
可以说,对课程博弈的探讨成为当前课程社会学研究的主流倾向,笔者仅在2005年的国际课程权威杂志上就收集到了许多类似的研究成果,如《多元社会的标准化知识》(Standardizing Knowledge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Curriculum Inquiry spring 2005.Blackwell publishing)、《国家精神,多元文化教育和以色列新历史教科书》(National Ethos,Multiculture Education,and the New History Textbooks in Israel.Curriculum Inquiry spring 2005.Blackwell publishing)、《南非国家课程申明的形成》(The Making of South Africa's National Curriculum Statement.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March-April 2005,Taylor & Francis Group Ltd)、《历史,认同和学校课程:中学生思想和观点的实验研究》(History,identity,and the school curriculum in Northern Ireland: an empirical study of secondary students' ideas and perspectives.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January-February2005,Taylor & Francis Group Ltd.)等。
显然,围绕课程而展开的博弈和争斗过程是非常复杂而激烈的,从国家到地方到学校,从教师到学生到家长,从政府机构到公司到企业和其他社会团体等,都无不卷入到学校知识的斗争中。恰如泰勒所言:“参与课程编制活动的人员和机构包括个人、团体、全国性协会和国际组织等,没有哪一个国家是由某一个机构或个人来进行课程编制的。”[7]。如此众多的博弈参与者进行排列组合所形成的博弈类型是非常多样的,既有支配集团内部的博弈、支配集团与被支配集团的博弈,也必然涉及政治精英与学术精英的博弈、支配集团与学生的博弈等。“贸工部、职业部、人力服务委员会、内政部的教育政策及其重点可能与教科部的非常不同。在教科部内部,部长和官员与皇家督学之间有时也存在分歧。继续教育部与国务大臣发生过几次公开冲突。这些争论和斗争是为控制教育的意义和概念所进行的。”[8]
需要提及的是,围绕课程展开的博弈并不会无休止地持续下去,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会达成阶段性的均衡,这种均衡一般是通过各博弈方的“妥协”①来达成的。这意味着,最终形成的课程文本(如课程政策、课程标准,教科书等),其实质就是各方博弈后的结果和体现。当然,这种由“妥协”达成的均衡只是一种阶段性的均衡,“均衡”不是一个绝对性概念,它总是相对于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而言的。也就是说,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下,不同利益群体就课程达成了“均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革,空间的转移以及价值取向的变化,人们以前认定的“均衡”不再“均衡”,他们要打破这种“均衡”,此时又形成了新的利益格局,新一轮的博弈也就开始了。所以课程博弈的过程,究其实质,是一个不断达成均衡,又不断打破均衡,形成新的博弈的过程。“均衡”显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静止的,它是流动的、发展的,打破旧的均衡而建立新的“均衡”恰恰就构成了课程改革不断进行的持续动力。课程,也就在不断地建立均衡与打破均衡中趋于完善。
收稿日期:2009-02-25
注释:
①当然,就某个特定的时期和阶段来看,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可能会完全拆毁或颠覆国家的介入,即不是所有的博弈都必然会走向均衡和妥协,但从整体上或长时期来看,博弈最终将走向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