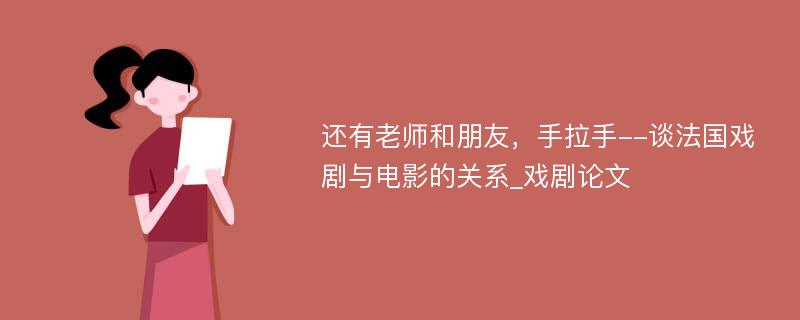
亦师亦友,携手并进——略论法国戏剧与电影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戏剧论文,关系论文,电影论文,亦师亦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法国是个有着悠久文明、深厚文化的欧洲大国。法兰西人民对人文和科学精神的不懈追求,更是造就了其辉煌的艺术。尤其是在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法兰西文化愈发芳香浓郁,从塞尚的绘画到拉威尔的音乐、从波德莱尔的诗歌到普罗斯特的小说、从安托万的戏剧到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法国的现代艺术可谓琳琅满目,始终引领着世界艺术的前进与发展。 然而,林林总总之中,究竟什么最能代表法兰西人的文化传统?什么最能代表独特的法国的人文精神呢?针对这些问题,无疑是仁者见山、智者见水。笔者则以为,其最集中、最鲜明的体现莫过于两种典型的法国艺术,一是以莫里哀、拉辛等人为标志的戏剧,一为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的电影。前者上承古希腊以来的欧洲悲剧与喜剧之传统,下启18世纪以来近现代戏剧之衍变,集各门艺术于一身,深刻反映了法兰西民族的精神气质与美学追求。后者则结合了现代科技与艺术,既体现着法国人永不故步自封、始终追求进步的科学态度,又表现出其海纳百川、勇于创新的实践精神。令人感慨的则是,自电影发明以来,法国艺术家们并没有将之与戏剧对立起来,虽然个别人有过误解,但更多则是如鱼得水地游走于两者之间,不断地丰富自己的艺术创作的同时,更为法国的戏剧与电影的共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的法国,戏剧与电影犹如一对父子、又如一双兄弟或朋友,在前行之路上既有激烈的竞争,更有真诚的合作。在许多艺术家的身上,尤其是20世纪前半期的艺术家之间,都鲜明地体现了戏剧与电影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的关系。 且让我们从法国现代戏剧发展的角度,选取若干与电影有着不解之缘或“无缘”的戏剧家作为代表,通过描述他们对电影的所作所为,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两种艺术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进而发现这种亦师亦友、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是如何有效地帮助了法国电影的成长,戏剧家们的及时出手又是如何让电影摆脱了困境,从而最终使之成长为一门强大的独立艺术,并以鲜明的法兰西民族特色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 一、安托万:以文学提升电影 应该说,当年卢米埃尔兄弟从里昂来到巴黎歌剧院附近的“大咖啡馆”放映其所发明的电影时,虽然曾经在首都民众当中轰动一时,但戏剧界人士的反应并不热烈。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认为,像《工厂大门》、《婴儿午餐》、《水浇园丁》、《火车进站》这类影片只不过是些简单地表现吃饭、下班、浇水、进站等“小把戏”而已,又怎么可能和立意深刻、情节复杂、人物生动的煌煌戏剧相提并论?须知,在电影呱呱坠地之初,以费多、萨拉库、吉特利为代表的林荫道戏剧正如日中天。巴黎歌剧院四周林立的剧院日日车水马龙,夜夜笙歌莺舞,又有多少人从外省乃至外国赶来,如痴如醉地沉湎于拉舍尔、莫奈—苏利、科克兰、莎拉·贝尔纳尔等“戏剧神怪”(monstres sacrés)惟妙惟肖的举手投足之中!戏剧家们对此自是喜在心头,一旁的咖啡馆纵然人头攒动,依然是冷眼相待。 不过,在严肃的戏剧艺术家眼里,林荫道戏剧却是某种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毒瘤,任其发展势必毁掉戏剧艺术。于是,年轻有为的安德烈·安托万(André Antoine,1858-1943)拍案而起,与几个志同道合者创立自由剧团,对走火入魔的法国戏剧进行拨乱反正,将其领上现代艺术的正道。诚然,这位日后被称为“法国现代戏剧奠基人”的功臣由于在戏剧领域艰苦卓绝地开疆辟土,既不可能参与电影的发明,也无暇顾及这位新生儿的成长。电影诞生之后的二十多年之久,安托万都没有投身其中,从而把“电影戏剧”创始人的美名拱手让给了罗培·乌坦剧院的经理乔治·梅里爱。这虽说是安托万个人分身乏术,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时的法国戏剧界对电影的态度并不积极。尽管如此,安托万却又是法国戏剧名家中最早参与电影活动的人士之一。值得指出的是,在他投身电影之际,恰逢新生电影遭遇“题材危机”之时。由于不重视脚本,电影家们邀请的编剧往往为一些蹩脚文人,使得拍出来的影片既没有想象力,更缺乏叙事能力,而这一切恰恰又是戏剧的强项。因此,正如法国电影史家萨杜尔所言:“为了从不景气的情况中摆脱出来,为了把那些比光顾市集木棚的观众更有钱的人吸引到电影院里来,电影就必须在戏剧和文学方面去寻找高尚的题材。”①可想而知,安托万的出场又是多么的及时、多么的必须! 1915年,安托万离开了打拼将近三十年的戏剧,开始其持续七年之久的电影导演生涯,先后拍摄了包括《土地》、《科西嘉兄弟》、《海上劳工》、《九三年》等在内的八部影片。光从这些片名中便可想而知,安托万作为一位强调文学性与艺术性的先锋戏剧导演,自然而然地带了这些困境中的电影所急需的先进理念。在他所拍的影片当中,就有六部改编自文学名著,且大多出自诸如雨果、左拉、大仲马这样的文学大家。此外,在其经营自由剧团期间,安托万曾经与左拉密切合作,大力实践其自然主义理论,这段经历又顺理成章地使之将自然主义原理运用于电影。一方面,他极为重视自然布景,视之为决定人物的重要元素;另一方面,戏剧演员之外,他还大胆起用毫无经验的业余演员,以免表演过于受到戏剧规则的束缚。这一切都给安托万的影片打上了深刻的自然主义烙印,其时并不为大家所欣赏,有的片子如《燕子与山雀》(1920)拍完之后甚至由于发行商认为过于“纪录”而无法排入后期制作,以至于六十多年之后(1982)才由法国电影资料馆根据安托万的指示加以剪辑并与观众见面。尽管如此,安托万的努力无疑有力地拯救了危机中的电影,尤其是其对文学性的重视大大提升了电影的品位。而他追求真实、讲究细节的做法则被认为直接催生了以路易·梅厄康东、雷乃·艾尔维勒等人为代表的法国新写实主义电影。② 二、帕尼奥尔:为电影注入“诗意” 在尚未完全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之前,早期的法国电影时乖运蹇,早在20世纪初就曾出现过许多影院并闭大吉的景象。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有了戏剧及时出手相助,有了梅里爱这样的剧院经理、魔术师将先进的舞台表现手法运用到电影,有了安托万这样的戏剧大师将文学与戏剧元素引入其中,法国的电影才得以起死回生,得以提升与完善。有意思的是,三十年之后,这幕历史再一次上演。随着先锋导演维果(Jean Vigo,1905-1934)的英年早逝,“法国电影似乎陷于完全衰落的状态”。③所幸的是,很快就有约克·费戴尔、让·雷诺阿、马赛尔·卡尔内等为代表的新一代艺术家崛起,法国电影不仅很快恢复了元气,甚至还有机会走向了世界。而在这个被称之为“诗意的现实主义”电影流派中,戏剧家出身的马赛尔·帕尼奥勒(Marcel Pagnol,1895-1974)同样功不可没。 其实,帕尼奥尔可以说是位半路出家的戏剧家和电影家,其最初的谋生手段甚至与艺术没有半点关联。但也正是他在中学担任英语老师期间开始迷恋上了戏剧并尝试写剧本,1924年小试牛刀便获成功,四年之后更因《窦巴兹》一剧一举成名,1929年其剧本《马里尤斯》因为生动地表现了其家乡马赛的风土人情而大获成功,甚至为其赢得了国际声誉。巧合的是,也是在这一年,帕尼奥尔在伦敦生平第一次看到了有声电影,大受震动之余,决定转向这门新兴艺术。《马里尤斯》的成功引起了美国好莱坞派拉蒙公司的注意,他们主动找上门来要求购买版权,颇有商业头脑的帕尼奥尔却只愿意参股合作。1931年,派拉蒙公司最终屈服,同意与之合作,并答应其由法国演员来担任演员的要求。在匈牙利裔导演考达(Alexander Korda,1893-1956)的执导下,《马里尤斯》果然一炮打响,不仅在巴黎轰动一时,而且成为在全球大获成功的法国第一部有声影片。于是,帕尼奥尔一不作二不休,立马完成了《马里尤斯》的第二部《范妮》,并于次年被搬上银幕。更有意思的是,这位富起来了的戏剧家竟然于1932年在巴黎成立了一家电影公司!两年之后,他又在马赛附近购置地产,立志将其打造成法国的好莱坞。1933年,帕尼奥尔不再甘心编剧,而是直接“触电”,导演了自己的处女影片,根据剧作家奥吉耶作品改编《普瓦利耶先生的女婿》。整个30年代,这位电影新手都以巨大的热情投入电影事业,平均每年执导两部,直到“二战”爆发。作为一位戏剧家和文学家,帕尼奥尔可谓对电影情有独钟,不仅自己乐此不疲,而且还动员小说家友人让·齐奥诺参与进来。从其电影名单中可以发现,帕尼奥尔的多数影片不是改编自他本人的剧本,就是改编自后者的小说,而像《窦巴兹》这部剧作,他甚至亲自执导了两次(分别在1936年和1951年)。1950年中期之后,功成名就的帕尼奥尔基本息影,主要兴趣转向撰写回忆录和创作小说。有趣的是,这位戏剧电影两栖艺术家竟然逆向地从自己的影片中获取灵感,根据《泉水玛侬》写出了长篇小说《山泉》。毫无疑问,像帕尼奥尔这样长期同时在戏剧与电影两个领域里耕耘的法国艺术家并不多见,而能在两个领域里都能获得成功者更是屈指可数。事实上,帕尼奥尔的加入除了大大丰富了“诗意的现实主义”之外,他虽然与“作家电影”无关,但却代表了法国戏剧与电影、作家与电影的完美结合。 三、科克托:戏剧、电影实验两不误 在讨论20世纪法国戏剧与电影关系史的时候,让·科克托(Jean Cocteau,1889-1963)无疑是一位绕不过去的人物。这是一位举足轻重且十分奇特的艺术家,他才华横溢、精力过人,涉足过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绘画、摄影、舞蹈等众多领域,被人誉为时代的“经纪人”、时尚的引领者和艺术家的保护神。然而,经过时代的大浪淘沙,在今人眼里,科克托堪称彪炳千秋的成就主要来自小说、戏剧与电影这三大领域。在其青年时代,正值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喧嚣一时,因而他也和其他先锋派艺术家一样,写诗歌、编杂志、与“六人组”办音乐会、跟佳吉列夫一起编创先锋舞蹈,可谓活力四射。当然,直至人到中年,除了诗歌和小说之外,科克托的主要兴趣还是在戏剧,作品(包括《奥尔菲》、《人类之声》、《爆炸装置》、《可怕的父母》、《冷漠的美男子》等)大多完成于其40岁之前。即使此后他的很大精力都投入了电影,他也从来没有放弃戏剧,而是一以贯之地坚持,直到离开人世。其实,在与音乐、舞蹈家们过从甚密的那段时期,他也更多是作为一名戏剧家参与其中,如《蓝神》(1912)、《游行》(1917)、《牝鹿》(1924)等都是其为舞蹈戏剧所作脚本;而与“六人团”音乐家们合作的脚本《埃菲尔铁塔上的婚礼》更是一部颇具影响的超现实主义戏剧。而他得以名垂青史的三部大作,即《可怕的孩子》(1929)、《可怕的父母》(1938)和《美女与野兽》(1945)中后两部一为戏剧剧本,另一为电影脚本,可见戏剧在科克托的艺术道路上有多么重要。 这样一位重量级的戏剧人物在其人生巅峰时期投身电影,其意义自是不同凡响。1929年,看似一个偶然的机会,竟然造就了一部被评论者认为是具有超现实主义特质的“先锋的里程碑”影片《诗人之血》。只不过,这部由四个部分组成的电影充满了梦魇般的情节与荒诞不经的场面,又由于制片人同样也是《黄金岁月》的制片人德·努阿利斯子爵,因而放映之后便遭到评论界的激烈批评,认为科克托抄袭了路易斯·布努艾尔。事实上,该片既是其先前诗歌和先锋戏剧的延续,更是其今后作品的预示,集中表现了科克托天马行空式的狂放想象力、其所钟爱的神话题材、镜像主题以及眼睛、雕像、门等图像等极具梦幻特征的手法。当然,最为重要的则是科克托所具有的无论是在戏剧创作还是在电影创作中那种敢于蔑视规则、打破规则的非凡胆识。而所有这一切都在之后的几部重要影片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美女与野兽》如此,《奥尔菲》(1950)更是如此。有人甚至认为,科克托的创作不仅为法国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开辟了道路,而且也影响了英格玛·伯格曼、文森特·米纳利等人④;也有学者认为新浪潮电影的兴起也有他的一份功劳。⑤而在我们看来,科克托最大的功劳应该是将其所特有的先锋派精神、天马行空式的想象和无拘无束的手法极其娴熟自如地应用于戏剧与电影,在革新了传统戏剧的同时,更是大大丰富了年轻的电影。 四、阿尔托:“残酷”艺术的引领人 如果说帕尼奥尔堪称戏剧与电影完美结合的典范,那么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1896-1948)却是一个不幸的反面例子。这位对当代西方戏剧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艺术家如今可谓家喻户晓,但在其生前却是默默无闻,没有获得过命运一丝一毫的垂青。阿尔托一生坎坷,最后的岁月竟是在精神病院和简陋的小医院里痛苦度过,直至孤苦伶仃地离开人世。然而,他对西方戏剧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而又久远,至今人们都依然可以在全世界无时无刻地感受得到。事实上,阿尔托的残酷戏剧理论的穿透力远远突破了戏剧的疆界,强烈地辐射到几乎所有的艺术领域,电影自然也不例外。 虽然比不上神人科克多,阿尔托本人却也是一个颇有才华的艺术能手。他自幼就喜欢在家庭晚会上表演,中学时代以写诗为乐。青年时代他前往巴黎发展,一边努力从事写作,一边投身戏剧。他勤奋努力,并表现出不同一般的才能,尤其在戏剧方面。他不仅表演出色,同时还担任舞台和服装方面的设计,着实为导演吕涅一波出力不小。然而,无论是在艺术剧院、还是后来在杜兰的工间剧院,或者是在庇托耶夫的剧院,阿尔托都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此时的巴黎艺术圈内,各种莫名的艺术思潮泛滥,形形色色的先锋实验盛行,阿尔托有机会结识了布勒东并应邀主持“超现实主义研究中心”。虽然不久两人便因理念不合而分道扬镳,但超现实主义者离经叛道的举动与思想无疑对其日后的“残酷戏剧”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为一位极具超前意识的艺术家,阿尔托同样十分关注电影。早年在主持超现实主义中心时,他就为电影写过脚本。在戏剧界颇受挫折之后,他开始尝试涉足电影,甚至与其时一些重要导演如阿贝尔·冈斯、弗立茨·朗格等人有过密切的往来或合作,并在多部影片中担任角色。据统计,阿尔托总共在23部影片中出演,只不过,由于其形象特异,因而始终没有获得要角,不要说主要人物,就是二号或三号人物也与之无缘,与其在戏剧界的遭遇如出一辙。而在他所写的十多部电影脚本中,唯有《贝壳与教士》于1927年被女导演热尔曼娜·杜拉克搬上了银幕。然而,这部唯一的阿尔托影片首映之日却因为不合超现实主义者们的口味而被搅黄,阿尔托对电影的痴迷就此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彻底失望,一如他先前对传统戏剧的态度。1933年,他在一篇题为《电影的早衰》中愤懑地写道:“电影世界是个死亡的、幻象的和断裂的世界。电影世界是个封闭的世界,与生活脱节的世界。”⑥言词之激烈堪比《残酷戏剧宣言》对西方传统戏剧的批评。从此,他开始专心致志地构建其残酷戏剧理论。 无须讳言,阿尔托的戏剧理论激进而又超前,因而不仅在当时不为人理解且自身的实验也鲜有成功,就是在“二战”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无人问津。然而,当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发现了《残酷戏剧》之后,立即如获至宝,不仅广泛运用于戏剧实践,而且突破了其疆界。于是,包括戏剧在内的西方艺术进入一个全新的“后现代”,各式各样的表演艺术应运而生:即兴戏剧、机遇戏剧、木偶戏剧、舞蹈戏剧……传统的规则被扫除、传统的界限被打破、传统的样式被摒弃,一个不讲规则、没有界限、充满对立与杂乱的新时代宣告到来!戏剧领域可谓全军覆没,音乐、舞蹈、绘画、当然还有电影同样概莫能外……而在20世纪末众多的戏剧与电影作品,“残酷”也成为必不可少的元素。而在著名戏剧与电影两栖导演帕特里斯·谢侯执导的《黑人与狗之战》、《屏风》等戏剧以及《受伤男子》、《玛戈王后》等影片中,“残酷戏剧之父”安托南·阿尔托的影子始终在游荡。 回顾起来,19世纪末,法国戏剧界总体上对新声初啼的电影并不以为然。不过,一些有识之士很快意识到其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因而积极地投身进去。20世纪初,当电影陷入困境之际,诸如安托万这样的资深戏剧家们的加入无疑是其恢复生机的有力保证。当然,戏剧家们的动机不尽相同,不少人视电影为戏剧的延伸,想利用这一新的媒介来为之服务,于是有了“罐头戏剧”一说。然而,更多的人则欲以先进的戏剧观念与技巧、以文学的养料来培育这个蹒跚学步的电影少年。正是在萨夏·吉特利、帕尼奥尔、科克托以及其他那些或功成名就或年轻有为的戏剧家们的热情帮助、参与之下,20世纪的法国电影才得以克服成长中所遇到的重重危机,跨过一道又一道的坎儿,从一个孱弱少年成长为一个结实壮汉。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电影终于独自挺立起来,告别了戏剧这根拐杖。 “二战”结束之后,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尤其是艺术观念始终不断的更新,法国的电影艺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克服了短暂的困难之后,“新浪潮”迅猛崛起,法国电影一时独步世界。此时的电影艺术应该说完全在依据自身的规律独立自主地发展与壮大。尽管如此,由于电影与戏剧有着共同的基因,因而两者之间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天然联系。戏剧作为一门有着二千五百多年历史的艺术,其深厚的底蕴依然是只有区区一百多年经历的电影取之不尽的宝藏,依然是电影精神上、物质上的良师益友。因此,无论是在美国还是英国、德国还是法国,乐此不疲地游走于戏剧与电影之间者至今都不乏其人。阿瑟·密勒、哈罗德·品特、莱·维·法斯宾德、热拉尔·德帕迪约以及帕特里斯·谢侯等都是极具说服力的榜样。 值得指出的是,2013年辞世的谢侯作为一位全才艺术家,戏剧虽为其终身职业,但后期则更多地献身于电影,同样成就骄人。他在戏剧领域取得的编剧、导演、表演、舞美等独特而又丰富的经验,使得他所执导的影片散发出特有的艺术魅力,无论是影片的结构、光影的运用,还是人物的塑造或场面的调度,无不打上戏剧的烙印。可以说,谢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法国戏剧与电影这两门艺术融为一体的化身。毫无疑问,作为20世纪下半期法国最后一位戏剧与电影两栖艺术大师,谢侯既非法国电影史上第一位戏剧家,自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位。可以进一步想象的则是,未来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其他各国,戏剧与电影这两门艺术都会一如既往地携手并进。 ①[法]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徐昭、胡承伟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 ②参见http://fr.wikipedia.org/wiki/Andre_Antoine。 ③同②,第326页。 ④参见http://fr.wikipedia.org/wiki/Jean_Cocteau。 ⑤参见范蓓《作为超文本现象的让·谷克多》,《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⑥转引自http://fr.wikipedia.org/wiki/Antonin_Arta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