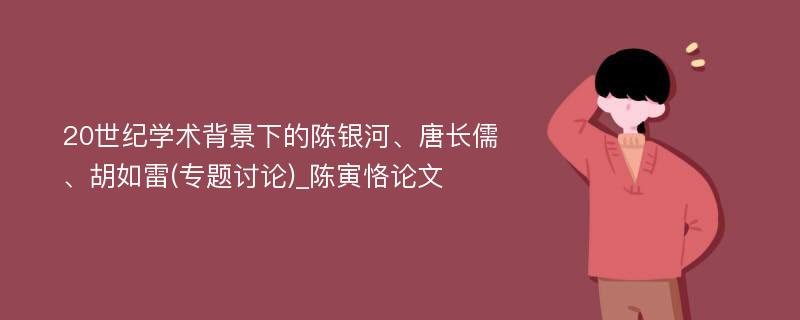
20世纪学术背景下的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专题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专题讨论论文,如雷论文,学术论文,世纪论文,陈寅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长孺师与吐鲁番文书
朱雷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在回顾唐长孺师毕生学术贡献时,就不能不提到在他倡议并领导下,历时十三年才完成的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唐师对吐鲁番文书的接触,据我所知,早年是通过王树柟的《新疆访古录》、金祖同的《流沙遗珍》等。新中国成立后,除了黄文弼的《吐鲁番考古记》,就是《文物》杂志20世纪60年代后所刊载的少量发掘简报,还有沙知先生利用出土文书研究有关契券制度的文章,以及所能见到的日本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更集中地看到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唐史的论著是在1962年。唐师嘱人由香港购回日本西域文化研究会所编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下两册,其中除引用敦煌文书外,还比较完整地引用了“大谷文书”。利用吐鲁番文书研究唐史中的某些问题,此时已引起了唐师的关注,只是由于“左”的干扰,特别是唐师于1964年去北京参加《二十四史》的校点工作,一去十年,直到1974年夏才完成,因而耽搁了下来。
1973年夏,为了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时任中共武汉大学历史系党支部书记的彭神保提出一个点子:为编写教材外出搜集考古材料。当时,居然得到校方同意,随即拟出路线图:洛阳——西安(包括周围诸县)——天水麦积山——兰州——新疆——敦煌——大同。于当年10月初成行,12月中旬由兰州赶到乌鲁木齐。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院展览厅中,看到了数件文书。在此期间,也看到了当年出版的11期《文物》杂志,其上有多篇新疆同人利用文书撰写的论文。接着又得到新疆博物院的热情介绍,使我们大开眼界,异常兴奋和激动。当时,彭神保提议给正在北京中华书局做校点工作的唐长孺师写信,介绍初步所见所闻。当年12月底到达敦煌千佛洞后,接到唐师的信,认为这批文书的价值,就在于在某些问题上,“将使唐史研究为之改观”。同时,提到已向国家文物局领导王冶秋、刘仰峤建议整理这批出土文书,并获得同意。1974年元月中旬,我们赶到北京,向唐师作了汇报,并见到国家文物局领导,知道王冶秋决定由唐师主持,由新疆与武汉大学合作,文物出版社负责出资,开展整理工作。
1974年春节后,唐师决定动身前,考虑到整理工作本身之需要,也考虑新疆方面文献资料的缺乏,故开出了一大批书目。这些图书既有基本史籍,也有内典;既有学术专著,也有工具书。除了向武汉大学校、系及研究室、图书资料室借用外,唐师的一套扬州版《全唐文》也装箱。又考虑到工作的特殊需要,还将在西安购得的一台旧式国产复印机一起运到新疆。而就在动身前夕,唐师一人被强留下来,要他去做他不愿做的事——“评法批儒”。而其他能去的人,也因种种原因,一直拖到当年9月中旬才动身去乌鲁木齐。
1975年4月底,唐师始成行赴新疆,先期带通晓英语、日语,熟知典籍年近六旬的谭两宜先生和我去乌鲁木齐。唐师去了吐鲁番哈拉和卓、阿斯塔那墓葬区,看到发现文书的古墓,也参观了交河、高昌两座古城,激动不已。但就在去南疆的库车后,因乘坐手扶拖拉机挂带的斗车上,行走在路况极差的“机耕道”上,强烈的颠簸致使右眼眼底出血,造成失明。由于新疆医疗条件差,唐师不得不返回北京,住进工农兵医院(即同仁医院)诊治。我与谭两宜则留新疆继续工作,谭两宜负责清理博物馆藏文书登记,我则又下吐鲁番地区博物院,清理、拼合、录文其所藏文书及墓志。
期间,王冶秋又专门给国务院写报告,提出由唐师负责,带领专班人员,整理吐鲁番文书。李先念副总理批示“拟同意”,又经邓小平副总理圈阅,遂决定将此项工作转至北京进行。我与谭两宜在9月底结束新疆工作,于10月初到北京,在医院了解到唐师本因深度近视,视网膜极易脱落,因眼底出血,造成晶体混浊,复明有难度,直到11月15日唐师才出院。这时,新疆博物馆也将馆藏文书装箱运到北京,参加整理工作的各路人马也陆续抵达,唐师开始全身心地投入领导整理工作。
在唐师指导下,我根据1962年冬在唐师指导下所作敦煌文书录文校补的体会,以及1974年、1975年在新疆初涉吐鲁番文书整理的点滴体会,加上学习历史所1958年所编《敦煌资料》第1辑,以及日本所出《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下册,吸取、借鉴其有益的方法,草拟了一个“录文须知”。经整理组讨论,定下了一个共同遵守的工作原则。
面对近万片的残片,首先要在辨识的基础上,作出准确录文,而录文和碎片的拼合是两项最基本的工作。但出于文物保护的要求,最开始还必须仅据那些照、洗并不高明的小照片,做录文与拼合。唐师也和大家同样拿着小照片去做录文工作,但由于右眼已失明,左眼戴镜矫正也只有0.3度,困难远非常人所能想象。最后,唐师发现若在照片背后用台灯照射,正面看起来就比较清晰,这一经验也为大家所仿效。
在录文核对,以及准确进行碎片的拼合时,就要接触原件了,而这些出自千余年前古尸身上之物,其中不少还有血污等因素,辨识既难,且多有尸臭味,甚至可能还有细菌,但唐师毫不考虑个人健康,每道工序皆不免省。我出于考虑唐师身体健康,劝他注意少接触,但唐师说:“我不看原件,怎么知道对与不对?”只好在休息时和进餐前带他去洗手。
字难辨识,残片难拼合,这都是常人所难以想象得到的。而在进入“定名”、“断代”阶段,更是艰辛,因为判断文书整理成功与否的标志,主要是根据释文拼合之准确,“定名”之遵合古制,“断代”之清晰等诸方因素。其中,文书之准确“定名”和“断代”所要求的学术水准是很高的,难度因而也是极大的。故作为文书整理的领导者,尤须在历史及古文献、书法诸方面具有渊博精深之学识,方能对这批从十六国到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官、私文书,以及古书、佛、道经典作出准确之定名。面对大量并无纪年之残片,既要考虑纸质,又要考虑书法之时代风格变化。除了这些“外证”,还特别需要从文书本身寻求“内证”,从而作出适当的判断(准确或比较接近的“断代”)。
由于整理组成员来自多方,学识、性格不同,甚或间有“利益”之冲突,也会影响整个整理工作。但唐师不仅凭借自己的学术威望,而且以“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处理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问题,保证了较快、较好地完成整理工作,并陆续出版了十册录文本和四巨册图文本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在全书出版后,文物出版社的多位编辑都多次给我讲到:“要不是唐先生的领导坐镇,你们的工作就不可能完成”。
人们往往只看到唐先生在整理工作上的贡献,可能忽视或不知,唐先生在完成整理工作过程中,又直接培养了那些有机会参加整理工作的同志,从具体到一个字的辨识,到文书的拼合、定名、断代,以及进一步的研究,皆直接或间接得益于唐师的教诲。特别是唐师决不搞知识私有,总是毫无保留地当众讲出自己的精辟创见。当时也有人立即抢先撰文发表。我曾和唐师谈及此事,但他毫不在意,依然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
由于唐师的倡导和领导,开始于1974年的整理工作,至1986年春,历时十三年,终于大功告成。唐师提出对吐鲁番文书的整理,是在他年届六十岁时,这时他在学术上早已功成名就,但他在学术上永不止步,永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始终保持高度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始终肩负着强烈的学术责任感。唐师长期离家,持续十年在北京校点“北朝四史”是这样;远赴新疆,克服目疾的折磨,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主持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更是如此。在唐师身上,可以深刻体会到什么是“忘我”的精神,什么是真正的学人风范。
1976年,唐山大地震。唐师虽有惊无险,并因避震入住故宫武英殿,接着又带领整理组转到上海继续工作,直到当年底,始返京。工作的繁重,生活的困难,加之年纪的增老,唐师生过病,还入北京医院救治过。特别是在恢复研究生的招收后,唐师还要返校给他的研究生和系里的本科生开课讲授,又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隋唐卷》主编,还有国内外学术会议,这些都要花费相当的精力,但始终没有影响他对整理工作的指导。唐师返校是因为研究生的培养需要,但唐师母骨折住院,唐师却没有为此请假回武汉照料。唐师在京工作期间,绝大多数日子,中餐在食堂就餐,早、晚餐就由我这个自入初中到参加工作后,均是吃食堂,而不会做饭菜的人去掌勺,但唐师从不高要求,更不责难我。
正是在唐长孺师坐镇和他身先士卒的率领下,终于完成了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出版。今天我们在缅怀唐先生的风范时,学习和继承他光明磊落、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以学到的。
〔朱雷(1937—),男,浙江省海盐县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
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与20世纪中国学术史
张国刚
(清华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84)
从宏观上看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发展史,可以观察到一个从否定传统到呼唤回归本土化的历史变化过程。首先是西方学术的冲击,中国学人作出过激的反应,用学术的现代化或西方化来否定本民族学术传统。然后在民族的危机感和自信心的双重作用下,又出现呼吁学术的本土化的趋向。但是,本土化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西学、恢复旧学。达到这样一种比较理性的认识,其实经历了几代学者的长期探索,其中就包括陈寅恪(1890—1969)、唐长孺(1911—1994)和胡如雷(1926—1998)。
陈、唐、胡都是20世纪研究唐史的大家。他们身前死后的声名与毁誉很不同,治学风格与个人性格也差异很大,但放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去审视,仍然可以从他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中看到某种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对于中国学术独特品格的不懈追求。20世纪中国学术史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处理传统旧学与现代西学的关系,只是不同的时期这个问题会以不同的方式被提出来而已。陈寅恪、唐长孺和胡如雷都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而留下了自己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先说陈寅恪。
在20世纪前期,陈寅恪所面临的是如何处理民族学术传统与外来学术思潮的关系问题。甲午战争以后,西学汹涌而入,“新史学”、白话运动、文学革命,都在批判传统中开辟了自己的道路,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更达到了一个高潮。但是,有人否定传统,就有人捍卫传统。20年代前后就有一些人从反传统到回归传统,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杜亚泉的论战以及“学衡派”的出现都是其表现。此时步入史学殿堂的陈寅恪,自然也要回答这一时代的中心问题。
陈寅恪二十多岁就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名满天下的梁启超、王国维和哈佛博士赵元任比肩而立。但我们无须人为地拔高或神化陈寅恪,似乎陈寅恪十四岁留学东洋、二十来岁游学欧美就已经抱着如何宏大的理想和志愿,这未必入情入理。出国留学当时是读书人向往的时代潮流,陈寅恪只是“预流”者之一。至于陈寅恪为何选择梵文和佛典翻译文学、西北史地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因缘际会的可能性最大。也许为晚清以来兴起的边疆史地研究风气所激励,也许受到海外东方学研究的影响,等等。当然,也可能陈寅恪觉得自己在这个领域能够博取中西新旧学术之长而补彼此之短。但是,陈寅恪在国外学的这身绝技,回国并没有“用武之地”,盖资料不足也,清华国学研究院内响应者寥寥!陈寅恪转而治中古史实有多方面原因。
陈寅恪唐史研究的名著当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及《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陈寅恪如今已经成为学术经典或标签。他睿智的片言只语不仅足以成为后来学者支持自己观点的根据:你看,陈寅恪都如此说;而且也为做翻案文章的人提供靶子,以显示自己文章的“创新价值”:你看,陈寅恪都讲错了。但是,陈寅恪真正的学术意义决不仅仅是对某一具体问题作出的研究结论,而在于开创了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新时代。更进一步说,陈寅恪通过他的中古史研究实践,表明了自己处理民族学术传统与外来学术理论关系的态度和方法。大家发现,陈寅恪论著的形式很传统,提出的问题却很现代,而处理问题的手法则中西合璧,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陈寅恪试图创造一个扎根于中国历史实际的学术范式和方法,那就是他总结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即在学术研究中要做到考古与文献资料的互相释证;中文与外文资料的互相补证;西方理论、概念与本国历史记载的互相参证。这样的总结本身就是中西合璧的方法论结晶。如果说前两点主要表现为史料范围的扩大,是对自古以来特别是乾嘉以来传统考据学的总结、升华和超越,那么关键的第三点“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就表现为史学观念的根本变革和更新,是一种旷古未有的全新的方法论(格义佛学与此不类)。因为,域外文献利用与现代考古学方法的引进和地下资料的发现,固然与西方学术的影响难解难分,但是,只有外来观念即理论、范式、概念的引进并用之于解释传统史料,才导致了近代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的根本特征。陈寅恪运用文化史观解释中国中古历史,试图构建中古史学的新框架。所谓关陇集团,所谓胡汉分野看文化不看血统,都是引进外来观念参证中古历史的尝试。陈寅恪说:“其真能于思想史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1] (P252)这样一种处理传统学术与外来理论关系的正确态度和方法,使他成为时代的翘楚!
再看唐长孺。
唐长孺比陈寅恪年轻二十多岁。他的研究范围也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与陈寅恪先生类似。在唐长孺精力最充沛的20世纪40—60年代,中国社会的政治面貌和文化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家庭教养还是师承受业,唐长孺所受的都是旧式教育,但在他盛年从事研究工作时却不能不面对新社会的意识形态环境。因此,对于他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如何处理好旧史料与新思想的关系是个严峻的挑战。如果说,陈寅恪那里“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还是一个广泛的概念的话,那么,在唐长孺这里就特定地被教条化了的唯物史观,或者说被苏联过滤了的“马克思主义”所指代。如何处理这个特定的外来理论与民族之本位的关系,是唐长孺那一代学者所必须面对的课题。
唐长孺们确实在努力学习唯物史观,他在1954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跋语》里说:“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惭愧,从解放到现在经过了五年的学习,然而一接触到问题的本质,面对着一大堆资料就常常会束手无策,不能作深入的追寻。”唐长孺这里流露的思想是很真实的。一方面,真诚地希望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之于学术研究;另外一方面又深切地觉得“学不到家”。因为唯物史观用之于具体学术研究,只能得其意而不能随便贴标签。唐长孺不会也不愿意削足适履,生搬硬套,所以,有时会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这充分体现了唐长孺襟怀坦荡,虽然不甘落后于时代的潮流,但仍忠于自己的学术良知。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受到陈寅恪的赞赏,陈寅恪收到赠书后回信对唐长孺说:“今日奉到来示与大著。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颂尊著,辄为心折。”[2] (P23)唐长孺虽然是“魏晋封建说”的支持者之一,在这方面的理论探讨并不多。他晚年的作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试图总结他关于中古历史的一些理论思考,提出了所谓“中国是一个亚洲型的国家,奴隶社会带有亚洲的特征,封建社会也带有亚洲型特征”[3] (P18),也基本上只有结论而缺少论证。倒是他对魏晋隋唐史的具体探索,仍然娴熟地运用了实证研究方法,很少“以论带史”(“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评法批儒”文章除外)。他的重要代表作如《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唐书兵志笺正》、《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山居丛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以及其他散见的论文等,都体现了微观入手、宏观着眼的学术境界。他在这些学术论著中显示的问题意识、研究思路、论证方法,都是对陈寅恪同时代学者所提倡的引西学入中学的研究理路的进一步发展。所以,陈寅恪用“心折”来表达对唐长孺学术贡献的赞赏。融新旧学问于一炉的实证研究,正是唐长孺获得中外学术界尊敬的一个重要原因。
于是,我们发现在唐长孺所处的时代,整个学术界都被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所笼罩,王国维、陈寅恪等倡导的学术传统被彻底边缘化了。于是,物极必反,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乃是唐长孺所作的传统学问。这样的实证研究更具有“兴灭继绝”的价值。尽管唐长孺也在学习马列著作,探索所谓亚洲型社会的特征,但是,他的学术成就和受人尊敬的原因却不在这个方面。
最后谈胡如雷。
胡如雷的命运就不同了。胡如雷从年纪上看比唐长孺小十几岁,所受到的教育却完全不同。像胡如雷这样在北伐战争时出生,新中国成立时二十来岁的历史学者,他们大都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下过很深的工夫,也确实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所震撼。在全国上下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年代里,他们接受了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由于年富力强,所受影响也最大。
胡如雷的代表作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此外,唐史方面的著作有《李世民传》、《唐末农民战争》以及晚年由散篇论文结集而成的《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隋唐五代政治史论稿》等。胡如雷的论文选题反映了5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的热点问题,他积极参与了“五朵金花”中土地问题、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胡如雷超出他的同辈人的是,别人也许只是撰写了若干理论型论文,只有他花十余年时间独立撰写了一部功力深厚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专著。毋庸讳言,这部著作受到《资本论》等著作的影响和启发,作者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关系、地租形态和地主经济等。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接着陈寅恪在继续做“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尝试之一;也可以说它就是唐长孺引据郭沫若的话所说的那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学到家”的理论著作;或者说是唐长孺“亚洲型社会”的理论化论证。难怪唐长孺等自叹学马列学不到家的老一辈学者对胡如雷等这一代新人的理论水平始终抱着激赏的态度。当然,胡如雷等对于唐长孺一辈学者的功底也是常怀羡慕之心。20世纪50—80年代的中国史学主要是这样两代人占据史坛的主角位置,他们彼此互补,彼此推赏!
今天,我们站在21世纪初叶,重新回顾20世纪的历史学发展,就很容易看出陈、唐、胡这三代史学家的学术演变轨迹。陈寅恪著作中的一些具体结论在今天也许已经难以服众,但是,他圆融无碍地引西学入中学,以文化史观解读中古历史奥秘的探索精神和方法却具有垂范意义。真所谓“先生之著作容或可商”,而先生之精神却“与三光而永光”(陈寅恪悼王国维语)。唐长孺自诩为陈寅恪的私淑弟子,用实证的研究业绩把陈寅恪等开创的以西学治中学的做法不漏痕迹地加以发扬光大,从而避免了陷于50年代风行的教条主义的泥淖。
至于胡如雷的贡献则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尽管如今很少有人评价或者引用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因为人们对于如何定义中国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有了分歧的看法。但是,胡如雷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理论,并不是单纯地在追求经典作家理论的普适性,他在书中的处理方式实际上是在探索一个能够解释和说明中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理论框架。不管这个框架是否合适,其中的许多理论探索(比如关于地主经济的一些分析)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尤其在今天,当我们呼吁寻求中国学术本土化道路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重视前辈学者所作的探索,其中,不仅包括陈寅恪和唐长孺,而且也包括胡如雷。因为胡如雷的研究其实也构成了中国史学本土化探索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我们今天评价陈、唐、胡等先贤学术论著及其贡献的意义所在。
〔张国刚(1956—),男,安徽省宿松县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中西文化关系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