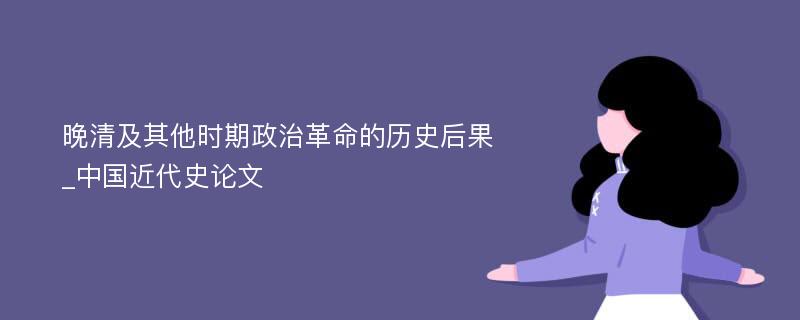
晚清政治革命的历史结局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及其他论文,结局论文,政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国内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为基本内容的辛亥革命素为世人所瞩目,其成败得失至今仍属于中外史学家争论不休的一个焦点,言人人殊。个中现象,既源于史学客体辛亥革命自身的复杂性,也同史学主体的主观差异性不无关系。本文拟就政治革命的历史结局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认识论问题略抒浅见,权充拙稿《辛亥革命的历史条件与历史结局》〔1〕一文的补充与续编。
一
作为史学主体的史学工作者往往借“历史的反思”之名义,回头审视同行们之于史学客体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准确地说,这与其说是“历史的反思”,还不如说是史学工作者的反思,即史学主体之于历史的认知活动。“历史的反思”之类提法只有相对于“哲学的反思”、“文学的反思”等等才具有确切的意义与针对性。历史本身不可能反思,只有借助于史学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才有可能跻身于人类的思维空间,从而使人“明智”。故“反思”不啻于“再思”的同义语。
为强调历史学的智力功能与社会作用的特殊性,突出有关史学课题及其成果的重要性,治史者大都习惯于把自己对某些历史问题的总结性认识包装成“历史规律”。比奔腾不息的江河要复杂得多的人类历史是否真有那么多非此即彼的规律?历史规律是像澳大利亚菲利普岛上的仙企鹅那样每晚8∶05分分秒不差地向岸边翩翩舞来或走来, 不厌其烦地以守时和重复出现给人类以验证和观赏,还是像自然科学所揭示的那些规律一样可以通过实验员关于既定条件的指令而重复出现,接受检验,抑或是借助于因果关系或概率统计或系统信息归纳出某种历史必然性从而形成历史决定论所致,这在中外哲学界和史学界还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笔者在这里并不打算直接参与历史规律讨论的任务,但清末政治革命的历史结局却不能不激起我们无尽的思索,并使我们不知不觉地碰撞某些被称作历史规律的规范性认识。
无庸讳言,在我国学术界,忽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科学性差异是长期存在的,有关历史规律的包装与表述有时难免塞进研究者个人的“私货”,把某些超时空地总结出来的所谓历史教训、失败原因也统统说成是历史规律,或者根据事物的结果来衡量事物的过程,或者根据自己所认定的某种历史规律推衍出一些同历史条件不相干的历史教训或失败原因来,在充当事后诸葛亮的同时,又不自觉地把历史学当成了“胜利者的宣传”〔2〕。 人们对近代君主立宪方案乃至近代资本主义道路所存在的某种合理性的否认就是如此。
恩格斯在论述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规律之间的关系时指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不过,“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3〕
循此思路,我们不妨认为,虽然某个历史发展区间的必然性结果大体只有一个,但促成这个必然性结果的因素往往是多种多样的,有些因素虽然在酝酿必然性结果的过程中就已消失,但它同迟到的结果之间也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因果联系,它为促成这个结果(无论是良果还是劣果)也注入了一分作用。尽管往往只有一种历史的可能性酿成了现实之果,但在这个现实之果产生之前的可能性并非只有一种,这些可能性的数量似乎比历史合力所包含的分力的数量还要多,它们的存在或消失都在随时影响着那种可望转化成现实的可能性,后者同现实之间也不是一种直接对应的关系,现实之果的瓜熟蒂落,还得取决于一个不断变化着的区间,可望转化成现实的那种可能性也往往在这个变化区间中经受考验,作出相应的充实、调整甚至再生。我们还不能说唯有符合结果的那种可能性就是历史的必然性所在,就是历史规律。否则,历史就无复杂性可言,历史决定论就容易走向宿命论和神秘论。
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与历史传统决定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尤其是新生的资产阶级民权政治制度的确立需要资本主义经济作为坚强后盾,对于那些为数众多的广大民众来说,政治上的自由与平等要求同经济上的自由竞争要求是一致的。往往是后者决定前者。如果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抱有某种学术偏见,那么,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这一层道理是可以称作历史规律的。马克思说:“如果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成熟,君主专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暂时的。”〔4 〕尽管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的君主专制被推翻总的说来不是暂时的,而是长久的,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无需仰仗他人主宰自己命运的程度,而且广大资本家还不可思议地被临时参议院拒之于民权政治的参政大门之外,中华民国的民权建设也的确不够理想。如果说辛亥革命的发生在内忧外患种种因素强烈刺激上,可以不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可以显示其超常的进步性,那么,革命发生之后的民权建设就最终跳不出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革命的成就就得大打折扣。
在近代中国,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始终发展缓慢,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实体及至清朝末年才刚刚形成,其力量也并不强大,资产阶级的民权政治思想与政治革命方案还主要不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不是如同瓜熟蒂落一般,而是孙中山等人当作一种救国良方从西方直接引进的。欲期这种良方在中国专制主义的厚实土壤里产生奇效,克服排斥反应,的确还需要一个精心培育和护理的过程,不是光凭革命激情便能解决问题。激情在暴力革命阶段无疑举足轻重,民权建设却更需要全社会的理性与知识。
二
列宁说:“变革可能已经成熟,而完成变革的革命者可能还没有充分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变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会继续腐烂下去,有时能达几十年之久。”〔5 〕列宁的估计对于民国年间的中国社会无疑是合适的。历史虽然在前进,但它始终伴随着痛苦和灾难,国人为着获取民国社会的进步而付出代价的过程是与进步本身相始终的。1912 年4月,当孙中山兴致勃勃地向国人宣告政治革命的任务已经连同民族革命的任务一起竣工时,头脑冷静的梁启超则直言不讳地提醒人们:“我国由五千年之专制一跃而进于共和,旧信条横亘脑中,新信条未尝熏受,欲求新政体之圆满发达难矣。”〔6〕
晚近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表明: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不会重复前人所走过的道路,模仿中的变异在所难免。应该说,经济的发展是如此,政治的发展也未尝不是如此。
一般说来,“一个过于落后的国家,原是不可能自行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统治花样的。可是,一个政府,在经济上,如照亚当·斯密所说,最容易仿效他国新的敛财征税制度;它在政治上,也许就最容易模仿他国新的统治组织。抛开社会关系或社会条件专从外观上技术上来学样,当然是会变质的。”〔7〕
关于民国初期的武人政治、政客政治与劣绅政治,关于民权的剥夺与人民对自身政治权利的漠视和麻木,自历史之有民国以来,痛心批露者和严辞抨击者层出不穷,无庸赘述。作者只想指出:个中现象在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发达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值得深思的〔8〕。既不足以说明辛亥革命就已“失败”, 也不足以说明辛亥革命“搞错了”,似乎当时应该坚持搞君主立宪制,更不足以说明民权思想已经深入广大民众的心。
如果光拿辛亥革命前夕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同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前夕英、法两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相比,中国无疑还略胜一筹。不过,时代之于辛亥革命的要求已远非时代之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的要求可比。何况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君主专制传统与纲常教育传统的国家,还是一个既庞大又落后的承受着“无形之瓜分”的孱弱国家,革命的难度就不是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可以望其项背。
对于孙中山这一代民主革命先驱来说,既要根治清皇朝的专制与腐败,又要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权模式来改造中国,以民权代替君权,其本身有一定的难度。前者要求革命者有足够的力量取而代之,后者则要求包括革命者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体人民具备相应的政治素质,匆匆来临的辛亥革命却并不具备这两个条件。
三
辛亥革命的结果,一是政治多元化;一是社会发展的无序化。政治多元化不失为在专制主义的废墟上培养独立人格、训练参政能力、调动民众的政治积极性与创造性的重要途径,而且还是民权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社会发展的无序化却又削弱着政治多元化的正面效应和整体效应,并且可能使备受欺凌的中华民族在对待西方列强新的侵略时显得软弱无力,这是一对矛盾。
这对矛盾不是在民国初年的政局中才产生的,而是在清末预备立宪时早就存在了。就克服国家危机、抵制外来侵略而言,应当加强统治者的权力和权威,高扬大范围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但这有可能给专制独裁者以可乘之机。就顺应政治现代化的世界潮流、提高民族政治素质与竞争力、尽快缩小中外差距而言,则应当削弱和下放中央集权,尽可能为地方和民众提供参政议政的机会,发挥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行民权政治,但这又有可能为地方主义者与山头主义者开方便之门。无论是末日皇朝,还是新上任的民国当权者,他们都不曾找到一个两全之策来。显然,以慈禧为首的当权者在19世纪每每扼杀改革生机所留下的那些历史欠债,还需要后人为之不断地连本带息偿还。
是先加强政府的权威好,还是偏重于加强人民的民主权利好,或是反其道而行之,这已不是学理上的问题,而是进退两难的具体操作问题,倘若先加强人民的民主权利,偏重于民权建设,则势必受到国民素质条件的束缚,导致社会无序化;如果是先加强政府权威,偏重于中央集权,则无论是在满汉矛盾制约下的晚清皇朝,还是在举国上下尚在欢庆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胜利、人民刚得到一连串甜蜜的政治承诺的民国时期,都只意味着政治冒险,人民将不会答应。“皇族内阁”和袁世凯“洪宪”帝制的相继惨败已明白无误地宣示了这一点。
清皇朝拒绝提前召开国会,君宪请愿运动以“皇族内阁”的出笼而中断和流产,是否可以断定梁启超等人提出君主立宪方案一开始就不切实际,君宪请愿运动一开始就搞错了或者不该搞,纯属徒劳?正确的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因为历史人物不尽是算命先生或预言家,即使是算命先生或预言家,也未必能算准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及其归宿〔9〕。 民国成立后,武人专制盛行,军阀混战,社会动荡,能否由此断言民主立宪制不适合中国国情、君主立宪制优于民主立宪制?我看也不能这么说。且不论清朝统治者被迫上了预备立宪这条船之后是如何内外交困和丑态百出;也不论满汉矛盾制约下的孙中山等一代反清革命战士和梁启超等真诚的君宪论者是如何容不下“皇族内阁”的拙劣表演,但我们至今确实不曾看到实实在在的君主立宪制是什么样子,它究竟能给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带来多少优于民主立宪制的实际好处,我们更不得而知了。谁能保证一个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中国就不出现武人专政和国家分裂的局面?谁能保证“皇族内阁”之后的君主立宪制必定是货真价实和“包你满意”?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君主制的两个缺点:一是国王的专制利益要求人民处于孱弱和悲惨的境地,推行愚民政策和剥民政策,以便确保人民无力反抗君主;二是政府中的显要位置都被一些擅长阴谋诡计的小人轻易地获取。完全可以设想,倘若在实行民主立宪制都还留有专制主义尾巴的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那么,传统的君主制所包含的这两个弊端未必能得到有效的清除,中国的君宪制与其说可以类似于英国式的君宪制或日本式的君宪制,还不如说更容易接近传统的君主专制,尤其是在满汉矛盾制约下的清皇朝更是如此。林语堂曾经号召国人:“现代人已非思想界的权威所能支配,不但是已死的圣人,不能支配我们,就是新起的任何思想家,也不能霸统思想界,造出清一色的局面。自然我们还有精神界的领袖,但是这些领袖的地位,已非如往昔的圣贤,其得我们的信从与否,其权全操在我们。过去取之权,都在我们思想界的平民的手中,而我们所赖以行去取抉择的权,又全在我们的批评能力。”〔10〕而“抉择的权”也罢,“批评能力”也罢,也只有在帝制推翻之后的民国才不致于成为空谈。
有位台北学者在批评梁启超等人的民权思想时认为:“当时的积极知识分子集矢于‘满族专制’。好像只要把‘满族专制’推翻了,国就可以强起来,一切问题就可以解决。提倡民主是好的。因为民主在原则上是为公的。可是,我想不出民主与国强有何必然的关联。如果我们要断定民主与国强有何必然的关联,那末就得证明民主是国强的充足而又必要的条件(Sufficient-necessary condition)。 如果我们要证明民主是国强的充足而又必要的条件,那末就得证明凡属强国都是民主的而且凡属民主的都是强国。事实不是这样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俄国、德国和日本都不是民主国,可是都比中国强。而且‘满族专制’真的推翻了,中国果强起来乎?决定一个国家的强弱,因素很多,政体不过是一个方面而已。显见梁启超的这项见解是不通的。”〔11〕
这段话其实提出了一个疑问:既然中国在推翻“满族专制”之后还是不见强大起来,为什么当初一定要推翻满族专制呢?对此,不妨借同时被这位学者引用过的那个柯瑞克斯人(KoriaKs )对异乡来客所提出的反问来请教一下这位学者:“如果你在家乡有那么多好处,那么为什么费这么多的事来到我们这里?”〔12〕
应当说,推翻帝制之后的中国不曾迅速富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如中国欲期富强必须具备多种条件一样。“满族专制”推翻之后,中国没有强大起来,并不能反证保留“满族专制”的合理性,不能说推翻清皇朝毫无必要,如同晚清洋务运动不曾使国家臻于富强,并不等于说当时的中国不搞洋务运动就好,中国按原地踏步就能富强。此其一。其二,即使是不曾迅速富强的中华民国也总比专制皇朝要进步,要有生气得多,总比前途未卜的“预备立宪”要实在得多。其三,尽管我们不能说凡是强国都推行民主制,但欲期中国富强,除了首先从根本上解决国内满汉民族矛盾、推翻腐朽皇朝、实行民权政治之外,实在很难找到其他更好的办法来。至于民国初年建设得不理想,确系事实,但也不必过于担心,因为“大抵开基之人未免草创,全属继志之士为之弥缝。”〔13〕
其实,上述学者所批评的梁启超的思想比起孙中山等人的思想来还不算最激进的。新生的中华民国主要属于孙中山一代民主革命先驱的杰作,自认“流质”多变的梁启超主要是以旁敲侧击的“催生者”的角色载入史册,他所期待的君主立宪制便连同清皇朝的“预备立宪”被举国上下的反满民族革命洪流所湮没,同反满民族革命接踵而来的以民主立宪为核心的政治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冷静地分析20世纪第一个10年那段风云变幻和惊心动魄的历史场面,不难发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有一个重要的失误,那就是把政治革命看得过于简单和轻松,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推翻清朝,端掉皇位,人民从君主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国家就会迅速富强,人民就会幸福美满。其实不尽然。
“娜拉走后怎样?”这是挪威戏剧家亨里克·易卜生(1828—1906年)留给地球村的居民不尽思索的话题。钱钟书早年撰写的一篇书评中写到:“‘革命尚未成功’,乃需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了,便要人家尊命。这不仅文学使然,一切社会上政治上的革命,亦何独不然。所以我常想,革命在事业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14〕
我们也许不难从钱钟书的评论中挑出许多宏观思辨性论著所常见的那类普泛化和绝对化的毛病,若以钱氏此言质之晚清政治革命,质疑乎?认同乎?
在稍示迟钝与茫然的思绪中, 作者忽然想起恩格斯在《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说过的一段话,谨作本文的结尾:
“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却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起而掌握国家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状态下能够并且应该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是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是安然容忍这个变革。但是,如果把每一个别场合的具体内容撇开不谈,那么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态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15〕
注:
〔1〕原载《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
〔2〕厄本与汤因比对话时所言, 《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页。
〔3〕〔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22卷595—59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1页。有趣的是, 清人孙宝瑄虽然不懂马克思主义,但他通过阅读西方历史书籍,也能领会出几分奥妙来。他说:“今人动曰民权民权,不知有商权而后有民权。商权者,民权之基也。吾读欧洲史,知中古世商业市府之发达,皆因十字军之役,王侯贵族借饷商人,许之特权以为报酬,而商人因之构结团体,保卫公利,脱封建诸侯之压力,渐渐干涉政权,遂为今日立宪之根基。是何故耶?盖天下万事倚财为命,财之权握于商人,国家求财于商人,商人不能不求权于国家,国家以权易财,商家以财易权。是故,有财权不患无政权矣。今我国士夫高睨大谈,不营实业,不求商权,不握财权,而妄希民权,是未弹而求炙雀,未卵而求时夜也。不其难乎!”他还说:“变法之本在立宪,立宪之本在财赋,财赋之本在实业,不易之论也。故日本维新之际,士族皆改业工商。今我士夫稍开明者,动好为大言,谈民权自由,不务实业,有愧多矣。”(《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99、729页。)
〔5〕《列宁全集》第9卷,第353页。
〔6〕《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 第70页。赵中孚先生的研究成果也证明:“传统社会从事现代化的改革,是一条痛苦而漫长的路途。若干社会学和政治学家,都肯定这是无可避免的现象。因为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对新事物的对抗力量无比巨大;其破坏——重建——整合的过程也相当复杂。与新兴国家的改革有基本的差异。中国是个典型的传统社会,自然不能免于困扰。事实上,这种困扰可能还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赵中孚:《近代中国军事因革与现代化运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12期,1971年版,第56页)
〔7〕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181页。
〔8〕在有关的学术论著里, 张亦工先生《民国初年的政治结构和文化初探》一文堪称颇有学术深度和理性思辨的一篇。参见《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
〔9〕1903年,有个既精通数学, 又“能推测未来事”的人对孙宝瑄说,“尚有五十年国祚”(《忘山庐日记》上册,第718 页)。此人所算就很不灵验,同后来的结果相距太远。倒是自称“能静居士”的曾国藩之幕客赵烈文猜得很准。他在1867年7月21 日(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私下对曾国藩说:“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详见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58—159页)事情凑巧得很,此言过后44年,清皇朝即遭灭顶之灾。梁启超在1910年的推断也比孙宝瑄的那位朋友所卜的要准确得多。他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一文中断定:“现今之政治组织循而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所必无之事也。”(《国风报》第1年第17期)
〔10〕林语堂:《论现代批评的职务》,《大荒集》
〔11〕〔12〕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289、123页
〔13〕郑樵《通志·总序》
〔14〕转引自《读书》1995年第6期,第76页。 林语堂则提出:“革命的人革命,反革命的人反革命,大家不要投机,观察风势,中国自会进步起来。”(《谈牛津》,《论语》半月刊第9期,1933年1月)此言不免有些漏洞,社会的发展自然以历史潮流为主体,以历史潮流为依归的“观察风势”之举未必都是坏事,它同某些政客们为个人私利成天见风使舵变化莫测的小人行为当有所区别。而有关价值判断必须是非分明而不是模棱两可。但就学术研究而言,林氏之论并非毫无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