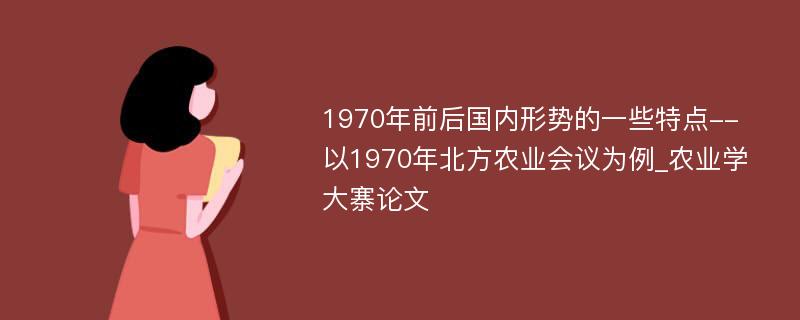
1970年前后国内形势的几个特点——以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方地区论文,几个论文,为例论文,形势论文,年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52;D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2)-05-0044-08
与“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三年相比,1970年虽然未曾出现“天下大乱”、“全面内战”之类的动荡、激烈局面,但由于前一段诸多矛盾的遗留及一些新任务、新背景的出现,因而具有更多的内涵,成为一种周期的起点。本文以1970年8至10月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为例进行考察、分析,以期从中发现“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规律性的内容及其在1970年的表现。
1
1970年前后,中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形势和任务。这一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非但没有像预计地那样“胜利结束”,还继续引发新的动荡,一则是因为国际、国内形势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和变数。
1969年中国共产党九大之后,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注:1970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表示,“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在1969年结束了。),他希望通过全面的“斗、批、改”运动(注:“斗、批、改”运动包括了整党建党、整团建团、清理阶级队伍、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商业革命、医疗卫生革命、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下放、精简机构等名目繁多的内容,并具有相当的随意性(例如清理阶级队伍到1970年初又发展为“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等等)。),落实政策,加强团结,恢复秩序,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并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逻辑发展经济,以胜利地结束“文化大革命”。“斗、批、改”运动内容庞杂,随意性大。就其本意来说,虽然有结束动乱、制止无政府主义的意向,但另一面却是要把一整套“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普及、推广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这又引发了新的动荡。
1969年初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更趋紧张。面对苏联强大的军事压力,根据毛泽东、党中央的决策,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建国以来规模空前的战备高潮。1969年下半年至1970年,国内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等各方面林林总总诸多运动、工作,都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展开、进行的。由于国内局势逐渐趋于稳定,特别是鉴于几年内国际形势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毛泽东、党中央正在酝酿对我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从1970年初开始,中美双方通过各种渠道加快了相互接近的步伐。
基于对党的重建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的认识,毛泽东把政府重建的工作提上日程。根据他的指示,从1970年初起,中央政治局开始筹备召开四届人大和讨论修改宪法。
“抓革命,促生产”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口号,是毛泽东现代化理论的基石。毛泽东希望并相信,在革命的高潮之后,必然会出现一个经济建设的高潮,正如在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必然会出现1958年的“大跃进”一样。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又由于人们在大乱之后要求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的迫切愿望,由于对战备形势过于严重的估计,在更深的层次上,由于计划经济所固有的“投资饥渴症”,一场新的以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为特征的新冒进开始了。1970年1月1日“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说:“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发展,一个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出现。”1970年3月,鞍钢率先提出五年内钢产量翻一番的口号,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并迅速在全国推广。与此同时,各省、市、自治区召开的计划会议和各部门的专业会议纷纷提出各自生产短期内“翻番”、大幅“跃进”的口号。这是在“左”的大背景下,经济上“左”的痼疾的再现。
“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过去了,但它却并没像人们预期地那样胜利结束。它所留下的如山之积的矛盾仍时时困扰着人们,引发出新的动乱和危机。在政治生活中,1970年初相继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运动等,再次造成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局面,伤害了大批干部、群众。在运动第一阶段攫取了巨大权力的林彪集团并没有因此满足,他们与江青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在筹备四届人大的过程中,两个阴谋集团的争夺已经白热化、表面化。在1970年8月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两个集团的摊牌以林彪、陈伯达的失利告终。同年10月,以林立果为头目的“调研小组”更名为“联合舰队”,加快了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步伐。
在经济生活领域里,新“跃进”虽然不会像“全面内战”那样使人感到恐惧,但也立即引发了经济上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注:这就是经济史上常讲的“三个突破”: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从一个特定角度突显了“文化大革命”的荒谬。另一方面,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高潮,不能不正视经济建设无形但却又是力量强大的规律,不能不对“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打倒一切”的极端做法和宣传进行一些调整、纠正。
自1970年始,报刊上的宣传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例如:“要用革命统帅生产,但不能用革命代替生产,下功夫抓生产,不一定是单纯业务观点”,“‘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是错误的”(注:《红旗》1970年第1期。);“要坚持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社会主义原则,把它同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区分开来”(注:《红旗》1970年第2期。);当前有人借口批判“生产第一”反对抓革命、促生产,借口批判“利润挂帅”反对企业经济核算,借口批判“管、卡、压、罚”反对合理的规章制度,借口批判“奴隶主义”反对遵守无产阶级革命纪律,这些都是错误的,等等(注:《人民日报》1970年4月18日。)。这些言论都与1967、1968年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蛮横批判形成鲜明对比。总之,前三年被批判、否定的许多东西,现在都被慢慢恢复。江青等人称其为“复旧”,自有其道理。
但是,这些初步的努力显然无法愈合“天下大乱”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巨大创伤。生产高潮初起,一系列严重事故的出现从客观上表明:“文化大革命”与现代化大生产是格格不入的。党中央在1970年12月发出的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中指出:今年以来,特别是下半年以来,有些地方不断发生重大事故。如煤矿冒顶、透水、瓦斯爆炸,车间、仓库失火,火车翻车、撞车,船舶碰撞、沉没,火药爆炸,设备损坏等,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在政治上带来不良影响。造成伤亡事故增加的主要原因为:一些单位和部门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严重,废除了原有必要的安全制度,劳动纪律松弛,各行其是,在生产中违章作业;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有关领导怕字当头,不敢抓安全生产、官僚主义和严重失职,等等。(注:参见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1967-198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3页。)
为整顿纪律,恢复秩序,落实政策,批判极左思潮并进行生产动员,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委召开了一系列专业会议(注:例如,从1969年11月至1971年8月,就先后召开了全国食糖及糖料生产会议、全国棉花生产会议等20多个专业会议。)。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各种专业会议之多、之密集,为新中国建设史上所少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会议在不同程度上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肆虐横行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强调落实政策和恢复、发展生产,提出了近期或中期生产、工作的规划,扭转了一些行业生产连续下滑的局面,揭开了1972年整顿的序幕。
总之,1970年间,大致有这样几类问题或任务摆在人们面前:一是按照运动的既定方针设置的任务,如“斗、批、改”,掀起新的生产高潮,等等;二是“文化大革命”自身性质所必然带来的“后遗症”,如阴谋集团的崛起及其相互争夺,“一打三反”之类继续造成严重扩大化后果的运动,以及经济上的盲目跃进;三是整个社会为了正常运行,迫切需要对“文革”的种种狂暴、乖谬的观念、做法进行限制或调整。这种社会内在的需要表现在人们行为层面上,便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纠正和抵制“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的努力,开始进入到比较系统地恢复党在“文革”之前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层面。后两者虽不是事先所设计、安排的,但却像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那样,是“文革”发展中的题中应有之义。“文革”没有如愿地在1970年“胜利结束”,相反,它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后果从反面把系统否定它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1969年底,张春桥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他说:一次革命高潮过去后,必定有唯生产力论思潮抬头;苏联在30年代,就是犯的这个错误;现在九大开过了,同样也面临着当年苏联的这个局面,有个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在张春桥看来,党内外存在着强大的“右倾翻案”势力,他甚至因此而感到悲观。张春桥从反面说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和贯彻的,同时,它又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历史的特点和要求。
2
与70年代初召开的一系列专业会议一样,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也面临着一些紧迫、困难的任务。经过60年代初的调整,我国的农业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大多也只是略高于1957年的水平,而北方地区农业落后、南粮北调的局面较1957年反而有所发展。1966年3月,中央、国务院决定把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北京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改变我国农业落后面貌、实现农业稳产高产、改变南粮北调局面的主攻方向。为此,专门成立了由周恩来担任组长的北方8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小组。但时隔两个月,“文化大革命”便爆发了。
“文化大革命”对农业的冲击和破坏,除了打倒“走资派”及无政府主义等使农村各级党政机关陷于瘫痪或半瘫痪,大批各级农业领导干部和农村基层干部由于受到迫害和打击无法实施领导外,更重要的,是“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对调整时期制定的、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农村经济政策和规章制度的批判和否定。
“文化大革命”最初是高举反“包产到户”的大旗走上历史舞台的(注:1965年11月,作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实际上借“退田”明白无误地把矛头指向了60年代初的“包产到户”。)。在1967年至1968年“大批判”高潮中,对“包产到户”、“责任田”、“三自一包”等讨伐批判的文章铺天盖地,不计其数。但是,这些蛮横的批判还未敢把矛头全面、直接指向《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以下简称《农业六十条》)等调整时期确立的一些卓有成效的农村基本政策。对《农业六十条》的否定是通过另一种途径——对带有浓厚极左色彩的大寨经验的狂热宣传和广泛推广来实现的。
从经济政策的角度看,当时的大寨经验,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有两项,一是改变基本核算单位,一是把劳动定额制改为大寨记分法。1967年上半年,昔阳县开始普遍推广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做法,并把它作为学习大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1968年年底,该县宣布全县实现了向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注: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1967-1984)》,第144页)这种“穷过渡”的做法在全国宣传和推广后,部分地区刮起了一股扩社并队的“穷过渡”风。据山西、河北、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1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统计,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调整后,仍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的仅占大队总数的5%,至1970年却上升到14%。其中,山西省的大多数生产队已合并为大队所有制,浙江省有1/4的社队实行了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注:参见邓力群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260页。)
大寨经验的另一主要内容,是以“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为特点的大寨记分法。1967年9月和1968年1月,农业部在大寨大队召开两次“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向全国推广大寨记分法。现场会纪要称: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是在批判定额包工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指出了管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方向和道路,是适合中国农村的好办法,是防止无产阶级江山变颜色的根本问题;各地要彻底批判以“工分挂帅”、“物质刺激”为核心的修正主义管理制度,积极热情地、有计划地推行大寨管理经验。(注:农业部:《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议纪要》,1968年4月。)当时的《人民日报》称“这套制度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用毛泽东思想挂帅,以打倒资产阶级‘私’字,树立无产阶级‘公’字的办法,解决了社会主义集体公有制经济和人们头脑里的‘私’字之间的矛盾,大大促进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是经济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注:《人民日报》1968年8月26日。);而在定额管理,按件计工的劳动管理制度下,“人民公社内部就会产生两极分化”。此外,大寨大队除实行大寨式工分外,还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按需自报”的口粮、蔬菜等实物分配等制度(注:《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改革不合理的管理制度》,《人民日报》1968年11月24日。)。随着全国农村学大寨运动深入开展,大寨记分法在许多地区推广开来。至1968年,山西、山东、黑龙江、上海、天津、广东、广西、湖南等省、市、自治区,实行大寨劳动管理制度的社队已占全部社队的半数以上(注:《人民日报》1968年9月。)。
“文化大革命”前三年对大寨经验的这种宣传、推广(注:当时所宣传和推广的大寨经验还有其他一些内容,如狠抓阶级斗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减少以至禁绝集贸市场、“以粮为纲”、收自留地等等。),实际上就是对包括《农业六十条》在内的一系列60年代初调整成果的否定,是在一定程度上向1958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回归。仅仅从这样一个侧面,不难看出“文革”与60年代调整及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不难看出“文革”发生的原因及其特定内容。
大寨经验的宣传和推广,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破坏了党当时行之有效的农村基本政策,严重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不能不受到广大干部、农民的抵制。1967年2月10日,国务院农林口各部门和北京郊区的群众组织向全国农业战线发出的紧急建议中提出,农村各项政策,凡中央没有作新规定的,不得任意更动,需要整改的问题,原则上放在运动后期处理。同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要求:农村各项政策,凡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没有做出新规定的,一律按原来的执行(注:《动员起来,打好三秋这一仗》,《人民日报》社论,1967年9月16日。)。同年12月4日,中央重申:人民公社现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关于自留地的制度,一般不要变动,也不要搞捐献(注: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967年12月4日。)。1969年2月《人民日报》社论再次强调:“对运动中新出现的政策性的问题,特别是牵涉到所有制的问题,要谨慎对待,请示报告。”在农村,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以分散的、消极的形式抵制“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宣传大寨经验与要求维持原有规定的实质,在于否定还是坚持《农业六十条》。尽管后者的声音微弱得不成比例,但它的存在毕竟对极左思潮形成了某种牵制。
“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力发展。1967至1969年间,我国农业总产值、粮食总产量、棉花总产量、生猪饲养量、水产品总量等都出现了下降和停滞的局面(注:全国农业总产值,1966年至1969年三年平均为642.5亿元,较之1966年的640.9亿元基本上没有增长。其中,1967年为651.3亿元,仅比1966年增长1.6%;1968年下降为634.5亿元,1969年为641.8亿元。全国粮食总产量:1967年为21782万吨,比1966年略有增产;1968年减少为20906万吨,比1966年下降2.3%;1969年略有上升,达到21097万吨,但低于1966年21400万吨的水平。参见邓力群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第268页。)。这种令人不安的局面在北方地区尤甚。据1970年统计,1957年北方地区14个省、市、自治区中,调出粮食的有内蒙、陕西、甘肃、宁夏和安徽淮北地区5个单位,调入的单位9个,调出调入相抵,北方地区净调入60多亿斤。“大跃进”后,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连续下滑。60年代上半期虽略有恢复,但仍未达到1957年的水平。至1969年,调出粮食的只有安徽的淮北地区,调入的单位10个,基本自给的3个。出入相抵,共调入近70亿斤,高于1957年调入水平。如此严峻的农业形势,也是召开北方农业会议的重要背景,正如余秋里在会议中所说:这次会议要解决南粮北调问题,这是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注:余秋里在参加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1970年9月13日。)。
3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于1970年8月25日在昔阳召开,8月31日转到北京,10月5日结束。会议第一阶段是在大寨大队和昔阳县参观;第二阶段(9月1日至13日)为“开展革命大批判,进行路线分析,总结和交流各地学大寨的经验”,主要解决学大寨学什么和怎么展开的问题;第三阶段(9月14日至10月5日)分组讨论实现《纲要》的措施和农村各项政策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正在江西庐山举行(8月23日至9月6日)。
参加会议的代表共1259人。其中,北方14个省、市、自治区代表940人,其余为其他省、市、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各部委代表。在29个省、市、自治区988位代表中,省、市、自治区机关代表167人,地区机关代表159人,县机关代表373人,人民公社代表50人,大队、生产队代表164人,支农各行业代表75人。
这次会议典型地反映出当时形势的特点:一方面,与“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相比,“左”的错误与极左思潮虽然失去了狂热的势头,但仍然十分广泛、严重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以及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的迫切需要,纠正错误,落实政策的呼声也逐渐高涨起来。这个特点反映在会议上,是以9月14日会议转入第三阶段为标志,会议实际上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
在会议的第一、二阶段的参观和“路线分析”、“大批判”中,代表们的发言照例大多是当时一些批判“三自一包”等“资本主义倾向”的套话。但在会议进入第三阶段,开始讨论实现《纲要》的措施和农村各项政策问题时,各种套话、空话、假话顿时少了许多,要求坚持《农业六十条》、落实政策的意见成为主流。代表们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是同当前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基本上相适应的,应稳定不变,要改大队核算,需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按《农业六十条》规定,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自留树、自留畜;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既要反对“工分挂帅”,也要反对“死分死记”、不问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吃饭不要钱”的平均主义做法;要严格控制非生产性用工和开支;在大力发展集体养猪的同时,继续鼓励社员个人养猪;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给生产队一点自主权,等等。总之,在这些事关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政策问题上,讨论的结果实际上坚持了《农业六十条》的原则,明显地不同于当时大红大紫的大寨经验,而这又都是在“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下进行的。
讨论的结果竟如此迥异于大寨经验,这正说明“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的危害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纠正这些错误的条件正在成熟。同时,一个重要背景的影响也是不应忽视的。1970年9月6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基本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注:1970年9月12日(即北方地区农业会议转入第三阶段的前一天)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广泛组织讨论《宪法草案》。)。《宪法草案》第一章《总纲》第七条规定中,重申了《农业六十条》有关基本原则。这些规定起码表明,在中央领导层内部,在农业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当时反对极左思潮的力量已经占了上风。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讨论《宪法草案》过程中,改变基本核算单位和收自留地之风不得不一度有所收敛。而这正是当时全国各方面形势的一个缩影。
9月23日,根据会议精神,《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农业学大寨》。与会议一样,这篇社论也表现出明显不同的两个部分。从字面上看,社论中充斥着“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之类的语言和对大寨的种种赞美,以及对“三自一包”等的批判。但是,在回答“学大寨学什么”这个“当前深入开展学大寨群众运动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时,社论提出: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是大寨经验中第一位的东西,学大寨首先要学这一条。至于经营管理、生产技术方面的一些具体办法,那是第二位的东西,一定要按照各地的实际情况办事。学大寨,不学第一位的东西,只学第二位的东西,不学根本,只学表面,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别人的某些具体做法,就有可能“学歪了”。只有正确地解决学什么的问题,才能排除右的和“左”的干扰,落实毛主席制定的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保证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社论机智地将大寨的“根本经验”与“具体办法”加以区分,并将后者定位于“第二位”,实际上降低了大寨“大队核算”及“记政治工分”的普遍意义,给抵制极左思潮留下了相当空间。社论批评“生搬硬套”的错误,指出存在“左”的干扰,并提出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及保证学大寨的正确方向的任务,给深受大寨“左”的经验压制的广大社员、干部以抵制错误的根据和勇气。
1970年10月4日,周恩来接见了参加北方农业会议以及商业、外贸等专业会议的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到工农业生产情况时,他说,现在工农业虽然发展了,但是按人口比例计算,比日本、西德等西方国家还差得远;要吸取1958年“大跃进”的经验,要注意平衡;在农村中,平调劳动力不给报酬,社员负担很重;有关政策问题要讨论,要留有余地。他还强调了1970年间他在各次专业会议上反复说到的一个问题:协作是社会主义协作,风格是共产主义风格,不要搞“一平二调”(注: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98页。)。周恩来的这些话,矛头直指当时包括农业在内的各领域中泛滥的极左思潮,在代表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会议期间,在国务院业务组领导主持下,各省、市、自治区代表及一机部代表,就工业支援农业,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问题,进行了多次座谈,并形成了《关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问题的座谈纪要》。虽然座谈会和《纪要》难以避免地带有当时急躁冒进的色彩,但它们对1970年后我国“五小”工业的跃进式发展还是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0月5日,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结束,同日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12月1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如同《农业学大寨》社论一样,《报告》把大寨的“根本经验”与经营管理中的一些具体办法加以区分,实际上贬低了“大队核算”一类“左”的错误。在谈及农村政策时,《报告》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农业六十条》的地位及意义,强调“必须继续贯彻执行”,要求反对平均主义,“切不可重犯穷富拉平的‘一平二调’错误”,等等。
《报告》引用代表们的发言指出:“前些时候,有少数地方不顾条件,违反多数群众的意愿,刮过一点任意改变基本核算单位、收自留地的风。面不算大,但波动不小,反映了某些领导干部有点形‘左’实右的思想苗头,很有必要提醒各级领导同志充分注意。”“我们一定要加强党的政策观念,克服某些地方存在着的无组织无纪律的倾向。”《报告》进一步批评说:“目前,有一些领导干部,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对待革命和生产、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有些人“不是用革命带动生产,用一好带动三好,而是用革命代替生产,用一好代替三好”。实际上,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批评已在一定程度上把矛头指向了“文化大革命”本身,它是当时形势发展迫切需要的产物。
以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为契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内容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其“左”的内容被淡化、形式化,而纠“左”和落实政策的内容却在“左”的外表中发展起来。这种变化在当时各领域、各行业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构成了1970年的一个重要特点。
4
如果说,在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上,已经明显地出现了与“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的意见,那么,在会后,这种意见不仅进一步发展成为对极左思潮的明确批判,而且比较普遍地成为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自觉行动。这样一个迅速而又广泛的变化得益于两方面的重要背景:一个是经济方面的,即当时的工农业生产高潮的客观需要;一个是政治方面的,也可能是更重要的方面。1970年9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批陈(即陈伯达)整风”运动又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而陈伯达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煽动极左思潮的重要人物之一;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批判极左思潮、落实政策在1972年达到高潮,这无疑推动着北方农业会议反“左”内容的进一步发展。
北方农业会议之后至1971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大多数省、市、自治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传达贯彻活动。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纠“左”力度不断加大。1971年初全国计划会议再次强调:应积极发展多种经营,要划清多种经营、正当家庭副业同投机倒把、弃农经商的界线,不可不加分析地把多种经营当做资本主义倾向批判;对所有制问题应持慎重态度,要解决好前一阶段某些地区改变核算单位和收自留地的遗留问题;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防止平均主义;反对高指标、高征购和说假话,不搞形式主义,等等(注:《1971年计划会议第3期综合简报》,1971年2月14日。)。
根据国务院指示,农林部于1970年10、11月向山西、安徽、天津、湖北、河北、江苏、四川、新疆等省、市、自治区派出调查组,了解、检查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情况。1971年4月,农林部给中央的《关于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情况报告》指出: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之后,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农村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明确了学大寨要学根本,而刮大队核算风和收自留地风正是学大寨没学到根本的表现;广大农村干部提高了执行党的政策的自觉性,前一时期出现的并队、改变基本核算单位和收自留地之风,已基本刹住;农田基本建设大发展,地方办“五小”工业的积极性大为提高,等等。《报告》还提出当前需要着重解决好几个问题:对那些仍未解决前一阶段搞并队、收自留地、搞大队核算的地区,要继续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注意解决新形势下出现的诸如抽调生产队劳动力过多,只抓粮食生产不抓多种经营、平调生产队劳力和物资,社队非生产人员和开支增加,加重社员负担使社员增产不增收、收入下降等问题。
在贯彻执行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尽管还充满着“掀起农业学大寨新高潮”、“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狠批‘三自一包’”等等语言和口号,但其落脚点往往却都在“认真执行党对农村的各项政策”,“认真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中关于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减轻农民负担”、“认真搞好年终分配”等方面,检讨了“收自留地”、“取消劳动定额”的错误,有的甚至说“并队”、“搞大队核算”是“走到邪路上去了”。
随着批判极左思潮的力度逐渐加大,197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普遍存在的分配不兑现、“分净吃光”、集体增产个人不增收、超支户多、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的状况,重申《农业六十条》仍然有效,要求各地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要生搬硬套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强调农业必须全面发展,不能把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做资本主义去批判。
1972年上半年,农业部派出的调查组纷纷反映:虽然还存在不少问题,但几年来,特别是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报告和中央分配指示以来,“党的农村政策落实情况是越来越好”;绝大部分大队长以上的主要干部落实了政策,“干部敢抓生产了”;“现在,公开主张‘割私有制尾巴’的人很少了”;“大家赞成‘大定额’(管理制)”,刹住了“四大改”(注:指搞大队核算、收自留地、吃粮不要钱、取消养猪奖励等。)之风;多数地方都把1967至1968年盛行的“政治工分”、“并队”、“收自留地”、“搞大队核算”当做“林彪集团形‘左’实右”的“妖风”进行批判,口粮分配、养猪积肥等政策落实了,“社员的家庭副业恢复了”,“社队企业发展了”,等等。
综合各地调查结果,农业部于当年8月分别写出了《关于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调查报告》和《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政策落实情况的调查报告》。两个报告反映了1972年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所取得的成绩,更鲜明地提出了纠“左”的要求和任务。报告反映:1967年后,“由于林彪反党集团煽动极左思潮,造成干部不敢抓生产”,粮棉生产下降。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和农村人民公社分配指示贯彻以来,“注意了划清政策的是非界限,抵制了林彪改变基本核算单位、收自留地的妖风,不断地抓政策落实工作,保护了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政策落实工作抓得比较好的地方,生产“单打一”的状况有了改变;计酬上的平均主义得到一定的克服;“一平二调”和加重社员负担的现象开始注意纠正;落实了“粮食一定五年”的政策,一般地做到了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报告同时指出,“政策落实情况很不平衡,还存在不少问题”。如“一平二调”、不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劳动计酬中的平均主义倾向、对社员家庭副业干涉过多、前一时期任意改变基本核算单位、收自留地的问题仍未妥善处理;也有些地方对落实政策中出现的右的苗头注意不够,对资本主义倾向批判不力,等等。在分析政策不能很快落实的原因时,报告指出,主要是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一部分领导干部宁“左”勿右;有的怕字当头,一见“包”、“定”、“奖”的字眼就极力回避,等等。报告还就生产队所有制、自主权、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以及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问题,不点名地直接批评了大寨经验。
1967年至1968年间,在“农业学大寨”的旗号下,“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一度泛滥。1970年以来,特别是在北方农业会议之后,“农业学大寨”的内容实际上已发生了重要的转换。从各个方面落实《农业六十条》已成为运动的主流,大寨大队那些“左”的和极左的观念和做法,已在相当的程度上和范围内受到抵制和削弱,这一健康的发展趋势在1972年达到高潮。农业方面的这一深刻变化,是当时全国批判极左思潮力量发展的产物,也是各方面、各领域变化的一个缩影。这正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
但是,在还没有可能从全局上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情况下,这种纠“左”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这不仅表现在其内容的不彻底,更表现在它发展的高潮只能引发新一轮的“反右倾”。1972年底周恩来纠“左”受阻、1973年江青等又提出“反右倾”后,1970年北方农业会议以来纠“左”的各种努力受到越来越尖锐的批判和攻击。大寨那些“左”的做法又被宣传为反击“右倾复辟”的典型。从这时起,“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左”的内容又迅速膨胀,自留地、集贸市场、劳动定额、社员养猪等又成为批判或限制的对象,农业生产再度出现下降和停滞的局面。但是,对于饱受“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之苦、并从1970年以来从落实政策中得到切实利益的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来说,要他们重复1967年、1968年的做法已经很困难了。1973年下半年至1974年上半年间,尽管“反右倾”之风恃政治高压不绝于耳,但却基本上是作为一种外在的、不得人心的东西受到农民和干部的抵制起码是冷落。所以,当1975年和1977年大寨大队领导人正式向中央提出向大队所有制过渡及取消自留地等问题时,不论是在高层还是在基层都没引起什么反响。
5
通过对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分析,对1970年的形势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1970年间,“文化大革命”非但未能像预想地那样“胜利结束”,相反,它在政治上、经济上所造成的恶果更深入地暴露,因而从反面把系统否定它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二)此时,“文化大革命”明显地遇到了来自两方面的严重挑战:一是“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全面内战”所遗留的大量严重社会问题使整个社会难以安定,以及它引发的野心家、阴谋家的争夺正迅速激化;一是整个社会为了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所必然产生的恢复秩序、实现稳定、发展生产的需求,这种需求反映在人们的活动中,就是越来越自觉和强烈地纠正“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的努力,这在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召开、贯彻过程中比较典型地表现出来。
(三)正像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及当时其他一系列专业会议)从经济政策上宣布极左思潮的破产一样,林彪事件从政治上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这两个从现象上看似乎风马牛不相极的事情,却正是在深层的社会发展规律上密切地联系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又都在1970年间开始以比较完整的形态表现出来。
(四)因为有60年代初调整的基础,又由于“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种种极端行为使人们有可能比较明显地感觉到极左思潮的荒谬,所以,1970年只是处于初始阶段的种种纠“左”努力,从开始起就有了比1958年更高的起点。在随后产生的比较有利的外界条件中(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这种努力很快发展为1972年周恩来的整顿。这种努力的基本内容之一,就是维护和恢复60年代初调整的成果。
(五)但是,在仍然维持“文化大革命”的框架之下,纠“左”越是深入,也就越接近它的极限。发端于1970年的纠“左”努力,在1972年达到高潮。随之而来的便是旨在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1973年下半年至1974年的“反右倾”和“批林批孔”。之后,又有1975年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及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直至最终结束十年动乱。这一周期在一些方面重复了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相继出现了“大跃进”、纠“左”、反右倾及调整时的某些特点,而1970年则正处于一个周期的开端,与1960年前后有些类似。所不同的是,由于各种历史条件的成熟,这次纠“左”有了更高的起点,因而更接近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