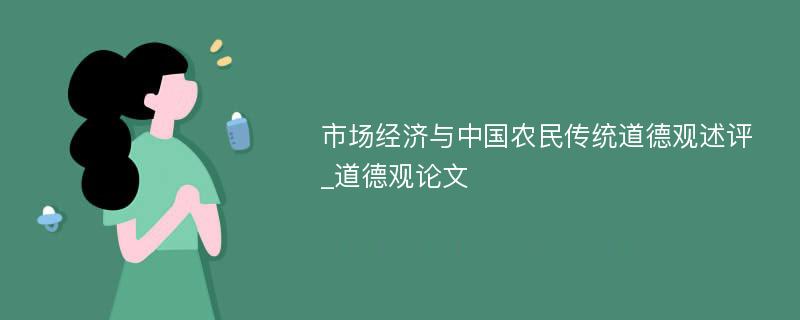
市场经济与中国农民传统道德观之检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论文,观之论文,中国农民论文,道德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社会学家W ·古德在其《家庭》一书中写道:“对于多数美国人来说,‘亲属’一词似乎有点古雅或带有乡土气息。‘亲属关系网’也使他们感到陌生。”〔1〕 但是,对于中国的农民、小生产者来说,“亲属”却是一个多么亲切、诱人的概念:“亲戚关系网”又是如此熟悉和重要,它是自己安身立命的基本依靠。基于血缘亲情和地缘人情面子而形成的浓厚的“圈子意识”,强烈地影响和支配着中国农民小生产者传统的道德价值取向,从而造成了农民小生产者道德标准和价值判断的二重化以及非中立性。
我们知道“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2 〕它基于人伦的原则而确立起来,是约束、规范每个家庭成员、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道德的功能,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其社会作用是确立和维护家庭、社会的生活秩序,保证家庭、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中国农民小生产者传统的道德观,是指小生产者在处理自己与家庭内部成员以及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所特有的善恶评价观念。由于小生产者在处理“圈内人”与“圈外人”的关系时所依据的道德价值观不同,因此,其善恶评价的标准也根本不同,甚至相互矛盾和根本对立。这种二重化的道德观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小生产者是以宗法血亲的“圈子”为核心由内外推、向外辐射,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人缘和地缘距离的远近、自他关系的尊卑等社会网络,形成和确立各种相应的人伦道德观,并通过民间风俗和传统习惯加以对象化。
这种“圈子意识”源于宗法亲情,并通过中国封建传统的宗法制度而得到强化。梁漱溟先生曾对此作过深入的分析。他写道:“中国的家族制度在其全部文化中所处地位之重要,及其根深蒂固,亦是世界闻名的。中国老话有国之本在家及积家而成国之说。”〔3 〕他还举出庐作孚先生对此观点的精深阐述:“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第二重的社会生活。这两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人每责备中国人只知有家庭,不知有社会;实则中国人除了家庭,没有社会。”〔4〕从梁漱溟、 庐作孚二先生的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农民小生产者的生活圈子有二:其一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圈子;其二是以地缘、邻缘为基础的亲戚、邻里、朋友圈子。这两个圈子里的人被小生产者看成是“圈内人”。除此之外,则被视作“圈外人”。在农民小生产者的心目中,“圈外人”既是指与自己没有直接血缘关系的人,也指与自己的家庭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等级身份相距甚远的人,例如,其他家族、村落的农民,尤其是地主、官员、士大夫等与自己地位反差强烈的人。当然,这种“圈内人”与“圈外人”的划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它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主体的实际需要而膨胀扩大,也可以收缩、递归和还原。以血缘和地缘为例,在小生产者看来:在一个家族里,核心家庭就是一个圈子;在一个村落里,家族就是一个圈子;出了村落到乡,村就构成一个圈子;出了乡到县,乡就构成一个圈子;出了县到省,县也就是一个圈子;出了省到全国,省也就是一个圈子;出了中国到国外,华人也就构成一个圈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与“圈内人”打交道时,封建统治阶级所确立的伦理道德规范(毋宁说是封建统治阶级从小生产者的道德心理要求中提升出来,又以“教化”的方式灌输到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中去而形成的道德规范),即儒家的纲常礼教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当然,小生产者在接受儒家的纲常礼教的“教化”时,也渗透着自己的特殊理解和选择。以儒家所宣扬的基本伦理道德规范“孝”为例,其提倡和宣扬的“孝道”有“显亲”、“娱亲”、“养亲”等几层内容。封建士大夫阶层特别重视的是“显亲”和“娱亲”。儒家经典就曾说过:“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而中国的农民小生产者对自己父母所尽的“孝道”,则不敢奢望“显亲”和“娱亲”,而只停留在“养亲”层面上,即让为自己辛苦了一辈子的父母在晚年吃口太平饭。
在与家庭内部成员打交道时,为了实现家庭内部和谐的价值目标,小生产者所遵循的主要道德规范是基于宗法血亲意识而确立起来的“孝”、“悌”。在与亲戚、邻里、朋友打交道时,为了维护邻里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小生产者所遵循的主要道德规范是基于人情面子意识而确立起来的“信”和“义”。
农村社会是直接群体,大家都是熟人,天天见面,和谐相处靠的是人情面子。所谓“面子”,是指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所造成的客观印象和舆论评价。一个人面子的得失、人缘的好坏、人情的厚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他之间是否恪守信诺、专诚如一。如果在亲戚、邻里、朋友面前失信,就会觉得“丢面子”,不仅受到自己良心上的谴责,而且也会遭到乡里公众舆论的谴责,自己会在熟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不好做人。因此,所谓“重然诺,轻生死”、“约誓遇事帮助”等等执着于“信”的观念,对于农民小生产者有强烈的道德魅力。联系邻缘的“信”(人情意识)的道德规范的进一步发展,便拓展为凝结性更强的道德规范——“义”,演化出结盟意识——互帮互助。“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等等。这些来自民间的格言、俗语、口号,体现的是小生产者对“义”的执着和结盟意识的外泄。
但是,一旦超出了自己的“圈子”,在与“圈外人”打交道时,小生产者便不奉行“圈内人”所遵循的道德规范,而是内外有别,公私分明(公德是指与“圈外人”打交道时的道德;私德是指与“圈内人”打交道时的道德。)
对于农民小生产者二重化的道德标准,苏联学者B·H·米罗诺夫曾作过考察和分析。他在分析沙皇统治时期俄国的农民的道德观时指出:“农民的道德准则具有二重性。村社道德中存在着很多官方认可的道德,村社道德在村社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方面得到充分的实施,在同其他村社农民的关系方面,这种道德准则不太起作用,而在同国家、其他阶级、其他等级头面人物的关系中,这种道德很难实行。在农民看来,欺骗邻居、亲属是不道德的,而为了农民的利益欺骗政府官方或者地主,是受到表扬的道德行为。偷窃邻居的东西、破坏所分土地的地界、未经允许在村社的树林里砍柴,这是不道德的。而摘地主园子里水果、在地主的林子里砍柴或耕了地主的地,则不认为这些行为有什么不道德的地方。这样,农民那里有一种道德在处理村社内部成员关系中起作用,还有一种道德——处理同外人、特别是同非农民关系时的道德。”〔5〕
显然,中国的农民小生产者的传统道德观也是适合上述分析的。我们且以农民小生产者对于“道”、“德”、“信”这些基本道德规范的两种不同的理解为例。在小生产者看来,偷窃失“德”(圈子内),但偷了养家(圈子外),是孝子;欺骗失“信”(圈子内),但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对地主、上级官员进行欺骗(圈子外),是精明;杀人大逆不“道”(圈子内),惟杀富济贫或为了替亲报仇而杀人(圈子外),是英烈。这些行为往往能够得到乡里社会舆论的谅解、同情、支持以至赞叹。显然,中国的农民小生产者完全是根据是否有利于自己家庭和小团体的利益,作为判断道德行为善恶的标准的。
以“圈子意识”为核心的二重化的道德标准和价值体系,对于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某些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它使得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二重化,使之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性质,而是局限于个人家庭以及亲戚、邻里、朋友等狭隘圈子里,从而造成小生产者的社会公德意识缺乏、社会的公共道德规范难以得到遵守。正如有的学者在批判中国“国民性弱点”时指出的:“不遇公共之事物则已,如其遇之,于钱财则随意挥霍,于什物则必任情毁坏,盖以为此事之物,其保存于否,绝无与于吾一身一家之事,吾何为而代为之,护持也哉,夫以举国人皆存如是之思想……则国民恐永不能有道德心矣。”〔6〕
其次,它使得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交往关系时极具个人感情色彩,时刻注意对方是否属于自己的“圈子”,以情感代替理性,价值判断取代是非判断。这样势必造成人们的理性意识、公正意识、规范意识的缺乏,“规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淡薄,职业道德意识也就难以确立起来。社会学家M·J·列维认为,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是合理主义、普遍主义、功能有限制和感情中立的,而非现代化社会的社会关系是传统习俗的、个别的、功能无限制和具有感情色彩的。显然,小生产者对待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态度和所持的道德观,是不利于人们建立起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从而妨碍着中国社会关系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
在中国的农民小生产者看来,为人就是讲人缘、讲交情;办事就是凭关系、讲面子。铁面无私、秉公执法者反倒被其斥责为“不通人情世故”、“六亲不认”、“没有人情味”。在这种文化心理的驱使下,“关系学”盛行,“后门风”难止。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规范经济、法制经济,它奉行的是公平竞争、等价交换的原则。它就是要撕下笼罩在家庭关系和邻里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要求所有参加市场竞争的人在市场规则、社会规范以及法律、秩序面前一律平等;它就是要求执法者、国家公务员“不给任何人面子”,在价值取向上必须保持中立。显然,小生产者的“圈子”意识、“面子”意识,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相抵触的。在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支撑时,我们记起林语堂先生的一段话倒是不无见地:“在每个人失掉他们的面子以前,中国将不成其为民主国家。”〔7〕因为,只有不给任何人“面子”,严格按照法律、规章、 制度办事(法治),而不是凭人情面子办事(人治),民主才有基础和保证。
再次,“圈子意识”必然导致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盛行,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在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诸侯经济”和地方保护主义现象,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家族势力、帮派势力的重新抬头,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基于落后的小生产而形成的互助结盟意识、团伙意识仍有市场和土壤。所有这些,都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和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向深层次推进起着阻碍作用。
当然,我们并不能由此断言中国农民小生产者的传统道德观一无是处,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承诺的伦理价值原则格格不入、无法沟通。事实上,小生产者伦理价值体系中的合理内核,经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批判扬弃,经过引导和创造性转化,也可以纳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体系中来,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用成分。例如,小生产者对人间亲情的执着和对和谐的人际关系的价值目标的追求,经过我们的正确引导和创造性转化工作,可以用来克服市场化和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对工具理性、技术至上的片面化追求,避免人受物役、沦为金钱奴隶的拜金主义、物欲横流现象的滋长,由此体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又如,小生产者对“信”的执着,经过批判、扬弃也可以用来强化人们“重合同、守信用”的意识,而这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须的。总之,对中国农民小生产者的传统道德观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具体分析和创造性的转化工作。将其合理内容转化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与之相适应的价值体系的有用成分。
注释:
〔1〕W·古德:《家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第15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卷,第15页。
〔3〕〔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2页。
〔5〕B·H·米罗诺夫:《历史学家和社会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5页。
〔6〕参见《大公报》(影印本)第4册,第16页。
〔7〕参见林语堂:《吾国与吾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