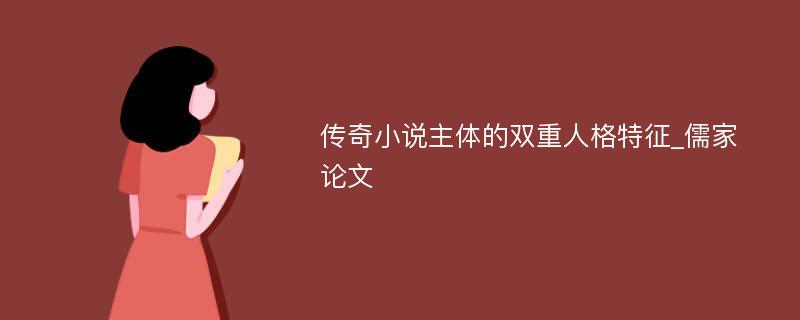
亦庄亦怪:志怪传奇小说创作主体的双重人格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重人格论文,主体论文,亦庄论文,特征论文,传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03-7535(2006)03-035-05
中国古代志怪传奇小说的创作,贯穿其中的一条主要思想脉络是如何处理“庄”与“怪”的问题。所谓庄,是儒家务民经实的庄重雅正,而怪则指小说创作者尚怪的宗教心理和宗教情感。儒家先圣孔子暧昧微妙的鬼神观念,造成后世文人在谈神论怪有否违背政教伦理的问题上进退失据,与此密切相应,表现在志怪传奇小说的创作中就是在庄怪之际游移不定,争论不休。
儒家学说是以经世致用、重人伦道德为精神特质的人本主义思想体系,对鬼神和彼岸世界的关注远不及对世务人伦的关切。据《论语》记载,孔子的弟子季路向孔子请教鬼神生死问题,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1] 显示了强烈的经世济民精神。孔子对怪力乱神的基本态度是“不语”,[2] 其学说体系以人为本,对其所不能言知的超自然的鬼神之事采取多闻阙疑之态度:“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3]“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4] 不大喜欢谈论鬼神之事。真正理解孔子的是宋人章炳文、陆九渊和明人都穆。章炳文《搜神秘览序》云:“孔子不语怪力乱神,非不识不知也,特以无补于教化耳。”[5] 陆九渊云:“‘子不语怪力乱神。’夫子只是不语,非谓无也。若力与乱,分明是有,神怪岂独无之?”[6] 都穆《跋博物志》言:“《论语》记子不语怪,怪固未尝无也,圣人特不语以示人耳。”[7] 这说明后世学人认识到孔子是承认鬼神的。鬼神祭祀是以鬼神存在为前提的,如果否定鬼神,祭祀的意义便不复存在,如《墨子·公孟》所言:“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8] 孔子曾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9]“非其鬼而祭之,谄也”,[10] 这是从宗教体验的角度要求祭祀者心存鬼神,且要合乎礼仪。《论语·述而》载,孔子病重,子路请求祈祷,并引诔文所言“祷尔于上下神祇”以说服孔子,孔子曰:“丘之祷久矣。”[11] 另据《国语·鲁语下》载孔子语云:“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12] 这表明孔子自己是承认鬼神存在的。孔子生活在特定的时代,难以超越那个时代的鬼神祭祀风习,但言谈鬼神与自己的人本主义思想体系和政治理想相悖,所以才主张敬鬼神而远之。远鬼神,畏天命是其思想体系的宗教特征。
孔子关乎鬼神之事的暧昧态度给后世造成极大的麻烦,埋下了冲突争议的种子。文人士大夫秉承圣师的言教,以修齐治平为安身立命之准的,重名教世务,以妄谈鬼神为耻。司马迁作《大宛列传》,对《禹本纪》、《山海经》的怪诞内容即采取阙疑回避的态度:“《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13] 然而,好生恶死乃人类天性,对来生的关怀是世界民族的普遍心理,作为正统思想的“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文化和作为国家民族宗教的宗法性传统宗教,均未能很好地解决人的生死问题,只是通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特别强调血缘延续的文化和朦胧不成体系的鬼神观念来让一个人的生命以另一种意义延续,但这种异体延续并不能满足个体生命永生的渴求。[14] 有了这一缺陷,在正统文化之外涌动着以扶乩、命相、风水、谶纬之学为主要内容的神秘文化,如两汉的经学与谶纬神学的对立,儒家正统文化与巫术祭祀、神仙方术的对立也就从来没有绝迹,从而也出现了秦始皇求长生不死之药、汉武帝好神仙方术、汉文帝“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15] 的举动。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满足了中国人的宗教需求,其构筑的神仙世界和极乐净土,是古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世界,故而得以迅速发展和传播。佛教因果报应理论和地狱观念对中国传统泰山治鬼说和鬼神观念的改造,建立起了适合中土传播的地狱鬼神体系,于是鬼神怪异之谈、祸福报应之说充溢阎闾士林。但这毕竟与周公孔孟之道扞挌冲突,对传统士人而言,实为一两难选择。
自古以来,吾国就形成了执中的国民性格。两端相较而取其中道是国民最基本的认知心理和处事行为模式。《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16] 宋代大儒程颢有言:“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17] 这种执中的国民性格深刻影响了国民的认知行为,在艺术鉴赏方面讲求中和之美,爱情方面标榜“发乎情而止乎礼”,为人处事主张不偏不倚,一如林语堂先生所言:“一个典型的中国式论断是:‘甲是正确的,而乙呢,也不错。’”[18] 对中国士人传统人格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有老庄开创的道家学说。老庄之学与儒家思想的结合养成文人士大夫圆融变通、与时俯仰的安身立命之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些个看似自相矛盾的命题却得以奇妙的结合。在这样的社会心理的影响下,面对鬼神之事,中国古代士人养成了“亦庄亦怪”的二重人格。
所谓“人格”,是一个人在其自然素质基础之上、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特征。“人格是一系列复杂的具有跨时间、跨情境特点的,对个体特征性行为模式(内隐的以及外显的)有影响的独特的心理品质。”[19] 可见,人格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独特心理品质或特征,而且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经过长期积淀形成的。宗教文化对中国古代士人的人格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所谓“亦庄亦怪”,是士大夫乐道鬼神怪异之事的宗教心理需求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政教人伦传统相互冲突,并最终走向契合的心理状态,是古代士大夫群体的普遍人格特征。“庄”者,正也,庄重也,秉儒家正道以教化为能事,立身清正;“怪”者,异也,奇也,好奇尚异,闻人谈鬼则喜。[20] 在“庄”与“怪”之间的游离徘徊,正是古代志怪传奇小说创作群体典型的二重人格特征。根据传播学、心理学和宗教心理学的理论,小说作者既是某种特定文化的传播者,同时也是该文化最直接的受众;他们有自我实现的愿望和各种各样的需要,譬如“博物致知”的信息需要,“设教劝善”的伦理需要,“游心娱目”的生活需要,“穷神洞幽”的宗教需求等等。这种不同目的的需求,也是“亦庄亦怪”二重人格形成的内驱力。志怪传奇小说作者正是通过创作来达到自我实现和需要满足的。
被称为“古今语怪之祖”的《山海经》,[21] 对鬼神怪异的记述和描写较早引起士大夫的注意和争论。西汉刘秀(歆)在呈送汉帝的《上山海经奏》中追忆,汉宣帝时,其父刘向为宣帝推荐《山海经》,引起极大兴趣,“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22] 由《易经》和古代阴阳家学说开创的神秘主义传统,经汉代董仲舒天命神学的改造,成为文人士大夫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山海经》的出现,适合了时代的变怪话语语境,所以在士大夫中得以传播,满足了他们对鬼神怪异之事的神秘感。这个时候,祯祥变怪之谈是通神穷变的途径,与名教事业并无冲突。至晋郭璞注《山海经》前后,士大夫中已经出现对怪异之谈的怀疑和批判声音,其《山海经序》云:
夫玩所习见,而奇所希闻,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略举可以明之者:阳火出于冰水,阴鼠生于炎山,而俗之论者莫之或怪。及谈《山海经》所载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则几于无怪矣;怪所不可怪,则未始有可怪也。[23]
郭璞说时人读《山海经》的记载,均以为怪异,实则并不可怪。其主要观点在于竭力论证《山海经》所记载的神怪的真实性。值得注意的是,郭璞已经注意到读者对小说的接受问题,认为怪异感的产生源于人的无知,将本不可怪的事物当成了奇怪之事,所谓“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24] 这并非说明郭璞有无神论倾向,只是他所认为的“怪物”与众不同而已,如“阳火出于冰水,阴鼠生于炎山”。据《晋书·郭璞传》,璞好卜筮占侯,精阴阳历算,曾作《游仙诗》,则是好道之士。[25] 所以他的观点是为了维护道教。略早于郭璞的张华,曾撰《博物志》四百卷,捃采遗逸,考验神怪,据前秦王嘉《拾遗记》卷九记载,此书引起了晋武帝的疑虑:“昔仲尼删《诗》、《书》,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乱神。今卿《博物志》,惊所未闻,异所未见,将恐惑乱于后生,繁芜于耳目,可更删截浮疑,分为十卷。”[26] 开后世禁毁小说之先声。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怪异之谈,士林之中存在两种声音,一即以晋武帝为代表维护儒家传统的反对声,一是以干宝、王琰、刘义庆等志怪小说作者为代表,竭力论证鬼神不诬的声音,鲜有尝试调和两者的努力,文人以“非庄即怪”为主要人格特征。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这些志怪传奇小说也未将志怪与儒家教化结合起来。无论是晋干宝的《搜神记》,还是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其宗教传化目的较为明显,除受佛道二教影响外,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这些作品大多以史家笔法穷神洞幽,力证鬼神不诬,相反与正统儒家思想的关系则较为淡漠。
与魏晋六朝士大夫对怪异鬼神之谈持批评态度不同,唐代浓郁的宗教氛围和修仙崇佛的文化心理,使得小说作者热衷于怪异之谈,并将其与儒家教化理念奇妙结合起来,能尽心游处于“庄”、“怪”之际。《独异志》作者李伉自序其书时宣布:“《独异志》者,记事之独异也。自开辟以来迄于今世……耳目可见闻,神仙鬼怪,并所摭录。”[27] 明确以单纯摭录鬼怪为目的,似乎作者并未因可能违背政教人伦传统而略感自责。即使个人行为有碍于儒教伦理,只要能够及时省悟并改过自新,依然不失为一正人君子。最令人称奇的是袁稹《莺莺传》中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男主人公张生的一番言论:“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这番言论深为时人叹赏,为张生赢得了“善补过者”的美誉。[28] 其背后共同的价值评判标准是儒家的中庸之道。
创作了《冥报记》的唐临在该书自序中对谈论因果报应的问题作如是说:
事法王道,理关天命,常谈之际,非所宜言。今之所录,盖直取其微细验,冀以发起同类,贻告子孙,征于人鬼之间,若斯而已。[29]
报应予夺由天命决定,是王者施行教化的工具,未可作为日常言说的谈资;之所以撰录报应故事,也是为了劝善惩恶,警示后人,征验鬼神。这里,唐临将两者完美结合起来了。唐代诗人顾况为戴孚《广异记》作序,为了解决怪异之谈与孔子遗训的矛盾问题,径直曲解“子不语怪力乱神”之“不”为“示”,认为《论语》的本意是说孔子以怪力乱神示人,欲达观象设教之目的:
予欲观天人之际,察变化之兆,吉凶之源,圣有不知,神有不测。其有干元气,汩五行,圣人所以示怪力乱神、礼乐刑政,著明圣道以纠之。故许氏之说天文垂象,盖以示人也。古文‘示’字如今文‘不’字,儒者不本其意,云‘子不语’,此大破格言,非观象设教之本也。[30]
天地之间的变化、人事兴替与吉凶祸福的根源神妙难测,它会干扰元气,紊乱五行,所以圣人通过示现怪力乱神,发扬圣道拨乱反正。此种解释,固然契合儒家的宗教观,但强解“不”以为“示”,则是无稽之谈,这反映了唐代士人试图调和语怪与不语怪两个传统的努力。
唐代小说史上一个著名的公案是围绕韩愈《毛颖传》的争论。韩愈作传奇《毛颖传》后,在士大夫中引起震动,皆大笑之以为怪,难以相信以道统自居的韩愈会作出此等文章。张籍投书韩愈,批评他“多尚驳杂无实之说”,“或以为中不失正,将以苟悦于众,是戏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义之道也。”张籍的批评是对韩愈以戏为文、尚怪好奇的倾向不满,认为创作态度不严肃,有失儒家雅正之道。韩愈在《重答张籍书》中回应道:
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恶害于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也。[31]
柳宗元得知此事后,也撰文为韩愈辩护:“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韩子穷古书,好斯文,嘉颖之能尽其意,故奋而为之传,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以励,其有益于世欤!”[32] 所谓“俳”即游戏笔法,自然予人以“奇”、“怪”、“驳杂”之感。柳宗元的基本立场是:古圣先贤亦有此风,此作有益于世。韩愈的学生李翱亦持同样观点,他在《卓异记序》中从无害有益的角度看待鬼神之谈:
神仙鬼怪,未得谛言非有,亦用俾好生杀。为人一途,无害于教化,故贻自广,不俟繁书以见意。[33]
神仙鬼怪于儒教事业并无害处,却可化导民众令其好生恶杀,故当任其自然发展。这场争论达成的基本共识是“中不失正”,即驳杂怪异之谈与儒家正道并无冲突。韩愈、柳宗元这些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的观点对当时文坛的影响不可忽视。
晚于韩愈的著名小说家段成式在《酉阳杂俎自序》中说:
夫《易》象“一车”之言,近于怪也;诗人“南箕”之奥,近乎戏也。固服缝掖者,肆年笔之余,及怪及戏,无侵于儒。无若《诗》《书》之味大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也。炙鸮羞鳖,岂容下箸乎!固役而不耻者,抑志怪小说之书也。[34]
“一车”典出《周易·睽卦》上九爻辞:“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35] 王弼注:“见豕负涂,甚可秽也;见鬼盈车,吁可怪也。”孔颖达疏:“鬼魅盈车,怪异之甚也。”原来是说出行目睹一车鬼,确为一件甚可怪异之事。[36] 段成式从儒家经典《易经》和《诗经》中找到了古人言怪的强有力依据,认为儒者在著述立言之余,语怪话异、剧谈戏论并不妨害儒家正道的奉行,所谓“及怪及戏,无侵于儒”。[37] 与此类似,前引顾况《戴氏广异记序》也从经史典籍之中发现儒家具有语怪传统:“……古者青乌之相冢墓,白泽之穷神奸,舜之命夔以和神,汤之问革以语怪,音闻鲁壁,形镂夏鼎,玉牒石记,五图九籥,说者纷然。”[38] 杜光庭《录异记序》亦云:“怪力乱神,虽圣人不语,经诰史册往往有之。前达作者,《述异记》、《博物志》、《异闻集》,皆其流也;至于六经图纬河洛之书,别著阴阳神变之事、吉凶兆朕之符。”[39] 儒家经典亦谈怪异之事,无疑使唐代小说作者记述、创作相关题材作品时释然于心,并努力解决了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促成了两者的合流。
宋以降,佛教与道教地位的下降,士大夫地位的上升,儒家文化对宗教和社会文化影响和控制力的进一步加强,打破了唐代以来形成的士大夫“亦庄亦怪”的二重人格特征的平衡。随着理学的兴起,这种趋势更加明显,语怪传统受到挤压,小说作者由二重人格向边缘化人格转变。据洪迈在《夷坚丁志》序中自述,其创作《夷坚志》时,受到的批评很激烈:
子不能玩心圣经,启瞷门户。顾以三十年之久,劳动心口耳目,琐琐从事于神奇荒怪,索墨费纸,殆半太史公书。曼澶支离,连犿丛酿,圣人所不语,扬子云所不读。有是书,不能为益毫毛;无是书,于世何所欠?[40]
批评者认为其三十年致力于一部神奇荒怪之书,毫无意义。对此,洪迈颇为自知,直言是书之作,“颛以鸠异崇怪”,“但谈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它”,他语含嘲讽地说:“六经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41] 与圣教人伦生发了疏离感,是人格上的自我边缘化。
明代文网森严,封建理学、伦理纲常之类说教充斥文坛,文士对谈神论怪深以为耻,以党同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为正统。刘大昌《刻山海经补注序》所批评的“世之庸目”对《山海经》所记怪异的看法,真正代表了正统士大夫的普遍观点:
世之庸目,妄自菲薄,苦古书难读,乃束而不观,以为是《齐谐》、《夷坚》所志,諔诡幻怪,侈然自附于不语,不知已堕于孤陋矣。夫子尝谓,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计君义不识撑犁孤涂之字,病不博尔。[42]
可见,明代士大夫以不语怪为荣,而在刘大昌看来,《山海经》也只余广博见闻的意义了。在此种文化氛围下,瞿佑的传奇集《剪灯新话》书成之后,自以为涉于语怪,颇多忌讳,不欲流传,然求观者甚众,遂借儒经亦曾言怪以自解:
《诗》、《书》、《易》、《春秋》,皆圣笔之所述作,以为万世大经大法者也;然而《易》言“龙战于野”,《书》载“雉雊于鼎”,《国风》取淫奔之诗,《春秋》纪乱贼之事,是又不可执一论也。今余此编,虽于世教民彝,莫之或补,而劝善惩恶,哀穷悼屈,其亦庶乎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之一义云尔。[43]
瞿佑为了减轻来自正统士大夫的压力,抬出了作为“万世大经大法”的儒家“圣经”自我辩护,一方面从中寻求依据,竭力阐明《剪灯新话》“劝善惩恶”、“哀穷悼屈”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在作品中穿插大量诗词,雕琢文采。他的好友凌云翰、桂衡等人亦极力称许其学养、文采和该书褒善贬恶的鉴戒意义,但这些努力仍然未能使《剪灯新话》逃脱遭禁的命运。[44] 从本质上讲,这种“寓怪于庄”的努力实则是高压统治下的人格分裂现象。至清代,志怪传奇作者群体发生分化,以蒲松龄、李庆辰为代表的落魄士人,假鬼神之谈寄托孤愤之情,其人格彻底边缘化。[45] 而以袁枚、纪昀、俞樾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或借之以自娱,或者将小说变成载道教化的工具,寓庄于怪,小说的文学性则被严重削弱了。[46] 但其进步意义在于,有人已经认识到“幻由心造”是鬼神怪异之谈的根源。清末王韬《淞滨琐话》自序云:
自来说鬼之东坡,谈狐之南董,搜神之令升,述仙之曼倩,非必有是地,有是事,悉幻焉而已矣。幻由心造,则人心为最奇也。[47]
即是说前贤的鬼神之谈未必实有其事,而是人心产生的幻象,这就揭示了鬼神故事的实质问题,也打破了干宝以来利用小说自证“神道不诬”的志怪传统,使得这个时期的志怪传奇小说具备了自身特点。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志怪传奇小说创作和发展演变的历史,与小说作者处理“庄”、“怪”问题的心路历程同步。作者所展现出来的“亦庄亦怪”的人格特征,是执中的国民性格支配下,儒家政教观念与世人为满足自我需要而求怪求奇的“语怪”传统相互冲突融合的结果。这种冲突融合形成的普遍认识是:怪固不足道,然并不妨害儒道,且有劝善惩恶以助教化之功用,虽不必夸扬其辞,却当令其自然传播。这就成为韩愈、纪昀之流的大儒和牛僧孺、李德裕之类的高级官僚好尚怪异之谈,创作志怪传奇小说的重要动力。
标签:儒家论文; 士大夫精神论文; 文化论文; 双重人格论文; 读书论文; 韩愈论文; 国学论文; 孔子论文; 山海经论文; 剪灯新话论文; 博物志论文; 怪异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