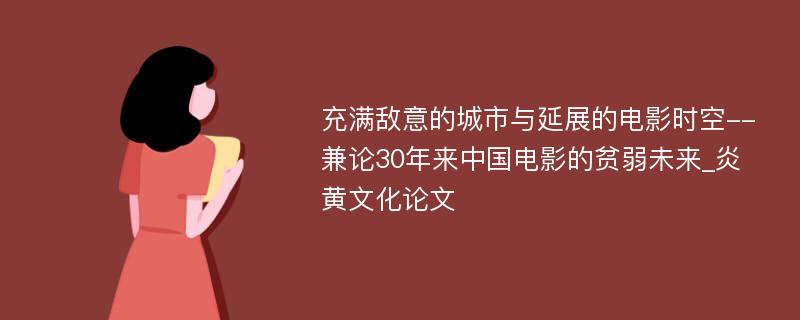
敌托邦城市与延伸的电影时空——兼论中国电影三十年贫弱的未来想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弱论文,三十年论文,中国电影论文,时空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3年,上海新中华杂志社编辑部刊登了一则通告,要求读者就“上海的将来”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两个月后,编辑部收到了100多篇短文,作者中虽有茅盾、林语堂、郁达夫这样的知名作家,但大多数投稿人都是普通读者。杂志社选取了其中的75篇文章,以《上海的将来》为题于次年结集出版。呼应当时流行的左翼阶级分析观,集子的序言勾画了一个被阶级差异所分裂的上海:
上海是世界第六位的大都市,是中国第一位的大商埠;是国际帝国主义对华经商的大本营,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滋长的根据地。上海的市民,日益增加;上海的建筑,日趋高大;这都足以表示上海的繁荣与欧化的。但在另一方面,在日益增加的上海市民中,不知有若干人在号饥呼寒;在日趋高大的建筑旁,不知有若干人在风餐露宿。上海的生活贫富与变化与对比,有主人,有奴隶;有高等华人,有马路瘪三;……①
除少数几篇由非政治或缺乏政治兴趣的作者所写的文章外,新中华杂志社的上引序言为整本文集定下了基调。大多数投稿人对“上海的将来”做出了两种判断:要么崩溃,要么重生。一位作者认为,为了预测上海的明天,我们首先应该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上海应不应该有将来?2)上海能不能有将来?3)如果上海不应该有将来、但这座城市在将来却依然存在,那么,这个城市的将来又会是什么样子?② 很多投稿者认为,回应这些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应该超越就上海谈上海的局限,进而将这座城市摆在民族国家的大语境中加以考察,揭示其异己对立的本质。“虽说上海的地面是我们中国的”,某投稿人写道,“事实上有一寸土真正是中国同胞的吗?不是。”③ 上海这座“自由市”,或曰“上海国”,根本就是中国民族国家利益的对立面:“上海一天天的繁盛、扩大,中国便一天天的凋零、衰落。上海成了天堂,中国遂如地狱。”④ 就此意义说,关于上述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无疑是上海绝不应该有将来。无论上海多么繁盛,它都只是“帝国主义吮吸中国人脂膏的吸盘”。因此,为确保中国在世界上的独立民族国家地位,上海必须全然“没有将来”。如果有所谓“将来”的话,那这一“将来”必定是都市上海的彻底崩溃:“我不能允许上海还有它的‘将来’,假如是有,那它的‘将来’应该是毁灭!”⑤“若有人问我,上海的将来是繁荣或是衰亡,我将毫无疑虑及踌躇地回答:衰亡”。⑥“上海如不能走向健康的繁荣,毋宁走向痛快的毁灭”。⑦
围绕“上海能不能有将来”的问题,一些投稿者认为,答案的关键在于上海能否从外国和剥削阶级统治崩溃后的废墟中重生。尽管现实和未来的图景一片漆黑,上海仍被很多投稿者视为是民族重生的物质基石,同时也是生产终极答案、美好结局以及启示录般预言的最佳场所。“假如中国的民族主义能够抬头,那中国怒吼的第一声定是从上海发出”。⑧ 新生的上海不仅将从英国和日本兵营、黄浦江上的外国军舰以及英法日警察、红头阿三和白俄包探等外国邪恶势力中解放出来,而且也将成就为一座没有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城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基本对立以及“上海是一座剥削阶级的压榨机”的事实,将最终导致二者之间冲突的尖锐化,其结果是“构精化生”出一座纯净无瑕的新都市:
在那新上海里面,没有主人与奴隶的分别,也没有“高等华人”与“马路瘪三”的对比。住在“贫民窟”里的穷鬼子,将乔迁至“高楼大厦”去居住;住在“高楼大厦”的“安乐公”则将乘飞机逃到“火星”去度寓公的生活。⑨
不过,据作者看来,通向未来无阶级城市的路途并不平坦。“临盆之日,母体难免流血的痛苦”,剥削阶级“将作最后的挣扎”,而“黑虫”们(即普罗阶级)在新上海诞生之前也不得不经历一次“伟大的牺牲”。
正是在此处,毁灭与重生的母题变得逐渐清晰起来。在许多投稿者的未来想象中,作为一个因中国其他地方衰落而畸形繁荣的半殖民地城市,上海无论是从文化礼教还是从法律道德上都必须为“破坏”和“吞噬”中国的一切而遭“诅咒”。⑩ 从这点看,为确保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存在与强大,上海必须没有将来。霓虹灯必须被死亡吞灭, “黑墨的浓云”将笼罩都市的天际。(11) 另一方面,婴儿临盆的隐喻也暗示了上海的启示录特质。在毁灭的都市废墟上,一个摆脱了外国统治和阶级压迫的新世界将会诞生。如果上海有将来,那么它会是一个在民族和阶级争斗中重新诞生的“新上海”。上海的重生, “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此层面说,上海的将来富含宗教似的启示意义:在“灾难的背景”下,亦即“邪恶”都市轰然崩溃的瓦砾中,一个全新的理想世界将最终从旧时代的废墟中诞生。
尽管《上海的将来》收录的都是一些随感式的短文,其中所图绘的未来都市景观大多模糊不清,但在超越现实的箍限、寓意性地构筑一个乌托邦或敌托邦城市方面,却将自身与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现实主义文化氛围拉开了距离。本文以《上海的将来》铺展话题,将主要讨论二十世纪以来在西方和日本电影文化中渐成传统、而且不断产生经典的敌托邦城市想象,并在此基础上观照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电影所积淀的相应作品。文章认为,敌托邦城市的影像想象,是拓展电影时空、丰富电影类型、特别是黑色电影和科幻电影的重要途径:就哲学层面而言,敌托邦城市的建构,映射的乃是二十世纪以来人类对现代性、启蒙主义以及文明和科技发展的反思与批判。因此,对敌托帮想象传统的探讨,不仅试图为中国电影寻找某些普适性的主题,而且意在与贯穿中国现代思想的唯进步论、唯科学主义等建立批判性的对话关系。
敌托邦社会与敌托邦想象
尽管“敌托邦”(dystopia)一词的使用大致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后期,(12) 但敌托邦想象直到二十世纪、特别是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在西方思想中逐渐发展成形,并由此催生了一批另类于工具理性和进步主义的文化经典。(13) 如果说启蒙主义思潮和工业革命、技术进步向来就不乏批判的对立面的话,那么,两次世界大战对文明的废墟性毁灭则严重加深了西方文化语境中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焦虑和恐惧。这不仅因为独裁政体同时可能滋生并成熟自左翼和右翼思潮,更因为技术的进步并未允诺完满的人生和美好的世界,反而直接导致了轻易毁灭文明之手段的达成,更危及人类所赖以存活的地球本身。敌托邦想象的背后乃是对现实社会、文化和科技发展的警示和批判,它贯穿于西方现、当代思潮的始终,由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共同图绘,只不过现代主义者可能还对“荒原”的疗治抱有幻想,而后现代主义者则干脆认为敌托邦也许并非想象、而是当代社会本身。福柯关于“圆形监狱”(Panopticon)机制的探讨,仰赖的正是对当代西方监控和惩戒空间的建筑学观察。
典型的敌托邦想象常常与个性和情感被极端专制的政体和极端有序的理性意志所消泯相关。前苏联颇有争议的小说家扎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1884-1937)在其代表作《我们》(We,1923年出版)中所图绘的敌托邦,正是这样一个经过了“两百年战争”阶段后、仅有0.2的原地球人类存活的未来世界。在完全被绿墙隔绝的“绝对国”(One State)里,“大施主”(the Benefactor)统治着众多无名无姓、被完全以字母和数字编码的男女。他们的日常生活受数学原理所控制,每天的睡眠时间、活动时间和工作时间均经过细密的测试,必须严格遵守。在性生活方面,每个人均被给定一定数量的性交伙伴,相互以粉红色票据、按规定的计划和时间进行交配。小说男主人公D-503开始时对“绝对国”充满了献身精神,并试图乘坐自己设计的飞船将“绝对国”的幸福传播到绿墙之外。不过,他很快陷入了与颇具反叛精神的异性I-330的情感纠葛中,对“绝对国”的忠诚也随之匮蚀。挣扎于梦境与现实、想象与数学真理以及自我与社会的矛盾之间,D-503几近疯狂。小说结尾。他在监狱里接受了“大手术”(the Great Operation),想象能力被彻底去除,不再受爱恋和情感所困扰,进而成功地回返到原初的境界,玻璃之城也恢复了往日的和谐与秩序。
控制敌托邦世界的力量,无论是专制政府还是跨国公司,都表现为对自由意志和批判精神的极端敌视,试图千方百计予以扼杀。扎米亚京的未来世界,是一个遍布透明玻璃房的城市。之所以透明,是因为每个人都必须时时处于“绝对国家”的监控之下。而向以想象和异端著称的诗人和作家,则被要求“创作”大量颂赞“绝对国家”荣耀和美丽的作品装上飞船,散播到绿墙之外的世界。同样,在美国当代作家雷·布莱伯利(Ray Bradbury)的敌托邦名作《华氏451》 (Fahrenheit 451,1953年出版)中,独立思想和知识也被视为未来社会的最大威胁。要消灭自由意志和批判精神,必须先清除其载体即书籍。于是,负有特殊使命的“消防员”遂粉墨登场,他的职责不是救火,而是焚书,见一本烧一本。在布莱伯利未特别时间化的未来世界里,书籍、特别是文学作品成了见不得阳光的禁忌,胆敢读书的人一旦被思想警察发现,将马上被精神病院收押。(14) 敌托邦世界的控制体系在英伦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笔下更演变为无时无刻不在运转的超动力机器,而维持和保证该机器正常运转的力量正是渗透于社会各角落的思想警察。奥威尔代表作《1984》(1948年创作、次年出版)所想象的三十六年后的世界,乃是党领袖“大哥” (Big Brother)绝对控制的天下。在这个党就是一切的国度里,臣民们不仅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受到监控,而且他们的精神活动也受到思想警察的严格管束。小说主人公史密斯(Winston Smith)对“大哥”的叛逆以及对自由爱恋的追求很快被思想警察机构的卧底发现,他因思想罪被立刻逮捕,等待他的是一系列包括洗脑和肉体折磨在内的“重新整合”工程。小说结尾,行将被处死的史密斯完全皈依了“大哥”,由衷体味到了党与“大哥”的慈爱。
在敌托邦想象中,物质的匮乏已远离人类,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系列生活难题,似乎也因科技的高度发展而消逝。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2)的敌托邦经典《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年出版)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看似乌托邦的未来图景:在福特纪元632年、也就是公元2540年。人类似乎已经达到了普遍幸福的境界。地球上的大多数人生活在稳定、统一、富足的“世界国” (the World State)中,生物基因技术的发展使人类不再依赖女性的子宫繁衍后代,而是通过流水线作业完成新生命的诞生过程。尽管在流水线上成就的婴儿并非生来平等,而是被划归为五个阶级,分别从事劳心、劳力、创造、统治等工作,但由于一种被称为“索麻” (Soma)的迷幻药物的发明,被统治的劳力者们却总能生活在健忘的愉悦之中,始终心满意足,欢欣雀跃。工作之余,人们被允许无休止地放纵自己的欲望,包括疯狂购物和自由滥交。尽管无节制的性发泄在“美丽新世界”看来具有建设意义,但在这个人类的生死均受到严格控制的社会里,爱情、婚姻和为父为母却被视为诲淫诲盗,称某女为母亲是对她最严重的侮辱。也正是在这个看似人人都拥有“幸福”的“美丽新世界”中,个性被群体的癫狂所淹没,独立思考的权力被技术程序控制所剥夺。没有了战争,没有了贫穷,没有了社会阶层之间的争斗,但这一切却是经由去除艺术、文学、宗教和其他人类表达情感和欲望的方式以及婚姻和家庭等一系列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后达成的。就此意义说,和《1984》、《我们》、《华氏451》等敌托邦小说一样, 《美丽新世界》也构成了对未来的审判。
影像敌托邦:从《大都会》到《人类之子》
虽然电影作为一种文化样式迟至十九世纪末年才面世,但电影的敌托邦想象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内容的丰富性方面都不逊于文学。电影在空间营造上的具象性更将小说中常常处身背景的城市推到前台,彰显出敌托邦与城市之间的联系与紧张。实际上,影像敌托邦与城市之间的联姻不过是电影—城市对应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自电影发明以来,城市、城市生活与城市空间一直是摄影机眼睛捕捉和研究的对象,卢米埃尔兄弟的巴黎和马丁·斯科西斯的纽约已经永久烙印在关于两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中。另一方面,就形式而言,“电影一直具有某种惊人且独特的能力,即通过场面调度、实景拍摄、灯光、摄影与剪辑来捕捉并表现城市的空间复杂性、多样性和社会律动”;电影和电影工业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了某些城市的文化地理景观乃至身份认同。(15)
影像敌托邦的传统或许可以从德国导演弗里兹·朗(Fritz Lang)的默片经典《大都会》(Metropolis)找到源点。从内容看, 《大都会》所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有时甚至略显幼稚:公元2026年,在万城之城的“大都会”,生活着截然不同的两类人,资本主义的精英们居住在天堂般花团锦簇的都会上层,而终日不见阳光的都会下层则拥挤着为城市运转拼死劳作的普罗大众。天真无邪的玛丽亚带着一群穷苦的孩子来到都会上层,诉说地下层大众的苦难;但都会统治者不仅迅速拘押了玛丽亚,还以她为原型生产了一个几可乱真的机器人,冒充玛丽亚回到地下层,煽动普罗大众闹革命,而这就为都会精英们的血腥镇压提供了口实。影片结尾,由庞大机器驱动的城市在暴力和无政府状态中崩塌。
从很大程度上说,视觉震撼力、而非故事本身成就了《大都会》的经典意义。无论是庞然耸立的摩天楼还是令人窒息的城市天际线、也无论是日以继夜运转的大机器还是列成方队缓慢移步的普罗大众,弗里兹·朗所图绘的未来世界以其对比强烈、动静相衬、充满几何感的构图冲击着人们的视觉,极大地拓展了电影的时空想象和表现力。随着叙述的推演,通体环绕在电流中的机器人玛丽亚成就了另一种奇观,进一步繁复化了影片的敌托邦建构。正是由于这种视觉震撼力,我们在后来很多科幻或敌托邦影片中,都能找到《大都会》影响的痕迹。(16)
敌托邦影片的未来城市想象往往以渗透到日常生活各个角落的高科技公司取代了独裁政体对普通民众实施监控。技术的发展不再象征着社会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富足,而意味着人性的泯灭和私人空间的消失。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1982年混合了科幻与黑色电影类型的敌托邦名作《银翼杀手》(Blade Runner)为2019年的洛杉矶勾画了一幅阴郁的城市图。彼时的天使之城,已是泰里尔公司(Tyrell Corporation)掌控的后现代荒原。高耸的建筑物冒着莫名的黑烟和火球,阴雨不间断地飘落在白昼等同于黑夜的街道上(洛杉矶向来以阳光普照四季著称)。这是一座缺乏生命的城市,绿色植物早已被污黑的环境吞噬,复制的生物踟蹰于肮脏的角落,空荡的街头只有偶或一见的鬼魂般的警车;这也是一座仍然烙印着阶级和种族差异的城市,有钱人早已逃离到地球之外,天使之城随处可见东亚移民和文化的残迹,巨大的广告墙不间断地闪烁着艺伎女郎的诱惑之唇。如果说《大都会》的几何形结构象征着未来城市的森严秩序的话,那么《银翼杀手》的洛杉矶则是后现代混乱而密抑得透不过气来的非理性拼图。新与旧、白昼与黑夜、繁荣与凋零、实在与仿像、人类与机器人杂陈在漫无边界、缺乏中心的城市,令历史和意义不再可能。 《银翼杀手》所建构的天使之城,既映射了1980年代美国人对全球化、移民爆炸以及异国文化蚕食“美国生活方式”的焦虑,又在哲学意义上对启蒙运动以来根植于人们头脑的进步、发展、理性等观念提出了质疑。
仿像对实在的改写以及技术反制人类的主题同样体现在沃卓斯基兄弟(Wachowski Brothers)的《黑客帝国》 (The Matrix,1999年)中。影片所构建的敌托邦,是人类逐渐被自己所完善的技术即人工智能(AI)控制的世界。人与智能人、控制与反控制之间的争斗贯穿“帝国”的始终。不过,令《黑客帝国》更耐人寻味的也许在于沃氏兄弟对实在(reality)的哲学思考。影片中,智能人谋划了一套终极意义的阴谋理论,即实在本身不过是都市社会的群体梦幻建构。为了使人类臣服于控制、并使其成为动力源,智能人精心设计了一个供人类栖居的虚拟实在,一个完美无缺的生命仿像。横陈在一排排人工子宫中,沉睡其中的人类丝毫未觉察自己早已演变成数亿只为智能人提供能量的电池:而助佑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正是被称为“母体” (matrix)的超级计算机。这是一个具有终极意义的敌托邦,因为置身“母体”的每一个人都把仿像当成了实在,把沉睡体味为清醒,也把过往误辨为此在。就此意义说, 《黑客帝国》的敌托邦想象,又是对当代社会特别是城市和技术发展的警训;它昭示出被媒介化了的城市的非历史化倾向,并迫使我们思考技术进步背后的伦理意义。
根据英国小说家P.D.詹姆士(P.D.James)1992年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人类之子》(2006年,Children of Men)更是把关于未来的阴郁想象推到了极致:2027年的伦敦,人类已丧失了繁育后代的功能,文明赖以绵延的载体面临濒绝的危机。尽管影片并未明示群体失育的缘由,但直接与当代社会问题构成明喻关系的恐怖主义、环境污染、暴力迫害以及反移民主义等似乎暗示了人类正走向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路。影片一开始,伦敦街头小咖啡馆里的电视新闻仿佛判决了文明的死刑:全球最年幼的成员、十八岁仍被称为孩童的迪亚哥(Baby Diego)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因拒绝为自传签名而遇刺身亡,这也意味着人类在地球上存活的时间又缩短了。不过,人类似乎并没有因为末日将临(在只有死亡没有出生的状态下,人类至多还有不到一百年的苟延残喘机会)而停止因种族、国家和意识形态不同所导致的自相残虐。由于尚存最低限度运作的政府,英国遂成了全球难民蜂拥而至的所在。在反非法移民的浪潮中,英国迅速蜕变为军事化的警察国家,军警们在戒备森严的城市里搜捕漏网的非法移民及其同情者,并将他们关押在与奥斯维辛毫无二致的集中营。尽管黑人孕妇的出现和生产似乎允诺了某种希望的存在,但监狱般分割的街道、沉郁压顶的黑云、抵抗组织与军警之间的巷战以及影片结尾大雾弥漫的河面都大大强化了原已被阴霾笼罩的城市的敌托邦色彩。
实际上,敌托邦想象并不仅仅局限于西方语境,在日本电影、特别是日本文化跨境传播的主要形式即动画片中,我们也不断能经验到敌托邦的东方品格。当迪斯尼世界仍然被童话、仙女、狮熊、玩具、神童所占据的时候,日本动画电影已经进入了叙述更加繁复、主题更富玄思意味、人物更具跨文化特质、空间与背景设计更形未来风格的成人世界。在《日本动画:从〈Akira〉到〈幽灵公主〉》一书中,美国学者苏珊·奈皮尔(Susan J.Napier)总结认为,日本动画所呈现的三种形态,即启示录形态(apocalyptic)、节日狂欢形态(festival)和挽歌形态(elegiac),均涉及了当代世界共同面临的诸多问题,包括技术与人类社会、历史与记忆以及敌托邦式(dystopian)的未来想象等。正是通过对这些全球性问题的思考,使日本动画不仅超越了迪斯尼产品所构建的童稚世界,而且超越了民族国家疆界的限域,在“全球-本土”律动作用下的跨文化“动画空间”(animated space)混生出一种“无国家”(stateless)的文化:
正如差不多每一个非日本观众马上会注意到的,日本动画中的人物常常不具有日本人的特征,他们构成了或许可以被称为去文化特性的动画风格。与其说日本动画必然突显了日本的文化身份,倒不如说其叙述至少构成了对日本身份特性的诘难,这一点甚至在其含有强烈的文化特性时亦是如此。……
与一般真人饰演的影片通常必须在预先存在的语境中表现业已存在的客体、本质上更具表述性的空间不同,动画空间(animated space)具有不受语境限制的潜质,它可以完全出自动画创作者或艺术家的头脑想象。因此,动画乃是构建跨国家、无国家文化的最佳力量。(17)
日本动画关于未来世界的想象可以从《Akira》 (1988年)和《攻壳机动队》 (Ghost in the Shell,1995年)中窥见一斑。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核子打击的国度,日本的影像敌托邦常常摆脱不了1945年那场人间灾难的阴影。《Akira》开始时定义时空的“2019年第三次世界大战后的新东京”字幕以及缓缓笼罩摩天楼群的黑色蘑菇云、大爆炸后残留的黑色坑洞,都直接唤起人们关于长崎与广岛的灰暗记忆伏层。但影片很快超越了地理的限域,转而通过对都市(东京在影片中不过是一个符号)的数度毁灭加入到了后现代关于敌托邦世界的全球想象中。熟稔电影史的观众都会马上体味到, 《Akira》的动画空间无论是在构图还是在氛围营造、精神气质上都与前面所讨论的《银翼杀手》一脉相承。而二者又与敌托邦原典《大都会》发生传承关系。《攻壳机动队》的“动画空间”更超越了地理和国家的边界,在现实与未来的混杂中创造了一个由环环相联的网络所支配、半机械人(cyborg)与普通人共存的未来世界。影片混杂了在东方佛学、日本神道、西方基督教等影响下生发的关于技术与人类文明、性别和性别僭越、灵魂与身体、起源与生存的跨文化思考。与此相应,机械人草稚索子(Kusanagi)也呈现了性别、人种和文化身份的混杂。在抒情而徐缓的节奏中,草稚索子颇具哲学意味的玄想和独白突显了人类试图摆脱自身局限、但却永远无法获得终极自由的亘古困境。或许也正因为《攻壳机动队》对技术文明和人类未来等普世议题的关怀,才使影片超越了地域和类型的限制,得以被不同文化、年龄和国家的人们所激赏,成为日本动画跨国影迷社群中的经典,并因《黑客帝国》系列对其的传承而演变为跨文化、跨边界影像流动与消费的例范。
中国文化与电影中的未来想象
尽管中国文化传统中曾出现过《山海经》、《搜神记》、《封神演义》、《西游记》和《聊斋志异》这样的颇富奇幻想象色彩的作品,但先秦以来奠定的知识传统却并不鼓励奇思异想。孔子的现世关怀和远避怪力乱神的态度当然是这一传统的中坚,就是他对历史的看法也凸现了对未来想象的敌意。在孔子看来,他周游列国所宣扬的理念不过是恢复西周以降日益崩坏的道统。也就是说,孔子的历史观是后视的,一切问题的答案均可以从完美无瑕的西周礼乐中寻得。虽然道家哲学、特别是庄子汪洋恣肆的想象为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知识传统填补了亮色,但与儒学相似,道家哲学也把理想寄托在远古道人合一的寡民小国,越是近代,道与人之间的分裂越无法弥合,更遑论未来。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桃花源记》也许是古中国传统中少见的乌托邦之作,它脱离现世时空的想象拓展了文学表述的视阈。不过,除篇幅短小、没有空间展开想象外,甚或由于道家归隐山林思想的影响,《桃花源记》的乌托邦建构更仰赖于远古而非未来。
中国文化中的未来想象似乎直到晚清民初时期才得到了空前的释放。一方面,这与西风东渐、西洋器物涌入以及国人眼界渐宽相关;另一方面,这种释放亦未尝不可以看成是儒学式微、传统基石动摇的佐证。晚清国势的颓萎促使一批传统儒士重新思考中国的前途,以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认为小说是开启民智、传播政治理想的最好载体,于是“政治小说”应运而生。梁氏发表在《新小说》创刊号上的《新中国未来记》开回即描述了2062年国运昌盛、中国雄霸世界的美好景观,接着叙述推回到六十年前的2002年,彼时改良和革命两派的知识分子代表黄克强与李去病正为中国未来前途激烈争论。(18) 尽管《新中国未来记》混合了小说、历史和政论体写作,人物和情节均显苍白,但梁氏关于中国的未来想象却或多或少启发了清末大量“未来主义”和科幻体小说的出版(包括译介,如鲁迅翻译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和《造人术》等)。翻译过日本科幻小说《电术奇谈》的清末小说家吴趼人通过对《红楼梦》的续写,展示了他对中国未来的独特想象。《新石头记》让贾宝玉在经历了几世轮回后重返人间,不仅游历了洋场上海,而且无意间闯入了一个充满飞车、潜艇等新发明的未来世界。与《新中国未来记》的感时忧国精神相通,吴趼人借宝玉之眼所展露的未来,也映射着张扬中华文明的国家情怀:不仅种种新器物新发明源自中国传统,就是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乃至人种进化等方面也以教化天下的不二法门即中华文明为佳。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扬弃也体现在康有为密不示人的未来构想之作《大同书》里。尽管始作于1902年康避居印度期间,但全书直到1935年、也就是康死后八年才完整出版,其中的波折起伏或许与康氏不断修正自己的未来理想有关。戊戌变法失败后,康周游欧美各国,对西方选举制度、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社会家庭关系颇多微词,体现在《大同书》关于未来世界的想象中,则表露为对国家、军队、阶级、种族、家庭、婚姻和私有财产的全盘否定。在“大同”的未来世界,不仅只存在一个为全人类谋福利的公政府,社会上人人平等,科技和生产力高度发达,而且婚配也实现了契约化,以两年为一周期,双方满意的可以继续续约,不满意的则自动中止婚姻关系。
就严格意义而言,晚清以来中国文学和思想中勃生的未来想象并未烙印在中国电影中。如果说电影作为一种叙事形式直至1920年代中后期方在本土臻于成熟、因此希望彼时的中国电影大胆表现未来不免是种苛求的话,那么,1930年代后中国电影的左翼转向除了为多数影片的结局附着上对未来的朦胧而抽象的憧憬外,集中把镜头聚焦在了当下的民族、阶级和城乡矛盾上,体现了很强的现世批判精神。(19)
1978年后,也就是习惯所称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时期,相对宽松和自由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允诺了未来想象之门的开启。不过,巡礼这一时期生产的中国电影,我们仍然很难找到一部经典意义上的想象未来的作品。倒是与未来想象有亲缘关系的科幻电影逐渐浮出表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电影类型贫乏的缺憾。1980年,被很多人称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科幻片”的《珊瑚岛上的死光》 (张鸿眉导演)在上海电影制片厂诞生。尽管叙述落脚在当下,但片头从国外影像资料中剪辑进来的高速公路网和繁忙车流的鸟瞰画面,再加上影片中出现的海底工厂、海底长廊、水下电梯、空间放电以及那束致命的红色激光束等,还是给影片增添了某种异时异地的未来色彩。《珊瑚岛上的死光》之后,中国科幻电影、或更准确地说是“准”科幻电影或在梦境上做文章(《异想天开》,珠江电影制片厂1986年出品)、或依附于儿童电影门类(《霹雳贝贝》,北京电影制片厂1988年出品; 《大气层消失》,儿童电影制片厂1990年出品;《魔表》,儿童电影制片厂1990年出品)、或演变成公安智斗恶徒的外包装(《隐身博士》,西安电影制片厂1992年出品;《再生勇士》,上海电影制片厂1995年出品),在科幻意义上基本没有超越《珊瑚岛上的死光》所成就的水平。
中国电影未来想象的贫弱当然与传统文化中的现世精神和现代文化中的现实主义崇拜有关,更由于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和矛盾使然,但五四以降逐渐形成传统的唯进步论以及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唯科学主义和进步发展主题日益垄断中国人关于未来的思考等,也或许是影像未来、特别是影像敌托邦缺席的重要缘由。五四知识分子发起的中国式启蒙运动,一方面烙印了民族主义的痕迹,是晚清富国强兵宏愿在思想和观念上的深化,另一方面也承继了西方启蒙思想对传统的否定和对社会进步和人类理性的绝对信仰,认为社会总是按照进步的路径、通过人类理性对世界的认识和掌控向更好更高的阶段发展,最后达致完美的境界,每一个更新、更将来的社会一定也是更好的社会。文革后国门的重新开启,让中国人又一次经历了晚清似的挫败感,认识到自身物质财富的匮乏和科技水平的落后。于是,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遂成为三十年来的主导理念和支配性话语,官方和媒体合谋制造了一个又一个不容置疑的未来之梦:小康梦,私车梦,房产梦,老板梦,股东梦,富人梦,国际大都市梦,国际金融中心梦,等等。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梦”的合理与否,而在于它们背后时时闪现的唯科学主义和对进步发展的迷思般崇拜,即认为自然科学和技术是阐释生活的唯一权威;文明一直在规律性地进步,而且永远会因科技的发展而不断进步乃至臻于完美;未来一片光明,而且会越来越光明。正是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中国文化、中国电影中的未来想象或是充满幼稚的乐观,或是依附于强势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话语,或是被历史、古装和武打癖荡涤一空。
科学史学家江晓原在为敌托邦小说《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所作的序言中,曾注意到这样一种反讽现象:“西方人如今在大部分领域还处于强势”,却对未来充满忧虑和敌托邦恐惧,而“积弱百年”的中国仍然属发展中国家。但文化中所呈现的未来景观却被单一的乐观主义所笼罩。(20) 这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逻辑在新语境下的重演,还是映射了观念与思维上的某种错位乃至垄断?在序言的末尾,江认为,“随着中国的富强”,中国的未来想象也会“逐渐告别盲目的乐观主义”,而且“这样的作品已经开始在中国出现了”。(21) 也许,这里所表达的只是序言作者的将来时愿望而非完成时的现实。
2008年10月改定于上海
注释:
① 新中华杂志社《上海的将来》1页;中华书局1934年出版。
② 《上海的将来》丁默邨文;同上38页。
③ 《上海的将来》谢承平文;同上44页。
④ 《上海的将来》樊仲云文;同上61页。
⑤ 《上海的将来》丁默邨文;同上39页。
⑥ 《上海的将来》查士骥文;同上42页。
⑦ 《上海的将来》王造时文;同上33页。
⑧ 《上海的将来》丁默邨文;同上39页。
⑨ 《上海的将来》刘梦飞文;同上5页。
⑩ 《上海的将来》曾觉之文;同上77-8页。
(11) 《上海的将来》丁绍恒文;同上45页。
(12) 根据《牛津英语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说法,“敌托邦”一词的使用首先出现在1868年约翰·斯图亚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等在英国国会的一次发言中。
(13) “敌托邦”一词译自英文“dystopia”,它的反面是“乌托邦”(utopia)。中译之所以不采用“异托邦”或“反乌托邦”,是因为英文中也有“heterotopia”和“anti- utopia”的提法,前者可译为异托邦,指既非乌托邦亦非敌托邦的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所在,后者则更倾向于昭示乌托邦的谬误。
(14) 华氏451度被作者认为是书籍会自动燃烧的温度,因此小说被命名为《华氏451》。1966年,法国新浪潮导演特吕弗将其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
(15) 美国洛杉矶、印度孟买、法国巴黎乃至中国的上海都是这方面的显例。引文见马克·席尔(Mark Shiel)《电影与城市:历史与理论》(Cinema and the City in History and Theory);马克·席尔等编《电影与城市:全球语境中的电影和都市社会》(Cinema and the City:Film and Urban Societies in a Global Context)第1页;英国Blackwell出版社2001年版。
(16)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星球大战》中的C-3PO原型出自机器人玛丽亚,《银翼杀手》(Blade Runner)的城市景观基本拷贝自《大都会》等。
(17) 苏珊·奈皮尔《日本动画:从〈Akira〉到〈幽灵公主〉》(Anime:From Akira to Princess Mononoke,Experiencing Contemporary Japanese Animation)24页;美国Palgrave出版社2001年版。
(18) 《新小说》由梁启超1902年11月创刊于日本横滨,第二年即改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发行。关于《新小说》月刊和“政治小说”的详细讨论,参见邱明正主编《上海文学通史》(上册)359-37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9) 关于左翼电影叙事政治的讨论,参见孙绍谊《叙述的政治:左翼电影与好莱坞的上海想象》,载《当代电影》2005年第6期。
(20) 江晓原《未来的天空:有没有阳光?》(代译序);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著《羚羊与秧鸡》(韦清琦、袁霞译)第8页,译林出版社2004年出版。
(21) 同上。
